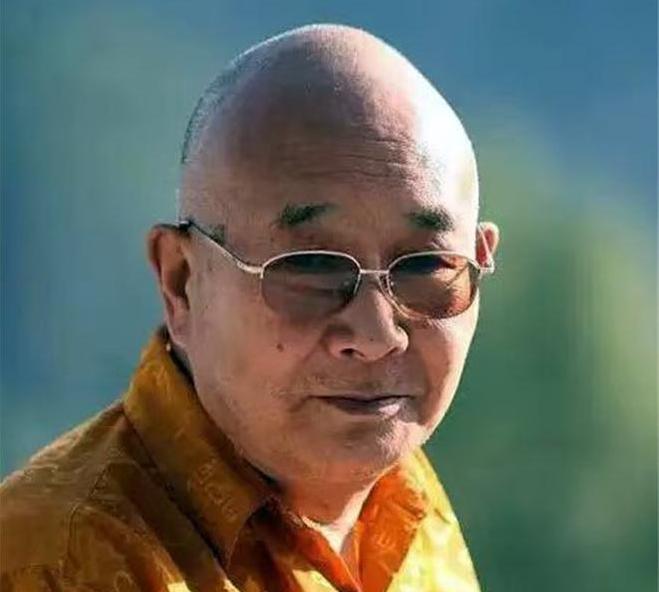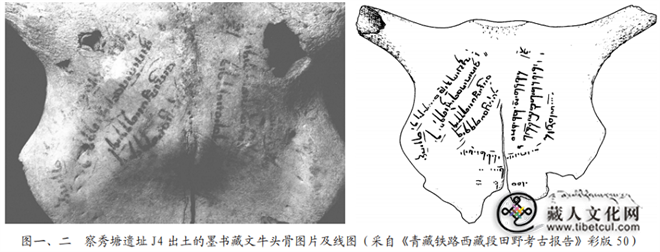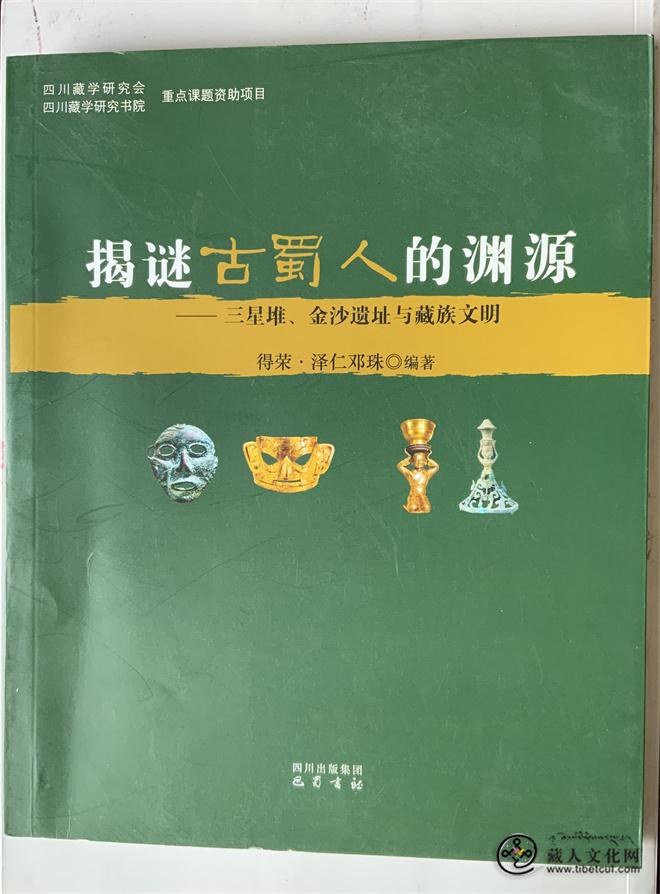摄影:觉果
摄影:觉果
摘要:文章以武威佛教为研究对象,系统梳理其自汉代以来的发展历程,探讨其在佛教中国化进程中的历史地位与作用。武威作为丝绸之路重镇,自佛教东传以来,逐步成为汉传与藏传佛教交汇融合的重要节点,尤其在魏晋南北朝、隋唐及宋元时期,通过译经、建寺、石窟开凿等活动,推动了佛教与中原儒道文化、多民族文化的深度融合。明清至民国时期,武威佛教虽历经波折,但仍在民族交融与边疆治理中发挥积极作用。新中国成立后,武威佛教在党和国家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引导下,逐步实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展现出佛教中国化的当代路径。武威佛教的发展不仅是宗教本土化、时代化开拓和实践的典范,更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重要文化纽带。
关键词:武威;佛教中国化;开拓;实践
武威位于甘肃省中部、河西走廊东端,处于亚欧大陆桥和西陇海兰新线经济带核心位置,自古是多民族争夺、交流、交融之地,羌、月氏、匈奴、汉、鲜卑、吐蕃、西夏、蒙古等诸多民族及政权曾经长期在此,或驻牧耕田或设郡拓疆或移民戍边或军事占领或政权统治……一簇簇历史巨浪,一波波风云变幻,汇聚成一部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壮阔史诗。武威扼守中原通往西域的咽喉,张骞通西域后,商队、使节与僧侣在此往来交汇。特别是汉辟“河西四郡”于元狩二年(前121年)设立武威郡后,武威正式纳入中原王朝版图,渐成为丝绸之路商贸、军事与文化枢纽,对中西文化交流和经济贸易产生了深远影响。丝绸之路是经贸之路,也是文化交流和精神信仰之路。早期佛教通过丝绸之路由西域向中国内地传播交流中,武威以其得天独厚的地理和人文优势成为佛教从印度经西域传入中原的重要“中转站”。早在公元前3世纪,印度阿育王分舍利建塔时,凉州就建有供奉佛舍利的姑洗塔。自东汉始,经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武威一直居于中国北方佛教发展中心地位。一度中外名僧汇聚,西行求法、佛经翻译、寺窟建造、弘法立宗等,皆立中国佛教史之丰碑,在佛教中国化进程中发挥了重大历史推动作用,遗留下丰厚的佛教文化遗产。而自吐蕃占据凉州到西夏、蒙古统治及之后的千年历史变迁中,藏传佛教也在武威产生过重要影响,特别是公元1247年西藏宗教领袖萨迦班智达与蒙古汗国皇子阔端在凉州举行的历史性会晤,使武威成为西藏纳入中央政府有效行政管辖的重要历史见证地……一桩桩与佛教有关、又牵动中华民族团结统一的历史事件及儒释道、多民族在这里相遇相融相合的历史见证,使早期佛教传播成为武威厚重历史文化中的辉煌篇章。
一、武威(凉州)佛教:书写了古丝绸之路上人类思想文化和多民族交流发展的史诗,开创了早期佛教中国化的辉煌时代
佛教创立于公元前6至5世纪的古印度,开始主要流行于恒河中上游一带地方,公元前3世纪孔雀王朝阿育王统治时代,佛教已经超出恒河流域,向印度各地以及周围国家传播。向南传到斯里兰卡和东南亚国家;向北传入大夏、安息以及大月氏,并越过葱岭(新疆西南部帕米尔高原的古称)传入中国西北地区,再传入内地。据唐代律宗大师释道宣编《广宏明集》和西夏所立《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等记载:佛祖涅槃后,阿育王在全世界造八万四千宝塔安置佛舍利。姑臧(今凉州)姑洗塔即其中之一。如果说佛教传入中国的第一站为受印度、波斯文化影响较大的高昌、龟兹、于阗等西域佛国,那么第二站便是佛教中国化转型中具有开创性和先河地位的武威。西域传来的佛教在此同中原儒道文化和北方诸少数民族文化交汇融合,使外来佛教在武威的传播已经具有了鲜明的本土化特征,体现在佛经翻译、寺窟建造及壁画造像等方方面面,折射出对外域文明传播过程中的重要整合过滤作用,并由此辐射到中原各地,使得武威成为早期佛教传播交流中的中转站,奠定了佛教中国化进程中的历史地位。
(一)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武威中国北方佛经翻译中心、“中国石窟鼻祖”及佛教中国化的开拓地
两汉时期(前206—220年)是佛教初传时期,据记载,早在西汉武帝时期(公元前140年—公元前88年),佛教便从西域经河西走廊传入凉州,比中原地区早约百年。武威雷台汉墓出土铜车马仪仗中的莲花纹饰,显示东汉晚期佛教符号已渗入丧葬文化。魏晋南北朝时期(220—589年)是中国历史上政权更迭频繁、民族融合加速、思想文化多元发展的重要时期,也是佛教在中国发展的全盛时期。西晋末年,藩王混战、胡族侵扰、社会动荡,西晋灭亡之后形成东晋十六国的混乱局面,而此时在前凉刺史张轨治理下,凉州成为西北唯一安宁之地,因此,《永嘉长安谣》云“秦川中,血没腕,惟有凉州倚柱观”。在西晋永嘉至隋统一的282年里,甘肃境内先后有东晋十六国和南北朝时期的多个割据政权,其中包括甘肃省河西走廊地区先后出现的五个以“凉”为国号的政权,即:汉族张氏建立的前凉(301—376年),氐族吕氏建立的后凉(386—401年),鲜卑族秃发氏建立的南凉(397—414年),汉族李氏建立的西凉(400—421年),匈奴族卢水胡沮渠氏建立的北凉(397—439年),史称“五凉”。这些政权大都以推崇佛教来维护巩固其统治。尤其在以凉州为中心的“四凉政权”(前凉、后凉、南凉、北凉)推动下,佛教在整个河西地区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范文澜《中国通史》言“:凉州自前凉以来是战争最少的地方……吕光通西域后,西方的佛教和文化东流,先在比较安定的凉州停留,再由凉州流向内地,因之凉州在十六国时期是中国北部的重要文化区,对北魏的文化也起着重要的作用”。
前凉政权世踞凉州,自张轨永宁元年至张天锡咸安六年(301—376)历76年,皆重视佛教事业。《魏书·释老志》记载“:凉州自张轨后,敬信佛教。敦煌地接西域,道俗交得其旧式,村坞相属,多有寺塔。”此时佛教在河西已广泛传播,突出表现为敦煌莫高窟的开凿和前凉官方主持的凉州佛经翻译活动。《开元释教录・总录》卷四记述了前凉末期张天锡在位时的凉州佛经翻译情况“:优婆塞支施仑,月支人,博综众经,来游凉土,张公见而重之,请令翻译。以咸安三年癸酉(373年),以凉州内正厅后湛露轩下,出须赖经四部。龟兹王世子帛延传语,常侍西海赵潇、会水令马亦、内侍来恭政三人笔受,沙门释慧常、释进行同在会证。”是说一位名叫支施仑的月支国优婆塞(在家居士),精通各类佛典。游历至凉州时,刺史张天锡对他十分赏识,特邀他主持佛经翻译。公元373年(咸安三年癸酉年),在凉州刺史府内正厅后方的湛露轩中,支施仑主持翻译出《须赖经》《首楞严》《金光首》《如幻三昧经》四部经典。翻译中,由龟兹王世子帛延担任口译转述,西海郡常侍赵潇、会水县令马亦以及内侍来恭政三人共同执笔记录整理,凉州僧人释慧常和释进行共同参与,对译文进行核证。
据东晋高僧释道安(312—385)著《渐备经序》等记载:西晋著名高僧佛经翻译家竺法护(229—306),虽早期在敦煌,后期在长安翻译佛经,晚年也曾在凉州活动。后凉州僧人释慧常将“敦煌菩萨”竺法护所译于西晋末年、但在数十年中未能“流宣”、因而“遂逸”在凉州的《渐备经》以及凉州新译之《首楞严》《须赖》等诸经,一并通过凉州“互市人”送至长安僧人安法华,再通过安法华送襄阳释道安。并言当时“中原经典固有来自凉土者。”《凉土异经录》是释道安对当时译于凉州、译者缺失、无法考定的汉文佛典所做的编目,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较为全面的关于“凉土异经”的目录,其中所记凉州译经达五十九部、七十九卷,可见凉州译经历史之早、数量之多。据载,张天锡因宫中多次出现“祥云萦绕、佛光闪烁”的灵瑞现象而改宫建寺,于升平七年(363年)建成宏藏寺(唐武则天时改为大云寺)。该寺花楼院建有一座七层木塔,高一百八十尺,每层周围有二十八间房,西侧有四户八窗,面列四户八窗,一一相似。宏藏寺“屋巍巍以崇立,殿赫赫以宏敞”,成为河西佛教建筑的重要象征,亦显前凉佛教盛况。
后凉时期(386—403),后凉政权的建立者吕光破龟兹携鸠摩罗什至武威,并始建罗什寺。鸠摩罗什驻锡凉州虽17年之久(385—401年),但因吕光本人并非敬信佛教者,所以没有支持佛经翻译。但因罗什大师佛教造诣高深,被称为“道流西域,名被东国”的贤者和“国之大宝”,声名远扬。他到凉州后,西域、中原等地的高僧大德及大量信徒慕名而来,为凉州佛教传播和发展聚集了大批人才。特别是罗什在凉州讲学,培养弟子,吸引僧肇等中原名僧西行凉州求法,形成跨区域的佛学研究和交流网络,奠定了凉州佛教传播和佛学中心的基础。同时,罗什在凉州期间潜心学习汉语,深悟汉文化精髓,为之后在长安的译经事业打下了坚实基础。罗什在长安译经三百余卷,以其“文质兼备”的翻译理念,开创了以优美的东方语言诠释佛法真谛的新译风格,深化了佛教与中国本土文化的完美融合,并丰富发展了汉语词汇,这也得益于他在凉州17年的深入研学。因此唐代官修史书《晋书・载记》说:“今之新经,皆罗什所译”,充分肯定了鸠摩罗什及其译经活动的重大历史贡献,这不仅是对历史事实的陈述,更是一个新的时代文化标志的象征。鸠摩罗什的新译佛经,使得佛教在中国的发展获得了更加精确、丰富和易于传播的经典依据,深刻影响了此后中国佛教的走向乃至整个东亚文化圈。413年鸠摩罗什在长安圆寂,据说他生前承诺,若所译之经无谬,火化时舌不焦烂。后依教焚尸果然“薪灭形碎,唯舌不灰”。遵其遗嘱,在武威鸠摩罗什寺内专建大师舌舍利塔供奉。因此,距今1600多年的武威罗什寺(塔)是佛教东传的重要地理标志。
佛教在凉州兴盛之时,西行取经活动也在此启程。最早西行求法者就是凉州名僧竺佛念,他去西域后,于秦弘始十五年(413年),同罽宾国沙门佛陀耶舍译出《长阿含经》22卷送回凉州。竺佛念是鸠摩罗什入关前北方佛教译经的核心人物,他主持或参与翻译经典总量超200卷,被后人尊为“译人之宗”,推动了早期佛教译经事业及中原戒律研究的开始。东晋隆安元年(397年),凉州僧人智严、宝云同往西域,在乌夷国(又名焉耆国)分手。智严抵达罽宾国入摩天陀罗精舍学三年禅法,也寻得一些国内尚无的经典,并邀请罽宾名僧佛驮跋陀罗来中国传法。回国后,曾去山东、建康(南京),又带领弟子多人去天竺,78岁去世于罽宾。宝云在西行天竺途中学习梵语、胡文,从天竺返回后与智严共同翻译了《普曜经》《无量寿经》《佛本行经》等经。智严、宝云西行途中,还曾与同为西行求法的法显大师相遇同行。后秦弘始元年(399年),凉州智猛等15位僧人一同从长安出发,经凉州、张掖、玉门关,渡流沙,经鄯善、龟兹、于阗,越葱岭,过罽宾、奇沙、迦毗罗卫国,至华氏城,获得《大般泥洹经》《摩诃僧祇律》梵本,于宋景平二年(424年)返回,途中4人去世,9人行至地势险要、气候多变、冰天雪地的帕米尔高原而畏难折回,唯智猛、昙纂回到凉州,且在凉州译出汉文《大般泥洹经》20卷。同时期赴西域求法者还有北凉国主沮渠蒙逊的堂弟沮渠京声,他西渡流沙到于阗,进入瞿摩帝大寺,跟随高僧佛陀斯那学习佛法,后将所获《佛说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治禅病秘要经》等经典译为汉文。
公元397年,后凉建康太守段业被匈奴卢水胡首领沮渠男成等人推举为主,建立北凉,定都张掖。段业死后,沮渠蒙逊统治北凉,并于412年迁都姑臧(今武威凉州区),421年灭西凉而控制河西。自沮渠蒙逊,北凉将佛教奉为国教,尤以佛经翻译和石窟开凿推动凉州佛教有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成就斐然,因此,北凉佛教在中国佛教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沮渠蒙逊组织译经团队,邀请中天竺高僧昙无谶至姑臧,尊为国师,主持翻译《大般涅槃经》《金光明经》等百余卷重要佛经。《大毗婆沙经》梵本是凉州僧人道泰西游求得,沮渠牧犍时,邀请西域名僧浮陀跋摩及道泰主持,慧嵩、道朗等300多位僧人参与,在姑臧闲豫宫完成了这部百卷巨经的翻译工程。北凉统治者组织的这些规模宏大的译经活动中,尤以昙无谶翻译的《大般涅槃经》《金光明经》《菩萨戒本》等核心经典,奠定了大乘佛教传播的理论基础,彻底改变了中国佛教的思想格局,对后世天台宗、华严宗、禅宗等中国化佛教宗派提供了核心思想源泉,深刻影响了南北朝乃至隋唐佛教思想发展的轨迹。同时,玄高、昙曜等高僧在凉州修习禅观,推动了北方禅学发展。范文澜《中国通史》言:凉州是禅学最盛行的地方,魏文成帝兴佛后,先后任沙门统的师贤、昙曜,都是凉州禅师,作为北朝佛学主流的禅学,以及规模巨大的佛教艺术,都寻源于凉州。总之,北凉时的凉州聚集了大批西域和中原僧人,形成了“僧坊百余,僧尼数千”僧才济济的局面,成就了北方重要译学中心的盛世。著名佛学家汤用彤著《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记述“:北凉译人有道龚、法众、僧伽陀、昙无谶、沮渠京声、浮陀跋摩、智猛、道泰、法盛共九人。凉土僧人晋末之往西域者,有沮渠京声、道泰、宝云、法盛等。而法显、智严、法勇、支法领等均经凉州至西域,皆在沮渠氏王北凉之时……当日凉州传译之盛况,亦甚可惊也!”
石窟开凿是北凉推动佛教发展的又一盛举。约在公元412—439年间,沮渠蒙逊召集昙曜等凉州高僧和大批能工巧匠开凿了武威天梯山石窟,首创中心塔柱窟、覆斗顶等形制,并在技艺精湛、气势宏大、光彩夺目的石窟建筑、佛像塑造和彩绘壁画中,将西域犍陀罗艺术与中原艺术特色完美融合,创“凉州石窟模式”,开中国石窟艺术之源头,由此天梯山石窟被史学家称为“中国石窟之祖”,是佛教艺术本土化的杰出典范。439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率大军攻克姑臧灭北凉,终结了中国北方长达百余年的十六国分裂格局。为巩固其统治,拓跋焘将凉州3万余户迁徙至平城(今山西大同)。对此,《魏书·释老志》记载“:太延中,凉州平,徙其国人于京邑,沙门佛事皆俱东,象教弥增矣。”迁徙数万人中就有师贤、昙曜等著名高僧在内的大批凉州僧人及工匠,为北魏开凿云冈、龙门石窟创造了条件,随迁的还有大量佛教典籍。这一影响深远的凉州精英大迁徙,直接促成“沙门佛事皆俱东”的历史转折和北魏佛教鼎盛的局面。凉州高僧昙曜还主持了云冈石窟的开凿工程。通过凉州、长安等北方僧侣、典籍、造像等传入中原,促进了佛教与中国文化的大融合,佛教也逐渐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言:两晋时期(265—420年),中国佛教的传播中心有三处,一在凉州,一在长安,一在庐山。凉州是佛教沿“丝绸之路”进入中国的中转站。有许多重要佛经的翻译是出自凉州。西方僧人到中国内地,往往先到凉州熟悉汉语。且该地不像关中是四战之地,当时的凉州比较安定,有许多僧人文化人到此避乱,也促使该地形成文化重镇。自此一直到南北朝,佛教翻译如火如荼。所翻译的佛典在数量、质量和内容等诸多方面,都远远超过前朝。时姑臧、长安、建康、庐山、洛阳等地成为中国佛典翻译中心。因此,包括敦煌在内的整个河西走廊乃至更远的地区,受到凉州佛教文化的强烈影响,极大地促进了佛教与儒道文化及西北各少数民族文化的深度融合,进而全范围推动了佛教中国化进程。
(二)隋唐时期武威佛教盛况与融合了中国思想文化的宗派体系形成
隋唐时期(581—907年),以隋文帝结束自西晋末年以来近300年的分裂割据局面、实现政治统一为新纪元,迎来了中国历史上经济繁荣、文化灿烂、对外交往的黄金时代,对东亚乃至世界文明产生重大影响。隋唐时期也是中国佛教发展的黄金时代,在政治统一、经济文化繁荣的大背景下,佛教与中国本土文化进一步深度融合,逐步以理论的升华、组织制度的完善和中国特色宗派体系的形成,开创了佛教深度中国化发展的标志性阶段。而隋唐佛教之鼎盛正是以国家统一强盛为重要背景的。尤其盛唐的凉州是“七里十万家”的国际性繁华商贸都市,虽有北魏时凉州佛教之北迁,但仍凭借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深厚的历史积淀、隋唐帝国对丝路贸易的保障和对边疆的重视,以及佛教自身发展的惯性,成功地延续并巩固了其作为西北地区佛教中心的地位,在沟通东西方佛教文化交流、塑造中国佛教艺术风格、维系西北边疆佛教信仰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核心作用。隋大业五年(609)隋炀帝杨广西巡河西走廊时,亲临凉州番和瑞像寺(今永昌圣容寺),布施大量财物,并下旨扩建,御笔亲书改寺名为“感通寺”。天梯山石窟在隋代又有新建,唐代最盛,现存造像也以唐代最多最精。其中被定为国宝的一铺三身彩塑坐佛与胁侍菩萨,更是以其优美造型、精湛工艺和独特的“东西文化合璧”的文化特征,创唐代佛教造像艺术的巅峰,整个佛窟规模宏大,气势宏伟。正面中央的释迦如来造像,安然端坐,气度非凡,高约30米;左右两侧分别立迦叶、阿难、普贤、文殊、广目、多闻六尊造像,或威武或慈善或智慧或忠诚,各具神态,精妙逼真。建造这样的巨型大窟,反映出唐代凉州经济文化空前繁荣及佛教文化艺术的高超水准和雄浑气派。罗什寺等凉州名刹也在隋唐得到进一步扩建修缮。武则天时颁《大云经》于天下,并敕令全国各州建大云寺。时赐凉州《大云经》,并将前凉所建宏藏寺改名大云寺,成为皇家敕建寺院。据敦煌文书记载,此时凉州有“伽蓝三百余所”。唐贞观三年(629年),玄奘大师西行取经途经凉州,颇为其繁荣和佛教盛兴所震撼。《大唐西域记》中记载“凉州为河西都会,襟带西蕃、葱右诸国,商旅往来,无有停绝”。据《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载,玄奘在凉州“停月余日。道俗请开《涅槃》《摄论》及《般若经》。法师皆为开发”。开讲之日,盛况空前,听众中除当地各族信徒外,还有西域来的商人与僧众。据传,其间玄奘曾挂单暂住城东南的安国寺,后由大云寺住持慧威法师派弟子道整和惠琳护送西行。公元644年,玄奘取经回国又到凉州。此时他已得到唐太宗支持,进入凉州城时,官方举办了盛大迎接仪式。玄奘到大云寺看望众僧,并赠送了礼物。
隋唐时期,武威佛教文化已经与社会生活深度融合,民间造像和写经活动频繁,出现民间佛书远超“六经”的境况,敦煌出土文书中也有大量凉州民间《金刚经》等佛经抄本。宴乐“西凉乐”也融合佛教仪式音乐与龟兹乐舞,成为宫廷“九部乐”之一。佛教石窟壁画内容和风格愈体现出世俗化趋势。尤其民间佛教结社盛行,一些佛教寺院以举办大型法会活动等,吸引往来商贾、僧侣和当地信徒共聚,促成佛教更为广泛发展。唐代佛教最大成就是融合了中国思想文化的宗派体系的形成,建立了各具特色的理论体系和修行法门,全面实现了佛教中国化。时武威兴盛三论宗、华严宗、禅宗、净土宗、临济宗、密宗诸宗派,是武威佛教本土化、中国化深入发展的重要标志。
(三)五代十国宋及蒙元时期武威佛教传播发展的新趋势
五代十国(907—979年),是唐亡宋兴之间中国历史上的一段大分裂时期,武威先后为凉州吐蕃人建立的“六谷部”政权及回鹘、党项等民族交替控制,战乱频仍,但由于这些民族政权,皆推崇佛教,加之当地民众“世信佛教”和五凉时期奠定的寺窟塔林立的雄厚基础,佛教仍在动荡中保持了旺盛生命力“。六谷部”统治期间,在凉州也兴建了数座寺院,并有佛经翻译活动。晚唐大中二年(848),张议潮率归义军收复河西,汉传佛教有所恢复,凉州寺院如清应寺重新成为讲经中心。
五代末至北宋初期党项人崛起,1016年党项占领凉州,1036年攻取瓜、沙、甘三州,尽有河西各地。1038年党项首领李元昊在兴庆府(今宁夏银川)称帝,建国西夏。西夏政权与宋朝并存,时近200年之久。西夏统治时期,升凉州为西夏辅郡,地位仅次于首都兴庆府。《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西夏碑)记述了当时凉州城之繁荣:“武威当四冲地,车辙马迹,辐辏交会,日有千数。”西夏建国后,以佛教为国教,不断从吐蕃、北宋积极引进佛教,大力倡佛。西夏立国初期以发展中原佛教为主,中、后期则大力推行藏传佛教,促成了汉、藏、西夏文化交融、藏汉佛教融合发展的独特格局。据史书记载,太宗李德明“幼晓佛书”,其子李元昊亦“晓浮图学”,数任统治者皆带头信仰佛教,以政令推行佛教,规定每一季度第一个月的初一为“圣节”,百官和百姓届时都要烧香礼佛。因此,此时的武威不仅是政治、军事重镇,也是佛教传播的核心枢纽。据记载,西夏在武威进行了较大规模的修寺建塔活动,扩建维修了凉州护国寺(原大云寺)、圣容寺、崇圣寺、海藏寺等古寺,尤以西夏乾顺天祐民安四年(1093)重建凉州感应塔及护国寺最为盛名,动用了大量财力、物力和人力,建成后立碑赞庆,使护国寺成为西夏皇室最重要的宗教活动中心。还在天梯山石窟、亥母洞等处新开洞窟、建寺造像、增绘壁画。《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碑文载“:释教尤所崇奉,近自畿甸,远及荒要……佛宇遗址,无不必葺”,彰显了国家力量对佛教的全面扶持。天梯山石窟及造像壁画,亥母洞寺的西夏泥活字佛经、造像和塔形类“擦擦”、唐卡残片等珍贵文物,皆是佛教与武威当地民族文化深度融合的重要佐证。
西夏乾定三年(1226年)七月,蒙古军围攻西凉府,次年灭西夏。至此,凉州为蒙元政权统治,并成为其经略西藏的重要基地。南宋淳祐七年(1247年)初,镇守凉州的蒙古窝阔台汗之子阔端与西藏萨迦派第四任法王萨迦班智达在凉州白塔寺会晤,就西藏归顺蒙古问题达成协议,这是之后西藏归属元朝统治的重大历史事件,使武威成为西藏纳入中央有效行政管辖的历史见证地,藏传佛教萨迦派也由此向河西及蒙古地区广泛传播。而此时汉传佛教则在民间自发活动,与藏传佛教并行发展,但部分寺院改宗为萨迦派。如萨班在凉州城四方改扩建的“凉州四寺”(即东部幻化寺〈白塔寺〉、西部莲花寺、南部金塔寺、北部海藏寺)也反映了这种变化。且蒙元以后,佛教发展的主要趋势是寺塔建造兴盛,而石窟建造和佛经翻译逐渐减少。
(四)明清及民国时期武威汉传佛教发展的曲折境遇
明代,随着崇信佛教的诸少数民族统治势力退出、丝绸之路贸易及西域佛教逐渐衰落及统治者不再以国家政令发展宗教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河西地区的佛教不再有以往内外交流传播之盛况,而是以历史的惯性和影响力向民间深入扎根发展,武威佛教也呈现新的趋势,如在家居士增多,寺庙数量增加,蒙元时期所建藏传佛教寺院也大多改建为汉传。另外,一些历史悠久的大寺得到修缮重建。据史料记载,明时在凉州城乡,修复和新建佛道二教寺观庙宇有百余座。明洪武十六年(1383),在凉州坐禅的日本僧人志满募捐与本城副将鲁光祖重修大云寺。明宣德年间(1426—1435),重修了元末毁于兵火的凉州白塔寺,并赐名“庄严寺”。明正统十年(1445),明英宗皇帝下旨,修缮鸠摩罗什寺,并敕书颁赐给罗什寺《永乐北藏》一部,计358类、685函、3584卷。明成化年间(1465-1487年),太监张睿重修海藏寺,历时五年完工,敕赐“清化禅寺”。民勤圣容寺等诸多汉传佛教寺院也建于明代,但明代后期,注重扶持道教,汉传佛教寺院有所减少,而藏传佛教则主要分布于藏族部落聚居的今天祝一带。
清代基本沿袭明代汉地佛教政策。武威民间佛事活动兴盛,寺庙数量增多,僧尼过千。清乾隆十四年(1749)编修完成的《五凉考治六德集全志》(简称《五凉全志》)记载的武威主要寺庵有60处。[1]其中武威县(今凉州区)44处:即大云寺、清应寺、罗什寺、安国寺、洞儿寺、蒿家寺、西来寺、地藏寺、清佛寺、海潮寺、白衣寺、观音寺、弥陀寺、光明寺、东竺寺、百塔寺、大佛寺、上房寺、演教寺、庄严寺、弘化寺、土佛寺、杂木寺、下(大)水寺、百林寺、金塔寺、菩提寺、接引寺、善应寺、洪济寺、善法寺、石城寺、龙宫寺、龙眼寺、海藏寺、圆通寺、永寿寺、亥母洞(寺)及藏经阁、达摩庵、文殊庵、道德庵、净土庵、慈悲庵等。古浪县10处:即龙泉寺、清凉寺、转轮寺、永寿寺、白衣寺、寿国寺、大佛寺及观音阁、菩萨殿、普陀庵。镇番县(今民勤县)6处:即准提寺、南塔寺、圣容寺、宝塔寺、地藏寺及镇国塔。清代依然重视古寺修复。康熙年间重修了白塔寺塔院和海藏寺。雍正年间海藏寺修复后,寺院住持际善法师经八年跋涉,至北京请经,雍正帝赐海藏寺明版大藏经6820卷,且令川陕等地施银920两,际善法师以白马驮经归寺,供奉于灵钧台上的无量殿内,此殿遂改名藏经阁。清乾隆、光绪年间,海藏寺又两度重建,现存海藏寺大雄宝殿、三圣殿、山门、牌楼等皆属清代建筑。清代后期,战乱灾荒接连,民众苦不堪言,许多寺庙香火断绝。民国时,仍天灾人祸接连,许多寺庙遭到毁坏。尤以民国十六年(1927)大地震破坏最甚,凉州罗什寺、白塔寺、大云寺、清应寺、大佛寺、延寿寺、洪济寺等寺院佛殿大都震毁,古浪、民勤大多佛寺也毁于这次地震。因此,清末民初武威佛教受到较大冲击,寺院、僧人明显减少,佛教日渐衰败。如民国时今凉州区寺院已减少到20余处(还包括几处藏传佛教寺院),僧尼百余名。为振兴武威佛教,当时兰州法幢寺创建者心道法师曾来武威弘法,倡扬“法幢正宗”教义,闻法皈依和拜师剃度者甚众。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武威佛教界启建护国息灾法会,并成立中国佛教会甘肃武威分会,心道法师任理事长。同年,心道法师又到民勤枪杆岭山接引寺宣法,并更寺名为金刚岭山法幢寺,后升座为民勤圣容寺方丈,亦启建息灾护国法会,倡导成立民勤佛教会。虽然心道法师做了很多努力,但民国后期的混乱局面和艰难环境下,武威佛教复兴之愿终难实现。
作者简介:李才仁加,原甘肃省佛学院副院长、(全国)藏传佛教三级学衔教材编委会委员,曾受聘为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统一战线高端智库评审专家,甘肃省佛学院第一、二届经师评定委员会及第一届中级学衔评定委员会副主任。
原刊于《甘肃民族研究》2025年第4期,注释及引用略,原文版权归作者及原单位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