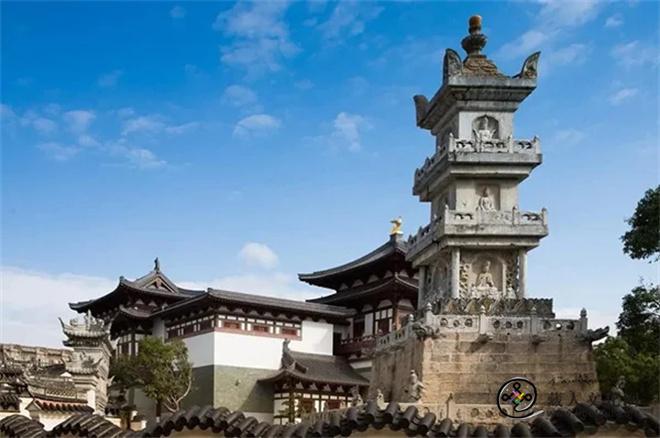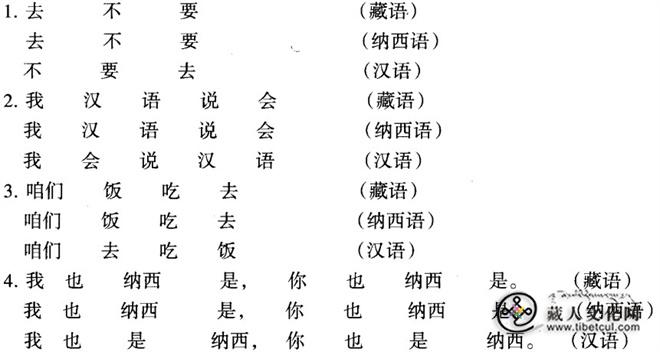摄影:觉果
摄影:觉果
果洛石经是近现代在青藏高原产生的具有浓厚地方特色的一种宗教文化工程。为此,果洛藏族人民不仅付出了艰苦劳动,而且倾注了许多闪光的智慧和高超的技艺。
至于果洛石经产生的主客观因素,已在另外文章中从宏观的角度作了较全面的分析和叙述,本文拟就微观的角度对果洛石经的创建过程作具体考述。
一、年代考证
从藏传佛教的整个历史过程来看,果洛石经产生的年代不算很早,最早的石经,迄今也只有一百年左右的历史。然而,果洛石经不同于藏族地区普遍形成的嘛呢石堆,它以镌刻藏文大藏经为主要对象,其规模极其宏大,创建过程又十分严肃认真。因此,果洛石经的历史长短,则不应成为衡量果洛石经的主要价值标准。遗憾的是,凡是记述有关果洛历史、文化、宗教等方面的文字资料中,对于果洛石经却没有详实的记述,这给后世研究者带来诸多不便。
通过实地考査和搜集到的有关资料,大致上还可考证出果洛石经产生或形成的年代.譬如,“1890年,査喇嘛桑俄丹增在此开始了《甘珠尔》石刻活动,……” ①这是始建于今果洛达日县境内的岗巴石经墙的记载,至于何时完成,则没有交待。只是说“《甘珠尔》石刻板竣工开光时,昂欠部落头人多德来到岗巴寺,捐献了马鸣金佛像一尊。其后华若多杰建立了转嘛呢轮房。1930年,达合勒布喇嘛贡却坚赞在《甘珠尔》经石(板)堆放处建起了石塔,并督促继续刻制《解脱经》、《佛光十地经》等。”②引言中虽然没有说明石刻《甘珠尔》何时竣工,但至1930年时岗巴石经墙中的《甘珠尔》石刻,不仅早已竣工,而且又开始继续镌刻其它经文的准备工作。估计岗巴石经墙中的大藏经《甘珠尔》部,最迟也在二十世纪初业已完成。单从大藏经《甘珠尔》部产生的时间而言,岗巴石经墙在果洛地区的石经墙中属于历史最悠久的一座石经墙。因为果洛地区的绝大多数石经墙产生的年代都晚于岗巴石经墙,如“1922年,达西喇嘛桑却多杰来到红科地区,提倡建立一个固定的寺院,在达日河谷的班玛曲池地方(达日萨纳沟ロ,现吉迈乡址附近)石刻《甘珠尔》佛经,并进行了讲经活动,……。” ③此乃位于今果洛达日县境内的达格沙那石经墙处始建石刻《甘珠尔》的具体年代。这比岗巴石经墙中的石刻《甘珠尔》至少也要晩二、三十年。
就果洛地区的每一座石经墙的整体形成而言,很难用十分具体精确的年月来界定,因为它是经过很长时期逐渐形成或完成的。也就是说,果洛地区的许多石经墙,一般是从镌刻小型的短篇经文开始,逐步发展到鼎盛阶段,即镌刻大型的长篇经文——石刻大藏经。根据《东吉寺志》(藏文手抄本),东吉寺始建于公元1837年,该寺第五代主持拉章·格果在东吉寺首创石经墙,但其规模很小。之后,东吉寺第六代主持乍加朱格·旦增排杰又继续扩建东吉石经墙。这二代主持正是果洛阿琼贡麻官人扎西东珠(公元1816-1872年)执政时期。后来东吉寺第三十一代寺主格拉·加羊尼玛(于公元1956年去世)对东吉石经墙进行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扩建。至此东吉石经墙的发展已达鼎盛时期。加羊尼玛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大成就者,他为东吉寺的发展,尤其对东吉石经墙的兴隆做出过重大贡献。因此,后人在东吉石经墙前筑有他的宝(法)座,供信徒腾仰膜拜。可见,东吉石经墙的整个形成过程,从公元十九世纪中叶算起至二十世纪中叶为止,整整一个世纪。鉴此,果洛地区的每一座石经墙的形成,似乎要经历一段较长的历史过程。
然而,果洛石经墙中也有集中财力人力在较短时期内完成或形成的。例如赛希石经墙和多勒石经墙就属于此类。赛希石经墙和多勒石经墙是由两位果洛本地活佛分别创建或完成的。两位活佛又是兄弟俩,兄长叫赛希朱格·加贝格勒扎巴,弟弟叫多勒朱格或多俄曲吉尼玛。人们为了纪念这两位创建果洛石经有功的巨匠,将他们各自创建的石经墙分别用他俩的名字命名为“赛希石经墙”和“多勒石经墙”。这两座石经墙,尤其“多勒石经墙”是目前果洛地区保存最完好、规模最宏大的一座石经墙,具有很高的学术研究价值。
由于迄今未获可依据的有关资料,“赛希石经墙”和“多勒石经墙”创建的确切年月日,无从知晓。眼前唯一的途径或方法只有通过创建石经墙的两位活佛的零星事迹来推测。有关资料对两位活佛的生卒年月也没有十分清楚的记载,但两位活佛属于近现代人物,对于他们的事迹,民间不少老人还能追忆或叙述片段。赛希和多勒两位活佛大约出生于十九世纪末,父亲叫雪拉•索南丹增,母亲系苏如麻部落,他们共有五个兄弟,老大为赛希活佛,次为多勒活佛,之后依次为珠古党桑、拉才加贡、拉玛格佐。其中后三位活佛分别在今甘孜藏族自治州境内的三座寺内长期任寺主或深造。
至于赛希和多勒两位活佛的生卒年月,有多种说法:一说赛希活佛的转世灵童,即第二世属马、现年63岁(指1992年),赛希活佛本人在45岁左右去世(根据果洛甘德县龙加寺诺桑和尚于1992年60岁时口述记录)。以此推算,赛希活佛于1884年出生,1929年去世;有说赛希活佛于1906年出生,1946年至1948年任东吉寺住持(根据《东吉寺志》手抄本);另一说赛希活佛于1941年去世(根据果洛州政协副主席更衆桑保先生口述记录)。
多勒活佛于1957年(有说1952年或1954年)去世,享年60岁(根据龙加寺阿柯卓贡于1992年50岁左右时口述记录)。据此可推算出多勒活佛是在1897年或1894年或1892年出生的。
由于果洛地区在解放前长期处于政治动荡、战火不断的特殊环境,没有给后人留下可依据的许多文字史料,除了重大事件外,其余许多历史人物或事迹全靠ロ头相传或凭借人们的记忆留存。当然.其中也可找到一些比较一致的看法,如赛希石经墙的创建稍稍早于多勒石经墙.而且创建二处石经墙时两位活佛都在30岁左右。基此赛希石经墙和多勒石经墙创建的年代可定在二十世纪初或最迟也不会超过三十年代。另外,当地的许多老人特别提到两位活佛相继去世时,各自创建的石经墙还没有完全竣工,是后人继承其事业并逐渐完成的.总之,就多数观点或资料分析,多勒石经墙和赛希石经墙始建于二十世纪初,而完成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或者五十年代。由此可知,赛希石经墙和多勒石经墙的创建过程仅用了三四十年。
以上只是笔者根据在实地考察中获得的珍贵ロ碑或文字资料,对赛希石经墙和多勒石经墙的创建年代所作的初步推断,有待今后进一步考证。
二、资基来源
由于果洛地区位于青藏高原,平均海拔在四千公尺以上,而且其居民绝大多数是牧民,没有固定的居住点,一年四季逐水草迁移。这种自然环境和文化习俗,以及当时的社会政治氛围,致使果洛地区没有产生更多的建筑寺院。然而,藏族人所共同具有的强烈的宗教信仰心理,没有令果洛藏族人就地罢休,而是另避蹊径,采取创建“石经墙”这样一种宗教信仰方式。而创建石经墙就象建筑一座寺院一般,首先需要筹措一大笔资金。例如,当赛希活佛在岗龙沟阳面的某修行洞静修时,有一天在附近小滩上出现一道令人喜悦的彩虹,他前往观赏显示彩虹的地段,正好此地有一块巨大的石板(今仍保存在赛希石经墙中),赛希活佛触景生情,便产生在该地镌刻石经的念头。之后,赛希活佛去向当地官人噶妥多科申请并买下这块地(其它石经墙没有买地盘的记载或传说),开始了创建赛希石经墙的浩大工程。在具体筹措资金的来源方面,主要有三个渠道:第一,信教群众的自愿布施或捐献;第二,高僧活佛或地方官人向属下群众摊派;第三,由创建者活佛自己将多年积蓄的财产全部贡献(这是一笔数目相当可观的资金)。在资金来源的种类方面,五花八门,诸如金银财宝,牲畜及其畜产品,等等。在整个创建石经的过程中,又呈现有力出力、有钱出钱的局面。
至于创建一座石经墙究竟需要筹措多少资金,现在没有任何可依据的记载,因而无从知晓。目前,唯一的线索只有说法不一的镌刻石经的具体价格。例如,有些石经墙是这样计算石刻工价的:在石板上镌刻出一页两面藏文经书,其报酬是壹银元,现在折合人民币为30-40元不等。如果拿实物来兑现,当时一匹马折合10银元,一头牛折合6银元,一只羊折合1银元。但折合的标准又随着各地区社会经济形势的变化或不同历史时期而出现小差异。果洛州甘德县龙加寺老和尚隆珠,过去曾在多勒刻经处当过“石官”(即组织或管理石匠的一个官街),时年69岁(指1992年)。他对过去石刻费用比较清楚,如镌刻一部《贤劫经》需要120两银子,雕刻一个《贤劫经》目录10两银子;镌刻一部《解脱经》19两银子;一部《金刚能断经》4两银子;一部《长寿经》2两银子;一部《普贤行愿》1两银子;一部《忏悔经》半两银子;雕刻“十万六字真言”一套(将六字真言重复雕刻一万遍,号称“十万六字真言”)40两银子。而目前(1992年)镌刻一部《贤劫经》需要3,500元人民币,再加雕刻其目录费50元人民币,共计3,550元人民币,个别地区可用1,100元人民币就能镌刻一部《贤劫经》。如果使用实物,一匹马可折合400元人民币,一头牛为200元人民币,一只羊为30元人民币(这是1980年至1991年之间的计价)。
根据以上提供的价格,以镌刻一部经书为3,000元人民币计算,镌刻一套大藏经(包括《甘珠尔》103部,《丹珠尔)234部,共337部),约需70万元人民币。值得说明的是,虽然绝大多数石经墙没有将整套大藏经镌刻完备(一般没有镌刻《丹珠尔》部),但是却把《甘珠尔》部,以及《贤劫经》等重要经典重复镌刻数遍,甚至更多,实际上每处石经墙的容量远远超出整套大藏经。
三、石料采择
果洛地区位于青藏高原的腹心地带,其地貌构造,提供了丰富的石料资源。在果洛地区创建“石经墙”,具有良好的客观条件。然而,果洛地区的石经墙不同于藏族地区普及面很广的“嘛呢石堆”,即不可随处创建。因为正规的石经墙在其创建过程中的许多规则或条件都与建筑寺院极其相似。例如,在选择石经墙地点时,也有一系列可遵循的规则,尤其要看其地形是否具有祥瑞标志,或呈现过福兆或遗留圣迹,等等。这就意味着石头或石板最多的地段不一定作为选址的标准,因而果洛地区的许多石经墙都建在距离石山较远的地带。诸如赛希石经墙、东吉石经墙、梅·沙那石经墙、达多却旦塘石经墙,都建在远离石山、环境秀美僻静的小平川。这样,给采择或运送石料带来许多困难。解放前在果洛地区没有一条马路,几乎所有的道路都是自然形成的羊肠小道。因此,耗牛这一青藏高原特有的家畜,便成为果洛地区运送石板的最佳运输工具,一头耗牛的载重量是50公斤至100公斤。每头耗牛按石板大小可驮运二块至五六块不等。
在石料采择以及加工等方面,果洛地区的石经墙略异于中国内地的石板佛经,就拿闻名世界的北京房山地区的“房山石经”来说,其石料都是就地取材,特别对石料的加工极为精致。对于房山石经的创建过程在唐初唐临著的《冥报记》中有这样的记述:“……凿岩为石室,既磨四壁,而以写经,又取方石,别更磨写,藏诸室内,每一室满,即以石塞门,用铁锢之……。”这与果洛石经墙的创建过程及其形制有着明显的差别,特别是房山石经的石板都经过精细的加工,其形制均为长方形,而且有比较统一的大小规格。比如房山石经山上有九个藏经板的岩洞,洞内共藏经板4190余块,其经板大都为长达2公尺以上,最长的有2.5公尺,宽为80至90公分间;在山下云居寺南塔前的大地穴内,共藏有10080余块经板,除极少数外,其余都是长75公分,宽35公分。果洛石经墙的石板则没有严格的规格标准,其形制可谓五花八门。但值得一说的是,果洛石经墙的石料主要为石灰岩和硅质岩,这类石料的最大特性是石面光滑而质地比较脆软,易于刻写各种文字,而且不用人力磨制等加工,全是从各处石山中开采挖掘出来的天然石块。其形状规格可谓无形不有,除个别大型石板外,一般都在一公尺见方以内,具体可见“果洛石经墙的分布及其规模”一文(载《西藏研究》1997年第1期)。
由于果洛石经墙采用的石料不用任何加工,在规格上也没有统一的标准,无论男女老少,人人均可采择或选用,只是运输成为最大的困难。特別是用耗牛驮运一次石板,按其距离长短不等在途中需要一至四、五天。例如,赛希石经墙的石板是从班龙(今甘德县岗龙乡三大队境内)运来的,在来回途中需用两天。东吉石经墙的石板来源主要有二处:其一是班龙(同上),在途中需要五天,其二是札买(今甘德县多卡乡境内),在途中需用两天。有些石经墙的石板是从许多地方驮运来的,路途较短,如达日县境内的梅·沙那石经墙,其石板是从卡热龙、热楞、热童、更龙等地方驮运来的,来回只需一天。也有极个别就地取材的石经墙,如多勒石经墙采用的石板一半是从附近采择的。
简言之,驮运石板是一项极其艰苦的工程,而且毎座石经墙的石板数目高达三百多万块(如多勒石经墙)。由此可见,果洛藏族人民仅为搬运石板就付出了巨大的劳动力。
四、镌刻过程
镌刻在石经墙的创建过程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一环。因为它是一项具有高难度的技术性工作,而且又是保证石经墙质量的重要环节。如创建一座石经墙,除了以雄厚的资金作保障外,还必须组织或招引一大批石匠,特别是雕刻各类神佛像和主要目录时,一定要由技术闲熟、经验丰富的石匠来担任。
此外,创建石经墙时有专门设立的组织或管理具体镌刻石经的机构,其中的领导人即“石官”,由创建石经墙的大活佛任命,毎年或二年内换届一次。“石官”将各项镌刻石经的任务,有计划地承包给大小不等的各个石匠团伙,由他们具体安排完成,石匠团伙中有专门刻写经文的人员,这类石匠不需要很高的技艺,甚至其中的大多数人不识藏文,但他们的模仿刻写的手艺十分闲熟。有专门雕刻神佛像和佛经目录的人员,这类人为数不多,但他们是众多石匠中的佼佼者。他们一般是从前辈师傅那里经过长期的训练,具有很高的雕刻技术。有专门逐字逐句校对石经的人校对人员,这类人员一般是由识字有文化的僧侣组成,而且他们发现错误后有权勒令重新刻写。有专门监督验收的人员,因为验收是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环节,由“石官”亲自把关。最后是石经墙竣工而举行的隆重仪式,这与寺院竣工后所举行的“开光安坐”仪式完全一致,其形式到内涵都与寺院没有两样,在此不必赘语。
上述石匠的来源,主要是各处石经墙附近的本地人。但由于果洛石经墙是一项没有终结的宗教文化工程,自公元十九世纪末开始,直至今日仍有人在不同程度地进行扩建或补充。在这长达一个世纪的历史进程中,果洛地区已形成专门刻写石经的几个部落,如甘德县岗龙乡内的“智廓德哇”、达旧县吉近乡内的“仲巴措哇”等。这些部落曾经主要依靠镌刻石经以维持生活。
石匠中也有来自外地的,主要是从今四川省甘孜州的石渠县和色达县来的藏族同胞。石渠和色达两县是藏族地区在建筑石经墙方面有着悠久历史传统的地区之一。因此,来自上述两县的石匠,虽然其人数很少,但他们一般都具有较高的镌刻石经的技能,这对提高果洛石经墙的质量起到了促进作用。
总之,通过对果洛石经墙的年代考证、资基来源、石料采择和镌刻过程等四个方面的具体叙述,可以看出,果洛石经墙历史虽不很悠久,但它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以及自身的独特风格,并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藏传佛教文化的丰富多彩,为进一步深入研究藏传佛教文化提供了一个崭新的领域。
注释:
①②③《达日县志》第39页、第39页、第41页,油印本,达日县志编纂委员会1989年10月编.
原刊于《西藏研究》1997第三期,原文版权归作者和原单位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