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明信,汉族,1917年12月生于湖北沔阳,成长于北京,著名藏学家。1938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历史系,同年开始学习藏文。1941—1948年,任成都华西大学边疆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在此期间,入甘肃省拉卜楞寺学经,考取“绕降巴”学位。1950年调入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参事室,在和平解放西藏协议谈判过程中任首席代表李维汉翻译。1953年调入民族出版社任藏文编译室副主任,参与整理《五体清文鉴》,组织出版《格西曲札藏文辞典》等。1979年调入北京图书馆(现国家图书馆)善本部少数民族语文组工作,任研究馆员,1988年离休,后返聘至1998年。黄明信先生具有深厚的藏文和藏传佛教研究功底,长期致力于藏族历算学研究,并取得了显著成果,是国内外为数不多的藏历学家之一,其《藏历的原理与实践》被公认为是填补学科空白的学术力作。黄明信先生历任西藏天文历算学会副理事长、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干事、中国古民族文字研究会名誉会员。1992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17年5月29日逝世,享年100岁。
黄明信,汉族,1917年12月生于湖北沔阳,成长于北京,著名藏学家。1938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历史系,同年开始学习藏文。1941—1948年,任成都华西大学边疆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在此期间,入甘肃省拉卜楞寺学经,考取“绕降巴”学位。1950年调入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参事室,在和平解放西藏协议谈判过程中任首席代表李维汉翻译。1953年调入民族出版社任藏文编译室副主任,参与整理《五体清文鉴》,组织出版《格西曲札藏文辞典》等。1979年调入北京图书馆(现国家图书馆)善本部少数民族语文组工作,任研究馆员,1988年离休,后返聘至1998年。黄明信先生具有深厚的藏文和藏传佛教研究功底,长期致力于藏族历算学研究,并取得了显著成果,是国内外为数不多的藏历学家之一,其《藏历的原理与实践》被公认为是填补学科空白的学术力作。黄明信先生历任西藏天文历算学会副理事长、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干事、中国古民族文字研究会名誉会员。1992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17年5月29日逝世,享年100岁。
本文由黄明信口述,黄维忠 央宗整理而成。
拉卜楞岁月(1941-1948)
原来在学校的时候根本没想到学藏文,那时候一心一意的就是想出国留学,上英国,或者是上美国去留学。后来到第四年不是抗日战争嘛,抗日战争起来了,北京被日本人占了,呆不住了。我们就跑到长沙,北大、清华跟南开3个学校合在一起,长沙临时大学,还有一部分到南粤去上的。这时日本人也快来了,占了武汉,长沙已经不安全了,学校又从长沙搬到昆明。搬到昆明要走的话,当时得到香港,香港到安南(现在叫越南),从安南坐安南的窄轨铁路到昆明去。可是那个时候安南还是归法国人殖民地,他们先去的人说是法国人海关检查的时候很不客气,把箱子里的衣物乱扔,欺负中国人。我们就不愿受法国人这种欺负。从长沙到昆明3000里地,当时正在修公路,汽车的公路,很不好走,我们就步行,有300个人检查身体,身体都挺棒,可以从长沙步行3000里路走到昆明。后来称为一个“壮举”,就是很不容易的。这一路就看到了少数民族,就是什么苗族、壮族这些个少数民族,语言不一样,文字也不一样,有些民族甚至没有自己的文字。才知道了中国很大,还有这么多不同的民族、不同的语言,于是很多人就从这就改变主意研究少数民族。可是当时就主要是西南的少数民族,主要就是苗族、壮族这些民族,我想大家都研究这些,我也不容易出人头地,我到人少去的地方,到新疆或者到西藏去,那儿人更少,就更容易出人头地。当时也不知道天高地厚,以为自己可以做多大的事情似的。可是一下去不了。怎么去不了呢?当时新疆原来是可以去的,后来新疆政治态度变了,把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等6个人关到监狱里头。所以新疆去不了啦。想去西藏,当时,班禅要回到西藏去,这个班禅是第九世班禅,当时蒋介石国民政府给他派了500人的卫队,西藏人说,班禅回来我们很欢迎,500个汉人的卫队我们不欢迎,不要进来,所有的汉人都不受欢迎,我原是要跟着班禅一块回去的,也去不了啦。后来班禅就在西昌故去了,转世为第十世。新疆、西藏去不了,就想先去青海,往这边到新疆也可以,到西藏也可以。后来在青海就知道藏文的重要,藏文除了藏族之外,蒙古族人念的经也是藏文经,还有土族、纳西等好几个民族都是念藏文,所以我就下决心学藏文。
一、初识藏文(湟川中学)
1938年到1940年我在青海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湟川中学做教员。我去湟川中学是通过李书华介绍的。李书华是我父亲在保定时候的学生,后来他去法国,我父亲给他过帮助。他后来主持北平研究院,中国的最高研究机构是中央研究院,此外还有一个北平研究院,中央研究院是英美派的人主持的,北平研究院是大陆派去留学法国、德国的人主持的。他认识教育部的次长杭立武,打了招呼,我才去了。湟川中学的校长是德国留学的,他是教育部长朱家骅的学生,是北大的。所以那儿的数学教员、化学教员都是北大的,可以说是北大的天下。我是由于李书华找教育部的次长给推荐的,湟川中学校长没法拒绝,允许我去了。我去了之后还有人问我,这里是北大的天下你怎么能进来了?我在湟川中学呆了2年。
湟川中学的学生必修藏文课,一个星期2个小时,我也跟着学。我觉得我要学好,2个小时是不够的,必须得业余去学。一年之后我感觉仅仅业余而不是专心,是很难学好的。因此下决心攒一些钱离职去学。藏族的文化中心是寺庙,必须住到一个寺庙的附近。青海最著名的寺庙是宗喀巴故乡的塔尔寺,为什么我没有去塔尔寺而去了甘肃夏河的拉卜楞寺呢?我在湟川中学做教员时的同屋的王树民曾经参加顾颉刚领导的西北考察团,到过拉卜楞。他跟我说拉卜楞寺的重要,因为在安多,最有名的是塔尔寺,塔尔寺不如拉卜楞寺,很多蒙古人都到拉卜楞寺学,甚至于在苏联境内的布里亚特都人有三四十人来拉卜楞寺来学。这样我就去拉卜楞寺了。
二、入拉卜楞寺学经
我去拉卜楞不是为了信仰:第一,李安宅的研究毕竟从寺外,再深入必须从寺内。第二,经济,中英庚款的收入主要来自粤汉铁路的投资,战争时期,收入锐减,研究补助费停止,我的计划落空,就此撤退,于心不甘。当地就业,不能专心学习、研究。入寺后的收入,还勉强能维持生活继续学业,于是受戒出家,进入寺院。
 1930年代的拉卜楞寺
1930年代的拉卜楞寺
1940年秋到1948年春,我在甘肃夏河学习藏文,研究藏传佛教8年,这8年里头前几年没有别的事,就专门在寺院里头学习因明学。后来做了参议会的秘书,做了喇嘛学校的教导主任,我就没有很好的学习了。所以说起来是8年我在那学藏文、藏传佛教,实际上就是前边5年是专心学,后来3年别的事多,就没有好好学习。所以我学这个8年实际上也是没有真正学透。
1.1940年秋到1941年春,自费学习藏文
我是1940年秋到拉卜楞寺去的。在我以前,就有一个燕京大学的社会系的教授叫李安宅,他夫妇两个已经在那儿了,他们研究社会学的。还有一个拿中英庚款补助的人张逢吉在那里。我在湟川中学教2年书攒了300块钱,够一年花的。我跟中英庚款反正有点关系,中英庚款有这个奖学金,我想我一定能够申请到,所以就到了拉卜楞去了。中英庚款是从粤汉铁路上赚钱的。当时日本人已经到了湖南,粤汉铁路断了,没有收入了,这种奖学金没有了。我原来希望得到中英庚款的补助的,也得不到了。可是半路退回来我又不甘心,所以就入寺院。寺院里边有布施,就是有施主给布施,布施给钱给酥油,那么也勉强可以维持生活。寺院里头经常有布施,一般的小喇嘛除了布施之外,自己家里都还给钱;自己家里没有钱的,完全靠布施也可以活,可是比较困难。我当时没有收入,只有靠布施,生活比较困难的,布施啊主要是给你吃的,给酥油、糌粑,有的酥油都是比较陈腐的,长了绿霉的,因为这一个年级的施主十几年才轮到一次他布施;糌粑陈旧受潮了之后也不好吃,可是没办法,我就靠布施的那点儿酥油、糌粑还有点儿钱勉强维持生活。
当时你入寺的时候,一个在寺院里有资格的人带你去找赤哇(院长),赤哇就给你指定老师,有一个世俗老师,一般就是领你去的那个人,另外指定一个讲法的老师,你也可以自己要求,我希望某个人做我的老师也可以,只要你希望不是太大,比如你希望的这个老师资格太高,那不一定同意,一般中等的老师,赤哇点头就可以。于是你的世俗老师就领你去讲法的老师那里,讲法老师有时候觉得自己学问还不太够,你这个学生我还教不了你那么多,又介绍比他高一级的人,也有。一般除了赤哇指定的老师外,可以自由听讲,反正在学程的范围之内,你找两个三个老师都可以,所以我们有时候在老师门前蹲在那儿好几个人,等上一班的人出来你再进去。每个年级好几个活佛里有个主要活佛,这个年级一般就以这个活佛的名字来命名的,我上的那个年级叫“根敦达尔吉仓”,也不说某一年某一级,这个根敦达尔吉一般地位比较高一点,他的师父也是学问比较高一些,所以我就在他那个师父那儿听讲,有不少人除了自己指定的师父之外,就跟他听讲。
2.生活费条件改善,学业受影响
后来我在那儿认识了李安宅,他是燕京的教授。他去四川华西大学建立了一个边疆研究所,钱呢不是华西大学给的,他自己找的钱,他有些办法弄了些钱,从研究所里给了我一个助理研究员的名义,我拿助理研究员的钱,多少钱不记得了,反正是比较好一点,每个月都给寄,那个时候物价变化很快的,寄来了马上换成银元,这样生活就好一点。
那时各省、各县都成立参议会。拉卜楞是属于甘肃省的夏河县,夏河县那个时候成立参议会,就蒋介石那时候就要搞民主嘛,民主有参议会。夏河县参议会的议长是拉卜楞寺的大襄佐阿莽仓,他是拉卜楞寺的寺主嘉木样呼图克图的弟弟,掌握实权,参议会得有个秘书,由省里面直接指定。当时在省政府里有个认识我的人,叫张心一,这个人是早期清华留美的,我因为是清华的,所以见过他。一般甘肃省里的民政厅、财政厅都是直接派过来的,财政厅就是孔祥熙、宋子文他们给派的,民政厅是陈立夫他们派的,这个教育厅就找了当地甘肃省的人。张心一虽然不是谁的系统的人,可他资历比较好,是金陵大学的教授,用英文写过著作,所以甘肃省主席为了说省政府里有甘肃的人,用他了。他因为跟清华有关系,所以成立参议会的时候他就推荐我去做秘书。一个县的秘书按理说我是不大看得起的,可是第一阿莽仓是议长,第二我是张心一推荐的,所以我也就接受了,秘书又有一份收入,大概也有二三十块大洋吧。另外后来1944年成立拉卜楞寺青年喇嘛职业技术学校,我是教导主任,那儿也有一份薪水,所以我有3份薪金,就比较好了,我还自己买了一所小房子。我那房子是在我入寺后5年左右买的,花了200大洋,不大,一居室,两间房子,卧室通炕,没有给别人住的地方。这样条件改善了,可是学业受到影响了,本来我学因明是很扎实的,从头学起的,因明前几年的内容都是关于主要名词术语的概念,到最后一部分是讲因明理论,那个时候我事儿就比较多了,就没有学好,所以我说我的学问是夹生的,没有真正熟,因明没有学透。
3.拉卜楞寺青年喇嘛职业技术学校
拉卜楞寺寺主嘉木样的弟弟阿莽仓跟他的哥哥黄正清两个人想揽权,把他架空。所有人到了拉卜楞,希望见到寺主嘉木样,他们就说嘉木样现在在静坐,不见客,所以外边的人就见不着嘉木样。可是嘉木样本身他不甘心做这样一个傀儡,他要有他自己的干部,那时一般的喇嘛光念经,不注写字,也不会记账。他就搞了一个学习班,教学生写字、写信、记账,以便掌权。
后来他成立了一个拉卜楞寺青年喇嘛职业学校。国民党的教育部部长朱家骅很注意边疆民族的事。他把这个学校由教育部直接理管,校长是教育部任命的,而且教导主任也由教育部任命。一个中等职业学校的教导主任一般都是由学校的校长任命的,可是拉卜楞寺青年喇嘛职业学校的教导主任是由教育部直接任命的。因为那个校长嘉木样他管不了,所以他想通过这个教导主任来掌握这个学校。
当时那个学校学生哪来的呢?青年喇嘛就是由嘉木样下命令给他的拉卜楞寺的6个扎仓(僧院),每个扎仓出10个学生成立了一个班。他原来那个干部班就叫甲班,新成立这个叫乙班,乙班的学生年龄都很小。房子就是用嘉木样给他的父亲的一个花园,在那个花园房子里头上课,但这也不是长久的办法,拉卜楞寺本身一些守旧的人不喜欢这个学校,就怂恿他的父亲说要把这个房子收回,这个学校没有房子就办不成了,原来这个学校学生们每逢他本身的扎仓里头放布施,他们就回去领。对于各扎仓的主持人来说,那些个小喇嘛他可以支配他们做好些个事情,而这些职业学校的学生他就没有权支配,所以他们不高兴了。后来因为没有房子成了问题,学校当时只供热茶,学生自己带着糌粑、酥油在学校里头吃。这也不是长久的办法,我就到教育部去说这个情况,说是学校最好是公费,搞一个印刷班、一个医药班,搞印刷跟医药的设备都需要钱,学校办公也需要钱,于是我就代表嘉木样去要求教育部给钱。教育部还真给了,汇回去之后就马上换成大洋,4万现大洋。可是这个中间,我就回北京来看我母亲,我在北京这段时间里头,嘉木样得了天花去世了,别的人都是小的时候得过天花,而他小时候没得过天花,到30岁才得天花,很难治愈,就去世了。各扎仓派了10个人去,这个时候嘉木样去世了,他们就把学生召回了。没有学生,这个学校就空了,我跟教育部讲这种情况,教育部说希望我做校长,我说这校长我做不了,反复过了有一年多的时间,最后教育部才同意了,学校解散了。我就回到北京了。
4.获得绕绛巴学位的情况
我看有一个地方介绍我说我考过“拉然巴”,拉然巴在拉萨是最高的学位,他们以为我大学毕业之后在拉卜楞8年,一定是得到了最高学位了,其实不然。拉卜楞的学位跟拉萨不大一样,拉萨那儿是拉然巴、措然巴、林赛、朵然巴,四级。拉卜楞那儿只有两个,一个叫绕绛巴,一个叫朵然巴,朵然巴在拉萨的话是第四级学位,比较低的,在拉卜楞呢是比较高的。为什么叫朵然巴呢,是指台阶,要经过二三十年吧(待位)。“绕绛巴”这个名词,说翻成博士是最合适的,是广博、渊博的意思,可是不能翻成博士,翻成博士就误会了,以为跟西洋的博士一样,所以我就用"绕绛巴"这个名字。
 闻思学院经堂
闻思学院经堂
藏族的这个考试并不是说是有多少题目来考你,它是口头辩论,有人说是立宗,我专门有篇文章讲这个(指的是《藏传佛教的口头辩论-立宗答辩的组织形式与答辩规矩》)。立宗,不是我说出一个什么观点或者论点,也不是他说,那么是谁说呢?是他提出来一个观点或者一个论点,我回答他是或不是,对还是不对,所以这个事情也不能说是他一个人决定的,也不是我一个人决定的,提呢是他提出来,我说是对,他就要想办法证明这个不对,我要说这个不对,他就得证明这个是对,我们两个人辩论在这个地方,所以不能说这个论点是他提的,也不是我提的,是双方这么样互相对答来决定的。所以有人说我的因明研究,我提出了好几个论点,别人都驳不倒我,这个是他们不知道藏传佛教辩论的情况,不是那么回事。
对方提出一个论点来,一般都是他的师父替他设计出来的,而且告诉他,如果对方承认的话,你怎么去驳他;如果对方不承认的话,你怎么去驳他,事先要做好多准备。在辩论以前,先有一段两人的互相谈话,问什么书你看过没有,书的内容主要论点是什么,问的那些个书啊,我未必全都看过,可是呢,我们是坐在那儿,一个年级,两个人是叫做“把门儿”的,是能够开口回答的,他可以跟后面的人商量,那个人问到什么书,他没有看过的话,后面的这些人有一个人看过就行,而且能够说出来这个书的主要论点是什么,叫“盘道”。先是很大范围地说,逐渐范围缩小,缩到一本书,一本书的某句话怎么讲,你怎么理解。而这句话确实是有不同的理解的,可以这么理解,也可以那么理解,你就说出来你怎么理解,他为什么要问到这儿呢,就是将来他问的那个问题最后他要引经据典,引什么经呢,就引这句话,他先跟你说好了,你是这么理解的,好了好了。于是他又从头说起,说到最后引经据典,说出这句话来,这句话的理解反正有两种,当初你说了你是怎么理解的,那你不能再改了,所以所谓的考试就是这样回答,没有什么考不考取的问题。
拉卜楞寺的朵然巴是年数比较多,13部经完全学完了以后,还得待位,就是没有正式考以前要经过十几年。绕绛巴并不要所有的经都念完,不是五部大论嘛,第三部“中论”分新旧两个集,“中论”新集完了就可以考。不是自己报名,是赤哇指定的,他认为成绩不错的,可以考的,选4个人,这4个人就是要经过所谓的考试,就是答辩。每个人正式的答辩要两天,第一天是4个朵然巴来问,第二天是12个朵然巴,总共要有16个人来问他,要回答16个人的问题。这16个人叫16个长老/尊者,当初释迦牟尼委托16个人继承佛法。
 我考的时候,实际的年级还没到“中论”,按我原来登记的年级是已经到了,可是它可以自动退级,比如这部分我还没学好,我可以再退一级,尤其是一年级的时候,小孩子オ十二三岁,就一年一年地退,到16岁了,年岁大了理解力比较强了,可以跟着一级一级上去。我到拉卜楞在同年级里年岁是比较大的,可是我等于是从头学起,一般人以为啊你大学毕业之后,如果硕士、博士、博士后加在一块儿也不过7年,你一定是取得最高学位了,可是不然,我在那儿等于是从一年级学起。我登记的级别是够了绕绛巴了,实际上呢我还没有学到中论级别。头一天是老师专门给我补课,把中论的主要论点跟我讲过一遍。讲之前,我没有学过,就自己看看书,辩论的东西不经过实际辩论,光看书是不行的。
我考的时候,实际的年级还没到“中论”,按我原来登记的年级是已经到了,可是它可以自动退级,比如这部分我还没学好,我可以再退一级,尤其是一年级的时候,小孩子オ十二三岁,就一年一年地退,到16岁了,年岁大了理解力比较强了,可以跟着一级一级上去。我到拉卜楞在同年级里年岁是比较大的,可是我等于是从头学起,一般人以为啊你大学毕业之后,如果硕士、博士、博士后加在一块儿也不过7年,你一定是取得最高学位了,可是不然,我在那儿等于是从一年级学起。我登记的级别是够了绕绛巴了,实际上呢我还没有学到中论级别。头一天是老师专门给我补课,把中论的主要论点跟我讲过一遍。讲之前,我没有学过,就自己看看书,辩论的东西不经过实际辩论,光看书是不行的。
当时跟我一块儿考的那几个人学问都不怎么样,赤哇指定有的是他真正认为这个学生不错,也有些个是人情面子,其中有个我知道,是卓尼的人,他是属于元老的侄孙子,推荐给赤哇,甚至于还有花钱的,当然是个别的了,主要是赤哇认为好的。赤哇指定了以后,要做准备,还要找施主,你得在家乡里能有一定的威信,会有施主,范围就是在扎仓里头,我是在闻思学院,其他的几个学院都是密宗的,人都不多,二三百人吧,大部分人都在闻思学院里,有1000多人。
考完了学位以后你的师父领着你,在寺院里拿着个香串走,等于告诉大家这个学生考取了绕绛巴。还有就是在正月会的时候,正月会应该是赤哇讲法,在他开讲以前,你得坐在那儿,回答一些低年级的人的提问。
南开大学一华北人民革命大学(1949-1950)
后来就是1949年春到1949年夏,我那个时候已经从拉卜楞寺回来了,在南开大学教了一个学期的书,教西藏史,那个时候南开大学有意搜罗几个搞西藏的,有个边疆研究所,里面有王森、韩镜清,后来学校改革,文学院就取消了,像我们搞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都到北大的东方语文系了,别人都发了聘书,就我好久不发聘书,可能是对我的历史有点怀疑吧,让我上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一年,因为那个时候刚解放,你教社会科学方面的东西,马克思主义不懂就不行,这一年主要是去学习马克思主义,同时也是交代历史,半年在拈花寺,半年在西苑。
民委工作期间(1950-1958)
在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一年交代清楚历史之后,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知道我,就把我要到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去了。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有一个参事室,这儿的人就做那个文字翻译工作,除了藏文,还有蒙古文的、维吾尔文的、壮文的还有朝鲜文的,做这种翻译。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协议谈判时,我在李维汉身边工作,事后写过一篇回忆文章,证明协议确实充分考虑了西藏方面的意见,有积极的影响,2003年出版的《见证百年西藏》上又重载。1953年成立民族出版社,我任藏文室副主任;其他蒙古、维、哈、朝各室的主任都是本民族人,而我不是,因此只能是副职。1954至1956年第一、二、三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藏文翻译组有六个地区、单位来的人,各出一人做副组长,正组长平旺是人大代表很忙,实际由我负责的、也只能是副职。民族出版社的主要任务是翻译出版重要的政策文件。传统的藏文里佛学词汇很丰富,而现代词汇贫乏,建国初翻译政策文件、毛泽东著作遇到困难,我参加了开创时期的工作,对藏文里哲学、社会科学名词术语译法的确定作出了一定的贡献。此外,我还主持过藏汉双解的《格西曲扎藏文词典》和一些民族遗产的整理、出版工作,包括《五体清文鉴》的影印出版,对此书的成书过程进行了考证,此文在40余年之后2003年出版的《贤者新宴》里又被重刊。
 国图流年(1979-1998)
国图流年(1979-1998)
1978年我被从山西长治的农场借调到成都参加《藏汉大辞典》的编辑工作。其中藏历方面条目释文的汉文翻译遇到困难,为此,我学习藏历,有些收获。1979年平反后调到北京图书馆。《藏汉大辞典》是原来北京大学的一个教授叫张怡荪,他受陈寅恪的启发搞了藏文。搞藏文就是拿汉文的佛经、藏文的佛经对照这么看,搞出了这么一个藏文的词汇。后来他给方毅、邓小平写报告,说是他要继续做《藏汉大辞典》。当时有一个英文的《藏文辞典》,后来就批准了他们必须继续做这个辞典,做辞典他要人,要人就从山西把我借调到成都编那个辞典。我去了之后过一段时间就是右派分子全都摘帽子,摘帽子就是可以回到原单位民族出版社。可是我就不愿意回到民族出版社,民族出版社老是讲什么政治任务,我是希望搞点传统藏文的东西。当时北京图书馆管藏文的人叫于道泉是中央民族学院的教授。他在雍和宫学过藏文,后来到法国吧也学过藏文。他的妹妹叫于式玉,于式玉也到拉卜楞去过,知道我,她就把我推荐到北京图书馆。因为她主要是在北京大学东方语言系教藏文,同时兼着北京图书馆的那个藏文工作。她在北京图书馆那儿她不拿薪水,义务在那儿。后来知道我摘了右派帽子,可以工作,就把我介绍到北京图书馆。
我到北京图书馆的时候60岁了。一般的单位60岁你就退休了,就不吸收新人,北京图书馆吸收我了。北京图书馆呢藏文书有1000多包,可是它就是等于是一个登记簿,把书名登记上了,藏文书的书名很长的,它除了正式的名称之后前面还有好些形容词,后边还有好些形容词。做这个书目录的时候,必须把这前后的拆掉,那你没有一定的学识,剪裁的工作是做不好的。而且它的书名和作者的名字并不是在这个书的前面。汉文书是书名底下是作者的名字,藏文书不是,藏文书作者的名字在书的末尾。那一大堆话里边说的是某某人写的。从那里边摘出作者的名字来,没有一定的学力也做不了。还有分类,过去也没有过分类。所以我在北京图书馆,是做书名目录、作者目录、分类目录。我把这份工作的经验写成了文章。用汉藏两种文字写成《北京图书馆藏文古旧图书著录条例说明》,发表在《中国藏学》创刊号上,成为各处图书馆编制藏文古籍目录的重要参考资料。在北图工作的时候,我去青海塔尔寺,把那里所有的经版都印刷了一部,共200余包,丰富了馆藏。
在北京图书馆先做这些,后来就是做了些研究工作。写了两本书,一本是关于藏族历史人物年代的;一本是关于《至元法宝勘同总录》的。我在北京图书馆干了10年,1988年就退休了,退休之后又返聘了10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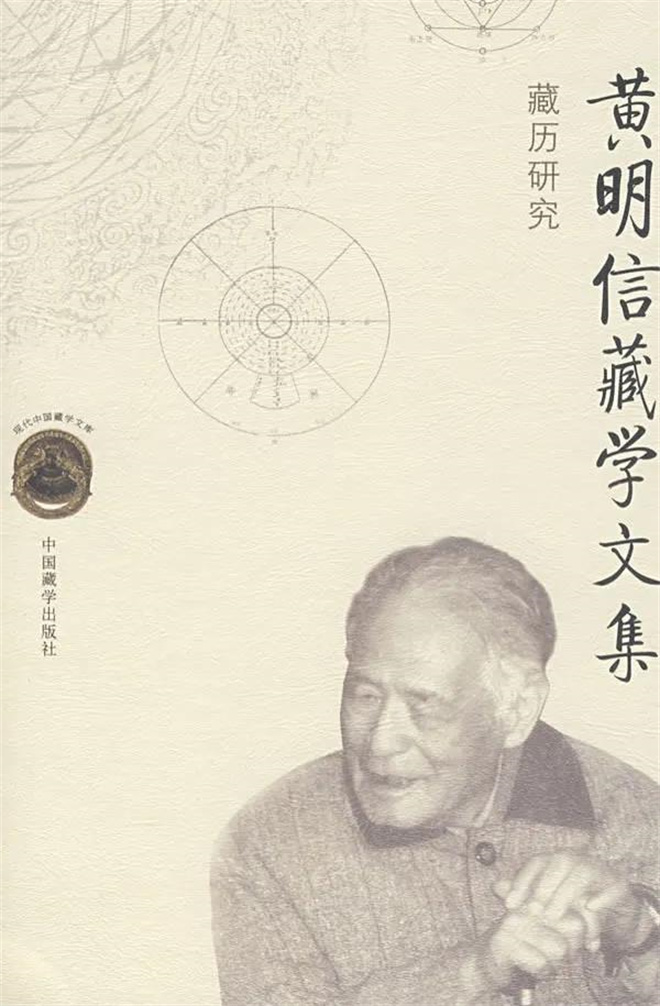 学术研究
学术研究
我一生作学术研究,研究的成就自评两个字-“夹生”。我从全国最知名的两个大学之一的清华大学毕业后,在藏传佛教的重镇拉卜楞寺学习8年,这个学历足够欧美学历的“博士后”(硕士2年、博士3年、博士后2年,共7年)。其后又在民族出版社藏文室、国家图书馆民族语文组做研究馆员,都是文化单位,按说我对于藏族文化的研究应该有较高的成就,但是惭愧得很,我的所谓研究成果总的说来是夹生的。即以我晚年知名度较高的藏历方面我也并未完全吃透。何以如此?我反复思考,至今没有想明白。我的学问可以说主要是三部分,一个是图书馆,一个是因明,一个是藏历。图书馆那一部分呢,藏文书不像汉文书,书名、作者,封面、首页上都有,照录就可以了。藏文书是长条的,著作的本名前后常有不少附加成分,必须从中抉择出其本名,如果照录其封面上的全文,则读者很难查找。作者的名称在后记里,也须要编目者自己抉择。都需要学识,不是简单拿过来就可以。书目分类这个工作跟现代西洋图书馆分类的方法不一样,怎么样来把这两个弄在一块儿,我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拿不出一个通用的分类法,更不要说数码化与国际接轨。藏历主要的问题我解决了,可是另外藏历里还有一些历注,讲吉凶祸福的,那部分我没有研究,其实研究的话也还是有内容的,就是你从某个事、哪些问题上要占卦,从那里面可以看出当时的社会问题,比如关于婚姻、买卖各种都有。藏历我的收获比较大,可是也没有完全做透。因明我没有真正学完,除《藏传佛教的立宗与口头辩论》一文外,未能拿出其他研究成果。三者都没有达到应有的水平,所以我说我的学问是夹生的,都没有做透。
一、藏历研究
在藏学界里,按照印度的传统,有大五明、小五明之说。天文历算是小五明之一。西藏学者一致认为必须先把内明和因明学通,然后才能学其他各“明”。如果先学了其他的明,再学内明和因明,就不容易学好。我在拉卜楞的时候,严格按照传统方法学习,先学了内明跟因明。在学习藏学的过程中,对因明的学习我花的时间最长,不过还是没有学透,一方面是因为在我学习因明学的最后几年受到了拉卜楞寺青年喇嘛职业学校事情的干扰,一方面是因为在逻辑学方面我还缺乏一些基础。上世纪40年代离开时五部大论尚未学完,历算尚未学过。
我有点儿贡献的是藏历里跟天文学有关的部分,占星术部分没有研究。我学藏历是70年代末,参加《藏汉大词典》的编辑。这个词典是藏汉双解、小百科性质,其中应该有藏历方面的词条。一般搞藏历的人大多只会按照公式演算,不深究其原理,不能写好。而这位作者曾经深究其原理,所以写得很好,一定会给词典增色,可惜没有人能准确地翻译成汉文。以前陈遵妫先生写《中国天文学史》时,为了藏历曾经亲自去到拉萨,找到历算研究所的所长,但是翻译人员不懂专业,无法沟通,空手而归。现在这里遇到同样的问题。我想,我的藏语好,当年数学基础也好,应该能够解决,就毅然承担下来。
我在藏历专家的指导下,按照藏历所给的公式和数据,做过推算日食月食的例题,还推算过金木水火土五星的位置。我将自己的记录拿给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陈久金先生。陈先生仔细看了之后指出,用来决定闰日、空日的“太阴日”,虽然现代科学里未讲,但确有科学意义,所以闰日、空日的设置不是迷信。这下就解决了藏历不是迷信的问题。为此,藏族的历史学者非常感激我们。因为过去他们讲不清,现在我们帮他们讲清了它的道理。西藏藏医院院长强巴赤列要求我在论文的“恭请者”名字里写上医算院,标志藏族学界对我的贡献的肯定,是我最引为骄傲的一件事。
二、因明研究
我在藏学里学习时间最长的是因明,不过也未学透。正当我学习到因明学的最后一年,受到青年喇嘛职业学校事情的干扰没有学好,而且我没有逻辑学的基础。本来我在大学一年级的时候,是有机会跟金岳霖学逻辑的,我却贪图虚名选学了微积分。后来在因明学方面我能拿出来的只有《口头辩论规矩》《藏传因明学书目》这些外围性的东西,拿不出来深入一些的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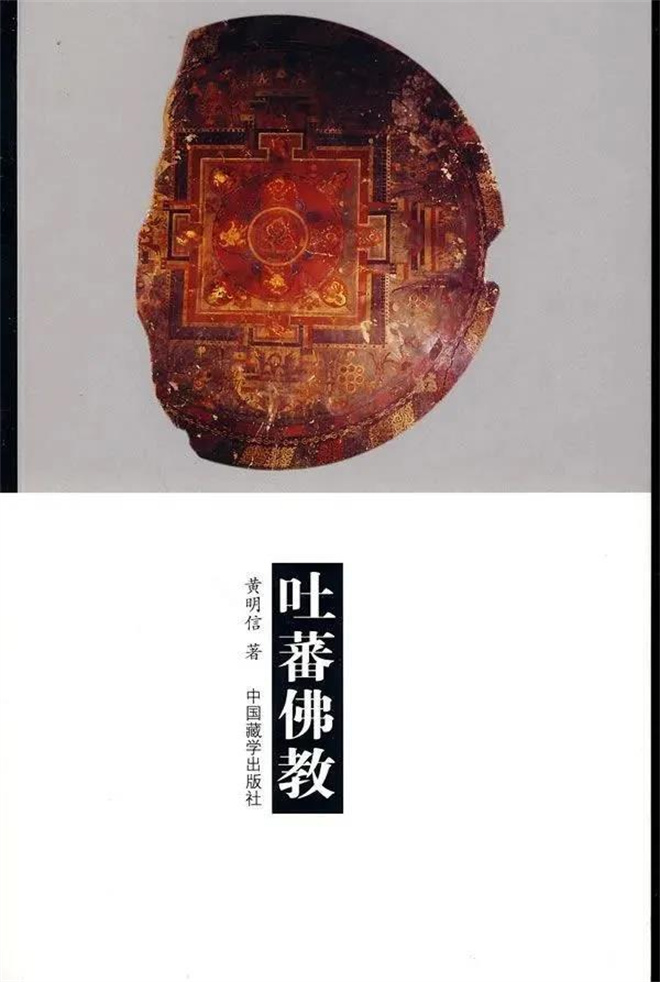 三、藏传佛教研究
三、藏传佛教研究
1986年任继愈先生邀我给他主编的《中国佛教史隋唐卷》写吐蕃佛教部分,我参考柳诒徵和邓之诚的方式,史料选读加解释、分析,写了近20万字。该书因故未及时出版,此稿亦因而搁置,20年后,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我的藏学论文集拟收入此稿,20年来藏学研究发展很快,我年老鲁钝,未能及时修改补充,不过自认为其中顿渐之诤、译经事业两章尚有特色,同意收入,2010年又出单行本。
佛教典籍有南传北传两支,北传主要有汉文、藏文两支。二者大都直接从梵文译出而有所不同,究竟有哪些同、哪些不同,成为众所关心的大问题。元朝初年皇帝集中几个民族的学者对勘,这是一项大工程,编出《至元法宝勘同总录》一书,历来学者们对此书的功绩均有很高的评价。我利用馆藏的汉、藏、日文资料逐条查对,发现原书所记“蕃本同”“蕃本缺”并不完全准确,原书记为“同”而在今本大藏经中未查到者约1/3,记为“缺”而查得不缺者有1/4,还有一些其他问题,写出《汉藏大藏经目录异同-(至元法宝勘同总录>及其藏译本笺证》一书。藏族历史人物的生卒年代是了解历史不可或缺的资料。汉文里有“人名词典”可查,藏文里以前没有这种辞书。“教历”(bstan-rtses)里有这种资料,但不便检查。我与谢淑婧合作编写了《藏族历史人物年代手册》(藏文),按人名的字母顺序排列,其有异说者给出出处,还照顾到一名多人和一人多名的情况,读者使用方便。当然藏族历史人物不止这些,尚有待补充。以上两书分获首届中国藏学研究珠峰奖基础资料成果类二等奖、三等奖,2010年本人又获第二届中国藏学研究珠峰奖荣誉奖。奖状上有国徽,是国家级的。
原刊于《中国藏学》2016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