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пјҲ еҗҙйӣЁеҲқпјҢи‘—еҗҚж–ҮеҢ–еҮәзүҲдәәгҖӮ1976е№ҙеӨ§еӯҰжҜ•дёҡиө·еңЁиҘҝи—Ҹзҡ„д№ЎгҖҒеҺҝгҖҒең°еҢәгҖҒиҮӘжІ»еҢәе·ҘдҪңпјҢжӣҫд»»йӮЈжӣІең°еҢәж–ҮеҢ–еұҖй•ҝпјҢиҘҝи—ҸиҮӘжІ»еҢәе…ҡе§”е®Јдј йғЁж–ҮиүәеӨ„й•ҝпјҢеҢ—дә¬еҮәзүҲйӣҶеӣўи‘ЈдәӢй•ҝпјҢзҺ°дёәиҘҝи—ҸзүҰзүӣеҚҡзү©йҰҶйҰҶй•ҝгҖӮпјү
иҝ‘ж—ҘпјҢзҸӯзҰ…йўқе°”еҫ·е°ј·зЎ®еҗүжқ°еёғеүҚеҺ»еҸӮи§ӮдәҶжӢүиҗЁзүҰзүӣеҚҡзү©йҰҶпјҢ并й«ҳеәҰиөһжү¬дәҶйҰҶй•ҝеҗҙйӣЁеҲқе…Ҳз”ҹдёәи—Ҹең°ж–ҮеҢ–дј ж’ӯеҒҡеҮәзҡ„зӘҒеҮәиҙЎзҢ®гҖӮеҗҙйӣЁеҲқе…Ҳз”ҹдёҠдё–зәӘ70е№ҙд»Јд»ҺеҶ…ең°еӨ§еӯҰжҜ•дёҡжқҘеҲ°иҘҝи—ҸпјҢдҫҝжҠҠз”ҹе‘ҪиһҚе…ҘиҝҷзүҮй«ҳеұұеҺҡеңҹпјҢ38е№ҙеҗҺзҡ„2014е№ҙпјҢйӮЈдәӣйҡҫеҝҳзҡ„еҫҖдәӢе’ҢеӨ§еҚҠиҫҲеӯҗзҡ„з”ҹе‘ҪиһҚиҝӣдәҶдёҖжң¬еҸ«еҒҡгҖҠи—ҸеҢ—еҚҒдәҢе№ҙгҖӢзҡ„д№ҰгҖӮ

зҸӯзҰ…йўқе°”еҫ·е°ј·зЎ®еҗүжқ°еёғеҗ¬еҸ–зүҰзүӣеҚҡзү©йҰҶйҰҶй•ҝеҗҙйӣЁеҲқпјҲе·Ұпјүзҡ„д»Ӣз»Қ
гҖҠи—ҸеҢ—еҚҒдәҢе№ҙгҖӢи®Іиҝ°дәҶеҗҙйӣЁеҲқе…Ҳз”ҹж—©е№ҙй—ҙеңЁи—ҸеҢ—з”ҹжҙ»е’Ңе·ҘдҪңзҡ„ж®өеӯҗе’Ңи¶Јй—»пјҢд»Һж”ҝжІ»гҖҒз»ҸжөҺгҖҒж–ҮеҢ–гҖҒзӨҫдјҡз”ҹжҙ»зӯүдёҚеҗҢзҡ„еұӮйқўеҸҚжҳ дәҶиҘҝи—Ҹзҡ„ж—Ҙеёёз”ҹжҙ»гҖӮд№ҰдёӯзҷҫжқҘдёӘе°Ҹж•…дәӢпјҢж–Үеӯ—е№ІеҮҖжё…жҫҲпјҢз®ҖжҙҒжңүе‘іпјҢдёҚе°‘зҜҮз« пјҢиғҪи®©дәәжғіеҲ°гҖҠдё–иҜҙж–°иҜӯгҖӢгҖӮд№ҰзЁҝеҢ…жӢ¬жұүж–ҮгҖҒиӢұж–ҮгҖҒи—Ҹж–Үдёүз§Қж–Үеӯ—д»ҘеҸҠжҸ’з”»пјҢз”ұдёӨдёӘ家еәӯгҖҒдёӨдёӘж°‘ж—ҸгҖҒдёӨд»ЈдәәпјҢе…ұеҗҢе®ҢжҲҗгҖ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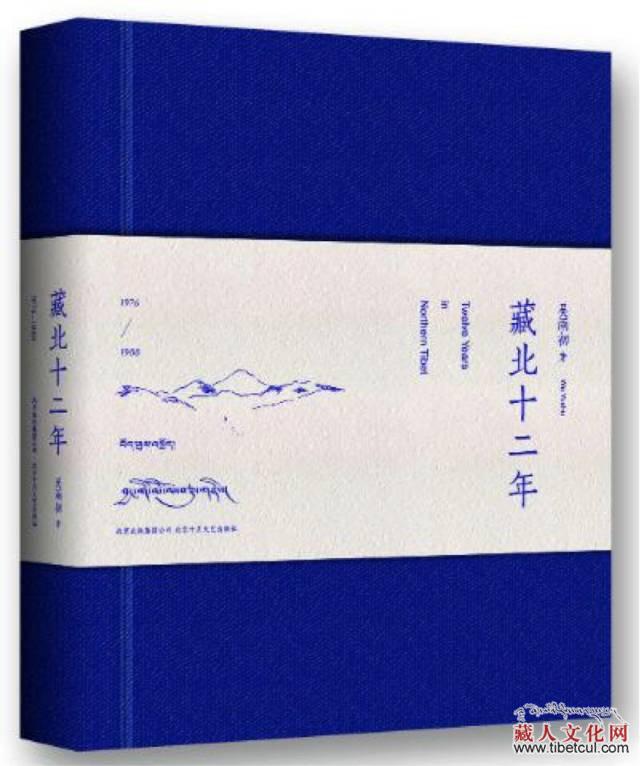
дёӢйқўпјҢжҲ‘们жқҘеҗ¬еҗ¬еҗҙйӣЁеҲқе…Ҳз”ҹиҮӘе·ұи®Іиҝ°иҝҷжң¬д№Ұзҡ„еҲӣдҪңж•…дәӢпјҡ
еҗҙйӣЁеҲқ
иө·еҲқеҸӘжҳҜжғідәІиҮӘзј–дёҖжң¬и—ҸиҜӯж•ҷжқҗ

1985е№ҙдёӢд№Ўе·ҘдҪңз»„еҗҲеҪұпјҢе·Ұиө·з¬¬дёүдәәдёәеҗҙйӣЁеҲқгҖӮ
жҲ‘зҡ„иҝҷжң¬е°Ҹд№Ұ——еҗҚеүҜе…¶е®һзҡ„е°Ҹд№Ұ——еј•иө·дәҶдёҖдәӣжңӢеҸӢзҡ„е…іжіЁпјҢйҰ–е…ҲжҲ‘иҰҒж„ҹи°ўи®ёеӨҡйҷҢз”ҹзҡ„иҜ»иҖ…гҖӮе…¶е®һпјҢжҲ‘еҺӢж №е„ҝжІЎжғіеҶҷд»Җд№Ҳзұ»дјјеӣһеҝҶеҪ•д№Ӣзұ»зҡ„д№ҰгҖӮжҲ‘еңЁеҢ—дә¬еҮәзүҲйӣҶеӣўеҪ“дәҶиҝ‘еҚҒе№ҙзҡ„иҖҒжҖ»пјҢжҜҸеӨ©жҺҘи§ҰжңҖеӨҡзҡ„е°ұжҳҜд№ҰгҖӮжңүйӮЈд№ҲеӨҡеҘҪд№ҰпјҢи®©дәәй«ҳеұұд»°жӯўпјҢиҜ»йғҪиҜ»дёҚиҝҮжқҘпјҢиҝҳеҶҷд»Җд№Ҳд№Ұе•ҠпјҹеҸҰдёҖж–№йқўпјҢд№ҹжңүйӮЈд№ҲеӨҡж»Ҙд№ҰпјҢжҠҠе®қиҙөзҡ„зӨҫдјҡиө„жәҗеҸҳжҲҗдәҶеһғеңҫпјҢжҲ‘еҸҲдҪ•еҝ…еҶҚеўһеҠ дёҖжң¬е‘ўпјҹиҝҷжң¬д№ҰжӯЈеҰӮ第дёҖеҲҷж®өеӯҗжүҖеҸҷпјҢиҝҷжҳҜжҲ‘зҡ„и—ҸиҜӯж–Үж•ҷжқҗгҖӮжҲ‘жғіеӯҰи—ҸиҜӯпјҢдёҖж—¶жүҫдёҚзқҖеҗҲйҖӮзҡ„ж•ҷжқҗпјҢе°ұеҝҪеҸ‘еҘҮжғіпјҢиҮӘе·ұжқҘзј–ж•ҷжқҗеҗ§гҖӮ
еҘҪеҸӢзҡ„ж…§зңјиөҸиҜҶдҝғжҲҗдәҶдёҖжЎ©зҫҺдәӢ

еҗҙйӣЁеҲқпјҲе·Ұпјүеҗ‘еҢ—дә¬еӨ§еӯҰиҖғеҸӨж–ҮеҚҡеӯҰйҷўиө йҖҒжңүе…ізүҰзүӣзҡ„еӣҫд№Ұе’ҢжқӮеҝ—
йӮЈжҳҜ2014е№ҙгҖӮжҲ‘жҜҸдёҖдёӨеӨ©еҶҷдёҖдёӘиҮӘе·ұдәІиә«з»ҸеҺҶзҡ„и—ҸеҢ—еҫҖдәӢпјҢи®©жҲ‘еҘіе„ҝзҝ»иҜ‘жҲҗи—Ҹж–ҮпјҢ然еҗҺпјҢжҲ‘и·ҹзқҖеҘ№иҜ»дёҖйҒҚпјҢеҪ•дёӢйҹіжқҘпјҢеҶҚиҮӘе·ұеҺ»еӯҰгҖӮеҶҷеҲ°еҚҒеҮ дёӘе°Ҹж®өеӯҗж—¶пјҢеҪ“ж—¶жӯЈеңЁжӢүиҗЁеҚҸеҠ©жҲ‘зӯ№е»әиҘҝи—ҸзүҰзүӣеҚҡзү©йҰҶзҡ„еҢ—дә¬еҚҒжңҲж–ҮиүәеҮәзүҲзӨҫеүҜжҖ»зј–иҫ‘йҫҷеҶ¬зңӢеҲ°дәҶпјҢд»–иҜҙиҝҷеҸҜд»ҘжҲҗдёҖжң¬д№ҰгҖӮжҲ‘еӨ§дёҚд»Ҙдёә然пјҢж №жң¬жІЎжғіиҝҮиҰҒеҮәд№ҰгҖӮеҶҷеҲ°еӣӣдә”еҚҒдёӘе°Ҹж®өеӯҗж—¶пјҢжқҘиҘҝи—ҸеҮәе·®зҡ„еҢ—дә¬зҡ„и—Ҹж–ҮеҢ–зҲұеҘҪиҖ…иӢұж–№ж•ҷжҺҲзңӢеҲ°дәҶпјҢеӨ§дёәжғҠе–ңпјҢз”ҡиҮіиҜҙиҝҷз®ҖзӣҙжҳҜеӨ©жүҚд№ӢдҪңпјҢеҳұе’җжҲ‘дёҖе®ҡиҰҒеҮәд№ҰпјҢиҖҢдё”иҰҒзҝ»иҜ‘жҲҗиӢұж–ҮпјҢиҝҳиҰҒй…ҚеӣҫгҖӮд»–иҜҙпјҢжҲ‘жқҘз»ҷдҪ й…ҚеӣҫпјҢи®©жҲ‘еҘіе„ҝжқҘз»ҷдҪ зҝ»иҜ‘иӢұж–ҮгҖӮж•ҙж•ҙдёҖдёӘеҶ¬еӨ©пјҢ他们зҲ¶еҘідҝ©зҡ„дёҡдҪҷж—¶й—ҙе…ЁйғЁиҙ№еңЁиҝҷ件дәӢдёҠгҖӮ“е…¶дёӯеӨ§йғЁеҲҶеҶ…е®№еңЁгҖҠдәәж°‘ж–ҮеӯҰгҖӢжқӮеҝ—2015е№ҙ第3жңҹдёҠеҸ‘иЎЁиҝҮгҖӮиҝҳжңүеҚҒжңҲж–ҮиүәеҮәзүҲзӨҫжҖ»зј–иҫ‘йҹ©ж•¬зҫӨгҖҒеҚҒжңҲж–ҮеҢ–е…¬еҸёзҡ„йҷҲжҳҺдҝҠйғҪжҜ”жҲ‘жң¬дәәжӣҙзңӢеҘҪиҝҷдәӣж–Үеӯ—пјҢеҰӮжһңдёҚжҳҜиҝҷж ·пјҢж №жң¬е°ұжІЎжңүиҝҷжң¬д№ҰгҖӮ
и—Ҹж–Үзҝ»иҜ‘еӨ®еҳҺзҺӣпјҢжҳҜжҲ‘зҡ„и—Ҹж–ҮиҖҒеёҲпјҢд№ҹжҳҜжҲ‘зҡ„е…»еҘігҖӮеҘ№зҲ¶дәІж¬Ўд»ҒжӢүиҫҫжҳҜжҲ‘еңЁи—ҸеҢ—ж—¶зҡ„еҘҪжңӢеҸӢпјҢеҸҜжғңиӢұе№ҙж—©йҖқгҖӮд»–дёҙз»ҲеүҚпјҢжҲ‘йЈһеҲ°жӢүиҗЁпјҢд»–жүҳеӯӨдәҺжҲ‘гҖӮжңүе…іжҲ‘дёҺеҘ№зҲ¶дәІзҡ„ж•…дәӢпјҢжҲ‘жӣҫз»ҸеҶҷиҝҮдёҖзҜҮгҖҠжӮІдјӨиҘҝи—ҸгҖӢеҸ‘иЎЁеңЁгҖҠеҚҒжңҲгҖӢжқӮеҝ—дёҠпјҢзҪ‘дёҠеҸҜд»ҘжҗңзҙўеҲ°гҖӮ
жӣҫз»Ҹзҡ„йӮЈдәӣиӢҰеҰӮд»ҠзңӢжқҘжІЎжңүзҷҪеҗғ
жҲ‘еҲҡиҝӣи—Ҹж—¶пјҢиў«еҲҶй…ҚеҲ°иҘҝи—Ҹжө·жӢ”жңҖй«ҳгҖҒжқЎд»¶жңҖдёәиү°иӢҰзҡ„и—ҸеҢ—гҖӮйӮЈйҮҢзҡ„е№іеқҮжө·жӢ”еңЁ4500зұід»ҘдёҠпјҢжңүзҡ„ең°ж–№иҫҫеҲ°5000еӨҡзұігҖӮең°еҢәиЎҢзҪІжүҖеңЁең°йӮЈжӣІй•ҮпјҢжҳҜдёҖдёӘеҸӘжңүдёҮжҠҠдәәзҡ„е°Ҹй•ҮпјҢдёӯй—ҙеҸӘжңүдёҖжқЎй©¬и·ҜгҖӮе…Ёең°еҢә9дёӘеҺҝеӨ„пјҢ40дёҮе№іж–№е…¬йҮҢпјҢеҸӘжңү20еӨҡдёҮдәәгҖӮжҲ‘еҲ°иҝҮи—ҸеҢ—еҮ д№ҺжүҖжңүзҡ„ең°ж–№пјҢйўҶеҸ—иҝҮйЈҺйӣӘгҖҒжү¬жІҷгҖҒдёҘеҜ’е’ҢйҘҘйҘҝпјҢдҪҶйӮЈж—¶еҸӘжңүдәҢеҚҒеӨҡеІҒпјҢ并没жңүи§үеҫ—зү№еҲ«иү°иӢҰгҖӮй«ҳеҜ’зјәж°§жҳҜе®ўи§ӮеӯҳеңЁпјҢдҪҶдәәйҷ…е…ізі»йқһеёёеҘҪпјҢж°‘ж—Ҹе…ізі»йқһеёёеҘҪпјҢдёҚеҗҢж°‘ж—Ҹзҡ„еҗҢдәӢеңЁдёҖиө·пјҢж №жң¬е°ұдёҚеҲҶд»Җд№Ҳж°‘ж—ҸпјҢдёҖиө·е·ҘдҪңпјҢдёҖиө·з”ҹжҙ»пјҢиӢҰдёӯжңүд№җпјҢд№җеңЁе…¶дёӯгҖӮжҲ‘еҗҺжқҘеӨҡж¬ЎеӣһеҲ°иҝҮйӮЈжӣІпјҢеҺ»е№ҙиҝҳеӣһеҺ»иҝҮпјҢзҺ°еңЁе·Із»ҸйўҮ具规模зҡ„дёҖеә§еҹҺеёӮдәҶпјҢжңүи¶…еёӮгҖҒе®ҫйҰҶгҖҒй…’еҗ§гҖҒжӯҢеҺ…гҖҒиҮӘз”ұеёӮеңәпјҢдёҖеә”дҝұе…ЁпјҢиҝһиҝӣеҹҺзҡ„зү§ж°‘д№ҹдәәжүӢдёҖйғЁжүӢжңәпјҢиҖҢеҪ“ж—¶иҝһдёҖ家йҘӯйҰҶйғҪжІЎжңүгҖӮжҲ‘еҲ°йӮЈжӣІй•ҮиҘҝеұұзҡ„еў“ең°еҺ»жӢңи°’йҖқеҺ»зҡ„жңӢеҸӢпјҢзңӢзқҖиҝҷеә§ж–°е…ҙзҡ„еҹҺеёӮпјҢжіӘжөҒж»ЎйқўгҖӮдёҖдҪҚи—Ҹж—ҸиҖҒеҸӢеҜ№жҲ‘иҜҙпјҢдҪ 们йӮЈж—¶еҖҷеӨҡд№Ҳиү°иӢҰе•ҠпјҒзҺ°еңЁзҡ„жқЎд»¶иҝҷд№ҲеҘҪпјҢдҪ 们еҸ—зҡ„иӢҰд№ҹеҖјдәҶпјҒеҰӮжһңжІЎжңүд»ҠеӨ©зҡ„еҸ‘еұ•пјҢдҪ 们йӮЈж—¶зҡ„иӢҰдёҚжҳҜзҷҪеҗғдәҶеҗ—пјҹиҝҷиҜқи®©жҲ‘еҫҲж„ҹеҠЁгҖӮ
笔尖зҡ„иҮӘ然жөҒж·Ңз”ҹжҲҗзҫҺеҰҷзҡ„ж–Үеӯ—
зҡ„зЎ®пјҢеғҸеҫҲеӨҡдәәдёҖж ·пјҢеңЁйқ’е№ҙж—¶д»ЈйғҪжңүиҝҮж–ҮеӯҰжўҰпјҢжҲ‘д№ҹеҶҷиҝҮдёҖдәӣе…ідәҺи—ҸеҢ—йўҳжқҗзҡ„иҜ—жӯҢгҖҒе°ҸиҜҙгҖӮдёҠдё–зәӘе…«еҚҒе№ҙд»Јж¶ҢеҠЁзҡ„ж–ҮеӯҰж–°жҪ®пјҢд№ҹжіўеҸҠеҲ°и—ҸеҢ—иҚүеҺҹгҖӮи®°еҫ—еҪ“ж—¶пјҢеңЁдёҖй—ҙеңҹеқҜеұӢеӯҗйҮҢпјҢзғ§зқҖзүӣзІӘзҒ«пјҢе°ұзқҖиңЎзғӣе…үпјҢиҜ»еҲ°жңҖж–°зҡ„ж–ҮеӯҰдҪңе“ҒпјҢж„ҹеҸ—зқҖдёҖдёӘжҝҖеҠЁдәәеҝғзҡ„ж—¶д»Јзҡ„еҲ°жқҘгҖӮеӣ дёәиҮӘе·ұж–ҮеӯҰеӨ©иөӢдёҚеӨҹпјҢд№ҹеӣ дёәе‘Ҫиҝҗзҡ„йҳҙе·®йҳій”ҷпјҢеҗҺжқҘзҰ»ж–ҮеӯҰи¶Ҡиө°и¶ҠиҝңдәҶгҖӮиҝҷжң¬е°Ҹд№ҰпјҢжң¬дёҚжҳҜдёәеҲӣдҪңиҖҢеҲӣдҪңзҡ„пјҢд№ҹдёҚжҳҜиҷҡжһ„зұ»ж–ҮеӯҰдҪңе“ҒпјҢеҮәд№Ұе®Ңе…ЁжҳҜдёҖдёӘж„ҸеӨ–гҖӮ
гҖҖгҖҖеңЁи—ҸеҢ—йӮЈеҚҒдәҢе№ҙпјҢжҲ‘д»Һд№ЎеҲ°еҺҝгҖҒеҶҚеҲ°ең°еҢәпјҢж•…дәӢеӨӘеӨҡдәҶпјҢеҶҷдёҖеҚғдёӘе°Ҹж®өеӯҗд№ҹеҶҷдёҚе®ҢгҖӮеӣ дёәжҲ‘дёҚжҳҜдёәдәҶеҶҷеӣһеҝҶеҪ•пјҢиҖҢжҳҜдёәдәҶиҜӯиЁҖеӯҰд№ пјҢжүҖд»ҘпјҢеҸӘиғҪз”ЁжңҖз®Җзҹӯзҡ„ж–Үеӯ—пјҢеҶҷйӮЈдәӣжңҖж—Ҙеёёзҡ„дәӢгҖӮеҰӮжһңеҶҷй•ҝдәҶпјҢеҶҷеӨҡдәҶпјҢеҶҷеӨҚжқӮдәҶпјҢзҝ»иҜ‘жҲҗи—Ҹж–Үе°ұжҜ”иҫғйҡҫпјҢеӯҰд№ иө·жқҘе°ұжӣҙеӣ°йҡҫдәҶгҖӮиҝҷж ·пјҢжҲ‘ж №жң¬жІЎжғіеҶҷд»Җд№Ҳй«ҳеӨ§дёҠзҡ„дёңиҘҝпјҢжғіиө·дёҖеҲҷе°ұеҶҷдёҖеҲҷпјҢйӮЈдәӣд»ҘеҫҖзҡ„дәәе’ҢдәӢж¶ҢдёҠеҝғеӨҙпјҢдҪҶжҲ‘еҸӘиғҪжҢ‘жңҖз®ҖеҚ•зҡ„еҶҷгҖӮ
гҖҖ еҶҷдёҖеҲҷпјҢе°ұдәӨз»ҷеҘіе„ҝзҝ»иҜ‘дёҖеҲҷпјҢ第дәҢеӨ©ж—©дёҠе°ұеҲ°жӢүиҗЁжІіиҫ№еҺ»жң—иҜ»иғҢиҜөи—Ҹж–ҮгҖӮе°Ҫз®ЎжҲ‘иҝҷд№ҲеҠӘеҠӣпјҢи—ҸиҜӯж–ҮиҝҳжҳҜжІЎжңүеӯҰеҘҪпјҢжңҖеӨҡд№ҹе°ұжҳҜеҲқе°ҸзЁӢеәҰгҖӮеӯҰд№ иҜӯиЁҖжҳҜиҰҒеӨ©иөӢзҡ„пјҢжҲ‘жІЎиҝҷеӨ©иөӢпјҢеҸӘиғҪйқ жңҖз¬Ёзҡ„еҠһжі•гҖӮжҲ‘еҶҚеҠӘеҠӣд№ҹиҫҫдёҚеҲ°з”Ёи—Ҹж–ҮеҶҷдҪңзҡ„ж°ҙе№ігҖӮзӣёеҸҚпјҢи—Ҹж—ҸеҗҢиғһеӯҰд№ жұүиҜӯиғҪеҠӣеҫҲејәпјҢжҺҢжҸЎжұүж–Үж°ҙе№іеҫҲй«ҳгҖӮжҲ‘и®ӨиҜҶзҡ„дёҖдәӣи—Ҹж—ҸжңӢеҸӢгҖҒзү№еҲ«жҳҜи—Ҹж—ҸиҜ—дәәе’ҢдҪң家пјҢ他们用жұүиҜӯеҶҷдҪңпјҢжҖқз»ҙж–№ејҸе’ҢиҜӯиЁҖдҪҝз”Ёж–№ејҸеҫҲеҘҮжҖӘпјҢжңүдёҖз§Қзү№еҲ«зҡ„ж„ҹи§үгҖӮиҷҪ然用зҡ„жҳҜжұүж–ҮпјҢеҸҜжҲ‘们жұүж—ҸдәәеҚҙжҖҺд№Ҳд№ҹеҶҷдёҚеҮәйӮЈз§Қе‘іе„ҝжқҘгҖӮ
е…¶е®һйӮЈдәӣеҫҖдәӢд»ҚеңЁдј йҖ’并жңӘиҝңеҺ»
дёҚдёәеҲӣдҪңзҡ„еҲӣдҪңжҳҜж„үеҝ«зҡ„гҖӮжҲ‘жңүе№ёйҒҮеҲ°дәҶйӮЈд№ҲеӨҡе–„иүҜзҡ„дәә们пјҢиҮід»ҠеҝҳдёҚдәҶйӮЈдәӣз»ҷжҲ‘е…іеҝғгҖҒеё®еҠ©е’ҢжҒ©жғ зҡ„дәә们гҖӮжӣҫз»ҸеҺ»жүҫиҝҮйӮЈдёӘжҠҠжҲ‘зҡ„еҸҢи„ҡжҡ–еңЁжҖҖйҮҢзҡ„иҖҒйҳҝеҰҲпјҢеҘ№е·Із»ҸеҺ»дё–гҖӮйӮЈдёӘйӘӮжҲ‘е…¶е®һеҫҲе–ңж¬ўжҲ‘зҡ„д№Ұи®°е·Із»ҸйҖҖдј‘еӨҡе№ҙпјҢиҝҳжҖ»жҠұжӯүең°иҜҙиҮӘе·ұи„ҫж°”дёҚеҘҪгҖӮйӮЈдёӘж•ҷжҲ‘еҒҡй…ёеҘ¶зҡ„еӨ§е§җпјҢеүҚдёҚд№…иҝҳиҜ·жҲ‘еҲ°еҘ№е®¶еҒҡе®ўгҖӮжҲ‘еҺ»е№ҙеҠһзҗҶе®ҢйҖҖдј‘жүӢз»ӯеҗҺпјҢдё“зЁӢеҲ°жҲ‘е·ҘдҪңиҝҮзҡ„еҳүй»ҺеҺҝйәҰең°еҚЎеҺ»зңӢжңӣйӮЈйҮҢзҡ„зү§ж°‘д№ЎдәІ……жңүзҡ„еҫҖдәӢпјҢиҮӘе·ұжғіиө·жқҘйғҪеҘҪ笑пјҢжҲ‘зҗҶеҸ‘ж—¶жҖ»жғіиө·и®©жҲ‘зҗҶеҸ‘зҡ„дә‘зҷ»е•ҰпјӣжҲ‘еӨұзң ж—¶еҗғе®үзң иҚҜд№ҹдјҡжғіиө·йӮЈдҪҚй”ҷжҠҠе®үзң иҚҜеҪ“ж„ҹеҶ’иҚҜеҗғзҡ„иҖҒдәәгҖӮжҲ‘жҜҸеҶҷдёҖеҲҷе°Ҹж•…дәӢдәӨз»ҷжҲ‘еҘіе„ҝзҝ»иҜ‘ж—¶пјҢеҘ№жҖ»и§үеҫ—иҝҷдәӣж•…дәӢзҰ»еҘ№йӮЈд№ҲйҒҘиҝңиҖҢеҸҲдәІиҝ‘гҖҒйӮЈд№ҲйҷҢз”ҹиҖҢеҸҲжё©жҡ–пјҢжңүж—¶еҖҷпјҢеҘ№зҝ»иҜ‘ж—¶д№ҹдёҚзҰҒ笑еҮәеЈ°жқҘгҖӮйӮЈдәӣж•…дәӢеҸ‘з”ҹж—¶пјҢеҘ№зҲ¶дәІд№ҹе°ұеҘ№зҺ°еңЁиҝҷд№ҲеӨ§е№ҙйҫ„гҖӮ
гҖҖ жҲ‘еңЁеҢ—дә¬е·ҘдҪңж—¶пјҢжҜҸе№ҙйғҪдјҡеӣһеҲ°иҘҝи—ҸпјҢжқҘзңӢзңӢиҝҷйҮҢзҡ„жңӢеҸӢпјҢд№ҹдјҡеңЁеҢ—дә¬жҺҘеҫ…жқҘиҮӘиҘҝи—Ҹзҡ„жңӢеҸӢгҖӮжңүдёҖе№ҙпјҢеҘіе„ҝеҲ°еҢ—дә¬иҝҮжҳҘиҠӮпјҢжҲ‘们еңЁеҢ—дә¬еҮәзүҲйӣҶеӣўзҡ„жҳҘиҠӮиҒ”ж¬ўдјҡдёҠдёҖеҗҢз”Ёи—ҸиҜӯжј”е”ұгҖҠжҖқеҝөгҖӢпјҢи®©еҗҢдәӢ们ж„ҹеҠЁдёҚе·ІгҖӮеҸҜиғҪеӣ дёәжҲ‘еңЁиҘҝи—Ҹе·ҘдҪңиҝҮзҡ„зјҳж•…пјҢеҗҢдәӢ们еҜ№иҘҝи—Ҹйўҳжқҗзҡ„д№ҰзЁҝд№ҹж јеӨ–е…із…§гҖӮеҠ еӨ®иҘҝзғӯзҡ„гҖҠиҘҝи—ҸжңҖеҗҺзҡ„й©®йҳҹгҖӢзҡ„еҮәзүҲе°ұжңүиҝҷж ·зҡ„иғҢжҷҜгҖӮиҝҷйғЁд№ҰеҮәзүҲеҗҺпјҢиҺ·еҫ—дәҶйІҒиҝ…ж–ҮеӯҰеҘ–пјҢиҝҷжҳҜи—Ҹж—ҸдҪң家第дёҖж¬ЎиҺ·еҫ—иҝҷдёӘеҘ–йЎ№пјҢеҸҜжғңеҠ еӨ®иҘҝзғӯжІЎжңүиғҪеӨҹдәІиҮӘжӢҝеҲ°иҺ·еҘ–иҜҒд№Ұе°ұдёҺдё–й•ҝиҫһдәҶгҖӮеҠ еӨ®еҶҷзҡ„пјҢзҡ„зЎ®жҳҜиҘҝи—ҸжңҖеҗҺзҡ„й©®йҳҹпјҢеӣ дёәд»ҺдёҠдё–зәӘд№қеҚҒе№ҙд»ЈжұҪиҪҰиҝӣе…Ҙзү§ж°‘家еәӯд№ӢеҗҺпјҢз”ЁзүҰзүӣй©®иҝҗиҝҷз§ҚеҸӨиҖҒзҡ„еҠідҪңж–№ејҸе°ұж¶ҲеӨұдәҶпјҢжҲ‘们дёәзӨҫдјҡзҡ„еҸ‘еұ•иҖҢж¬ўж¬Јйј“иҲһпјҢдҪҶжҲ‘们йңҖиҰҒдҝқеӯҳиҝҷз§Қж–ҮеҢ–и®°еҝҶгҖӮеҠ еӨ®зҡ„иҝҷжң¬д№ҰпјҢзҺ°еңЁдҪңдёәиҘҝи—ҸзүҰзүӣеҚҡзү©йҰҶзҡ„и—Ҹе“Ғеұ•еҮәгҖӮ
йҡҸзқҖиҘҝи—ҸзӨҫдјҡзҡ„еҸ‘еұ•пјҢи¶ҠжқҘи¶ҠеӨҡзҡ„дәәжқҘеҲ°иҘҝи—Ҹж—…жёёгҖҒз»Ҹе•ҶгҖҒе·ҘдҪңгҖҒйЈҳжіҠе’Ңз”ҹжҙ»пјҢеҜ№дәҺиҘҝи—Ҹзҡ„и®ӨиҜҶд№ҹжӣҙдёәеӨҡе…ғгҖӮж’ҮејҖйӮЈдәӣж•…ж„Ҹ“зҘһз§ҳеҢ–”е’Ң“еҰ–йӯ”еҢ–”дёҚиҜҙпјҢжҲ‘们жҜҸдёӘдәәеҜ№дәҺиҘҝи—ҸпјҢйғҪжңүиҮӘе·ұдёҚеҗҢзҡ„и®ӨиҜҶгҖҒдёҚеҗҢзҡ„е®ЎзҫҺи§’еәҰгҖӮжҲ‘зҡ„гҖҠи—ҸеҢ—еҚҒдәҢе№ҙгҖӢд№ҹеҸӘжҳҜе…¶дёӯдёҖдёӘи§’еәҰгҖӮжҲ‘жІЎжңүйҖүжӢ©е®ҸеӨ§еҸҷдәӢпјҢд№ҹжІЎжңүйҖүжӢ©зҰ»еҘҮиҷҡжһ„пјҢжҲ‘еҸӘжҳҜдёәдәҶиҜӯиЁҖеӯҰд№ пјҢеҶҷдәҶдёҖдёІе°Ҹж•…дәӢпјҢеҰӮжһңиҜҙиҝҳжңүдёҖдәӣд»·еҖјзҡ„иҜқпјҢйӮЈе°ұжҳҜе®ғжҳҜзңҹе®һзҡ„пјҢжҳҜжҲ‘дәІеҠӣдәІдёәдәІй—»дәІи§Ғзҡ„иҖҢе·ІгҖ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