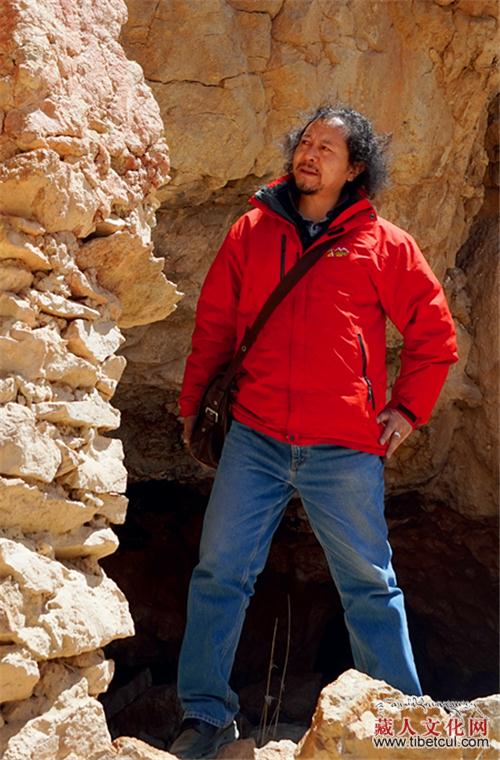
“дёҖдёӘдҪңжӣІе®¶еҝ…йЎ»йӣҶдёӯзІҫеҠӣеҒҡиҮӘе·ұиғҪеҒҡзҡ„дәӢжғ…пјҢдёәеӣҪ家е’Ңж°‘ж—ҸжүҝжӢ…иҮӘе·ұиҜҘжүҝжӢ…зҡ„иҙЈд»»пјҢи®©дј з»ҹж–ҮеҢ–еҫ—еҲ°дј жүҝгҖҒи®©еҪ“д»ЈиүәжңҜеҫ—еҲ°еҸ‘еұ•гҖӮ”
гҖҖгҖҖж—¶е…үеҖ’жөҒ45е№ҙпјҢи§үеҳҺиҝҳеҸӘжҳҜиҘҝи—ҸеҪ“йӣ„иҚүеҺҹдёҠзҡ„дёҖеҗҚж”ҫзүӣеЁғпјҢйҹід№җеҗҜи’ҷе°ұжҳҜе”ұдј з»ҹзҡ„зү§жӯҢгҖҒи·ідј з»ҹзҡ„жһңи°җпјҢеҪ“ж—¶зҡ„е°ҸеӯҰиҝҳжІЎжңүејҖи®ҫдё“й—Ёзҡ„йҹід№җиҜҫгҖӮгҖҖгҖҖ
гҖҖгҖҖеҰӮд»ҠпјҢ53еІҒзҡ„и§үеҳҺе·ІжҲҗдёәдёӯеӣҪйҰ–дҪҚдҪңжӣІдё“дёҡеҚҡеЈ«еҗҺпјҢд№ҹжҳҜдёӯеӣҪ第дёҖдҪҚи—Ҹж—Ҹйҹід№җеӯҰзЎ•еЈ«е’ҢеҚҡеЈ«пјҢд»–зҡ„еҚҡеЈ«еӯҰдҪҚи®әж–ҮгҖҠиҘҝи—Ҹдј з»ҹйҹід№җзҡ„з»“жһ„еҪўжҖҒз ”з©¶гҖӢиў«иҜ„дёә2007е№ҙеәҰе…ЁеӣҪдјҳз§ҖеҚҡеЈ«еӯҰдҪҚи®әж–ҮпјҢжҳҜиҝ„д»Ҡе…ҘйҖү“е…ЁеӣҪзҷҫзҜҮдјҳеҚҡ”зҡ„е”ҜдёҖдёҖзҜҮдҪңжӣІеӯҰ科зҡ„и®әж–ҮгҖӮзҺ°еңЁиҘҝи—ҸеӨ§еӯҰиүәжңҜеӯҰйҷўд»»ж•ҷзҡ„и§үеҳҺпјҢдёҚд»…еңЁиҘҝи—ҸејҖеҲӣдәҶ“дҪңжӣІдёҺдҪңжӣІжҠҖжңҜзҗҶи®ә”дё“дёҡпјҢиҝҳйҖҡиҝҮдёҚж–ӯзҡ„ж•ҷеӯҰдёҺеҲӣдҪңпјҢдёәдәӨе“Қд№җиҝҷдёҖйҹід№җдҪ“иЈҒеўһж·»дәҶжө“йғҒзҡ„йқ’и—Ҹй«ҳеҺҹзү№иүІгҖӮгҖҖ
гҖҖгҖҖ“еӯҰд№ йҹід№җзҡ„дәәеҫҲеӨҡпјҢдҪҶжҠҠйҹід№җдҪңдёәиҒҢдёҡеқҡжҢҒдёӢеҺ»зҡ„дәәеҚҙдёҚеӨҡпјҢеӨ©еҲҶдёҚжҳҜдё»иҰҒеҺҹеӣ пјҢе…ій”®жҳҜеқҡжҢҒпјҢеқҡе®ҲдёҺйҹід№җз»“дёӢзҡ„зјҳеҲҶпјҢжүҚиғҪеҲӣе°ұзңҹжӯЈзҡ„дјҳеҠҝгҖӮ”и§үеҳҺиҜҙгҖӮгҖҖгҖҖ
“жҲ‘иӮҜе®ҡеңЁеӯҰж ЎйҮҢж•ҷд№Ұ”гҖҖгҖҖ
гҖҖгҖҖ1995е№ҙи§үеҳҺд»Һеӣӣе·қйҹід№җеӯҰйҷўзЎ•еЈ«з ”究з”ҹжҜ•дёҡпјҢд»–з»ҷиҮӘе·ұеҲ¶е®ҡзҡ„иҒҢдёҡ规еҲ’и®©иә«иҫ№дәәеӨ§еҗғдәҶдёҖжғҠгҖӮд»–жІЎжңүз•ҷеңЁй«ҳж ЎпјҢиҖҢжҳҜеҲ°дәҶиҘҝи—ҸиүәжңҜеӯҰж ЎдёҖжүҖдёӯдё“д»»ж•ҷгҖӮйӮЈдёҖе№ҙпјҢд»–еқҗзқҖеӨ§е·ҙиҪҰеҲ°ж—Ҙе–ҖеҲҷгҖҒеұұеҚ—гҖҒжһ—иҠқгҖҒйӮЈжӣІпјҢеҝҷдәҶж•°е‘ЁпјҢжӢӣдәҶ6дёӘеҲқдёӯжҜ•дёҡзҡ„дҪңжӣІдё“дёҡеӯҰз”ҹпјҢеӯҰеҲ¶6е№ҙпјҢдҪңжӣІгҖҒе’ҢеЈ°гҖҒжӣІејҸгҖҒеҜ№дҪҚгҖҒй…ҚеҷЁзӯүиҜҫзЁӢйғҪз”ұд»–дёҖдәәж•ҷжҺҲгҖӮгҖҖгҖҖ
гҖҖгҖҖи§үеҳҺиҜҙпјҢдҪңжӣІдё“дёҡзҡ„еӯҰз”ҹдёҖиҲ¬йғҪжӢӣеҫ—еҫҲе°‘пјҢиҝҷжҳҜз”ұеӯҰ科规еҫӢеҶіе®ҡзҡ„гҖӮеӣ дёәиҖҒеёҲйңҖиҰҒдёҖеҜ№дёҖж•ҷеҜјпјҢиҖҢдё”йңҖиҰҒжҢүз…§еҹ№е…»ж–№жЎҲдёҖжӯҘжӯҘиҗҪе®һгҖӮ20еӨҡе№ҙеүҚжӢӣз”ҹж—¶иҝҳеҒҡдёҚеҲ°зҗҶи®әиҖғиҜ•пјҢдё»иҰҒжҳҜиҖғжҹҘеӯҰз”ҹеҜ№йҹід№җзҡ„ж•Ҹж„ҹеәҰгҖҒйҖ»иҫ‘жҖқз»ҙд»ҘеҸҠеҲҶжһҗеҲӨж–ӯиғҪеҠӣпјҢзЎ®е®һжңүеҫҲеӨҡеӣ°йҡҫе’ҢжҢ‘жҲҳгҖӮгҖҖгҖҖ
гҖҖгҖҖе°ұиҝһ“дҪңжӣІ”иҝҷ件дәӢеңЁиҘҝи—Ҹд№ҹжҳҜеҗҺжқҘжүҚжңүзҡ„гҖӮеҪ“д»Ҡдә”зәҝи°ұе·ІжҲҗдёәе…Ёдё–з•Ңз»қеӨ§еӨҡж•°еӣҪ家йҹід№җж•ҷиӮІдҪ“еҲ¶дёӯйҮҮз”Ёзҡ„и®°и°ұзі»з»ҹгҖӮдҪҶжӯӨеүҚпјҢиҘҝи—Ҹж°‘й—ҙйҹід№җзҡ„дј жүҝдё»иҰҒйҮҮз”ЁдёҖдәӣзұ»дјјеҸЈиҜҖзҡ„ж–№ејҸеҜјеј•йҹід№җе®һи·өпјҢеҰӮйҳҝеҗүжӢүе§ҶжҲҸеү§иүәжңҜиЎЁжј”дёӯзҡ„йј“й’№еҝөиҜҖзӯүгҖӮеҲ°дәҶ20дё–зәӘеҲқд»ҘеҗҺпјҢжӢүиҗЁ“еӣҠзҺӣеҗүеәҰ”иЎҢдјҡзҡ„иүәдәәеңЁиЎЁжј”“е Ҷи°җ”е’Ң“еӣҠзҺӣ”жӯҢиҲһйҹід№җж—¶д№ҹжңүдҪҝз”Ёе·Ҙе°әи°ұзҡ„з»ҸеҺҶпјҢдҪҶеҪұе“ҚдёҚеӨ§пјҢиҖҢиҘҝи—Ҹе®—ж•ҷйҹід№җе’Ңе®«е»·йҹід№җпјҢиҷҪ然жңүдј з»ҹзҡ„и®°и°ұж–№ејҸпјҢдҪҶйғҪжІЎжңүдә”зәҝи°ұйӮЈд№Ҳе®Ңе–„пјҢдёҚе…·жңүи¶…и¶Ҡзү№е®ҡж–ҮеҢ–иҢғз•ҙзҡ„йҖҡз”ЁжҖ§гҖӮгҖҖгҖҖ
гҖҖгҖҖзі»з»ҹеӯҰд№ дәҶйҹід№җеҲӣдҪңзҗҶи®әд№ӢеҗҺпјҢи§үеҳҺи§үеҫ—иҘҝи—Ҹзҡ„йҹід№җиҰҒиө°еҗ‘дё–з•ҢпјҢе…ій”®иҝҳжҳҜиҰҒеҠ ејәдәәжүҚеҹ№е…»гҖӮ“дәәжүҚеҹ№е…»дёҚжҳҜдёҖеӨ©дёӨеӨ©зҡ„дәӢпјҢжҳҜжҜ•з”ҹжҠ•е…Ҙзҡ„дәӢжғ…пјҢд»Җд№Ҳж—¶еҖҷиғҪеҹ№е…»еҮәдјҳз§Җзҡ„дәәжүҚиҰҒжңүй•ҝиҝңзҡ„规еҲ’пјҢжүҖд»ҘжҲ‘и§үеҫ—иҮӘе·ұиӮҜе®ҡжҳҜйҖүжӢ©ж•ҷд№ҰгҖӮ”и§үеҳҺиҜҙгҖӮгҖҖгҖҖ
гҖҖгҖҖ“еҰӮжһңжҲ‘еҲ°ж–ҮиүәеӣўдҪ“пјҢжңүеҫҲеӨҡеә”жҖҘзҡ„д»»еҠЎйңҖиҰҒе®ҢжҲҗпјҢе°ұеҫҲйҡҫйқҷдёӢеҝғжқҘжҗһж•ҷеӯҰгҖӮжҲ‘жңүдёӘж·ұеҲ»зҡ„ж„ҹеҸ—пјҢдёҖдёӘдҪңжӣІе®¶еҝ…йЎ»йӣҶдёӯзІҫеҠӣеҒҡиҮӘе·ұиғҪеҒҡзҡ„дәӢжғ…пјҢдёәеӣҪ家е’Ңж°‘ж—ҸжүҝжӢ…иҮӘе·ұиҜҘжүҝжӢ…зҡ„иҙЈд»»пјҢи®©дј з»ҹж–ҮеҢ–еҫ—еҲ°дј жүҝгҖҒи®©еҪ“д»ЈиүәжңҜеҫ—еҲ°еҸ‘еұ•”пјҢд»–иҜҙгҖӮгҖҖгҖҖ
гҖҖгҖҖеӣӣе·қйҹід№җеӯҰйҷўж•ҷжҺҲйӮ№еҗ‘е№іеқҰиЁҖпјҢи§үеҳҺзҡ„еқҡжҢҒд»Өд»–йқһеёёеҗғжғҠгҖӮ“иҝҮеҺ»еҮ еҚҒе№ҙпјҢд»–й”ІиҖҢдёҚиҲҚеқҡжҢҒеӯҰд№ жҳҜйқһеёёдёҚе®№жҳ“зҡ„гҖӮд»–жӣҫз»ҸеҪ“иҝҮиҘҝи—ҸеӨ§еӯҰиүәжңҜеӯҰйҷўеүҜйҷўй•ҝпјҢеҗҺжқҘиҫһжҺүдәҶиЎҢж”ҝиҒҢеҠЎпјҢдё“е®Ҳж•ҷеӯҰйҳөең°гҖӮдёәдәҶи—Ҹж—Ҹйҹід№җдәӢдёҡжүҖеұ•зҺ°еҮәзҡ„敬дёҡе’ҢиҜҡжҒіпјҢеҫҲд»ӨдәәдҪ©жңҚгҖӮ”йӮ№еҗ‘е№іиҜҙгҖӮгҖҖгҖҖ
гҖҖгҖҖи®°иҖ…дәҶи§ЈеҲ°пјҢи§үеҳҺжңҖж—©жӢӣ收зҡ„6еҗҚеӯҰз”ҹдёӯпјҢжңү4еҗҚиҖғдёҠдәҶдёӯеӨ®йҹід№җеӯҰйҷўдҪңжӣІзі»жң¬з§‘пјҢиҝҷеә§иүәж ЎеҗҺжқҘд№ҹ被并е…ҘиҘҝи—ҸеӨ§еӯҰгҖӮи§үеҳҺе…ҲеҗҺеҲ°дёҠжө·йҹід№җеӯҰйҷўж”»иҜ»еҚҡеЈ«еӯҰдҪҚгҖҒеҲ°дёӯеӨ®йҹід№җеӯҰйҷўеҒҡеҚҡеЈ«еҗҺпјҢеҮәз«ҷеҗҺеӣһиҘҝи—ҸеӨ§еӯҰд»»ж•ҷгҖӮиҝ„д»ҠпјҢд»–е·Іеҹ№е…»дәҶ5еұҠжң¬з§‘з”ҹе’Ң7еұҠзЎ•еЈ«з”ҹгҖӮиҝҷдәӣжҜ•дёҡзҡ„еӯҰз”ҹе·Із»ҸжҲҗдёәиҘҝи—Ҹйҹід№җеҲӣдҪңйўҶеҹҹзҡ„дёӯеқҡеҠӣйҮҸпјҢиҖҢиҘҝи—ҸеӨ§еӯҰ“дҪңжӣІдёҺдҪңжӣІжҠҖжңҜзҗҶи®ә”дё“дёҡд№ҹе·ІеҪўжҲҗдёҖж”ҜеҗҲзҗҶзҡ„еёҲиө„йҳҹдјҚпјҢеӯҰ科еҸ‘еұ•е…·еӨҮдәҶиүҜеҘҪеҹәзЎҖгҖӮгҖҖгҖҖ
гҖҖгҖҖ“жңӘжқҘеҸ‘еұ•зҡ„е…ій”®иҝҳеңЁдәҺдәәжүҚеҹ№е…»иҙЁйҮҸгҖҒеҲӣдҪңжҲҗжһңд»ҘеҸҠиҖҒеёҲзҡ„еӯҰжңҜжҲҗжһңгҖӮ”и§үеҳҺиҜҙгҖӮгҖҖгҖҖ
ж·ұиҖ•и—Ҹйҹід№җгҖҖгҖҖ
гҖҖгҖҖ2015е№ҙдә”дёҖеӣҪйҷ…еҠіеҠЁиҠӮпјҢиҝҷдёҖеӨ©пјҢи§үеҳҺиў«жҺҲдәҲ“е…ЁеӣҪе…Ҳиҝӣе·ҘдҪңиҖ…”иҚЈиӘүз§°еҸ·пјҢиҝҷжҳҜиҝ‘е№ҙжқҘиҘҝи—Ҹй«ҳж Ўзі»з»ҹиҺ·жӯӨиҚЈиӘүзҡ„第дёҖдәәгҖӮгҖҖгҖҖ
гҖҖгҖҖе§Ӣз»Ҳеқҡе®Ҳж•ҷеӯҰ第дёҖзәҝзҡ„и§үеҳҺпјҢдёҚд»…жҺўзҙўж•ҷиӮІеҲӣж–°пјҢдёҚж–ӯжҺЁеҮәж–°иҜҫзЁӢпјҢиҝҳжҢҮеҜјеӯҰз”ҹз”іжҠҘ“еӣҪ家еӨ§еӯҰз”ҹеҲӣж–°жҖ§е®һйӘҢи®ЎеҲ’”зӯүе®һи·өйЎ№зӣ®пјҢжҢҮеҜје№¶йј“еҠұеӯҰз”ҹеҲӣдёҡеҸ‘еұ•гҖӮд»–е…ҲеҗҺжүҝжӢ…дәҶ“дёӯеӣҪеҚҡеЈ«еҗҺ科еӯҰеҹәйҮ‘дёҖзӯүиө„еҠ©йЎ№зӣ®”гҖҒ“й«ҳзӯүеӯҰж Ўе…ЁеӣҪдјҳз§ҖеҚҡеЈ«еӯҰдҪҚи®әж–ҮдҪңиҖ…дё“йЎ№иө„йҮ‘иө„еҠ©йЎ№зӣ®”гҖҒж•ҷиӮІйғЁ“ж–°дё–зәӘдјҳз§ҖдәәжүҚж”ҜжҢҒи®ЎеҲ’”гҖҒ“еӣҪ家зӨҫ科еҹәйҮ‘иүәжңҜеӯҰйЎ№зӣ®”зӯүпјҢиҚЈиҺ·“иҘҝи—ҸиҮӘжІ»еҢәдјҳз§Җж•ҷеёҲ”гҖҒ“е…ЁеӣҪжЁЎиҢғж•ҷеёҲ”зӯүиҚЈиӘүз§°еҸ·гҖӮгҖҖгҖҖ
гҖҖгҖҖ“жҲ‘жң¬иҜҘдёҖдёӘдәәеңЁзү§еҢәж”ҫзү§пјҢжңҖеҗҺд»ҺдәӢйҹід№җж•ҷиӮІпјҢиҝҷжҳҜдёҖдёӘжңәзјҳпјҢйҷӨдәҶеӣҪ家зҡ„еҹ№е…»д»ҘеҸҠиҮӘе·ұд»ҺдёҚж”ҫејғеӨ–пјҢдёҖи·Ҝиө°жқҘеҫ—еҲ°дәҶеҫҲеӨҡдәәзҡ„ж”ҜжҢҒе’Ңеё®еҠ©пјҢжҲ‘зҡ„дёӘдәәдё“еңәйҹід№җдјҡе°ұжҳҜжҲ‘еҜ№зӨҫдјҡзҡ„еӣһжҠҘпјҢеёҢжңӣд»ҘжӯӨжқҘеҗ‘дё–з•Ңе‘ҲзҺ°еҪ“д»ЈиҘҝи—ҸиүәжңҜйҹід№җж•ҷиӮІзҡ„еҙӯж–°йЈҺйҮҮгҖӮ”и§үеҳҺиҜҙгҖӮгҖҖгҖҖ
гҖҖгҖҖ2016е№ҙ10жңҲ29ж—ҘпјҢи§үеҳҺзҡ„дәӨе“Қд№җдҪңе“Ғдё“еңәйҹід№җдјҡеңЁеҢ—дә¬дёӯеұұйҹід№җе ӮдёҫеҠһпјҢејҖи—Ҹж—ҸдҪңжӣІе®¶д№Ӣе…ҲжІігҖӮдёәиҝҷеңәйҹід№җдјҡжү§жЈ’зҡ„и‘—еҗҚжҢҮжҢҘ家и°ӯеҲ©еҚҺи®ӨдёәпјҢи§үеҳҺжҳҜз”ЁдәӨе“Қд№җзҡ„жҖқз»ҙеңЁеҲӣдҪңпјҢд»–зҡ„дҪңе“ҒеҫҲжңүж·ұеәҰпјҢе§Ӣз»ҲиҙҜз©ҝзқҖи—Ҹж–ҮеҢ–зҡ„зІҫй«“гҖӮгҖҖгҖҖ
гҖҖгҖҖйӮ№еҗ‘е№іжҠҠиҝҷдёӘйҹід№җдјҡз§°дёәдёҖдёӘ“ж–ҮеҢ–дәӢ件”пјҢ“д»ҺдёҖеҗҚж”ҫзҫҠеЁғжҲҗй•ҝдёәиҺ·еҫ—дҪңжӣІдё“дёҡжңҖй«ҳеӯҰдҪҚзҡ„еӯҰиҖ…пјҢиҝҷжҳҜйқһеёёеҖјеҫ—еәҶиҙәзҡ„гҖӮжҲ‘еҗ¬дәҶж•ҙеңәйҹід№җдјҡпјҢйҖҸиҝҮиҝҷдёӘйҹід№җдјҡиғҪж„ҹеҸ—еҲ°иҘҝи—ҸиүәжңҜйҹід№җзҡ„еӯҰ科е»әи®ҫж°ҙе№ігҖӮ”йӮ№еҗ‘е№іиҜҙгҖӮгҖҖгҖҖ
гҖҖгҖҖеңЁиҝҷеңәйҹід№җдјҡдёҠпјҢи§үеҳҺжңүеӣӣйғЁдҪңе“ҒдёҺи§Ӯдј—и§ҒйқўпјҢеҢ…жӢ¬еҸ—и—Ҹдј дҪӣж•ҷеҜәйҷўгҖҠеҘўж‘©д»–гҖӢеЈҒз”»еҗҜеҸ‘еҲӣдҪңзҡ„з®ЎејҰд№җеҚҸеҘҸжӣІгҖҠеҮҖз•ҢгҖӢпјҢиҝҷйғЁдҪңе“ҒйҮҮз”Ёз®ЎејҰд№җеҚҸеҘҸзҡ„еҪўејҸпјҢйҖҡиҝҮйҹід№җиҜӯиЁҖпјҢзј–з»ҮдәҶйҖҡиҫҫеҝғжҷәеҮҖз•Ңзҡ„йҹіе“ҚеӣҫжҷҜпјӣиҖҢеҸҰдёҖйғЁдҪңе“ҒгҖҠйӣҶе»“гҖӢеҲҷйҖҸиҝҮз®ЎејҰйёЈйӣҶзҡ„еЈ°е“ҚеҲӣдҪңеҮәдёҖеә§“йҹід№җеқӣеҹҺ”пјҢеңЁеҗҜиҝӘеҝғжҷәзҡ„еҗҢж—¶д№ҹиғҪи®©еҗ¬дј—ж„ҹеҸ—е…¶й—ҙзҡ„超然ж„Ҹи¶ЈгҖӮгҖҖгҖҖ
гҖҖгҖҖйӮ№еҗ‘е№іи®ӨдёәпјҢи§үеҳҺ30е№ҙеҲӣдҪңзҡ„иҝҷеӣӣйғЁдҪңе“ҒйғҪеұһдәҺдёӯгҖҒеӨ§еһӢдәӨе“ҚжҖ§дҪңе“ҒпјҢеҫҲжңүи—Ҹж–ҮеҢ–зү№иҙЁпјҢе‘ҲзҺ°дәҶи—Ҹж—Ҹж–ҮеҢ–жң¬иә«зҡ„йҹід№җйЈҺйҹөпјҢеҗҢж—¶еҸҲжңүеҫҲж·ұзҡ„е“ІзҗҶж„Ҹд№үпјҢдҪңе“ҒдҪ“зҺ°еҮәиҘҝи—Ҹж–ҮеҢ–дёҺзҺ°д»Јйҹід№җиһҚеҗҲзҡ„е“ҒиҙЁгҖӮгҖҖгҖҖ
гҖҖгҖҖ2016е№ҙ12жңҲд»ҪпјҢи§үеҳҺзҡ„еҸҰдёҖйғЁе®ӨеҶ…д№җдҪңе“ҒиҝҳеңЁжіўе…°жј”еҮәгҖӮиҷҪ然дёҚиғҪеҲ°зҺ°еңәиҒҶеҗ¬пјҢи§үеҳҺеҚҙеҜ№жј”еҮәйқһеёёиҮӘдҝЎгҖӮгҖҖгҖҖ
гҖҖгҖҖд»–иҜҙпјҡ“иҷҪ然иүәжңҜйҹід№җиө·е§ӢдәҺ欧жҙІпјҢдҪҶеҒҮеҰӮжҲ‘еңЁиҝҷ收еҲ°дёҖдёӘд»ҺзҫҺеӣҪеҜ„жқҘзҡ„дҪңе“ҒпјҢжҲ‘дёҖзӮ№йғҪдёҚдјҡеҘҮжҖӘпјӣеҗҢж ·пјҢжіўе…°зҡ„еҗ¬дј—еҗ¬еҲ°еңЁйқ’и—Ҹй«ҳеҺҹдёҠеҲӣдҪңзҡ„дәӨе“Қд№җд№ҹдёҚдјҡеҘҮжҖӘпјҢеӣ дёәеӨ§е®¶иҝҗз”Ёзҡ„йғҪжҳҜиүәжңҜйҹід№җеҲӣдҪңйҖҡз”Ёзҡ„иҜӯиЁҖпјҢеҗҢж—¶дҪңе“ҒеҸҲе…·жңүзӢ¬зү№зҡ„ең°еҹҹзү№иүІпјҢиҝҷе°ұжҳҜеҜ№иүәжңҜеӨҡж ·жҖ§зҡ„ејҳжү¬пјҒ”гҖҖгҖҖ
гҖҖгҖҖиҝ„д»ҠдёәжӯўпјҢи§үеҳҺзҡ„дҪңе“Ғе·Іе…ҲеҗҺеңЁеҸ°ж№ҫгҖҒйҰҷжёҜгҖҒж–°еҠ еқЎгҖҒж—Ҙжң¬гҖҒеҢ—зҫҺгҖҒ欧жҙІзӯүең°жј”еҮәгҖӮгҖҖгҖҖ
и—ҸеңЁе·ҘдҪңе®ӨйҮҢзҡ„жўҰгҖҖгҖҖ
гҖҖгҖҖйҷӨдәҶеҒ¶е°”и·ҹ家дәәеӣўиҒҡпјҢи§үеҳҺжҠҠж—¶й—ҙйғҪз»ҷдәҶйҹід№җпјҢд»–еңЁиҘҝи—ҸеӨ§еӯҰйӮЈй—ҙ30еӨҡе№ізұізҡ„е·ҘдҪңе®Өи§ҒиҜҒдәҶд»–зҡ„иҝҮеҫҖгҖӮгҖҖгҖҖ
гҖҖгҖҖдёҖеј д№ҰжЎҢгҖҒдёҖеҸ°з”өи„‘гҖҒдёҖжһ¶й’ўзҗҙгҖҒдёҖеҜ№йҹіе“ҚгҖҒеЎһж»ЎдәҶеҮ дёӘд№Ұжһ¶зҡ„еӣҫд№Ұе’ҢеҪұйҹіиө„ж–ҷгҖҒж—§иҙ§ж‘ҠдёҠж·ҳжқҘзҡ„еҮ жҠҠи—ӨжІҷеҸ‘жҳҜд»–е·ҘдҪңе®Өзҡ„“ж Үй…Қ”гҖӮгҖҖгҖҖ
гҖҖгҖҖиҝҷйҮҢжҳҜдёҖдёӘејҖж”ҫзҡ„иҜҫе ӮпјҢйҷӨдәҶз»ҷз ”з©¶з”ҹдёҠиҜҫпјҢеӯҰз”ҹжңүй—®йўҳзҡ„ж—¶еҖҷеҸҜд»ҘйҡҸж—¶еҲ°и®ҝпјҢдёҺиҖҒеёҲеӣҙеқҗе–қиҢ¶гҖҒдәӨжөҒгҖӮгҖҖгҖҖ
гҖҖгҖҖ“иҝҷеҮ жҠҠи—ӨжІҷеҸ‘гҖҒз”өи„‘гҖҒйҹіе“ҚйғҪжҜ”иҫғйҮҚиҰҒпјҢеӣ дёәзӣҙжҺҘи·ҹж•ҷеӯҰзӣёе…іпјҢиҝҳжңүйӮЈеј жЎҢеӯҗд№ҹеҫҲйҮҚиҰҒпјҢжңҖиҝ‘еҲӣдҪңзҡ„еҮ йғЁдҪңе“Ғзҡ„жҖ»и°ұйғҪжҳҜеңЁйӮЈйҮҢе®ҢжҲҗзҡ„гҖӮ”и§үеҳҺиҜҙгҖӮгҖҖгҖҖ
гҖҖгҖҖ3е№ҙеүҚпјҢдёҖдҪҚжҜ•дёҡз”ҹдёәи§үеҳҺиҖҒеёҲйҖҒжқҘзҺ°еңЁзҡ„йӣ…马е“Ҳйҹіе“ҚпјҢеӣ дёәд»–е®һеңЁзңӢдёҚдёӢеҺ»иҖҒеёҲжүӢйҮҢйӮЈдёӘз”ЁдәҶеҚҒеӨҡе№ҙгҖҒж—©е·Із ҙж—§дёҚе Әзҡ„з”өи„‘йҹіз®ұгҖӮгҖҖгҖҖ
гҖҖгҖҖи§үеҳҺиҮӘе·ұеҚҙдёҚд»Ҙдёә然пјҢ“е°Ҹйҹіз®ұеёҰзқҖж–№дҫҝпјҢеҶҚиҜҙжңүж—¶жҸ’дёҠиҖіжңәеҗ¬д№ҹеҫҲж–№дҫҝпјҢиҝҳдёҚдјҡе№Іжү°еҲ«дәә”гҖӮгҖҖгҖҖ
гҖҖгҖҖ1994е№ҙпјҢиҝҳеңЁеӣӣе·қйҹід№җеӯҰйҷўиҜ»з ”究з”ҹж—¶пјҢи§үеҳҺзҡ„дҪңе“ҒгҖҠж— йўҳгҖӢиҚЈиҺ·еҸ°ж№ҫзңҒз«ӢдәӨе“Қд№җеӣўз¬¬дёүеұҠеҫҒжӣІжҜ”иөӣ第дәҢеҗҚпјҢд»–з”Ё12000еӨҡе…ғзҡ„еҘ–йҮ‘еҫҲеҘўдҫҲең°д№°дәҶдёҖеҸ°з»„иЈ…з”өи„‘пјҢй…ҚеӨҮдәҶдёҖдёӘе°Ҹйҹіз®ұгҖӮ“жҗһз ”з©¶иҰҒжҹҘйҳ…иө„ж–ҷпјҢеҸ‘йӮ®д»¶дҫҝдәҺжІҹйҖҡпјҢжүҖд»Ҙе°ұжғізқҖиҰҒжңүдёӘз”өи„‘еӨҡеҘҪпјҢиҷҪ然йӮЈж—¶еҖҷй’ұдёҚеҘҪжҢЈпјҢдҪҶд№ҹдёҖзӮ№йғҪжІЎзҠ№иұ«е°ұд№°дәҶеҸ°з”өи„‘гҖӮ”и§үеҳҺиҜҙгҖӮгҖҖгҖҖ
гҖҖгҖҖеҫҲеӨҡдәәи§үеҫ—иҰҒжҗһйҹід№җеҲӣдҪңпјҢжңүдёӘи¶ҒжүӢзҡ„д№җеҷЁеҫҲйҮҚиҰҒпјҢи§үеҳҺеҚҙи§үеҫ—жңҖйҮҚиҰҒзҡ„иҝҳжҳҜдҪңжӣІиҖ…зҡ„еҶ…еҝғеҜ№йҹід№җзҡ„ж„ҹзҹҘеҠӣгҖҒеҜ№з®ЎејҰд№җзҡ„жҠҠжҺ§еҠӣгҖӮгҖҖгҖҖ
гҖҖгҖҖ“еҲӣдҪңеӨ§еһӢдәӨе“Қд№җдҪңе“ҒпјҢдёҚиғҪе…ЁйғЁеңЁд№җеҷЁдёҠйӘҢиҜҒпјҢе…ій”®жҳҜиҰҒеҹ№е…»ж•Ҹй”җзҡ„еҶ…еҝғеҗ¬и§үгҖӮ”еӨҡе№ҙжқҘпјҢи§үеҳҺжүҖжңүдҪңе“Ғзҡ„д№җи°ұйғҪжҳҜз”ЁжүӢд№ҰеҶҷгҖӮгҖҖгҖҖ
гҖҖгҖҖ40еӨҡе№ҙзҡ„жұӮеӯҰе’Ңж•ҷеӯҰз»ҸйӘҢи®©и§үеҳҺж·ұж·ұж„ҹеҲ°пјҢйҹід№җеҲӣдҪңдёҚеҸӘж¶үеҸҠж—¶й—ҙеқҗж ҮпјҢиҝҳжңүз©әй—ҙеқҗж ҮгҖӮд»–еҲ»ж„Ҹдёәе·ҘдҪңе®Өзҡ„еўҷдёҠз•ҷзҷҪпјҢд»ҘдҫҝйҡҸж—¶иғҪеңЁдёҠиҜҫж—¶жҢӮдёҠеҗ„з§Қең°еӣҫгҖӮд»–иҜҙпјҢеҰӮжһңйҹід№җдё“дёҡзҡ„еӯҰз”ҹеҜ№ең°зҗҶзҹҘиҜҶжІЎжңүжё…жҷ°еәҰпјҢ他们еҜ№йҹід№җе’Ңдәәж–ҮеҺҶеҸІзҡ„еӣһйЎҫе°ұдјҡеҸҳеҫ—жЁЎзіҠдёҚжё…пјҢжҢӮдёҠең°еӣҫе°ұдҪҝеӯҰз”ҹжңүдәҶж„ҹжҖ§и®ӨиҜҶпјҢдҫҝдәҺеӯҰз”ҹд»Һе…Ёзҗғзҡ„з»ҙеәҰејҖжӢ“иҮӘе·ұзҡ„и§ҶйҮҺгҖӮгҖҖгҖҖ
гҖҖгҖҖи§үеҳҺиҜҙпјҢд»–зҡ„жўҰжғіе°ұжҳҜжҠҠиҘҝж–№дҪңжӣІзҡ„жҠҖжі•и·ҹдёӯеӣҪдј з»ҹж–ҮеҢ–з»“еҗҲиө·жқҘпјҢйҖҡиҝҮж•ҷеӯҰз ”з©¶е’ҢеҲӣдҪңпјҢз”Ёж №жӨҚдәҺйӣӘеҹҹй«ҳеҺҹзҡ„иҘҝи—Ҹж–ҮеҢ–жқҘдё°еҜҢеҪ“д»ЈиүәжңҜйҹід№җпјҢз•ҷдёӢе…·жңүж—¶д»Јж„Ҹд№үзҡ„дҪңе“ҒпјҢдёәеҗҺжқҘдәәзҡ„еҸ‘еұ•жү“дёӢеҹәзЎҖгҖӮгҖҖгҖҖ
гҖҖгҖҖдёҺжөҒиЎҢйҹід№җзӣёжҜ”пјҢдәӨе“Қд№җдёҖеңәжј”еҮәеҫҖеҫҖиҰҒи°ғеҠЁдёҠзҷҫдәәпјҢжј”еҮәжҲҗжң¬йқһеёёй«ҳжҳӮпјҢиҝҷж„Ҹе‘ізқҖпјҢиүәжңҜйҹід№җеҲӣдҪңиҖ…жҳҜеӯӨзӢ¬зҡ„пјҢеҸҜжҳҜи§үеҳҺдҫқ然ж„ҝж„ҸдёәжӯӨеҖҫе°ҪжҜ•з”ҹд№ӢеҠӣгҖӮгҖҖгҖҖ
гҖҖгҖҖеңЁд»–зңјйҮҢпјҢиүәжңҜйҹід№җе’Ңе“ІеӯҰжҳҜжңҖеҘ‘еҗҲзҡ„дёӨдёӘйўҶеҹҹгҖӮ“з ”з©¶е“ІеӯҰзҡ„дәәпјҢд»ҺдәӢзҡ„е°ұжҳҜзәҜзІ№зҡ„зҗҶи®әз ”з©¶пјҢжІЎжңүзҗҶи®әзҡ„жҢҮеј•пјҢе®һи·өйҡҫд»ҘиҫҫеҲ°еә”жңүзҡ„й«ҳеәҰпјҢе°ұеғҸиҚЈж је’Ңеј—жҙӣдјҠеҫ·зҡ„жҲҗе°ұеңЁжҹҗз§ҚзЁӢеәҰдёҠеҲҶеҲ«д»ЈиЎЁзқҖз‘һеЈ«е’ҢеҘҘең°еҲ©еңЁе“ІеӯҰйўҶеҹҹзҡ„иҪҜе®һеҠӣпјҢиҘҝи—ҸиүәжңҜйҹід№җзҡ„еҸ‘еұ•д№ҹеҝ…е®ҡжҠҳе°„еҮәдёӯеҚҺж–ҮеҢ–зҡ„иҪҜе®һеҠӣгҖӮ”гҖҖгҖҖ
гҖҖгҖҖдёәдәҶи®©жӣҙеӨҡдәәиғҪиҒҶеҗ¬еҲ°иҘҝи—Ҹзү№иүІзҡ„дәӨе“ҚдҪңе“ҒпјҢи§үеҳҺжҠҠиҚЈиҺ·“е…ЁеӣҪзҷҫзҜҮдјҳз§ҖеҚҡеЈ«еӯҰдҪҚи®әж–ҮеҘ–”зҡ„еҘ–йҮ‘еҶҚдёҖж¬ЎзҢ®з»ҷдәҶйҹід№җпјҡеңЁеҢ—дә¬дёҫеҠһзҡ„йӮЈеңәдёӘдәәдәӨе“Қд№җдҪңе“Ғдё“еңәйҹід№җдјҡиҖ—иө„е·ЁеӨ§пјҢи®©д»–зҡ„дҪңе“Ғд»ҺжҖ»и°ұеҸҳжҲҗйҹіе“ҚпјҢжӣҙеӨҡеҗ¬дј—жңүдәҶжҺҘи§ҰдәӨе“Қйҹід№җзҡ„еҘ‘жңәгҖӮгҖҖгҖҖ
гҖҖгҖҖи§үеҳҺдәӨе“Қд№җдҪңе“ҒеңЁйҹід№җеҸҷдәӢдёҠжһҒе…·еј еҠӣпјҢиҝҷз§ҚеҲӣдҪңйЈҺж јеҫ—зӣҠдәҺд»–йҮҺеӨ–йҮҮйЈҺзҡ„“зҲұеҘҪ”пјҡгҖҖгҖҖ
гҖҖгҖҖеёҰзқҖеӯҰз”ҹж—©дёҠ7зӮ№еҮәеҸ‘пјҢдёҖи·ҜдёҠеҸҜиғҪеҗ¬дёҚеҲ°еӨҡе°‘жӯҢеЈ°пјҢз”ҡиҮіиҝһз”өиҜқдҝЎеҸ·йғҪжІЎжңүпјҢдҪҶжҳҜжҢ‘жҲҳиҚ’йҮҺпјҢдёҺйӣӘеұұгҖҒж№–жіҠгҖҒи—ҸйҮҺй©ҙгҖҒи—ҸзҫҡзҫҠдёҖиө·иө°иҝҮзҡ„еҺҶзЁӢдјҡи®©дәәжү“ејҖеҝғиғёпјҢи®©еҲӣе“Ғжӣҙе…·еј еҠӣпјҢи®©ж°”жҒҜжӣҙеҠ жӮ й•ҝе®Ҫе№ҝпјҢд»ҺиҖҢиөӢдәҲйҹід№җж— йҷҗзҡ„з”ҹе‘ҪеҠӣгҖӮгҖҖгҖҖ
гҖҖгҖҖдёҚиҝҮпјҢи§үеҳҺжңҖеӨ§зҡ„зҲұеҘҪиҝҳжҳҜж•ҷд№ҰгҖӮжҜҸеҪ“еҜ№еӯҰз”ҹзҡ„жҸҗй—®жңүдәҶж–°зҡ„жҖқзҙўе’ҢйўҶжӮҹпјҢд»–е°ұйқһеёёе…ҙеҘӢгҖӮ“йӮЈдёӘж—¶еҖҷпјҢе°ұзңҹжғіз«ӢеҲ»еҶІиҝӣиҜҫе ӮпјҢдёҺеӯҰз”ҹ们еҲҶдә«гҖӮе№ҙиҪ»дәәзҡ„еҸ‘еұ•йңҖиҰҒеқҗж ҮпјҢйңҖиҰҒдёҖдёӘжүҝеүҚеҗҜеҗҺзҡ„й“ҫжқЎжқҘжҝҖеҠұ他们пјҢжҲ‘еҸӘжғіжҠҠиҮӘе·ұзҡ„жүҖеӯҰжүҖзҹҘжҜ«ж— дҝқз•ҷең°еҲҶдә«з»ҷ他们гҖ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