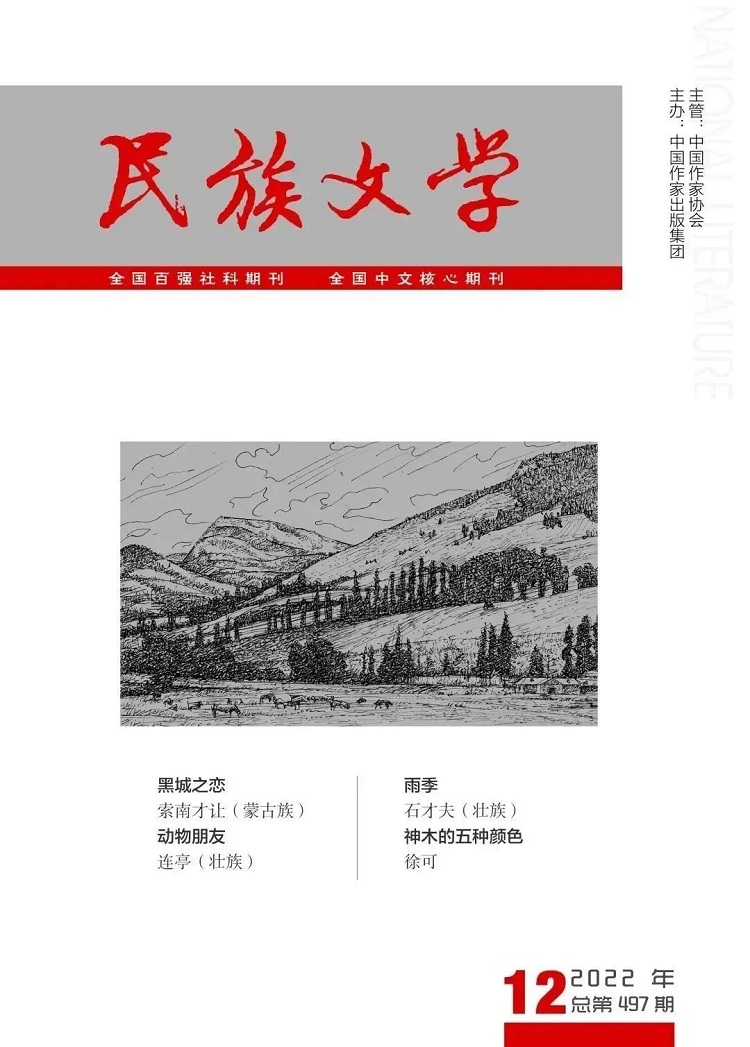
上篇 等待城墙再次成长
我们的关系还没有确定,但都心里有数了。这天晚上,我从家里出来,发信息给她:你到服务中心这里来。知道了。她说,我白天路过的时候,看见那里有人。但现在,外面太黑了,我害怕。那我来接你。我说。不用了,你来接我更害怕。你怕什么?我说。怕什么?你说我怕什么?大半夜的跟一个男人出去,好吗?你到底来不来?再过半个小时看吧,这会儿我看电视呢。她说。那你看吧,不用来了,我回去了。我说。你这个人真没意思。她说。你把我晾在这里算几个意思?我就是开个玩笑。我可不想开玩笑。好了好了,我现在就出来。
我点了一根烟,离开路灯的光圈,站在了黑暗里。楼上办公室的灯亮着,谁在那里?徐金盛,还是都成仓?或者是妇联主席党慧明。这女人的精力实在是太充沛了,干事那叫一个雷火。我再往黑处走了几步。约在这里见面实在不安全,但刚才办公室好像没人,我记不太清楚了,我应该朝上面看了一眼,乌漆墨黑一片。但更有可能是我想着要看,结果却没看,我心里装着事。四月的夜晚冷飕飕,我冻得一哆嗦,这才发现自己没有穿衬裤,但这怎么可能?我开始分析自己为什么没穿衬裤,又是什么时候脱掉的。我居然想不起来。往前推,去西宁那几天我穿着呢,我记得在枫林酒店,我洗澡时还在犹豫要不要洗一洗。回来后四天无所事事,但肯定没有脱掉,因为那几天天气很冷。接着去藏毯厂帮朋友看地毯,心血来潮地离开马路,从田野间走路回来,直接越过黑城,走向那段病恹恹的明长城,在那里逗留了很长时间……然后再往前,一直走到了拉脊山脚下,坐在一块很大的、遮风效果极佳的石头背后很长时间——那段时间想了什么?在手机上读网文,听了歌,拍了照片,那天是三月二十八日吧——下午四点过后,起身,活动了僵硬的双腿,回家。膝盖骨里空荡荡的,酸涩感很强。饿得双腿软绵绵的,头冒虚汗。身体这么糟糕吗?我开始害怕起来。那种害怕很复杂,不是单纯地担心疾病,不能恢复正常、意外受伤、痛苦的煎熬,以及死亡这一终极恐惧都让我感到害怕。但那时候,我依然穿得很正常。再往后的日子,就是来了一拨客人的这几天。这已经不知道是这一年多时间里的第几拨参观团了。但这次来的这些人有些不一样,他们是书画家、摄影家、戏剧家还有作家,来黑城采风。我知道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上午了,书记徐金盛领着他们在石头街上漫步参观,到处指指点点。我站在汪生全家的大门口,看着他们慢慢地走到小广场上,很有兴致地欣赏我们村的几个妇女的广场舞。一曲结束,他们说说笑笑了一阵子,有个卷发红脸膛男子走到广场中央,说要唱一段秦腔。他叫上来一位女士,简单地酝酿了一下,唱起来。我还是第一次当面听人唱秦腔,很有意思。他俩既走台又演唱,表演得很尽力。围过来的人多了,大声叫好,要求再来一段。两位答应着,休息了片刻,又唱起来。
等我到镇上买了膨胀螺丝,租了电钻,又到锦华饭店门口开上车回来时,他们在办公楼底下,支着大铁锅,在揪面片儿。显然,这种午饭他们很喜欢。我放慢车速,数了数,他们有十一个人,有五位女士。我用借超长电线的机会去找文婷,才知道昨晚上有两位女艺术家住在她家。半夜里,她们兴致很高,要去走走石板街,看看月亮,是我陪她们去的。文婷说,昨晚的月亮真大呀,又亮又清晰。石头朝着月亮的一面都在发光。她们激动坏了。
哦,肯定是的。我说,在城市里,哪有月亮的光,都被灯光吃了,还有汽车尾气和乱七八糟的气体。
回来时已经四点了,我都冻死了,她们还舍不得回来。我觉得她们这样的人真好,喜欢生活的美是真诚的。
我有些奇怪,难道我们不真诚吗?不一样,我们看见的生活是实实在在的生活,她们却能看见不一样的东西,那应该是隐藏起来的更好的一些什么,但我们看不见。
也许是这么个理,但是你想过没有,我们能发现的很多事情他们却不知道。一时说不上来具体的,但是你好好想想,心里就是有那么一种感觉,我们的很多秘密他们不知道,这个秘密不是那种秘密,是大的那种,就好像……
我知道你的意思。她说,可是我更想成为她们那样的人。
她们是干什么的?
是作家。
她们带书了吗?自己写的书。
她们说太沉了,没带。但是我上网查了,她们写了很多书。
都是些什么书?
有一本好像叫《重返现场》。
是小说吗?
好像是。
肯定不是网络小说,网络作家没时间采风。我接过电线。此时,我们在她家被当作库房的旧房子里,里面很暗。窗户本来就小,现在又钉上了木条加固,幽森森的。我靠上前去,她一闪身,到了门口。中午那会儿,有戏曲家要唱秦腔,你来听吗?
你会去吗?
我当然去。
那我也去。昨天我也听了,功底深厚,唱得好。
我很羡慕那位女老师,她的气质真好,你发现了没?
哪个?
就是唱秦腔的那位女老师啊。
哦,没错。的确非常好。我想,那应该是常年舞台表演的效果,就像军人总是昂首挺胸一样。
但我做不到。她说。我看出来她真的对自己感到失望了,好像受到了很大的刺激。
不是做不到,是我们从来没有机会,也没有必要去那样做,我们做自己就好了,她们也是在做她们自己,因为职业或者艺术,你才会觉得她们很不一样。
我好像有点驼背,你觉得呢?
没有啊,我没看出来,有吗?
有的。我知道,我走路的时候喜欢塌着肩膀,就好像累得抬不起头一样。
这是一个习惯,改一改就好了。
她父亲去县里了,她妈就在广场上练舞,再过几天,村里的舞蹈队就要去参加演出比赛了,因此这些天,广场的音乐从早到晚不消停。她妹妹因为疫情,从兰州大学放假回来了,正从卧室的窗户观察我们。你妹妹在监督我呢,好像害怕我把你拐跑了。我朝文洁挥挥手。她面无表情地看着我。
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那你什么态度?
不是明摆着吗。
我还是不太明白,你忽远忽近的。
从她家出来,绕过了挖断的巷道,经过古井的时候,有四五个艺术家在那里聊天。聊的正是这口井。这口古井已经有一千年了,是北宋一位叫王厚的威州团练使的“政绩”。他在崇宁三年时率军攻打青唐城——就是现在的西宁市——逼得青唐王子溪赊罗撒什么什么的逃到了溪兰山中,再逃至青海湖,最后,又到了溪兰宗堡——即现在我所居住的地方:黑城——被王厚围堵歼灭。据《续资治通鉴》记载,这口井是为解决当时守城将士们的吃水问题开掘的。因为水质优良且从不断绝,故一直饮用到1996年,黑城通了自来水,才被封存。我小时候,可没少喝这井水,冬天的时候,帮母亲提水——再后来自个儿来挑水——也没少受罪。当时并不觉得有什么好的,水就是水,难道还能变成饮料,但现在回想——尤其是喝了自来水一对比后——真是大不一样。这井水的那种干净至纯的感觉,太珍贵了。
我回家前先到土主庙那里看了看。那位画家还在画画,旁边已经有一幅完成的作品了。我在他旁边站了一会儿,他没有看我,很专注地工作着。他画的是石头街的一截,古城墙和那几棵古树都跃然纸上。他身后,土主庙边上的那棵披满了红绸的老树正在发着新芽子,在他斜对面,古城墙豁口下是水泥硬化路,绕着黑城一圈。在二十年前,这个豁口是没有的,我小时候常在城墙上玩,可以完完整整地走一圈,走到南城门了,手脚并用爬过去,接着走。城墙有两三步宽,看起来很高很危险,却从未掉下来过。因为上墙,那些年母亲揍我的次数数不清。现在,她已经有十来年没有打我了,所以她将这些精力放到了对那些往事的回忆上。几天前,我陪她到城外散步回来,经过北墙根时她又说起一件事。说那一年,我大概八九岁,一场大暴雨过后,城里到处是泥潭,院子里圈了一大汪浑水,墙根小小的排水洞效果不显,我父亲正在旋大排水洞,但一转眼,我不见了。接着她和父亲心有灵犀地朝墙头一看,我蹲在城墙上,正笑嘻嘻地看着他们。适合上墙的地方就在土主庙旁边,他们都不知道我是怎么用这么快的速度跑到土主庙那边上墙又踩着城墙跑回来的。当时我吓得脑子嗡的一下,这可不是平时。母亲说,墙是黄土墙,雨一泡,滑得跟鱼儿背子一样,随便一下,就会栽下来。你父亲气得当晚就犯心脏病了,你这个二流子。她嗔怒地瞪我一眼,看着城墙,陷入了回忆。母亲说的这件事我毫无印象,她以前说的很多我闯过的祸,除了她,估计没人记得。以前不觉得怎么样,但自从父亲走后,她的记忆力越来越好了。我发现,她可以追逐到事件最轻微的细节,而后,由此引出更多的事件。刚开始的时候,大部分事件都没有我参与——我想那是因为我还没有出生,或者太小了——但到了后来,尤其是最近两三年,主角大部分都是我,好像我正是在她的故事中慢慢长大,然后导引着事情的发展。
我赶在中午到来之前干完了活儿。母亲花很长时间绣了一幅超大的百鸟朝凤图,我拿到西宁市精心装裱。客厅沙发背后一直空白着,就等这幅杰作呢。这是母亲刺绣多年来最呕心沥血和雄心勃勃的一幅作品。她多次表明,这是留给我的纪念。我会当传家宝传下去的。每次我都这样说。她虽然呵斥我不正经,但心里却很高兴,绣得更加仔细认真。有时候一坐大半天,抬起眼来,茫然无神,一副心神耗费过度的样子。但她不听劝,执拗的态度体现在作品的进度上,这么大的一幅图,她不到两年便完成了。整个黑城,以及周边村寨,我认为没有可以与这幅作品媲美的刺绣。其配色的精湛、细节的完美、构图的大气令人惊叹。这真的是一幅可以当作传家宝的宝贝,因为里面有母亲倾情投入的精气神和一个母亲对儿子和家的全部情感。
当我将百鸟朝凤图挂上去,拉开窗户上的窗纱,满屋生辉。效果之好,让她高兴得合不拢嘴。看来我是白担心了,搭配得很好啊,你看呢?她满怀信心地问。简直就是不得了。我说,这还不把别人眼热死?以后我们出门,得把门锁牢。胡说。谁会偷这个。就是因为这个才会心动,其他的东西哪有这个宝贵,我得小心一些。
她从各个角度观赏、审视。她复杂的感受我无法准确描述,总之,最后她心满意足地去做午饭了。我说去还电线,出门径直走到小广场。综合办公室楼下,几个婶婶又开始做大锅饭了,跳舞的依然还在努力。艺术家们参观了一上午,回到了这里,有的坐在凉亭里喝茶,有的站着闲聊。文婷从办公室楼上下来,在大铁锅旁边绕了一圈,慢慢地来到广场。两位戏曲家开始准备表演了。黑城好运小卖部门前下棋的几个老头儿丢下棋子,背着手也踱过来。我站在文婷身边,朝她笑笑。我妈的刺绣挂上墙了。我说。肯定非常好看,我想去看看。她说。那你下午过来吧。我说。我不好意思,太不好意思了,她一个劲地摇头。也不着急,反正以后你有的是时间看,可以看一辈子。我小声说。不要脸。她躲开我一些距离。下午我去镇上,你要去吗?我不跟你一起去。她说。这时候,男戏曲家说了几句对黑城的感受和感谢的话,要开唱了。他们唱的是《秦香莲》中的一段,有六七分钟长。
听完一曲,满足地吐出一口气,我已经决定好好研究研究秦腔,既然这么喜欢,那就尽情地去听吧,去唱吧。这是一个高级的爱好,没有人会反对。我发现文婷的目光一直追随着那位女戏曲家,她的羡慕再次显露无遗地表现在脸上。要不要去认识一下?不用,有什么意义呢?可以学习唱戏啊。她看了我一眼,我什么时候说过喜欢唱戏吗?我被噎得没话说。她已经变得兴味索然,没有交谈的兴致了,她甚至都不再看任何人一眼。她走后一会儿,我抖抖手里的电线,追了上去。
音乐响起,争分夺秒的婶婶们又开始跳起来了。我说。
她们怎么了?她们的现在,就是我的将来。她情绪低落,说话很冲。
很好啊,老年人,开开心心身体健康就是一切。我说错什么了吗?
我只不过是说了句实话,你就不耐烦了。她毫不客气地推开我,说,推土机来了,让开。
你们家的推土机长这样?这是挖掘机。
反正我看到了几十年后的自己,我是农村女人,又有什么区别。
不一样的,时代发展这么快,说不定到时候我们都成城里人了。
可是意义没有变,我还是和她们一样,做着一样的事。
我们的事情不都一样吗,大同小异的事,生活也这样。我被搞糊涂了,我能理解她心中的不甘与反抗,但正是这种态度在我看来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因为大众就很好,我很不想让她因为不甘心而去辛苦做事。那你想干什么,你可以不跳广场舞啊,再说,到了那个时候,谁知道有没有广场舞。
这么说,你其实心里也是这么想的。她一副果然如此的表情。
你明明知道我不是那个意思。我说。我的火气也上来了,但我不想让她看出来。
那你什么意思?她依然不依不饶。就算……她有些哽咽。就算到时候我不跳广场舞,可我也是一个农村的老太婆,我永远成不了另外一种人,我早就知道了,因为我没有上好学,没有学历没有知识,也没有什么才华,无论我羡慕什么想要干什么我都没有那种才华,我越想做别的事就越觉得最适合做的就是一个农村妇女,你说我怎么办?我该干什么?我是想唱戏可是我得有那个天赋得有一副好嗓子啊,得有一副好身材啊,你看看我这个矮子,你再看那个老师,看看她的条件你再看看我,你跟我说我能干什么?我可以干什么?
我想抱抱她,被推开。巷道里空静,挖管道的工人不在,昨天新翻出来的泥土吐露出农村的气息。我仰着头,看着城墙根那一排杨柳的干干的枝条垂下,贴着土墙乘凉。听着她轻轻的抽泣,心里一阵刺痛。如果去爱一个人的前提是要了解她,那我做得远远不够,是根本不合格的。我根本不了解她的心思,不知道她在想什么,不知道她精神的苦楚,我只是想得到她,让她成为我的妻子。但是,然后呢?我没有想过,或者,是潜意识中有了固定的传统的不需要去追寻的答案:一个农村的家庭妇女。是这样吗?我真不知道了。此刻的答案,很有可能已经被篡改了,我已经不承认了。
好一会儿后,她渐渐平复下来。我握住她的手,心里一阵发虚。现在,不管她怎么想,我认为自己还没有做她男人的资格,但又因为这个突然的事件,我更觉得有信心了,因为我知道了她的苦闷,我可以和她一起去抗争去奋斗。别担心,我说。无论你想干什么,我都会陪着你,和你一起努力。我还会和你一起变老,就算是去跳舞,我也和你一起跳,不和别的老太婆跳。
你讨厌,我才不去跳,要去你去,你和那些大妈打情骂俏,你最适合干这个。
行啊,只要你没问题,我完全没问题。
你要是敢和别的女人多说一句话,我饶不了你。
我的天哪,你还没进家门就吃上醋了?我可怎么活啊。
你现在后悔完全来得及,我可以放你一马。
晚了,现在九头牛也拉不回我了。成功地逗她开心,我将电线递给她,朝大门内张望,再一次看见文洁正看着我们。我张张嘴,涌上喉咙的难听话还是咽了下去,再怎么说她也没错,又是未来的小姨子,又是很有上进心的大学生,给点面子吧。文婷似笑非笑地觑着我。一看你的表情,就知道准不是好话。知道文洁怎么说你吗?说你是个狡猾的善于伪装的人。我伪装什么了?我说,我爱你是真的。肉麻。她说你肯定心里在骂她,她从你的表情上看得清清楚楚。这么说来,她比你了解我,干脆你们姐妹都嫁给我算了。请你转告她,我也会好好爱她的。她朝妹妹招手让她出来。我掐了一下她的脸蛋落荒而逃。文婷在身后喊,你要是能和她争辩半个小时,我就什么都听你的。我迟疑了一下,但随即强忍回头的冲动离开巷子。
4月28日这天晚上十一点多,我看完了《一念永恒》最后一章。这部网络小说我断断续续看了半年,总体感觉还是挺不错的。回想自己这十来年的阅读水平,觉得有所进步。我记得第一次读网文还是2010年的冬天,那天我去找都成毅,他正在读小说。他用手机读,用的是一部灰屏的诺基亚手机,他每读一行便要摁一下下音键翻出来一行。但一行只有十几个字,所以他要一刻不停地摁键。我问他为什么不设置成翻页,这样摁一次键可以读到一页文字,最起码有五六十个字吧。他说他不习惯那样读。正是他引导我读网文的。我读的第一本书是关于三国的,名字现在已经想不起来了。但我记得第二本书是《寻秦记》,那本书太好看了,我一口气读了两遍,并受到此书的影响,喜欢上了战国先秦时期的历史。有关这方面的书籍或者影视作品,我会多看几眼。我和都成毅由此成为阅读伙伴,经常交换阅读体会,分享好书。他是一个很有身份的人,从过去到现在一直是。他很看重家族荣耀,绝不干有辱门风的事情。小时候,我们几个常常闯祸的小子中,他是最有顾虑的一个,长大后他也是最稳重的一个。他的先祖,是南京江宁府上元县乐人,始祖官至清五品钦差,后迁至青海,入籍湟中县,并在民国年间移至黑城村落户。说起他祖上的事迹,尽管都成毅也一知半解,但他在这方面的收集和整理上是有一些功夫的,说起那许多年前在南京城里正月十五的花灯,那欢乐时刻发生的意外,又因为这些意外而造成的流放,前往这遥远的边疆路途上的遭遇……家族坎坷艰辛,代代奋斗代代相传的精神,如同家谱一样清晰地传承在他的血脉中。事实上,不只是他都氏家族,黑城的如解氏、汪氏、刘氏、田氏,还有我这一脉人丁稀薄的冯氏,祖籍都在南京,都是那一次意义深远的元宵节中的“罪犯”。那些无法一一证实的陈年旧事,于后辈的猜测与推断中弥补出一个个家族迁徙的轮廓。而这些从南方来的祖先们,他们的后人经过几代后,又成为地地道道的北方人。所以对我们这些后人而言,所谓的南北之分,早就在先祖们的迁移中化为乌有,剩下的,只有一颗中国心。
夜晚总是流淌进历史的大河中,让清醒着等待的人经历某种精心安排的时间去回顾体味。我睡意尽去,心如撞鼓,于是穿好衣服,走到外面石板街上。夜晚的黑城寂静无声,仿佛回到了远古时期,有一种胆怯却好奇的懵懂意味。我心里喜滋滋的,很快走出石板街,从北门出了城,延续多年的习惯,迈着多年来形成的步子,我开始再一次绕走我的黑城。这次没有数步子。也不用数,这个小游戏我玩得太多了,在我养成散步的习惯之前——大概就是从八九岁开始的——我便养成了丈量黑城的习惯。东面213步,西面214步,南北分别是202步和200步。这是近两年比较准确的数字。但在以前,我的成长没有定型之前,数字的变动是很频繁的,几乎每个季节都不一样。这个小游戏陪伴了我很长一段时光,特别是在我心情不好的时候,我会独自享受这个在别人看来万分枯燥乏味的游戏。我会一圈接一圈地走,走一步数一步,把每一步控制得差不多,越精准越好,乐此不疲。当然,儿时的游戏现在成为生活的一部分,并且是最核心中最难以割舍的那一部分。这些年我渐渐地才有些明白,我是把生活中日常的一部分很自然地转化为一种更具有意义的形式,我将去长途旅行的步伐浓缩在了黑城身上,具体在了少年时的城墙上。黄土坯的墙头,收缩了世界的比例,我不用离开,就可以走完整个世界。这就是我这些年从来没有离开过的原因。我总有一种感觉,或者更像是一种仿佛受到保护的直觉:这黑城的城墙,受尽岁月和历史的盘剥,经历了高原的沧海桑田后,重新焕发生机,宛如枯树抽芽,将再次成长起来。说不定在某一天,我再次走出家门,悠悠地拐过北门,倚着墙根,沿着庄稼密匝匝的田埂踱步,恍惚间,这段厚腾腾的城郭产生新的步数,它已悄然生长了一截,围绕它的庄稼荡漾,它也在春意沉醉的晚风中扬起一片得意的微尘。
……
【佳作点评】孟繁华:爱情点燃的青春之火
读索南才让的《黑城之恋》,我情不自禁地想到了50年代初期王蒙、宗璞等的青春写作。那是一个转折的时代,青年作家们发自内心地拥抱生活、拥抱时代,但他们选择了更尊重艺术规律而对其他方面不得不有所牺牲。所牺牲的某些方面,并不是那些青年作家有意为之,而是他们内心真实情感的诚恳流露。虽然不久他们因此遭遇了厄运,但是历史是公正的,二十多年以后,他们终于成了“重放的鲜花”,恢复了艺术的纯真面孔。如果说那是那代人的“青春写作”,最让人感动的,就是他们情感和修辞的诚恳,他们没有学会油滑和造作。
索南才让——这位刚刚获得了鲁迅文学奖的天才作家创作的《黑城之恋》,就诚恳到了50年代青春写作的程度。不同的是,今天的索南才让不必再有当年的纠结或谨小慎微。他可以有如骏马,在他写作的荒原上任意驰骋。《黑城之恋》的故事发生在一个小城——黑城。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城,虽然也有大妈的广场舞,有休假的大学生,但总体上它安静,城市没有喧嚣,人心不大浮躁,本质上还是前现代的生活样貌。即便是恋爱中的一对青年男女,思想还不那么“开展”,特别是女孩文婷,泼辣可也羞涩,炽热却有节制。小说使用了双重比较的方法:一是讲述者“我”和恋人文婷对生活的态度、对黑城情感的比较。“我”是一个做虫草生意的人,生意说得过去,虽然每天无所事事,但对黑城有深厚感情。通过读书自学,对家乡、对生活有了新的认识。“我”对普通的日常生活兴致盎然,就是黑城的水,“尤其是喝了自来水一对比后——真是大不一样。这井水的那种干净至纯的感觉,太珍贵了”;还有母亲巧手编制的“百鸟朝凤图”,都深深地植根于“我”对黑城的情感深处,“我”少年时代建立起来的文化记忆几乎就是与生俱来:“我”曾无数次地用脚丈量黑城的城墙——
我会一圈接一圈地走,走一步数一步,把每一步控制得差不多,越精准越好,乐此不疲。当然,儿时的游戏现在成为生活的一部分,并且是最核心中最难以割舍的那一部分。这些年我渐渐地才有些明白,我是把生活中日常的一部分很自然地转化为一种更具有意义的形式,我将去长途旅行的步伐浓缩在了黑城身上,具体在了少年时的城墙上。黄土坯的墙头,收缩了世界的比列,我不用离开,就可以走完整个世界。这就是我这些年从来没有离开过的原因。我总有一种感觉,或者更像是一种仿佛受到保护的直觉:这黑城的城墙,受尽岁月和历史的盘剥,经历了高原的沧海桑田后,重新焕发生气,宛如枯树抽芽,将再次成长起来。
但共同生活在一个小城的文婷不一样。一个青春早期的女孩,对人生充满了迷蒙和惆怅。在艺术家和跳广场舞的大妈那里,文婷看到了不一样的人生和未来。一方面,文婷隐约感到:那些跳广场舞的大妈“她们的现在,就是我的将来。她情绪低落”,“反正我看到了几十年后的自己,我是农村女人”;一方面,文婷家里住过几个来黑城采风的艺术家。这让文婷看到了另一种生活或人生。女艺术家们看到了黑城的月亮又大又圆,“激动坏了”,“回来时已经四点了,我都冻死了,她们舍不得回来。我觉得她们这样的人真好,喜欢生活的美是真诚的。我有些奇怪,难道我们不真诚吗?不一样,我们看见的生活是实实在在的生活,她们却能看见不一样的东西,那应该是隐藏起来的更好的一些什么,但我们看不见”;“我很羡慕那位女老师,她的气质真好”。在艺术家的生活、情感方式和个人气质中,文婷觉得自己事事不如人,而且毫无前景可言,她的沮丧溢于言表。在这种状态下,“我”与文婷建立了恋爱关系。
艺术家的到来不仅在文婷心里波涛汹涌,而且“艺术家们谈吐不凡,我受到刺激,生出不甘之心。所以别说文婷,我也感慨良多,并做了决定”。这个决定改变了我的人生态度:“我现在越来越明白,一个人活过25岁,便会进入一个成熟期,这个成熟不是平常认为的那种成熟,而是以一种觉悟了的心态,开始寻找自身的一些东西,又去除一些怀疑的东西。来来去去地折腾,总会有结果出现的。当然,我现在并不想知道,我才刚刚开始一段旅程,姑且,将这一段人生称之为寻根吧。”这是我理性地思考人生的结果,更可惜的是——
这种现象也在文婷的身上出现了,我之所以喜欢她,不是因为她漂亮,是她的某种困惑与追问与我志同道合,我们有话说,尽管我们到现在都没有在这方面好好地、开诚布公地谈一谈,可是这不紧要,因为从一言一行中,我们已经交流了无数次,在更深的精神和意识中,我们交谈了无数次。我很庆幸能遇到她。
我们得承认,这是一篇非常正面,非常“主旋律”的小说,也是一篇爱情点燃了青春之火的小说。因小说写得诚恳,文婷的转变不仅不显得突兀或不自然,反而让人感到是水到渠成的结果。
小说还有一个“非常危险”的人物。这个人物是文婷的妹妹文洁,一个伶牙俐齿的大学生。她性格开朗,言辞犀利,与“我”和她的姐姐文婷都形成了比较鲜明的比较。如果小说沿着这条线索继续展开,一个“姐妹易家”的故事将不期而至。特别是文洁替姐姐文婷收下“我”的那束鲜花的情景以及文洁和文婷的对话——文洁潜意识里如果说没有对我的任何想法是不真实的。另一方面,文洁虽然是大学生,甚至有明显的优越感,但在讨论黑城历史的时候,她的华而不实的虚浮暴露出来了。“我”虽然是一个民间的历史爱好者,但毕竟读了很多历史书,文洁臆想的关于黑城的历史显然是经不住追问的。这也是“我”对虽然比姐姐文婷还要漂亮的文洁不曾动心的一个方面。在踏实又诚实的姐姐面前,漂亮的妹妹魅力尽失。这也是这条线索戛然而止的重要原因。但文洁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人物,正是在文洁和文婷的比较中,文婷的质朴、天真以及内心活动的一览无余,给人一种踏实、本分和安全感,这也正是文婷的可爱之处;而文洁伶牙俐齿甚至巧言令色,尽管有可爱之处,但终还是难以让人托付吧。
小说的青春气息,特别是小城青年男女特殊的交往方式、爱慕方式,充满了生活气息,那种生活中生长出的语言,是无论如何都难以编排的。更重要的是,无论是有多少人涌向了大城市,涌向了那触手可及的“现代”生活,且不说他们的难处和付出的代价,他们无处诉说的心理创伤,可能是永远难以愈合的。而“我”和文婷的“黑城之恋”、黑城生活,经过短暂的“现代冲击”,很快风平浪静,岁月静好。没有经过“现实”冲击的田园生活是前现代生活;经过“现代”冲击和洗礼的小城生活,一定是结实、温馨和心神安定的生活,因为对那曾经令人魂不守舍的“现代”,已经了然于心。
原刊于《民族文学》(汉文版)2022年第12期(责任编辑:安殿荣)

索南才让,蒙古族,青年小说家。1985年出生于青海。在《收获》《十月》《花城》《小说月报》《 民族文学》《青年作家》等杂志发表作品,作品入选《小说选刊》《中华文学选刊》等选刊,以及《2020青春文学》《2021中国短篇小说20家》《2021中国微型小说年选》等年度选本。有作品入2020收获文学榜,曾获“《钟山》之星”文学奖年度佳作奖、华语青年作家奖、青稞文学奖、红豆文学奖、青海省青年文学奖、青海省“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称号等。2022年获得第八届鲁迅文学奖。

孟繁华,北京大学文学博士,沈阳师范大学特聘教授、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所长,北京文艺批评家协会原主席,中国文艺批评家协会顾问,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监事长,辽宁作协副主席,《文学评论》编委。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当代文学研究室主任。著有《众神狂欢》《1978:激情岁月》《梦幻与宿命》《传媒与文化领导权》等30余部以及《孟繁华文集》十卷。主编文学书籍100余种,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文艺研究》等重要刊物发表论文500余篇,部分著作译为英、法、日、韩、越南等文,百余篇文章被《新华文摘》等转载、选编、收录。曾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理论评论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批评家奖、丁玲文学奖、《十月》特别奖,多次获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理论成果奖、中国文联优秀理论批评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