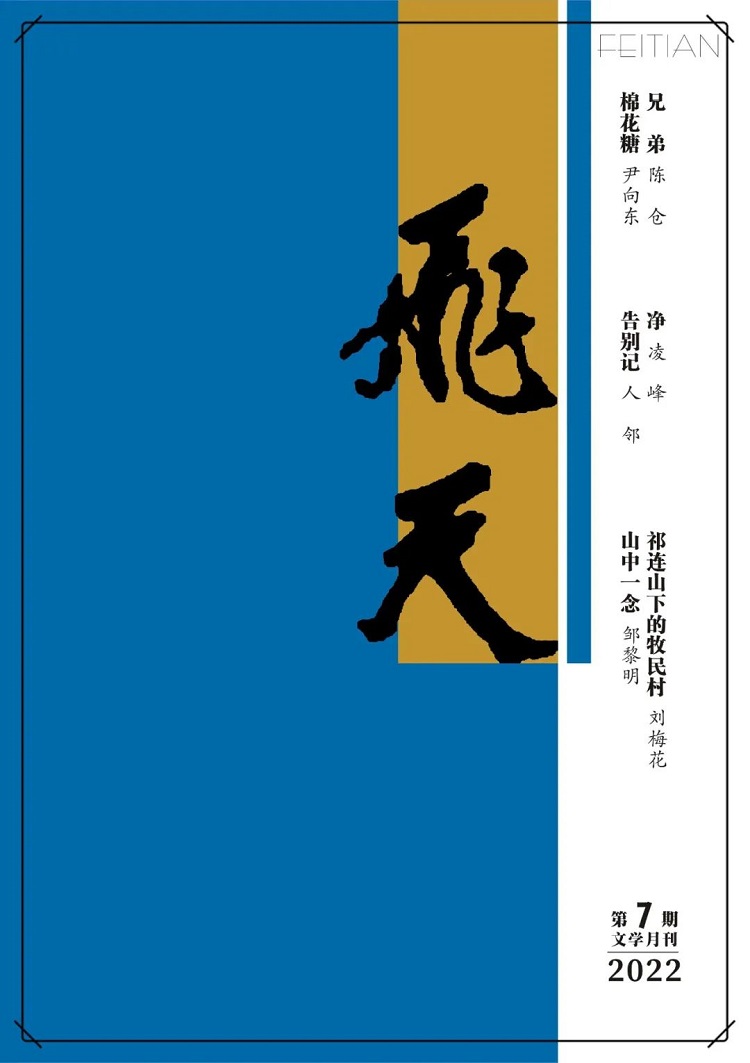
杜铁是父亲给他取的名字,因他婴儿时贪恋母亲的奶头。无论饱还是饿,必需含着奶头才安稳。一离开,他就哭。父亲是石匠,下体力干活,晚饭爱喝酒,酒后常夸耀自己是三代贫穷。杜铁出生半岁还没去上户口,因父亲想不出名字,又不愿让别人帮忙。见孩子贪奶劲头十足,一旦哭开,除了奶头,什么都诓不了。父亲骂他是铁疙瘩,脑袋里灵光一闪,就叫杜铁。
这名字概括了杜铁的执着,他不喜欢变化的生活,如果可以,他能够一生都专注于一件事情。
那时候砖厂正兴旺,拥有一个大院子。从山上挖泥土、拉泥土,到选石头、压成砖坯晾晒,再到遂道窑里烧制成红砖,有上百人在各个环节中忙碌。杜铁招进砖厂当工人,负责将方形泥条压制成砖坯。他站在操作台前,泥条顺溜槽滚来,他手扶泥条,送上切割器,右脚用力一踏,像踩汽车的油门踏板,咣地一声,推进器猛推泥条,数根笔直的钢丝就将泥条切成砖坯,再踩踏板,砖坯整齐跌落在架子车上。说来就这样简单,但那时候砖厂兴旺,杜铁也年青,沉迷于手中的活,以及目前的生活状态。他把简单的事做出了花样,带点表演性质。转身手扶泥条、躬腰抬脚,再踩下去,动作既夸张又省力,传送带、滑轮、踏板、推进器,各个环节的声音在他的操作下有了节奏。他像个指挥,正把砖厂大院的噪声有机组合。
杜铁不喜欢变化,生活却不会停滞,变化不可阻挡。
唐怡到康定投奔亲戚,四处打工。砖厂需要许多零时工,她就来拉板车,把湿砖坯拉到院中晾干。她喜欢杜铁站在操作台前的模样,她把架子车放在切割机下,回身看杜铁操作。她的眼神痴迷,一脸崇敬,架子车装满都不知拉走。有人欣赏,杜铁的动作更大、更夸张。转身、躬腰踩踏、手挥舞起来、再转身。如果给他穿上彩袖,他不是切砖,是跳舞,跳欢快的藏族弦子舞。那时候的唐怡还很娇小,斯文安静,她看着杜铁,眼睛不停地闪,脸颊上几颗雀斑也起起伏伏,直到别人提醒砖坯已装满架子车,才带着痴呆的眼神奋力拉去。
杜铁对唐怡这人没感觉,只对她的名字有兴趣。刚进厂时,别人说她叫唐怡,杜铁条件反射般想起六岁的事来。有一夜,父亲应邀去朋友家喝酒,酒醉回来时,杜铁已经睡熟。父亲带回一颗糖,想叫醒沉睡的杜铁,叫了许久,杜铁半睁开眼,应一声又睡去。父亲无奈,直接将糖塞进杜铁的嘴。杜铁明白有好事,只是无法醒来,他在睡梦中尝到这糖不似过去的硬糖,不仅甜,还很绵软。第二天问父亲,才知吃的是棉花糖,从上海带来。父亲尽其所能形容那颗糖的样子,说像猪儿虫一般又绵又软又白。许多年里,杜铁展开想象,所有绵软都往那颗糖集中,一块块长条形的白色棉花糖整齐卧在椰子丝里,让人心里直颤。厂院里,见到唐怡他没触动,任谁提到这名字时,杜铁就想起那颗糖,后脊发一阵麻。
杜铁虽然对唐怡这人没感觉,别人却把俩人在拉车时的种种表现注意到。那年月,男女间的微妙最能激发众人想象,唐怡和杜铁被编排进歌谣:
难忘的秤砣
小赵的脑壳
砖厂的机器
杜铁来操作
谁敢接下他的活?
唐怡拉车送秋波!
大人说,孩子们跳橡皮筋时也唱。歌谣本身没什么,不过秋波对砖厂的许多人来讲都太陌生,听着像电影里妖媚的太太小姐们。唐怡不妖媚,一点也不。整日穿件劳动布工作服,连女性的特征都不太明晰。因这秋波,她给人的印象总不正经。
杜铁初听这歌谣,不明白唱的什么,也跟着哼唱,好朋友建军说,才知编排的是自己。从此怕羞,再不敢和唐怡说话。路上遇见,也早早回避开。站到操作台前,唐怡推车进来,他低下头,眼睛不往别处看,做砖坯的动作小了许多。
唐怡却不同,听见有歌谣编排他们,特别高兴。拉车时眼睛瞪得极圆,毫无顾忌地盯着杜铁看。那天下午,太阳极大,厂院被太阳烘烤得沉闷,许多人都光着膀子工作。汗水淌满脸,经太阳一晒,结成盐渍。沉闷的厂院直到唐怡拉车走向砖坯车间,才有了生气。有人哼起歌谣,熟悉的旋律盘旋脑中,许多人都跟着哼。唐怡听见歌谣,心里高兴,瞅着杜铁,见他低下头,不敢看别的地方,他不敢看钢丝,不敢看泥条,向着唐怡那方向的东西全不敢看。唐怡见他手扶泥条,手还没离开,已踩下踏板。唐怡尖声吼,众人围上来,他举起手掌,右手中指、无名指和小指从第二个指节处整齐断裂。血在喷涌,砖坯、操作台淌满暗黑的血。杜铁举起手,看着三根手指只剩短短一截,他的表情有些茫然,像不知怎么回事。工友们将他送到医院,唐怡也要跟去,别人说你不要再添乱了。她才收住追赶的脚步,脸色惨白地看人们远去。那时候医院技术也不全面,断掉的手指没能力接上,只有包扎。
杜铁从医院回来,已是晚饭时间,三根手指层层叠叠裹着纱布,右手吊在绷带中。几个好朋友帮他弄晚饭,边弄边说:“这三根手指因唐怡而断,养伤期间得让她来服侍。”
杜铁说:“不能再开这样的玩笑,别人还是个姑娘。”
众人起哄,直嚷:“是姑娘怎么会送秋波?”
杜铁说:“什么时候送了?都是乱编排出来的。”
建军说:“照我看来,她对你是真有意思,不过她配不上你,一个临时工,会拖累你。”
杜铁认真想了想这事,一个临时工,工钱说没就没,俩人在一块儿,势必会打破他现有的安稳生活。他用左手非常别扭地吃饭,边吃边摇脑袋。
第二天杜铁坐在家门前晒太阳,看忙碌的砖厂大院。车间午休时,他看见唐怡径直走来,忙回房关上门。唐怡站在门外敲,边敲边喊:“杜铁,快开门,我来帮你做饭。开门啊,你手伤了,我来帮忙。”
杜铁靠在门背后,大气都不敢出。
唐怡叫了许久,才转身走开,边走边说:“这个杜铁,手伤成那样,还有什么害羞的。”
唐怡不气馁,没人时她进不了门,专挑有人时再去。砖厂大院里,年青人在晚饭后爱串门闲聊。杜铁平时对人好,谁来他都欢迎,加上手给伤着,家里更热闹,都聚在这。一来陪他,二来凑趣。一些人家里吃饭迟,生怕错过什么趣话,端着碗就来杜铁家,蹲在角落里边吃边听。唐怡选这样的时间推门而入。大家正说笑话,唐怡进来,瞬间清静,只能听见蹲着吃饭的吞咽声。唐怡看大家,三条独凳和两根长凳上坐满了人,杜铁右手套在带子上,包裹三根手指的白纱布已经染脏,他和建军挤在长凳上,一见到她,忙埋下脑袋。大伙脸上的表情挺滑稽,既想笑,又憋着。
唐怡走到建军身边,踢踢凳子说:“让我坐会。”
建军忙起身站到一边,她就挨着杜铁坐下。还是没人说话,都静静地等待,她拿眼一睃众人,说:“怎么都不说话?”又扭过头去看杜铁的伤手,“痛不?”语气柔得众人无法待下去,纷纷找借口告辞。
他们拉了门,伏在窗下听俩人说什么。唐怡如此直接,只俩人挨着,定有好玩的事。他们安静地等待许久,不见有人说话,悄悄从窗口望进去,杜铁的脑袋仍然低垂,唐怡两条腿叠起来伸向前方,把玩自己的手。他俩就这样一直坐着,坐到天已黑透,唐怡才起身,仍不说话,面带笑容看看埋头的杜铁,转身离去。让在窗下一直等待笑话的人满怀失望。
事情从第二天开始变得戏剧,唐怡单方面要求杜铁结婚,她给砖厂的姐妹们讲肚里怀着他的孩子。她讲这话时,满脸都是幸福和骄傲。
杜铁听见传闻,气得发疯,顾不上害羞,跑去质问,他身后跟着一群看热闹的人。
唐怡正在院子里晾衣服,看见杜铁,眼睛不停地闪,几颗显眼的雀斑也活泛开,说:“来了哈,我知道你会来。”
杜铁左手扶右手,右手在纱布套中不停颤抖,满脸涨红地说:“你怎么能四处造谣?”
唐怡说:“我没造谣。”
杜铁说:“好,我问你,你肚里……肚里怎么了?”他不好意思说怀孩子。
唐怡一点也不羞地说:“我肚里有孩子了。”
“谁的?”
“你的。”
“怎么可能,你这人,哎,你说,怎么怀上的?”
“我们同坐一条长凳,坐了许久,我相信有许多人看见,他们都躲在窗外。”
众人开怀地笑起来,有人说:“是啊,我们看见了。”
唐怡骄傲地看着杜铁。
杜铁没想到她用这方法讹人,说:“坐一条凳,你就,就有我孩子了?”
“难道不是这样?”唐怡反问。
听她认真地说出这话,没人再笑。她的单纯劲把杜铁搅懵了,无法继续追问,转话说:“你究竟喜欢我什么?”
唐怡挺起胸脯,说:“我就喜欢你把切砖都切成跳舞,没人能像你这样快乐。”
杜铁指着伤手说:“快乐什么?一不小心,三根手指没了,我现在是残疾人。”
唐怡说:“三根手指算什么,以后有我在,一点不碍事。”
杜铁看着什么也不懂的唐怡,阳光中的唐怡长眼睫毛全显出来,她将袖口高高挽起,两条白萝卜似的手臂上一层浅浅的绒毛发出淡黄的光,她扎着两根小辫子,前额的留海坠几颗水珠,一闪一闪地亮。杜铁想起那颗糖,那颗集中了所有柔软的糖,笑容像水纹般在他脸上荡漾。
他们就这样结婚了,婚礼简单而热闹,婚后杜铁一直都称唐怡为棉花糖,他简单而快乐的单身生活也就此打破。曾经的笑话,促成一段美满姻缘。说美满,还缺点东西,之前唐怡逼婚,说怀了杜铁的孩子。俩人结婚,该有孩子时,却怀不上。不知谁的原因,唐怡肚里埋不下一颗种子。
人们打趣说:“你们在凳上坐的时间不够长。”
唐怡也会打趣,说:“是啊,看来我得和他坐上一辈子才能怀一个。”
没孩子并不影响他们的幸福,杜铁很快陷入二人生活,并从中找出新的乐趣。他像父亲那样在晚饭时喝酒,不仅和唐怡喝,隔三岔五就叫人去。有酒的饭局总很绵长,喝着小酒谈天说地,笑声一阵阵从杜铁的小瓦房里传来,引得更多的人前去。砖厂大院里,最热闹最开心的家庭,当数他们。
连厂长都酸溜溜地说:“杜铁,你用了什么迷魂大法,把家里搞得这样热闹?有这能耐,可以当工会主席了。”
杜铁说:“厂长,你要不嫌弃,也来家里喝一杯,凑个热闹。”
遇上过年,大年三十那一夜,凌晨零点新旧年交替之时,康定家家户户都会点燃鞭炮,鞭炮齐响,连说话都听不清。杜铁和唐怡每年必早早在门前摆好鞭炮,到新旧年交替的时刻,杜铁看着手表大声数秒,他们鞭炮响起时却总赶不上时段,要不就是杜铁的表不准,全城鞭炮炸响时,他们的还没点着。要不就是唐怡心切,杜铁才刚开始数秒,她已点着,鞭炮响起,直到快炸完,全城的鞭炮声才正式响起。等这阵炮声之后,俩人还会在砖厂大院中放长烟杆似的烟花,他们一人持一支,点燃之后高高举起,一颗颗带红光的火球冲上厂院上空,伴随俩人的笑声,闹腾许久。大年三十他们坚持熬夜,直到天边开始发白,俩人还会在门前放一串早炮,这才上床睡觉。那串早炮会将许多沉睡的人炸醒,他们听着炮声,知道是杜铁和唐怡所为,嘟哝骂一句,又沉沉睡去。
厂里买回一台大电视,放在会议室里,大家吃过饭,都去占位置看电视,看《来自大西洋底的人》,看《上海滩》。杜铁家从此轻闲,没人再来。这难不到他们小俩口,没有孩子是件很方便的事,不用操心。小俩口只留一人在家做饭,另一人极早去占座位,他们一直都占据最居中的好位置。做好饭,连锅带碗端去会议室,边吃边看,偶尔,还会提着酒瓶,把酒局延伸到会议室。众人围着他们,像每日都为陪他们而来。
只是好景依然不长,电视迅速普及到每个家里,没人再去会议室看那台黑白电视,到后来,俩人也买回一台小彩电。夜里,偶尔从他们窗前路过,能听见俩人看着综艺节目对饮,不时哈哈笑起来,像家里还有许多人在一块那样热闹。
杜铁习惯的生活原本就此稳定,砖厂却又面临倒闭。最初,各企业裁员,传闻众多,砖厂里也时时传,各种消息真伪不明。大家在一个池塘里养着,水闸没开时,水浑点没什么,得过且过。某一天水闸忽然大开,连浑水都淌尽,只有沦陷的淤泥让人无边恐惧。
唐怡刚听见这些消息,急得没法,回家给杜铁说:“怎么办?我原本是零时工,拖累你,现在砖厂倒闭,我俩更麻烦。”
杜铁说:“零时工和正式工有什么区别?还不是靠体力吃饭,砖厂如果倒闭,我也成零时工,我俩更配,有这身体力,不愁找不着活。”
“你手残了,会不会有影响?”
“我断掉的只是三根手指,又不是整条手臂,不碍事。”
杜铁这样说,唐怡放下心来。他们没想到砖厂从传闻到倒闭十分迅速,俩人说这话的第三天,砖厂开了一个大会,宣布倒闭。除了到退休年龄的人能拿工资,别的一律领取半年工资后自理未来。工人们群情激昂,无处发泄,不知谁领头走上厂院门前的公路,人越集越多,数十个下岗工人盘坐到公路上。那条路是318国道,两边的车都堵成长龙。
杜铁也去了,唐怡要跟去,杜铁说她是零时工,混里边成什么话。最初大家只在公路上静坐抗议,天渐渐暗下来,气温降低了许多,有人去厂里抱出木柴,在公路中央点起大火,围火而坐。
唐怡原本站边上随众人看热闹,大火腾起,怎么看都更像是篝火晚会,热闹的气氛让她再也忍不住,跑回家拎出两瓶酒,她挤过看热闹的人群,高声喊着:“杜铁,我拿酒来了。”工人们给她让道,她傍着杜铁坐在人群中央。酒倒在盅里传着喝,两瓶酒很快喝完,受这气氛感染,别人也跑回家把酒拎来。酒喝下肚去,众人的情绪都涌上来,他们回首往事,想当初砖厂兴旺时的情景,却不感伤,因为有人忆起那首简单的歌谣:
难忘的秤砣
小赵的脑壳
砖厂的机器
杜铁来操作
谁敢接下他的活?
唐怡拉车送秋波!
众人齐声高唱这简单的歌谣,杜铁唱得最卖力,他举着双手打拍子,三根手指只有短短一截,醒目地挥动。他的脸吼红了,衬着火光,红得透亮。这首歌减弱了抗议,消解了悲怆,歌声一完,大家哄笑一片,再接着喝酒。随酒意越深,只要有人领头,大家都唱,像小孩子们无聊地重复游戏。到凌晨四五点,多数人抵不住疲惫,回家睡觉,少数几个喝醉酒的人围坐火边,最后被时刻戒备的工作人员搀扶回家。回家路上,杜铁和唐怡仍嘟哝哼唱,直到脑袋安稳地放在枕头上,唐怡说:“好久没这样畅快了,明晚继续!”
第二天的318国道车来车往已恢复正常,几个警察漫不经心地站在厂门前,把唐怡想继续的念头彻底封住。砖厂在近似闹剧的抗议中倒闭,许多人想起唐怡拿酒来,责怪她把严肃悲怆的抗议彻底带向了篝火晚会。
依据优惠政策,杜铁领到买断工龄的钱,一共六万元,他和唐怡一块儿去存到银行里。
砖厂倒闭了,不再有机器轰鸣,不再有泥土连同石块从山上顺溜槽轰隆隆倾泻而下。有一段时间厂院还没出售,机修车间、砖坯车间以及遂道窑像风干的尸体横存院中,只有宿舍楼生气尤存。砖厂的倒闭似乎并没给人们造成更多困难,他们托亲戚朋友各找出路,很快投入另一种生活。
杜铁下苦力做过不少事情,去建筑工地扛砖、背水泥,去矿厂挖矿。有一段时间,他和街上擦鞋的一帮人联手替别人搬东西。一个电话打来,就跑去搬各种重物。时常看见他背着大件的冰箱、衣柜,额头上布满汗珠,在楼道攀爬。唐怡也去餐馆打工、当保姆、当家洁,有活就干。俩人天刚亮开走出厂院,到天一点点黑时,才又回来。
建军家条件好,父母拿钱,兄弟姐妹们资助,他在砖厂大院里开起家庭麻将馆。同在厂院,过去是好朋友,日日看见俩人起早贪黑,杜铁手又有残疾,心里不忍,时常提桶清油、一袋大米接济他们。建军提东西去,那些曾经爱去杜铁家喝酒吃饭的也学着了,家里做什么菜,比如炖肉,极肥的肉舀一钵,送过去。
“杜铁,朋友带了些大米来,我们吃不完,你拿些去。”
“杜铁,这是老婆单位发的清油,家里还有许多,你们拿着,别浪费了。”
他们拿东西来时,爱这样说,回避了施舍和救济的本意,只找无关痛痒的理由让俩人接受。
有一天,杜铁帮一个单位搬办公室,忙到很晚,唐怡一直等着他。俩人回来,天都黑了,见家门前放着两条腊肉,唐怡拎回家,忙碌做饭,将就这腊肉煮了一截。杜铁拿出酒杯,倒了二两酒,坐到小方桌边说:“老让他们这样送东西,不是个事。”
唐怡说:“别人是好心,这也说明你人缘好。”
杜铁说:“我知道是好心,可心里总不是味,砖厂倒闭,都下了岗,为啥是他们送我东西?”
唐怡说:“他们下岗都有出路,我原本就没工作,现在你也去打工,手又残疾,就比不上别人了。”
杜铁端起酒杯,喝了一口酒说:“我得想个办法,不能老这样了。”
腊肉肥的多,瘦的少,薄薄地切出来,唐怡用筷子夹起一片,看见油亮亮地泛着黄光,她将腊肉放进嘴里,刚想说别人能送是好事的话,脸色猛一变,改口说:“是得想个办法了,不能让他们再送。”
杜铁见她这模样,笑起来,说:“怎么改变主意了?”说着,也尝了一片腊肉,这肉存放太久,有股哈喇味。
唐怡撇嘴说:“真把我们当成要饭的了,什么东西都拿来。”
那会儿都住老楼,厕所是公厕,自来水也共用,家里没有。自来水龙头下修有两池子,低点的池子洗衣服,高点的池子清洗食物、碗筷。不知从什么时候起,高池子里总放只菜盆,里边要么装着待清洗的猪蹄,要么是刚杀的鸡或鱼。盆子一直放着,没人管。最初以为是哪家忙,临时有事。一段时间里,盆子老碍事,大家才留意起来,盆子里装的东西要放上大半天,众人都看见了,才见杜铁或唐怡款款而来,缓慢地洗。
遇天气晴好,俩人晚饭时爱把小方桌搬到门外。
他们还特意请建军吃饭。杜铁说:“我们在外面吃行不?”
建军说:“外面好,通透,别有情调。”
唐怡展示厨艺,做出好些可口的菜,三人喝酒,见有人路过,杜铁说:“来,坐下喝两杯,反正没什么事,喝两杯。”
小方桌边最终坐了七个人,喝下酒,说话声调自然高。喝到兴头,众人又唱起歌,欢快的气氛荡得满院都是,让院里的人感觉砖厂从未倒闭,曾经安定从容的生活也没任何改变。
建军回到家中,躺床上许久无法入睡,吃饭时的兴奋劲还在持续。暗想杜铁和唐怡身上有种感染力,能让身边的人都蓬勃起来。他俩的生活并不窘迫,起码在精神上比许多人都宽裕。想到这,省悟俩人请客大有意思,从此他不再拿东西给他们。原想回请一次,俩人都太忙,时间不合适。
砖厂大院售给房地产开发商,要拆老宿舍楼,别人都去亲朋好友那里想办法,暂时租住。唐怡原打算也去外面租房,杜铁让她别着急。大院里有人立起机器打地洞勘探,做开发规划。杜铁与他们聊天,打听今后这砖厂大院会变成什么样子。他们说这地方以后会修起无数高楼,建成生活小区。杜铁无法想象砖厂高楼林立的模样,不过他兴奋地跑回家来给唐怡说:“我们不用花钱租房了。”
唐怡说:“不花钱哪里有法?”
杜铁说:“你跟我来。”
他将唐怡领到砖厂大院的角落里,那里有两间小房,紧挨河边,呈一个小死角,房子的一小半就建在河堤上。
杜铁说:“这是砖厂曾经的配电房。”
房门虚掩,杜铁推开门,里边的电器早被卖的卖盗的盗,满屋凌乱地堆着些垃圾。
唐怡说:“他们不拆这房?”
杜铁说:“这里没一点利用价值,我早注意到配电房了,做规划的人说楼房要在离河堤两米远的地方修建。我们收拾一下先搬进来,这地方不在规划内,住上人,他们想拆房也没办法。”
俩人将配电房收拾干净,杜铁爬上房顶,用瓦片把漏雨的地方都补了补。他们最后一个搬出老屋,家具搬进去,两间小屋一间是寝室,一间是厨房、客厅、饭厅混搭。收拾妥后,唐怡满意地看着房间说:“租房的钱倒是省下了,只是以后上厕所不方便。”
杜铁说:“怎么不方便?出门是河,河对面是荒山,没人能看见,现在比老房还方便,我们自带天然卫生间。”
听杜铁说,唐怡笑起来,说:“这是我们的新家,第一顿饭一定得像模像样。”
俩人一块儿忙碌,做出几样菜,听着耳边的河水声,感觉这情调既异样又别致。只是躺上床后,寂夜之中河水声突兀出来,整夜都像有一列火车轰隆隆地从床头驶过。他们不停翻身,许久都无法入睡。第二天刚醒,唐怡说:“昨夜我做了个梦,梦见自己掉入河中,沉到河底,你伏在河边看不见我,哭得伤心。”
杜铁拍着脑袋,说:“有意思,我昨晚也梦见河,梦见我们就躺在河水上,随水不停飘流。”
唐怡说:“等新房修好,就不用听这水声了。”
杜铁说:“住段时间习惯就好。”
不久,一幢幢新楼矗立起来,曾经的砖厂有了新的名字,南苑小区。老住户按平方补差价,纷纷搬进新楼,更多陌生的家庭也来购房。不过对于唐怡和杜铁来说,新的问题又出来了,他们补差价的钱不够,好在开发商念及他们是砖厂的老职工,承诺钱凑足后,一样可以补差价住进新楼。
看着新楼就在眼前,唐怡叹口气说:“原指望新楼修好就住进去,现在又得等了。”
杜铁笑起来,说:“如果让我们搬进新楼,没这水声做伴,可能还睡不着。”
唐怡说:“总算有个盼头,没赶尽杀绝,我们只需再等些时间而已。”
杜铁卷起右手,三根断裂的手指像秃顶的头,他鼓着肱二头肌说:“有这一身力气,我们的好日子总会到来。”
高矗的新楼以及整个小区最终将他们隔离在外。要走上正道,得绕着楼房的背面,沿河堤跨过各种垃圾堆,才能来到南苑小区正面的巷子。因住户猛增,这条巷子比过去热闹许多,茶坊、小超市、小食店挨着排列。大部份人都陌生。杜铁和唐怡每日从小巷里外出打工,偶尔遇上砖厂的人,停下攀谈几句。初时杜铁还像过去那样热情,总说:“你绕过来玩嘛,我那虽小,却非常清净,喝点酒,说说话挺舒服,也只有我那里还有砖厂的老味道。”说过几次,没一人回应,想来也是,这年月喝两杯酒谁会绕那么远,去垃圾堆边喝?这巷子到夜里会支起许多烧烤摊,不仅方便,还非常热闹。杜铁不再邀人去家里,没什么话可聊时,他望着高楼说:“要不了多久,我也会住进来。”老邻居们看他和唐怡依然蓬勃,明白他们没日没夜地苦干,正努力凑着房钱。
他们所居的小房被高楼隔离,俩人也似被南苑小区屏蔽,没人再留意他们,连好朋友建军也有一大段时间没再见过。
那一年股票暴涨,一路飙升到六千多点。康定炒股票的人少,都将存款投入基金当中。人们遇见,谈论的事只一件,赚了多少?杜铁和唐怡四处打工,走哪里都能听见基金的事。俩人回来,晚饭时谈起这事,他们不明白股票也不明白基金,只明白所有人都在这上面挣钱。俩人打工许多年,到现在房款还差三万才凑足,按照基金的涨势,他们的存款投进去,半年时间就能将钱凑齐。俩人端着小酒杯,从配电房的窗口望出去,南苑小区的楼房高高在上,整齐排列的窗户此刻亮着灯,每扇窗户都有好看的窗帘悬着,映着灯光透出各种图案。
唐怡说:“如果我们搬进去,我要配粉红色的窗帘。”
杜铁脑袋里却是棉花糖的颜色,说:“不,得配奶白色。”
杜铁说奶白色,唐怡就不再坚持,点头说:“奶白色也好看,高贵。”
俩人盯着那些窗口,沉默了一会,唐怡说:“买基金不?”
杜铁说:“买!明天就去银行。”
唐怡说:“买!”
第二天一早起来,俩人去银行买基金。他们去时,银行的门还没开,俩人走到柜台前,办理业务的是个年青女孩,一笑两个酒窝。杜铁拿着存折,又问了问基金的事。那女孩笑容满面地告诉他们,基金这业务在康定还属于新业务,一两句话说不明白,感觉买基金比直接炒股安全许多,现在存款利率又低,买基金怎么也比存款划算吧?俩人放下心来,选了一支涨势极好的基金,把八万元全投进去。
他们在大盘进入五千多点时买进,买好基金,俩人像往常一样去干自己的活。半月之后,有一天杜铁正替别人搬家,手机响起来,他的手机铃声是《小苹果》,电话是唐怡打来,声音挺焦急,说:“听说没?基金开始跌了。”杜铁当即将手中的活托付给一块儿打工的,俩人汇合后往银行里跑,一查,才知道他们的基金已亏损一万。俩人走出银行,回到配电房里,唐怡说:“取不?”
杜铁的铁脾气显露出来,说:“亏了一万,这时候取,就真亏了。等着吧,总会涨起来。”
俩人无心再去打工,整天跑银行,让别人帮查亏损数额。那数字眼见一天天多起来,一万、两万、三万。
唐怡说:“取了吧。”
杜铁说:“这时候取,那些钱就白白扔了,起码得等到保本。”
不想一月时间里,大盘数字狂泻而下,跌回近两千点才停。他们去银行查,只剩两万了,唐怡对那有酒窝的女孩说:“你这女子,当时你说买基金比存钱划算,现在我们已亏了六万,你说怎么办?”
女孩哭丧着脸说:“这样的事谁都没办法想到,亏的不仅仅是你们,我家里亏得更多,全国人民都在亏,能怪谁?再说,你们买基金不是我逼迫的,你们自愿来银行买。”
杜铁站在一边,出气的声音极大,他只简单说了一个字:“取!”
他们带着两万元回到配电房,杜铁脸色阴沉,唐怡也愁眉苦脸,他们沉闷地坐在配电房中。天渐渐暗下来,新楼许多窗户的灯又亮了,唐怡看着那些灯,说:“怎么办?南苑小区的新楼房离我们越来越远了。”
杜铁望着黄昏里的新楼,说:“该我们的就是我们的,不该我们,怎么拼都没用。”
唐怡叹口气,一时无话。
杜铁站起来,他想开了,不再阴沉着脸,说:“走,吃东西去。”
唐怡说:“去外面?”
杜铁说:“去吃烧烤,有两万元在,心焦什么?”
唐怡和他有着相同的心情,俩人来到南苑小区的烧烤摊前,点了许多烧烤,又要了一大堆啤酒。烧烤摊烟雾缭绕,薰得一切都朦胧不清。俩人喝酒,不像过去那样节制,一杯杯倒满了干,那一晚他们不愿意谈论股票,谈论亏掉的钱,只沉默地喝酒。喝了一会儿,遇建军路过,瞧见他们,上前问:“咦,你俩今夜怎么来这里喝酒了?”
透过烟雾,杜铁看见建军衣着时尚,完全变了模样,指指身边的凳子说:“来,坐下,喝一杯,好些时间没一块儿喝酒了。”
看见老朋友,建军也高兴,坐下来倒杯啤酒,先敬过两人再问:“有一大段时间没看见你们了,在忙些什么?”
唐怡说:“能忙什么,每天四处打工呗。”
建军说:“长期打工也不是办法,我现在开茶妨,就在南苑小区二楼。说实话,我感谢砖厂破产,不然我开不了茶坊,劳累一年挣的钱当不了茶坊两月的收入。你们也尽快找个生意做起来嘛,现在这社会单靠体力,哪能挣到钱。”
杜铁看着建军,这个曾经的好朋友,砖厂变成南苑小区,他们基本失去联系,虽同在一个地方,却相隔甚远。现在建军变成茶坊老板,他不仅否定了杜铁靠体力挣钱的信念,竟然感谢起砖厂的倒闭。杜铁想不明白其中的缘由,像想不明白六万元在短短一月内就没了一样。
杜铁的眼睛发直,他端起酒杯,一口干了,拉着曾经的好朋友说:“你说说,你现在能干,人聪明,你说说我的六万元怎么说没就没了?它们去了哪里?”
杜铁一谈这个,唐怡就讲起买基金的事。闸口一经打开,俩人开始尽情倾吐。杜铁只纠结钱去了哪里的问题。唐怡却不停地回忆买基金那天的情景,回忆银行里替他们办理业务的女孩子,她记得那女孩的酒窝很迷人。
建军发现他俩已醉,去买了单,好不容易才将两人劝回。他看着他们的背影,俩人一路上还在相互诉说,他们的双肩斜着,背也有些驼,烟尘蒙蒙中,他们的背影总给建军一种错觉,俩人会随时坍塌到地上去。
那一天之后,在南苑小区的巷子里就能时常看见他们了。按杜铁的想法是能过一天过一天,忙了许多年,俩人该好好轻松一段时间,先把两万元花了,再去打工,省得对未来有盼头,反而烦躁,倒不如把这些念想全扔干净,活得轻松快乐,像砖厂兴旺时那样。基金的事让唐怡也灰了心,听杜铁这样说,觉得在理。不去打工,感觉无事可干,唐怡问:“待在家里我干些什么?”
杜铁说:“你看你就是个苦命人,让玩,尽然不知玩什么。你去建军那里打麻将吧,许多人都爱去他那玩。”
唐怡说:“你呢?”
杜铁说:“我是会享福的人,我过去最爱看电影,后来有电视方便,可惜我们忙,没好好看过。”
他们最早的小彩电坏了,杜铁替别人搬家时,拾回一台四十多英寸的大电视,连着音箱,那是别人淘汰的,抵了些工钱由他拿走。杜铁躺在床上打开电视,电视里正播《亮剑》,他一看就沉迷进去。
唐怡初来建军的茶坊,只站在边上看别人打麻将,只两三天时间,她就把麻将学会了,和别人打小牌,五元一局。她没想到一旦学会,这东西竟然有魔力一般,再也丢不掉,刚进麻场,都摸不清底细,也有三五个爱牌如命的,在茶坊里打连场,吃饭都叫外买。有一次连打两天两夜,到第三天黎明,人人脸青面黑,都没法继续,只唐怡大着嗓门说:“来啊,再摆上!”
俩人早晨睡懒觉,到中午起来,胡乱吃点东西,唐怡准时出门去打牌。她走在巷子里,染成土黄色的头发蓬松地披在后背,一手夹烟,一手捏着手机,随脚步摆动,不慌不忙地走,像一只肥胖的母鸡前去觅食。时常打夜场,唐怡抽烟很厉害,刚燃完一支,立即接上。烟熏火燎之后,她的嗓音开始沙哑,一说话,远远就知她来了。
杜铁则窝在家里没完没了地看电视剧,看到天将黄昏,才走到巷子。遇见烧烤摊边有熟人时,搭讪着坐下。他不仅迷电视,也迷上了酒。看见啤酒眼睛立即发亮。倒上酒,来不及吃东西,端酒的手微微颤抖,先得干一杯解馋,手不再抖,才挽起袖口将三根断指举起来,抱怨砖厂,说他是残疾人,他曾在砖厂做出如此大的贡献,但现在连住楼房的资格都没有。抱怨完砖厂,开始抱怨命运,说砖厂破产,虽早不存在了,还能让他骂骂。辛苦挣下的六万元被基金套走,连骂谁都找不着。每次喝酒,必喝到成堆的酒瓶立在脚边。老熟人不好说什么,夜深了,多取两瓶酒放桌上,再结账而回,留他一人继续喝。醉酒之后要摸回家去,一动脚都是酒瓶叮叮当当倒地的声音,给人感觉他脚下始终系着几支空酒瓶。除了老邻居,大家已不知他叫杜铁,只称他为杜酒瓶。
如没熟人,他自己坐下,简单点几样吃的,要一堆啤酒,自斟自饮,偶尔抬起头冲二楼喊:“棉花糖,打完没?我等你吃烧烤呢。”
唐怡在楼上也喊:“你别影响我,手气差,吃你的。”
偶尔唐怡赢钱,俩人都在烧烤摊前坐下,点菜点啤酒,然后冲着楼上叫砖厂曾经的朋友们,但没人前去,包括建军,谁也不忍让他们请客,又不愿自己拿钱请他们。不过这影响不了俩人快乐,他们同样可以喝得尽兴,醉酒之后相互搀着回配电房。
日子似乎又安稳下来,杜铁很快习惯了悠闲的生活。只是唐怡时常有些新想法。有天中午俩人起床,唐怡用沙哑的嗓音说:“杜铁,我俩去医院检查检查吧,要个孩子。我们没法生,去领养一个也成。”
杜铁说:“你怎么想起这个了?你不觉得这是上天眷顾我们,才没有孩子?有个孩子多麻烦,现在的孩子从出生到长大成人,全是钱堆出来的。有个孩子我们哪能这样轻松幸福?”
一说到钱,唐怡再不愿想孩子的事,只是时常忧郁,还新添了个口头禅,有事没事都爱说:“哎,看不见希望了。”
杜铁说:“这样的生活多好,别瞎想了。”
建县节前昔,俩人的电话忙碌起来,有许多活儿都找他们去做。康定建县,十年为一大庆,有盛大的文艺演出晚会,整座城市也要装饰一番。那帮过去一块儿搭活搬东西的人,应付不了庞大的工作,差人手,想起杜铁,给他打电话。那个早晨,杜铁和唐怡都躺在床上,前一夜俩人在烧烤摊边醉得不轻,这时正酣睡。红极一时的《小苹果》把他们从沉睡中吵醒,杜铁没接,直接挂了。不一会那首歌又响起来,杜铁揉着眼睛,半撑起身体,被吵醒的火无处发,听是叫去北门广场搬铁架搭舞台,他说有事去不了。倒头睡了不到十分钟,电话再次响起,那边说工钱给得好,十年大庆,钱不是问题。杜铁没好气地嚷:“能给多好?能好到六万?我现在不干这事了,你们别来烦我。”
杜铁的电话安静了,唐怡的电话却又响起来,仍是找她去干活的事。平日里一帮四处打工的,这会儿把能想到的人都叫了。唐怡回电话挺有意思,她不像杜铁那样冲对方发火,挺委婉地说:“我现在胖了,干不动体力活,再说,我也不用再干这些了。”
唐怡的确胖了,全身紧绷的肉都松懈下来,打麻将熬夜,眼袋呈灰褐色。杜铁被彻底吵醒,无心再睡,听唐怡回电话,笑了起来,说:“你这样讲,别人以为你过上好生活了,想不到你挺要面子。”
唐怡说:“我们还剩多少钱?”
杜铁说:“有五千多。”
唐怡说:“这钱用完了以后怎么办?”
杜铁说:“我有一身的力气,找点饭钱是轻松事,还有五千多,别担心。”
唐怡起床,四处看了看,两间小小的配电房里,所有家具,都是杜铁替别人搬家拾回来的。她把剩菜剩饭合一块儿热到电炉上,和杜铁吃。杜铁见她的脸色阴沉,问:“怎么了?”
唐怡摇头说没事。
吃完,见她情绪低落,杜铁说:“你去打牌吧,我来收。”
唐怡仍然摇头,默默地洗碗,把整个家都理了一遍,抹去电视、窗台上厚厚的灰尘后,准备出门,临走,她再次回头打量房间,看着杜铁叹口气说:“哎,看不见希望了。”
杜铁以为她去打麻将,没当回事。当夜她没回来,杜铁睡到第二天中午,仍不见人,才去建军的茶坊寻。到茶坊一问建军,说唐怡根本没来过。他当时就傻在茶坊里,失了魂一样。他想起这一段时间唐怡的种种表现,她忧郁的眼神以及临出门时说的话都不太正常,符合人们所说的抑郁症。这许多年里,她从没这样消沉过。他不知发生了什么,只怨自己大意,没注意她的异样。建军问他是不是吵架了,他摇头。建军安慰他说可能在别的地方打麻将,说着把附近茶坊的电话都打了一遍,没见着唐怡。茶坊里都是老客,大家猜测她为什么跑?会去哪里?有人小声说她长期打麻将,输多赢少,家里也没钱,她四处借,茶坊老板、老熟人,凡能开口的,都去借过,有可能借到高利贷躲债去了。建军看着杜铁,忙递眼色,让别说这个。杜铁已听清别人的话,高利贷和黑道沾边,都是不祥的事,他哭起来,边哭边说:“我那可怜的棉花糖啊,你究竟去哪里了?你打麻将需要钱,怎么不给我说?我明白你心痛我,怕拖累我,可你不能跑啊,就算欠别人钱,我们挣来还不就完了。我这辈子没本事,连你打小麻将的钱都挣不了,你要出个什么事,我可怎么办?”
杜铁越哭越厉害,众人无法劝慰,说什么他都听不进。时间大概是下午四点多,杜铁止住哭,茫然地看着众人说:“不行,我得去找棉花糖,找不回她,我也回不来了。”
说着他独自下楼,走出巷子,向城里走去。
建军看着他,知道这简单的话有多绝望,曾经无数次的变更、动荡,哪怕基金亏损,能改变的仅仅是他的生活态度,唯有找不着唐怡,才会给他致命一击。不过谁也没能力帮他,就算眼睁睁看他走向死亡。建军只能想着那首歌谣,看他的背影孤单远去。
砖厂在郊区,从砖厂到城里,有一段距离,大概两公里。杜铁走在路边,他看见沿路的灯柱、广告牌以及树上都张灯结彩,想起前一天忙碌的电话,如果没有这些电话,唐怡会像平时那样去打麻将,绝不会情绪低落。他看着一路的彩灯、彩旗,恨透了这个喜庆的节日。
他先去熟悉的人家找,挨着敲门,问唐怡来过没有。许多人都说一大段时间没见过了。有几家一见杜铁,忙说唐怡借钱的事,让想办法还上。唐怡真去别人那借了钱,这加重了杜铁不祥的预感。找遍熟人家,没任何消息。杜铁开始进入茶坊寻找,一家家问。茶坊的生意特别清淡,大部份人跑去看建县节的文艺演出。
杜铁几乎去了康定的每一家茶坊,也几乎跑遍每一条大街小巷。他后来站在北门广场外,场内正在进行大型演出,音乐混合各种嘈杂,一浪浪袭来,既喜庆又含混。广场大门紧闭,门前有许多公安和武警执勤。杜铁呆呆地看了看他们,否定了唐怡在里边看节目的想法,无论从情绪和经济上来说,都不可能。
时间已经很晚,城里灯火通明,不过行人稀少。杜铁来到下桥边,他看了看翻滚的河水,该找的地方都找了,康定城小,唐怡在这里除了他,也没别的亲戚,种种最坏的可能都挤进脑袋。更绝望的事是,就算把唐怡找回家,像她临走时说的那样,对未来依然看不见任何希望。杜铁长叹一口气,这条河从他出生开始,就在耳中喧响,几十年岁月一直奔腾不息,尤其住进配电房后,这条河成了唯一的邻居。他想起唐怡在配电房第一晚时做的梦,她梦见自己掉进河中。杜铁的心再一次收紧,这梦显然是个预兆。他伏在河栏上,看着翻腾的河水,满脑袋都想着要跳下去,追随唐怡而去。决心已定,那首歌谣简单的旋律飘浮在脑中,显得极为遥远,他尽力捕捉,听见街上的喧哗忽然大起来。
许多人都涌上街头,大概是晚会散场。他等待他们离开,再继续自己的事情。人越来越多,桥上、街沿都站满了人,他们不走,也在等待。杜铁有些纳闷,这些人像有意跟他作对,他愤怒地盯着人群,却没人注意到半个身子都探出桥栏的他。正在这时,当空一声炸响,所有灯光瞬间黯淡,红色的光芒映亮整座城市和群山。杜铁被那声炸响惊着,心里颤了颤,他抬起头来,一朵巨大的礼花正在夜空中盛开、漫延。跟着又是几声巨响,各色礼花相继在高空绽放出各种形状,发出耀眼的光芒。杜铁惊呆了,过年时,他和唐怡也爱放火炮、烟花。他们所放的火炮和烟花无论声响还是规模都没有这阵式,天差地别。这是他第一次在现场感受如此盛大的礼炮。他听边上的人说,礼炮专门派了部队去放,在后山无人的荒地上,驾着一大排礼炮。
轰隆一声,又一颗礼炮升腾而起,红色的亮点直奔高空,在挨着云层的地方炸响,响声似炮弹炸裂,震撼人心,随之一朵巨大的礼花在天空绽放。
满街的人纷纷举起相机、手机,不停地拍。还有人随着礼炮炸响打起尖锐的口哨。每一个人,无论孩子还是老人,无论男人还是女人,脸上都只剩下激动。炙热的情绪在人群中流淌,泛出波澜。
随第一声礼炮炸响开始,夜空中再没停止过绽放,各种礼花发出不同的声音,迸射出各色光芒,盛开在雪山之上,半个天空都是彩色的光影不停流动。
杜铁的心怦怦乱跳,他高昂起头,不错过每一次烟花绽放。烟花足足响了半小时才停下,人们四散开去。杜铁仍然盯着天空,他不知眼泪何时打湿了黝黑的脸庞。
他向家里走去时街上已空无一人,他没法压抑心里的激动,所有希望重又升起,他想得让唐怡戒掉麻将,他也不再沉溺于酒,他们将从新开始,像过去一样,充满朝气地生活。他还想唐怡怎么可能跳河呢?她不是寻短见的人,也就一时心烦,找地方放松一下。他相信今夜高高在上的礼花她一定也看见了,她会同样激动,同样燃起希望之火。他甚至十分肯定她这时候已回家,当转过南苑小区的巷子,他们小小的房间一定亮着灯光。
近两公里的路他都兴奋地小跑前进,直到进入南苑小区熟悉的巷子,直到即将拐入高楼背面,能看见家的地方,他的步履才再一次沉重起来。
原刊于《飞天》2022年第7期

尹向东,藏族,又名泽仁罗布,四川康定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自1995年开始文学创作以来,在期刊发表中短篇小说、散文一百多万字。著有中短篇小说集《鱼的声音》、长篇小说《风马》。作品被选入《新华文摘》《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中华文学选刊》《长江文艺好小说》等多种选刊,收入《2009中国年度短篇小说集》《21世纪年度小说选2014短篇小说》《2001——2010新世纪小说大系生态卷》等选本。获过多种文学奖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