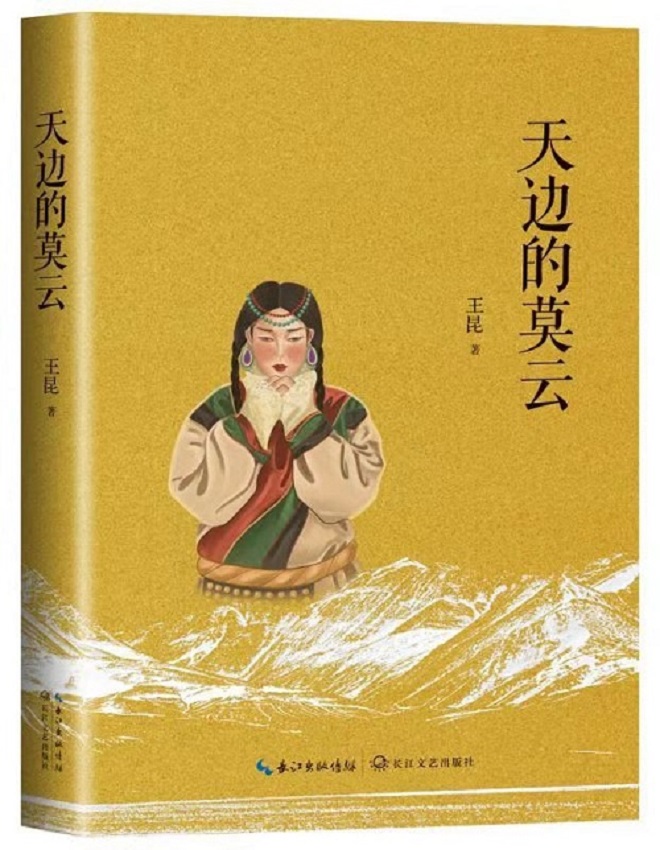
01
еӨӘйҳіиҝҳжІЎжңүе®Ңе…ЁеҚҮиө·жқҘпјҢиҢҒеЈ®зҡ„е…үиҠ’е·ІеңЁжқӮйӮЈж—Ҙж №зҘһеұұз»Ҳе№ҙиҰҶйӣӘзҡ„еұұе·…еӣӣж•ЈејҖжқҘпјҢз…§иҖҖзқҖж•ҙдёӘж јеҗүйғЁиҗҪпјҢз…§иҖҖзқҖйӣӘеұұи„ҡдёӢиө·дјҸзҡ„жІҷж—ҘеЎҳиҚүеңәгҖӮ
еңЁжқӮйӮЈж—Ҙж №еұұдёӢзҡ„жүҺжӣІжІіиҫ№пјҢж–‘й©ізҡ„иҚүең°дёҠж’‘ејҖеҮ йЎ¶жҙҒзҷҪзҡ„еёҗзҜ·пјҢеғҸеҮ жңөзҷҪдә‘еҒңй©»йӮЈйҮҢпјӣеёҗзҜ·еҗҺйқўдёҚиҝңеӨ„пјҢжҳҜдёҖжҺ’з®ҖеҚ•дҝ®йҘ°дәҶеұӢйЎ¶е’Ңй—ЁзӘ—зҡ„и—ҸејҸеңҹеқҜжҲҝгҖӮ
еёҗзҜ·жҳҜдё»дәәжҳҘеӨҸж”ҫзү§ж—¶з”Ёзҡ„пјҢеңҹжҲҝеҲҷжҳҜзүҰзүӣи¶ҠеҶ¬ж—¶зҡ„дҪҸжүҖгҖӮйӮЈз®ҖйҷӢзҡ„еңҹжҲҝе‘Ёеӣҙеһ’зқҖжҲҗзүҮжҲҗзүҮзҡ„иӨҗиүІеңҲеқ—пјҢйӮЈжҳҜж¬Ўд»ҒеӨ®е®—жҜҸеӨ©з§ҜзҙҜзҡ„收иҺ·гҖӮж¬Ўд»ҒеӨ®е®—еҮ д№ҺжҜҸеӨ©ж—©жҷЁдёғзӮ№е°ұиғҢдёҠй•ҝй•ҝзҡ„зүӣзІӘиўӢеӯҗеҮәй—ЁпјҢжІҝзқҖжӢүзҸҚ欧зҸ е’ҢзүӣзҫӨиө°иҝҮзҡ„и·Ҝеҫ„пјҢжҠҠзүҰзүӣжҺ’еңЁи·ҜдёҠе·Із»ҸеҚҠе№Ізҡ„зІӘе ҶжҚЎжӢҫеӣһжқҘгҖӮ
иҝҷдәӣж•ЈиҗҪеңЁиҚүзҡ®дёҠзҡ„зүӣзІӘпјҢжҳҜжқӮйӮЈж—Ҙж №зҘһеұұиөҗз»ҷиҝҷзүҮиҚүеңәзҡ„е®қи—ҸгҖӮиҖҢж—©жҷЁеҲҡжҺүдёӢжқҘзҡ„зүӣзІӘпјҢж¬Ўд»ҒеӨ®е®—дёҚдјҡзҗҶе®ғ们пјҢеӨӘж–°йІңзҡ„зІӘе ҶжӢҫдёҚиө·жқҘпјҢе®ғйңҖиҰҒдёҖиҪ®йҳіе…үзҡ„жҷҫжҷ’гҖӮ
ж¬Ўд»ҒеӨ®е®—з«ҷеңЁжҲҝеүҚпјҢеҸҢжүӢиҷ”иҜҡең°дҪңжҸ–пјҢеҜ№зқҖй«ҳй«ҳзҡ„жқӮйӮЈж—Ҙж №зҘһеұұгҖӮдҪңдёәж јеҗүйғЁиҗҪзҡ„еӯҗж°‘пјҢж¬Ўд»ҒеӨ®е®—жҜҸеӨ©йғҪиҰҒжӢңи°ўдёҖдёӢжқӮйӮЈж—Ҙж №еұұзҘһпјҢе®ғжҳҜж•ҙдёӘйғЁиҗҪзҡ„е®ҲжҠӨзҘһгҖӮзӣёдј еңЁеҫҲж—©д»ҘеүҚпјҢжІҷж—ҘеЎҳиҚүеңәиҜһз”ҹдәҶиҝҷзүҮзү§еҢәжңҖеӨ§зҡ„йғЁиҗҪвҖ”вҖ”ж јеҗүйғЁиҗҪпјҢе®ғзҡ„зҷҫжҲ·е°ұжӣҫз»Ҹй©»жүҺеңЁиҝҷзүҮиҚүеңәдёҠгҖӮ
д»ҺйӮЈж—¶иө·пјҢжқӮйӮЈж—Ҙж №е°ұдёҖзӣҙжҠӨдҪ‘зқҖиҝҷзүҮиҚүеңәзҡ„еӯҗж°‘гҖӮеҜ№зқҖзҘһеұұпјҢж¬Ўд»ҒеӨ®е®—иҜҙеҮәдәҶиҮӘе·ұзҡ„зҘҲжұӮе’Ңж„ҝжңӣпјҢе°ҸеӯҷеҘіжӢүзҸҚ欧зҸ зҡ„дёҖдёӘиҖіжңөеҗ¬еҠӣдёҚеҘҪпјҢж¬Ўд»ҒеӨ®е®—еёҢжңӣеҘ№иғҪеҝ«дәӣеҘҪиө·жқҘгҖӮ
иҝӣеҲ°жҲҝеӯҗйҮҢпјҢж¬Ўд»ҒеӨ®е®—жҚЎиө·еҮ дёӘе№ІзүӣзІӘеқ—ејҖе§Ӣзғ§зҒ«пјҢеҘ№жҠҠдёҖжЎ¶зүҰзүӣеҘ¶еҖ’иҝӣй“Ғй”…йҮҢпјҢејҖе§ӢзҶ¬еҲ¶еҘ¶й…ӘгҖӮйҷӨдәҶиҮӘеҲ¶еҘ¶й…ӘпјҢж¬Ўд»ҒеӨ®е®—дәІжүӢеҒҡзҡ„зүҰзүӣиӮүе№Ід№ҹеҝ…дёҚеҸҜе°‘пјҢйӮЈжҳҜе°ҸеӯҷеҘіжӢүзҸҚ欧зҸ еҳҙйҮҢзҰ»дёҚдәҶзҡ„дёңиҘҝгҖӮ
ж¬Ўд»ҒеӨ®е®—家жҳҜиҺ«дә‘д№Ўз»“з»•зү§е§”дјҡзҡ„дёҖдёӘж•Јиҝңзү§зӮ№гҖӮз»“з»•зү§е§”дјҡзҡ„иҚүеңәжҜ”иҫғеӨ§пјҢзү§жҲ·д№Ӣй—ҙдҪҸеҫ—д№ҹеҫҲеҲҶж•ЈпјҢдёҖжҲ·дёҺеҸҰдёҖжҲ·зҡ„и·қзҰ»йҖҡеёёе°ұжңүеҚҒеҮ е…¬йҮҢгҖӮж¬Ўд»ҒеӨ®е®—еҫҲе°‘еҲ°зү§е§”дјҡеҺ»пјҢйҷӨдәҶжңүеҮ ж¬ЎеҲ°жӢүзҸҚ欧зҸ жүҖеңЁзҡ„зү§еҢәе°ҸеӯҰпјҢдёҖиҲ¬еҘ№йғҪдёҚдјҡзҰ»ејҖжүҺжӣІжІіиҫ№гҖӮ
еҘ¶й…ӘеңЁй”…йҮҢеҮқеӣәпјҢж¬Ўд»ҒеӨ®е®—е°ҶеҲҡеҲҡжӢҫеӣһзҡ„еҚҠе№ІзүӣзІӘпјҢеһ’ж”ҫеңЁйҷўеўҷи§’гҖӮеңЁиҝҷжө·жӢ”дә”еҚғзұізҡ„жІҷж—ҘеЎҳиҚүеңәдёҠпјҢйқ жқӮйӮЈж—Ҙж №зҘһеұұжҠӨдҪ‘пјҢзүҰзүӣеҗғзқҖйІңе«©зҡ„иҚүиҠҪпјҢе–қзқҖеӣӣеӯЈеҶ°е°Ғзҡ„йӣӘеұұеңЈж°ҙпјҢе®ғ们дә§зҡ„еҘ¶д№ҹиҗҘе…»е……жІӣгҖӮ
й—ЁеүҚзҡ„жүҺжӣІжІіжҳҜжұҮе…ҘжҫңжІ§жұҹзҡ„ж”ҜжөҒпјҢдё№еўһе–ҮеҳӣиҜҙиҝҮпјҢиҝҷйҮҢжөҒж·Ңзҡ„еңЈж°ҙдјҡеҲ°иҫҫеҘҪеҮ дёӘеӣҪ家гҖӮж¬Ўд»ҒеӨ®е®—жғіпјҢд№ҹе°ұжҳҜиҜҙпјҢжүҺжӣІжІійҮҢзҡ„еңЈж°ҙе…»иӮІзқҖеҮ дёӘеӣҪ家гҖӮ
ж јдә‘жқ‘йӮЈдёӘеҲҡеҲҡеӨ§еӯҰжҜ•дёҡеӣһжқҘзҡ„ж јжЎ‘жӢүе§Ҷд№ҹиҜҙиҝҮпјҢдёҚиҝҮпјҢеҘ№е’Ңдё№еўһе–Үеҳӣзҡ„иҜҙжі•дёҚдёҖж ·гҖӮж јжЎ‘жӢүе§ҶиҜҙзҡ„жӣҙеғҸеӨ–йқўдәәзҡ„иҜҙжі•пјҢиҜҙиҝҷйҮҢжҳҜдёӯеҚҺж°ҙеЎ”гҖӮвҖңдёӯеҚҺвҖқзҡ„ж„ҸжҖқпјҢж¬Ўд»ҒеӨ®е®—жҮӮеҫ—пјҢдҪҶж°ҙеЎ”жҳҜдёӘд»Җд№ҲпјҢж¬Ўд»ҒеӨ®е®—并没жңүеҗ¬жҮӮж јжЎ‘жӢүе§Ҷзҡ„и§ЈйҮҠгҖӮеҗҺжқҘпјҢеҗ¬жІҷж—ҘеЎҳиҚүеңәзҡ„жҙӣжүҺжӣје·ҙиҜҙпјҢвҖңж°ҙеЎ”вҖқе°ұе’ҢвҖңиҚүеңәвҖқдёҖж ·пјҢеӯҳз»ӯзқҖе·Қе·ҚйӣӘеұұдёҠжөҒж·ҢдёӢжқҘзҡ„йӣӘж°ҙгҖӮ
дҪҶдёҚз®ЎеҰӮдҪ•пјҢж¬Ўд»ҒеӨ®е®—дёҖ家е’ҢеҘ№д»¬зҡ„зүҰзүӣйғҪжҳҜе–қзқҖжқӮйӮЈж—Ҙж №жұҮе…ҘжүҺжӣІжІізҡ„еңЈж°ҙй•ҝеӨ§зҡ„пјҢе’ҢйӮЈеҘҪеҮ дёӘеӣҪ家зҡ„дәәдёҖж ·гҖӮеҜ№пјҢзүҰзүӣд№ҹжҳҜ家дәәпјҢж¬Ўд»ҒеӨ®е®—жғіеҲ°е®¶йҮҢзҡ„зүӣзҫӨе°ұеҫҲејҖеҝғгҖӮ
ж јжЎ‘жӢүе§ҶжҳҜиҝҷзүҮиҚүеңәдёҠзҡ„зү§ж°‘зҡ„йӘ„еӮІпјҢжҳҜиҚүеңәдёҠзҡ„й№°пјҢеҘ№еҸҜд»Ҙеҗ‘зқҖйӣӘеұұд№Ӣе·…еұ•зҝ…йЈһзҝ”гҖӮж јжЎ‘жӢүе§ҶжүӢйҮҢжңүдёҖдёӘеёёеёёй—ӘзқҖе…үдә®еҸ«вҖңжүӢжңәвҖқзҡ„й•ҝж–№еҪўдёңиҘҝпјҢеҘ№з»Ҹеёёз”Ёе®ғжқҘеҜ»жүҫвҖңзҷҫеәҰвҖқгҖӮж¬Ўд»ҒеӨ®е®—дёҚзҹҘйҒ“вҖңзҷҫеәҰвҖқиҝҷдёӘиҜҚжҳҜе•Ҙж„ҸжҖқпјҢдҪҶиҝҷеҫҲзҘһеҘҮпјҢд»ҘеүҚе…Ёйқ еҺ»еҜәеәҷйҮҢй—®е–ҮеҳӣжүҚиғҪзҹҘйҒ“зҡ„дәӢжғ…пјҢж јжЎ‘жӢүе§ҶиҜҙеҘ№вҖңзҷҫеәҰвҖқдёҖдёӢе°ұиғҪзҹҘйҒ“пјҢиҝҷи®©еҳҺе°”иҗЁеҜәйҮҢзҡ„дё№еўһе–ҮеҳӣеҫҲжҳҜдёҚж»ЎпјҢи®ӨдёәиҝҷеҶІж’һдәҶзҘһзҒөгҖӮ
дҪҶжҳҜжёҗжёҗең°пјҢзү§еңәжӢҝзқҖвҖңжүӢжңәвҖқзҡ„дәәеӨҡдәҶиө·жқҘпјҢеҳҺе°”иҗЁеҜәзҡ„еғ§дәә们д№ҹе°ұдёҚз®ЎйӮЈд№ҲеӨҡдәҶпјӣжёҗжёҗең°пјҢеғ§дәә们зҡ„жүӢйҮҢд№ҹжңүдәҶиҝҷж ·зҡ„дёңиҘҝгҖӮвҖңдёӯеҚҺж°ҙеЎ”вҖқпјҢе°ұжҳҜж јжЎ‘жӢүе§Ҷд»ҺжүӢжңәдёҠвҖңзҷҫеәҰвҖқзҡ„иҜқгҖӮеҘ№иҜҙз»ҷжқӮйӮЈж—Ҙж №зҘһеұұдёӢзҡ„ж¬Ўд»ҒеӨ®е®—еҘ№д»¬еҗ¬пјҢдәҺжҳҜж•ҙдёӘиҚүеңәдҫҝи®°дҪҸдәҶиҝҷдёӘиҜҚиҜӯгҖӮ
02
еҘ¶й…ӘеҒҡеҘҪдәҶпјҢж¬Ўд»ҒеӨ®е®—ж’‘иө·и…°еҸҲзңҜзјқиө·зңјзқӣжңӣдәҶдёҖзңјйӣӘеұұгҖӮ
д»ҠеӨ©еҘ№жҜ”еҫҖеёёеӣһжқҘеҫ—ж—©дёҖдәӣпјҢиҰҒзӯүзқҖи—ҸеҢ»жҙӣжүҺжӣје·ҙиҝҮжқҘдёәеҘ№жІ»з—…гҖӮж¬Ўд»ҒеӨ®е®—зҡ„з—…еңЁжІҷж—ҘеЎҳиҚүеңәеҫҲеёёи§ҒпјҢдҪҶд№ҹеҫҲжҠҳзЈЁдәәгҖӮж¬Ўд»ҒеӨ®е®—и·ҹ家дәәиҜҙпјҢиҝҷдёӘз—…еҸҜд»ҘдёҚз®Ўе®ғпјҢдәәжҖ»жҳҜиҰҒжӯ»д№ҲпјҢйӮЈе°ұеҚҮеӨ©дәҶгҖӮдҪҶжҳҜпјҢиҝҷж ·зҡ„з—…еҪұе“ҚжҚЎжӢҫзүӣзІӘпјҢејҜи…°д№…дәҶе°ұдјҡжҷ•еҖ’гҖӮиҖҢзүӣзІӘеӨӘиҰҒе‘ҪдәҶпјҢеңЁжІҷж—ҘеЎҳиҚүеңәпјҢжҜҸеҲ°еҶ¬еӯЈпјҢж°”жё©еёёеёёеңЁйӣ¶дёӢдёүеҚҒж‘„ж°ҸеәҰе·ҰеҸіпјҢжІЎжңүзүӣзІӘеҸ–жҡ–пјҢйӮЈдјҡеҶ»жӯ»зүҰзүӣе’ҢжӢүзҸҚзҡ„гҖӮ
зүӣзІӘи·ҹйӣӘеұұдёҖж ·йҮҚиҰҒгҖӮдёәдәҶдёҚиҖҪиҜҜжҚЎжӢҫзүӣзІӘиҝҷж ·зҡ„еӨ§дәӢпјҢж¬Ўд»ҒеӨ®е®—еҶіе®ҡвҖңж”ҫиЎҖвҖқгҖӮ
дёүеӨ©еүҚпјҢеҘ№жүҳд»ҳд»Һд№Ўж”ҝеәңеӣһжқҘеҠһдәӢзҡ„ж јжЎ‘жӢүе§ҶпјҢи®©еҘ№дёҖе®ҡиҰҒиҪ¬ејҜеҺ»дёҖи¶ҹжҙӣжүҺжӣје·ҙзҡ„иҜҠжүҖгҖӮжҙӣжүҺжӣје·ҙзҡ„иҜҠжүҖеңЁдёҖжқЎеҸҜд»ҘйҖҡеҫҖжӢүиҗЁзҡ„еӨ§йҒ“иҫ№дёҠпјҢжҙӣжүҺжӣје·ҙд№ӢжүҖд»ҘжҠҠиҜҠжүҖејҖеңЁйӮЈйҮҢпјҢжҳҜеӣ дёәйӮЈйҮҢиҝҮеҫҖзҡ„дәәжҜ”иҫғеӨҡгҖӮж¬Ўд»ҒеӨ®е®—еҗ¬д»–们иҜҙиҝҮпјҢеүҚеҺ»еёғиҫҫжӢүе®«жңқеңЈзҡ„дәәзҫӨдёӯпјҢеҫҲеӨҡйҖ”з»ҸиҝҷйҮҢзҡ„з—…дәәйғҪдјҡеҲ°жҙӣжүҺжӣје·ҙзҡ„иҜҠжүҖжҠ“иҚҜгҖӮжҙӣжүҺжӣје·ҙзҡ„иҜҠжүҖд»ҺдёҚ收иҙ№пјҢжҙӣжүҺжӣје·ҙиҜҙпјҢеҸӘиҰҒжҳҜз—…дәәпјҢе°ұйңҖиҰҒеё®еҠ©гҖӮ
жҙӣжүҺжӣје·ҙжҳҜжІҷж—ҘеЎҳиҚүеңәдёҠзҡ„и—ҸеҢ»пјҢз”ұдәҺзҺ°д»ЈеҢ–зҡ„еҢ»з–—жүӢж®өеңЁиҝҷйҮҢеҸ‘еұ•зј“ж…ўпјҢеҫҲеӨҡе№ҙжқҘпјҢд»–дёҖзӣҙеқҡжҢҒз”Ёи—ҸеҢ»иҚҜж–№ејҸдёәзү§ж°‘们治疗гҖӮжҙӣжүҺжӣје·ҙе…ұжңүе…ӯдёӘеӯ©еӯҗпјҢйҷӨе…¶дёӯдёҖдёӘйҖҒеҲ°еҳҺе°”иҗЁеҜәзҡ„дё№еўһе–Үеҳӣиә«иҫ№дҝ®иЎҢд№ӢеӨ–пјҢе…¶дҪҷйғҪеңЁе®¶йҮҢеё®д»–йҮҮйӣҶиҚҜжқҗгҖӮ
жҙӣжүҺ家зҡ„е°ҸйҷўеӯҗпјҢе°ұиҰҒжҲҗдёәдёҖдёӘе°ҸеҲ¶иҚҜеҺӮдәҶгҖӮд»–зҡ„дёңеҺўжҲҝйҮҢдҪҸзқҖдёҖ家дёғеҸЈпјҢиҖҢиҘҝеҺўжҲҝе…ЁжҳҜеҗ„з§ҚиҚүиҚҜе’Ңзҹіеқ—гҖӮйӮЈдәӣе·Із»Ҹиў«еҠ е·ҘеҘҪзҡ„иҚҜдёёпјҢз„•еҸ‘зқҖеҗ„з§ҚйўңиүІпјҢе®ғ们被装иҝӣдёҖдёӘдёӘзҺ»з’ғ瓶еӯҗпјҢдёәж•ҙдёӘжІҷж—ҘеЎҳиҚүеңәзҘӣйҷӨз—…з—ӣгҖӮ
жҙӣжүҺжӣје·ҙзҡ„иҚҜжқҗжқҘиҮӘжқӮйӮЈж—Ҙж №зҘһеұұе‘Ёиҫ№зҡ„й«ҳеұұдёҠпјҢжңүдәӣжҳҜжӨҚзү©пјҢжңүдәӣжҳҜзҹіеқ—гҖӮжҙӣжүҺжӣје·ҙеңЁжүҺжӣІжІійҮҢйҮҮйӣҶй…ҚиҚҜз”Ёзҡ„зҹіеқ—ж—¶пјҢжӣҫз»ҸжңүдёҖж¬ЎеҲ°ж¬Ўд»ҒеӨ®е®—家讨ж°ҙе–қгҖӮеңЁдёәж¬Ўд»ҒеӨ®е®—й—®иҜҠд№ӢеҗҺпјҢжҙӣжүҺжӣје·ҙи®ӨдёәеҘ№еҫ—дәҶдёҖз§ҚйңҖиҰҒд»Һиә«дҪ“йҮҢвҖңж”ҫиЎҖвҖқзҡ„з—…гҖӮ
жҙӣжүҺжӣје·ҙиҜҙпјҡвҖңеҘҪз«Ҝз«Ҝзҡ„пјҢе°ұжҳҜиЎҖж¶ІеӨӘеӨҡдәҶпјҢйңҖиҰҒж”ҫеӣһеҺ»гҖӮвҖқж¬Ўд»ҒеӨ®е®—иҢ«з„¶ең°зӮ№зӮ№еӨҙпјҢд»Җд№ҲеҸ«ж”ҫеӣһеҺ»е‘ўпјҢеҘ№и§үеҫ—еҗ¬зқҖе°ұиЎҢпјҢиҮӘе·ұд№ҹдёҚз”ЁеҺ»еј„жҳҺзҷҪгҖӮ
е°Ҫз®ЎеӣһжқҘеҫ—еҫҲж—©пјҢдҪҶж¬Ўд»ҒеӨ®е®—д»ҠеӨ©жҚЎдәҶж»Ўж»ЎдёҖиўӢеӯҗзүӣзІӘгҖӮж¬Ўд»ҒеӨ®е®—жҠҠе®ғ们з ҢеңЁжҲҝеӯҗе‘Ёеӣҙзҡ„з©әең°дёҠпјҢдёҖеұӮеұӮз Ғж”ҫж•ҙйҪҗпјҢеҸӘйңҖеҶҚжқҘеҮ ж¬ЎеӨӘйҳіпјҢе®ғ们еҪ»еә•жҷ’жҺүж№ҝж°”пјҢе°ұеҸҜд»Ҙж‘ҶеңЁжҲҝеӯҗе‘Ёеӣҙзҡ„зүӣзІӘеўҷдёҠдәҶгҖӮ
зүӣзІӘеўҷз ҢеңЁжҲҝеӯҗзҡ„еӨ–еӣҙпјҢиҝҷж ·пјҢи§ҶеҠӣдёҚеҘҪзҡ„жЈ•зҶҠе°ұдёҚйӮЈд№Ҳе®№жҳ“и·ЁиҝҮеҺ»дәҶгҖӮжӢүзҸҚ欧зҸ еңЁеҚҒдәҢеІҒзҡ„ж—¶еҖҷпјҢе°ұзў°еҲ°иҝҮжЈ•зҶҠгҖӮ
03
жқҘдәҶйӣӘзҒҫзҡ„йӮЈдёӘеҶ¬еӨ©пјҢжқӮйӮЈж—Ҙж №зҘһеұұж•ҙдёӘзҷҪдәҶиә«еӯҗгҖӮеұұйЎ¶жёёиө°зҡ„йӣӘиұ№йғҪеҶ»жӯ»дәҶпјҢжӣҙеҲ«иҜҙжҲҗзҫӨзҡ„зүӣзҫҠгҖӮжӢүзҸҚ欧зҸ зҡ„зүҰзүӣзҫӨеңЁйӮЈдёӘйӣӘеӯЈжңүдёҖж¬ЎеҫҲеӨ§зҡ„жҚҹеӨұпјҢжңүдёүеҚҒеӨҡеӨҙе·Із»ҸжүҫеҲ°дәҶе°ёдҪ“пјҢиҖҢеү©дҪҷзҡ„еҚҒеӨҡеӨҙеҚҙдёҚзҹҘеҺ»дәҶе“ӘйҮҢгҖӮ
еқҗеңЁзүӣзІӘзӮүеӯҗеүҚзғӨзҒ«зҡ„ж—¶еҖҷпјҢеҘ¶еҘ¶ж¬Ўд»ҒеӨ®е®—иҜҙеү©дҪҷзҡ„зүҰзүӣиӮҜе®ҡе·Із»ҸеҶ»жӯ»дәҶпјҢиҖҢжӢүзҸҚ欧зҸ еҚҙй“ҒдәҶеҝғиҰҒеҺ»еҜ»жүҫе®ғ们гҖӮ
еҘ¶еҘ¶жғіеӨҡиҜҙеҮ еҸҘйҳ»жӢҰжӢүзҸҚ欧зҸ пјҢдҪҶжӢүзҸҚ欧зҸ иҜҙпјҢиҰҒи®°дҪҸдё№еўһе–Үеҳӣзҡ„иҜқе‘ўгҖӮж¬Ўд»ҒеӨ®е®—е°ұдёҚеҗӯеЈ°дәҶгҖӮ
еӨ–йқўйЈҺйӣӘеҫҲеӨ§пјҢеҮәдәҶеёҗзҜ·е°ұеҫҲйҡҫиҝҲжӯҘпјҢе№ёеҘҪзүӣзҫӨеүҚдёҖеӨ©иҝ”еӣһеёҗзҜ·еҢәж—¶иё©еҮәдәҶдёҖжқЎйҒ“пјҢеҰӮд»Ҡзҡ„ж–°йӣӘйЈҳиҗҪдёҠйқўпјҢд№ҹиғҪзңӢеҮәйҒ“и·Ҝзҡ„з—•иҝ№гҖӮжӢүзҸҚ欧зҸ з©ҝзқҖж·ұж·ұзҡ„зүӣзҡ®жҜЎйқҙпјҢйӮЈжҳҜдёҠдёҖж¬Ўиөӣ马иҠӮзҡ„ж—¶еҖҷпјҢеҘ¶еҘ¶жүҳдәҶжүҚд»Ғй—№еёғеӨ§еҸ”йӘ‘дәҶдёӨеӨ©зҡ„ж‘©жүҳеҲ°еҺҝеҹҺдёәеҘ№е®ҡеҒҡзҡ„гҖӮ
и®ҫеңЁеҺҝеҹҺиҫ№дёҠжҒ©з§‘иөӣ马еңәйҮҢзҡ„жҙ»еҠЁжӢүзҸҚ并没жңүеҸӮеҠ пјҢдҪҶжҚ®еҸӮеҠ дәҶиөӣ马зҡ„жүҚд»Ғй—№еёғеӨ§еҸ”иҜҙпјҢеңәйқўйқһеёёж°”жҙҫпјҢеҫҲеӨҡеӣҪ家зҡ„дәәйғҪжқҘдәҶгҖӮдҪҶжҳҜжүҚд»Ғй—№еёғд№ҹз–‘жғ‘дёҚи§Јең°иҜҙдәҶпјҢеҘҪеҘҪзҡ„иөӣ马иҠӮпјҢеңәйқўд№ҹеҫҲзғӯй—№пјҢдҪҶеҒҸеҒҸжҢӮзҡ„ж ҮиҜӯдёҚжҳҜиөӣ马иҠӮпјҢиҖҢжҳҜеҸ«д»Җд№ҲжіӣжҫңжІ§жұҹжөҒеҹҹж–ҮеҢ–иүәжңҜиҠӮгҖӮ
е’ҢжүҚд»Ғй—№еёғзҡ„зңӢжі•дёҖж ·пјҢйҡ”еЈҒжқ‘йӮЈдёӘеҫҲжңүеӯҰй—®зҡ„ж јжЎ‘жӢүе§Ҷд№ҹдёҚе–ңж¬ўиҝҷж ·зҡ„еҗҚеӯ—пјҢйҮҚзӮ№дёҚзӘҒеҮәгҖӮиөӣ马е°ұжҳҜиөӣ马пјҢеҘҪеҘҪиөӣд№ҲпјҢжҗһд»Җд№Ҳж–ҮеҢ–иүәжңҜиҠӮпјҹж јжЎ‘жӢүе§ҶиҝҳиҜҙпјҢйўҶеҜјдёҖдёӘжҺҘдёҖдёӘең°и®ІиҜқпјҢжІЎе®ҢжІЎдәҶпјҢ马е„ҝйғҪзқҖжҖҘдәҶпјҢиҝһзқҖжӢүдәҶеҮ ж¬ЎзІӘдҫҝгҖӮ
з©ҝзқҖжҜЎйқҙзҡ„жӢүзҸҚ欧зҸ иғЎд№ұжғізқҖиҝҷдәӣдәӢжғ…пјҢеҘ№иө°еҫ—еҫҲжҖҘпјҢдёҖиҫ№иө°зқҖпјҢдёҖиҫ№дҪҝеҠІиЈ№зҙ§дәҶжҠ«еңЁиә«дёҠзҡ„зҫҠзҡ®жЈүиў„пјҢи…°йҮҢзҡ„жқҹеёҰеҶҚзҙ§дёҖдәӣпјҢи„‘иўӢеҶҚеҫҖзҫҠзҡ®еёҪеӯҗйҮҢй’»ж·ұдәӣгҖӮеҘ№еӨ§дҪ“зҹҘйҒ“еӨұиёӘзҡ„зүҰзүӣдјҡеҫҖе“Әе„ҝйҖғе‘ҪпјҢд№ӢеүҚжүҫеӣһжқҘзҡ„дёүеҚҒеӨҡеӨҙпјҢеҘ№е°ұжҳҜеҮӯзқҖиҝҷж ·зҡ„йў„ж„ҹжүҫеҲ°зҡ„гҖӮ
жҢүз…§зү§еҢәзҡ„д№ жғҜпјҢжӢүзҸҚ欧зҸ дёҚйңҖиҰҒеҺ»жүҫиҝҷдәӣеӨұиёӘжҲ–е·Іжӯ»еҺ»зҡ„зүҰзүӣпјҢжӣҙдҪ•еҶөпјҢе®ғ们зҡ„зЎ®жӯ»дәҶгҖӮеңЁи—Ҹж°‘зҡ„дј з»ҹйҮҢпјҢз”ҹдёҚеёҰжқҘгҖҒжӯ»дёҚеёҰеҺ»пјҢз”ҹзҡ„ж—¶еҖҷе…үзқҖиә«еӯҗпјҢеҲ°еұұеқЎдёҠзҡ„еҳҺе°”иҗЁеҜәйҮҢпјҢжүҫдё№еўһе–ҮеҳӣйӮЈйҮҢйўҶеҸ–дёҖдёӘеҗҚеӯ—е°ұиЎҢдәҶпјӣиҖҢеҲ°дәҶжӯ»зҡ„ж—¶еҖҷпјҢеҰӮжһңиғҪиҙЎзҢ®жӯ»еҺ»зҡ„иӮүиә«пјҢи®©еӨ©дёҠзҡ„з§ғ鹫йҘұйЈҹдёҖйЎҝпјҢиҝҷдёҖз”ҹзҡ„иҪ®еӣһе°ұз®—еңҶж»Ўе®ҢжҲҗдәҶгҖӮ
е’Ңж јеҗүйғЁиҗҪйҮҢзҡ„дәәдёҖж ·пјҢйӣӘеұұдёӢд»»дҪ•жңүз”ҹе‘Ҫзҡ„дёңиҘҝдёҖж—ҰеӨұеҺ»з”ҹе‘Ҫд№ӢеҗҺпјҢе®ғ们е°ұеҝ…йЎ»еҺҹеҺҹжң¬жң¬ең°еӣһеҪ’еӨ§иҮӘ然еҺ»гҖӮжӯ»еҺ»зҡ„зүӣзҫҠж— и®әжҡҙжҜҷдәҺе“ӘдёҖеӨ„зҡ„жҡҙйЈҺйӣӘпјҢйғҪе°ҶжҳҜз•ҷз»ҷйӣӘиұ№гҖҒйҮҺзӢје’Ңз§ғ鹫зҡ„зҫҺйЈҹпјҢзүҰзүӣе®ҢжҲҗдәҶе®ғ们зҡ„з”ҹе‘ҪиҪ®еӣһпјҢд№ҹжҳҜе№ёзҰҸзҡ„гҖӮ
04
дҪҶжӢүзҸҚ欧зҸ е°ұжҳҜжғіжүҫеҲ°е®ғ们пјҢжӣҙеҮҶзЎ®ең°иҜҙпјҢжҳҜи§ҒеҲ°е®ғ们пјҢе“ӘжҖ•еҸӘзңӢдёҖзңјд№ҹе°ұж»Ўи¶ідәҶпјӣиҝҳжңүдёҖдёӘйҮҚиҰҒзҡ„еҺҹеӣ жҳҜпјҢдё№еўһе–Үеҳӣе‘ҠиҜ«иҝҮзү§ж°‘пјҢдёҖж—ҰзүӣзҫҠжӯ»дәҶпјҢеҚғдёҮдёҚиҰҒи®©е®ғ们зҡ„е°ёдҪ“жіЎеңЁзҘһеұұдёҠжөҒж·Ңзҡ„жІійҒ“дёӯпјҢдё№еўһе–ҮеҳӣиҜҙйӮЈж ·дјҡжұЎжҹ“дёӢжёёж°ҙжәҗгҖӮ
жӢүзҸҚ欧зҸ зӘҒ然жғіеҲ°пјҢдёӢжёёж°ҙжәҗпјҢжҳҜдёҚжҳҜе°ұжҳҜж јжЎ‘жӢүе§ҶиҜҙзҡ„йӮЈд»Җд№ҲвҖңжіӣжҫңжІ§жұҹжөҒеҹҹеӣҪ家вҖқе‘ўпјҹд№ҹе°ұжҳҜиҜҙпјҢеҰӮжһңдёҖеӨҙзүҰзүӣеңЁиҝҷйҮҢжұЎжҹ“дәҶдёҖжқЎжІійҒ“пјҢеҘҪеҮ дёӘеӣҪ家зҡ„дәәйғҪдјҡе–қеҲ°дёҚжҙҒзҡ„ж°ҙдәҶгҖӮжғіеҲ°иҝҷйҮҢпјҢжӢүзҸҚ欧зҸ жӣҙиҰҒеҮәжқҘжүҫеҲ°е®ғ们дәҶгҖӮ
е’ҢдәәдёҚдёҖж ·пјҢйӮЈдәӣзүӣе„ҝиҮӘд»Һз”ҹдёӢжқҘеҗҺпјҢиҝҳжІЎжңүеғҸдәәдёҖж ·е№ёзҰҸең°иў«дё№еўһе–Үеҳӣиө·иҝҮеҗҚеӯ—е‘ўпјҢдҪҶжӢүзҸҚ欧зҸ зӣёдҝЎзүӣе„ҝд№ҹжңүе®ғ们зҡ„еҗҚеӯ—пјҢиҰҒдёҚ然пјҢзүӣзҡ„еҰҲеҰҲжҖҺд№ҲеҢәеҲ«еҸ«е”Өе®ғзҡ„еӯҗеҘіе‘ўпјҹ
ж— ж•°ж¬ЎпјҢжӢүзҸҚ欧зҸ зңӢеҲ°иҝҮжҜҚзүӣеҜ№зқҖзүӣзҫӨе“һе“һеҸ«иҝҮд№ӢеҗҺпјҢе°ұжңүе°ҸзүӣйЈһеҘ”иҝҮеҺ»пјҢйӮЈдёҚе’Ңж¬Ўд»ҒеӨ®е®—еҘ¶еҘ¶е–ҠиҮӘе·ұжҳҜдёҖж ·зҡ„еҗ—пјҹжӢүзҸҚ欧зҸ жғіеҲ°иҝҷйҮҢ笑дәҶпјҢеҘ№зҡ„жӯҘеӯҗиҝҲеҫ—жӣҙжңүеҠІдәҶгҖӮ
еңЁжқӮйӮЈж—Ҙж №зҘһеұұзҡ„иҘҝеҚ—ж–№пјҢжҳҜдёҖзүҮзј“еҶІзҡ„жІҹеЈ‘еқЎдёҳгҖӮеңЁе°ҶеҲ°иҫҫеұұж №и„ҡзҡ„йғЁдҪҚпјҢдёҖжқЎжІійҒ“еңЁиҝҷйҮҢз»•дәҶдёҖдёӘејҜпјҢйӮЈдёҖејҜжІійҒ“е®Ҫж•һпјҢеӨҸеӨ©ж—¶ж°ҙиҚүиҢӮеҜҶпјҢеҶ¬еӨ©ж—¶е№ІиҚүй“әең°гҖӮиә«ејәеҠӣеЈ®зҡ„зүӣе„ҝ们дјҡжӣҙе–ңж¬ўеҲ°жқӮйӮЈж—Ҙж №зҘһеұұдёӯдёҠйғЁе•ғйЈҹйқ’йқ’зҡ„иҚүиҠҪпјҢй—ҙжҲ–еӯҳеңЁзқҖеӨ§йҮҸзҡ„иҷ«иҚүеҸҠе…¶д»–зҸҚиҙөзҡ„жӨҚзү©ж №иҢҺпјҢдёҖдәӣе№ҙиҖҒзҡ„зүҰзүӣеҸҜиғҪжӣҙе–ңеҘҪиҝҷж ·зҡ„е®үйҖёд№Ӣең°гҖӮеҳҺе°”иҗЁеҜәе°ұеңЁиҝҷзүҮе®үйҖёд№ӢдёӯгҖӮ
жӢүзҸҚ欧зҸ ж•°иҝҮеӨұиёӘзҡ„зүҰзүӣпјҢеӨ§еӨҡжҳҜе№ҙиҝҲзҡ„иҖҒзүӣпјҢе®ғ们е°ұеғҸеёҗзҜ·йҮҢзҡ„ж¬Ўд»ҒеӨ®е®—еҘ¶еҘ¶дёҖж ·пјҢеҗ‘жқҘжҜ”иҫғе®үйқҷгҖӮе…¶е®һпјҢдёҚеҸӘж¬Ўд»ҒеӨ®е®—еҘ¶еҘ¶пјҢеңЁзҘһеұұдёӢйқўпјҢжүҖжңүжңүз”ҹе‘Ҫзҡ„дёңиҘҝйғҪжҜ”иҫғе®үйқҷгҖӮ
дёҖдёӘдёҚз•ҷзҘһпјҢжӢүзҸҚ欧зҸ йЎәзқҖжІійҒ“иҫ№ж»‘дәҶдёӢжқҘгҖӮеӨ§йӣӘиҰҶзӣ–пјҢе°Ҫз®ЎзңӢеҮәжҳҺжҳҫзҡ„жІійҒ“пјҢдҪҶж №жң¬еҲҶдёҚеҮәжІіжІҝеңЁе“ӘйҮҢгҖӮеҘҪеңЁеҶ¬еӯЈзҡ„жІійҒ“йғҪиў«еҶ°е°ҒдәҶпјҢдёҚдјҡжңүж°ҙпјҢжҢЈжүҺзқҖзҲ¬дәҶиө·жқҘпјҢеҘ№жү‘жү“зқҖиә«дёҠе’Ңи„–еӯҗйҮҢйқўзҡ„з§ҜйӣӘпјҢ然еҗҺдёҖжӯҘжӯҘеҗ‘зқҖжІійҒ“дёӢжёёиө°еҺ»гҖӮ
05
иҝңиҝңзҡ„жңүдёҖеӨҙзүҰзүӣиәәеңЁйӮЈйҮҢпјҢжӢүзҸҚ欧зҸ и§үеҫ—иҮӘе·ұзҡ„иҝҗж°”еӨӘеҘҪдәҶгҖӮзӣ®ж ҮйӮЈд№ҲжҳҺжҳҫпјҢзүҰзүӣзҡ„иә«дёҠз«ҹ然没жңүз§ҜйӣӘпјҢдјјд№ҺиҝҳеңЁеҠЁгҖӮ
жӢүзҸҚ欧зҸ и§үеҫ—иҝҷеӨӘзҘһеҘҮдәҶпјҢеҘ№иҪ¬иҝҮиә«жқҘпјҢеҶІзқҖжқӮйӮЈж—Ҙж №зҘһеұұж·ұж·ұејҜдёӢдәҶи…°пјҢзҘҲзҘ·иҝҷеӨҙзүҰзүӣиҝҳжҙ»зқҖгҖӮ
жҳҜзҡ„пјҢе“ӘжҖ•еҸӘиғҪжүҫеҲ°иҝҷдёҖеӨҙиҝҳжҙ»зқҖзҡ„пјҢйӮЈд№ҹжҳҜзҘһеұұжҳҫзҒөдәҶгҖӮжӢүзҸҚ欧зҸ еҠ еҝ«дәҶжӯҘдјҗпјҢж·ұдёҖи„ҡжө…дёҖи„ҡпјҢеҶІзқҖйӮЈеӨҙеҫ®еҫ®жҷғеҠЁзҡ„иәәеңЁжІійҒ“з§ҜйӣӘдёҠзҡ„зүҰзүӣиө°еҺ»гҖӮ
и·қзҰ»е№¶дёҚиҝңпјҢдҪҶи„ҡдёӢзҡ„е№ІиҚүз»Ҡзј пјҢжӢүзҸҚ欧зҸ иҙ№еҠӣең°з”ЁдәҶзҶ¬дёҖй”…еҘ¶иҢ¶зҡ„ж—¶й—ҙпјҢжүҚеҲ°дәҶзҰ»зүҰзүӣеҮ жӯҘиҝңзҡ„ең°ж–№гҖӮзүҰзүӣзҡ„иғҢеҶІзқҖеҘ№пјҢеӨҙеҗ‘зқҖжқӮйӮЈж—Ҙж №зҘһеұұпјҢеӨ–дҫ§дёӨжқЎи…ҝеҗ‘дёҠзӣҙзӣҙдјёзқҖпјҢдјјд№Һж—©е·ІеңЁйЈҺйӣӘдёӯеғөзЎ¬дәҶгҖӮиҝҷж ·зҡ„зүӣе„ҝжҖҺд№ҲеҸҜиғҪиҝҳжҙ»зқҖпјҢеҰӮжһңдёҚжҙ»зқҖпјҢжҖҺд№ҲдјҡдёҖзӣҙеңЁеҠЁпјҹзӣҙеҲ°зҺ°еңЁпјҢзӣҙеҲ°жӢүзҸҚ欧зҸ иө°еҲ°зүҰзүӣи·ҹеүҚпјҢеҸҲз»•еҲ°зүҰзүӣеӨҙйғЁпјҢеҘ№иҝҳжҳҜзңӢеҲ°зүҰзүӣзҡ„ж•ҙдёӘиә«еӯҗеңЁеҠЁгҖӮ
жӢүзҸҚ欧зҸ жңүзӮ№зҙ§еј пјҢеҘ№еҶҚж¬ЎеӣһжңӣжқӮйӮЈж—Ҙж №зҘһеұұпјҢзҘһеұұе•ҠпјҢдҪ дҝқдҪ‘жҲ‘еҗ§гҖӮ
зүҰзүӣзҡ„зңјзқӣд№ҹзқҒеҫ—еӨ§еӨ§зҡ„пјҢзңјзҸ еӯҗдёҖеҠЁдёҚеҠЁпјҢеҳҙе·ҙеҚҠеј зқҖпјҢйҮҢйқўеЎһж»ЎдәҶз§ҜйӣӘгҖӮйЎәзқҖзүҰзүӣзҡ„и„–еӯҗпјҢжӢүзҸҚ欧зҸ зңӢеҲ°дәҶзүҰзүӣзҡ„иӮҡеӯҗдёҠжңүдәӣдёҚеҗҢеҜ»еёёд№ӢеӨ„вҖ”вҖ”йӮЈдәӣжҡ—зәўзҡ„иЎҖиҝ№пјҢдјјд№ҺиҝҳеҫҲж–°йІңпјҢйӮЈеҲҮйқўдёҚе№ізҡ„дјӨеҸЈпјҢеҸҲеҘҪеғҸжӣҫз»ҸжңүдәәеҜ№еҘ№иҜҙиҝҮиҝҷз§Қжғ…еҶөгҖӮ
жӢүзҸҚ欧зҸ зіҠж¶ӮдәҶпјҢеҘ№з«ҷеңЁйӮЈйҮҢдёҚзҹҘеҰӮдҪ•жҳҜеҘҪгҖӮжҳҜзҡ„пјҢеҘ№дҫқзЁҖи®°еҫ—пјҢжңүд»Җд№Ҳдәәз»ҷеҘ№иҜҙиҝҮпјҢзў°еҲ°иҝҷз§Қжғ…еҶөйңҖиҰҒжҖҺд№ҲеҠһпјҹдҪҶжҳҜжҖҺд№ҲеҠһе‘ўпјҢеҘ№е®Ңе…Ёеҝҳи®°дәҶпјҢжҳҜз«ӢеҚійҖғи·‘пјҢиҝҳжҳҜз•ҷдёӢжқҘдёәдёҖдёӘз”ҹе‘ҪзҘҲзҘ·пјҹ
еҘ№еҝҳи®°дәҶпјҢеҘ№жҒҗжғ§ең°еҝҳи®°дәҶпјҢе…ЁйғҪеҝҳи®°дәҶгҖӮ
жүӢи¶іж— жҺӘдёӯпјҢжӢүзҸҚ欧зҸ з”Ёеҫ®ејұзҡ„еЈ°йҹіе–ҠдәҶдёҖеҸҘпјҡвҖңзҘһеұұе•ҠзҘһеұұе•ҠгҖӮвҖқ然еҗҺпјҢеҘ№дјёжүӢжҺҖдәҶдёҖдёӢйӮЈе·Із»Ҹиў«жү“ејҖзҡ„зүӣиӮҡеӯҗгҖӮ
зһ¬й—ҙзҡ„е®үйқҷпјҢзҙ§жҺҘзқҖдёҖйҳөжІүй—·зҡ„еӨ§еҠЁйқҷпјҢзүӣзҡ„иӮҡеӯҗеғҸжҳҜдёҖжүҮй—ЁдёҖж ·ең°жү“ејҖдәҶгҖӮдёҖдёӘиЎҖж·Ӣж·Ӣзҡ„жҜӣиҢёиҢёзҡ„еӨ§и„‘иўӢдёҖеј ж…өжҮ’зҡ„еҲҡеҲҡиў«жғҠйҶ’зҡ„и„ёдјёдәҶеҮәжқҘгҖӮ
06
жӢүзҸҚ欧зҸ жӣҫз»Ҹеҗ¬иҜҙиҝҮпјҢеҰӮжһңеңЁжһҒеҜ’зҡ„еҶ¬еӨ©йҒҮеҲ°иў«ејҖдәҶиӮҡеӯҗзҡ„зүҰзүӣпјҢдёҖе®ҡи®°еҫ—иө¶зҙ§и·‘ејҖгҖӮеӣ дёәпјҢйӮЈзүӣзҡ„иӮҡеӯҗйҮҢпјҢе°ұеғҸдёҖдёӘеҫЎеҜ’зҡ„жҲҝеӯҗпјҢдёҖе®ҡзқЎзқҖдёҖеӨҙиҙӘе©Әзҡ„еӨ§жЈ•зҶҠгҖӮ
зҺ°еңЁжғіиө·жқҘжңүзӮ№жҷҡдәҶгҖӮжӢүзҸҚ欧зҸ дёҖдёӢеӯҗеӨ§и„‘е°ұз©әзҷҪдәҶпјҢж—¶й—ҙйқҷжӯўдәҶпјҢе°ұиҝһжқӮйӮЈж—Ҙж №зҘһеұұд№ҹдёҚеңЁжӢүзҸҚ欧зҸ зҡ„и„‘еӯҗйҮҢдәҶгҖӮ
жӢүзҸҚ欧зҸ зҡ„еҸҢжүӢеҚҠиң·зқҖжЁӘеңЁиғёеүҚпјҢеҘ№дёҖеҜёи·қзҰ»д№ҹдёҚж•ўеҫҖеӣһ收пјҢз”ҡиҮіеҳҙе·ҙд№ҹдёҚж•ўеҗҲдёҠпјҢеҘ№е°ұйӮЈж ·зӣҙзӣҜзӣҜең°зңӢзқҖжЈ•зҶҠпјҢжЈ•зҶҠз«ҷз«ӢзқҖпјҢжҳҫ然被дәәжү“жү°и®©е®ғдёҚеҝ«гҖӮе®ғзҡ„еҸҢзҲӘеңЁиғёеүҚиҖ·жӢүзқҖпјҢе®ғжҳҫ然еҗғйҘұдәҶпјҢдјјд№Һ并没жңүж”»еҮ»дәәзҡ„жү“з®—гҖӮ
еҒңдәҶеӨ§зәҰдёүеҚҒз§’й’ҹпјҢжЈ•зҶҠжү“дәҶдёӘе—қпјҢ然еҗҺз”©з”©и„‘иўӢпјҢеҸҲй’»еӣһзүӣиӮҡеӯҗйҮҢйқўзқЎи§үеҺ»дәҶгҖӮ
д»ҺйӮЈд»ҘеҗҺпјҢжӢүзҸҚ欧зҸ е°ұжӣҙе’ҢеҘ№зҡ„зүҰзүӣеҲҶдёҚејҖдәҶгҖӮ
зҺ°еңЁпјҢжӢүзҸҚ欧зҸ зҡ„зүҰзүӣзҫӨе·Із»Ҹеҝ«иҰҒеҗғйҘұдәҶпјҢиҝҷдәӣеәһеӨ§з¬ЁжӢҷзҡ„иә«дҪ“ејҖе§ӢжңүдәҶж–°зҡ„жҙ»еҠӣгҖӮ
жӢүзҸҚеҸҲдёҖжғіпјҢе®ғ们д»Җд№Ҳж—¶еҖҷжІЎжңүиҝҮжҙ»еҠӣе‘ўпјҹеҮҶзЎ®ең°иҜҙпјҢиҝҷдәӣз•ңз”ҹпјҢжө‘иә«йғҪжҳҜеӨҡдҪҷзҡ„еҠӣж°”гҖӮзңӢзқҖе№ҙиҪ»зҡ„е°ҸзүҰзүӣеҺ»ж”ҖзҲ¬дёҖеӨҙе’Ңе®ғе№ҙзәӘзӣёд»ҝзҡ„е°ҸзүҰзүӣеұҒиӮЎпјҢжӢүзҸҚ欧зҸ е‘өе‘өең°з¬‘ејҖдәҶгҖӮ
е’ҢзІҫеҠӣж—әзӣӣзҡ„е°ҸзүҰзүӣзӣёжҜ”пјҢжӢүзҸҚ欧зҸ зҡ„жҙ»еҠӣжҳҜе®Ңе…ЁзӣёеҸҚзҡ„гҖӮиҮӘд»ҺеҮәз”ҹпјҢжӢүзҸҚ欧зҸ зҡ„иә«дҪ“е°ұйқһеёёеӯұејұпјҢдёҖеңәжҺҘдёҖеңәзҡ„еӨ§з—…и®©еҘ№йӘЁзҳҰеҰӮжҹҙпјҢдҪҶеҚҙжҢәзқҖдёҖдёӘеҘҮжҖӘзҡ„еӨ§иӮҡеӯҗгҖӮ
жҙӣжүҺжӣје·ҙиҜҙжӢүзҸҚ欧зҸ зҡ„иӮҡеӯҗйҮҢй•ҝдәҶиҷ«еӯҗпјҢиҝҷиҷ«еӯҗдјҡи®©жӢүзҸҚ欧зҸ жҙ»дёҚдәҶеӨҡд№…гҖӮдҪҶжҳҜпјҢеҚідҫҝдёҚд№…е°ұдјҡз”ҹе‘Ҫз»Ҳз»“пјҢзҒөйӯӮз»Ҳе°Ҷиө°дёҠеӨ©е ӮпјҢзҘһзҡ„дҪҝиҖ…д№ҹдјҡеёҰеҘ№йЈһеҚҮеҲ°зҒөйӯӮжүҖиғҪеҲ°иҫҫзҡ„жңҖй«ҳзҡ„ең°ж–№гҖӮ
07
дёҖеӨ©еӨ©зҡ„пјҢжӢүзҸҚ欧зҸ дҫқ然еҫҲеҝ«д№җгҖӮеҘ№зӣёдҝЎзҘһзҒөеәҮжҠӨзқҖиҚүеңәдёҠзҡ„дёҖеҲҮз”ҹе‘ҪпјҢеҘ№е’ҢеҘ¶еҘ¶иҝҳжңүиҝҷдәӣзүҰзүӣеңЁжқӮйӮЈж—Ҙж №зҘһеұұдёӢзӣёдҫқдёәе‘ҪгҖӮ
еҘ№д»¬иө¶еңЁеӨ©дә®д№ӢеүҚе°ұеҮәеҸ‘дәҶпјҢжӢүзҸҚиҷҪ然еҗ¬еҠӣдёҚеӨӘеҘҪпјҢдҪҶж”ҫзү§жҳҜжҠҠеҘҪжүӢпјҢеҘ№жіЁж„ҸеҠӣдё“жіЁпјҢ并иғҪжҠҠзүҰзүӣзҫӨи°ғж•ҷеҫ—жңҚжңҚеё–её–гҖӮзүҰзүӣе–ңж¬ўеёҰзқҖйңІзҸ зҡ„е«©иҠҪпјҢжӢүзҸҚжҮӮеҫ—еёҰе®ғ们еҺ»е“ӘйҮҢеҜ»жүҫгҖӮ
жӢүзҸҚжңүдёӨдёӘе“Ҙе“ҘпјҢдҪҶжҳҜйғҪеӨӯжҠҳдәҶгҖӮжӯ»еҺ»зҡ„е“Ҙе“ҘжҳҜж”ҫеңЁжүҺжӣІжІійҮҢж°ҙ葬зҡ„пјҢеңЁй«ҳеҺҹдёҠпјҢжңӘжҲҗе№ҙзҡ„еӯ©еӯҗжӯ»еҺ»пјҢйғҪиҰҒж”ҫеңЁж°ҙйҮҢпјҢи®©йұјзұ»еҗһйЈҹ他们зҡ„иӮүдҪ“пјҢд»Ҙе®ҢжҲҗиҮӘе·ұз”ҹе‘Ҫзҡ„иҪ®еӣһгҖӮ
жӢүзҸҚ欧зҸ жңҖеӨ§зҡ„ж„ҝжңӣе°ұжҳҜжҙ»еҲ°жҲҗе№ҙпјҢйӮЈж ·пјҢеҘ№зҡ„иә«дҪ“е°ұдёҚз”Ёиў«жіЎеңЁж°ҙйҮҢпјҢиҖҢжҳҜзҘһзҡ„дҪҝиҖ…жқҘе®ҢжҲҗиҮӘе·ұз”ҹе‘Ҫзҡ„еёғж–ҪгҖӮ
дё№еўһе–Үеҳӣжӣҫз»Ҹи®ІиҝҮпјҢйҮҠиҝҰзүҹе°јеңЁдҝ®иЎҢж—¶пјҢжӣҫд»ҘеӨҙзӣ®и„‘й«“гҖҒиӮўиҠӮжүӢи¶іеёғж–ҪпјҢиҲҚиә«йҘІиҷҺпјҢеүІиӮүе–Ӯй№°гҖӮдё№еўһе–ҮеҳӣиҰҒжҲҗдёәйӮЈж ·зҡ„дәәпјҢж¬Ўд»ҒеӨ®е®—е’ҢжӢүзҸҚ欧зҸ йғҪеёҢжңӣжҲҗдёәйӮЈж ·зҡ„дәәгҖӮ
дё№еўһе–ҮеҳӣиҝҳиҜҙиҝҮйқһеёёй«ҳж·ұзҡ„дёҖж®өиҜқпјҢйӮЈжҳҜд»–дёҠдёҖж¬ЎеҲ°жІҷж—ҘеЎҳзү§жқ‘йҮҢжқҘзҡ„ж—¶еҖҷгҖӮеҪ“ж—¶пјҢж¬Ўд»ҒеӨ®е®—еёҰзқҖиә«дҪ“еӯұејұзҡ„жӢүзҸҚ欧зҸ и®©дё№еўһе–Үеҳӣж‘©йЎ¶гҖӮеҗҺжқҘпјҢеқҗеңЁдәәзҫӨдёӯй—ҙпјҢд№ҹжҳҜеқҗеңЁж¬Ўд»ҒеӨ®е®—е’ҢжӢүзҸҚ欧зҸ еҜ№йқўзҡ„дё№еўһе–ҮеҳӣиҜҙпјҡжӯ»дәЎеҸӘжҳҜдёҚзҒӯзҡ„зҒөйӯӮдёҺйҷҲж—§зҡ„иәҜдҪ“зҡ„еҲҶзҰ»пјҢжҳҜејӮж¬Ўз©әй—ҙзҡ„дёҚеҗҢиҪ¬еҢ–пјҢжҲ‘们жӢҝвҖңзҡ®еӣҠвҖқжқҘеёғж–ҪпјҢжҳҜжңҖе°Ҡиҙөзҡ„вҖ”вҖ”иҲҚиә«еёғж–ҪпјҢиғҪиөҺеӣһз”ҹеүҚзҪӘеӯҪпјҢи®©йҖқиҖ…зҒөйӯӮ延з»ӯдёҚзҒӯжҲ–иҖ…еҫ—д»ҘиҪ®еӣһгҖӮ
ејӮж¬Ўз©әй—ҙпјҢиҝҷдёӘиҜҚйқһеёёеҸӨжҖӘпјҢеңЁжІҷж—ҘеЎҳпјҢеҸӘжңүеӨ§еұұе’ҢзүӣзҫҠпјҢжӢүзҸҚ欧зҸ е®һеңЁжҗһдёҚжҮӮд»Җд№ҲеҸ«дҪңејӮж¬Ўз©әй—ҙгҖӮ
еңЁеӨ–йқўиҜ»иҝҮд№Ұзҡ„ж јжЎ‘жӢүе§ҶиҜҙпјҢиҝҷйҮҢеӨ§еӨҡж— еңҹеЈӨжҲ–еҶ»еңҹеқҡзЎ¬йҡҫжҺҳпјҢж— жі•еҸҠж—¶жҺ©еҹӢе°ёдҪ“пјҢдёәйҒҝе…Қе°ёдҪ“дј ж’ӯз–ҫз—…пјҢдҫҝеӣ ең°еҲ¶е®ңйҮҮз”ЁдәҶе…¶д»–еҪўејҸгҖӮ
ж јжЎ‘жӢүе§Ҷзҡ„и§ЈйҮҠпјҢи®©ж¬Ўд»ҒеӨ®е®—зӣ®зһӘеҸЈе‘ҶпјҢжҙӣжүҺжӣје·ҙеҗҺжқҘеҗ¬иҜҙеҗҺпјҢд№ҹжһҒдёәдёҚж»ЎгҖӮдҪҶдё№еўһе–Үеҳӣз«ҹжІЎжңүжү№иҜ„ж јжЎ‘жӢүе§ҶпјҢеҸӘжҳҜ笑зқҖиҜҙдәҶдёҖеҸҘпјҡвҖңйӣ„й№°йғҪжңүеұһдәҺиҮӘе·ұзҡ„еӨ©з©әгҖӮвҖқ
жӢүзҸҚ欧зҸ и§үеҫ—пјҢиҝҷжҳҜдёҖеҸҘй«ҳж·ұзҡ„иҜқе‘ўгҖӮ
еҺҹеҲҠдәҺгҖҠдёӯеӣҪдҪң家гҖӢ2020е№ҙ11жңҲ

зҺӢжҳҶпјҢе®үеҫҪж·®еҢ—дәәпјҢе…ҲеҗҺжңҚеҪ№дәҺжҹҗзү№з§ҚйғЁйҳҹгҖҒжӯҘе…өж—…гҖҒиӯҰеӨҮеҢәгҖҒдҫҰеҜҹеӨ§йҳҹзӯүпјҢзҺ°дҫӣиҒҢдәҺиҒ”еӢӨдҝқйҡңйғЁйҳҹжҹҗйғЁпјҢеҢ—дә¬еёҲиҢғеӨ§еӯҰдёҺйІҒиҝ…ж–ҮеӯҰйҷўиҒ”еҠһз ”з©¶з”ҹзҸӯеңЁиҜ»ж–ҮеӯҰзЎ•еЈ«гҖӮеңЁгҖҠдәәж°‘ж–ҮеӯҰгҖӢгҖҠдёӯеӣҪдҪң家гҖӢгҖҠи§Јж”ҫеҶӣж–ҮиүәгҖӢгҖҠеҚҒжңҲгҖӢгҖҠйқ’е№ҙж–ҮеӯҰгҖӢгҖҠж–ҮеӯҰиҜ„и®әгҖӢгҖҠи§Јж”ҫеҶӣжҠҘгҖӢгҖҠж–ҮиүәжҠҘгҖӢзӯүеҲҠеҸ‘иЎЁеҗ„зұ»ж–ҮеӯҰдҪңе“ҒдәҢзҷҫдҪҷдёҮеӯ—гҖӮеҮәзүҲдёҺеҸ‘иЎЁи‘—дҪңгҖҠз»ҲжһҒзҢҺдәәгҖӢгҖҠжҲ‘зҡ„зү№жҲҳеҫҖдәӢгҖӢгҖҠUNжӯҘе…өиҗҘжҲҳдәӢгҖӢгҖҠе…ӯеҸ·е“ЁдҪҚгҖӢгҖҠеӨ©иҫ№зҡ„иҺ«дә‘гҖӢгҖҠз»қйқһе…ө家常дәӢгҖӢзӯүе…ӯйғЁгҖӮиҺ·еӨҡдёӘж–ҮеӯҰеҘ–йЎ№гҖ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