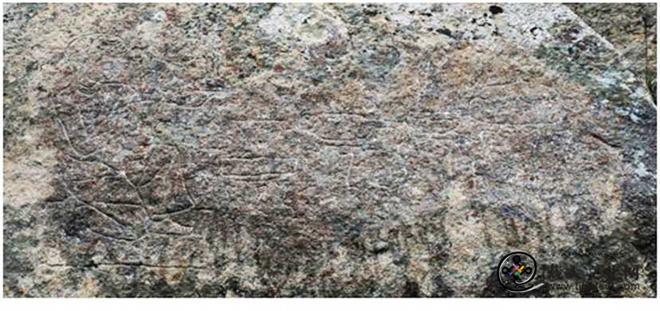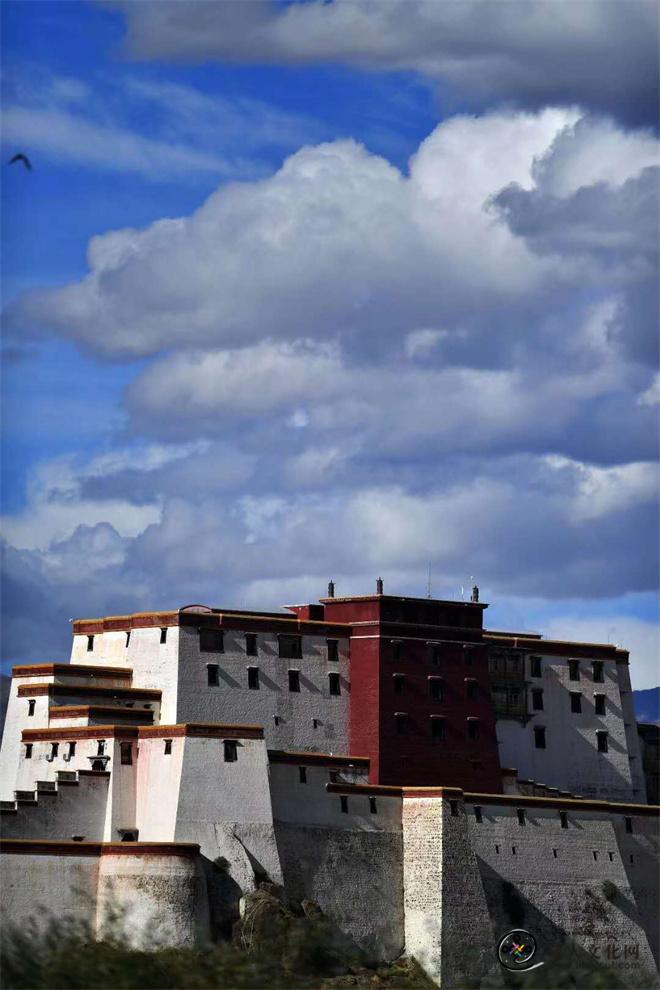摄影:觉果
摄影:觉果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在现代交通、运输技术及市场经济等因素的交互作用下,涉藏地区的市场化和城镇化速度明显加快,西藏与内地食物与人口的流动速度远超历史时期,联系愈发紧密,在这个过程中食物的地域性与社会性被逐渐消解、重构,人们越来越难以通过食物来判断其“族性”。基于此背景,以川菜为代表的汉地饮食文化深入到边疆地区城市——拉萨。川菜馆在融入当地时,克服了高原环境的挑战,同时也适应了当地人的饮食口味,在充分尊重吸收当地饮食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实现了在地化。在此过程中,川菜原本的地域与社会属性被突破,嵌入当地社会后也被赋予了新的社会性,川菜成为可供汉藏等各民族人群共享的饮食文化体系,川菜馆则为各地域人群提供持续交往的场域,进一步促进了汉藏等多民族之交流互动。
关键词:拉萨;川菜;川菜馆;在地化;族群互动
三、川菜馆的自然与人文在地化实践
拉萨的川菜馆为何能如此成功地实现对拉萨主城区的覆盖?除了四川人的涌入以及川菜本身口味广受当地人欢迎之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川菜馆经营者对当地自然与人文生态的尊重,积极采取在地化的实践。诞生于成都平原的川菜,其主食制作与食材选取为适应高海拔环境作出了一定调整。主食上,川菜以米和面为主食,故其在当地传播时需借助技术手段克服高海拔环境带来的低气压问题。以煮挂面为例,在成都仅需一口普通锅敞着就能煮熟,而到了西藏后就必须用上高压锅,低压环境加上高压厨具的运用,恰好调和了锅内的气压,使得烹饪出来的食物软熟度刚好,也因此高压锅被广泛用于煮面、饺子、汤圆等,它也成为拉萨川菜馆里最常见的厨具。不过低压环境对米的影响较小,米饭和内地一样可以用电饭煲煮,米线则仅用一个盆就能煮熟,这使得“米”在当地广泛传播。在食材方面,川菜以猪肉为主,辅以各种蔬菜,而藏族传统饮食以糌杷为主食,辅以肉类、奶制品,蔬菜占比较小。
当以蔬菜为主要食材的川菜进入当地后,与当地较为单一的饮食文化体系形成了结构上的互补。蔬菜和历史上的茶叶一样起到消食解腻的作用。随着拉萨城镇化进程加快,上班族增多,当地人对轻食、健康饮食的需求日益增多,“多加菜,少点肉”成为当地人到川菜馆就餐的一大原因。但受自然环境条件与食材运输成本等限制,拉萨市场上的蔬菜价贵,为降低成本,川菜馆不得不在当地寻找成本低廉的本地传统食材进行替代,其中土豆成为最常见的替代品。借助技术手段和在当地寻找可替代食材是川菜馆在面临青藏高原严酷自然条件下所做出的调整,这种调整使得川菜本身灵活的特性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发挥,使其得以实现地理层面的在地化,也因此具备了在高海拔地区传播发展的顽强生命力。
川菜馆也在人文方面进行了在地化实践。在拉萨,很多川菜馆都不同程度地吸收了当地的藏族文化元素。具体到餐厅的运营上,川菜馆会按照中餐馆经营惯例,在每天下午晚班开始前的5-6点召开餐前会议,由领班或经理对当晚各项工作事宜进行安排,同时也让员工进行热身活动,或是喊ロ号,或跳企业舞蹈。为突出西藏地方特色,经营者将藏族民间舞蹈融入餐前的企业舞蹈中。如“谭鱼头”让店员在店门口排成圆圈,跳锅庄舞。经营者通过这一方式,不仅拉近了汉藏员エ间的距离,增强了企业向心力,还打造出了富有西藏地方特色的企业形象,吸引了本地居民与外地游客,可谓一举多得。餐馆在装修与店面设计上也积极采用藏文化元素,除了店名、菜单采用藏汉两种文字,像“骆豆花”这样的川菜馆还把藏族传统文化中的吉祥八宝图案运用到招牌设计中,用这种方式向本地消费者传达了“欢迎”之意。
一些对当地藏族饮食口味把握较为精准、对藏族文化运用最为成功的川菜馆,褪去了川菜馆的外衣,披上了藏餐馆的新装,颇有化大道于无形的意味。典型如肖家河家常面馆,笔者进店点馄饨时,服务员会自然地用藏语问要不要加辣椒?听ロ音,该店收银员、服务员、厨师大都是康巴人,进店用餐的食客也多是藏族。笔者的田野调査对象央金说她曾去过该店的罗布林卡分店用餐,店里员エ也大都是康巴人。当笔者告诉她这是一家川菜馆时,她非常惊讶,此前她一直认为这是一家藏面馆。2018—2021年,央金在西藏大学读书时经常到肖家河家常面馆吃面,觉得口味很正宗,很符合藏族人的饮食习惯,这家餐馆的在地化程度可见一斑。该店之所以能如此成功地实现在地化,除了在经营过程中全部雇佣藏族员工以及在拉萨经营时间较长外,还与其经营的主要餐品为面食有关。在青藏高原地区,青裸、大麦、小麦是制作主食的主要原料。其中,青裸麦粒炒熟后可磨制成“糌杷”,青棵粉用于制作藏面、藏包子等;大麦主要用于制作饼类,如白饼;小麦则用于制作包子、馒头、面条等。藏族在主食选择上较为偏爱面食,面食种类丰富意味着餐馆迎合了本地藏族的饮食偏好。肖家河家常面馆以售卖热汤面、饺子、馄饨、凉面为主,恰与当地人的这种饮食偏好相契合。
属于中餐体系的川菜并不像西方餐饮那样,对食材、佐料的配比必须精确到克,相反,厨师在制作过程中可照其意愿把握火候和控制食材的取舍,这给川菜带来了较大的灵活性。历史上,涉藏许多地方饮食受传统文化影响,大部分人不食用来自“鲁”界的海鲜类食物,信奉佛教的藏族人在拜佛时禁食蒜类等带有辛味的食物,拉萨大多数川菜馆经营者们在了解到这些饮食习惯后,选择尊重其饮食禁忌与宗教文化,会在点餐时提醒哪些菜品是有海鲜的,哪些又是加了蒜的。当藏族顾客提出“不吃蒜”的要求后,厨师可以在不破坏味型整体性的基础上运用其他佐料为客人提供相应菜品。尚甜也是涉藏地区饮食特征之一,拉萨人尤喜甜茶等带有甜味的食物。作为西方工业快餐象征的可口可乐在进入拉萨后迅速被当地人追捧,敏锐的川菜经营者发现之后,推出“川菜+可乐”的模式进行销售,广受当地人欢迎。这一模式也很快成为拉萨川菜馆普遍采用的营销手段。
川菜馆在适应高原环境并吸收涉藏地区饮食文化元素顺利实现在地化的过程中,川菜本身也融合了川藏两地的食材与饮食文化,从而适应了市场的需要。可以说,川菜馆在拉萨的在地化,代表着另一维度上汉藏等多民族人群之关系,在不同人群的日常交往中,“你”不必变成“我”,“我”也不必成为“你”,而是采取一种相互尊重彼此差异的态度,互鉴优点,包容并蓄,和而不同。在川菜馆,碰撞产生出来的是适应经营者盈利,适合汉藏等各民族食客消费的川菜。此过程体现的正是文化交往活动里“和”的一面,“和”的前提是两地饮食文化存在过巨大差异,“不同”为两地饮食的交流互鉴提供了发展空间,随着汉藏等多民族百姓交往的深入,“不同”逐渐消解,演变为真正意义上的“和”。然而,共性的增多不代表个性的抹灭,在当下或未来各民族在交往时“不同”也将持续发挥作用,为将来族群交往中更多的“和”创造条件。“和”与“不同”相伴相生,允许、尊重不同族群之间差异的存在,才能碰撞产生出更高层次的有利于中华各民族交往的“和”文化。共性为族群交往提供可能,个性则有利于保持族群文化自身的独特性与生命力,族群交往的意义也正在于此,处于交往活动中的人,互为镜像、互通有无、互相借力、共谋共生。
四、饮食与汉藏族群边界之变迁
历史上,西藏与内地之间的交通长期不便,两地人群相互之间的了解并不深,对彼此的饮食习惯都存在一定的偏见。在清代,西藏民众认为食用内地饮食会染上天花。甚至在20世纪初,西藏一些百姓仍把是否食用肉类与男子气概联系起来,认为食用肉类的西藏男性是阳刚且有力量的。偏见会随着双方交往的深入而逐渐消除,尤其是改革开放后内地人群和饮食大量进入拉萨,那些认为猪肉、鱼、鸟及蛋内有黑丸,“食之颇有害于精神”的饮食禁忌被市场化和世俗化所湮没。虽然现在部分藏族人依旧不食鱼虾,但另外大部分人已接受了把鱼、虾作为食物的观念,把鸡肉当作食物更是屡见不鲜了。这个过程,正如“川渝香辣蟹”的厨师何先生所认为的:“现在藏族跟汉族来往的多,所以’汉化‘也比较严重,有些藏族人也就吃(蟹)了”。所谓“汉化”,近代以来在城市现代化浪潮的裹挟之下,成为“现代化”或“城镇化”的代名词,并以“汉化”之名在边疆地区让“我”成为“他者”,也让“他者”成为“我”,在这里“汉化”即为“涵化”。在所谓“汉化”的席卷下,拉萨街头的四川人喝着酥油茶,藏地百姓家里制作着火锅等川省饮食,成为司空见惯的事,当地人更是习惯了“早上吃糌杷,中午吃中餐(吃得最多的还是川菜),晚上吃面”的饮食安排。
拉萨市现阶段以川菜为代表的汉藏饮食文化之间的互动,不过是历史长河中汉藏等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延续和一个片段。千年来,围绕“食”这个主题,西藏和内地发生过诸多互动,仿佛汉藏之间存在一条连接古今、横跨地域的虚拟“走廊”。伴随着走廊上“人”与“物”的频繁流动,一些固有观念不断被挑战与改变。此过程中,食物的“族性”逐渐消解,食材与烹饪方法成为各民族共享的物质文化。诚然,在不同地域人群的交往过程中,物质在交换,文化在交换,思想也在交换。餐饮文化亦如是,由于文化的可习得性,谁习得了谁便是文化的持有者和继承者。同理,川菜馆的配菜秘方由谁所掌握,谁便成为川菜的代言人。不同地域、不同文化的人群共同享有饮食文化的使用权,在“文化”面前没有人可以说其拥有了绝对的所有权,处于文化中的人群皆可被化之。正如王明珂与彭兆荣所说,客观的饮食并不是一个可以分别出我群与他群的标志,必须在一定的“context(情境)”下,一个具体的物才能产生特殊的“identity(身份认同)”。某些食物与其烹饪方式,在历史上可能在较长一段时间内为某一地域的人群所拥有,被时间赋予了正统性,使其看上去像是某一人群的标志,如谈论四川饮食离不开火锅。然而,随着人群流动以及交通物流条件的进步,食物制作技术得以在不同地域的人群之间传播,食材也能实现远距离运输,从而使原本不产“米”的地方也能吃上“米”,不识汉地烹饪技术的人群也可学到火锅的制作技术。人的跨地域流动总会给其他地方带去被称为传统饮食文化的东西,因为“他者”不可能离开互动而存在,而互动则意味着变迁,这种变迁不仅发生在饮食文化上,也发生在语言上。
由于四川饮食是与四川人一同进入拉萨的,四川人开的川菜馆作为商业场所在给从事该行业的人提供就业机会时也为经营者和员工提供了与当地人认识交往的渠道,饮食互动间接地促进了双方语言的交流。西藏大学“川味味道”里兼职的学生卓玛,2021年是她到该店工作的第三年。一次,一个学生用四川话点餐,她也学着对方的语调说了一句,出于好奇,笔者追问她是否能听懂四川话,卓玛说店里员エ平时说的四川话她基本上都能听懂。卓玛的故事并非个例,事实上,很多在川菜馆工作的藏族员エ都能听懂甚至可以说四川话。在川菜馆,语言的交流不是单向的,不仅藏族员工会学习四川话,来自四川的员工也会向藏族同事学习藏语。在川菜馆工作的次仁阿姨就对笔者说:“以前在川菜馆一起工作的四川人老是说,阿佳啦(姐姐),这个用藏语怎么说那个用藏语怎么说,在一起工作两年后他们大部分都会说一些藏语了。”
这与1963年张小平到拉萨市堆龙德庆县实习期间的所见形成了鲜明对比:“从现在开始我必须与藏族同胞用藏语交谈,因为这个语言环境没有人懂汉语,这就逼我必须说藏语。”可见当时汉藏百姓之日常交流并不畅通,然而今日两地民众在交流时,彼此的语言随着双方交往的深入,逐渐被对方习得,加上普通话的推广,沟通成本大大降低,沟通效率也极大提高。这种交往不再局限于“菜”“白菜”“萬笋”“酸萝卜”“萝卜”等饮食词或者文献典籍的译介,而是更大范围地对参与族群互动双方的日常生活细节的填充与覆盖。以工作于川菜馆中的员エ为例,饮食文化、语言随着社交网络从工作场所延伸到私人交往之中,再慢慢渗入到双方的日常生活中,私人社交网络的建立则又为下一步的饮食、语言文化交往铺平了道路。次仁阿姨同笔者说,现在她和原来的四川同事仍然是很好的朋友,有时还会私下约着吃饭、打麻将。次仁阿姨在家也会制作家人喜欢吃的川菜。可见,在此过程中,处于族群互动关系网络中“人”的社会身份逐渐超越民族/族群身份,取而代之的是同事、朋友、通婚对象等身份,新身份意味着当地社会对从外地来的人的认可度不断提高,也意味着对其文化与传统习惯的接受度不断提高,这在通婚意愿上表现得尤其明显。2020年,有79对汉藏结合的夫妻在拉萨市民政局登记结婚,其中21对有四川户口。此时互动双方的社会身份已进阶到家人身份,是更高层次的融合。综述之,川藏之间由饮食交流引起的族群互动所带来的影响超越了饮食本身,推动了两地在语言文化等维度的共享、互鉴。
五、结语
与饮食文化有关的族群边界从发生变迁再到新的族群认同形成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并非一蹴而就。川菜在拉萨甚至西藏的传播之所以能获得成功,除改革开放带来的有利条件外,还与清代川军、川商入藏驻藏有密切关系。历史上一些四川人进入西藏后与当地人通商、通婚,更与当地人一同生活,从而促成川菜在西藏有了长时间的历史积累,如今川菜馆在拉萨遍地开花实在是一种顺理成章的事情。这些条件的具备使得两地各族人民在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共生共享。共生意味着共享,这种共享不仅发生在拉萨,在其他涉藏区域也同样存在,如在甘南地区不同民族共享糌杷文化,对同一饮食文化的共享导致彝汉、回汉、藏汉饮食的同质化发展,带来了族群边界的变迁以及传统饮食禁忌的消散。显然,这种变迁并非只发生在现代,在历史上也存在,区别只在于范围的大小、程度的深浅。在本文所探讨的改革开放以来的时代背景下,由于交通条件的变化,人口迁移的出现,族群互动的程度逐渐加深、范围也更加广阔,原本持有这些食物文化的人群与食物一起进入新的社会情景,被重新解读赋值。在此过程中食物及其文化不断越界、融合产生新的饮食文化,饮食文化体系从单一走向多元。
作者简介:励轩,四川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首席专家,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教授,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臧正,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22级博士研究生。
原刊于《中国藏学》2024年第3期(总第164期),注释略,原文版权归作者及原单位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