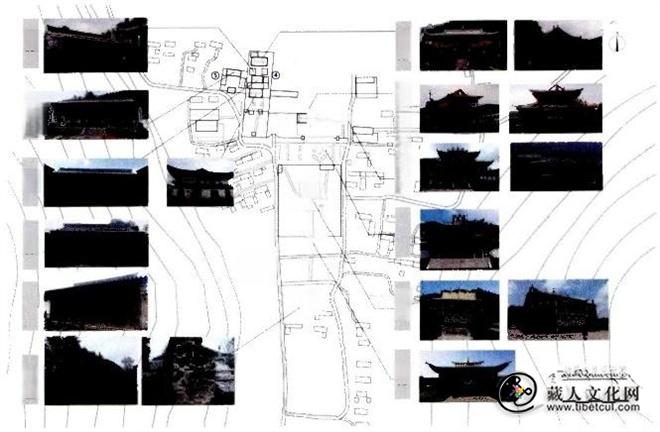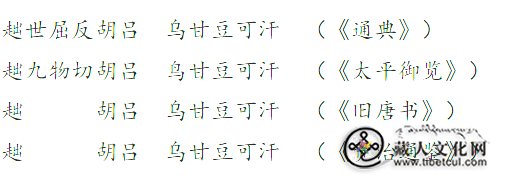摄影:曾晓鸿
摄影:曾晓鸿
摘要:青海湖祭海仪式不仅是环湖地区各民族的民间活动,亦是中央王朝所重视的祭礼之一。自雍正时期起,清代掌握了青海湖祭海仪式的主祭权,并通过赐匾额、加封以及配置主祭人员等一系列举措完善祭祀制度,同时,构建和巩固国家合法性和意识形态。这种神权与政权的统一形式,正好弥补了清廷在青海地区军事力量的薄弱和法律制度实施的空缺。清代青海湖祭海仪式作为国家祭祀活动,其具体仪式过程及相关的文化符号中承载着丰富的政治意涵。通过举行祭海仪式,清廷向边疆地区传递统一的政治形象和文化认同,进而加强并巩固了边疆地区与中央政府之间的联系和互动关系。通过会盟,赢得青海蒙古、藏等各民族对清朝政权的认同与趋于中央政府的向心力,从而加强和巩固西北边疆地区的稳定。简而言之,青海湖祭海仪式作为清朝政治权力的实践与表现形式,构成了国家对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的关键手段。该仪式不仅有效维护了国家权威,而且促进了族际之间的交流与团结,缓解了边疆地区的民族紧张氛围,为边疆地区的稳定与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支持。在国家治理与现代化建设中,挖掘和借鉴中华传统文化的治理理念和思维值得重视。
关键词:清代;青海湖;祭海仪式;边疆治理
一、引言
仪式作为人类学重要的研究领域,“它上可大至如‘道’之宏达、之玄奥;下则微若生活之屑沫,日常之琐碎”。仪式的范畴已扩展至几乎无所不包的领域和空间,使其成为观察人类情感、研究社会文化的一种视角和工具。
广义上的仪式涵盖了社会性活动。如人际交往的行为规范、日常礼仪以及国家庆典等政治礼仪;而狭义上的仪式则主要侧重于祭祀活动。在人类学研究中,仪式多与宗教祭礼相关。英国人类学家罗伯逊·史密斯最先探讨社会形态与宗教仪式的相互关系。他认为,“原始宗教中占首要地位的不是信仰和神话,而是仪式、制度和惯例”,“所以,宗教仪式的本质不是精神的而是社会的,它的十分重要的社会功能就是增强社会群体的整合”。基于此,法国社会学家爱弥尔·涂尔干进一步阐述仪式功能。他强调,“仪式是产生于集合群体之中,并必定要激发、维持或更新该群体中的某种精神状态”。更确切地说,任何传统仪式,在逻辑与客观层面均承载着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功能,并展现出明确的“集体效益”作用。拉德克利夫-布朗从社会生活、习俗与信仰的视角,探讨宗教仪式的基本功能。他认为“原始社会每一种习俗和信仰在社区的社会生活中都起到某种特定的作用,就像活体的每一个器官,在这个有机体的整体生活中都起着某种作用一样。”信仰仪式有助于调节和维护不同阶层、不同性别的社会群体关系,被视为社会团结的纽带,增强群体凝聚力。麦克斯·格鲁克曼在其著作《非洲部落的秩序与反叛》中提到,在对立和冲突中仪式充当一种安全阀的作用。之后,埃德蒙·利奇,玛丽·道格拉斯、维克多·特纳、克利福德·格尔茨等学者将仪式的社会内部研究继续推进,使之成为仪式研究最为活力的理论视角。
中国素有“礼仪之邦”之称,“祭祀”为五礼之首,且“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戎”即武力,是国家权力符号最突出、最为直接的表达形式,而国家却从未忽视以“祀”为代表的国家权力符号系统的构建与重塑。可见,祭祀仪式成为国家治理的重要途径。于是,历代王朝皆建立了严格的国家祭祀体系。清朝基本沿袭了这一祭祀传统,并借助青海湖祭海仪式,向边疆地区展现了统一的政治形象和文化认同,从而加强了边疆地区与中央政府之间的纽带和互动。本文从文化人类学仪式研究视角出发,通过查阅档案文献并结合田野调查,在梳理清代青海湖祭海仪式内容、祭祀体系的完善过程的同时,着重探讨清代青海湖祭海仪式在清朝国家事务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二、清代主祭青海湖神之初起
环青海湖居住的诸游牧民族视青海湖为圣湖并加以崇拜。蒙古人入驻青藏高原后,各部落为商讨军国事务和协调部落关系,沿袭了传统的会盟制度。同时,基于蒙古人对山川神灵的尊崇,青海蒙古族将青海湖祭海仪式与会盟(简称“祭海与会盟”)相结合,一般在春季举行祭海与会盟,以祈求福祉,禳除灾害、消解疾病,确保一年人畜平安。祭海与会盟遂成为青海蒙古族涵盖宗教、军事、政治、民俗等多重领域的重要民间活动。然而,自罗卜藏丹津叛乱事件之后,该传统发生了显著变革。
据记载,雍正元年(1723)农历五月十五日,罗卜藏丹津在青海湖东察汗托洛亥召集诸蒙古台吉会盟,强令各青海蒙古部落取消清朝的封号,“俱令呼旧名号”,一概不许称清廷册封的王、贝勒、贝子、公等称号,“勒令众等呼伊为达赖浑台吉”,以“恢复先人霸业”为口号,发动了叛乱。同年十月,清廷派川陕总督年羹尧为“抚远大将军”,任四川提督岳钟琪为参赞军务,率大军征讨罗卜藏丹津。据记载,“雍正二年(1724),大兵征青海,岳钟琪追贼党阿喇蒲坦温布等至西海北岸伊克哈尔吉河。时人马渴甚,求水不得,忽有泉从营前涌出成溪,士马就饮,得不困乏。众欢呼奋勇,遂进获贼首。督臣以青海效灵奏闻,诏封青海之神,立碑致祭”。
年羹尧与岳钟琪以青海湖神显灵为名呈报清廷,“彰显灵异,俾青海诸蒙古皆知敬仰”。雍正皇帝也认为此乃青海湖神庇佑,并亲撰《御制平定青海告成太学碑文》,文中称之为“师以顺动,神明所福。旬日凯归,不疾而速”“天讨既申,群酋惕息”。其意是指清军在青海湖神的庇佑之下顺利平定罗卜藏丹津叛乱事件,但实际上以此来证明清廷军事行动的正义性。平定罗卜藏丹津叛乱事件后,为加强对广大牧区蒙藏事务的管理,在借鉴康熙年间多次在青海地区派遣办事大臣经验的基础上,正式设立了“钦差办理青海蒙番子事务大臣”(下文统一使用“西宁办事大臣”一称)。清廷规定,在西宁办事大臣的主持与监督下,每年秋季在青海湖滨的察汗托洛亥举行祭海与会盟。以后清廷派遣官员主祭青海湖成为定制。
罗卜藏丹津叛乱事件成为清朝政府加强青海地区治理的导火索,也是清廷掌控青海湖祭海仪式主祭权的转折点。环湖各民族所信仰的圣湖崇拜与中央王朝国家祭海仪式分别为两个互不干扰、相对独立的祭祀体系。清朝旨在彰显国家统治“天下”的合法性与政治统一性,将民间圣湖崇拜与青海湖国家祭祀整合为统一的神灵体系。以此,实现了清廷政权和神权的统一,也证实清朝皇权威仪已覆罩青海地区。随着祭祀方式的演变,青海湖祭海仪式制度与内容亦随之进行了调整。
三、清代青海湖祭海仪式制度的逐步规范
祭祀体系是中国人在国家行政体系之外另建权威的一种常见形式,封建国家政权通过祭祀这一媒介将自己的权威延伸至乡村社会。中国历代王朝普遍通过建立石碑与海神庙、加封、御赐匾额、派遣专祭人员等举措明确民间神祇的合法地位和尊崇程度,逐步构建一套完善的祭祀体系,从而扩展其影响力,强化国家对地方的治理能力。清代随着青海湖祭海仪式主祭权之确立,为了实现全国范围内的统治,朝廷对国家祭祀体系的构建与完善尤为重视。
(一)建立石碑与海神庙
清朝为进一步巩固主祭青海湖的合法地位和权威性,雍正四年(1726)九月,诏令在青海湖滨的克图垭豁竖立正面有汉、满、蒙古三种文字书写阴刻的“灵显青海之神”石碑。遗存的石碑,碑身高150厘米、宽74厘米、厚14.5厘米。石碑两侧饰以竖刻盘龙纹,背面阴刻“雍正四年九月吉日立”九字,左右两侧分别镌刻满、蒙古两种文字。石碑座底有水纹或海浪刻纹,象征青海湖水。同时,还修建了一座碑亭。乾隆二十七年(1762),西宁办事大臣容保重划蒙古各部驻牧地区,仍定每年七月举行祭海会盟。从“仍定”二字可推断在此期间祭海仪式的大致时间。
嘉庆九年(1804),西宁办事大臣都尔嘉将“灵显青海之神”石碑迁移至察汗托洛亥地区。道光三年(1823),陕甘总督那彦成在此地筑建察汉城。察汉城以红沙土夯实而成,极为坚固。城呈长方形,城墙南北长410米、东北宽300米、顶宽约2.5米。城四角各有马面一座。城开东、西二门,门宽6米。西门外26米处有一道宽3—4米、长26米、高6米的遮墙。道光十二年(1832),西宁办事大臣恒敬上奏:“两成祭祀,而庙宇终未建修,神灵无所依凭为憾,爰出俸廉,鸠工庀材,为殿三楹,安设神位”,并在察汉城北约100米处修建了海神庙。光绪三十三年(1907),经钦差大臣(西宁办事大臣)庆恕等在青海湖东察汗托洛亥的察汉城建成海神庙,正殿三间,额题“青海胜境”四字,东西配殿三楹,中间建楼牌三楹。并将雍正碑(“灵显青海之神”石碑)移到大殿正中,并举行祭海祀典。自此,清代青海湖祭海仪式有了固定的祭祀场所。
(二)赐匾额和加封
自清廷主祭青海湖以来,清朝皇帝屡次赐匾、封号。雍正四年(1726)三月,雍正皇帝“敕封青海湖神为灵显青海之神”⑩。光绪三年(1877)九月十三日,光绪帝颁西宁青海海神匾额为“威靖河湟”。光绪五年(1879),清廷赐西宁府海神庙匾额为“德至泽洽”。光绪三十三年(1907),赐察汉城海神庙“青海胜境”匾额。宣统元年(1909),西宁办事大臣庆恕领官民在西宁城祭祀西海神求雨,清廷赐“泽溥西陲”的匾额。
从上述赐匾与加封的时间规律来看,清朝每位皇帝继位后不久或者重新修建祭祀场所后均会赐青海湖匾额与封号,以此宣示朝廷对青海湖地区的话语权和统治权。清廷如此重视青海湖祭海仪式,其原因在于祭海与会盟是青海蒙古族传统的融宗教、军事、政治、民俗于一体的重要活动。清朝统治者为了维护青海地区安宁,防止地方势力扩张,巧妙利用环湖民众的信仰,对青海湖加封不绝。其匾额及封号寓意恢宏大气,赋予青海湖有利于治国安邦的政治意义。
(三)设立西宁办事大臣主持和监督祭海与会盟
西宁办事大臣的常规性监督职责是主持和监督祭海与会盟。清朝青海湖祭海仪式的举行或暂缓,祭祀参加人员的确定、海神庙的修缮、会盟后的纠纷解决等问题均由西宁办事大臣决定。
据记载,雍正三年(1725),达鼐被任命为首任西宁办事大臣并被派到青海主持与监督祭海仪式,由青海副都统陪祭。乾隆十六年(1751),西宁办事大臣舒明奏准,每年例行的查旗、会盟、祭海等活动,皆因蒙古旗牧民生计维艰,无力承担乌拉差役而无法正常进行。乾隆二十七年(1762),西宁办事大臣容保重新划定蒙古各部落驻牧地界之际,奏准仍定每年七月举行祭海会盟。乾隆三十八年(1773),西宁办事大臣伍弥泰奏请,“青海龙神应该每年祭祀,嗣经礼部议准,每年的秋季致祭一次。太常寺颁发香帛,陕甘总督委道、府一员陪祭”。光绪三年(1877),西宁办事大臣豫师捐资在西宁府城西负郭修建海神庙一座,内供“青海湖之神”牌位,以为官民祈雨之所。光绪二十年(1894),奎顺在西宁府知府倭什铿额陪同之下前往祭海,蒙古王公、札萨克、贝勒及藏族千百户陪祭。光绪二十一年(1895),由于匪患四起和道路梗塞等因素,奎顺决定暂缓一次祭海与会盟。
自雍正至清朝终亡,照例由西宁办事大臣担任主祭青海湖,同时由陕甘督委、西宁府官员陪祭。西宁办事大臣的设立,使清代青海湖祭海仪式制度更为完善,并对该仪式的延续发展起到关键作用。西宁办事大臣主持和监督祭海与会盟,意味着清廷掌控了青海蒙古的祭祀权和司法仲裁权。至此,清代青海湖祭海仪式制度逐渐完备,更加符合国家现实环境和政权的自我诉求,并以制度形式固定下来。
总之,清朝通过敕加封号、颁发匾额、设立西宁办事大臣以及蒙藏民族一同祭海与会盟等方式不断完善祭祀体系。仪式体系的规范化使青海湖祭海仪式成为被认可和接受的官方活动。一方面,中央政府对祭海仪式的重视和支持进一步巩固了政治秩序和统治的合法性。另一方面,仪式的规范化有助于塑造和强化参与者对政治实体的认同。此外,参与者共同严格遵守仪式流程和行为准则。这种共同体验和参与有助于促进社会团结,加强祭祀群体的认同感。
四、清代青海湖祭海仪式内容与政治认同之塑造
“礼有五经,莫重于祭”,祭礼作为礼制中最重要的一项内容,具有非常严谨又复杂的仪式过程。在青海湖祭海仪式上,清代也不例外。根据相关历史文献记载,清代青海湖祭海仪式内容如下:每年祭海之时,钦差办理青海蒙古番子事务大臣一行人从西宁启程,经丹噶尔最终抵达青海湖滨的察汗托洛亥。青海诸蒙古王、公、台吉及藏族千百户齐集察汉城恭候西宁办事大臣。
祭海当日,全体起立等候主祭,各蒙旗王公、札萨克、藏族千百户和地方官等陪祭人员入席。西宁办事大臣、西宁镇总兵官入上座,各蒙古王公、藏族千百户分坐在左右两侧。1957年8月由青海文史馆整理的“祭海与会盟”材料中记载:“会宴规定了今年一大宴,明年一小宴。逢大宴的一年,每位王公的座前,设点心糖果,每桌汤羊一只,还有绸缎袍褂衣料以及马蹄胸、小刀、火镰、鼻烟等物品,按爵职大小分配;小宴的一年,每个王公宴前只设肉菜八碗,没有羊只,其他礼品和大宴相同。”所有参加祭海人员就位之后,由主祭人西宁办事大臣主持祭海仪式。西宁办事大臣宣祭海仪式开始。
1.迎神。祭海仪式第一环节是奏乐迎青海湖之神,随后由蒙古族歌手演唱《祭海歌》。歌词大意为:
虎年初一的吉辰,
那米黄色的骡子是西宁办事大臣的乘骑。
是王爵晋升的日子,
那铁青色的骡群,
随从的大小官员们各自晋升在其位。
是官员们随从而至。
神威的虎符大印啊,
在那美丽的青海湖畔,
握在你的右手多神奇,
搭起蓝色的大牙帐,
六十本法规文典拿在你的左手多威严。
大臣诺彦(首领)欢聚一堂,
银碗斟满马奶酒,
举行起隆重的祭海仪式。
是敬你的琼浆玉液,
祝愿吉祥如意!
钉上银掌的大走马呀,
尊贵的海神,
是供奉你远征的坐骑。
保佑我们吧!
2.行礼。《祭海歌》演唱完毕后,全体人员对海神庙内供奉的“皇帝万岁万万岁”牌位行三跪九叩之礼。之后,由主祭官宣读皇帝的圣旨并传达其旨意。
3.献祭。在“灵显青海之神”的石碑前进香、进帛、进祭品。祭品包括:太牢(牛、羊、豕)、藏香、蜡烛、俎豆、帛、五谷粮食、酒、茶、果品、龙旗一对、御仗四根等。
4.宣读祭文。主祭官用汉、满、蒙古三种语言宣读祭文。祭文内容如下:
惟神位协坎,惟法符兑泽。鲸波万顷,萦回环昧谷之乡;鲸浪千里,衍溢被流沙之城。属幅员之绵亘,编艺桑麻,沂潮汐之往来,周兹坟壤。曩以天戈奋勇,以后效灵。涌泉惊疏勒之奇,饮马届元冥之候。爱以显号,式拊丰碑。朕眷乃神功,贻兹美报。涌濡布洞,祈祷既洽与舆情,芬苾荐诚,望秩宜归于祀典。祇申秩享,特诏祠官。於戏,配殷祀于渎宗,具助隆文之备,助资生于边徼,永征灵贶之长。格奉明禋,尚其来格。
5.送神。全体人员向青海湖方向行三跪九叩之礼送神。随后,再朝着青海湖方向望燎。
6.礼成。由主祭官宣“礼成”二字并鸣炮。
7.抢宴。祭海仪式的最后一个环节,参加祭海仪式的蒙古各王公、札萨克及藏族千百户纷纷争抢献祭的牛羊肉,俗称“抢宴”,又称为“赐宴”。此举不仅彰显勇武矫健、剽悍之风,更寓意着通过抢宴祈求一年平安顺遂、健康喜乐。随后,参与会盟的人员在皇帝牌位前行跪拜谢恩之礼。
8.会盟。祭海仪式结束后,次日依据清朝规定的会盟礼节举行会盟。西宁办事大臣抵达会盟地点东科尔寺,蒙古王公、贝勒等在此5里外迎接。会盟过程中,西宁办事大臣首先宣读皇帝谕旨,即颁布政令。青海蒙古王公和藏族千百户汇报一年来各旗之间发生的争端、久拖未决的刑事案件及民事纠纷事件,以及王公缺位申请继承等要案。随后,预定次年各族朝贡觐见等事项,西宁办事大臣“面饬”各族严守约束,安定放牧、防止事端。会盟结束后,蒙古王公拜会西宁办事大臣,并赠送哈达、马匹、氆氇等礼品。最后,西宁办事大臣颁发清廷赏赐给蒙古王公和藏族千百户的绸缎衣料、领顶、茶封、小刀、鼻烟壶、瓷器等物品。随后,各归牧地。
清代青海湖祭海仪式时间、场所、主祭人员、祭祀用品及仪轨等皆已明确规定,从而使青海湖祭海仪式体系逐步走向规范化。值得注意的是,清代青海湖祭海仪式作为一项国家祭祀活动,其具体环节与相关文化符号具有丰富的政治功能。一是从实物的政治功能看,祭海仪式中的“皇帝万岁万岁万万岁”牌位、圣旨、龙旗、仪仗等作为青海湖祭海仪式中的重要实物符号,凸显了中央政权及皇帝形象的权威性和神圣性。这些物品不仅展示了青海地区各民族对皇帝的尊崇和敬意,也体现了中央政权对青海湖地区的关怀和支持。这些物品的运用,不仅使仪式的庄重性和合法性得到进一步加强,同时也加深了参与者对中央政权、神灵力量和边疆统一的认同感。二是从语言文字的政治功能分析,祭海歌与祭文内容均展现了蒙古王公和藏族千百户对青海湖祭海仪式的赞美和祈愿,表达了他们渴望获得神灵庇佑和国家荣耀的愿望。三是从行为的政治功能来看,参与祭海仪式的人们通过行三跪九叩之礼,对皇帝牌位表达敬意。这显示了蒙古王公和藏族千百户对皇权的尊崇与尊敬,同时彰显了他们对传统秩序和权威的顺从,以及对皇帝权威的认同和无条件服从。此外,在祭海与会盟过程中,西宁办事大臣以实施恩德政策安抚与笼络蒙古王公和藏族千百户,从而客观上加强了少数民族王公贵族与清政府之间的政治联盟,以及他们对清中央政权的向心力。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提升清中央政府在青海地区的控制和管理能力。
五、清代青海湖祭海仪式的影响
青海湖祭海仪式作为清代国家祭祀体系的组成部分,既是宗教与信仰的体现,也是政治与社会稳定的基石,在清廷边疆治理政策的实施过程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一)强化了对边疆民族地区治理的能力
在面对青海地区的地方势力时,清朝统治者深知,唯有制定出行之有效的治边方针才能实现安邦治国平天下。因此,清廷遵循历代王朝一贯秉持的“恩威并施”和“因俗而治”策略,一方面对边疆割据势力和反清势力采取武力镇压和军事征服的手段,另一方面则对少数民族实施“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的方针,充分尊重并维护各少数民族的社会习俗和宗教信仰。正如美国学者韩森在其著作《变迁之神:南宋时期的民间信仰》中提出的“封赐神祇是一种有效的统治方法”一样,雍正皇帝在用武力和军事镇压地方割据势力的同时,巧妙地利用“青海湖显灵”之说,将青海湖封为“神”并纳入国家祭祀体系。这正好弥补了清廷在青海地区军事力量的薄弱和法律制度实施的空缺,清朝政府用奇特自然现象来构建和巩固国家合法性和意识形态,以此获取当地民众的神权认同和政权认同。这种神权与政权的统一形式,反而得到青海蒙古、藏等民族对清廷政治权力的高度认同。这为清朝在边疆地区推行治理政策的顺利实施提供了有利条件。清廷指派主祭官员后,利用祭海仪式的契机,将政治统治的权力扩展至青海地区,旨在实现对该地区的长期直接治理。因此,朝廷将祭海仪式与青海蒙古族的政治性会盟相结合。清朝通过祭海与会盟,开始直接推行更为深入的治理措施。例如,在平息罗卜藏叛乱事件后,年羹尧向雍正皇帝拟奏了“青海善后事宜十三条”及“禁约青海十二条”,成为清朝治理青海地区的重要策略。
由此可见,青海湖祭海仪式构成了清朝政府对青海地区实施的有效边疆治理策略之一,青海地区各民族进一步被纳入清朝中央政府的管理体系。清朝统治者深刻认识到“边疆一日不靖,内地一日不安”的道理。因此,通过举行祭海仪式,深入青海地区,以赢得青海蒙古、藏等各民族对清朝政权的认同与趋于中央政府的向心力,从而加强和巩固了西北边疆地区的稳定,进而发展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征程实现了新的跨越。
(二)有效推进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明朝中叶,随着东、西蒙古各部落进入青海湖周边地区,原游牧于青海湖四周及黄河两岸的藏族部落大部分被迫迁移到黄河以南,“其留者不能自存,反为所役属”。清初,随着和硕特部落在青海影响的加大,青海藏族民众成为向和硕特蒙古部落首领缴纳租赋的部众,不受清廷直接管理。久而久之,藏族部落“知有蒙古,不知有厅卫营伍诸官”。罗卜藏丹津叛乱事件之后,和硕特蒙古的统治势力彻底瓦解。与此同时,藏族人民成功摆脱了蒙古贵族的奴役,迎来了休养生息的历史机遇。然而,逐渐显现的牧地与人口增长之间的严重失衡,促使藏族向青海蒙古各旗展开了争夺草场的斗争,特别是黄河以北的草场成为藏族各部落所争夺的地区。
为了妥善处理蒙古、藏族因争夺丰富的自然资源而引发的冲突,道光二十三年(1843)那彦成命藏族“同蒙古一体来会盟”。这促使以蒙古、藏族为主体的祭祀圈的形成。关于“祭祀圈”,日本学者冈田谦提出,“祭祀圈是共同奉祀一个主神的民众所居住之地域”在此基础上,诸多研究者不断运用和修正祭祀圈理论及其社会功能。其中,许嘉明提出,“祭祀圈是指一个以主祭神为中心,共同举行祭祀的信徒所属的地域单位,其成员则以主祭神名义下之财产所属的地域范围内之住民为限”。刘晓春认为,在仪式之前,村落或村民之间存在着差别,而一旦沉浸于仪式中时,不仅成员之间的差别消失了,而且村落中各成员之间阶层地位的差别也消失了,整个村落处于一种特殊的仪式时空,参与者严格遵守祭祀规则。
蒙古、藏族为主体的青海湖祭海仪式祭祀圈内,青藏高原的蒙古族与藏族共同祭祀青海湖神,并遵循清廷制定的祭海仪式制度。蒙古、藏族因共同信仰青海湖神而组成了一种特殊的祭祀组织,维持定期的共同祭祀活动。仪式过程中,蒙古、藏族沉浸于独特的仪式氛围中,严守祭祀规程,避免触犯禁忌。通过共同祭祀同一神祇,蒙古、藏族之间克服了原有的离散状态,实现了信仰与传统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他们互相认同彼此的信仰实践,进而形成了共同体的认同感和互助关系,从而增强了族际间的交流、交融。通过会盟,蒙古、藏族得以正面交流沟通,并将一年中所发生的矛盾与纠纷呈报西宁办事大臣,由其作出裁断并实施奖惩,从而使蒙古、藏族之间的矛盾由第三方公正评判。不仅如此,清朝借助祭海与会盟的契机对蒙古王公、札萨克、台吉以及藏族千百户进行封赏与恩赐,不仅彰显了清廷至高无上的权威,同时也加强了清廷与蒙古、藏族之间的联系。
青海湖祭海仪式作为一种信仰文化现象,以其主神为核心,以信仰为纽带,不仅能强化蒙古、藏等各民族集体意识,进而有效推进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固。更体现了清廷对多民族社会的管理和统治理念,以及对族际间的交流和共融的重视。
六、结语
仪式作为一种强制性的社会力量,具备激发、维持或重塑群体内部特定心理状态的功能,是社会群体周期性地强化自身凝聚力的重要手段。清朝在沿袭历代中央王朝传统祭祀制度的基础上,构建了一套较为完备的国家祭祀体系。此举不仅提升了青海湖祭海仪式实施和实效性,而且促进了国家认同感的形成。简言之,青海湖祭海仪式作为清朝政治权力的实践与表现形式,是国家对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的重要手段,不仅有效维护了国家的权威,而且有助于增进蒙古、藏等各民族之间的团结与交流,舒缓边疆地区的民族紧张氛围,为边疆地区的稳定和发展提供了坚实保障。以此强化“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政治意义。当前,古代国家祭祀所承载的政治功能的社会背景已不复存在。然而,在现代国家治理实践中,我们应当善于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治国理念与思维模式,广泛吸收古代边疆治理的宝贵资源和内容,为新时代的国家治理提供更为具体且深邃的古代思想和智慧。(作者简介:包美丽,内蒙古师范大学民族学与人类学学院讲师)
原刊于《中国藏学》2024年第6期,原文版权归作者和原单位所有,注释及引用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