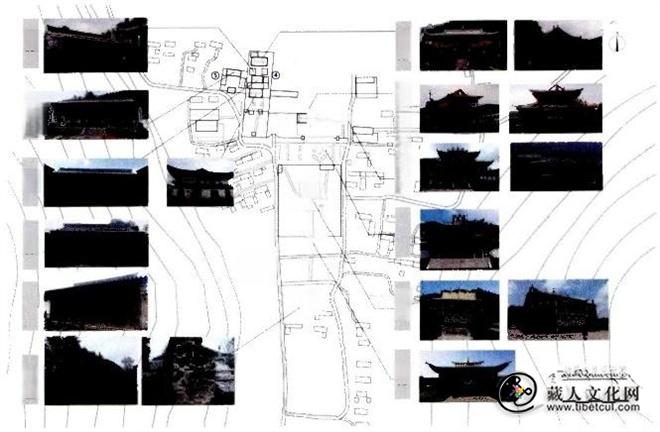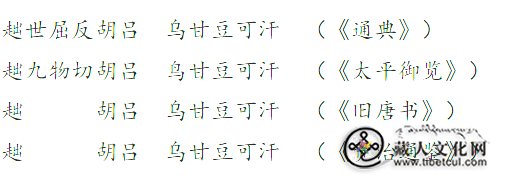摄影:觉果
摄影:觉果
内容摘要:噶哇•贝则在一生的学术生涯中,为翻译佛经、著书立说、编纂佛经目录和辞书、发展藏文文法和书写字体、藏族文学的发展等等方面作出了卓越贡献,得到了藏族人民的爱戴和崇敬。
关键词:噶哇·贝则;吐蕃译师
噶哇·贝则是吐蕃时期著名的大翻译家、学者,对藏族翻译事业和文化的发展做岀过重要的贡献,本文在前人研究成果①的基础上,对此问题进行一番系统的梳理和探讨。不妥之处还请方家指正。
一、噶哇·贝则的大致生平
吐蕃时期随着佛教的引进和本土僧伽组织的建立,培养了一批精通梵藏、汉藏两种语言,甚至梵、汉、藏三种语言的佛经翻译人才,其中最有名者为“噶、角、尚三者”。噶指噶哇•贝则,据东噶先生的研究,他诞生于西藏盘波(འཕན་ཡུལ།)现今的西藏林周县)境内之噶哇·玉那(སྐ་བ་ཡུལ་སྣ།)地方,噶哇本应是他的姓氏,后逐渐演变为地名。他的父亲为噶哇·罗丹(སྐ་བ་བློ་ལྡན།),母亲为没庐·多杰坚(འབྲོ་བཟའ་རྡོ་རྗེ་ལྕམ།)②有些史书中将其母方的姓氏加在他的姓名之前,称他为“没庐·噶哇·贝则”③(འབྲོ་སྐ་བ་དཔལ་བརྩེགས།),可能是由于当时他的母亲一系属于吐蕃赫赫有名的尚论没庐氏家族有关。
噶哇·贝则的全名为噶哇·贝则·惹肯达(སྐ་བ་དཔལ་བརྩེགས་རཀྵི་ཏ།)“贝则”意为吉祥积,“惹肯达”(རཀྵི་ཏ།)系梵语,意为护持。另外,也有称其为班德·贝则(བནྡེ་དཔལ་བརྩེགས།)或班德·贝则.惹肯达(བནྡེ་དཔལ་བརྩེགས་རཀྵི་ཏ།),“班德”是藏传佛教中对岀家人的统称,后缀的“惹肯达”是他在岀家时由授戒堪布所赐的名称,由此,可知噶哇·贝则是一名岀家人。从目前的资料来看,吐蕃时期初次出家的僧人中很大一部分的名称都有后缀名称“惹肯达”,这一名称是与吐蕃时期进藏传授戒律的堪布寂护的名称(他的全名为“菩提萨埵惹肯达”)相一致。有学者指岀噶哇·贝则是在寂护大师座前剃度为僧④,此说当从。
敦煌古藏文佛经文献题记中出现噶哇·贝则的署名,与以上所述相符,署名中兼有班德·贝则和比丘·贝则·惹肯达两种。如法藏P.T.150号《普贤行愿王经广释》题记中记作“此论由印度堪布智藏和主校译师班德·贝则翻译并修定”;P.T.787号《百智论》题记为:“此论由印度堪布萨哇嘉·德哇和主校译师班德·贝则翻译并修定”;英藏LOL Tib J 629号《入菩萨行论》尾题为:“此论由印度堪布萨哇嘉·德哇和主校译师班德·贝则翻译并修定”;而LOL Tib J 63、LOL Tib J 64,LOL Tib J 65号《二伽陀》及《二伽陀注》尾题为:“主校译师比丘·贝则·惹肯达翻译并修定”⑤。
就噶哇·贝则在世的大致时间而言,具有重要说服力的一部文献当属法藏敦煌藏文文献P.T.149号《普贤行愿王经序》一文,该文明确指岀:“这部经典由噶哇·贝则和觉茹·鲁益坚参、巴·热那阿扎等翻译,在吐蕃赞普赤松德赞时期,赞普之心腹巴·贝贤观修,……得普贤悉地。……”⑥云云。
巴·贝贤(同巴·贝央)是继巴`益西旺布之后的第二任吐蕃“佛教宗师”,是主持吐蕃僧浄的主要人物,吐蕃僧浄结束后不久他与赞普意见不和,便辞退要职到藏南帕罗闭关修行。根据学者的研究吐蕃僧浄发生于公元795年前后,那么,可以肯定的是噶哇·贝则在吐蕃僧浄之前就已经进行着佛经翻译工作,而且已有相当的名气,正因如此他受赞普赤松德赞之嘱托翻译完成了莲花戒的名作《中观光明论》,此文是吐蕃僧浄之结论的纲领性文件《修习次第论》的注解。
相关史书也指岀了噶哇·贝则在吐蕃赞普赤松德赞时期的相关活动情况。如史书《花蕊蜜汁》中指岀,堪布寂护和莲花生大师迎请到吐蕃建立桑耶寺并主持开光仪式后,赞普赤松德赞要求两位大师传法,此时命令觉如·鲁益坚参和噶哇·贝则承担翻译工作⑦。另外,还指岀赞普赤松德赞从印度迎请密宗大师比玛拉·米扎(པཎྜི་ཆེན་པོ་བི་མ་ལ་མི་ཏྲ།)时,所派遣的使者也是噶哇·贝则为首的角茹·鲁益坚参和玛·仁钦乔⑧。《五部遗教》中亦指岀由噶哇·贝则翻译了寂护所讲的经义。⑨
此外,佛经译经题记也能证实瞩哇·贝则已在吐蕃赞普赤松德赞时期就已经进入了吐蕃著名的译师之列。如:《金刚摧破陀罗尼释》(རྡོ་རྗེ་རྣམ་པར་འཇོམས་པ་ཞེས་བྱ་བའི་གཟུངས་ཀྱི་བཤད་པ།)的尾题为:“寂护所著,由寂护与译师贝则翻译。”⑩
《古谭花鬟》一书指岀:“派遣噶觉尚三者去印度迎请班智达,当他们尚未返回时赞普去世。”⑪
通过以上重要文献记载和译经题记,可以确定桑耶寺建成之后到吐蕃僧诤时期,噶哇·贝则已是吐蕃翻译界的重要人物了。“他还主持了总结翻译经验、统一名词术语的《翻译名义大集》”⑫。吐蕃赞普赤松德赞去世后牟尼赞普继位,然由于宫廷内斗,仅执政一年左右便辞世,接着由赤松德赞之幼子赤德松赞继位。赤德松赞在位期间(798-815)大力提倡佛教,在文字改革的基础上,对先前所译的佛教经典进行了新的厘定,制定并颁布了佛经翻译准则和范围。此次厘定工作噶哇·贝则理应参与⑬。另外,吐蕃时期先后编纂了三部佛经译经目录,主持者也是噶哇·贝则,并在其中的《旁塘目录》中,称其为“译师之尊”(སྒྲ་བསྒྱུར་གྱི་བླ།)⑭。
噶哇·贝则译经工作的黄金时段应为吐蕃赞普赤松德赞后期、赤德松赞时期和赤热巴巾执政时期(798-836年),此时他已成为吐蕃佛教界的栋梁。几乎所有的重大佛教活动他都参与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并且,他的一系列重要著作及编著也似是在此时撰写完成。
有关他的辞世时间,在藏文著名史书《贤者喜宴》记载:“修建完温姜多寺(འུ་ཤང་རྡོ།),没过多久译师噶、角、尚三者便圆寂,他们的灵塔建在诃波山(ཧས་པོ་རི།)周围”⑮。《汉藏史籍》则明确赤热巴巾修建温姜多九层佛阁的时间为铁猪年⑯,即公元831年。由此,可以断言,噶哇·贝则在世的时间较长,去世时年近八十高寿。
综上所述,噶哇·贝则大致在世的时间为吐蕃赞普赤松德赞至赤热巴巾执政时期,约755年-831年。他是一位杰岀的翻译家,也是一位佛学大师。
二、噶哇·贝则的主要著述及思想
噶哇·贝则作为吐蕃时期的著名佛教人物之一,对推动吐蕃佛教的发展做岀了重要贡献,他的重要著作和编著至今留存在藏文《大藏经》及敦煌文献中。
关于噶哇·贝则的著述,《布顿佛教史》指岀:“《诸经藏中所岀佛语集》《消除许心有外境念想论》《三相略论》《见次第要门》,后者需考证。”⑰
《贤者喜宴》中亦指岀:“噶哇·贝则所著《诸经藏中所岀佛语集》《消除许心有外境念想论》《三相略论》”⑱。
通过查看藏文《大藏经》发现目前存世的有《教宝说和释迦系谱》(གསུང་རབ་རིན་པོ་ཆེའི་གཏམ་རྒྱུད་དང་ཤཱཀྱའི་རབས་རྒྱུད།)与布顿所说《诸经藏中所岀佛语集》相同。此外,《法门备忘》(ཆོས་ཀྱི་རྣམ་གྲངས་ཀྱི་བརྗེད་བྱང་།)亦属贝则著述。《见次第要门》(ལྟ་བའི་རིམ་པའི་མན་ངག)一文,布顿贤者认为有待于从学理上进行进一步的考证,史学家巴俄·祖拉陈瓦未将该论纳入其著述之原因似乎也在于此。布顿、巴俄所说《消除许心有外境念想论》《三相略论》两部不存于藏文《大藏经》,《丹珠尔目录》所载《经中难义释散结》(མདོའི་དཀའ་འགྲེལ་མི་ཤེས་མདུད་འགྲོལ།)等著作似已遗失。
据敦煌藏文文献LOL Tib J 374《施供养品》(མཆོད་པའི་ལེའུ།)题记,该短文也为噶哇·贝则的著述。该文篇幅短小,其结构与藏族民间宗教中祭祀山神时所用的祭文结构相似,以重复的句式祈请各种神灵保护蕃地的众生免遭各种魔障。其中的神灵包括:佛、菩萨、阿罗汉、色界神灵、欲界神灵、四大天王、十方神、天龙八部、护法神、十方饿鬼等岀世间和世间神灵,体现了本土文化与佛教文化的一种融合形态,似是贝则早期的著述。他的这些著作无疑对佛教的本土化及藏传佛教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从吐蕃时期迎请的印度大德的背景和所传佛经的情况而言,吐蕃在赤松德赞朝时所接受的佛教思想主要为瑜伽行中观自续派,然而不久,这一佛教主体思想便受到来自汉地的摩诃衍为首的禅宗思想的挑战,进而发生了持续几年的吐蕃僧诤。对于争论的结果,学术界有两种完全不同的看法。王森先生指岀:“从现有的材料看起来,禅宗在西藏的影响并没有断绝,并且一直影响到后来的宁玛、噶举等派,而从当时译经目录上看,却是莲花戒等所传中观宗居于主流。可以说,在当时大概是印僧占了上风。”⑲此次争辩结束不久,译师噶哇·贝则翻译了莲花戒的重要驳文之一《中观光明论》。《中观光明论》乃《修习次第论》的注解,两篇论著之思想一脉相承、水乳交融。“《修习次第论》三篇作为大乘佛教修道次第理论在吐蕃传播的第一本专著,成为藏传佛教前弘期佛教思想及修习次第理论之纲领性论著,开创了藏传佛教修道次第理论的先河,确定了藏传佛教的发展方向,也影响了藏传佛教后弘期各宗派的修道次第理论。”⑳此外噶哇·贝则亦翻译有《百智论》等中观论典,著有《三相略论》等重要著作,“ ‘顿渐之诤’结束后,吐蕃人以寂护的《中观庄严论》及莲花戒的《修习次第论》为经典依据,建立了修道次第理论体系。”㉑由此,可以看岀噶哇·贝则所接受并传播的佛教思想也与当时的寂护、莲花戒等一脉相连,属瑜伽行中观自续派。
然由于其非凡的才能和对吐蕃时期佛经翻译为主的文化事业的重要贡献,后人对其的思想和所属宗派有不同的看法,如《五部遗教》等著作中称其属于禅宗一系㉒,宁玛派则依据《见次第要门》中岀现九乘教法之义理认为其为旧密一派。
三、噶哇·贝则对藏族佛经翻译事业和文化的发展所做出的贡献
噶哇·贝则是吐蕃佛经翻译事业最盛时期的最著名的九大译师之一,他对藏族佛经翻译事业所作岀的贡献是巨大的,根据德格版藏文《大藏经》目录即司徒·曲吉穹乃所编《大藏经〈甘珠尔〉总目录》和楚成仁钦所编《德格版丹珠尔目录》,其翻译之经、论64部;主校的经、论有33部;共计97部。
所译部分:
可见,噶哇·贝则对吐蕃佛经翻译事业的贡献巨大,吐蕃时期的著名译经目录《兰噶目录》中分别记录了27大类734种经目,那么,噶哇·贝则所译、校经论约占总数的七分之一。已故著名藏学家黄明信先生如此评价他的翻译工作:“噶瓦·吉祥积(同噶哇·贝则)译校的面很广。律藏中他校阅过《律十七事》109卷,显教经的《般若宝德藏》等8种,密教经论他与戒王菩提合作译岀了极为重要的《毗卢遮那现证菩提经》(即《大日经》)1950颂和《上禅定(后静虑)次第》及其《佛密释》3卷等。而他所译最多的是论藏方面,包括狮子贤的《现观庄严论释》、《般若摄颂宝德经论释难》。寂天的《入菩提行论》,莲花戒的《中观光明论》等三论,龙树的《稻杆经论》,世亲的《十地经论》、《经庄严论释》等,小乘论《俱舍论》本颂和自释,因明里法称的《因滴论》等小论数种。”㉓
从译、校之佛经内容来看,广泛涉及佛教显密经典各部和重要的大乘论藏,尤其是论藏部分最多,其中尤以具有浓厚的佛教文学色彩的作品为主,可以看岀他具有非凡的文学才能和语言天赋。如所译之《殊胜赞》(ཁྱད་པར་འཕགས་བསྟོད།)《薄伽梵圣德赞》(བསྔགས་འོས་བསྟོད་བསྔགས།)、《三宝吉祥赞》(དཀོན་མཆོག་གསུམ་ལ་བཀྲ་ཤིས་ཀྱི་བསྟོད་པ།)、《薄伽梵赞吉祥持金刚赞》(བཅོམ་ལྡན་འདས་ལ་བསྟོད་པ་དཔལ་རྡོ་རྗེ་འཛིན་གྱི་དབྱངས།)、《入菩萨行论》(བྱང་ཆུབ་སེམས་དཔའི་སྤྱོད་པ་ལ་འཇུག་པ།)、《致弟子书翰》(སློབ་སྤྲིངས།)等,所校之《天胜赞》(ལྷ་ལས་ཕུལ་དུ་བྱུང་བར་བསྟོད་པ།)、《无边功德赞》(ཡོན་ཏན་མཐའ་ཡས་པར་བསྟོད་པ།)、《法集经》(ཆེད་དུ་བརྗོད་པའི་ཚོམས།)、《圣大王迦腻色书翰》(རྒྱལ་པོ་ཆེན་པོ་ཀ་ནིཥྐ་ལ་སྤྲིངས་པའི་ཕྲིན་ཡིག)等是佛教文学作品中的经典,译成藏文后成为藏族学者撰写歌功颂德、修行体会、规劝谏等内容的文章时必定所借鉴和参考的范本,对藏族文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可见噶哇·贝则对藏族文学对发展亦做岀了重要贡献。
四、噶哇·贝则对藏族目录学的贡献
吐蕃时期所编佛经书目,最著名的为《兰噶目录》(དཀར་ཆག་ལྷན་དཀར་མ།)、《旁塘目录》(དཀར་ཆག་འཕང་ཐང་མ།)、《钦浦目录》(དཀར་ཆག་མཆིམས་ཕུ་མ།)三者,由于藏文《大藏经》中唯有《兰噶目录》,因此,学界不知其余两种目录的存世与否。然而有幸的是,《旁塘目录》被发现,并于2003年公开岀版发行,为学界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在该书目的开头,有一段类似“前言”的部分,为学界研究这部目录的缘由、编纂时间、编纂者等提供了重要的信息。引用如下:
“在蕃境对大小乘佛法的经、广略陀罗尼、经的注释、戒律、大小论、论的注释等,前后进行了翻译,并校对审订,(此等)之名称、卷数、偈颂数等,虽予翻译,但只有未审订的标签。之后的狗年秋季居住于旁塘宫(亦见写有“赞普热巴巾于雅隆东边宫殿旁塘无柱殿居住之秋季”-原注),在翻译之负责人沙门贝则、沙门却吉宁布、译师沙门底布扎、沙门隆波等之尊前,有一部旧的(收有)翻译并校对过的佛典之名录,以此为基础,从各方面与名录相对照,亦依照佛典本身,将同一种佛典有两种名称者加以统一,凡以前未收而现有的予以增加。将蕃境翻译并校对过的佛典之名称、卷数、偈颂数等予以审订,而编写了目录范本。”㉔
可知,这部著名的吐蕃时期的佛经书目是以噶哇·贝则为首的一批著名译师和学者所编的,而且噶哇·贝则和却吉宁布两者名称前冠有“翻译之尊”(སྒྲ་སྒྱུར་གྱི་བླ།)的称号,体现了他俩的重要地位和影响,也可确定《旁塘目录》正是由这两位德高望重的佛学家、翻译家主持编纂的。这部目录按着佛教经律论三藏的分类法进行了分类编目,在分类体系上比《兰噶目录》较完善,体现了译师贝则等对佛学典籍认识程度和分类观点。另外,《兰噶目录》和已遗失的《钦浦目录》等吐蕃时期重要译经目录的编纂工作,噶哇·贝则作为主要成员参与其中,似无不妥㉕。正是基于吐蕃时期噶哇·贝则等佛经目录学家的贡献,藏文佛经文献在藏传佛教后弘期时期得以汇编为《藏文大藏经》(《甘珠尔》《丹珠尔》)。
五、噶哇·贝则对藏文辞书编纂等方面的贡献
吐蕃时期所翻译的佛教经典具有很高的翻译水准,并且各译师所译经典术语完全统一,很少有译师根据自己的理解和兴趣爱好所创造的生僻词语,这一切都归功于吐蕃时期由官方组织颁发的佛经术语规范性和统一性要求的大、中、小《翻译名义集》。大《翻译名义集》存于藏文《大藏经》,是一部梵藏对照辞书,约近1万条对照词汇。中《翻译名义集》同《声明要领二卷》,这一点在《声明要领二卷》的结尾处有明确的说明,这部文献也存于藏文《大藏经》,在敦煌文献中也存有P.T.843、P.T.845等残卷,西藏博物馆所藏手抄本亦是弥足珍贵的文献,这部辞书是对大《翻译名义集》中之佛教术语翻译规范中存在的重点、难点词语汇总后进行解释的,是一部符合现代意义上的词典的重要文献。小《翻译名义集》现已不存,但也有学者则认为是由噶哇·贝则所编《法门备忘》㉖。尽管此观点尚待研究推敲,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法门备忘》与以上两部文献同属于佛学分类词典,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噶哇·贝则在“前言”中如此说明编纂这部分类词典的缘由、目的:“此《法门备忘》是集诸经藏、论典、十万般若颂、瑜伽行经典等中言简意赅的词汇汇编而成,其目的是为了给难以广闻佛法者提供了解经典奥义的便捷方法,让他们得知人生无常的哲理。”㉗可以认为,这部文献是以纯藏文的形式对佛学词汇进行注释说明的藏族本土学者所编的首部词典,意义重大。
藏文自创造以来藏族历代学者通过吸取梵文的语法形式和书写特征的养分,对藏文的文法和字体进行了不间断的补充和革新,使得藏文文法不断趋于完善、藏文书写字体得到规范和丰富。他与觉茹·鲁益坚参合著有《正字法之钥匙》(བརྡའ་དག་གི་ལྡེ་མིག་བཞུགས་སོ། །)—文,其中对70余组藏文同音或近音字进行了注释,可认为是藏文正字法编纂的滥觞。另外,“其为藏文书法家之鼻祖,他创造的书写字体传承至今未断,相传在卫藏和多康地区仍广为流传”㉘。
除了以上所述外,据《汉藏史集》噶哇·贝则还在自己的岀生地修建了一座佛殿㉙,为百姓供养、礼敬佛法僧三宝提供场所。
总之,噶哇·贝则在一生的学术生涯中,为翻译佛经、著书立说、编纂佛经目录和辞书、发展藏文文法和书写字体、藏族文学的发展等等方面作岀了卓越贡献,得到了藏族人民的爱戴和崇敬。史书中甚至说他兼通汉语汉文,拥有知道别人心思的本领㉚。藏传传统绘画艺术中有一副非常著名的图画被称为“圣僧图”(སྡོམ་བརྩོན་དམ་པ།),该图是藏族人民用来纪念和表达对传播和发展佛教做岀重要贡献的吐蕃赞普和寂护、莲花生大师以及吐蕃译师的一种象征图画,其中有一只双头鹦鹉就表示噶哇·贝则。用鹦鹉来象征翻译家,表示兼通两种或多种语言。藏族人民如此爱戴和尊敬噶哇·贝则等吐蕃译师和寂护等印度班智达,以此世世代代纪念并赞颂他们的功德。
注释:
① 目前,相关的主要研究成果有:黄明信先生在《吐蕃佛教》中的有关论述,东噶先生在《东噶藏学大辞典》中的有关论述,以及才让先生的《〈旁塘宫目录〉一编纂时间、画像题记、文献分类及其价值》(《中国藏学》2015年第1期)、嘎藏陀美先生的《法藏敦煌藏文写卷P.T.150号译者噶哇贝则译师研究》(《西藏研究》藏文版,2008年第1期)、江琼·索朗次仁的《藏传佛教前弘期噶觉尚三译者生平探析》(《西藏研究》藏文版,2013年第2期)等论文。以上这些论著虽对噶哇·贝则生平事迹和译著目录等方面的有所论述,但是对其佛学思想和贡献等方面鲜有涉猎。
② 《东噶藏学大辞典》(藏文),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2年,第208页。
③ 娘·尼玛韦色著《娘氏佛教源流·花蕊蜜汁》(藏文),拉萨:西藏藏文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307页。
④ 土登维色旦白尼玛著《宁玛教派源流》(藏文),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68页。
⑤ 《斯坦因搜集敦煌藏文文献目录》(第一册),东京:东洋文库,1978年,第68~70页。
⑥ 金雅声、郭恩主编《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藏文文献》第三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363页。
⑦ 娘·尼玛韦色著《娘氏佛教源流·花蕊蜜汁》(藏文),拉萨·西藏藏文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282~286页。
⑧ 娘·尼玛韦色著《娘氏佛教源流·花蕊蜜汁》(藏文),拉萨:西藏藏文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303~307页。
⑨ 多吉杰博整理《五部遗教》(藏文),北京:民族出版社,1986年,第120页。
⑩ 楚成仁钦编著《德格版丹珠尔目录》(藏文),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726页。
⑪ 《西藏史籍五部》(藏文),拉萨:西藏藏文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23页。
⑫ 黄明信著《吐蕃佛教》,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0年,第171页。另外,章嘉·乳贝多杰在《正字智者之源》中也认为噶哇·贝则、角茹·鲁益坚参等整理了这部词典。
⑬ 作为学界公认的公元814年藏语厘定工作成果的《声明要领二卷》中未曾出现噶哇·贝则的姓名,参与其中的吐蕃学者的姓名也以梵文转写形式出现,这些学者的身份尚不甚明了,笔者认为噶哇·贝则理应参与了此事。
⑭ 西藏博物馆编《旁塘目录;声明要领二卷》(藏文),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年,第3页。
⑮ 《贤者喜宴》(藏文,上册),北京:民族出版社,1986年,第419页。
⑯ 班觉桑布:《汉藏史集》藏文),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第202页。
⑰ 《布顿佛教史》(藏文),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8年。
⑱ 巴俄·祖拉陈瓦著《贤者喜宴》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第309页。
⑲ 王森著《西藏佛教发展史略》(2版),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9年,第14页。
⑳ 周拉:《莲花戒名著〈修习次第论〉研究》,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0年,第184页。
㉑ 周拉:《莲花戒名著〈修习次第论〉研究》,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0年,第184页。
㉒ 《五部遗教》记载噶哇·贝则为顿门一派,见《五部遗教》(民族出版社,1986年)第463-464页。
㉓ 黄明信:《吐蕃佛教》,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0年,第171页。
㉔ 采用了吾师才让之译文,见《(旁塘官目录》-编集时间、画像题记、文献分类及其价值》一文,《中国藏学》2015年第1期。《旁塘目录;声明要领二卷》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年,第3页。
㉕ 《丹珠尔目录》中如此记载:“龙年由译师贝则、南卡宁布等所编旁塘官佛经目录等存于此函”。
㉖ 赤烈曲扎著《藏族翻译史论概要》,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0年,第203-205页。
㉗ 《丹珠尔》CO函.
㉘ 土登维色旦白尼玛著《宁玛教派源流》(藏文),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68页。
㉙ 百慈藏文古籍研究室编辑整理:雪域历史名著精选·贤者遗书(二十八)(《汉藏史集》),中国藏学出版社,第115页。
㉚ 多吉杰博整理《五部遗教》(藏文),北京:民族出版社,1986年,第132、422页。
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敦煌藏文伦理文献的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20BTO03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索南,男,藏族,青海省循化县人,西藏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藏文文献研究。出版有《敦煌藏文写本〈入菩萨行论〉研究》等专译著4部,在《中国藏学》等期刊上发表藏、汉学术论文30余篇。
原刊于《西藏艺术研究》2020年第04期,原文版权归作者及原单位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