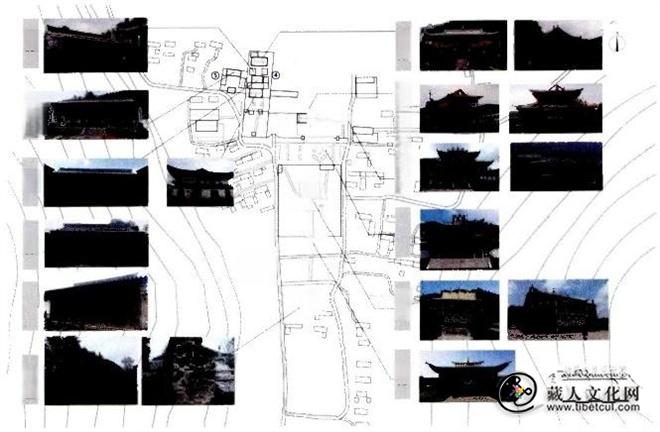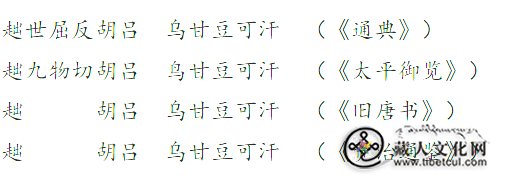摄影:觉果
摄影:觉果
摘要:敦煌藏译本汉文典籍作为9至10世纪汉藏文化交流的重要遗产,不仅对于探究古代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互动具有重要价值,同时也为当代语言学、文献学及历史学领域提供了丰富的研究资料。回顾过去近七十年的研究历程可知,1954年苏远鸣先生对《孔子项讬相问书》的精辟考证正式开启了学界对敦煌藏译本汉文典籍的专题研究。随着探讨的深入,藏译汉文典籍文献研究呈现出跨学科特征,海外学者对敦煌藏译文献的辨识、语义解释及拉丁字母转写贡献出重要成果。这对文献还译、对比分析及汉藏文化交流的探讨尤具新颖视角。因此,从学术史视阈系统回顾和梳理相关研究历程有助于反思敦煌藏译本汉文典籍研究的基本理论和主要方法,为未来接续研究提供新的学术增长点。
关键词:敦煌;藏译本汉文典籍;翻译;研究;综述
引言
在敦煌发现的古藏文文献中,相较于汉藏佛教文献译文,传统汉文典籍藏译本显得弥足珍贵。迄今为止,已发现的此类文献仅包括《春秋后语》(PT.1291)、《孔子项讬相问书》(PT.992、PT.1284、ITJ.729)、《古太公家教》(PT.987、PT.988、中村不折藏本)及《尚书》(PT.986)等四部作品。自1954年法国学者苏远鸣(Michel Soymié)在《亚洲学报》上发表《孔子项讬相问书》的研究成果以来,已经过了整整七十年的学术探索,汉文典籍敦煌藏译本研究也在多个领域取得了显著成就。
本研究旨在回顾近七十年来汉文典籍敦煌藏译本的研究历程,并展望未来可着重探讨的方向。从1950年代初期拉露女士对PT.986《尚书》的识别,到苏远鸣对《孔子项讬相问书》的考释,再到今日学者对这些文献的深入分析与诠释,汉文典籍敦煌藏译本研究已跨越语言、文学、历史与文化等多个学科领域。国外学者在文献的语义学注释、拉丁转写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而国内学者则在还译、对比分析及汉藏文化交流上展现出独到的视角。
敦煌藏译汉文典籍的学术价值不仅体现在对原文的忠实还原与诠释上,更在于其作为文化交流的见证,记录了汉藏两个民族在思想、文化和社会层面的互动。通过对这些文献的研究,我们可以更好理解古代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互动,以及汉藏两大文明在历史长河中的相互影响与借鉴。
未来,我们期望通过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利用现代语言学、文献学、历史学等多学科理论与工具,对这些珍贵文献进行更为系统、全面的分析,以期揭示其深层的文化意义与学术价值。希冀本研究能够为学术界提供新的参考与启示,进一步推进汉藏文化交流与敦煌文献研究。
一、近七十年国外研究情况
国外研究敦煌藏译古汉文典籍的时间相对较早。例如,早在1950年,拉露女士在其所编《法藏藏文文献的解题目录》第二集中首次指出PT.986为《尚书》之《周书》部分。[1]1954年,法国学者苏远鸣(Michel Soymié)在《亚洲学报》上发表研究成果,对《孔子项讬相问书》(PT.0992、PT.1284卷)进行了较为完整的考释。[2]1961年,拉露女士在《法藏藏文文献的解题目录》第三集中提出PT.1291是《尚书》(拉露作《书经》)的改写本[3],而后来的研究者纠正为《春秋后语》(卷七《魏语》)。1969年,英国藏学家黎吉生(Hugh E.Richardson)发表的《藏文古词的chis和tshis》(Tibetan Chisand Tshis)刊于《大亚细亚》(Asia Major)期刊,其中有PT.986卷(《尚书》的藏文译本)中所提到的“chis”(治)一词的研究,但并没有对《尚书》的藏译文作更多讨论,[4]而对于其中包含的藏文翻译汉文典籍的专题研究则起步相对较晚。
1979年,日本藏学家今枝由郎(Yoshiro Imaeda)在当年牛津大学召开的国际藏学讨论会上发表《关于“治”一词的翻译问题》一文,继黎吉生后对该词汇进行深入讨论。该文章的汉文版由王尧先生翻译并刊载在《民族译丛》1982年第1期上。1980年,今枝由郎在《敦煌吐蕃文书中的战国策》中[5],首次认定敦煌古藏文PT.1291号文书是《战国策》译本。这一提法对国内外研究起到重要影响,如王尧和陈践发表《敦煌吐蕃文书第PT.1291号〈战国策〉藏文译文证补》,重新对这件文书进行释读。只是该观点后来被马明达所纠正,提出了卷号1291实则为《春秋后语》的看法。
1985年,山口瑞凤编辑的《讲座敦煌》《敦煌胡语文献》出版。其中由今枝由郎执笔,介绍了敦煌藏文文献里中国和印度的古典文献,包括PT.986(《尚书》)、PT.1291(今枝由郎误作《战国策》,实为《春秋后语》)及《罗摩衍那》的数种藏文写本。[6]对于PT.986,文章介绍了其各行所对应的《尚书·周书》中《泰誓中》《泰誓下》《牧誓》《武成》的部分,然后主要分析了藏译文的翻译特点和策略;认为该译本并非逐字逐句的直接翻译,而是融入了孔安国《传》、孔颖达《正义》以及其他若干资料,对《尚书》原文进行了具有概括性和阐释性的翻译。比如,汉文《牧誓》所述的庸、蜀、羌、髳、微、卢、彭、濮八国之人,在藏译本中并未逐一列出,而是以“sna phra mo la gtogs pa”(意指各级小官吏)一词高度概括,显示出遇到受众不熟悉且未必有用的内容时译者的语言转化能力。今枝由郎最后指出,藏译本所述这些故事的文献来源,即其汉文原典的出处,值得学者深入探究。总之,今枝由郎阐述的PT.986翻译技巧与风格特征,大体已被黄布凡先前的研究成果《〈尚书〉四篇古藏文译文的初步研究》覆盖,尽管他没有像今枝由郎那样进行深入详尽的考证与辨析。
1991年,藏学家柯蔚南(W.South Coblin)在黄布凡先生的基础上推进了《尚书》藏译本的研究,撰写了《古藏文〈尚书〉的研究》,分两部分发表在《美国东方学会会刊》[7],其中对PT.986号进行了拉丁转写(黄布凡转写的是国际音标-IPA)和英文翻译,并对相关疑难词汇和历史史实加以纠正和考证。最后以藏文字母的顺序对藏文本中的词汇做了索引表,将汉文本《尚书》也翻译成英文,以方便不懂汉语的读者对比研究。从而有力推进了藏译汉文典籍,尤其对《尚书》藏译本的研究。
1992年,著名藏学家石泰安(Stein)用法文撰写了《两卷敦煌藏文写本中的儒教格言》(Confucian Maxims in two Dunhuang Manuscripts)①,首次对法藏敦煌藏文文献PT.987、PT.988号进行较全面的介绍。同时,他在文章中成功辨认出其中的两段文字,一段说到姜太公渭滨垂钓,另一段是《论语·卫灵公》里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石泰安称之为“儒家格言(maximes confucianistes)”。
1993年,一直致力于周朝研究的学者——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夏含夷(Edward Schaughnessy)在关于《尚书》的研究中写道:敦煌古藏文PT.986卷是一部对《尚书》中的三篇章节进行诠释的作品,他在该文献的最后部分汇集题为“周书”[8]。据本人推断,此后20年间,国外再没有出现针对敦煌藏译本汉文典籍的研究成果。
国外最新的一篇相关论文是2018年伽拉提(Emanuela Garatti)撰写的Pelliot Tibétain986:New Approaches to a Tibetan Paraphrase of a Chinese Classic among Dunhuang Manuscripts一文。该文剖析了敦煌第17号洞中所发现的藏译汉文典籍PT.986卷,也就是藏译本古文《尚书》片段。伽拉提根据该卷的物理形态指出,PT.986并非孤立的抄写行为,而有可能是在官方背景下制作的。其理由为:一是该卷是长达200厘米、宽31厘米的大卷,使用的纸张质量上乘,且有加固处理,显示出其在写作时的官方用途;二是手稿的书写清晰、组织良好,由两位抄写员完成,文本的布局经过精心设计,符合当时敦煌地区官方文件的书写规范;三是在内容上,PT.986展现了对《尚书》中关键章节的完整释义,其中包括对周朝征服商朝的历史事件叙述。伽拉提特别关注手稿中对中原哲学和政治概念的翻译策略,如“道”“德”和“天命”等。这些概念在藏文中得到了深思熟虑的对应表达,显示出译者对原意的准确把握和对中文概念的深刻理解。[9]
总之,国外学者发现和关注敦煌藏译本汉文典籍的时间较早,起到了开拓性的作用,虽然早期工作主要集中在文献的识别和基础性研究,但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基础。再者,国外学者在文献的语义学注释和拉丁转写方面做出的努力,不仅有助于跨语言的学术交流,也促进了对文献原意的深入理解。国外研究者还运用跨学科研究方法,结合语言学、文献学、历史学等多学科理论与工具,对文献进行更为系统和全面的分析,体现了对文献深层文化意义与学术价值的追求。
二、近七十年国内研究概况
国内对敦煌藏译本汉文典籍的研究,从20世纪90年代后方才开始。例如,1981年,冯蒸在《敦煌藏文本〈孔丘项讬相问书〉考》[10]中,首次参考苏明远(M·Soymié)的法译文,并根据敦煌文献中三种《孔丘项讬相问书》藏文版,互相参照后进行了汉文还译;之后,参考现存的十五个敦煌汉文版《孔丘项讬相问书》中有明确记年的写本(此写本卷末有“天福八年癸卯岁十一月十日净士寺学郎张延保记”的题记,天福八年是公元943年),提出藏文写本也可能是10世纪左右的写本。最后,举例说明了古代藏语在若干拼写法方面的特征和写法上的歧异。
同年,黄布凡在《〈尚书〉四篇古藏文译文的初步研究》中指出,《尚书》有古文和今文两种文本,而敦煌古藏文文献中的藏译本《尚书》实则为《尚书·周书》的《泰誓》(中)、《泰誓》(下)、《牧誓》《武成》4篇。在该藏译本的原文方面,他认为“藏译本译者至少参考了伪孔传(晋人梅赜假托汉代孔安国之名所作的《尚书孔氏传》)和孔颖达《尚书正义》,有多处是将伪孔传和孔疏与原文合在一起翻译。此外,也有几处既非依据原文,也非依据伪孔传和孔疏”[11]。他以译文中《武成篇》中“王季”名字的写法等为线索和依据,推断译文也有可能是依照《史记》和其他史料或现在见不到的其他注本或者译者听到的传说或解释而翻译而成。他也根据该卷书法特点讨论了其成立年代为9世纪中叶或9世纪末,并指出译文对于研究藏文史、汉藏翻译史、中古汉语音韵、拟汉字中古音研究方面的价值。在最后,他逐字逐句做了拉丁文转写和汉文隔行对照,并对一些疑难词汇作了较详细说明,推进了国内《尚书》藏译本的研究进程。
1982年,王尧和陈践指出,敦煌汉文写卷中有29个卷号为伪孔传《古文尚书》,包括英藏6个卷号,法藏23个卷号,并罗列了这29个卷号的编号及其篇名;还提出敦煌藏文本《尚书》的出现,与当时流行在敦煌一带的汉文写本有关的观点。②
1983年,王尧和陈践发表了两篇重要论文,分别是《PT.986〈尚书〉译文》和《敦煌吐蕃文书第PT.1291号《战国策》藏文译文证补》。前文基于黄布凡的研究成果,重新梳理了藏文所译《尚书》内容具体为《泰誓》(中)、《泰誓》(下)、《牧誓》《武成》4篇,在还译为汉文后与伪古文《尚书》原文进行对照和解释。③后文提出了编号为PT.1291号的藏文写卷影印件实际为《战国策·魏策》的古藏文译本,并列出《田需贵于魏王》(《魏策二》)、《华军之战》(《魏策三》)、《秦魏为与国》(《魏策四》)、《王假三年》(《史记·魏世家》)、《秦王使人谓安陵王》(《魏策四》)、《魏攻管而不下》(《魏策四》)等篇目。同时,认为这篇《战国策》的古藏文译本,虽晚于马王堆帛书《战国纵横家书》,但早于南宋成书的《战国策》姚宏校本和鲍彪注本[12]。同年,王尧、陈践编写的《敦煌吐蕃文献选》由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为国内敦煌古藏文文献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研究资料,推动了敦煌学的发展。
1984年,王尧撰写了《敦煌藏文写本手卷研究近况综述》一文,其中对藏文版《尚书》中为何单选《泰誓》(中)、《泰誓》(下)、《牧誓》一篇和《武成》一篇进行翻译而不选择其他部分提出自己的见解。他推测这几篇都属于《周书》范围,可能当时吐蕃以“周”自命,俨然有“以周伐殷”的姿态,为进驻河湟,继而据秦陇、入长安的行动寻找历史根据,因此颇有“影射史学”的意味。[13]
马明达也在这年发表《PT.1291号敦煌藏文文书译解订误》,对关于PT.1291卷被断定为《战国策》的藏文译本的论文进行了纠正,认为该文献实际上是《春秋后语》。相比之前的研究,由于藏译本PT.1291卷里记载着超出《战国策》的内容,所以一致认为藏文译者在翻译这些文本时不仅使用了《战国策》还参考了《史记》中的一些记载,以进一步完善译文。而马明达首先列举出了PT.1291号与《战国策》中许多不相合的地方并指出,“《战国策》并不是一部世系清楚、编年明晰的史书,年代紊乱和史料真伪错杂,正是它遭到后代诟病的地方。而藏译本《魏策》六章中,竟有四章具有今本《战国策》所没有的世系和纪年,这与《战国策》的体例大不相合;”[14]并对比敦煌P.2589号汉文《春秋后语》残片指出,PT.1291号为已经亡佚但根据《战国策》改编的《春秋后语》中《魏语》某些片段的藏文译本。[15]
1994年,郝苏民基于1981年冯蒸对《孔子项讬相问书》的梳理,从故事情节层面对比了汉、藏文写卷《孔子项讬相问书》与卫拉特西蒙古民间故事《骑黑牛的少年传》,揭示出藏文和蒙文版的翻译是汉族传统文化对周边民族的影响。同时,他还认为,“无论是爪哇文、藏文,还是蒙古文的译文,都非出自一个翻译者之手,被译的时间也非同一时期,但它们却不约而同的运用了一种更趋向于所译语言的民族化的方法。”而且“译者们着重的是一切有利于传递原作实际信息”,并提出这些显示孔子从小儿处悟道的故事是宣扬儒学观点的世俗故事。[16]
2005年,聂鸿音对P.988号藏文写卷进行了考补。他在石泰安(Rolf Stein)的基础上,对其所指的chos、rtsal、yangcheng等关键字的译法提出质疑和纠正;从而指出敦煌PT.987和PT.988两个写卷中的一些名言警句实则源自《论语》《孟子》《后汉书》等汉文史籍;并结合敦煌汉文本《太公家教》和西夏黑水城文献,认为这部书体现了唐宋之际西北俗文学的一种典型风格,其底本是流行在河西地区的汉文童蒙课本,原作大约与《太公家教》或者敦煌所出的《新集文词九经抄》等属于同一类型。[17]
2011年,郑炳林、黄维忠所编《敦煌吐蕃文献选集》(文学卷)由民族出版社出版,其中收录了《孔子项托相问书》的三种版本,即法藏PT.992卷、PT.1284卷和英藏ITJ.729卷,并附有简短说明、注释以及陈践和冯蒸的还译本。[18]这给研究人员提供了很多便利。同时,陈践对敦煌古藏文PT.992《孔子项托相问书》做了较详细释读,在与敦煌汉文文献中的《孔子项托相问书》进行比较后指出,敦煌古藏文文献中汉译藏文文献的存在表明汉藏民族间文化交流的多元化与频繁性,也指出藏译本删减、增译等翻译策略。[19]
2012年,南卡加完成了题为《〈孔子项讬相问书〉藏译本研究》的学位论文。这项研究主要基于传统翻译理论《语合二卷》中提出的四种基本译法之一——意译法,探讨藏文译本的翻译策略和技巧。他不仅分析了不同译本所采用的翻译方法,而且还对译文中出现的漏译和误译部分进行重新翻译和修正,提出自己的见解。论文最后也扩展到了对译文历史价值、文学价值和文化价值的简明探讨。
2014年,陈践以《敦煌古藏文PT.986文书〈尚书〉四古词译释》为题,对新旧藏文词典未收入的“为社稷立战功”“敦伦”“进谏”“残虐”等四个古词进行了详细辨析,并与伪《古文尚书》相应的语词作了准确的对译。他相信,PT.986文书是吐蕃时期顶尖译者的杰出作品,内容翻译准确且易于理解,这不仅丰富了我们的文化财富,也为难以解读的古词提供了可信的释读,具有校正其他文献中错误翻译的价值。[20]
2015年,马晟楠发表了《法藏敦煌文书PT.986〈尚书·牧誓〉的藏汉对勘研究》。[21]其中,采用藏汉对勘方法,选取《牧誓》篇中的五个句子进行语言学描写和分析,以期更好理解两种语言的深层语义关系。该文揭示了藏汉翻译中的多种语言现象,如汉语的“孤立型”特点导致语序对句义的重要性,而藏语由于形态变化的存在,语序的改变对句义影响较小。此外,汉文原文中的强调结构和特殊句式在藏文译本中可能丢失或简化,反映出不同语言在表达强调和语义关系时的语法手段差异。文章也讨论了翻译过程中信息的损耗和偏差问题,指出这可能源于翻译者的双语水平、文化背景和主观意图等因素。
随即,沈琛通过《敦煌藏文写本PT.1291号(〈春秋后语〉)再研究》,对PT.1291号文献的学术史进行了回顾,并在马明达的研究基础上,进一步对PT.1291号文献进行详细的校对和重新翻译,纠正了之前译文中的一些错误;还与汉文《春秋后语》原文进行比对,揭示出藏文翻译的特点和规律。在翻译方法上,他也指出,藏文翻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并非逐字逐句直译,而是根据理解和表达的需要,对原文进行适当的删减和意译。例如,对于历史典故、不熟悉的地名和人名,翻译者采取模糊化处理或删削,而对于晦涩难懂的汉文表达,则变换为简单易懂的说法。④
2017年,萨尔吉和萨仁高娃首次对日本台东区立书道博物馆藏中村不折旧藏敦煌西域文献(Nakamura Fusetsu collection)中藏文版《古太公教》开展了较详细的转录、翻译和分析。其中结合法藏敦煌藏文文献P.T987、P.T988号,对该件中村不折旧藏本全卷以及PT.988号的后半部分予以转录、翻译,并介绍了3篇藏文文献的价值、翻译风格以及与《太公家教》等敦煌汉文写本童蒙读物的关系等。[22]
不久,陈践基于上述二人的成果,对中村不折旧藏敦煌藏文写本《古太公家教》进行拉丁文转录、汉译和比较研究。他不仅对《古太公家教》前1-61行进行录文、翻译,并刊布该文献首、尾的影印件,还对其62-163行做了翻译,并与其他译者的汉译本、敦煌汉文写本展开比对研究。[23]
2018年,朱丽双较完整地梳理了敦煌藏文本《尚书》的研究现状,并探讨了该文献的来源问题,提出该文本很可能是对敦煌地区流传的汉文《尚书》传本的翻译,而非源自吐蕃本土的藏译本抄本。[24]对此,张先堂也曾推测,PT986《尚书》及其他几部作品可能是吐蕃文人直接根据唐代敦煌地区广泛流传的汉族古代和当代文学作品而编译的。[25]
2020年,朱丽双发表了两篇涉及吐蕃王权叙事和儒家文化的论文。第一篇对古藏文中关键政治文化术语chos与gtsuglag做了考析。她以PT.988(《太公家教》)、中村不折旧藏《古太公教》和PT.986(《尚书》)等藏译敦煌汉文文献为据,提出一系列在敦煌古藏文文献中称赞吐蕃赞普及与礼仪行为相关的“gtsugl ag”,二词可释作“礼”。相应地,chos lugs意为礼俗、礼法;chos gtsug lag意为最好(最高、最上)之礼(礼仪、礼制)。礼是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中古时期中原地区历代王朝治国的根本和基石,但其也曾对吐蕃王朝产生过某些不为今人所知的作用。[26]第二篇中提出吐蕃的政治文化既有欧亚内陆文化的传统,又有中原儒家文化的遗迹。儒家礼仪制度引入吐蕃,发生在松赞干布统治时期,其目的在于以成文的礼制形式,规定上下权利、区别君臣名分、确定赞普至高无上的统治地位,从而保证王室的长治久安。[27]
总的来看,国内对敦煌藏译古汉文典籍的研究虽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与国外研究相比,国内研究在还译、注释、对比分析及汉藏文化交流视角上展现出鲜明的特色和独有的视角。另外,国内研究在方法上重视文献的还译,且擅长使用对照分析。还译不仅考验译者的语言功底,也要求深刻理解汉藏文化之间的差异。而通过将藏译本与汉文原本进行对照分析,可以揭示出翻译过程中的文化适应与信息传递特点。其中可概括为两大特色:一是立足于文献学与历史学的交叉点,深入挖掘文献背后的文化脉络;二是强调文献在文化交流中的桥梁作用,展现了汉藏文明相互影响的历史深度。而国内研究者往往以汉藏文化交流的角度贯穿始终,试图通过文献的翻译与传播,洞悉汉藏两个民族在思想、文化乃至政治层面的互动与融合。
三、研究反思与未来展望
敦煌藏译本汉文典籍作为9至10世纪汉藏文化交流的珍贵史料,包含丰富的历史信息,映照出古代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互动。通过对近70年来敦煌藏译本汉文典籍的研究历程进行回顾,希冀在总结既往科研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宽视野,推进这一独特文化遗产的理解与诠释,并对当前相关研究作以下反思。
(一)注重文献传播与接受的探讨
尽管国内外学界在敦煌藏译本汉文典籍的语义学注释、拉丁转写、还译、汉藏文化交流等方面做出了贡献,但从传播与接受的角度切入者相对较少。一方面相关研究往往局限于个别文献或片段,未能从宏观与整体的视角审视典籍,对于文化交流的深层动力、过程及复杂性的探讨仍显不足;另一方面关于敦煌藏译本汉文典籍的来源、传播途径以及受众的相关资料不够丰富。未来的研究需要着重关注敦煌藏译本汉文典籍如何在不同文化和社会环境中被转化、接纳和吸收。譬如,分析吐蕃时期汉藏文化交流的具体机制、翻译活动的社会文化背景、此种交流如何影响两地的社会结构和知识体系,以及汉藏文化之间的互动如何影响文献的翻译工作和受众对文献的理解等。
(二)加强汉藏译音与中古音的比较研究
整理敦煌藏译本典籍中的译音词,为中古时期汉语和藏语(甚至包括其各自的方言)研究提供新的材料。敦煌藏译本《大雅》《论语》《礼记》等典籍中有大量人名、地名、书籍名称均采用音译。整理并分析汉藏对音用字,能够为汉语和藏语的古音构拟提供宝贵的数据支持,进而加深对古代语音演变规律的理解与认识。
(三)藏语词汇史研究
通过译文研究藏语词语的发展、演变,可以为藏语词汇史研究打开新的视角。比如,敦煌古藏文文献中的词汇,许多在当今人们的口语中仍然使用,而那些在现代口语中已不再使用的词语却在十世纪后的藏文文献材料中仍能见到;还有一些古词在现实生活中和文献中都难觅踪迹,但可以借助译文中对应的汉语得知其含义。
(四)藏文文法著作年代的判别研究
目前学界对《三十颂》和《字性法》的著作年代尚未达成一致。与吐蕃时期的其他古藏文文献一样,敦煌藏译本汉文典籍中有些虚词的用法并不完全合乎这两部文法的规范。例如,属格助词gi、kyi与作格助词gyis、kyis的用法;指示代词ste、te的用法;虚词cig、zhig的用法;词尾pa、ba的用法等。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敦煌译本中出现的下加符号“瓦苏”以及藏文字母中唯一的双辅音字母较多,且形态上呈现出一定规律,有助于推测藏文字母表定型的年代。此外,通过敦煌译文和其他古藏文文献中不规则的语法现象,还可以推定《三十颂》和《字性法》两部文法的著作年代。
(五)藏文学术界要对敦煌藏译本汉文典籍引起足够关注
敦煌古藏文文献作为宝贵的文献遗产,在以藏文为媒介的学术界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目前研究者对于敦煌本藏译汉文典籍的关注度尚显不足,仅有一篇藏文写就的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对此进行了探讨。这种状况显示了藏文学术界对这一领域潜在价值的认识不够。今后应提高对敦煌藏译汉文典籍研究的重视程度,认识其在语言、文化、历史研究中的独特价值。
(六)翻译技巧与风格的研究
研究敦煌译文的翻译技巧和风格,为汉藏翻译史增添浓墨重彩的一笔。敦煌译文虽然译于九世纪初,但其翻译的部分文献原文并非当时的汉语,而是年代更早的古汉语。对于当时的译者而言,除了跨语言、跨地域、跨文化之外,还必须面对跨越时代的挑战。因此,敦煌译文所采用的翻译技巧和风格具有极为特殊的研究价值。
(七)学术价值与社会影响的实证研究
现有研究对敦煌藏译本汉文典籍学术价值和社会影响的评估,多停留于描述性层面,缺乏对这些文献在当代学术和文化交流中的实际应用与影响的实证研究。未来应加强对敦煌藏译本典籍在当代教育、文化传承,以及跨文化沟通中现实意义的探讨,促进研究成果的实用转化。
(八)敢于消除预设
当前对藏文本古汉文典籍的研究中,存在一些先入为主的思考模式,这些模式可能限制了我们对文献真实性的理解。其中,一些学者倾向于将藏文本视为翻译作品,并未考虑到此种文本可能是当时口传抄录的成果。这种预设可能导致现代研究者忽略了文献形成过程中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例如,王尧在《敦煌藏文写本手卷研究近况综述》一文中对为何藏文本单选《泰誓》两篇、《牧誓》一篇和《武成》一篇进行翻译,而不选择其他篇目的问题进行推测。不过,我们并不能因为敦煌发现的藏文本《尚书》仅有以上篇目,推断出吐蕃人只选择了这几篇文献进行翻译,因为其他篇目可能佚失,并非没有译成藏文。又如,石泰安在介绍藏译文献时表示:“难以确定这个藏文写卷是吐蕃人自己编写的还是敦煌某种汉文著作的藏译本”⑤。今人的确难以确定敦煌藏文本是编写的还是翻译的作品,抑或是某个抄写员将河西地区口头流传的内容记录成册。因此,未来的研究需采取更为开放和细腻的视角,主动挑战并超越现有的分类与假设,并且注重从多维度考察文本的生成背景、流传路径及文化功能。
(九)引入创新性研究方法
现有研究多采用传统的文献对比分析法,较少见到创新性的研究方法。未来的研究可以尝试引入认知语言学、社会语言学等为敦煌藏译本汉文典籍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探索其在语言接触和语音标注中的意义。此外,结合人工智能和信息化技术,对大量文献进行词汇和语法结构的分析,挖掘出潜在的语言演变规律。还可以利用机器学习算法,对文献中的语言特征做出更精确的识别与分类,从而拓展研究面。
综上所述,近七十年来敦煌藏译本汉文典籍的研究历程,不仅揭示了古代丝绸之路沿线文化交流的深度与广度,还为我们理解汉藏两大文明的互动融合提供了宝贵的实证材料。从早期的文献识别与考释,到近年来的多角度、跨学科探讨,研究者们不断拓宽视野,深化认知,先后在语言学、文献学、历史学等基础学科上取得丰硕成果,更在翻译学、文化史、语音学等多个领域内开辟了新的研究路径。
结语
未来的敦煌藏译文献研究应当继续秉持开放与创新精神,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手段,以更加精细化和系统化的方式,深入挖掘敦煌文献的内在价值。同时应加强国际学术合作,促进跨学科对话与交流,共同构建更加全面的敦煌学研究体系。以跨文化比较分析法,我们能更准确地复原历史语境下的文化交流场景,以及在更宽广的层面上探索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普遍规律。另外,对于藏译本中语言现象与翻译策略的深入探讨,也有助于重构古代语言面貌,为我们理解语言变迁与文化适应提供实例,也能为保护和传承濒危语言资源提供理论与实践支撑。
一言以蔽之,敦煌藏译本汉文典籍的研究,不仅是对历史文献的学术性解读,更是一种文化自觉的体现。这促使我们反思过去、理解当下、展望未来,并将这些文献作为桥梁促进不同文化间的相互理解和尊重,为构建全球多元文化共存的和谐世界贡献力量。因此,持续深入开展敦煌藏译本研究,是一项学术使命,也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促进世界文化多样性的时代责任。
注释:
①⑤该文在2010年由阿瑟·麦基翁(ArthurP.McKeown)译成英文并结集由荷兰博睿书店出版。参见Stein,Rolf.TibeticaAntiquaVI.MaximesconfucianistesdansdeuxmanuscritsdeTouen-houang[J].Bulletindel'Ecolefrancaised'ExtrêmeOrient1992(79)1:9-17。
②笔者未能找到该论文集,此处转引自王尧《近十年敦煌吐蕃文书研究简况述评》一文;另外参见《敦煌古藏文文献探索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416—432页。
③笔者未能找到1983年版的论文,此处转引自《敦煌古藏文文献探索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416-432页中收录的《PT.986〈尚书〉译文》条目。
④论文题目中写有“再研究”,但笔者未能找到沈琛之前的研究,参见《PT.1291号敦煌藏文写本〈春秋后语〉再研究》,《文献》,2015年第5期。
参考文献:
[1] Marcelle Lalou.Inventaire des Manuscrits tibétains de Touen-houang conservésà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M].Paris:Bibliothèque
Nationale,1950,vol 2,p.31.
[2] Michel Soymié.Lentrevue de Confucius et de Hiang To[J].Journal Asiatique,242,1954,pp.311-393.
[3] Marcelle Lalou.Inventaire des Manuscrits tibetains de Touen-houang conservésà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M].Paris:Bibliothèque
Nationale,1961,vol 3,p.3.
[4] Hugh E.Richardson.Tibetan Chis and Tshis[J].Asia Major(Volume XIV Part2),January 1969.
[5] Yoshiro Imaeda.L'identification de l'original chinois du Pelliot Tibétain 1291, traduction tibetaine du Zhanguo ce 战国 策[J].A0H, 34. 1-3, 1980,pp.53-69.
[6] Imaeda Yoshiro 今枝由郎 (1985). Chūgoku-Indo koten Shokyō-Sengokusaku-Rāmāyana 中国インド古典《書經》-《戰 国策》-《ラーマーヤナ》[M]. In: Tonkō kogo bunken 6 / 敦煌胡語文献 6: 557-573. Tokyo: Daitō 大東).
[7]Coblin.South. A Study of the Old Tibetan Shangshu Paraphrase, Part I [J].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 1991a (111),2: 303-322. Coblin.South. A Study of the Old Tibetan Shangshu Paraphrase, Part II [J].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991b(111),3: 523-539.
[8]Shaughnessy.Edward.Shang shu 尚书 (Shu ching 书经). Early Chinese Texts: A Bibliographical Guide [M]. Edited by Michael Loewe. Early China Special Monograph Series,1993, No.2. Berkeley.The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Early China and The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J].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93,pp.376-389.
[9]Emanuela Garatti. Pelliot Tibétain 986:
[10]冯蒸.敦煌藏文本《孔丘项讬相问书》考[J].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81,(2):6-22.
[11]黄布凡.《尚书》四篇古藏文译文的初步研究[J].语言研究,1981,(0):203-232.
[12]王尧,陈践.敦煌吐蕃文书第PT.1291号《战国策》藏文译文证补[J].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83,(3):32-45.
[13]王尧.敦煌藏文写本手卷研究近况综述[A]//朱东润,李俊民,罗竹风主编.中华文史论丛(第30辑)[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14][15]马明达.PT.1291号敦煌藏文文书译解订误[J].敦煌学辑刊,1984,(2):14-24.
[16]郝苏民.西蒙古民间故事《骑黑牛的少年传》与敦煌变文卷《孔子项诧相问书》及其藏文写卷[J].西北民族研究,1994,(1):171-193.
[17]聂鸿音.敦煌P.988号藏文写卷考补[J].民族研究,2005,(3):78-84.
[18]郑炳林,黄维忠编.敦煌吐蕃文献选集(文学卷)[C].谢后芳,等译.北京:民族出版社,2011:210-220.
[19]陈践.敦煌古藏文P.T.992《孔子项托相问书》释读[J].中国藏学,2011,(3):96-105.
[20]陈践.敦煌古藏文PT.986文书《尚书》四古词译释[J].民族翻译,2014,90(1):25-29.
[21]马晟楠.法藏敦煌文书PT.986《尚书·牧誓》的藏汉对勘研究[J].故宫学刊,2015,(1):68-78.
[22]萨尔吉,萨仁高娃.敦煌藏文儒家格言读物研究——以中村不折旧藏本《古太公教》为中心[J].中国藏学,2017,(1):39-59.
[23]陈践.敦煌藏文文献《古太公家教》译释(上)[J].西藏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38(2):46-51.
[24]朱丽双.敦煌藏文本《尚书》的研究现状及其文献来源问题[J].中国藏学,2018,(1):156-162.
[25]张先堂.敦煌文学与周边民族文学、域外文学关系述论[J].敦煌研究,1994,(1):54-63.
[26]朱丽双.古藏文政治文化术语chos与gtsuglag探微[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47(5):166-176.
[27]朱丽双.吐蕃崛起与儒家文化[J].民族研究,2020,(1):93-104.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古代汉文典籍的藏文翻译传播与影响研究”(批准号:23CZW064) 、中央民族大学2023年青年科研能力提升项目(批准号:02300301)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才让扎西,男,青海同德人,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敦煌古藏文文献、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
原刊于《青藏高原论坛》2023年9月第3期第十一卷总第四十三期(责编:星全成),原文版权归作者和原单位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