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藏古来自为神圣教法之区(Chos Kyi Choi Kha),绵长的雅鲁藏布江两岸经声梵乐悠扬入耳,终年香火不绝,紫烟缭绕,弥漫着浓郁的宗教气息。行不多远就会有庄严的寺庙和高耸的佛塔触人眼目。整个卫藏教区寺院棋布、佛塔林立。各个寺院中数不清的佛塔、佛经和佛像不仅装点了卫藏这个名副其实的教法之区,而且虔诚的藏民笃信就是通过身、语、意三门虔敬的三宝绐他们带来了无穷的加持和福荫。为了求得更多的福荫并得到灵魂的超度,一代代善男信女对这些佛宝顶礼膜拜,并竟相以添砖加瓦、增益经典为头等大事,将无数的财力和智慧耗费在兴建佛寺、翻译佛经上,以构筑通往极乐世界的桥梁。面对这世所罕见的奇观,虔诚的香客定然要千方百计到此圣地周游一遭,以得到灵魂的安寂,若不了此宏愿则难以进入幸福之至境;有心的学者除了叹为观止、抚掌称颂藏族人民巧夺天工的智慧和勤劳勇敢的美德外,亦肯定会对它的由来、兴衰之历史,兴味盎然的,故而历代不乏有心者引经据典.殚精竭虑地了解它、研究它,揭开其神秘的面纱,把一幅幅完整、真实的历史图画展示在人们面前。本文试作论述的《卫藏圣迹志》一书的作者既是一位笃信佛谛的西藏喇嘛,又是一位饱学五明的著名学者,因而它既是一本为善男信女显示解脱道的地理指南,朝圣的香客若得人手一册,定可在卫藏教区如愿畅游一番;又是一本卫藏寺庙志,有兴趣的学者从中可以窥见卫藏寺院分布、各教派的势力范围以及盛衰兴替的历史面貌。尽管《卫藏圣迹志》行文简略,篇幅不长,但是可以将它作为登堂入室的钥匙,去打开卫藏教区的迷宫。以下拟就《卫藏圣迹志》一书的作者、流传情况、价值及其特色略述一二,以引起国内西藏学诸同好的注意。不当之处亦望博雅方家不吝赐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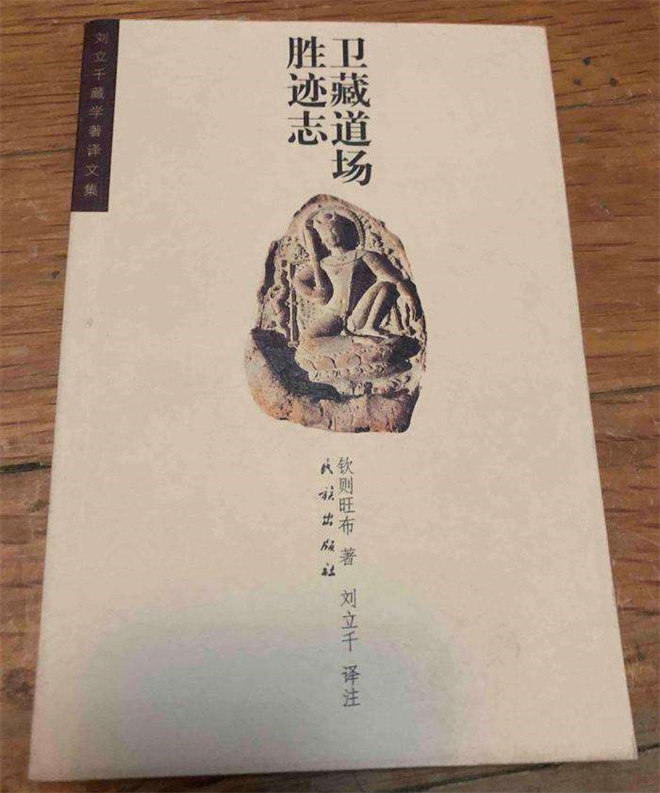 《卫藏圣迹志》一书的作者名钦则旺布公哥登贝监藏班藏卜(mkhyen-brtse dbang po kun dgav bstan pa’i rgyal mtshan dpal bzang po),简称钦则(译言智悲)。关于钦则喇嘛的生平事迹有恭桑德钦渥赛林寺(kun bzang bde chen ‘od gsal gling)的格西噶玛扎西曲盼(dge bshes karma bkra shis chos vphel)所著的《尊者上师一切智仁慈妙音钦则旺布公哥登贝监藏班藏卜传》(mkhyen brtse’i dbang po kun dga’ bstan pa’i rgyal mtshan dpal bzang po’i rnam thar)可资利用。此书写成于藏历水龙年、即公元1892年,它按藏文圣者传记(rnam thar)的一般格式分内传、外传和秘传三部分,详细地记载了他的寺院生活,他所熟读的经书、秘法的传承、灌顶受戒及其神秘的经历和留下的圣迹等情况。惜手头没有此书,因而无法详细地叙述其生平事迹,兹仅粗述其大概。钦则喇嘛于藏历第十四胜生的火龙年、即公元1820年出至于朵甘思的协茂岗(zhal mo skang)地方。协茂岗似为朵甘思六岗之一,即是指康区的邓柯一带,在今甘孜藏族自治州境内。钦则十二岁时就在塔尔孜(Thar rtse)出家为僧,后入德格的八邦寺(dpa’ spung )学法。八邦寺在当时是康区一个很有名的学术中心,寺中有几个教派共存,互相诘难辩驳、探索佛学之真谛,学术空气甚为浓郁,这对年少的钦则广采百家之长,得到较全面的教育提供了良好的机会。钦则上师主要受宁玛派剃度,宁玛派是藏传佛教后弘期各宗派中最古老的一派,亦是最崇尚知识学问的一派,与格鲁派讲究苦行修炼的风气迥然不同,每一个宁玛派寺院往往成为当地的学术文化中心。钦则身为宁玛派敎徒自然亦被此风化,自小就博览群经、通晓诗、书、声律、工巧等各种学问,因而少时就卓犖不凡,小有名声。1840年,钦则从康区来到了神往已久的卫蔵神圣教法之区,在宁玛派大寺敏珠林(Smin grol gling)中接受圣职。敏珠林在今山南扎囊县境内,是宁玛派在卫蔵地区的主要中心之一,它是居美多吉(vgyur med rdo rje)于十七世纪上半叶创建的,是当时西藏佛教的一个文化中心。在当时的西藏,觊觎高官厚禄者常到此间镀金,以求仕途通达,官运亨通;欲附弄风雅、吟诗作画成就文人之口才墨趣者,亦梦寐以求到此寺中深造,这已成为一种时尚。连藏王颇罗鼐(一)当年亦曾在敏珠林寺内学法。寺内设有天文、医学、诗画、历算等课程,现代西蔵画坛二大派中就有一派是敏珠林派。钦则在这样一所文化气息浓郁的寺院中任圣职多年,自然是近水楼台先得月,耳濡目染亦易将天资甚高的钦则喇嘛熏陶成一位经纶满腹的高僧,何况他早已饱读经书、学富五明了。后来他离开敏珠林寺,来到了后藏萨斯迦派的根本道场萨斯迦寺中学法。萨斯迦寺也是历久不衰的大寺,以寺内藏书宏富著称,当时的高僧大德一般都要到此寺中手披万经,并互相切磋砥砺学问。钦则喇嘛得此机会既读书又识人,道德文章自然更臻完善。可以说钦则喇嘛接受的是当时西藏僧人所能达到的第一流的教育,他之所以能写出《卫藏圣迹志》一书与他熟谙藏传佛教各宗各派的历史、教法传承以及分布情况是息息相关的。
《卫藏圣迹志》一书的作者名钦则旺布公哥登贝监藏班藏卜(mkhyen-brtse dbang po kun dgav bstan pa’i rgyal mtshan dpal bzang po),简称钦则(译言智悲)。关于钦则喇嘛的生平事迹有恭桑德钦渥赛林寺(kun bzang bde chen ‘od gsal gling)的格西噶玛扎西曲盼(dge bshes karma bkra shis chos vphel)所著的《尊者上师一切智仁慈妙音钦则旺布公哥登贝监藏班藏卜传》(mkhyen brtse’i dbang po kun dga’ bstan pa’i rgyal mtshan dpal bzang po’i rnam thar)可资利用。此书写成于藏历水龙年、即公元1892年,它按藏文圣者传记(rnam thar)的一般格式分内传、外传和秘传三部分,详细地记载了他的寺院生活,他所熟读的经书、秘法的传承、灌顶受戒及其神秘的经历和留下的圣迹等情况。惜手头没有此书,因而无法详细地叙述其生平事迹,兹仅粗述其大概。钦则喇嘛于藏历第十四胜生的火龙年、即公元1820年出至于朵甘思的协茂岗(zhal mo skang)地方。协茂岗似为朵甘思六岗之一,即是指康区的邓柯一带,在今甘孜藏族自治州境内。钦则十二岁时就在塔尔孜(Thar rtse)出家为僧,后入德格的八邦寺(dpa’ spung )学法。八邦寺在当时是康区一个很有名的学术中心,寺中有几个教派共存,互相诘难辩驳、探索佛学之真谛,学术空气甚为浓郁,这对年少的钦则广采百家之长,得到较全面的教育提供了良好的机会。钦则上师主要受宁玛派剃度,宁玛派是藏传佛教后弘期各宗派中最古老的一派,亦是最崇尚知识学问的一派,与格鲁派讲究苦行修炼的风气迥然不同,每一个宁玛派寺院往往成为当地的学术文化中心。钦则身为宁玛派敎徒自然亦被此风化,自小就博览群经、通晓诗、书、声律、工巧等各种学问,因而少时就卓犖不凡,小有名声。1840年,钦则从康区来到了神往已久的卫蔵神圣教法之区,在宁玛派大寺敏珠林(Smin grol gling)中接受圣职。敏珠林在今山南扎囊县境内,是宁玛派在卫蔵地区的主要中心之一,它是居美多吉(vgyur med rdo rje)于十七世纪上半叶创建的,是当时西藏佛教的一个文化中心。在当时的西藏,觊觎高官厚禄者常到此间镀金,以求仕途通达,官运亨通;欲附弄风雅、吟诗作画成就文人之口才墨趣者,亦梦寐以求到此寺中深造,这已成为一种时尚。连藏王颇罗鼐(一)当年亦曾在敏珠林寺内学法。寺内设有天文、医学、诗画、历算等课程,现代西蔵画坛二大派中就有一派是敏珠林派。钦则在这样一所文化气息浓郁的寺院中任圣职多年,自然是近水楼台先得月,耳濡目染亦易将天资甚高的钦则喇嘛熏陶成一位经纶满腹的高僧,何况他早已饱读经书、学富五明了。后来他离开敏珠林寺,来到了后藏萨斯迦派的根本道场萨斯迦寺中学法。萨斯迦寺也是历久不衰的大寺,以寺内藏书宏富著称,当时的高僧大德一般都要到此寺中手披万经,并互相切磋砥砺学问。钦则喇嘛得此机会既读书又识人,道德文章自然更臻完善。可以说钦则喇嘛接受的是当时西藏僧人所能达到的第一流的教育,他之所以能写出《卫藏圣迹志》一书与他熟谙藏传佛教各宗各派的历史、教法传承以及分布情况是息息相关的。
钦则喇嘛一生不仅读万卷书,而且还行了万里路,《卫藏圣迹志》一书正是他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结晶。钦则喇嘛死于一八九二年,纵观其一生七十余年,我们发现有很大一部分时间他是在巡行、朝圣生活中度过的。他的足迹几乎遍及前、后藏的所有名山大川。在《卫藏圣迹志》中出现的大多数地名亦同时出现在他的传记中。他不只是一位虔诚的香客,更是一位有心的学者,每到一地,他就对此地所有的圣迹一一加以详细的考察。对其沿途所经大小寺院的地望、院中所蔵三门佛宝、寺院建筑,以及各寺所独有的殊胜秘宝一一记载下来,真实地向后人展示了一幅十九世纪下半叶卫藏神圣教法之区的历史图画。
《卫藏圣迹志》全名为“卫藏若干圣地和名胜的神圣的名称述略,称为‘信心的种子’(Dad pa’i sa bon〉”,又名“以拉萨为中心的前藏寺院和雅砻、山南、后藏、藏北的热振等诸多伽蓝的寺志,称为‘希有预言明鉴’(Ngo mtshar Lung ston),习称为《卫藏圣迹志》(dbus gtsang gnas yig)。常见的有三个不同的版本,国内比较易得的是拉萨木刻版,它包括小尺寸(30x9厘米)的四十叶,每叶六行,名为“希有预言明鉴”。第二个版本是徳格木刻版,共有二十九叶,尺寸亦很小(32 x 8 厘米),每叶有六行。第三个版本是抄本,共有小尺寸(29 X10厘米)的三十四叶,每叶亦是六行,用规则易辩的草书(dbu-med)书写。这三种版本除了个别字母有所不同外,没有很大的区别。拉萨版三十二叶后面不属于本书的内容,似为另一部著作。手抄本的有些地方漫漶过甚。其准确性显然要低于前二个木刻版①。
《卫藏圣迹志》一书的创作动机明显受到了作者宗教信仰的影响。钦则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他写作《卫藏圣迹志》当然有其明确的宗教目的——自身得到灵魂的超度,并超度一切有情众生。比书开章即开宗明义,“愿三宝赐予吉祥的花朵,跳出美誉吉祥的三有生死和涅槃之外,用慈悲的影子消除有情众生的痛苦,犹如尽如人意的白伞盖”②。尽管作者套用了佛教饰词,但已一语道破了他写作此书的目的。在钦则心目中,西藏是“经大圣莲花手洁净遍习佛法的全部佛教圣地”,“四周由雪山环绕的区域,即是著名的吐蕃三区之一——卫藏神圣教法之区,它是雪域之一庄严”③。而钦则所记述的“具四解脱之圣迹,如一切有情众生得以完全成熟的地方”,他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刻意求成的卫藏寺院道场圣迹指南则是“一切具信仰者走向解脱的路标”。亦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圣迹志》才担负了有益佛教和有情众生的巨大责任,叙述了全雪域地方所存之胜地和圣迹,所有这些地方都是教法和善知识大德曾涉足的地方”④。宗教信仰固然有其落后的成分,但若自我陶醉于信仰之中,潜心于完成某一宗教事业,定会创造出非凡的力量和辉煌的成就。钦则凝几十年心血而著成的《卫藏圣迹志》自然无法使自己和别人“跳出美誉吉祥的三有生死和涅槃之外,用慈悲的影子消除有情众生的痛苦”,但他却为后人留下了研究西藏宗教历史所弥足珍贵的历史资料,其传誉后世、嘉惠后人的不朽价值是无法低估的。
《卫藏圣迹志》一书的价值首推其真实性和实用意义。《卫藏圣迹志》一书并不是钦则喇嘛躲在禅室僧房中披览古籍、日思夜想而信笔挥就的,而是在他一步一个脚印地踏勘了整个卫藏教区的绝大部分圣迹后,将其沿途的所见所闻,结合其所读典籍择要记录而成的,因而书中所提供的材料有相当的可靠性。由于此书不仅标明了各圣迹的地望,而且还提供了游历的路线,途中所花的时间,乃至朝山拜佛的门道,因而顺钦则喇嘛笔端所指,朝圣的香客即可获得一张卫藏教区圣迹游览图,既经济实用,又不错过每一处圣迹。西方早期探险者和旅行家涉足西蔵者甚多,不少人留下了洋洋几十万言的游记,例如达斯的《拉萨和卫蔵旅行记》⑤、杜齐的《去拉萨及其徼外》⑥等,但没有一本书在记载卫藏圣迹之全面和系统上足以与仅二万余言的《卫藏圣迹志》一书相媲美,无怪乎西方学者要悼呼:“我们必须牢牢记住本书只在部分意义上是一部学术著作,在很大程度上,它可以为现实的目的服务,可以为去卫藏圣迹朝圣的香客提供道路、山口、寺院和庙宇等情况”⑦。《卫藏圣迹志》一书的实用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当然,我们不能过分强调其实用价值而忽视其学术价值。《卫藏圣迹志》记载的钦则游历路线清楚地为后人展示了当时卫藏地区的山川道路面貌,是研究西藏历史地理学之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他记载的各寺院的建置沿革、所藏身、语、意三门佛宝情况等是研究各个寺院历史者不可不读的入门之作。钦则记载各寺院的情况尽管着墨不多,但大多面面俱到。我们从他对举世瞩目的布达拉宫的记载中就可略见一斑。其云:“布达拉宫为观世音菩萨之宫殿,从此宫的上、中、下三层均可以见到五世达赖喇嘛的舍利塔,此为南瞻部洲一庄严。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墓碑之门的前面,有一再生为大象的导师的牙齿等奇观,还有格桑嘉措、江白嘉措、隆道嘉措、粗称嘉措、开珠嘉措等大师的舍利金塔。在安措洛该夏若圣观音的院内,还有扎巴坚参的塑像,称为则脱玛。克什米尔班智达的陶像、塘东杰伯的塑像称为贾村玛,莲花生大师在恭塘山顶的脚印和其它许多殊胜秘宝。其下是法王松赞干布的寝室。除此之外,尚有时轮和密集的立体坛场和许多别的寺庙,一般说来,它们是不许外人入观的”⑧。他对其它寺院的记载亦大致类此。尽管自钦则上师撰成此书至今不过仅百年,但在此期间,西藏几经劫难,许多寺院建筑已变得面目全非了,寺院中所藏之佛像、佛经亦散乱狼藉,今非昔比了,因此,我们若想了解真正古色古香的卫藏风范,那么钦则上师为我们留下的这本小书亦就不可不读了。
《卫藏圣迹志》记载的是圣迹,不管是寺庙、扎仓、佛经、佛像,还是喇嘛、译师、高僧大德,它们全都不出宗教的范畴,但宗教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并不象那些善知识大德们所企求的那样超然物外,一个寺院的盛衰兴替本身就反映了该寺院所代表的那个宗派势力的消长,而各宗派势力的此起彼落则正好反映了当时卫蔵地区社会政治面貌的变化发展,因而《卫藏圣迹志》一书的价值还在于它能间接地为研究清代卫蔵政治史者提供有用的素材。
要说这仅是间接地提供史料的话,那么《卫藏圣迹志》一书用于研究西藏佛教史是最合适不过的了。书中所记载的蔵传佛教各宗派的寺庙建筑、布局结构,各宗派喇嘛所诵习之经典、崇拜的偶象,以及教法之传承系统,各种宗教仪式、各寺院中的门户分裂等等无一不是佛教史之至为重要的内容。《卫藏圣迹志》一书对于研究藏传佛教史的价值是毋庸置疑的。《卫藏圣迹志》一书的学术价值还在于其珍贵的史料价值。钦则在撰写此书时参阅了《噶当教法史》、五世达赖喇嘛著《大昭寺志》、阿旺江巴(Ngag-dbang byams-pa )著《四寺志》,让迥多吉著《语录大乘海》.公哥仁钦著《萨斯迦寺志》、多罗那它(Tāranātha)著《觉囊寺志》以及《莲花生遗教》中的桑耶寺偶象目录等著作。这些著作都是记载西藏寺院分布、教法传承、寺庙建筑以及所藏三门佛宝的上乘之作,它们分别记载了属于宁玛派、噶当派、萨斯迦派、觉囊派等藏传佛教各宗派的内部情况,是极为珍贵的第一手资料。钦则在反复研究这些资料的基础上,结合其实地考察的成果,一一加以验证,择其要者,融汇贯通于他自己的作品中。钦则当时所参考的资料当然还远不止上面所提到的那些,而他当时所博览的文献资料,陵夷至于今日大多数已散佚不可复得,即使幸存下来的亦已十分难见,钦则扶众书之精英融于《卫藏圣迹志》一炉,尽管数量不多,但其资料价值亦是不可小觑的。
《卫藏圣迹志》一书在写作技巧上亦很有特色,最突出的特点即是广收博引,而又提纲挈领、言简意赅,使读者读来一目了然,无冗长繁琐之弊。往往是寥寥数语就把一座寺院的基本情况说个一清二楚,这在每每铺阵过甚、藻饰满篇的藏文佛学著作中是难能可贵的。我们可举他对热振寺(Rwa sgreng)的描写为例,钦则在书中载道:“(卫藏)之第一区伍茹(dbu ru)北部有藏北的热振阿兰若,此为仲敦巴杰微迥乃(Vbrom-ston-pa rgyal-ba vbyung-gnas )的根本道场。有如天国果树的极乐园中,有多座佛殿。佛像之主要者为以持金刚之大智慧种子中繁衍出尊者妙金刚。今生和来世凡有所请必能成就,仿佛如意的摩尼珠宝。此外,在此还能朝拜赛林巴(gser-gling-pa)、阿底峡、仲敦巴等上师的舍利金塔。如经允许,在大住持之私邸,可拜见偏头的阿底峡大师的肖像和别的众多秘象。在寺院附近还有许多别的东西可供瞻仰,诸如仲敦巴(出生时种的)树,四季不绝的甘露之泉等等。此寺后面的狮子岩下,有一祢作“羊衮"(Yang-dgon)的下院,其中有宗喀巴大师写作《菩提道次第》(Lam rim)时的法座等许多奇观。靠近此寺的帕朋塘是空行母桑哇意希的宫帐。由此向左环行,念诵黑如迦密咒时,人们将在乌仗那地方获得再生,云云”⑨。热振寺是噶当派的根本道场,它是噶当派的创始人仲敦巴为了纪念其师尊、孟加拉高僧阿底峡大师而于一〇五五年在藏北建造的,因寺中有阿底峡的舍利金塔而名闻遐迩。这么重要的一座寺院,在钦则笔下仅用了三百余字就明白地交代过去了。
《卫藏圣迹志》一书最大的缺陷是它较多地选择了宁玛派和萨斯迦派的圣迹加以着力描绘,而一些甚为重要的格鲁派寺院却不无遗憾地被疏忽了,这无疑与钦则身为宁玛派教徒和曾在萨斯迦寺学法等背景有密切的关系。由于格鲁派的寺院建筑较之宁玛派、萨斯迦派而言要来得更加现代化一些,因而稍稍可以减轻这种疏忽给后人带来的遗憾。另外此书记述的范围过于狭窄,许多人物、经典以及圣迹在此书中只是一提了之,没有作更多的说明,使全书给人以不充实感。尽管如此,《卫藏圣迹志》仍不失为研究西藏学者所必读的一本好书。
《卫藏圣迹志》一书早已引起国外藏学家的重视.意大利藏学家杜齐(G. Tucci)的私人图书馆中就藏有此书的德格木刻版和手抄本二个版本,他在其著作《印度和西藏》、《去拉萨及其徼外》中亦曾引用过此书⑩。另外,毕达克的《十八世纪早期的汉藏关系》⑪,霍夫曼的《本教之历史资料》⑫等书中亦都引用过《卫藏圣迹志》的材料。英国藏学家黎吉生(H. Richardson)手中收藏有《卫蔵圣迹志》的拉萨木刻版。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意大利已故女藏学家费拉丽以此书译注作为她的学位论文,可惜赍志病故,而毕达克继其遗志、奋力完成,将《卫藏圣迹志》译注本以英文出版。并对费拉丽的手稿作了仔细的校勘。在完成这项工作时还得到杜齐、黎吉生、彼得、奥夫斯奈德等人的帮助。因此,他们出版的译注本《卫藏圣迹志》一书可以说是国际藏学界通力合作的产物,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自一九五八年作为罗马东方丛书之一问世以来,成了国际蔵学家所必备的工具书,久负盛名。书中的七百余条注,几乎对书中出现的每个人物、每个地名、寺院和专有名词都作了注释。对书中出现的每个人物的历史面貌作了简短的叙述,并提供了一个研究这些人物、寺庙、地名等的参考目录,对每个寺院的历史缘起、沿革和现状亦都作了说明,它用现代藏学研究所能掌握的大量知识对成书于十九世纪下半叶的《卫蔵圣迹志》作了大量的补充。经过他们的劳动,《卫藏圣迹志》一书已远远超出了“寺志”的范畴,成了一本内容十分丰富的有关西蔵历史、宗教研究的小百科全书。
由于受语言文字的障碍,国内藏学界对《卫藏圣迹志》一书的内容知之者不多,亦很少有人利用此书中的宝贵资料,这与近年来国内藏学研究蓬勃兴盛的趋势是不相适应的。因此,若能引起国内诸同好的兴趣,尽早从《卫藏圣迹志》一类的藏文著作中汲取珍贵的素材,以提高国内藏学研究的水平,这就是笔者不揣浅陋、草此短文之用意所在。
*本文二校时,刘立千先生译注的《卫藏圣迹志》汉译本己经问世,这是值得庆贺的。
注 释:
①见费拉丽(A. Ferrari)等译注,Mkhyea Brtse’s guide to the holy places of central Tibet ,Rome,导言。
②藏文拉萨版《卫藏圣迹志》,页一一二。
③同上书,页二。
④同上书,页三十——三十二。
⑤SCh. Das,Journey to Lhasa and Central Tibet,London 1904.
⑥G. Tucci, To Lhasa and beyond,Rome,1950.
⑦语见费拉丽上揭书,导言。
⑧《卫藏胜迹志》页四一五。
⑨同上书页二一三。
⑩G. Tucci,Indo—Tibetica,第四卷,第一部,页45(Rome,1932—1934)。To Lhasa and beyond,pp123-124.
⑪见L. Petech,China and Tibet in the early 18th century,Leiden 1950,pp 51,85.
⑫见H. Hoffmann,Quellen zur Geschichte der Bon—Religion, Mainz 1950,P147.
原载《南京大学学报》一九八六年研究生专刊〈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