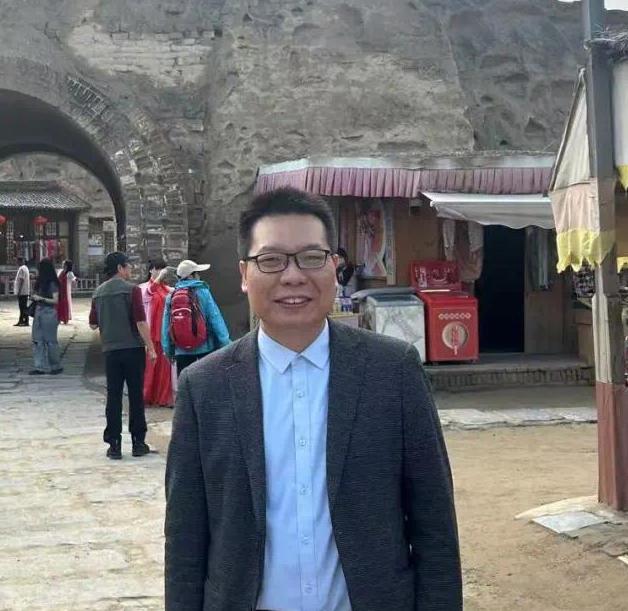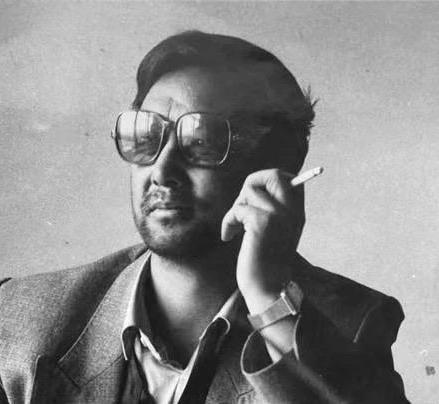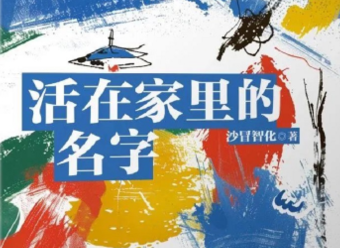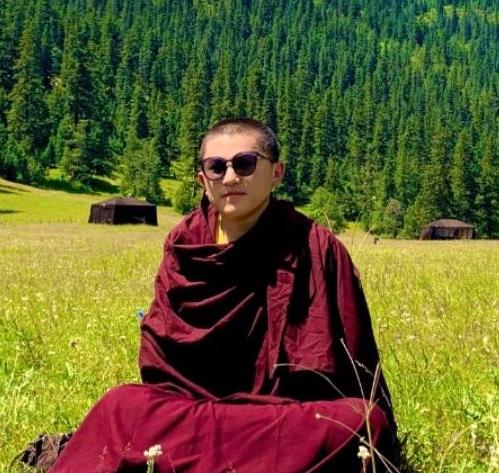青年作家赤·桑华作为新世纪藏族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自2013年《怀念一只叫扎西的老狗》《1986年的雨衣》等‘卓香卡系列’之后,接续着对‘卓香卡’这一故乡老村的记事般叙说。在他《混沌岁月》《果美·才让扎西短篇小说集》以及《卓香卡》等短篇小说集所收录的三十余部作品,大多篇目是以“卓香卡”这一空间主体为核心,通过儿童视角和成长叙事,讲述着卓香卡的“小人物”和“小事件”。新作《羊把刀藏在春天》,同样隶属于“卓香卡系列”作品。“卓香卡系列”最明显特征便是儿童视角的运用和对童年生活的追忆。赤·桑华小说将儿童视角的“不可靠叙述”化为文化隐喻载体,赋予文本在表层荒诞与深层推演间形成对峙博弈的同时,将文本题旨指向青藏高原底层民众的生存状态和地方性文化经验。这为当代藏族文学中叙事策略的多元化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和借鉴,有着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
一、《羊把刀藏在春天》:权力结构的隐形书写
从叙事学视野看来,赤·桑华短篇小说新作《羊把刀藏在春天》,通过局限型视角的不可靠叙述方式来传达故事主旨。小说通过儿童叙述者的转述,呈现了外来者“张师傅”在卓香卡村落的身份转变,即从屠夫到护林员,再到疯癫、衰老,最终离去的过程。而孩子作为叙述者,小说在故事的讲述方式上,践行着事件表层的行动和其结果展示,并不对事件的前因后果作透视性的解释和评价。而不可靠性恰恰产生于儿童视角的表层展示与情节设计的内在逻辑之间的价值张力。正如陈志华讲到:“不可靠叙述”是一个看似简单实际上颇为复杂的概念。20世纪以来的中外文学作品中,以天真叙述、傻子叙述为代表的叙事文学作品数不胜数,不可靠叙述已成为一种非常重要的文学现象。”同样,韦恩·布斯在《小说修辞学》中首次提出“不可靠叙述”这一概念时,对其作了界定:“当叙述者的讲述或行动与作品的思想规范(也即隐含作者的思想规范)相一致时,我将这类叙述者称为可靠的叙述者,反之则称为不可靠的叙述者。”这里布斯将衡量不可靠叙述的标准指向了作品的规范,即作品中事件、人物、文体、语气、技巧等各种成分体现出来的作品的伦理、信念、情感、艺术等各方面的标准。由此可知,所谓“不可靠叙述”,并非指一般意义上的不可信抑或故事的虚构性。
众所周知,虚构是文学叙事的基本属性之一,而不可靠叙述主要是对20世纪以来大量偏离规约对局部文学现象的理论概括。“不可靠”并非指向文本内容的真实性与否,而是特指由文本叙述话语所体现的事实陈述、主体感知、价值判断等方面的不一致,从而引发读者对于叙述者,甚至整个文本叙述可靠性的怀疑,进而在阅读中重组事件、重逢判断。”也就是,虚构性是文学文本的本质特性,而不可靠叙述则是小说叙述的一种表现形式与叙述策略。那么,不可靠叙述作为叙事策略,在《羊把刀藏在春天》作者是如何通过孩子的叙述来暗示着更深层次的社会批判或人性探讨,而不仅仅是表面上的故事发展。
首先,在《羊把刀藏在春天》,儿童叙述者的认知局限性,将故事粉粹于局部展示,价值评估趋向片面单一。在小说开头,作为儿童的‘我’对张师傅的介绍和评价是通过母亲或伙伴们的转述来完成的。如:“久迈卡果问我:“你怕张师傅吗?”//……“怕啊,我阿妈说张师傅是专门割小孩耳朵和剁手指的人。不信的话,我们可以去看看,他房间里有一麻袋小孩的耳朵,还有一麻袋小孩的手指。”……我本来一听到张师傅的名字就害怕,他这么一说,我更害怕了。”“我”对张师傅的恐惧仅仅源于母亲的恐吓,这种夸张的威胁被孩子不加批判地接受,形成对张师傅的妖魔化想象。同时,儿童叙述者将张师傅的杀猪场景与《格萨尔王传》中的“屠夫辛巴”类比,将主人公的血腥行为与先前印象结合,在文本话语表层,树立了恐怖怪诞的单一形象。
其次,情节设计消解着儿童叙述的童真,在文本内外形成价值冲突。对《羊把刀藏在春天》进行整体细读,不难发现,儿童叙述者对故事主人公张师傅的评价是有失偏颇的。尤其在加错老师发生冲突的桥段设计,一定程度上,瓦解着叙述者“我”对张师傅的先前定论。正如小说中讲道:“有一天放学回家的路上,不知道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加措老师好像是为了证明谁更厉害。……加措老师像铁耙子一样的手揪住张师傅的头发,左右甩动。……加措老师指着远处说:“狗屎,滚蛋!”张师傅捡起掉在地上的帽子,一瘸一拐地跑了。”在这里加措老师对张师傅的暴力,虽然在儿童叙述者眼中呈现是“谁更厉害”的比较,停滞于人物外在行动展示。但是这样的情节设计,在深层次的意义导向上,对先前的恐怖形象起到了消解作用,进而使叙述者的话语与文本潜在的价值流动形成对峙冲突,引起读者对儿童视角的事件展示产生怀疑和意义重组。
再者,进行整体细读,可以发现《羊把刀藏在春天》是将边缘‘小人物’的生存困境置于叙事主轴,用潜文本的方式进行着小说主旨表达。结合小说内容可知,主人公张师傅从“流浪汉”到“护林员”的身份转变,暗含着卓香卡村民对边缘人物即流浪汉张师傅的工具化利用和集体驱逐的生存困境。而当故事发展到临近结尾,即阿奶卓果与张师傅的关系被戏剧式地公之于众时,作为弱势群体的阿奶卓果和作为边缘人物的张师傅,在集体舆论和主流价值打压下,被驱逐和走向了毁灭。进而,再回过头来看小说中‘加措老师对张师傅的暴力’、‘村民对张师傅的利用与驱逐’等诸情节,便容易折射出封闭社群对外来者的排挤、打压,以及知识权威对底层的压迫和道德困境下的女性失语等系列社会问题,进而使潜藏于故事背后的不对等权力结构浮现于文本,完成叙事意义的表达。文本表层的儿童视角的局限性,如崇拜加措老师的魁梧身材、张师傅给羊羔扎辫子时的疯言疯语、‘像猪一样哀嚎’的性丑闻等在儿童视角下的简化展示,在某种意义上,恰恰暴露了权力结构的自然化与不可见性。再加,作为小说结尾和张师傅的归宿——雪地上的脚印,成为了对边缘者命运的无声控诉——他们的故事,永远在儿童视角的缝隙中若隐若现,等待读者穿透表象,追问被遮蔽的真相。
故而,儿童视角在《羊把刀藏在春天》中如同一面棱镜,既折射出藏地村落的生存图景,也映照出人性与社会结构的裂痕。孩子的天真叙述既是对真相的遮蔽,也是对真相的逼近。
二、《阿妈卡姆家的母牛》:众生平等的理念重构
纵观赤·桑华的小说创作谱系,儿童视角与成长母题始终作为标志性叙事策略贯穿其文本实践。除上述内容论及的最新作品《羊把刀藏在春天》之外,其早期代表作《阿妈卡姆家的母牛》同样建构了极具张力的不可靠叙述范式。值得注意的是,两部作品虽相同运用儿童视角的叙事装置,却在编织文本的细节构造上呈现出各自特性。这种叙事策略的分野,既彰显作家对成长主题的多维诠释,亦暗含其创作观念从经验复现向哲学思辨的演进轨迹。进而,笔者认为,在分析《阿妈卡姆家的母牛》之前,务必将叙事视角和叙事声音两者,作简短的概念辨析尤为关键。
热拉尔·热奈特早在《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中,谈论叙事作品的视角时,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开创性的探讨,他首次将“谁看?”和“谁说?”区分开来,把叙事文本中的“观察”与“声音”隔开,提出“观察者是在看的人,而叙述者是在说的人”,并且从人物和叙事者两者间对故事内容的掌握程度来分类叙述类型,即内外聚焦。这种分类明显是侧重于“声音”层面。同样,“自西方现代小说理论诞生以来,从什么角度观察故事一直是学界关注的一个焦点。”叙事学发展至今,对于小说叙事视角这一范畴所进行的概念界定和分类标准,学者们各言其书,有众多学说,在此无需赘述。但无论从何种角度对“叙事视角”一词进行概念界定和分门别类,都无法撇开的是何以理解事件感知者和讲述者之别的问题。对此申丹也论述道:“视角是指叙述时观察故事的角度,所谓人物视角就是叙述者借用人物的眼睛和意识来感知事件。”由此可以看到,视角和叙述作为一个常用搭配,以示对于感知者和叙述者的明确区分。诚然,在具体的文学实践中,感知者和叙述者既可重合又可分离。就拿‘儿童视角’来说,它既不能确定事件的感知者是儿童,也无法肯定故事的讲述者就是儿童形象的叙述者。在具体文本中若要搞清楚‘儿童视角’这一叙事策略到底是属于哪一类型,或者分析其修辞效果和叙事意义时,务必结合具体的文本语境和叙事进程来加以分析和论述。例如,赤·桑华短篇小说《阿妈卡姆家的母牛》中:
“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没搞明白其中的秘密,后来阿妈告诉我:因为阿妈卡姆认为她的母牛能值五百块钱,所以起了“五百”这名字。我问阿妈:“阿妈卡姆家的牛真值五百块吗?”阿妈笑笑说:“一头牛能值五百?哪有这么好的事。……阿妈的回答,让我隐隐约约地明白了,阿妈卡姆为什么要对母牛叫“五百”,这名字的确有点奇怪。”
在这段,叙述者是以当下的写作时间为参照,回忆的方式呈现了事件过程,并且人物对话的直接言语运用,从叙事话语即修辞层面也是对事件的再现完成了一定程度上的现实还原。因此,在直接言语的语境内,叙述者和人物无疑都是存在于过去事件的空间内,也就是感知事件的视角与叙述声音是相分离的。这时的叙述者“我”是过去时空中的“我”,而文本的“声音”是文本话语生产的时间点为基础的。然而,对比直接言语引用的前后所出现的叙述话语之主体,便会发现同样担任叙述功能的叙事主体却发生了置换。“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没搞明白其中的秘密,后来阿妈告诉我”这一句中的叙述者“我”显然是以作者的代言人身份显现于文本,是文本中建立的作者形象,是区别于文本叙述者‘我’的儿童形象。“阿妈的回答,让我隐隐约约地明白了,阿妈卡姆为什么要对母牛叫“五百”,这名字的确有点奇怪。”而这一句,虽然在叙述者‘我’的称谓上同样没有变,但仔细分析,不难发现其‘我’所指向的主体已不同于引用直接言语之前的作者的第二自我,而是延续和继承了直接引用所营造的叙事氛围,是以人物当年的感知和视角进行叙述。所以,此时感知、观察事件的视角与叙述事件的声音是重合的。故而,第一种为叙述者“我”目前追忆往事的眼光,第二种为被追忆的“我”过去正在经历事件时的眼光。倘若叙述者放弃前者而转用后者,那么就有必要区分“声音”与“眼光”,因为两者来自两个不同时期的‘我’。”然而当隐含作者(文本中建构出来的作者形象,也可以理解为文本的价值规约)以叙述干预的方式对故事本身进行评头论足时,故事中显现的人物立场与本文所倡导的价值判断之间会产生是否一致的张力和矛盾。这一现象在赤·桑华小说的具体文本中是如何运作的?不妨看看《阿妈卡姆家的母牛》一文的如下分析。
首先,从故事事实与叙述者的价值判断层面来讲,在《阿妈卡姆家的母牛》中,小说开端叙述者以宣布式的语气讲道“村里有些人,因为阿妈卡姆给自家的母牛起了“五百”的名字,就把她当成疯子,我觉得他们才是真正的疯子。可话又说回来,阿妈卡姆也的确是个很搞笑的人,这倒不可否认。”其后通过表述阿妈卡姆如何将她家的奶牛当作旁人一般,不仅跟它聊天谈心,而且每天寸步不离地围着它、守着它的举动,某种程度上论证了阿妈卡姆的“疯癫”。此时叙述者的一切表述貌似符合逻辑、忠于事实。然而随着故事的发展,叙述者通过其他人物的阐述和故事情节的展开,认识到阿妈卡姆的不容易,即丈夫很早离世、儿子密咒师意外身亡、儿媳妇玉措重病难医等,最后只剩下身体残缺的孙女嘎玛措与她相依为命。进而得知,小说文本却致力于隐晦地、深层次地向读者传达着阿妈卡姆并不是在儿童视角中所呈现的那样不合于常理,她行为上的怪诞并不是因为疯癫或精神失常,而是由于现实的无奈和孤独使然。由此可知,小说文本中叙述者“我”以儿童视角对人物做的观察和判断,在一定程度上,是与故事原貌相违背的。文本中儿童视角所表述的一切,是不知其所以然的一种表面现象的描绘,哪怕在结合文本语境的需要对其进行必要的解释和评价等叙述干预也是不可信和不可靠的。因此,在《阿妈卡姆家的母牛》中儿童视角的同故事叙述者虽然是属于故事内的人物,但始终站在事件中心的边缘,以旁观者和目击者的身份讲述主人公阿妈卡姆的行为。再加儿童视角本身带有的限制性即认知层面的局限性,在报道事件时产生过于重视表面进展和人物的外在行动与言语,使之未能让读者看到事件的全貌。在这种叙述过程中,叙述者由于自身的主观性,在事件本身和表述之间使其产生变形,进而凸显出作为中介者的身份。此时,读者不得不对叙述者的讲述保持警惕和防备心理,进而将注意力倾注于故事的整体结构与文本规约。
其次,从小说整体结构和价值立场看,在小说后半段,叙述者在叙说阿妈卡姆的行动、思绪、言语时,便超然于限制型的旁观视角,也就是放弃了先前的儿童视角,以全知型叙述视角俯瞰世间万物的姿态,把故事后半段讲述出来。在小说结尾,将存在于不同空间的阿妈卡姆和她的母牛之间,如同拥有心灵感应一般,察觉到了彼此的不祥征兆,且在相同时间点彻底倒下,变成了亡灵。叙述者把事件发生的外在情景与人物的内心活动,透视性地将其如实如真地叙述出来。此时,作为隐形于故事之外的叙述者所作的讲述显然是可靠且可信的。那么,若追问作者何以在结尾部分把叙述者的视野扩展至全知?笔者认为,需要结合文本语境,挖掘文本表面之下的深层涵义,才能真正地理解浅层叙事布局之下的小说内涵。也就是,梳理小说文本中推导和建构出来的作者形象即隐含作者或文本所提倡的价值原则之后,对叙述者和人物的言语进行对比分析,便容易发现叙事交流中各个叙事主体间的张力。
在叙事学研究方法中,在把握贯穿整个叙事文本的价值归依或创作原则等问题时,总会涉及“隐含作者”这一叙事范畴。布斯在1961年出版的《小说修辞学》一书中初次提出此概念时,虽然仅仅是区别日常生活中真实写作者与“进行创作状态时刻”的作者两者,意在强化写作意图和文本规约的可寻性。便通过强调“隐含作者”的文本性,来论述作品中呈现的价值理念其实与真实作者的立场、态度及价值判断等可以相偏离,甚至违背的现象。然而,叙事理论不断发展,到美国学者西蒙·查特曼在《故事与话语》中,将隐含作者看成读者从所有文本成分中收集和推导出来的建构物,而不是将其视为一个文本中隐形的作者形象。进一步把“隐含作者”这一概念以作者层面的“编码”和读者层面的“解码”过程,糅合到文本本身呈现的文本规约和原则上,视为叙事文本的主要宗旨和表述指向。而全知全能的作者型叙述模式是最接近其写作状态时的作者意图,抑或写作者在组织言语或情节时因其所受的限制最少,可以任意干扰性地评价或进行价值判断,来完成叙事目标及理念的叙述手段。那么一部叙事作品的“隐含作者”即文本在价值上的规约或意义指向,其实是贯穿全文的,且在作者型叙述声音等层面,能够找到清晰明确的依据。
在《阿妈卡姆家的母牛》中,作为叙事交流主体的儿童视角叙述者、主人公阿妈卡姆、文本价值归依即隐含作者三者间所进行的“交流”,是较为明显的。布斯讲到:“我们和沉默的作者进行交流,好比从后面观察处于前面的叙述者,观察其幽默的、或不光彩的、或滑稽可笑的、或不正当的冲突等行为举止,尽管他们可能具有某种心灵或感情上的补偿性。作者可以做出种种暗示,但是不能说话。读者可以表示同情或哀叹,但是决不会将叙述者视为自己所信赖的向导。”那么,作为作品中的意义导向和价值归依,其隐含作者在该小说中,也以一种若隐若现的方式,隐藏于文本中。仔细阅读这本小说会发现,文本表面上,是利用儿童视角的直接纯粹的特性,把人物的行为和言语直接阐述,并对其进行表象化的评价。也就是,叙述者“我”对阿妈卡姆的所作所为即与她家的母牛和大树进行聊天、陪伴、如同人类一般赋予照顾和交流等,保持无法理解,甚至归类到精神失常。然而,文本中屡次出现万物相通、众生平等之主题。例如:“阿妈卡姆停顿了片刻,转过身,又开始对牛讲起故事来了:“五百,我给你讲个故事吧!从前一个地方有个屠夫,有一天,屠夫宰羊时刀子明明放在身边,可怎么找也找不见,最后发现刀被羊藏在腹下,他顿时醒悟,自己这一生宰了那么多羊,懊悔万分,他搁下羊去跳悬崖,没想到他立地成佛了。这事被一个老喇嘛听到后,心想他一个屠夫都能成佛,那我就更不用说了,他也去跳悬崖,结果被摔死了……”她讲了一个很长的故事,我听着感到又惊喜又伤心。”
这里作者运用“故事中的故事”即元故事的形式,把相同主题的故事引入小说,讲明领悟万物皆有灵,对动物产生怜悯之心,才能就地成佛的根源之信念。这一价值理念无疑也是这本小说进行所有叙事行为的意义指向。当然,在赤·桑华的小说文本中,此类故事母题的小说,并非仅限这一部。如短篇《当羊皮鼓响起时》,也是将人与动物之间具有的心灵感应,这一世界观念贯穿于小说始终,把万物有灵之信念放到小说文本的意义指向。这篇小说的整体结构是以吉先等几个人物,为追寻自家羊群被偷窃的痕迹为情节主线展开,而当他们找到羊群时,它们早已跳入悬崖、自行了断生命。此时,小说的主旨便借助神秘人物的出现,进一步呈现于文本表面。正如文中所言:“修行师双手举到胸前,顿了顿说:‘我从没有见过羊自杀的,也没听说过。不过我今天早上就看到了。我念超度经念到现在,愿这些畜生能获得解脱。’说着便两眼又闭上了。……这些羊儿们肯定知道了,盗贼们会把它们卖给屠宰场的。’说完,手中的朵玛扔向下面的山谷里,羊皮鼓又一次敲响了,嘴里不停地念着什么。”这里把羊群写成具有自残意识和对动物进行超度的故事桥段,对于藏族同胞们的现实日常来说,便是常态和符合实际的。而赤·桑华把这种富有地方色彩和民族韵味的事件,引入小说人物和情节设计中,通过结构安排和叙事策略的巧妙使用,从悬念、反讽、意象等多种文本意义层面,对其赋予区别于说教和功利层面的文学审美的意蕴。
值得提出的是,相较于《当羊皮鼓响起时》,无论从叙事策略和审美意蕴,以及文本意义的阐释空间来看《阿妈卡姆家的母牛》略胜一筹。它不仅把万物有灵、众生平等、六界轮回等佛教理念和价值观贯入小说文本,且把这种理念隐藏于文本深层,只有对小说文本进行整体细读和结构重组,才能揭示其不可靠叙述与隐含作者之间价值立场的矛盾和张力。
正如《不可靠叙述研究》中:“隐含作者对文本结构的整体安排往往造成对叙述者声音的否定,并由此发出自己的声音、叙述者可靠性的消解使人物的声音在话语层面获得了相对独立性,甚至构成对叙述者的否定;隐含作者通过让叙述者对众人声音的不可靠评价,曲折地传达出对叙述者的否定。”所言,在《阿妈卡姆家的母牛》一文,拥有儿童视角的叙述者的评价对人物阿妈卡姆的行动进行着否定,而小说文本的整体结构和深层隐含的众生平等之价值理念,却时时消解着叙述者叙事行为,从而完成了在叙事交流活动中各个叙事主体间的独立又相关联的叙事网络。进而使小说文本拥有了超越于故事表面进程的阐释广度,并且加强和深化了儿童视角的运用在叙事策略领域多方位探索。这也是这篇小说在叙事策略方面,为何运用不可靠叙述手段之原因,即将小说分为文本表面和文本深层次两种对峙的意识冲突,加深和强化了小说深度。
结 语
赤·桑华在《羊把刀藏在春天》《阿妈卡姆家的母牛》等“卓香卡系列”作品中,共同建构了极具张力的不可靠叙述范式。
儿童视角的不可靠叙述策略既保留叙事的质朴真实,又通过潜文本的张力,迫使读者穿透表象,追问被遮蔽的内在社会问题和权力结构以及哲学思考。值得注意的是,两部作品虽相同运用儿童视角的叙事装置,却在编织文本的细节构造上呈现出独特蕴意。前者通过碎片化记忆拼图与感官特写,完成对微观日常的精准捕捉;而后者则以环形叙事嵌套民俗符号,构筑起充满寓言张力的隐喻架构。这种叙事策略的分野,既彰显作家对成长主题的多维诠释,亦暗含其创作观念从经验复现向哲学思辨的演进轨迹。同时,这些叙事手法不仅拓展了当代藏族文学景观中儿童视角的叙事潜能,更将青藏高原地方性文化经验升华为普世性文学表达,值得关注和重视。

旦正措,青海同仁人,2017-2024年间在中央民族大学攻读本硕学位,2024级藏族文学方向在读博士生。二十余篇短篇小说、译作、学术论文散见于《民族文学》《章恰尔》《西藏文艺》等刊物。先后荣获“第三届全国藏语短篇小说大奖赛”二等奖、“理塘仓央嘉措诗歌节大赛”短篇小说组二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