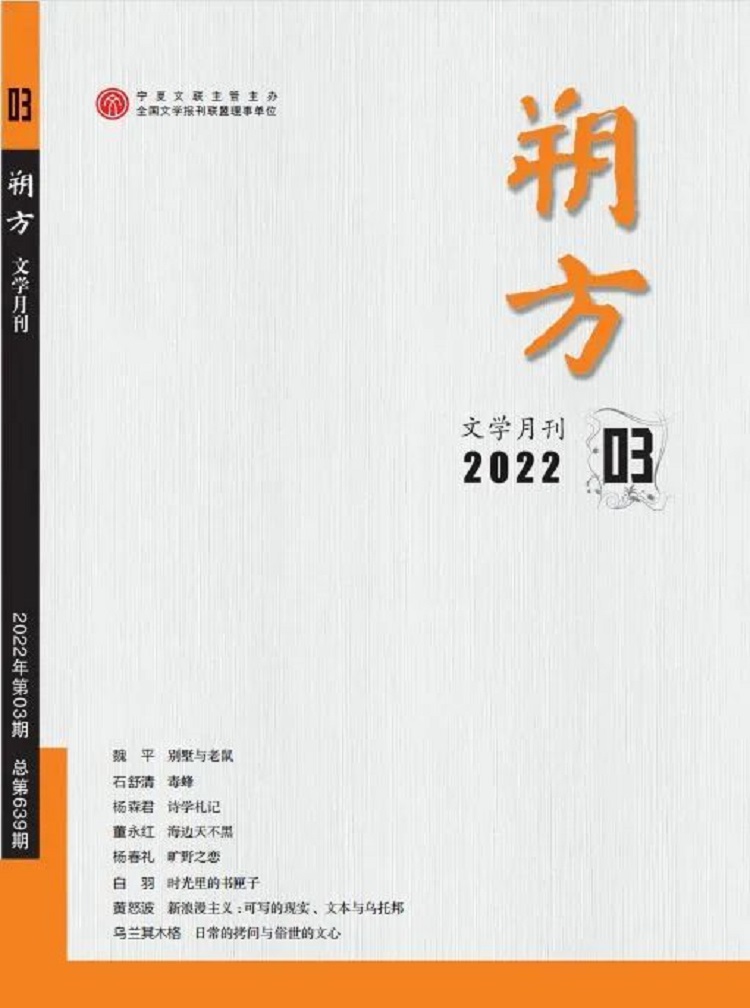
雪来了。像是虚空中惊落的梨花,带着一丝羞赧,静悄悄向水墨画一般沉郁的四野撒落,轻轻触碰,就化了。初雪是堆积不起厚度的,轻轻浅浅覆盖在山峦沟壑,墙头屋檐,染不白黑狗的尾巴,留不下野鸡纤巧的爪印,它只是带着一些记忆来了,让我们明晰,让我们在生命的深潭中观照安宁洁净的倒影。
那时我们围坐在热烘烘的土炕上,脚丫塞进奶奶暖暖的棉被窝里,雪一路静悄悄地落着,我们每个人手中都捧着一本书,就连不识字的老奶奶也捧着一本,身体圆滚滚的大花猫慵懒地倦卧在一旁“呼噜噜,呼噜噜”地打着鼾,看似沉溺在梦里,实际又很警惕,在翻动书页的轻微声响里,猫总会眯起一线慵倦的睡眼,充满警觉地一瞅,继续睡去,像个时刻待命的警长。“花猫警长”不睡觉的时候会一边讨巧地喵喵叫着,一边对我们的书虎视眈眈,常常趁人不备刺啦一声就撕破一页,又常常因此而狼狈不堪。“这死猫娃!”奶奶吓唬它怒喝一声,顺势将猫一把拎起,花猫警长惊得喵呜乱叫,使劲儿扑腾,奶奶又故意把手一松,猫儿便闪电般窜出虚掩的门缝,清寒丝丝缕缕溜进屋里,奶奶打了一个响亮的喷嚏。
光影轻扫着窗棂上的灰尘慢慢移动,薄薄一层金色拂过奶奶的黑盖头,拂过她褪色的肩袖,拂过她老树枝一样的双手,骨节突出的粗笨的手指那时变得十分灵活,她细细整理撕破的书页,指尖蘸点唾沫将卷起的边边角角一一捋平,像一位眉眼含情的母亲抚弄着她新生的婴儿,专注细腻,她一边抹着糨糊粘书页,一边懊恼地咕哝着“一定是猫爪子痒,碰到书就痒”,她喃喃自语。
粘好的书放到书匣子上晾着。笨头笨脑的长方形匣子,模样普通得有些寒碜,却是家里质地最好的一个老物件,它是柏木的。早先家在牧区时用来装糌粑,是只地地道道的糌粑匣子。生活在牧区的人家都有这样的一个糌粑匣子,两尺见方内里深阔,做工简陋,匣面上也不涂漆描画,保留着天然的木纹和点点疤痕,就讲究个结实耐用。深阔的匣子里面竖着一块挡板,将内容一分为二,小头装着酥油,大头放着炒面,匣子从来都装得满满的,像个小小的粮仓,放在柜子高处,沉甸甸地稳着全家人的心。
“柏木椽子,宁折不弯。”不似松木既不耐晒又不耐潮,容易开裂变形,柏木始终如一的保持着坚硬的质地,一件柏木家什几乎能用一辈子。因为木质的缘故,匣子保持着所有的年轮纹理也保持着树木身体里的点点疤痕,最显眼的一处疤痕像一只大大的眼睛,就在匣子的侧面,流云般的纹理间褐色疤痕顺时针洇开着,丝丝缕缕暗含惆怅。可能树木也有那刻骨铭心的时刻,或悲伤,或疼痛,又或暗自欣喜,所以身体里就留下了那样的疤吧?独自在家的阴雨天,因为无聊,会在那暧昧不明的光线里盯着那只眼睛看上许久,看久了,觉得它也在一直在瞅着你,欲诉还休,竟也有几分活物的神情。
平日里拌糌粑吃“辣子尕勺”最是热闹,一家人围在炕桌边,糌粑匣子就隆重上场了,老人们小心翼翼打开匣盖,慎重地拿出其中一块黄黄的酥油托在手掌上,像托着一小块金条。不过那金条是酥软的,小刀轻轻一切就断了,桌上有几只碗就切几块,金黄的小块酥油丢进青瓷龙碗里,浇上开水瞬间就化了。散发着醇厚焦香的炒面放进去,大人们就捧起青瓷龙碗,伸出手指开始拌糌粑,酥油渗进沙色的炒面里,熟稔的手指顺时针沿着碗沿拌开了。才一小会儿,一碗油润润香喷喷的糌粑就拌好了。配糌粑的洋芋臊子端上桌时,糌粑匣子会被奶奶细心收拾一番,填满陷下去的炒面,放进新酥油,边边角角上洒下的炒面,她都会一一用手指蘸着舔进嘴里。她一遍又一遍拭擦着那匣子,好像怀里捧着一个百宝箱似的。
那时,谁都不曾想到那匣子有一天会黯然失色。因为我们上学的缘故,我入学那年全家从偏僻的牧区搬到了镇里。镇子里商店肉铺、菜摊水果摊一应俱全,只要经济情况允许,买东西十分方便。镇子上的人那时都已经比较洋气了,高跟鞋喇叭裤烫发头随处可见,邻居们也都不怎么吃糌粑,说糌粑油腻膻腥味儿大。环境悄悄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一家人吃糌粑的频率大大下降了,白白软软的大米饭,鲜香的炒面片渐渐让我们和糌粑隔山隔水了。以前全家人最爱的“辣子尕勺”也变成一种偶尔调剂的吃食,慢慢地,我们竟也能闻出酥油糌粑里似有若无的膻腥味,油腻味,开始变得挑剔。这个过程像一枚叶子飘落在秋天一样自然而然又静无声息。匣子里的酥油放久了长暗绿的霉斑,炒面自然也跟着霉了。有一天,奶奶手心里捧着一块发霉的酥油可惜得直咂嘴,她用小刀一点一点削着酥油的点点霉斑,那躺在掌心里的酥油再也不像黄黄的金条了,时光让它形色难辨。“再也用不上了哟……”奶奶倒出匣子里所有的炒面和酥油,拎起匣子里里外外扫了一遍,那空荡荡的匣子好似呜咽了一声,躲进了柜底。
被冷落的匣子重新派上用场,是因为我们的书。镇子里有一家新华书店,我们没事就爱往书店里跑,隔着柜台那些大小不一薄厚不同的书像一个个崭新的世界般深深吸引着我们,“那本,就那本!”我怯怯地给营业员指着一本不知仰望过多少遍的小人书。营业员是个烫着大波浪卷发的中年阿姨,戴着黑框眼镜,气质斯文,脾气也好,她从书架上取下那本书放到我面前的柜台上,嘱咐了一句,“慢慢看,千万别弄脏弄皱了。”她早已在来来往往的顾客中认下我们几个兜里没钱又爱蹭书看的小孩子了。不过那天我要买书!花布衣兜里奶奶给的硬币发出细碎清脆的声响,那些反复计算过的硬币是够买这本书的,我出汗的掌心握着一把硬币哗啦啦撒在玻璃柜台上,有一枚还粘在手心里不肯下来,我轻轻将它取下。大大的柜台缩小了硬币在我兜里的体积,那堆小小的硬币显得又少又寒碜,有一瞬间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那几分钟前膨胀的富足感顿时像泄了气的皮球,幸而阿姨数了数硬币说,“钱正好,够着呢!”就这样,每每有了零钱我们就跑去买书,时间久了,我们的书需要一个“家”。可是去哪里给书找一个家呢?书架是不敢奢望的。有一天,奶奶灵光一现忽而就忆起了那只柏木匣子,她立马翻出来,细细拭擦了一番,又在通风处晾晒了几天,里面仔仔细细糊上一层报纸。当几本薄薄的书放进去后,那只匣子忽然就变了,像注入了灵魂一般,里里外外散发出一种朴素典雅的气质来,仿佛一位落难的公主终于回到了她的家乡,一切恰如其分,安宁美好。
那匣子从此占据着橱柜上最显眼的位置,也占据着我们心里紧要的那个位置,只要瞅一眼,心里就会生出一种渴望,像檐下的白鸽每天清晨怕打着翅膀飞向阳光,我们每天只要有空闲总会围绕在书匣子旁边。因为匣子装着书,屋子里的气息也悄然变化着,若有似无地总能嗅到一种浅俗的日常之上的书香气,一股淡淡的,厚重而静笃的油墨香。那香气是清越的,沿着鼻息慢慢渗入脑门,我们眼前就亮了,仿佛撞进了一扇门里,仿佛将要到达一个广阔的所在。那气息萦绕在心里,从未有过的优越,富足,高尚,自信。
每当闻到那书香,我们雀鸟般欢腾的心,瞬间就安静了,吵嚷声也弱下去了,姐妹二人四只小眼睛滴溜溜转着,总会去抢着拿同一本书,先下手的那个得意地捧着书开始读,没抢到的也不吵,反正书匣子里有的是书!薄薄的阳光从小格子窗里斜射进来,滚烫的炉灰里埋着几颗胖乎乎的洋芋,温暖清甜的香气渐渐变得浓郁,继而发出让人馋涎欲滴的焦香。那是奶奶给我们的奖励,姐姐总是读得比我快,我读一本,她能读三本,所以她有优先权,总是先挑最顺眼的那个烤洋芋吃。“不能一边看书,一边吃洋芋,书会全都吃到肚子里!”奶奶煞有介事地提醒我们,我们就调皮地反问她“吃到肚子里不是更好吗?有人还喝墨水呢!”“好什么好?记到心里是文章,吃到肚里一锅粥!”
买书的钱是奶奶从日常家用里省出来的,那些毛票硬币包在一块看不出颜色的碎花手绢里,压在炕毡下,只要我们说要买书,就有求必应。那时多数孩子只有几本书,有些除了课本之外一本课外书都没有。而我们很奢侈地拥有了成套的《红楼梦》《哪吒闹海》《聊斋志异》和一些零散的《隋唐演义》和《三毛流浪记》,虽然都是些“小人书”——连环画,但在潜移默化中培养了我们的阅读兴趣和习惯,给了我们最早的阅读体验和精神烛照。我们读书的时候,奶奶也跟着看,她一个字也不识,就看图画,她喜欢《红楼梦》,最喜欢黛玉葬花那一本。她坐在我们中间,认真地捧着书,一页一页仔细瞧着,口中喃喃自语。她总是忍不住地回头问我这一页的意思,又转头问姐姐那一页的意思,完全像个追着大人听故事的孩子。
其实,不识字的奶奶是很会讲故事的,也很会领悟故事的内涵,甚至会自己编故事讲给我们听。在没有上学前,没有书匣子时,奶奶就是我们的“故事匣子”,我们就是听奶奶那些带着泥土香气的灵性而温暖的民间故事长大的。那时觉得奶奶的故事像一千零一夜,怎么也讲不完。我最喜欢奶奶自己编的一个青蛙和灵珠的故事,有点像中国版的《青蛙王子》,我们简直百听不厌。那故事是讲一位母亲生出来一只青蛙孩子,怕被人看见就一直藏着,青蛙一天天长大,央求母亲要去上学,可怜的母亲没法拒绝,就缝了花布书包让小青蛙背着去上学了。青蛙在路上捡到一颗灵珠,那颗灵珠可以让生命起死回生,青蛙一路救了蜜蜂、白马、老鼠和一个人,不想那个人贪慕灵珠,说青蛙偷了他的珠子,青蛙被关进牢里,灵珠被抢。故事的结果是,小蜜蜂传递消息,老鼠打洞,白马带着青蛙回家,青蛙经过一系列人间磨难,变成了一个真正的男孩,而灵珠被贪婪的人们抢来抢去,最后碎成粉末……“世间哪有灵珠?善良的心才是灵珠!”奶奶说。
奶奶对一切有文字的东西都很敬重,只要是书,不管课本、电影画报、小人书都要放到高处,读书时她要求我们立身坐起,后背挺直,绝不允许躺着读。她总是帮我们把书拾掇得高高的,生怕一不小心被压倒屁股底下,她不许我们将用过的作业本到处乱扔,总是收拾得整整齐齐的,好像我们还会再用一遍。有时,她会翻开我们的旧作业本细细欣赏,说姐姐的字写得方方正正像印上去的,我的字还差一些,写着写着就打瞌睡了似的东倒西歪。
我知道她在说什么,小时候我就是个贪睡的孩子。记得有一晚因为打瞌睡写不完作业,看着姐姐裹着棉被睡下了,我就开始抽抽搭搭地哭起来,奶奶披着棉衣下炕来陪我,窗外北风呼呼地吹,屋里的铁皮炉子也熄了,远处的狗吠像跌进寒夜的深渊里一样朦胧空旷,我对着没做完的数学题眼泪鼻子糊了一大把。我一半撒娇一半撒泼地哭闹着,就是不肯往下写。奶奶明白了我的意思,说“你等着”,我以为她是要去叫醒被窝里的姐姐帮我写作业,因为之前有过先例。结果她从炕毡下抽出一把两指宽的竹制米尺,放在桌子上,黑着脸说,“没有苦心,怎么能学好!上次让你姐帮你写作业,我这是干坏不干好哇!”我吓得止住了哭泣,泪眼巴巴地望着她,她对我们从来都是宠爱的,从来都没有吓唬过我,但在学习这事上她变得不妥协,给心不给脸。
多年后,女儿刚上学时也跟我一样度过了一段艰难的适应期。那天女儿身体不舒服,写了一会作业后,就撒泼扔掉铅笔,哭起来。女儿像那个北风呼啸的夜晚的我一样,泪眼巴巴地央求我帮她写。我抱着女儿给她讲奶奶吓唬我的事,也说了和奶奶同样的话。女儿抱着我说,“妈妈,我错了。我慢慢写,总会写完的。”看着台灯下小小的身影低着头,挺着背,一笔一画,一字一格地写下去时,我看到了白发苍苍的老奶奶和那个小小的自己。
奶奶喜爱我们读书,却不功利,她就是觉得读书好,喜爱就是喜爱,再无其他。当邻居“罗百万”叔叔在雪天寒风凛冽的清晨,抡着棍子赶几个娃娃站在高高的屋檐上背书时,奶奶总不免咕哝一声,“多受罪哪!”罗叔叔铁了心背搭着手来来回回转着,像个私塾先生一样挨个抽打背不下书的娃娃的手心。娃娃们疼得直叫唤,我们听着胆战心惊,奶奶蹙着眉头,眼瞅着屋檐上几个吸溜着清鼻涕的娃娃,几次张开嘴巴又欲言又止,我们挤在暖暖的被窝里,暗自庆幸年轻的父母去远方谋生而奶奶又是这般的慈爱。
奶奶最是觉得读书高贵,最尊重读书人和她认为有学问的人,像学校里的老师,就是跟平常人不一样,怎么不一样?她也说不出来。奶奶那辈有个故交叫西山阿爷,据说是个老学究,深得家人尊敬爱戴。他有时会从乡下来我家住两天。记忆中老人总是穿着一身缀满补丁的灰褂子,佝偻着腰,身体缩得像风干的胡桃一般,皱皱的一张麻脸,银须颤颤地拄着拐棍一路走来,脚步却十分轻快。西山阿爷的眼睛很特别,很小的一双眼睛被皱纹挤着,深深陷进岁月的车辙里,像两粒豆子,可那是两粒金豆子!当他裂开没牙的嘴巴笑着望向我们,那双眼睛就像噙着泪花似的晶莹闪烁,被那样的眼睛看上一眼,胸中就仿佛点亮了什么,生出一些银色的芽,正闪着湿润的光。
奶奶和爷爷很是敬重西山阿爷,每逢老人到来,奶奶马上会点起灶火烙上几张冒着油星的烫面油香,如果时间允许还会蒸几笼香喷喷黄萝卜包子,倾尽所能地招待老人,但结果总是让我们这些馋猫大饱口福。每一回,西山阿爷都跪坐在炕上笑眯眯地唤我们坐到他身边来,他太老了,连两岁的弟弟都抱不动,只能爱怜地摸摸我们这个的脸蛋、那个的头,聚着光的眼睛星星一样逐一闪过我们的脸。我们围着瘦小的老人,总是期待着他能说些什么古今趣事,讲些我们不知道的学问道理,可是老人只会爱怜地朝着我们笑着。
闻着桌上油香和包子的香气,他不动筷子,我们谁也不敢动,只任口水哗哗往肚里流。西山阿爷小心翼翼拿起一个软乎乎的烫面油香,慢慢撕开,那油香在老人干枯的手指间金箔一样层层断开,里里外外都金黄灿烂。老人慎重地尝了一小口,然后撕开的巴掌大的油香被他一一分发到我们面前的小碟里,他知道我馋,总给我大些的。包子也一样,先慢慢掰开,再分给我们,老人吃得很少,但吃得很喜悦,好像尝到了什么山珍海味似的,脸上的每根皱纹都笑着。老人给我们讲,一粒种子从地底下生根发芽,经风霜雨露,拔节抽穗,日晒雨淋,变成细米白面是经历了一场艰辛的,我们且不可怠慢了它,不可没心没肺吞下它,每一粒粮食,都期待着享用者的赞美呢!我们听着,心都变得花瓣一样柔软了,越发觉得眼前食物的美好金贵,一个个小手捧起油香,学着西山阿爷的样子,一小口一小口地吃,就连掉下的碎屑也一一捡起放入口中。
老人看我们喜爱读书,就悄悄对爷爷奶奶说,读书是要明亮自己;不能把书的船看成是岸。娃娃们长大也就明理了。我们在一旁悄悄竖起耳朵听着,对西山阿爷意味深长的话,似懂非懂,只见爷爷奶奶频频朝那一身缀满补丁的瘦小的身影点着头。
书匣子伴着我们渐渐长大,上了初中后我们不再满足于小人书,奶奶依然支持我们买书,但碎花手绢里的毛票和硬币有时连买一本书都凑不够了。我们还会在雨雪天挤在奶奶炕上读书,不过那些书都是从同学手中借来的,有《红与黑》《简·爱》《呼啸山庄》,有琼瑶的《一帘幽梦》,有《笑傲江湖》《射雕英雄传》,奶奶凑过来看我们那些插图极少、满纸黑字的书,翻一会儿又无趣地放下,她再也介入不了我们的读书世界了。
铁皮炉里依然烤着洋芋,但我们不再害怕把书吃进肚子里,一边嚼着软糯的烤洋芋,一边哗哗地翻书。书匣子在我们身后的橱柜上,蒙上了灰尘,再度躲进一片阴影里,无聊的奶奶坐在炕角打盹。如此日复一日,那书匣子也像有生命似的老下去了,边角被岁月啃噬得不再光润,顽皮的弟弟在上面胡乱地涂鸦,淡黄的原木悄然成暗淡的褐色,原先那只神秘的眼睛仿佛也阖上了。偶尔,匣子里还会蹿出丝丝缕缕腐旧的霉味,像一个患了风湿病的老人。只有当家里来了亲戚或邻家小孩的时候,奶奶会像亮宝般打开匣子,将巴掌大的小人书放到孩子们手里,看着她们胡乱翻书时,她会堆起一脸皱纹满足的微笑。
播种一种行为,就能收获一种习惯,一种品格,甚至一种命运。读书带来的益处渐渐显露出来,姐姐每年都会在作文竞赛中获奖,当她捧着一张张鲜红的奖状回家时,奶奶总是高兴得直抹眼泪。后来姐姐如愿考上了大学,成了左邻右舍口中“鸡窝里飞出的金凤凰”。而我,虽然早早地招工进了企业上班,但一直保持着读书习惯。在上班不久后,我开始自学写作,尝试着投稿,第一篇作品就在当地报纸上发表了。记得那一篇六百多字的小散文发表后,奶奶如获至宝地反复摩挲着那张报纸,七十多岁的人激动得像个小孩子,嘴唇哆嗦着,不无遗憾地说,“要是我识字就好了,要是识字就好了!”虽然我读给她听了,但她却听不过瘾,每天睡觉时都将那张报纸叠好,压在枕头底下,白天又拿出来反复观看,看了半晌说,“狗看星星满天明呀!”随即抹去眼角渗出的泪珠。
我发表的“豆腐块”越来越多了,接着又获了几次小奖励,得到激励而一路顺风顺水的我控制不住地有些飘飘然了,一时自我膨胀地以为自己真是个“作家”了,那段时间只知道一个劲儿去写,买来的书都没翻过几页。奶奶看着案头崭新的书,纳闷地问,“买来的书咋就不读了呢?”我不知天高地厚地脱口而出,“我也在写书呢,将来写出来的书要比这些还好看哩!”奶奶怔住了。晚上吃饭的时候,她一反常态一个劲地往我碗里夹菜,说写书费脑筋,多吃菜。我以为我那日渐瘦小的奶奶被我这个“作家”的豪气给镇住了,没想到她缓缓开口道,“缸里的水每天都要挑来新的蓄上,烙馍馍的面放久了会生虫,长寿菊不晒太阳长不高,写书这事也应该在心里蓄上水吧?像吃饭一样,对吧?”
接着她兀自讲起一个故事,全然不管我是否在听?是否能听进去。那是个很浅显通俗的故事:有个非常聪明的人,读书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就很自满,自以为学了很多知识,就牵着骆驼去东方和西方寻找更广博的学问,他发誓今生要学完世界上所有的知识。有一天,他来到一条河边,遇到一位贤哲,他俩交谈甚欢,这时,一只小鸟落到河边浅浅啄了一口水,又很快飞走了。对方突然陷入沉思,这个人很纳闷,就在他起身要离开的时候,哪位贤哲说,“朋友啊,你我拥有的学问,与那浩瀚的大海相比,就如那只小鸟啄到的一滴水啊!”
2015年初,我去马来西亚参加一篇获奖作品的颁奖典礼,当我站在大西洋和太平洋交汇的马六甲,那一刻,我想起了我已去世多年的奶奶,想起了我们的书匣子,想起了西山阿爷的眼睛和那两句从未明白的话语,“读书是要明亮自己;不能把书的船看成是岸……”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大海,望着浩渺无际的海面,我真的觉得自己就是一只小鸟,在知识的瀚海里刚刚触到一滴水,或不到一滴。
光阴的河日夜流淌着,书匣子老去,奶奶也老去了。我们相继成家后,书匣子成了奶奶一个人的。有一回,我回家看她,只见平日清寂的小院里叽叽喳喳挤满了一群小孩,原来是她唤来巷子里的小娃娃来读书,她拿出我们孝敬她的水果糕点当奖励,那群小娃娃像一群小鸡围着老母鸡一样围着她,争相举着胖嘟嘟的小手,抢她手中的水果糕饼。她乐哈哈地说,“吃完水果要读书,一人一本!”她打开搬到院里的书匣子,取出那些破旧的小人书,一个娃娃手里塞了一本。孩子们吃完糖果,很快东一本西一本地把书给扔在地上,跑出去玩了,她挡不住他们,好像也不想挡。短暂的喧闹后突然清静的院子里风呼呼刮着,那些掉下或撕破的脆黄的旧书页枯叶一样被片片吹散,她佝偻着腰一边捡着地上的书,一边喃喃自语“现在的孩子,咋就不爱读书了呢?”
孤独的奶奶常常抚摸着书匣子,像无限留恋地抚摸那些暖意丛生的旧时光,可是谁都回不去。我想用笔给奶奶和自己留一份慰藉,当我悄悄告诉她我那并未深思的不成熟的计划时,奶奶浑浊多年的眼睛瞬间亮了,她惶恐而惊喜地说,“我的娃,奶奶不行了,好多故事都忆不起,那些故事都说不全了!”那时我告诉她,我想写她曾讲给我们的那些故事,把她的故事用文字记录下来,写成书。她讲,我写。愿望虽美,但后来,直到奶奶去世,我也没做到,我给自己心里挖了一个深深的洞,不知什么时候能补得上。
奶奶去世后没多久,老屋子也给卖了。收拾旧物件的时候,我没有看到书匣子,只当是被家里人劈柴烧火了。小人书倒是零零散散找到了几本,虽然破旧发黄残缺不全,但我还是收拾好,带回了自己家。直到后来女儿出生,渐渐长大,我给她买了一个大大的粉色收纳盒当书匣子,把那几本发黄的小人书也整整齐齐放进她崭新的书匣子里。女儿有时会翻出来看,每次都会奶声奶气地问,“妈妈,这是你小时候看过的书吗?是太奶奶买的吗?我好喜欢那个会讲故事的太奶奶哟!”
我也很喜欢,可是却再也见不到了。就连那最初陪伴着我们的书匣子再也见不到了,我看到时光的小毛贼早在我们疏忽散漫时载着一车又一车的物什走远了,留给我们的只是斑驳记忆。
不曾想到的是,前年我同一帮兄弟姐妹去做公益,当我们费尽周折找到那位在网上求助的病人时,竟认出她是我的一位远房亲戚,只是多年不曾走动都疏远了。患病卧床的她一个劲地招呼大家炕上座,那是一间小小的出租房,低矮的檐上覆着青灰色的碎瓦片。风微弱,墙头衰草却有着敏感的神经,不停抖擞。一棵樱桃树的枝丫冒过屋檐,细碎的叶子间缀满小小的青樱桃果。大院里住着四五家人,有一家的烟囱里冒出一股股乳白色的炊烟,更多的烟从那间小屋子里四处逃窜,烟幕后传出小孩子一阵剧烈的咳嗽,亲戚隔着小玻璃窗瞅着说,“这娃娃,烧柴潮湿了都不知道。”“他家大人不在吗?”同行的丁大哥问,“我去看看。”不等亲戚回答,他已经踏出小屋门槛。
“他大去踏三轮车了,他哥也去了,暑假嘛,帮帮家里也是应该的,可这娃娃就是不去,唉。”亲戚叹了一声。我心里想着与亲戚此次的相遇,有一搭没一搭听她絮絮叨叨地说着,无意中,在出租屋湿凉的泥地的角落里看到一只深褐色匣子的一角,角度恰好对着那块酷似眼睛的疤痕,真的是那只眼睛,在儿时的阴雨天与我反复对视过的眼睛啊。我已尘垢满面,它却认出了我!我的心瞬间像被闪电击中了一样,乱了方寸。
我走过去,几乎颤抖着蹲下身抚摸它落满灰尘的一角,我的手仿佛伸进时光的深潭里,不能自拔。我蹲在那匣子旁丧失了所有力气,我和它面对面,我看着它,知道我们永远失去了它。它无限谦卑地躲在阴影里,贴着潮湿的地面,上面堆放着一袋面粉和一些杂物。
“咋啦?”亲戚纳闷地问。
“没事。”我摇摇头,喉间仿佛卡了鱼刺。
憨厚的亲戚被我懵住了,她一瘸一拐地站在我身后说,“这匣子牢实耐用!”
“耐用就好。”我极力掩饰着升上喉咙间的哽咽,不敢转身。
“捡回来时里面还装着几本小人书,都被这院里的娃娃们抢去了,尤其那尕小子,看见书就像疯了一样。”亲戚说
“尕小子?就是那不愿去蹬三轮车的娃娃吧?”
“就是的,那娃不认命。”
亲戚顿了顿,接着说,“那娃不认命,就死认个读书,读书有用吗?而今大学生找不上工作的多了,那娃还说什么理想是做乔布斯那样的人,唉……”亲戚不知道,其实读书也是一种命运。
我走出了亲戚的屋门,院里的烟还未散尽,像青色的薄雾缠绕着阳光,一只小蜜蜂被光染成金色,正在那里盘桓。这才发现园中几棵樱桃树下种满了青菜。小小的破土而出的青菜,每瓣嫩芽都绿油油地顶着阳光,仿佛一些希望的小苗。丁哥帮那孩子收拾好了灶炉,站在门口朝我打了个手势,示意我过去。
潮湿昏暗的小出租屋里,小小的少年穿着纯白色短袖,瘦小的身影背对着我们,腰挺得直直的,在靠窗的书桌前正捧着一本书在读。是那个不会生火、不去蹬三轮车、不肯认命、想当乔布斯的尕小子!在周遭暗淡的光影里,孩子纯白的身影像暗夜里的一根白蜡烛,像我从前见过的一种光,看上一眼,胸中就仿佛点亮了什么,生出一些银色的芽,正闪着湿润的光。丁哥悄声说,“真叫人心疼!”他掏出一张纸币偷偷放到靠门口的小桌子上。
我悄声对丁哥说,下次,我们带些书来!
原刊于《朔方》2022年第3期

白羽,女,回族,本名马桂珍,甘肃夏河人。甘肃省作家协会会员。作品见于《散文选刊》《民族文学》《黄河文学》等。作品获《民族文学》年度散文奖、甘肃省民族文学奖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