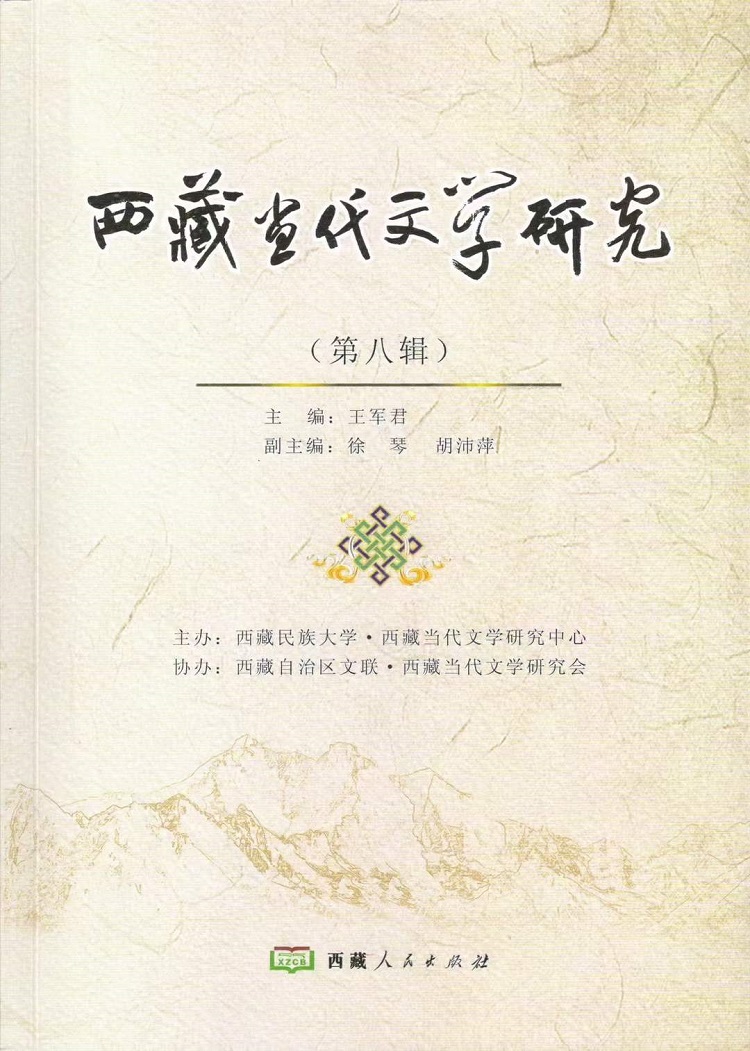
【摘 要】诗美反映的是诗人的创造力。沙冒智化的新诗集《月亮搬到身上来》,继续在他倾心的生命、智慧和语言三个重要诗学领域深耕细作,为汉语诗歌提供了新颖的诗美品质。诗集《月亮搬到身上来》是一种“神性下沉”的写作,使得诗歌有了一种大生命意识,突出了生命之间的整体性和联系性,因此诗集呈现出一种生命之大美的气象;沙冒智化借助了佛教的义理,他诗歌里的“我”主要是展示一个后工业时代的“自我存在”;在《月亮搬到身上来》中,通感和摹绘的修辞手法十分普遍,因而导致整体语言风格显得十分灵动新颖,陌生感十足。
【关键词】沙冒智化,《月亮搬到身上来》,神性下沉,自我存在,语言神秘
所谓诗美,就是一首诗作为诗歌历史所提供的新的品种、新的思想与新的艺术。1诗美是判断诗作优劣的核心诗学概念。“诗美”用来概括诗歌在一首作品里所提供的一切新的东西,也许是一种新的感觉,也许是一种新的体验,也许是一种新的意象,也许是一种新的情绪,也许是一种新的思想,也许是一种新的主题,也许包括形式方面,也许是一种新的表达、新的象征、新的句式、新的词汇、新的技巧等。2诗美反映的是诗人的创造力。笔者完全赞同依据诗美来评定诗歌,主张诗歌批评就应该让诗歌置身于悠久的诗歌历史中接受检验,判断其有没有产生一种新的质素,有没有给人带来美的感受。西藏诗人沙冒智化于2022年10月出版了他的新诗集《月亮搬到身上来》,继续在他倾心的生命、智慧和语言三个重要诗学领域深耕细作,为汉语诗歌提供了新颖的诗美品质。诗集《月亮搬到身上来》是一种“神性下沉”的写作,使得诗歌有了一种大生命意识,突出了生命之间的整体性和联系性,因此诗集呈现出一种生命之大美的气象;沙冒智化借助了佛教的义理,他诗歌里的“我”主要是展示一个后工业时代的“自我存在”;在《月亮搬到身上来》中,通感和摹绘的修辞手法十分普遍,因而导致整体语言风格显得十分灵动新颖,陌生感十足。
一、神性的下沉与生命的大美
神性是21世纪初期少数民族诗歌批评中的一个热词。如,许多评论家认为藏族新诗的神性特征十分显著。藏族诗人深受佛教、苯教文化的影响,在他们的意识深处,世间万物皆有灵性,它们和人类一样都有精神的经历,甚至比人类的历史还久远绵长。在藏族新诗中,除了常见的寺庙、僧人、菩提、经幡、风马等宗教文化词汇外,还喜欢使用天空、石头、碧草、河流、雄鹰、牛羊、风等充满地域特色又具有永恒特征的物词。神性写作保证了诗歌的高度和厚度,但却容易遮蔽个性心理,疏离现实生活。沙冒智化是“80后”诗人,他的诗创既有佛教、苯教文化的影响,也接受了传统和现代兼容的现代诗学理念。从2021年出版的诗集《月亮掉到碗里说》的厨房系列诗歌中就可以看出,沙冒智化非常关注现实生活和个人心理,并不一味地高蹈在大而空的世界中。他喜欢切入“绝对宇宙精神”从而开展追问,但也不排斥对日常生活的诗意体验,恰如诗集名称“月亮搬到身上来”,通过日常生活来体验永恒的存在。因此,诗集《月亮搬到身上来》是一种“神性下沉”的写作。比如他的诗歌《石头和刺猬》,首句“啤酒杯里蹲着一座雪山”,就已经把日常生活和永恒诗意统摄在了一起。一方面,通过写石头的刺和刺猬的刺的不同,极大地丰富了喝酒人的内涵;另一方面,又流露出雪山、大海、石头、刺猬四个意象的永恒和古老的意味,在喝酒的瞬间发现了永恒的美。
沙冒智化诗创的“神性下沉”使得他的诗歌有了一种大生命意识。大生命意识是中国诗学的一个古老传统。其悠久的历史可溯源至先秦“文化轴心”时代。《周易》强调“与我们周围的生命休戚与共”。3“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这句话指出万物之间有着紧密的关系。4屈原的《天问》《九章》《离骚》等诗歌的文化语境是一个“人神混沌”的世界,开创了一种向“天”寻道的诗歌传统。庄子说:“吾在于天地之间,犹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突出了人和自然万物不仅平等,而且互相依存的理念。5儒家的大生命观认为“天命是生命的本源,身心是生命的结构,心比身更重要”,所以儒家既强调修身,更强调修心。先秦时期形成的大生命观念认为人与自然是整体性、联系性的关系,类似于今天的“生命共同体”,已经非常重视警惕人的贪欲,把人看做是大自然中正常的一员来看待。在西方文化体系中,20世纪的德国伦理学家阿尔贝特·施韦泽向东方的印度和中国哲学学习,把世界看做一个整体,提出了“敬畏生命”的观点,这是西方对大生命观念系统化认识的开始。“神性下沉”让大而玄的天地宇宙与琐碎繁杂的日常生活互相融合,所以“啤酒杯里蹲着一座雪山”(《石头和刺猬》),“天空是一个蓝色的气球”(《蜕变的时间》)。沙冒智化的诗歌通过看似不经意的琐碎的日常事务,巧妙地和高远的天地时空联系在一起,实现了现实和玄学的联姻,也就有了一种强调人类和自然、现在和历史、时间和空间互相联系的大生命意识。因为大生命意识,诗歌展开了蓬勃大气的联想。请欣赏他的诗歌《月亮搬到身上来》中的部分:
……
风叫累了一棵树的根
心在着火
带着暖气的夏天坐在饭桌上
蚂蚁找着没有开口的语言
看到了爬行动物的善良
藏獒有雄狮的影子
脚底下的鸟计划着用翅膀换来天
汽车吃饱了油
一头母猪给猪仔讲述慈悲的容忍
月亮红了脸
白日梦在跑步机上爬山
……
风和根,夏天和饭桌,蚂蚁和语言,爬行动物的善良,鸟的机会,母猪的慈悲,这些语词搭配,新颖独到,颠覆习惯,但细想一下,又合情合理,令人深思。“敬畏生命”不是神化生命,贬低人类,而是把万物和人类联系到一个整体当中来认识,来思考。所以说,汽车才会“吃饱了油”,树根也会被风“叫累”。这种万物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认识,提升了万物的生命韵致,也升华了我们为人的人生境界。
诗集《月亮搬到身上来》塑造了一个充满智性的、空灵的“大生命”世界:有太阳、月亮、冰川、夜晚、石头、大地、河水、云、风等自然界物质形态,还有羊群、马匹、妈妈、秃鹫、鹰等组成的动物和人类世界形态。佛教的生命观是一种大生命观,认为所有生命包含全部十界,都潜藏着“佛”的可能性,因而所有生命都是宝贵的。正是基于此,所以在沙冒智化的诗歌中,所有的生命体自身都蕴含着丰富的蕴味,他们的存在不依托人的关注。大生命世界的建构使得沙冒智化的诗歌既不同于面对高山湖泊时开始哲思的神性诗歌,也区别于流连在日常生活中的碎片化写作。它的诗的世界是人类和大自然紧密联系的世界,我们的生活源自自然,自然中也有很多美的存在需要我们去体验。大生命意识显然对当今面对自然界越来越麻木,越来越缺乏感知的我们有着重要的警示作用。诗歌的使命之一就是不断地完善人的生命存在。沙冒智化主张:“写诗的过程,是学习人、“更像人”的过程,不能倒退到兽人时代。”6人和动物最本质的区别之一就是审美。新诗集《月亮搬到身上来》塑造的大生命世界让我们自己敞开了一个全新的生命感受,这也是新诗集提供的一个新的创造。我们以诗歌《守门石》为例来讨论这种全新的生命体验:
我家门口有块石头
我们把它当作宝物看待
不让他人用它作为石墙,石梯,石板
这块石头已经被时间磨出光
近几年我出门在外
每次想起那块石头
想起岁月画在它身上的
风水雨林的记忆
回家看到那块石头
它的身体已经被钢钉缝了好几个口子
一个病人身上插着好几个管子似的
它的姿势让我有点悲伤
它在我家门口
像妈妈一样
等我回家
守门石的生存方式随着岁月的流逝发生着变化,在诗人小的时候,守门石被当做宝物看待,但当诗人成年外出后,没有了真正爱恋它的主人的守门石已经像一个病人一样千疮百孔。此时的守门石作为审美对象,它的生存方式恰如诗人自身的生命体验一般令人一声长叹。在对“守门石”的生存姿态的感慨中也感慨着诗人和阅读者的自我生命状态。此首诗歌中,守门石不是一般的客观对应物,它的命运和抒情主体“我”的命运是被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对比舒婷的意象诗《致橡树》,诗中象征女性的木棉花就是纯粹的一个意象,并没有和诗人的命运捆绑。
二、诗性的智慧与自我的拯救
中国诗自宋代以来发展了一种智性诗歌,就是以禅入诗,以议论为诗,通过诗歌来阐释一种道理,比如非常有名的苏轼的《望庐山瀑布》。经过一千多年的演变,宋诗的智性传统在今天的理性抒情诗中得以传承。沙冒智化的诗歌很多是一种现代生命的诗意体悟。理解沙冒智化的理性抒情诗的关键是体认诗中“我”的形象。成功的抒情诗往往有一个显赫的“我”的形象,比如郭沫若笔下敢于抗争,肆意横流的“我”,又如舒婷《致橡树》里有独立个体意识,追求人格尊严的“我”,再如翟永明《女人》中追求精神独立、敢于反抗的“我”。沙冒智化诗歌的最大贡献之一是给我们塑造了一个不同于以往任何诗歌中的“我”,这个“我”,是一个已经深受佛理熏陶,却置身于人间烟火中,在人间琐事中修心修行体悟的形象。正如他在诗歌《一场雪》中宣称:“我用一双鞋走了三十六年/路边的花草受宠我的眼睛/你要独自走过一个春天/我的声音里下一场雪/没有路灯带路的今夜/星星是我看你的眼睛/我生来在孤独中修行/最终归还于你的孤独/我用阳光藏好的你/你用月光找回我。”在日常生活中体味哲理,在人间百态中升华经验的审美之路不是沙冒智化才开始的,在1930年代冯至的诗歌已经这样做了,但沙冒智化借助了佛教的义理,他诗歌里的“我”主要是展示一个后工业时代的“自我存在”。一个在烟尘中修行体悟的“我”的形象的出现也是时代的体现。在后工业时代,人们激情消退,审美疲倦,深陷碎片化的日常而无法自拔,因此,一个置身日常生活,体悟日常生活的“我”的形象的出现是诗歌的时代责任,这个“我”有以下的独特美学特征:
一是“我”对生存意义的不懈追问。如,诗人在诗歌《生前我的名字叫什么》中写道:“现在我只想理解一个问题/我生前的名字/到底叫什么?/或者我的另一个名字。”这种追问体现了诗人强烈的主体生命意识。以前诗歌的“我”是一个主要在社会层面活跃的“我”,但沙冒智化诗歌里的“我”不仅在社会层面活跃,而且开始了生存意义上的终极关怀。当世界开始变得混乱、荒谬而不可捉摸的时候,人们也无法用清醒的理性科学来阐释和把握这个世界,这时,生存意义的终极关怀就显得尤为重要了。“我”对生命的终极关怀矢志不渝,“在夜的四处/凭着嗅觉/我要躺在泥坑里的一朵石头花上/找出太阳的维度”(《时间身后的我》)。
二是“我”一直在了悟,体悟,觉悟,开悟的过程中。前面提到,“我”在日常生活中修心修行体悟。在佛教义理的加持下,《马,啊》一诗喊出了“牧马人,发现自己是匹马”这样的人生领悟。又如,在面对别人的诋毁时,诗人意识到这是在帮助自己检视言行,对此他表示感谢:“若这世上有人诅咒我/那是一个善良的嘴巴(《月石桥》)。”
这个“自我存在”颇具存在主义的味道。存在主义认为:个体发出的一种“存在”信息,将他“感知到”的“某一事物”向大众发布,由信息反馈而获得共鸣,相互感受到彼此的存在。此信息可能是隐秘的,由“接收者”感知这种隐秘的存在。“我的体内有很多语言的化石/里面藏着无名星上独有的一片海/但我们看不见,它在/一朵太阳花里”(《光的岸》),“我有一张地球的风景图/把他挂在我的眼里/去图中,拿回你的夜”(《九月第二十二天》),“我失眠的枕头里装着你的夜/躲开时间,把胡须种在脸上/若脸变成了一片森林,种点蔬菜和幸福/把草原退回帐篷里,等我”(《月叶下》),“我把心里的水倒进碗里/不小心把月亮倒了进去”(《不小心把月亮倒了进去》),“我的身体里有一片沙漠/也有一小块的绿洲”(《双层脸》),诗集《月亮搬到身上来》里有很多这样的自我存在信息书写,诗歌把这些信息向读者反馈从而希望和读者相互感受,彼此依存。这些信息都是隐秘的存在,“我”既是接收者,也是感受者。
这种在日常生活中“自我存在”的展示,实际上也是诗人对自我展开的一场场救赎。首先诗人是不断地通过存在信息来证明自己的存在,其次是希望寻找到自我救赎的路径。他写道:“不管离地面有多远/我只想入住/石头的空间里(《边界》。”洛夫认为,坐禅的开悟是一种生命的觉醒,作诗是生命的感悟,前者能够帮助诗人透过美和超越的本质,消除生命悲苦。7沙冒智化在《物体中》写道:“命生钢缝,骨软如草/当你看见黑夜忧伤的时候/站在光里阅读风/你的身体会轻松一点。”他又在《月叶下》一诗中写道:“太阳休息的时间,请你挂上一盏月亮/绿叶闭关之前,我要沿着河流回家。”由此可以看出,诗人是从人和世间万物的关系中寻找精神的出路。他写道:“体内,有张地图/其中一条路/通往放生的我/一盏婴儿般的灯/在时间的枝丫上/生长着爱的骨节(《十二月十六》)。”分析沙冒智化诗歌中的存在信息,主要还是来源于“大自然”。爱默生说:“田野和树林赋予人的最大快乐,在于揭示了人与植物建的神秘关系。我并不孤独,也不陌生。植物冲我点头,我也向它们致意。”8很显然,人与大自然的和谐使得沙冒智化获得了持久的快乐,缓解了他在现实生活中的焦虑和悲伤。“面对自然,即便他正经历苦痛,却有强烈的愉悦之情滋养身心。”9所以,诗人又会这样写:“谎言放生在夜里,喂给星辰/天一亮,都摆着一张张笑脸/苦苦央求放过自己(《谎言》)。”
三、语言的神秘与人的展开
有论者指出沙冒智化的诗集《时光的纽扣》的语言“滞重而又难以理解”。10换句话说,沙冒智化诗歌的语言不符合常规的逻辑经验主义,因此导致了阅读的困难和理解的障碍。在新诗集《月亮搬到身上来》中,语言风格继续了这一特点,如诗歌《日子走》:“走在路上的风/通往器官/不管为谁停留。”器官是谁的器官,是风的,还是人的,让人很难确认。其实读完全诗以后,也不难理解,诗人提到风,是通过“风”的永恒性来证明日子的恒远,是一种现代诗歌时间性的表达方式。“通过器官”,是让我们用感官来感受时间的永恒,是“摹绘”修辞手法的运用。摹绘手法将风吹人的触觉具体化、真切化、动态化。除了摹绘手法,沙冒智化还擅用通感手法。如,诗歌《幻觉》:“我的身躯里长着/一间土木结构的房屋/窗户锁在脑后/大门关在嘴里。”前面部分已经谈过,这是一种个体发出的存在信息的书写,在沙冒智化的诗歌中这种写法十分普遍,在此不再一一列举。这里就使用了通感的手法,房屋是视觉看到的,但被诗人的身体感觉(也叫心觉)感觉到了,这样的做法使得“房屋”这个意象活泼、新奇。在新诗集《月亮搬到身上来》里,通感和摹绘的修辞手法十分普遍,因而导致整体语言风格显得十分灵动新颖,陌生感十足。但沙冒智化语言创新的动力源泉在何方呢?笔者分析,他的语言个性主要源自三方面:
第一,佛性智慧促进了沙冒智化的语言创新。现代诗人深受语言神秘主义的影响,沙冒智化也不例外。语言神秘主义本身又与佛教中的禅宗关系密切。佛教认为世间万物皆为幻象,四大皆空,所以现代诗喜好重构整体内部的物与我,重新确认人与世间万物的关系,而非遵从肉眼可见的现实现象。这样一来,就让诗歌跨越了旧有的语言逻辑联系。如,诗歌《金巴是他们的名字》中写道:“风撞死的不是一只羊/是一片空空无影的天//喊着救命的/是一滴泪的轮回,不是一只羊。”依据佛理,风、羊、天、人四个意象之间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而我们人类的理性认知却十分有限。此时,语言的固有经验就被佛家的“妙悟”给超越和解构了,喊救命的自是庸俗的人,而不是超脱的羊了。
第二,大自然赠予诗人语言丰富的想象力和情感。语言的形象化是沙冒智化诗歌的一大特点。“好的作品和精彩的演讲都是永恒的隐喻。”11“每个自然形态都因它隐含的生命和终极缘由而具有意义。……每个自然物,如果观察得当,都展示了一种新的精神力量。”12例如诗歌《深夜里我看到很多宇宙的窗户》写诗人十六岁离开父亲后的感受,并没有直接抒情,而是采用了风、太阳、狗等几个自然意象来表达精神的存在和变化。“风”象征凌冽,“太阳”象征温暖,“狗”象征世态,这些起源于自然界的物质分别对应着一种思想状态。
第三,存在主义哲学思想的影响。存在主义要求不能把语言仅仅看成是交流思想或知识的符号系统,而是认为语言有生命力,语言是存在的住所,语言第一次使人有可能处于存在的展开状态。13沙冒智化十分重视语言的生命力,他认为:“诗歌是神的语言,神在我们的想象中脱胎换骨,神原本是我们自己的智慧。”14
沙冒智化诗歌语言对常规逻辑经验主义的超越,使诗歌主体(人)容易摆脱常规的限制从而得到某种的展开和跨越。例如,诗歌《雪是一幅唐卡》中写道:”雪来了,天和地缝在一起/在拉萨的胸口雕出花瓣和叶子/绘制成一幅唐卡/像极了经书上的阳文/种满白色的光芒。”天和地本是一对对立关系,但因为诗人极强的想象力连到了一起,这样的存在就不是对立的而是弥合的,人也因天地的缝合而处于和谐放松的状态中。语言的超越否定了现象界中实在的、经验的物我关系,更新了既定的文化心理模式,在经历了一瞬间的陌生感后很快将获得极强的美感和身体的愉悦,或者称作人可能处于存在的展开状态。如,诗歌《有一条河的玩具》中这样写道:“吃着沙粒的青蛙/咬断恐慌的清风/燃烧颜色的花朵/正在粉碎的青稞。”青蛙、清风、花朵、青稞这几种物质本象征对应着大家习以为常的思想情感,但当和“吃着沙粒”、“咬断恐慌”、“燃烧颜色”、“正在粉碎”搭配后象征的思想感情完全不一样了,在陌生化的感觉中人不断地得以展开。有论者说:“他的汉语写作,唤醒了汉语新诗中沉睡的角落。”15笔者在此补充一句,他的语言的神秘,使人不断得以展开。
四、结语
沙冒智化的新诗集《月亮搬到身上来》在生命、智慧、语言三个方面提供的诗美品质是可圈可点的。文学的重要使命之一就是不断地认识人,完善人,丰富人。新诗集通过生命、智慧、语言三个方面扩大或深邃了人们的情感与思想,提高或升华了人们的精神与境界。沙冒智化的“神性下沉”写作打破了评论界对西部少数民族作家动辄“神性写作”的标签,突显了个体写作特点,突出整体性的大生命意识既是诗歌境界的表现,也是一种时代责任的体现;一个颇具存在主义味道的“自我存在”的展示,让我们正视我们的存在状态,从而试图展开自我救赎;新诗集对语言的不断突破和创新,让我们也获得了新的体验和愉悦。总之,新诗集的诗美创造提供了新的体验、新的感觉和新的表达,其的创新意义不容忽视。最后,笔者还想简要讨论一下新诗集《月亮搬到身上来》中多次出现的死亡意识。以诗歌《蜕变的时间》为例,诗歌不断地通过各种显露的外在事务来深邃我们内在的世界,通过显露饥渴、惨痛、死亡、墓地、梦境等各种不愉快来让我们正视时间的流逝和死亡的到临,最终从有限到达无限,从而实现精神上的自由。诗歌《蜕变的时间》陈述生死,语气平和且坦率,不像后朦胧诗诗人海子那样激愤而悲壮。诸法无我,万物呈现出来的具体之相并非恒定不变。每个生命体时刻都在发生着变化。难怪诗中会出现“我是她双胞胎哥哥”、“她是我双胞胎姐姐”、“我天天看着远处的自己”、“我有两个双胞胎弟弟/我们互不相识”等身份辨认模糊混乱的语句。这种佛教文化影响下的生死书写也是一种现代诗的诗美创造。
注释:
1.邹建军:《新诗的经典性来自诗美的创造》//刘静沙宋石峰:《中国新诗评论读本[第一辑]》,大象出版社2019年版,第213页。
2.邹建军:《新诗的经典性来自诗美的创造》//刘静沙宋石峰:《中国新诗评论读本[第一辑]》,大象出版社2019年版,第214页。
3.李振纲:《<周易>的大生命世界观》//王学典,徐庆文,郑长玲:《第八届儒学大会学术论文集》,文化艺术出版社2018年版,第256-260页。
4.周鹏鹏译:《易经》,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5年版,第6页。
5.庄周.《庄子》·《秋水》,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5年版,第127-139页。
6.沙冒智化:《诗人是我的重要身份》,《文艺报》,2022年4月8日。
7.王芷菁:《禅宗:现代汉诗的形式——以废名、洛夫为例》,《星星》,2020年第5期。
8.拉尔夫·瓦尔多·爱默生:《论自然》,中国出版集团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10年版,第5页。
9.拉尔夫·瓦尔多·爱默生:《论自然》,中国出版集团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10年版,第4页。
10.魏春春:《身体的挣扎与语词的凌厉——沙冒智化诗集<时光的纽扣>简说》,《西藏文学》,2019年第5期。
11.拉尔夫·瓦尔多·爱默生:《论自然》,中国出版集团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10年版,第15页。
12.拉尔夫·瓦尔多·爱默生:《论自然》,中国出版集团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10年版,第18页。
13.海德格尔:《路标》,商务印刷馆2014年版,366页。
14.沙冒智化:《诗人是我的重要身份》,《文艺报》,2022年4月8日。
15.杨碧薇:《诗性克制无我》,《星星》,2020年第5期。
原刊于《西藏当代文学研究》第八辑

王四四(1978-),男,汉族,甘肃陇西人,西藏大学文学博士,广西民族师范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新诗、民族文学、西部文学等。

沙冒智化,藏族,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出生于甘肃卓尼,现居拉萨。作品发表在《人民文学》《诗刊》《十月》《中国作家》《民族文学》《西藏文学》等刊物,入选中外多种选本,被译为英、德、日、韩等多语种发表。出版有藏汉双语诗集《光的纽扣》《掉在碗里的月亮说》《担心》《梦之光斋》《厨房私语》《月亮搬到身上来》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