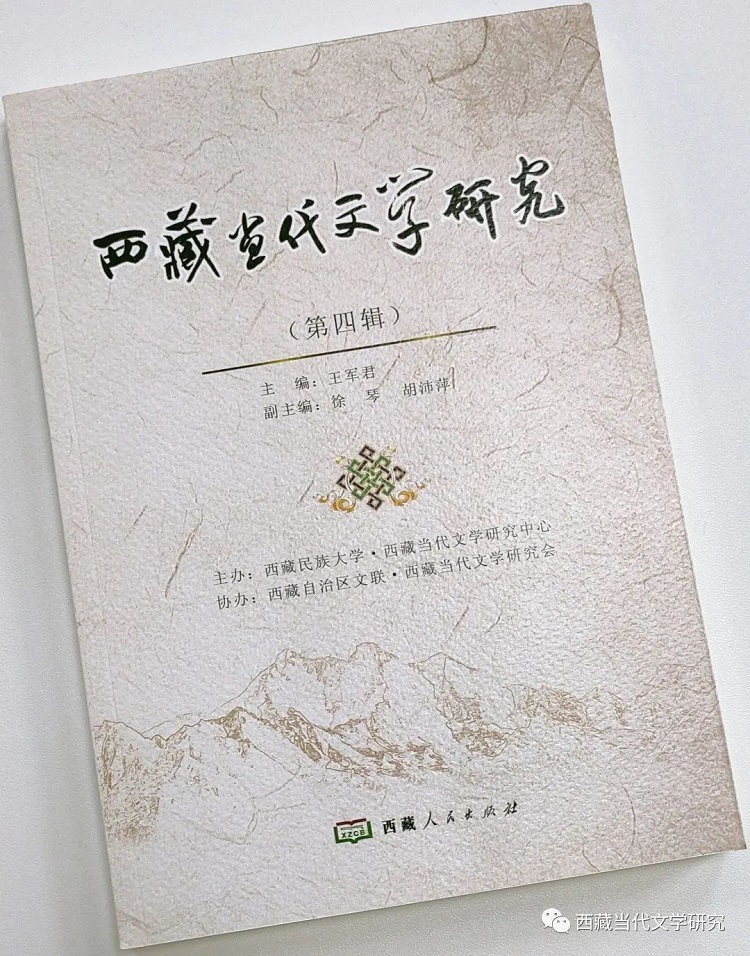
米兰•昆德拉说:小说是对存在问题的探索。对一个作家来说,这种存在问题会体现为如何理解生活,如何应对生活的挑战,以及如何思考个体与生活之间的关系。《强盗酒馆》是次仁罗布2020年出版的一部短篇小说集,这部作品植根于作家对西藏历史与现实问题的深切体验,收录的八篇小说从不同的侧面给我们展现出各具特色的人生经历,通过一个个不同的故事呈现出一个极富藏文化特色的、多样化的文学世界,其中也体现出作家理解生活、思考生活的独特方式。
小说集给我们展现的是一个充满不幸、苦难而又坦然、平和的世界。如果说人生总是充满了不幸与苦难,那么如何面对苦难、如何确立生存的意义就成为必须思考的问题。由此出发,作品以细腻的笔触建构起一个苦难的世界,并尝试从三个方面思考和探索了面对苦难的方式,这构成了《强盗酒馆》内在的叙事逻辑。
一
苦难一直是藏族文学的一个主题。诚如次仁罗布所说,“我们藏族传统文学里,很多都是在宣扬这种苦难的,已成为一个传统叙事的主题。”在次仁罗布不同时期的小说创作中,也始终表现出对人生苦难的敏感。《强盗酒馆》汇集了作者2009至2018年间发表的八个短篇小说,基本能够反映作者十年间创作的总体面貌,其中苦难是贯穿这些创作的一个重要线索。作品正是通过这一系列不同的故事,以叙事的方式建构起充满苦难的人生,而作品对苦难的呈现也显现出作者对人生的理解。
在小说叙事中,次仁罗布关注的是西藏底层民众的生活状态,或者说是底层生活中的苦难。八篇小说涉及到西藏的历史与现实,过去、现在与未来,其中既有民族历史转换的宏大背景,也包括个体生命的挫折和情感的无奈。外敌入侵的伤害、人情的冷漠、失去亲人的痛楚、生活的迷茫……所有这些都体现在一个个鲜活的个体之中。正是在这些“小人物”的身上,折射出生命本身的苦难底蕴。
《曲米辛果》具有宏大的历史背景,取材于百年前英军入侵西藏的那段独特历史,并从个体的角度展现出西藏底层民众对入侵者的反抗。由于双方力量的悬殊,这种反抗也体现出时代洪流之中个体与民族的悲剧性命运。小说叙事的个体化视角以及对英国人埃德蒙•坎德勒《拉萨真面目》的摘录也使得叙事更具现场感和生动性。可以说,这篇小说是以个体性的方式反映出民族的苦难与伤痛,以及对于民族苦难的反思。
《奔丧》的故事涉及到一名进藏的解放军与当地女子情感、生活的种种纠葛。两人成家后育有子女,但“父亲”最终选择返回了内地,并始终处于背离妻子和子女的强大心理负担之中。而他留下来的子女则需要在艰难的处境中寻找自己的生活,命运坎坷,苦苦挣扎。这个故事涉及到了历史和家族的苦难。
《八廓街》包含几个不同的故事。八廓街位于拉萨市的老城区,是一片具有浓郁藏族生活气息的旧街区。小说作者次仁罗布就在八廓街出生、成长,熟悉这里的每一个角落及其在历史中的转折与变迁。《八廓街》就是对发生在这里的故事的记录。《强盗酒馆》选择了《八廓街》中的三个故事,分别针对三个人物做了片段性的描绘,以底层个体的命运展现出八廓街在六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的历史景象。这是西藏历史上的一段特殊时期,传统宗教的影响受到冲击,人们进入到了一种世俗化的生活之中,当时狂热的政治斗争也直接影响到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在这一背景下,底层民众的命运也开始发生深刻的变化。
作者显然注意到了西藏社会变迁给底层民众生活带来的深刻变化。这里有嘎玛和益西在家庭生活中的吵吵闹闹,有旧式贵族朗杰晋美在时代转换中的不幸遭遇,也有美丽的梅朵在生活中的屈辱和挣扎。这些人物尽管身份不同,经历各异,但都感受着生活中的痛苦,承受着个人命运中的种种苦难。
《兽医罗布》的故事有着更为具体的历史背景与时代状况。作品中始终包含着牧区和县城两种视角和两种价值判断标准,这两种标准在很多地方看起来是矛盾的,而罗布就处在这两种价值标准的矛盾之中。作品中罗布对永青的帮助在牧区看来天经地义,正如小说中写道,“当我们告诉他兽医罗布在县城还有个老婆时,牧民朵儿古往地上啐了一口唾沫,续上一根烟,不屑地说,那有什么?在牧区几个姐妹就一个男人,或几个兄弟就一个老婆。再说,永青也没有让罗布答应娶她呢!我们有我们的生活方式,你不能以你们的标准来说这个对那个错,几百年来我们的祖先选择了最适合的生存方式。朵儿古说的也在理,自然环境、生存条件决定了婚姻的形式,我们只有包容和理解。”但这样的行为显然无法获得县城的认可,罗布也因此错过了多次提升的机会。最后在雪灾救援中,罗布带领救援队员赶到放牧点帮助牧民转移,自己却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但这样的英勇行为也因有人反映他存在生活作风问题而无法获得官方的表彰。
可以说,作品几乎篇篇都在描绘生活的痛苦与不幸,展现出个体在面对苦难时的渺小、坚忍与承受。这些苦难,或是来自于历史,或是来自于特定的时代,或是来自于贫困,或是人与人之间的利益算计与勾心斗角。可以说,它们从不同的角度呈现出了人生的苦难底蕴。
当然,文学中从来不缺少痛苦与苦难,文学与人生的苦难向来就有着不解之缘,“发愤著书”“穷而后工”也一直是中国传统文论中的主流。但文学的意义并不在于对苦难的外在呈现,更在于对苦难的理解和反思,并提供出面对苦难的独特方式。也就是说,苦难叙事的意义并不在于说人生是苦难的,更重要的是如何来面对苦难。
二
《强盗酒馆》对于苦难有着深刻的体认,并给我们提供了三种面对苦难的方式。通过这三种方式,我们能够接受和面对充满苦难的人生,能够找到苦难之中人生的意义。
第一,苦难的普遍化,将苦难作为人生的常态。
一般来说,对待苦难,我们可以进行反思和批判,寻找苦难的社会历史原因,并尝试加以消除;也可以将苦难看作是偶然事件,看作命运的不公,对此进行个体化的控诉;当然也可以将苦难看作是人生常态,是人生的本来面目,由此坦然接受,在苦难中寻求救赎与解脱。《强盗酒馆》显然走了第三条道路。
我们看到,在对苦难的理解上,作者从不会局限于一时一地,也无意将这些苦难归因于特定的历史与时代,并由此引向对特定历史或现实的反思与批判。相反,小说总是尝试从一种更加久远的视野来看待这些人生中的不幸,去除其中那些特殊、具体、偶然的因素,使之普遍化为人生常态。因此苦难就成为人生中必然的一部分,接受人生也就意味着坦然接受人生的苦难。
小说中的苦难固然有其历史、社会乃至个人的原因,如《曲米辛果》对历史的追溯、《奔丧》《八廓街》对特定时代的反思、《叹息灵魂》对个人命运的展现等等,但作者在叙事中并不强调、甚至会有意无意淡化这些苦难的具体社会历史背景和条件,不将其看作具体条件下的特定事件,而更愿意从一个更为宏观的人生视角来审视发生的事件,将苦难看作是生活的常态,或者说,是人生的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这一点也显现出藏文化对人生的独特理解。
另外一些小说,如《强盗酒馆》《红尘慈悲》《长满虫草的心》等并没有突出明确的社会历史背景,这使得其中所描绘的人生苦难似乎更具有了某种普遍性的意义。《长满虫草的心》描绘了盗挖虫草的小偷被人发现,并被溺死。他的魂灵看到了自己死后同伴之间为了各自利益的相互算计,也看到了家人在听到他的死讯时所关心的只是各自生活条件的改善。这篇小说体现出作家对人性的深刻思考。人性之中固有的自私、贪婪使得小说中所描绘的一系列事件具有了存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体现为人生的常态。
如果说苦难即人生,那么追问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苦难就是多余的、毫无意义的。由此我们可以理解小说对具体社会历史背景的淡化处理。在这样的人生中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坦然接受苦难,承受苦难,这样才能获得生存下去的力量。
小说集中的开篇小说《强盗酒馆》颇具特色。故事并没有明确的地点,只是表明这是在“城市的边缘”。“强盗酒馆”的声名来自于那些诡异的传说:醉酒醒来,脚上的皮鞋会变成一双破球鞋;明明靠墙醉倒,醒来后却和一个女子躺在床上;离开酒馆时,自行车的座椅和轮子早已不翼而飞;本来已经身无分文,离开时却发现口袋里平白无故多了几百元钱,等等等等,不一而足。所有人都对这类事情习以为常。在这个边缘的地方,似乎充满了慵懒、沉醉、散漫,人们可以放下生活中的种种规则与束缚,以坦然的态度面对种种突如其来的事件。小说中,面对祖传银碗的丢失,酒馆老板央金的态度是,“在我的酒馆里哪个人没有曾经丢失过东西,差不多人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现在轮到我也是很自然的。为了消除心头的气愤,我就骂一声:你这该死的贼,做活够利索的!”她所做的只是“再次端起酒杯把酒喝完。”
强盗酒馆无疑是一个隐喻。生活中的灾祸与痛苦是自然的存在,就像强盗酒馆中盗窃与丢失也是自然而然的,人人都习以为常。某一不幸事件的发生只是它恰好出现在了此时此地,恰好被我们遇到而已,因此完全没有必要耿耿于怀。对人生中那些必然发生的事件,最好的态度就是坦然接受,继续这世间的生活。
这篇小说可以说代表了次仁罗布小说创作的一个基调:对底层生活的描写,将苦难还原为生活的常态,由此以坦然的态度来面对人生的苦难。这一思想在之后的一系列小说中得以扩展和深化。
第二,着力发掘苦难之中的温情。
当然,小说也并非是在一味地赞颂苦难,而是突出了苦难之中的温情,这使得充满苦难的人生变得更有温度、更值得人们留恋。
《红尘慈悲》的故事发生在觉如,但这个地方和西藏其他的地方并没有本质的区别,作者也并不强调这一地方的特殊性,反倒是在叙述中力图将故事作为一个普遍的故事来讲述。作品一开始就告诉我们,“今生与你相遇的人,肯定是前世跟你有过关系的”,这是一个暗示,即不会局限于此时此地来理解发生的事件,而是把它和某种神秘的力量相联系,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超越生死的视角。
作品讲述了经历家庭变故之后,“我”如何挣脱出来,获得生活的意义的故事。“我”最终到了拉萨,绘画唐卡让“我”开始了完全不同的生活。但觉如仍然是值得留恋的,那里阿姆对爱情默默的隐忍与坚守让人动容,阿姆的充满爱与慈悲的眼神也成为“我”此生的寄托。作者的创作仍然在淡化社会历史背景,并更为明确地从一种宗教式的眼光来审视生活中的事件,更加强调此生中爱的价值。对此生的留恋与感动与对此生此世的超脱,看起来似乎是相互矛盾的要求,但却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整合在了一起,体现出生命的温情。
小说《奔丧》对作者具有特殊的意义。次仁罗布曾说,《奔丧》中“我”的原型就是自己。父亲是一名解放军进藏军人,在西藏和当地的女子结婚并生育了子女。但父亲最终回到了内地,再也没有回来。父亲一直生活在对妻子和子女的愧疚之中,而“我”也对父亲充满的怨恨。小说讲的是一个和解的故事。在面对父亲的死亡时,“我在哀乐的催化下,大颗大颗的泪珠滚滚而下,深深地向父亲鞠躬。我在心里告诉他,我原谅了他的过错,我要把心头积攒的怨恨、愤懑都剔除掉。此时,我仿佛听到父亲的一声长叹,这叹气声从我的灵魂上蹚过,拨动起我内心的爱来。我长时间地沉醉在这种酥软、柔绵的爱里,身心得到了净化。”在这一时刻,爱超越了怨恨,赋予生命以独特的温度和应有的价值。
或许,正是这种生活中的温情,才能让人们在苦难中得以坚持下去,才能给人们活下去的理由。同时,温情也使得人们能够以一种坦然的态度来看待苦难。的确,作品中我们能够时时感受到那种对待生活坦然的态度,但又不是超然于生活之外,而是就在生活之中,饱含着对生活的眷恋与温情。
第三,从死亡的角度反观人生,将苦难作为一种人生的历练。
文学是特定文化的产物和结晶,不同民族的文化总是会渗透到该民族的文学表达之中,体现出本民族的精神力量。藏文化中的死亡观念在根底上影响着《强盗酒馆》的苦难叙事,小说总是从死亡的角度来看待人生的苦难,在对死亡的了悟之中找寻人生的意义,同时坦然面对之前的那些挫折与苦难。
《叹息灵魂》也许最能体现次仁罗布的创作特色。父亲的突然死亡给家庭带来了巨大变故,“我”最终离家出走,四处流浪。经历了妻子难产、家庭乱伦、被人包养、生意破败等一系列变故和苦难,终于在面对死亡时获得了灵魂的寄托,最终成为了一名天葬师。这是一个灵魂成长的故事,人世间的的一切其实都是微不足道的,恰恰是死亡使得生命获得了真正的意义,正如小说中所说,“无论他们生前多么的有钱有势,或多么的贫寒穷困,只要躺到那块石台上面,一切顷刻间化为乌有,这可能就是尘世给我们的最大公平吧!”这是面对死亡时对人生的了悟。在这一刻,之前所经历的一切苦难都成为了一种人生的历练,都具有了自身存在的价值。
次仁罗布曾说,“‘当我每天都在迎接死亡的到来时,还要什么可以让我慌乱的。’这是藏族文化教我学会内心平静的方法,也是一种放弃俗世纷争的方法。这并不意味着妥协,只是凭着自己的能力干好自己分内的事,这是一种责任,也是你的义务。”可以看出,对死亡的自觉使得作者能够以一种超越性的眼光看待世间的一切纷扰、不幸与苦难,获得心灵的平静与解脱。
这种对苦难的超脱也体现在小说的叙事方式之中。《强盗酒馆》中的多篇小说都采用回忆的方式展开,如在《兽医罗布》中,不仅有讲述者的回忆,还通过两位女子的回忆交代了故事的许多前因。《叹息灵魂》也是通过对自身经历的回忆来组织整个故事。可以看到,回忆实际上是作家的一种习惯性的写作手法。正是在回忆之中,人们才能摆脱当时情境的局限,事件的意义才会清晰地展现出来,由此体现出一种超越性的眼光。
除回忆之外,小说中时时会引入灵魂参与叙事,这也是一种独特的叙事视角。灵魂叙事既能从外在的角度讲述所发生的事件,同时又能以亲历者的身份深入描绘事件中的切身体验,使得整个故事既突出了现场感又能展现出某种超越性。如《曲米辛果》的叙事就是通过亡魂的讲述还原了百年前英国远征军入侵西藏的情景。这是对于那段历史的追溯,但作品中生死的界限是模糊的,使得这段历史显得既真切,又飘渺。《兽医罗布》的故事看起来是一个现实的故事,但小说的结尾颇有意味,“罗布”的再次出现给这个充满现实意味的故事增加了某种神秘色彩,同样展现出一种高于此世生活的视角,充满了悲悯与温情。可以说,灵魂叙事拓展了小说的文学世界,构成了现实世界之外的另一种存在状态,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摆脱现实世界的出口。另外,除了灵魂叙事之外,小说在叙事过程中往往会设置一些特殊的人物,这样人物往往代表着某种超越性的视角,在特定条件下会给主人公以引导,完成特定的叙事任务,如《红尘慈悲》中的唐卡画师桑珠亚培,《兽医罗布》中算卦的老僧,《奔丧》中的贡布喇嘛,《叹息灵魂》中的天葬师等等,这些都使小说具有了某种超越现实的力量。
通过这些叙事方式,小说让我们能够超越世俗生活,从死亡的角度反观人生,由此那些现实的苦难就会成为实现最终解脱的必要阶段,也获得了自身存在的价值。
三
以上我们研究了《强盗酒馆》中的苦难叙事。总的来看,苦难的普遍化、对苦难中温情的开掘以及从死亡的角度审视苦难,成为《强盗酒馆》思考人生、面对苦难的三种不同的方式。统而言之,在作为人生本然状态的苦难之中,我们会时时发现苦难之中闪露出的温情,它们使得苦难具有了某种温度,使得人生具有了某种价值。而正是因为温情的存在,苦难似乎也变得可以忍受。同时,当我们不再执着于人生坎坷的过程,而是审视人生的终点,就会发现死亡的存在。在死亡的笼罩之下,生命中的苦难也就变得微不足道。而且,苦难恰恰是通向死亡、了悟生命真谛的必经阶段,这样苦难就具有了肯定性的价值。如果说,生存本身就体现为海德格尔意义上的“现身情态”,那么这三种不同的方式实际上也对应着三种不同的情绪体验:苦难的普遍化带来的是面对苦难的坦然态度,温情的开掘带来的是人世间温暖的情感,从死亡对苦难的审视带来的则是平和的心境。小说中这三种情绪体验往往交织在一起:坦然之中有着对生的眷恋与温情,温情中透出平和的心境,“向死而生”的平和心境又体现为坦然的人生态度。这些都体现出作品对苦难人生的深切体认和思考。
进一步来看,苦难的普遍化更多地体现在知性的层面,即认识到生活之中总是或者必然存在着苦难;温情的开掘更多地体现在情感的层面上,感受到对生的眷恋与温情;死亡的审视更多地体现在精神的层面,体现出精神的平静与超脱。因此,对苦难的三种态度实际上体现出人的三种存在方式,其中既包含着对生活的深切眷恋,也渗透了作者对生活的透彻了悟。很显然,只有学会接受生活中的苦难、痛苦与不公,才能达到最终的平和。在苦难之中,我们可以发现生命的温情,可以发现自身灵魂的成长,也能了悟生命的本来面貌。
事实上,小说中这三种态度有着共同的前提:苦难即人生。这一观念有佛教思想和藏族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但由此带来的问题就是,作品实际上并不去追问苦难的原因,只是无条件接受苦难,并在这一前提之下寻找人生的意义。苦难的普遍化使得追问苦难的原因变得毫无意义,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将其作为一个事实接受下来。苦难的温情化也使我们对苦难有了某种情感上的认同。苦难作为人生历练也给苦难赋予了某种肯定性的价值。所有这些都导向了对苦难的接受。正如作者所说,“我认为,人生就是由无数的缺憾组成的,在漫长而又短暂的人生中,我们在向往幸福、享受欢乐的同时,更需要不气馁不抱怨地去学会接受、承担生活给予我们的磨练与苦难。”可以说,对苦难的接受构成了小说思想的基点。小说从不想和苦难的人生抗争,而是尝试接受苦难,发掘出苦难人生中的闪光之处,从过来人的视角回望那些苦难景象。这就消解了面对苦难时可能有的种种激烈情绪,因此小说叙事始终体现出一种平和的基调。这构成了作者的创作特色,但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也给小说创作带来了某种限制。
与对苦难的无条件接受相应,在小说中,个人始终是渺小的。故事的开端总是个人被卷入生活的苦难之中,就像《叹息灵魂》中父亲的突然死亡、《红尘慈悲》中家庭的变故、《长满虫草的心》中突然被溺亡,这些事件的发生完全不受个人的控制。而接下来故事的发展也没有个人意志的参与,更像是一系列的苦难不断地落在主人公的身上,推动着他完成自己的命运轨迹。而最终对苦难的超脱也更多来自于某种外在力量的辅助,如上文提到的,在不同的小说之中均会出现某个引导性人物,帮助主人公在苦难之中完成灵魂的成长。因此,故事的开端、发展和终结实际上并不受个人的推动,而是某种命运的逻辑在起作用。这使得小说体现出某种“必然性”的力量,体现出生命背后某种更为恒久的力量。但由此付出的代价是,在人物塑造和故事讲述上不无类型化的痕迹。很显然,如何处理苦难与个体之间的关系,如何在对苦难的讲述中表现出个体的力量,事实上仍然是一个问题。
原刊于《西藏当代文学研究》(第四辑)

刘凯,文学博士,现为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文艺学、美学研究,特别是德国古典美学及二十世纪文艺学、美学理论研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两项,出版著作三部,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多篇学术论文。

次仁罗布,藏族,西藏拉萨市人,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西藏作家协会常务副主席,《西藏文学》主编,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代表作有《杀手》《界》《阿米日嘎》《放生羊》《神授》《八廓街》等小说,《放生羊》获第五届鲁迅文学奖,长篇小说《祭语风中》获中国小说协会2015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第三名。作品被翻译成了英语、法语、西班牙等多种文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