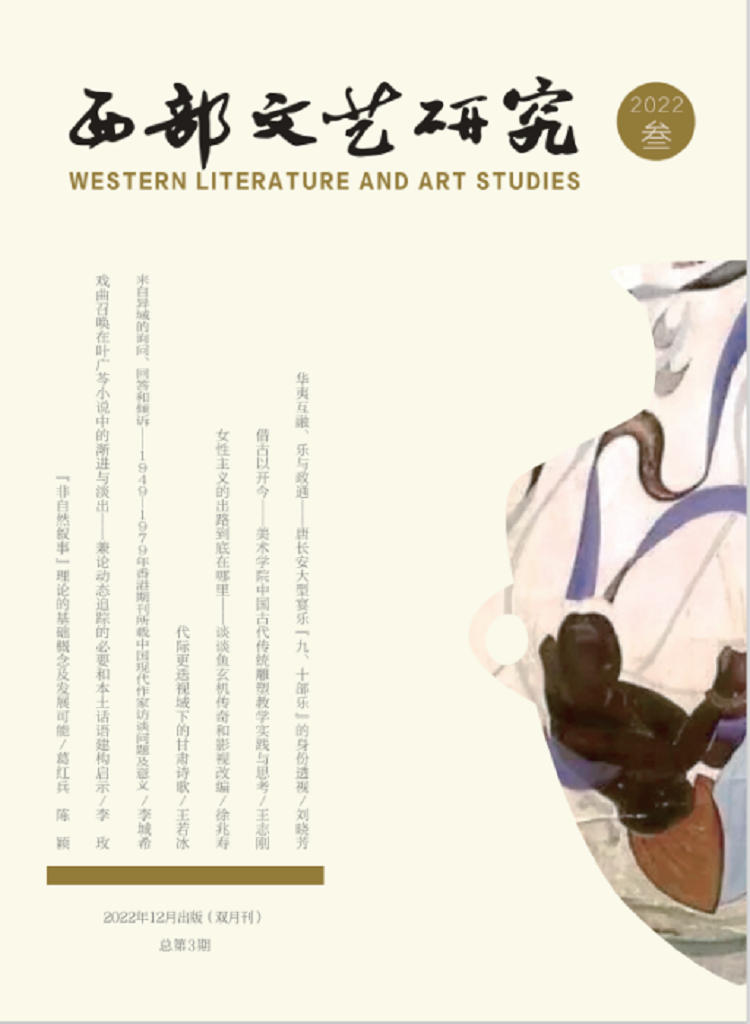
许多文学家心中都有一个自己的文学世界,70后甘南籍藏族诗人扎西才让亦是如此。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开始创作至今,在诗歌、小说、散文等方面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尤以诗歌见长。2010年起,出版的诗集有《七扇门:扎西才让诗歌精选》《大夏河畔》《当爱情化为星辰》《桑多镇》等。不难发现,这些诗歌均以扎西才让的故乡——甘南进行创作。甘南是多民族融合交汇的地方,许多藏族作家的文学作品中显示出了同质不同向的写作模式,其中完玛央金散文中的甘南对地域经验进行审美的提纯,王小忠的小说则将甘南地中的时代性进行观察和剖析。近三十年来,扎西才让的文学主题始终是故乡甘南。故乡之于扎西才让的意义不仅仅是地理空间概念,更是萦绕在他心中无法割舍的血脉根系。无论是蜿蜒曲折的大夏河还是人间百态的桑多镇,扎西才让在其中都寄托着他对故乡天下黄河的文学期许。或许是为了突破自我写作的空间单一性,扎西才让试图从甘南历史长河中发掘新的写作资源,为人们呈现出一个时间序列中的甘南景观,这或许就是《甘南志》的写作缘起。时间性与空间性的融合,使得《甘南志》表现出立足地方性的超地域性的文化特质。
地域性与超地域性
扎西才让出生在甘南,成长在甘南,在大学毕业以后又重回甘南,又因甘南独特的地理环境,因此在作者的作品中呈现出了独特的甘南地域性特征。首先从《甘南志》的题目命名来看,本身就有鲜明的地域性特征,并且作者将甘南放入一千万年的历史长河中,通过人类诞生,部落崛起,藏传佛教发展等众多视野,构建了藏族人民的生活图景,进而又将“光化公主”“麻娘娘”“格萨尔王”等民间传说穿插其中,使得扎西才让的作品呈现出了鲜明的地域特色。但作者曾说:“文学作品的地域化、民族化倾向,虽然有其意义和价值,但我个人始终认为,文学的核心任务,应该是发掘人性,表现人生、呈现生存的多种可能性。”显然,随着作家阅历的丰富,创作也愈发成熟,扎西才让作品的“地域性”渐渐发生变化。因为,甘南只是作家创作的一个起点或者支点,他并没有停留在对甘南外在的地域性符号进行书写,而是从自己熟悉的“桑多镇”里跳脱出来,将自己的生命进行缩小并融入到一千多万年的历史当中,说出了自己对于先辈的怀念,对土地的热爱和对于人生、人性的无限探寻。因此,“甘南”或这片地域不再是地理空间的概念,而是超越地理空间上生成的具有自我寻找,弥补世间不足并最终使得自己精神回归的超越时空的土壤。
《甘南志》中的地域性是非常明显的,但是超地域性又是贯穿始终的,看起来二者似乎相悖,但从另一方面来说,脱离了地域性的超地域性,会使得诗歌没有实际条件作为支撑,仿佛空中楼阁,而失去超地域性的地域性又会使得诗歌的创作走上死胡同,或成为一潭死水,了无生趣。这种情况下,平衡二者的关系尤为重要,因此作者采用了消隐“我”为主体,将“我”化为“他”“他们”“你”“你们”“我们”的创作方式进行创作,这样的好处就在于通过对抒情视角的转换,把“我”和叙述内容进行有意的拉远,不仅能客观的对甘南历史进行描述,而且还能不动声色地通过他人之口表达我对人物、历史的态度和思考。但是仅仅谈人称的变化则对于文学评论似乎没有太大意义,因为就文学创作而言,每一部作品都是作家对于人生思考和追求的一种文学式的表达。其实这种“隐匿”,不妨可以理解为是一种身份扮演,对自我面目的不同塑造,就仿佛带上了一幅“面具”。这种面具手法可以追溯到爱尔兰诗人叶芝的创作中,叶芝面具说的主要观点是用面具作为“第二自我”或“反自我”,也就是将我化身为“你”“他”“他们”或者历史中的某一个,都是作者“我”的另一面。这样既表现了个人经验的创作,又避免自我中心。作者在历史长河的发展中,讲述了从远古时期至今将近一千万年历史记忆中的伟大将领、亡灵怪神、鸟鱼虫兽等世间万物的故事,因此《甘南志》构成了扎西才让的一个多元主体以及元抒情的世界。
所以,在《甘南志》整部诗歌的创作上,可以清晰的看出,就叙述人称而言,以第一人称进行叙述的寥寥无几。但是这样的创作方式其实是有迹可循的,纵观扎西才让的作品,2010年的诗集《七扇门》中,几乎都是以第一人称进行抒情,在2018年的札记《诗边札记:在甘南》中,以“我”为主体进行叙述的只有卷四的11篇,仅占整部作品的约百分之七。在2019年的小说集《桑多镇故事集》中,一直持续隐匿自我的写作方式,再到2020年的诗集《桑多镇》中,这样的创作已经初具规模,而最终在《甘南志》中,“隐匿”自我的创作方式已经达到最高点。很显然,从2010年到2018年,作者的创作心境产生了很大的转变,可能随着作家阅历的不断丰富,时代的急遽变化进而使得作家在创作形式上有所变化。
首先体现在外部的变化,即两首相似诗歌抒情视角的变化。比如《甘南志》中的《在世的倒影》一篇在诗集《桑多镇》中就已出现过,但这绝不是简单的雷同,两篇相比而言,在《甘南志》中的这一篇似乎是对《桑多镇》一篇的提升和结果的呈现,在《桑多镇》中的《在世的倒影》中,抒情主体是“你”,但从“群鸟已隐退山林,野兽深匿了它们的足迹”中都可以感受到作者的一种孤独的情感,在诗歌最后则是悲情的结尾:“你终会离开这里,离开这里...我想你肯定厌倦了这秋风翻动下的无穷无尽的日子”。但在《甘南志》的《在世的倒影》中,抒情主体成了“一个僧人”,“僧人”是佛教的表现,相比于“你”这个没有特定概念的主体来说,更能从“僧人”的身上,看到作者对于植根于这片土地上的藏传佛教的执着与追求,“僧人”在这里,是作者“我”的另一面,而我用“一个僧人”智慧,通透的品性来彻底消除了之前悲伤、焦虑和迷失的状态,这时候结尾“初时清晰,后来,就被泪水鼓荡的模糊不清了”中的泪水并不是之前悲伤、感到迷茫的泪水,相比而言,多了一份释怀和感激,作者通过视角的转化,让自己对于历史,对于生命有了更豁达的态度,当我们细读时,一种强大的共性的力量在我们体内油然而生,让我们对甘南这片土地有了更深刻地认识,对于我们民族有了更崇高的敬意。还有《桑多镇》中的《死屋中的老鳏夫》和《甘南志》中的《死屋中的老鳏夫》进行对比,抒情视角也已经从“我们”转换到“孩子们”。“我们”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很可能就是三五结群的成年人,当“我们”看到“一张惊恐又悲伤的脸”之后,更多的是接受和坦然。但是对于“孩子们”来说,看到这样的一幕,除了惊慌失措之外,更多的是产生了猎奇的心理。因此,在后面对老鳏夫的经历和生活作了简述,他不仅是“士兵中的士兵,男人中的男人”,而且还曾“驾驭过三个如花似玉的女人”,这都是孩子们对心中很优秀的那一类人的幻想。借助小孩子的视角,表达了我对于曾经经历过战争的军人感到骄傲和自豪,同时也对他晚年不幸的境遇感到悲伤。
其次,体现在视角往往在诗歌的内部进行流动和变换。当诗人隐藏在面具后,是以面具抒情者的内视角进行叙述,当诗人跳脱出面具后,就又以诗人的身份进行叙述。在《取代》中,首先我以一个历史见证者的视角对于洮州猎人“误杀”妻子的画面进行了描述,整个过程是冷静而又坦然的,但是在最后说话的口吻已经成为猎人死去的妻子的口吻,“让我还原一段1949年8月的画面吧!”使得整个故事变得惊悚而又离奇,仿佛猎人的妻子已经知道这本就是一场有预谋的暗杀。在《姑姑的爱情》中,通过“她”向“我”视角的流动,也表达出了自己作为历史的局外人时,总是可以冷静的叙述,但是如果将自己深陷其中,那么情感将势不可挡。面具化的抒情方式,使得作者游离在不同的面具下,完成了自我的“隐匿”,这种“隐匿”自我的表达方式,是作者在阅历不断丰富后,对于人生思考的一个结果,其实人生就是这样,能“隐”的人必将懂得不露锋芒,不露锋芒则可以使自己走得更远,作者显现出独有的这种魄力就是“超地域性”的力量。
神性与俗性
甘南独特的地域和文化资源给予了甘南诗歌一片在高山雪域上安静和自给自足的沃土,基于青藏高原的特殊地貌和藏传佛教的信仰之间,扎西才让的诗歌也不例外,他笔下的高山、河流等世间万物都天然地笼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扎西才让诗歌中的神圣性往往不是生硬的,而是通过他的描写,整首诗歌显示出一派和谐的样子,日常事物与生活之外的事物形影相伴,存在之物和超验之物和谐共存。“男孩从草地随手采了一束苏鲁梅朵,投在水里,河水停止喧嚣,慢慢地向两边分开。待到男孩到达彼岸,河水相合,重新发出巨大的轰鸣。”《分水过河》在《在世的倒影》中,诗人将眼前的檀香树赋予了神性,“檀香树下,朝觐后的晨妇,大梦初醒就有了身孕。”仿佛檀香树这棵自然存在的生物走向了超验体系,将女性生育的特征和檀香树联系在一起,使得他被赋予了超验的神性,并且还透露出了生活往往是出乎意料的,不为我们自己所掌握的,“力大无比的洮州猎人,在森林里隐蔽下来,太阳落山时,他误杀了突然出现的妻子,——他把她看成那只高傲的麋鹿了”《取代》;在《甘南志》中还呈现了诗人多维度的书写空间,表现在现实的世界和古老的过去总是存在时空上的交叉。在《党项羌和西夏王朝》中,时间仿佛一架穿梭机,将我们放在现实和历史的重叠印记中,通过四组一问一答,将我们不断在现实和历史中进行转换,这里的“您问”和“答曰”可以看作是作者的自问自答,一边急于对历史的不确定找到合理的解释,一边又以看透世间万物的长者娓娓道来,作者二重身份的自由转换,将我们巧妙的带入这种二维世界;在《土官梦见亡兄归来》中通过和梦境中的死者进行对话,对于命运的不确定性也是以神圣的方式来展现。
扎西才让的“神圣”观念与伊利亚德在《神圣与世俗》中提出的“神圣和世俗是这个世界上的两种存在模式,是在历史进程中被人类所接受的两种存在状况。”也就是说,神圣和世俗并不是截然对立的,而是相互依存的。按照伊利亚德提出的“显圣物”一词,每一个神圣的存在都是通过日常生活中很普通的事情加以刻画从而显示出来的,比如对生活中的节日、人物的日常行为等进行分析,显现其神圣的遗存。在《莲花山风景保护区》中通过“我回忆莲花山的过去”、“我回忆莲花山的建筑”和“我回忆莲花山的由来”三段来写“我”对于莲花山的感情,也就是对于莲花的感情。莲花与佛教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佛教旨在普度众生摆脱苦海而从人生苦海的此岸到达极乐净土的彼岸,如同莲花出淤泥而不染,超凡脱俗。在《大德的侍僧》中“他从台阶上弯下腰,将一块青稞烙饼递给跪倒在地的乞丐”,“弯”“递”这一系列动作看出大德普及天下的善心。神圣和世俗相辅相成,不可完全孤立。作者从小在宗教浓厚的氛围中长大,身上流淌着宗教神性的血液,因此在成长的过程中,或多或少地继承了某些宗教遗产,可能是心理的或者行为的。比如在《文明之门》《创造》《部落的融合》中对于民族诞生的赞叹,都体现了作者于世俗生活中重建人、宇宙和自然界中原初和谐的渴望。
很多人认为,在工业化快速发展的今天,似乎大家都本着“金钱至上,利益为本”的原则误入了世俗的网,心中再无那份“神圣”。但是这样的说法似乎存在一个误区,那就是将神圣和世俗放入一个二元对立的世界中,成了非此即彼。但伊利亚德运用颇具心理学的“伪装”一词谈论神圣在世俗时代的遗存方式,他认为,尽管现代人常常宣称自己属于非宗教人,似乎已经脱离了神圣,但这只是意识层面的脱离,从日常行为来看,通常还在无意识下受着深刻的影响,只不过不易被察觉。比如许多家庭在新年来临之际都要在门上贴倒 “福”字,平日里也要贴门神、摆神龛。大多数民众尽管不信神灵,但还是会走进寺庙磕头烧香,本着趋利避害的心理,让这种神灵无处不在。但是神性不会从一而终地存在于民众的意识中,当他不灵验了,便会对他产生疑问。“人真的有罪吗?也许有也许没!”“人的灵魂真的会在六道中轮回吗?——也许会,也许不!人真的能被佛国的使者解救吗?——人,或许只能被自己解救。”《小索南的诘问》中,可见饱受战争的百姓再也无法相信“神”真的能将自己从苦海中救出。因为作者相信“肯定有光,能照亮他的灵魂”,可见作者对于这种神性的背离进行了有效的“修补”,给别人带来精神慰藉的同时,也使得自己对于本土佛教进行了有效的坚守。让这种神性的力量始终扎根在甘南这片土地上,形成了一种超越地域的精神力量。
回顾与坚守
一方热土,一腔热血,一世深情。故乡,通常是作家笔下歌之不尽的主题。作家在表现自己的乡土情结时,都有着属于自己的独特之处,如鲁迅笔下的鲁镇,沈从文心中的湘西世界,莫言记忆中的高密东北乡,等等无不如此。扎西才让说:“人一过四十,就想找到灵肉的归宿,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在这样的追问中,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了自己的处境——过去的四十多年,只是偏执地追问这三个终极问题的精神求索过程”。一定意义上来看,这三个问题的最终指向,就是自己的故乡——甘南。作者伫立在甘南大地,无论是蔚蓝的天空,辽阔的草原,还是历史长河中的历史遗存,在此时,都与他此时此刻的生命感受发生了激烈的碰撞,于是在回顾历史后依然坚守故乡,这才是超地域性写作的终极意义。
谈论故乡,那就离不开土地,土地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空间,费孝通“从乡村社区、文化传递、家族制度、道德观念、权力结构、社会规范、社会变迁等诸多方面深度解剖了中国乡土社会的结构及其本色”。断言:“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扎西才让很明显地认识到了中国人的根是土地,几千年来,农业社会积淀和人际关系结构模式的传承,让大多数中国人都和土地无法分割。扎西才让对于土地的感情是深沉的,这种感情体现在对于在甘南土地上万物的热爱和致敬。“西羌之地的青稞熟了。谁一进门就溘然而逝?谁将一个婴儿,托生在青稞的梦里”《西羌之地的青稞熟了》。远古之地的青稞,仿佛是我最原始的记忆,“婴儿”和青稞一样,都代表着最纯洁最原始的生命。在《高原异禽:树麻雀》中,对于“在洞穴、瓦片和房檐下筑巢,在农田里觅食,嬉戏”的树麻雀给予了赞美,这些具有强大生命力的麻雀,是引领我回顾历史、回望生命最原始记忆的指路灯。甘南大地上万物的生长都具有强烈的生命意识,随着时间的发展,甘南大地也在悄然发生改变:“地面上的建筑,也随之悄然诞生,双室相连的半穴居里头,住进了大写的人”《文明之门》,部落的形成,人类历史的开始,然而历史的发展、民族的的发展变革离不开的就是一代又一代历史人物的智慧与魄力,在《甘南志》中,扎西才让对历代部落领袖、英雄人物进行了深度的刻画。《无弋爰剑》中,这个叫无弋爰剑的戎人,在被秦俘为奴隶后流浪的过程中显示出了高原上应有的血性之气,他与大自然作斗争,与猛兽对抗,这样的胆识和魄力使得这个流浪的野人做了羌人的首领,扎西才让对这个戎人是肯定的,不仅对于他的魄力和胆识作了高度的肯定,更是看到了自己民族如此辉煌的过去,从而产生的民族自豪感;在《包永昌和他的<洮州志>》中对于包永昌呕心沥血的佳作《洮州志》中,包永昌这种“修志以资志,辩史以通鉴”的豁达胸襟更是深深地影响着作者《甘南志》的创作。对于历史伟人的赞赏和歌颂中,领悟到的是自身对于民族的热爱,从而达到心中的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但是甘南土地,并不是圆满的人间集合体,而是既糟糕又美好,既临近又遥远,既复杂又真实。
中国文学是一种源自土地、扎根土地的文学。但随着社会生产力、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使得产业结构在大幅调整,又由于商品经济的到来,让城市数量增多,势力范围更广,人与土地的密切联系随之断裂。在《牧羊人眼中的打工者》中,描述了曾经和我一起放羊的伙伴如今奔向那“遥远的青海,内蒙古和新疆”,对于“高楼”的向往使得“打工回来的人们,都像迷失了羊群的羔羊”,土地不断地被城市蚕食,城市也因此成为了土地眼中的“怪物”。这时候,对于血液和土地一脉相承的作者来说,作者拒绝了那些使他变得怪异的力量,在《野兽》中“他们的服饰是多么怪异:男孩子,有的夹克配马裤马靴...”“也许是诗歌的力量吧,他脱离了他的团伙”,这时候作者成为了真正的“守土者”。其实,作者不满的不是具体的哪一座城市,而是在控诉城市所象征的,对生命的蔑视以及对物质的无底线的欲望。在《来自欧拉的种羊》中,一群穿着皮袄的热情的小孩不竭余力的嘶喊着:“在它干了好事后,留下它的皮和肉吧,在它干了坏事后,留下它的血和骨吧”。《藏区市场》中,“现在堆砌如山的西瓜,等着被切食”,感受到了人欲望的膨胀。似乎只能通过占有欲来对躁动的现实世界进行反抗。人类欲望的膨胀带来的就是对土地的无限破坏,在《逝去的森林》中,对于甘南境内大片森林的破坏感到极度的惋惜与无奈。作者对于甘南土地的回顾和思考,使得这片平凡的土地上盛开了不平凡的花,显示出了比书写地域性更可贵的精神。
扎西才让诗歌的感人之处并不在于以甘南自然风光的优美来吸引读者,而是大胆地将甘南最真实的样子呈现在我们面前,不仅不隐藏甘南大地上的“痛苦和不幸”,而是在展现了最原始的风貌之后,依然歌颂自己的故乡。在《达娲央宗从飞机上俯视安果草原》《2015年的飞行者》《白色轿车狭路相逢》中对于甘南这个相对闭塞偏远的城市来说,交通的便利无疑让人更加值得兴奋;在《谁说世上没有好歌了?》《我们的新岁》中更是直接歌颂我们的国家,对于国家的精准扶贫,引洮济合供水工程等重大政策进行了记录和歌颂,彰显了作者作为一个甘南后人的骄傲和自豪,同时也是作为中华民族的一份子的骄傲和自傲,更加坚定了自己终将永远坚守甘南这片纯洁的土地。
山水景色只属于某个地域,而历史文化,却是可以超越地域的。文化从一个文明的高地流向另一个高地,在路途中被截留、被改造,历史从一个朝代走向另一个朝代,这其中留下的枝杈纵横,只怕比主流还要多、还要耐人寻味。这或许就是扎西才让创设时空交错的文学甘南之初衷所在,并诗意地表达出他坚守甘南大地追寻人类生命体验的文学诉求。
原刊于《西部文学研究》2022年第3期

王晓君,女,西藏民族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魏春春,男,山西怀仁人,文学博士,现为西藏民族大学文学院教授,从事当代藏族文学和西藏当代文学研究。出版专著《守望:民族文学的诗意创造》《新世纪藏族汉语文学“中国故事”话语实践研究》。先后在《民族文学研究》《当代文坛》《湖北社会科学》《阿来研究》《西藏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五十余篇,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一项、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一项。

扎西才让,藏族,1972年生于甘肃临潭,1994年毕业于西北师大中文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甘肃“诗歌八骏”之一,2019年全国少数民族“文学之星”、甘肃省“中青年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荣誉称号、第十二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获得者。著有作品集《七扇门》《大夏河畔》《当爱情化为星辰》《诗边札记:在甘南》《桑多镇》《桑多镇故事集》《甘南志》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