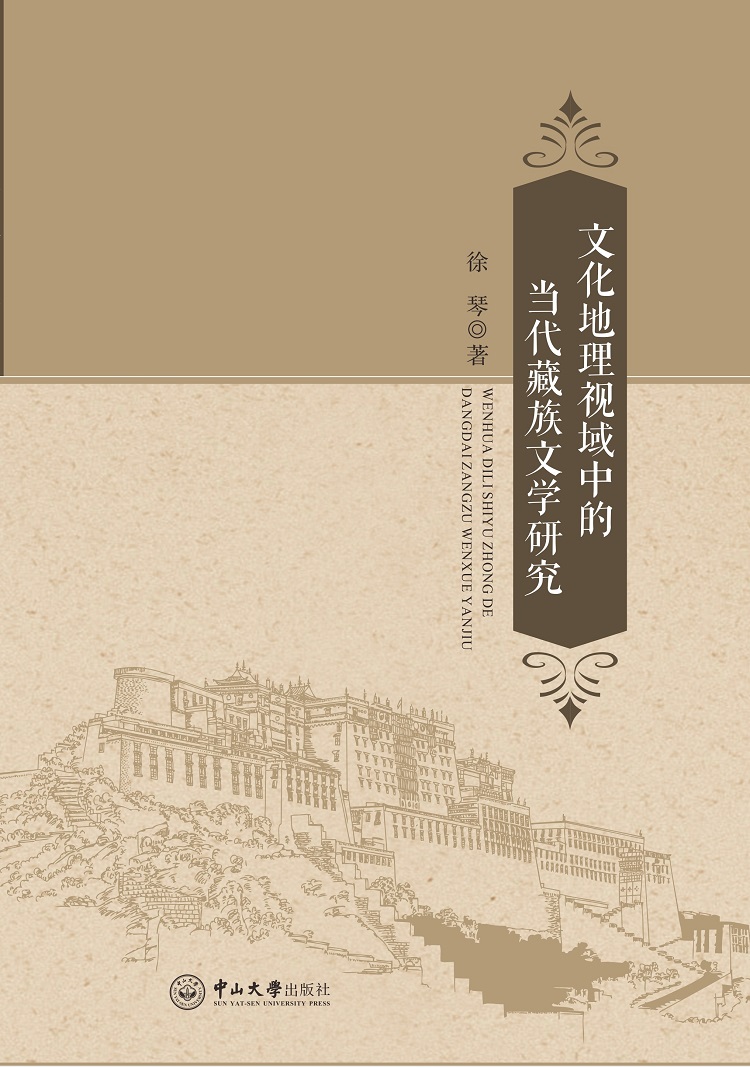
《文化地理视域中的当代藏族文学研究》
(徐琴著,中山大学出版社,2022年6月)
在当代藏族文学史上,央珍的创作具有独特的价值和意义。其短篇小说《卍字的边缘》获得第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长篇小说《无性别的神》获得第五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无性别的神》是当代西藏文学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被认为是一部“西藏的《红楼梦》”。作品以贵族德康家二小姐央吉卓玛特殊的命运、经历为线索,通过少女央吉卓玛的成长经历和内心感受,从侧面展现了二十世纪初、中叶西藏嘎厦政府、贵族家庭及寺院的种种状况,再现了特定时期西藏的历史风貌及现代化进程。
央珍很熟悉西藏的生活,在她笔下,西藏的风情风俗是自然而然的呈现,而不是为了吸引读者的眼光,与那些一味以西藏的神秘渲染来吸引读者眼光的作品有着天壤之别。同时,她的小说也与同时代的魔幻现实主义小说有很大不同,她认为西藏魔幻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家主要是进藏大学生和生活在内地的汉藏结合家庭的孩子,他们对西藏有一定的陌生感和疏离感,会对西藏的现象感到震惊和好奇,进而产生丰富的想象再加上本身的才华和艺术素养,所以产生了西藏的魔幻现实主义作家。而论及自己的时候,央珍说自己从小在拉萨长大,拉萨的一切对她来说是熟视无睹的,无从产生那种天马行空的想象1。她试图将真实的西藏在她的文本中呈现出来,在谈及其《无性别的神》时,央珍说:
“我在写这部小说的时候,力求阐明西藏的形象既不是有些人单一视为的“净土”和“香巴拉”,更不是单一的“落后”和“野蛮”之地;西藏人的形象既不是“天天灿烂微笑”的人们,更不是电影《农奴》中的强巴们。它的形象的确是独特的,这种独特就在于文明与野蛮、信仰与亵渎、皈依与反叛、生灵与自然的交织相容,它的美与丑准确的说不在那块土地,而是在生存于那块土地上的人们的心灵里。
而西藏作家的任务就是写出西藏人复杂而独特的心灵,写出在不同时代的彷徨和犹疑,痛苦和欣喜,而不是把他们简单化和标签化。”2
央珍拒绝对西藏的“简单化”和“标签化”的写作,她的创作试图呈现西藏世俗生活的真实图景,以普通人的肉身遭际来展现西藏历史的发展变化,有意识去建构民族的和自我的立场,这在当代藏族文学史上是有转折意义的。在《无性别的神》中,央珍以女性的视角将西藏大的时代变动通过小姑娘央吉卓玛的心灵感受呈现在读者面前,独特的女性视角以及从中所传达的深厚的民族文化内蕴使得这部作品意蕴深长。小说以央吉卓玛的成长经历来展开叙述,以其敏感细腻的心灵观照来呈现西藏的风云动荡。央吉卓玛的成长过程大致地分为四个时期:首先是被家人抛弃,离开拉萨之前。这一时期,她主要生活在德康府邸。由于在雪天降生,被说成是不吉利的人;弟弟因肺病夭亡,认为是她带来的灾难;父亲郁郁不得志也被看作是央吉卓玛造成的厄运。只有六岁的央吉卓玛已经听惯了别人对她所说的没有福气、不吉利的话语,她对一些不公的指责也已习以为常,但她的内心却是极为敏感的。当她从外祖母家的府邸住了一个多月回到德康府时,父亲病重,管家的“没有福气,的确没有福气”的话语使她有种刺心的痛,倍感凄凉,作品写小小的她“站在下马石边茫然环顾,在秋日的阳光下整座大院寂静冷清,散发出废弃的古庙般荒凉的气息。”3孤独的心灵感受到彻骨的寒冷。从此,她的行为开始改变,她不像原来那样刁蛮任性,对所有的一切感到茫然不安。父亲的死更让懵懂的她有了一种莫名的惆怅。父亲死后家境的衰落,母亲的忧伤,使得年幼的央吉卓玛陷入忧郁苦闷之中:“从此,央吉卓玛常常独自一人,静静望着天空中飘游的风筝,或者墙头的经幡,或者窗外夜晚的星星,会想出一些奇奇怪怪的问题,运气到底是什么东西呢?佛国到底在哪里呢?母亲为什么要哭呢?为什么过去常来家中玩的老爷太太现在都消失了呢?自己真的是不吉利的人吗?”4她开始思索自己的命运及周边发生的一切。第二个时期是在帕鲁庄园和贝西庄园时期。在这个时期,母亲抛弃她带着弟弟远走,央吉卓玛有了一种被遗弃的痛楚,即便是在睡梦中,央吉卓玛也害怕被抛弃,在她的心中,唯一的亲人就是奶妈:“奶妈呢?骡马队呢?都在哪儿?奶妈是不是也像母亲那样扔下自己远去?”5,年幼的央吉卓玛没有任何安全感。在帕鲁庄园仁慈的阿叔的怀里,央吉卓玛终于有了依靠和温暖,她和受到不公待遇的阿叔相互取暖,但久病的阿叔却最终离开了人世,央吉卓玛再也找不到快乐和慰藉。阿叔的去世给央吉卓玛很大的刺激,她像游魂一样在帕鲁庄园游荡,经历了新庄主的刻薄虐待,她的内心一片冰冷。当看到屠夫宰杀绵羊时,她充满强烈的怜悯之情,从羊的眼睛中央吉卓玛看到了自己,她想要逃避饥饿、尖叫和血腥。最终,她与奶妈逃到了贝西庄园。在贝西庄园,她再次感受到了久违的亲情,但仆佣拉姆备受蹂躏的遭遇让她内心充满同情。拉姆因为寒冷和困倦,挨着温暖的炉子睡着没能及时给少爷上茶,少爷就抓起火铲将火炉中的牛粪火倒入她的脖子,这给央吉卓玛以极大的刺激:“从此,一股刺鼻呛人的焦臭味伴随着拉姆痛苦地扭曲僵躺在污水中的形象,一直留在央吉卓玛的记忆中,以至,一闻到焦臭的糊味,总使她情不自禁地想起自己受挫折的命运。”6看到拉姆受难,敏感的央吉卓玛同时也看到了自己命运的不堪。在这一时期,央吉卓玛经历了情感的坎坷,既有温馨的渴望已久的爱,又有难以抑制的失去的痛苦,并且在这一时期由于生活的流离失所和辗转变迁,她的视野开始扩大,敏感的心灵感受到了难以抑制的伤痛。第三个时期是回到拉萨府邸及在德康庄园求学时期,回到拉萨,她再次领略到被歧视的痛苦。由于时局的动荡,她好奇地注视着周遭的一切,关押在德康宅院内的犯人,昔日四品官员隆康老爷的死去,世事的无常,使她感到恐怖,有着一种强烈的怅惘和伤感。由于年岁已大,母亲认为如在拉萨上学会丢脸,就把央吉卓玛送到德康庄园求学。在德康庄园,央吉卓玛终于体会到了不受歧视、受人尊重的愉悦,她喜欢上了这里无拘无束的生活和人与人淳朴的交往方式,但当她的心一天天平静下来并充满喜悦之时,却又不得不听从母亲的安排回到拉萨,她感到万分难过和委屈。在回拉萨途中朝拜圣湖的时候,她再次问自己:“这世上有神灵有佛国吗?命运到底是什么呢?自己真的是个不吉利的人吗?为什么神灵不保佑我,让我成为一个吉利的人呢?”7她对自己不吉利的命运发出了追问。第四个时期是在寺庙及解放军进城时期。回到拉萨后的央吉卓玛被母亲以摆脱尘世轮回之苦得到幸福为名送入佛门,久已遗忘的绛红色的宁静与温暖涌入央吉卓玛的心头,她愉悦地接受了母亲的安排。在寺院中,央吉卓玛感受到了心灵的平静,师傅的关爱使她的内心充满幸福:“看来我真是个有福分的人,原来居然到了这么美妙的净地。”8这是她第一次感受到自己是一个有福气的人,并且为之而自豪。然而在这样一个强调众生平等的佛法圣地,梅朵却因为是铁匠的女儿而遭到歧视,央吉卓玛陷入困惑之中。但当最终知道母亲送自己进入佛门的原因不是为了她的幸福而是为了省一笔嫁妆时,央吉卓玛的心掉入冰窟,再一次体会到了被抛弃、被愚弄的悲凉,从此,她开始怀疑所有的一切,不再相信别人,从此,那种被忽视、被冷落,甚至被欺骗的伤心和自尊心受到的羞辱所带来的痛楚,在她的记忆中永远无法抹去。她觉得家人离自己更为遥远和陌生,在她心中一直被视为崇高和圣洁的寺院也变得越来越虚无缥缈。当解放军进入拉萨,央吉卓玛感受到新生活的感召,她兴奋地渴盼着某种变化,内心产生了一种神秘而清晰的感觉,最终毅然丢弃旧有的生活,开始了崭新的生活:
她想看看外面的世界,想看看汉人罗桑的家乡、拉姆学习的地方,想看看其它地方的人是怎么生活,还想看看这世道怎么个新法、会变成什么样。她不知道自己这样离开拉萨离开寺院对不对,不知道应该像法友白姆和德吉那样安心在寺院祈祷念经,还是走向另一个有广阔的平原有大海有人人平等的新地方?不知道自己会从此继续穿着袈裟还是脱下它,像拉姆那样穿上军装?她就这样,带着激动、带着新奇和几分渺茫,等待着踏上另一片土地的日子。
不久,在西藏地方政府官员和班禅代表欢送的哈达丛中,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锣鼓声中,在许多老人和僧人甩围腰甩膀子的唾骂之中,曲珍和她的同伴们爬上了一条条用绳子拴住的牛皮筏,在拉萨河夏日波涛滚滚的河面上,浩浩荡荡离开了圣地。9
央珍的叙述隐忍而克制,她以真实的心灵书写呈现了西藏现代化的进程,在对民族历史进程的呈现中,对女性命运进行了深切的观照和细腻的表现。伴随着央吉卓玛的成长,既有人性的温暖和小小的温馨,又有刻骨的残酷和痛彻心扉的伤害。央吉卓玛从出生就被人认为是不吉利的,幼小的心灵早已受到刺痛,很小的时候她并不在乎别人的说法,只是以大哭大闹来发泄所有的不满。但当听到一向维护自己的管家也指责自己不吉利的时候,她感到刺耳惊心,备受伤害。当央吉卓玛进入寺庙,感受到所有人的尊敬,她开始觉得自己是个有福分的人时,奶妈的女儿达娃却说:“二小姐,您到现在还蒙在羊肚袋里呢,这大院中谁不知道太太是因为不愿给您置办嫁妆,是为了给家中省下一大笔钱,这才送您当尼姑呢。”10这句话对央吉卓玛来说不啻于是晴天霹雳:“她的脸部抽搐了一下,身体微微前倾,疑惑的目光直勾勾地盯着达娃,心里感到阵阵痛苦,感到一种混沌中的惆怅,感到神思恍惚,仿佛一个心神迷乱的人,脑子里有万千紊乱的思绪,同时却又是白茫茫的一片空白。”11真切的残酷现实让央吉卓玛感受到来自亲人的伤害,然而她却在残酷中寻找温情,在苦难中仍然保持着一颗温润之心,她用温情去点缀与化解尘世的冰冷,作品写出了女性柔韧的生命意识。央吉卓玛与奶妈巴桑之间的温情,央吉卓玛与阿叔之间的浓浓血脉情,央吉卓玛与姑奶奶之间的亲情、央吉卓玛与拉姆主仆之间的真挚情感,央吉卓玛与师傅之间的情谊,这些温情在央吉卓玛心里总能泛起阵阵感动的涟漪。譬如作品写帕鲁庄园的阿叔把央吉卓玛拥入怀中,告诉她这就是她的家时,“央吉卓玛浑身一颤,顿时,时光倒流到两年前。她又一次闻到那股味,牵肠挂肚的温馨和黯然伤感的苦香,从中还透出一股隐隐约约的腐烂。那是她最后一次和父亲见面时闻到的气味。想到这,她的心头生出一种无可名状的悲伤,随即,她陷入迷雾中。”12在阿叔这里,央吉卓玛找到了不受歧视地存在的欢乐,“她渐渐与阿叔有了一种无法述说的亲密,渐渐恢复了自己消失已久的感觉,渐渐又回到了两年前父亲在世时的自己:任性、快乐、淘气。”13“她在心中比较着自己的父亲和阿叔,他们之间她看不出哪些是相似的,但她觉得他们是同一种人,从后者身上她感到自己得到了更多而不确定的东西,同时还有一种新奇的感觉。”14然而,欢乐与宁静是短暂的,残酷总是猝不及防地来临,阿叔去世给她以很大的打击,作者写央吉卓玛茫然的痛与哀:“葬礼举行完毕。现在,太阳常常从空中隐去。现在,庄楼里总是空空荡荡冷冷清清。”15她朝田野中奔去,她痛切地感觉到阿叔已经真的死去:“阿叔已经死了,自己再也走不进那个房间,我再也见不到阿叔了,从今以后这世上再也没有人疼爱我了……”16“她走过回廊,走下楼梯。她走进大经堂,走出酿酒房。她推开所有没上锁的房门,走进去又走出来。她朝所有挂着锁的门缝向里张望,一遍又一遍。她走下石阶,在幽暗的天井里来回转悠。她拉开庄楼的大门,向庄楼西边的小溪走去,长时间地朝溪水对岸的两座褐色水磨房打探。最后,她走进北山坡上的村庄中,从一间间由地里长出来般的农舍跟前走过……”17她终于病倒,她面对奶妈哽咽道:“那怎么办呢,我只要呆在在庄楼里我就想阿叔,我一坐下来我就想哭,我心里好难过呀,奶妈。”18这样的话语写出了央吉卓玛的无助和孤独的处境。
在《无性别的神》中,从作者所描写的历史事件来看大致是在1940年到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这一时期,这十余年间是西藏社会生活发生巨大变动的时期。这一时期,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热振活佛上台出任摄政王,热振活佛被迫让位给达札,以及后来热振活佛与达札的争斗,僧人的暴动,噶厦政府的镇压,热振活佛被关押致死,一批跟随他的成员被肃反,以及解放军进军西藏,新的时代的到来。这十余年是西藏历史风云迭起动荡的时期,然而,充满刀光剑影的热振与噶厦政府之间的势力火拼,剧烈的时代风云动荡却通过小姑娘央吉卓玛的眼睛向我们描绘,难以承受的历史之重和生命之痛以一个善感柔弱的小姑娘的心灵体验呈现在我们面前。如热振活佛在政治斗争失败惨死后,他的同伙隆康老爷被关押在德康府邸,央吉卓玛小小的心灵不能明白为什么昔日荣光的老爷变成了现在衣衫褴褛的囚犯,备受侮辱,在死后还要被埋进乱坟岗,她感到惆怅和伤感。央珍是细腻敏感的,她的独特之处在于她能以小见大,让我们看到激烈动荡的时代风云变幻以及在历史风貌掩映之下心灵的颤抖。如通过隆康老爷的叙述我们得知央吉卓玛父亲的经历,央吉卓玛的父亲曾是噶厦政府的四品大官,由于留学西方,所以思想激进,行为西化,与环境格格不入,时运不济,郁郁寡欢,不到四十岁就去世了。从侧面描写了西藏的改革派与顽固保守势力的斗争以及顽固守旧派最终的得势,改革派的没落,这些描写都有历史的依据。宏大的历史通过细腻柔婉的心灵呈现在读者面前,朴素的日常生活背后掩映着历史的刀光剑影。
在《无性别的神》中,西藏的典章制度和贵族风俗也自然而然地融入作品之中。如小说写央吉卓玛的父亲死后,家族中没有男人就会失掉庄园。母亲起初不愿意找人入赘。但家庭越来越败落,从原来的大宅院搬到了一座独门小院,仆佣也少了许多,不久,母亲招赘了继父,母亲以德康家族的名分为他在噶厦处捐到了七品官位。后来因为这个七品官的收入太少,外祖母和姑太太就花银两为他换了一个收入更高的官职。我们从中可以看到贵族官僚制度的世袭性与腐败性。另外,我们在央珍的作品中还能看到央珍对旧西藏政治体制的细致了解,如她写央吉卓玛的母亲在德康庄园的时候去拜见当地的县长,描写县长的府邸建在高高的城堡里,在拜见时有一系列的礼仪,当去考查西藏旧时的典章制度和风俗的时候,可以看到央珍的这些描写经得起政治历史习俗的考验,细节的真实使得央珍的作品具有脚踏实地的真切感。
在作品中,央珍还用民歌来传达情感,展现西藏独特的风情,同时也渗透出女主人公的内心情感,如在色拉寺僧人和政府军打仗的时候,当官家要关上房门,担心强盗闯进来的时候,央吉卓玛想起来了在贝西庄园里听骡夫唱的《强盗歌》:
我骑在马上无忧无愁,
宝座上头人可曾享受?
我漂泊无定浪迹天涯,
蓝天下大地便是我家。
我两袖清风从不痛苦,
早跟财神爷交上朋友;
从不计较命长命短,
世上没有什么可以留恋。
……19
此时的拉萨,子弹在城市上空盘旋,但幼小的央吉卓玛却在大人的慌乱中,渴望着强盗们自由烂漫的生活。再如央吉卓玛在被护送从拉萨到德康庄园的路上时,她心情愉悦,呼吸舒畅,她渴望在原野中奔跑。当骡马队踏上了一条河边小道时,她感受到了一种得到自由和解脱的快乐,耳畔听到一支悠扬的民歌:
你骡马的铃声啊,
静一静,请不要再响了,
好让那些虔诚的人们回忆讲经场;
你湍急的流水啊,
静一静,请不要再喧闹了,
好让多情的我想一想昨夜的女房东。
……20
央珍的创作具有深厚的民族文化内蕴,在其写作中有意识地去建构民族的和自我的立场,避免民族和个体成为一种符号化的象征,从而被隐没于主流文化的历史之中。回顾藏族文学的发展之路,可以看到在五六十年代的藏族文学创作中,民族特色大多表现为一些外在的物化的描写。而在八十年代民族意识逐渐崛起的时代,藏族作家在其创作中着重展现的是对民族精神的建构与追寻,但这种建构和追寻更多的是一种理念化的东西。在央珍的创作中,我们看到的是一种自然而然的藏民族文化内蕴的流露。同时,央珍有意识地想用文学的方式呈现西藏真实的一面,显现了女性有意识地建构民族历史的努力。在央珍笔下,西藏的现实生活和历史变迁得以真实地呈现,同时,民俗风貌的描写和自然景物的鲜活展现,使得她的作品显得素朴而又有真切感人的力量。
注释:
1.参见索穷、央珍:《作家央珍:藏地女性与我的文学西藏表达观》,载《中国西藏》2016年第5期。
2.央珍:《走进西藏》,载《文艺报》1996年2月9日。
3.央珍:《无性别的神》,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1994年版,第1页。
4.央珍:《无性别的神》,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1994年版,第17页。
5.央珍:《无性别的神》,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1994年版,第47页。
6.央珍:《无性别的神》,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1994年版,第142页。
7.央珍:《无性别的神》,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1994年版,第238页。
8.央珍:《无性别的神》,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1994年版,第268页。
9.央珍:《无性别的神》,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1994年版,第351页。
10.央珍:《无性别的神》,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1994年版,第282页。
11.央珍:《无性别的神》,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1994年版,第282页。
12.央珍:《无性别的神》,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1994年版,第57页。
13.央珍:《无性别的神》,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1994年版,第60页。
14.央珍:《无性别的神》,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1994年版,第63页。
15.央珍:《无性别的神》,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1994年版,第73页。
16.央珍:《无性别的神》,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1994年版,第74页。
17.央珍:《无性别的神》,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1994年版,第75页。
18.央珍:《无性别的神》,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1994年版,第78页。
19.央珍:《无性别的神》,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1994年版,第172页。
20.央珍:《无性别的神》,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1994年版,第204页。
节选自《文化地理视域中的当代藏族文学研究》第四章第三节

徐琴,女,陕西汉中人。中山大学文学博士,西藏民族大学文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致力于现当代文学研究和藏族文学研究,在《当代作家评论》《当代文坛》《小说评论》《民族文学研究》《青海社会科学》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70余篇,其中多篇论文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全文转载。出版学术专著《文化身份的建构与书写——当代藏族女性文学研究》《文化地理视域中的当代藏族文学研究》等。主持 “当代藏族文学与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建构研究”“文化地理视域下的当代藏族文学研究”“当代藏族女性文学研究”等三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央珍(1963—2017),女,藏族。西藏拉萨人。198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生前曾供职于《西藏文学》编辑部、《中国藏学》编辑部。著作《无性别的神》被改编为二十集电视连续剧《拉萨往事》。另有散文、藏学论文等多篇发表。作品被翻译成英文、匈牙利文等出版。获第三届、第五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