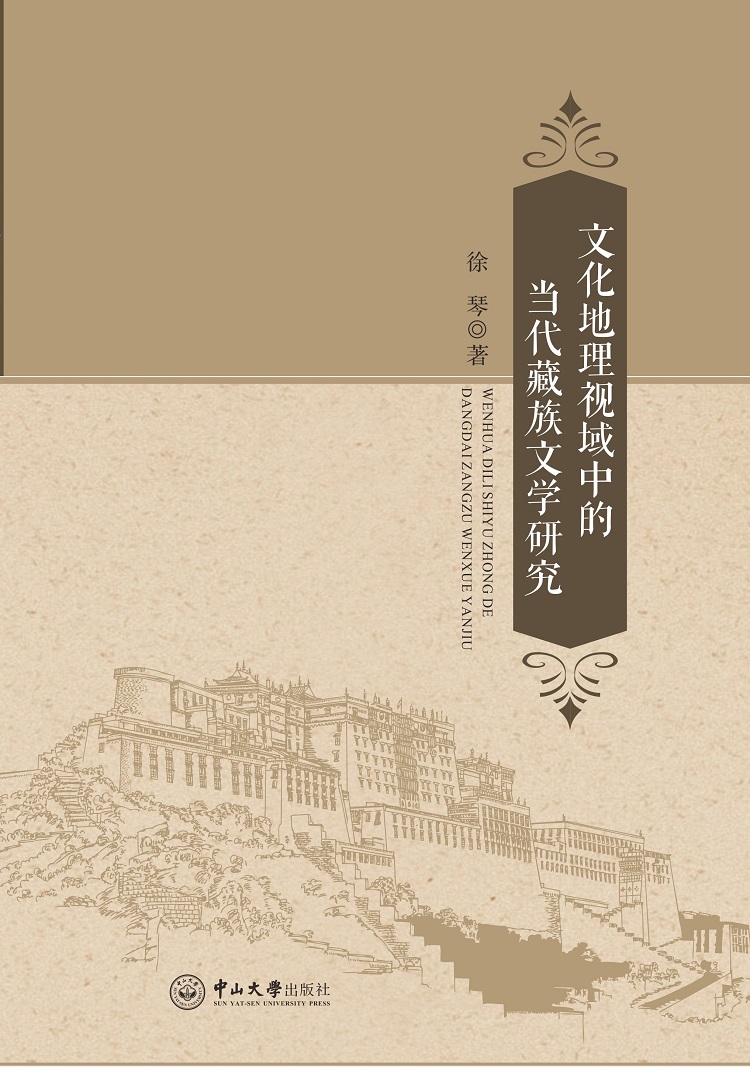
《文化地理视域中的当代藏族文学研究》
(徐琴著,中山大学出版社,2022年6月)
扎西达娃是上世纪80年代西藏文坛最具代表性的一位作家。著名作家马丽华对扎西达娃曾经这样赞誉道:“扎西达娃,一个被文坛肯定的名字。博览西藏小说群,无疑扎西达娃是最好的。他与八十年代一起出现在西藏文坛,从此一路领先,身旁身后总有一群同路者和追随者。由于他在西藏新小说领域的特别贡献,他成为一面旗帜。”1身处80年代西藏文学阵营的马丽华对扎西达娃的评价无疑是十分中肯的。
扎西达娃在文坛上崛起正值上世纪80年代,此期的中国正处于一个变革的时代,国外的各种文艺思潮被大量引进,在此背景下,重新认知和评价传统文化也成为寻求中国文学发展的必行之路,于是当代文学在80年代中期较集中地出现了“文化寻根”倾向。寻根文学的产生,与外来文化的影响和冲击密切相关,但在整体氛围上,对寻根文学影响最大的当推拉美魔幻现实主义。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虚构了一个村镇马孔多,通过对布恩迪亚家族命运的描写,反映了哥伦比亚乃至整个拉丁美洲的历史,整部小说浸淫着浓重的孤独意识和忧患情怀,也有着难以摆脱的荒诞和沉重之感。《百年孤独》以其形式和内容的震撼性强烈地撞击了寻根作家的心灵,契合了他们以现代的眼光去重新审视民族历史和现实,探查民族传统文化的强烈愿望。由于地域和文化因素等方面的相似性,西藏天然成了接受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最理想的文化土壤。因此,当拉美的苦难和孤独以文学的方式震动世界并引起中国作家的强烈反响时,在偏隅之地的藏族作家受到这样一种文化的感召,感受到强烈的冲击和共鸣,扎西达娃在马尔克斯这儿找到了突破口,无论是在作品的艺术表现还是在对民族传统文化和宗教的反思上,扎西达娃都深刻地受到了马尔克斯的影响。
“你在哺育了自己的大地上,重新找回了失落的梦想,这使你吓了一跳。你感到脚底下的阵阵颤动正是无数的英魂在地下不甘沉默的躁动,你在家乡的每一棵古老的树下和每一块荒漠的石头缝里,在永恒的大山与河流中看见了先祖的幽灵、巫师的舞蹈,从远古的神话故事和世代相传的歌谣中,从每一个古朴的风俗记忆中看见了先祖们在神与魔鬼、人类与大自然之间为寻找自身的一个恰当的位置所付出的代价。就送样,脑袋"吱一一"的一声。你开窍了,你的自信来了,你的激情来了,你的灵感来了,你开始动笔了。”2
在民族文化的感召下,扎西达娃把自己民族的苦难、孤独以及漫漫长路上的艰难探索都倾注于笔端,以精英知识分子的姿态展现了对民族历史和文化的探询。对民族文化的深刻挖掘与反省以及艺术形式上的探求创新,使得以他为旗手的西藏当代汉语文学焕发出独特的魅力,由此不再只是对内地文学现实主义审美规范的简单趋同,借助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使西藏文学实现了精神上的独立和形式上的超越。扎西达娃的一系列作品闪烁着神奇的光芒,他将神话与现实,宗教传统与风土民情糅合在一起,创造了一种似真似幻的略带神秘的具有魔幻色彩的藏民族生活图景。其创作立足于民族文化土壤,以独特的感受,批判的眼光审视了藏民族的发展历程,剖析了民族精神上的痼疾,反思宗教传统存在的现实性意义。
独特的地域风貌和深厚的宗教文化背景使得扎西达娃的创作独具魅力,与同时代的其他汉族作家相比,在整体创作观念和叙事手法上,扎西达娃运用魔幻现实主义显得更为自如。这一方面与他个人敏锐的文学触觉有着很大的关系,另一方面他所处的文化土壤也是其成功的有利因素。高寒缺氧的气候,蓝天白云的胜景,深厚的宗教文化氛围,使得青藏高原至今在外人的眼里,仍有难以言述的神秘。悠远的历史,古老的神话传说,神秘的宗教氛围使西藏社会披上了如梦似幻的色彩,特别是万物有灵和轮回转世观念深刻在藏民族的灵魂里,展现在宗教仪轨和日常生活之中,这使得西藏的世俗生活也充满了魔幻意味。与内地相比,西藏与拉美在地理环境、历史发展和文化观念等方面上的相似性使得扎西达娃在接受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影响时,显得更为洒脱自如。扎西达娃在其《系在皮绳扣上的魂》中这样写道:
现在很少能听到那首唱的很迟钝、淳朴的秘鲁民歌《山鹰》。我在自己的录音带里保存了下来。每次播放出来,我眼前便看见高原的山谷。乱石缝里窜出的羊群。山脚下被分割成小块的田地。稀疏的庄稼。溪水边的水磨房。石头砌成的低矮的农舍。负重的山民。系在牛颈上的铜铃。寂寞的小旋风。耀眼的阳光。
这些景致并非在秘鲁安第斯山脉下的中部高原,而是在西藏南部的帕布乃冈山区……3
西藏的地理自然与拉美的山地有着很大的相似之处,这为扎西达娃的魔幻现实主义提供了丰沃的土壤。由于地理气候等各方面原因,西藏长期处在封闭与落后状态,和平解放与社会主义民主改革,使西藏直接从农奴制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整个社会状况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传统的观念和长久的宗教信仰在藏民族生活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这和拉丁美洲的状况有一些相似之处:“古代的和现代的,过去的和未来的交织在一起,现代化的科学技术和封建残余结合在一起,史前状态和乌托邦共生共存,在现代化的城市里,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与印地安人原始集市为邻,一边是电气化,一边是巫师叫卖护身符。”4敏锐的扎西达娃在马尔克斯这儿找到了突破口,以魔幻的手法展现了自己对藏民族历史和宗教文化的探询与反思,就如张清华所论:“扎西达娃没有和这个年份中的一些寻根作家一样把‘文化寻根’看作是一个用边缘文化‘颠覆’正统文化的过程……他不是一般地‘反思’其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也不是简单地夸饰和推崇,他是怀着深深的宿命感来理解他的民族的。”5扎西达娃以精英知识分子的姿态对其民族的现实和历史进行深刻的反思,探讨民族前行之路,困惑与救赎鲜明地呈现在他的作品之中。
《系在皮绳扣上的魂》是扎西达娃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也是孕育在雪域大地上的魔幻现实主义的经典之作。作品写在马蹄和铜铃单调的节奏声中长大的婛跟着远方来的虔诚的圣徒塔贝踏上了离家出走的路,与过往的孤独和寂寞作别,去寻觅那遥远而又神秘的人间净土——香巴拉。挂在腰上的108个皮绳扣结记下了她与塔贝在寻觅的过程中的风餐露宿及虔诚膜拜,但是,香巴拉始终遥遥无期,疲倦困乏的婛没能抵御现代生活方式的诱惑,不愿跟随塔贝继续踏上求索之途,她留在了甲村,要享受世俗的安宁和幸福。但是,婛最终无法摆脱对塔贝的依赖,又回到了塔贝的身边,与他同去寻找那藏在莲花生大师纵横交错的掌纹里的路。最终,塔贝死在了莲花生大师纵横交错的掌纹里,其临终前听到的声音也并不是神的召唤,而是第二十三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向全世界发出的文明的声音。作品最后写“我”穿越时空进入虚构的世界,要中断塔贝的追寻之旅,在其弥留之际告诉他所听到的声音并不是神的启示。面对经历了苦难的历程无依无靠的婛,“我”打算把她塑造成一个新人,作品结尾“我代替了塔贝,婛跟在我后面,我们一起往回走。时间又从头开始算起。”6在现代文明和理性精神的烛照下,面对宗教传统和虔诚的信仰之途,扎西达娃有着深深的困惑和质疑,他用文学的方式对民族历史和宗教传统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探讨宗教和传统文化在现代文明的侵袭下所面临的困境和出路。
扎西达娃对民族历史的反思是充满困惑、矛盾与痛苦的。现代文明与古老宗教信仰的冲突是雪域大地上的人们在现代化进程中必然面临的精神困惑,也是一个有民族责任感的作家在写作时难以绕过的堡垒。他鲜明地看到现代文明对藏族社会的冲击,作品中塔贝是被象征现代的机器拖拉机撞伤而死亡,塔贝临终前以为听到的神的声音不过是奥林匹克运动会通过卫星向全球直播的声音,从中可以看到扎西达娃对于藏民族宗教信仰的反思。在《西藏,隐秘岁月》中,次仁吉姆在母亲怀孕两个月就出生,其出生时天降甘露,天边出现吉祥的彩虹,两岁时就显示出与凡人不同的迹象,在地上画生死轮回的图腾,刚会走路就会跳格鲁派金刚神舞,在沙地上踩出的脚印是天空的星宿排列图。但当她的右脸被英军上尉吻了一下之后便红肿流脓,显示在她身上的种种诸神化身的神迹也消失殆尽,这其实是西方势力的侵入对宗教神性的破灭的象征。对现代文明的理性认同与对西藏宗教的困惑迷茫如影随形地交织在他的作品之中,在现代文明的不断冲击下,当现代科技日渐主导人们的生活时,世俗的享乐不断冲击虔诚的苦修时,虚无缥缈的神又将居于何处?所以在作品中,婛被计算器、音乐、啤酒和迪斯科所代表的世俗生活所吸引,并试图离开塔贝。但正如婛所言“他把我的心摘去系在自己的腰上,离开他我准活不了”7,所以婛最终又回到塔贝身边。西藏传统宗教文化虽然受现代文明冲击,但却永远是民族之魂,是藏族人民难以抛弃的灵魂之念。一百零八颗佛珠、一百零八个绳结象征着虔诚的宗教信仰,也象征着藏族人所走过的漫长岁月。
长期贫穷落后的西藏肯定要走向现代,必然要向现代文明靠拢,这是无法阻止的。但藏族人民千百年来对宗教的信仰永远不会消逝,尽管在宗教和科学之间,扎西达娃有着清醒的理性思考,但作为一个藏人,对民族文化之根的困惑与追寻,让他的作品有着一种穿越历史的痛楚之感。从骨子里他对传统宗教文化充满依恋,但在现代文明的烛照下,返观并表现西藏历史与现实生活时,很容易发现其中的荒谬,所以扎西达娃陷入了两难处境。在《西藏,隐秘岁月》中,次仁吉姆和达朗从小就互相爱慕,原本等待父母去世后和达郎结合,但被冥冥的命运安排,削发为尼供奉岩洞中的神秘大师,达郎后来离开了廓康,只能在哲拉山顶与次仁吉姆遥遥相望。次仁吉姆拒绝了世俗的爱,为了供奉岩洞中的修行者,在多年的时间里,销蚀青春和爱情,虔诚而又迷惘无望地度过了人生。虽然在这个过程中她也曾有怀疑,但终其一生都生活在这种孤寂的信仰之中,由此呈现出宗教信仰的虚无与荒谬以及对人性的钳制,无疑扎西达娃对宗教是有深刻的质疑和反思的。但在作品最后,岩洞中已成化石的修行者在接受过西式高等教育的小次仁吉姆面前现身并向她昭示,指出佛珠上的一百零八颗佛珠:“这上面每一颗就是一段岁月,每一颗就是次仁吉姆,次仁吉姆就是每一个女人。”8历史的喧嚣都如过眼烟云,似乎唯有宗教信仰和那贯穿在血液中的民族之魂才是永恒的。扎西达娃在历史变迁中既看到了宗教的荒诞,也看到了民族文化的传承,但在内心深处,他又无法割舍这种深藏在骨髓中的民族宗教心理。
扎西达娃对民族之魂的追寻显得极为执着,在《泛音》中,次巴认为民乐团的演出不一定代表着真正的藏民族音乐,他探寻着民族音乐之魂,在闹市中,他被一个康巴老艺人的胡琴声迷住了,恍惚中以为是“先祖的声音”,他要寻找一种发自灵魂深处的呼喊,但苦寻无果,执着的次巴选择加入老艺人所栖身的流浪部落,去寻找那个声音发出的源头,但是否能找到,谁也不知道,作品最后这样写道:
旦朗在营地里,在先祖声音的召唤中,漆黑的眼睛前出现了一堆白骨,那上面有许多黑麻麻的东西,起先他以为是自己用铅笔写成的音符,当那堆白骨队在他眼前时,他才看清那上面全是些他无法理解的神秘的符号。这个时候,他的全部身心突然感到自己如同一位虔诚的教徒,在神明面前接受一个伟大深奥的教义,不由双腿一软,跪倒在地。9
次巴的寻找无疑展现出扎西达娃深刻的思考,永远的救赎之路到底是在哪里,作者是犹疑的,但他深知宗教精神和传统文化在藏民族的心灵中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这一点在他的作品中有着鲜明的映现。长篇小说《骚动的香巴拉》仍然以魔幻之笔书写西藏社会制度的变迁和传统文明的渐趋失落所引起的精神危机。作品以1959年西藏民主改革和文革十年为时代背景,通过凯西家族的历史变迁,以及凯西公社普通人的命运遭遇,展现了社会制度的变革所带来的一系列变化,有着对政治变迁和权力斗争的深刻思考,也写出了藏族传统文化的渐次失落以及宗教信仰的消失所引起的精神上的危机。敏锐的扎西达娃扑捉到藏民族身处现代文明与传统文化、宗教信仰与科学理性矛盾交织时期人们精神上的困惑和骚动。在经历困惑和灵魂的煎熬后,他将救赎的希望寄托在宗教上。在作品最后描写藏历正月十五拉萨盛大的宗教节日,这样写道:
但是仍然需要一个无形的替身来载负其人世间的苦难,并将各种苦难带到远远的地方去,人们从嘴里呐喊出一声‘神必胜!’的呼唤,苦难也就从他们心中抹去一分。在危机四伏、充满忧伤和各种不幸的孤独的地球上,西藏人从来没有绝望过,他们怀着雍容的气度话朝气蓬勃的乐观主义精神蔑视着西方的文明的人类创造出的一堆垃圾。在欢乐的赞美声中,人类的未来佛被抬出来了,它叫弥勒佛,藏语称强巴佛,它是继释迩牟尼之后的第六位佛……10
对宗教传统的难以舍弃与求神庇护的虔诚跃然纸上。他试图以对民族宗教文化的坚守来消解和抗衡历史的疮痍,并期冀用此来作为在现代文明侵袭下救赎灵魂的依托。面对藏民族必然前行的现代之路,扎西达娃的探求之途无疑是孤独而艰难的,他对宗教有质疑,更有难舍的依恋,他清晰地知道他的民族背负着因袭的重担,但并没有失去信心,正如《系在皮绳扣上的魂》中的“我”一样,是带着忧患、使命、信心向着未来之路探索。因此,评论家张军这样认为:“扎西达娃通过如魔的想象,是在现实与杂乱无章的现象进行透视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在这里想象的最终指向仍然是现实,但它终归是寓言化、象征化,甚至是神化的现实,而且这种现实更多的是同中生活的人的心理,尤其是人的精神困惑相关。”11扎西达娃关注到特定时期一个民族的困惑和忧虑,他的作品因对藏民族宗教信仰的理性反思而显得清醒而深刻,同时因对民族历史发展的不懈探求而带有厚重的历史质感。他的作品有对现实的触摸,有广阔的历史深度和契入骨里的思索,从这一点上来说,扎西达娃无愧是80年代藏民族的代言人。
注释:
1. 马丽华:《雪域文化与西藏文学》,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29页。
2.扎西达娃:《你的世界》,载《文学自由谈》1987年第3期。
3.扎西达娃:《扎西达娃小说集》北,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3页。
4.陈光孚:《魔幻现实主义》,花城出版1987年版,第23页。
5.张清华:《从这个人开始——追论1985年的扎西达娃》,《南方文坛》2004年第2期,第33页。
6.扎西达娃:《扎西达娃小说集》,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21页。
7.扎西达娃:《扎西达娃小说集》,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19页。
8.扎西达娃:《扎西达娃小说集》,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398页。
9.扎西达娃:《西藏隐秘岁月》,长江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233页。
10.扎西达娃:《骚动的香巴拉》,作家出版社1993年版,第384页。
11.张军:《如魔的世界——论当代西藏小说》,见《西藏新小说》,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51页。
节选自《文化地理视域中的当代藏族文学研究》第四章第一节

徐琴,女,陕西汉中人。中山大学文学博士,西藏民族大学文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致力于现当代文学研究和藏族文学研究,在《当代作家评论》《当代文坛》《小说评论》《民族文学研究》《青海社会科学》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70余篇,其中多篇论文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全文转载。出版学术专著《文化身份的建构与书写——当代藏族女性文学研究》《文化地理视域中的当代藏族文学研究》等。主持 “当代藏族文学与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建构研究”“文化地理视域下的当代藏族文学研究”“当代藏族女性文学研究”等三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扎西达娃,藏族,四川巴塘人,作家,编剧。中国作家协会第十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团委员,中国文联第十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西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西藏自治区文联主席。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骚动的香巴拉》、长篇游记《古海蓝经幡》、中短篇小说集《西藏,系在皮绳结上的魂》《西藏,隐秘岁月》《扎西达娃小说集》《扎西达娃小说选》《风马之耀》《夏天酸溜溜的日子》,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庄重文文学奖等奖励,作品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出版。先后担任《益西卓玛》《冈拉梅朵》《西藏往事》《皮绳上的魂》《阿拉姜色》等影视剧编剧,获得第20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剧本特别奖、第2届编剧嘉年华年度关注电影编剧奖、第21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最佳编剧奖、入围第53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改编剧本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