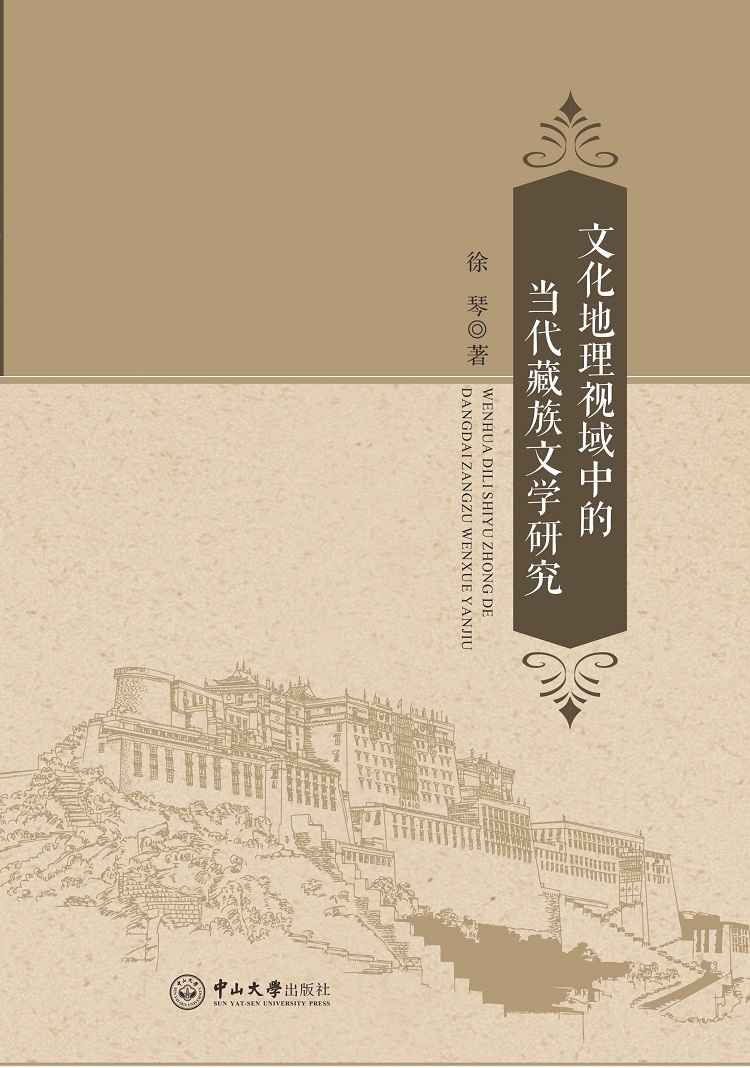
《文化地理视域中的当代藏族文学研究》
(徐琴著,中山大学出版社,2022年6月)
嘎代才让,一个行走于甘南地区,仰望神性天空的藏族青年诗人。他从1997年开始进行藏汉双文创作,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他创作了大量的诗歌,出版有诗集《西藏集》。
嘎代才让的诗歌内容较为广博,有对雪域西藏的朝圣,有萦绕心头的乡愁,有念恋不忘的亲情,有缅怀友人的友情,有酸甜苦辣的爱情,还有切合时代脉搏对玉树受难同胞的关怀与同情等等,正如蒙古族作家哈森对他的评价“一个将诗歌写作日常化的藏族青年”1。嘎代才让并不是“为赋新词强说愁”之人,他自己曾说:“写诗十余年,我一直在记录:与看得见或看不见的事件而做记录,与内心的反抗而做记录,与信仰的象征做记录,与时常的念诵做记录;不仅仅是用心记录,而是用生命去记录”。他把诗歌看成生活的一部分,用诗歌去记录琐碎而细小的事情,去表达微妙而复杂的心理变化,去抒发对圣地的向往与期冀等等,他用诗歌将自己真切的感受、想法表达出来,不矫揉,不造作。嘎代才让将诗歌写作日常化、细节化、个人化,使我们可以窥见诗人最隐秘的心灵颤动,同时也为我们呈现了多元化藏地生活的图景。
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与宗教文化在一定程度上造就和影响了嘎代才让的创作。“地域文化的内涵主要是指在一定的地理空间形成,并经过长期积累的包括观念、风俗在内,具有自我特色的诸多文化元素的总和。”2一方水土滋养一方的人,不同的地域文化导致人的思维方式、观念、习俗等方面的不同,从而导致了地域文化的差异性。嘎代才让在青海出生,中小学时代及工作和生活的很多时光是在甘南度过。他诗歌创作根据地理空间领域可以划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对出生地青海的描写,另外一部分是对现在生活地甘南及兰州的描写。
从古至今,羁旅漂泊的孤寂,怀念故土的思乡之情的抒发常常出现在文人墨客的笔下,杜甫借月亮来抒发思亲怀友念故乡的感慨;余光中借海峡表达回归大陆的渴望;嘎代才让是通过对记忆的追溯,并且有些诗歌直接以地名青海命名诗歌来表达对故土的怀念之情。诗人在《青海青海》中写道:“青海被高原的阳光穿着/像破旧的衣裳/一辆马车拉着几只羊/从身边经过/我有点痴了,对着这些瞬间的记忆/星辰居上/其下是歌声/今夜青海,又大又亮/此刻,我想起三江源/想起了三条江河从疲惫大风中流过/今夜我要埋住哭声”3诗人开篇将青海比作破旧的衣裳,穿在阳光的身上,既有比喻又有拟人,能被太阳穿在身上的衣裳,可见青海的辽阔,诗人由青海这一地名直接切入主题。马车拉着的不仅仅是几只羊,更是诗人自己,诗人的记忆跟随着马车前进的方向,渐渐唤醒,从白天到晚上,记忆在不停地跳跃,情感亦在不断地加强。如果说白天只是唤起记忆,那晚上则是情感的抒发。夜晚的青海,在月亮的映衬下显得又大又亮,面对此情此景诗人想到长江、黄河、澜沧江的源头的三江源,由此及彼,诗人联想到青海给予了自己生命,自己却身处他乡,至此诗人的思乡之情再也无法控制,疲惫的大风更是疲惫的诗人,忍住泪水,却忍不住浓浓的思乡之情。
在诗人的另一篇题为《青海》的诗歌中我们也可以感受到诗人对青海故土的深挚之情。“我选定一个黄昏后/突然觉得自己是孤单的/满脸的喜悦,远在青海/就已悄悄消失了/青海的时候/我怀疑窗外的世界将我丢下/一个人在黑暗中/寻找一丝光亮/后来从睡梦中醒来/我看见自己泪流满面/再后来月亮在深夜照出了我的骨头/和越背越沉的行囊”4,黄昏是明暗交接的时候,当黑暗一点点吞噬着光明,人的思维也开始涣散,诗人在现在的环境中感受到孤独,诗人想到在青海的时候,即使被世界抛弃,也要在黑暗中寻找一丝光亮。如梦初醒的他,泪流满面,这泪水既是对故乡青海的思念,更是对当时自己执着追求光明的想念。从太阳到月亮,由白天到夜晚,思乡之情越来越浓重,行囊也就越背越重,“月亮”作为诗歌中常用的意象,经常用来表达思乡之情,在这里“月亮”不仅用来表达思乡,还有指引方向,给人带来慰藉的象征。
从地理空间领域来看,嘎代才让诗歌创作的第二部分内容是对现在常居之所兰州和甘南大地的描写。“仿佛还在昨天/我们同时走近一个地方,拥抱/亲吻,害羞地扭过脸/那时天地很暗,太阳还没有出来/你我之间,有空气飞扬/我说你是草原/是草原明亮的眼睛/这是我渴望马匹的清晨/整夜我都盼望,有蹄声响起/你总是固执己见。/这么多年,一朵格桑灿烂于夜的时辰/就是甘南。早上六点/其实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的六点/风吹过,这地方/被一丝一丝的寒风所利用着/这种时候/我会记住草原的颜色/记住她的歌声/记住那匹渴望已久的马/太阳出来了,这是寂静的甘南的草原/男人在放羊,女人在河边打水/我已没有什么事可做了/我沉默不言”。5诗人走近甘南,在诗中,你就是甘南,诗人与甘南合称我们,并且相互走近,诗人喜欢这里,“拥抱、亲吻、害羞”一系列情绪词表达了诗人走近甘南的感受。同时,甘南与诗人的故乡又是不一样的,在这里诗人也在想念故乡,他渴望有马匹,有蹄声想起,但这里却是寂静的,有灿烂的格桑花开放,有放羊的男人,打水的女人,而诗人自己无事可做,除了看到眼前的这里,也在念着过去的自己。
在嘎代才让的诗歌中,“兰州”是一个频繁出现的词汇,“兰州还在下雨,站在城郊的马路边”6、“今夜,兰州的大街空旷/夜风吹着干净的衣服和我的骨肉/我在等有人来喝酒/......在兰州,我不奢望一瓶好酒了/虽然他们在某个角落还能喝”7、“来到兰州,来到这个开发几十年的城市/忘记了忧伤”8,诗人以兰州这个城市为中心,对兰州的生活细节,季节转变,发展变化等各个方面进行描写,同时将自己的情感融入这座城市,充分体现了他诗歌的地域文化与现实相结合的特点。
作为一个藏族作家,嘎代才让深受宗教文化的影响,藏文化因素渗入他的心灵与记忆中,成为其作品的文化内蕴。“独坐菩提树下。/背后的光,带有信仰的光泽/令人想到无羁的灵魂,日暮般的悲壮/包含了生死;超凡脱俗/像一颗颗闪光的眼泪在作祟/而受孕的生命,属于不时被/镀金的高处。/属于风,属于江河,属于神秘,/属于暗夜里,/燃不完尽的一盏油灯:肃穆、祥和,/当莲花矗立/于大地。与万物一同呼吸时/被冰雪滤过的芬芳,/能否繁衍至比信仰更辽远的,/比生殖更为重要的/一个复活的季节?/春夏秋冬:在摇动——/风雪之摇动,花蕊之摇动/硕果之摇动,/鹰翅长久地摇动。已将一切/美与善的姻缘,/还给了人类原有的心智。/于是,佛陀端庄静思/慈悯心顿生:/眺望雪原,望不到梦的边缘/高空下璀璨的星辰,在黎明时分/不明缘由地抽泣,/‘彩虹的天空,丢弃了它宿命的主人’/爱属于此刻,我奉命传送”9藏民族的宗教信仰不是空洞的、抽象的,而是借助一些常用意象去连接人与神的世界,以达到超脱自我的淡然境界。诗中出现菩提、油灯、莲花、佛陀、雪原等意象,以静坐思索为主线,从“无明”到“老死”,再到生命的诞生,生生死死,因果相循,这里有美好的相逢,亦有悲伤的离别,正是在这相逢与离别的时刻,情感达到爆发的临界点,爱在此时显现出来。诗人通过对意象的描摹,对藏传佛教思想的渲染,展现了生死轮回的淡定与智慧,以及对真情的传递与颂扬。
《谶书》中“我向长者打问/是一座长有菩提的庭院吗?/我和一位苦修一生的姑娘擦肩而去。来不及牵手。/来不及思念/我把这一场梦,称作‘天空’/留下了生动的谶记,并且说出了诸多/神袛的秘密……/长者笑了,默念经文,不作答”,诗人找寻长有菩提的庭院,就是在找寻佛陀,欲将自己对姑娘的爱慕,以及错失爱情的失落之情与之诉说,而得到的结果是长者的微笑不作答,“我”没有领会长者的意思,没有得到解脱,“我只身一人守候宗教的城堡/为你取暖”,“我”挣扎在对姑娘的爱恋中,相爱却错过,遇到得不到,“我爱上你,如同一头豹子,逼上山崖/抖动花纹,惊吓半个西藏——/黑暗中没落的国度,哽咽不语/像我的女人,发辫修长,不愿卸下嫁妆/黎明前的起身,传唱半截梵音中的英雄/十万明灯,集体嘶鸣……”10诗人将抒情与叙事完美的结合在诗歌中,让读者在他的叙述感受着他的情感的波澜起伏,体念其思想的深度。
嘎代才让感念万物,心怀慈悲,年少时将一只小绵羊送到了屠夫手上,多年以后还会梦见小绵羊,心里忏悔不已,为小绵羊写了一首组诗来表达忏悔之情。诗歌分为八个部分,分别是慈悲、忏悔、祈祷、回眸、瞬间、轮回、牺牲和挽歌,从小标题的拟定就可以看出嘎代才让是藏传佛教的虔诚信仰者,“自从,丢弃那只绵羊后/身边的野花从未停止绽放/今夜,我在如歌的草原上入睡/星辰之下,泪水不断”、“佛啊,我看见了虚空的大地/疼痛便抓住了我”、“我注定要成为一个赎罪之人/为自己的信仰与良心而后悔莫及”诗人丢弃了绵羊后,又遇到许许多多的绵羊,但是都不是曾经的那只,寂静的夜里,对绵羊的思念化为止不住的泪水,空洞的大地,再也没有了属于自己的绵羊的身影,“我”为“我”曾经的错误决定而后悔不已。“手执最后一份经卷/一遍遍长诵不止,怀抱羔羊,长久醒来”我为你诵经,为你祈祷,既是我的忏悔,更是对你美好的祝愿。“想问,你的生命将如何转移?/你的轮回中有我的影子吗?”11藏传佛教认为生命是轮回的,生生世世,永不间断,诗人在诗歌的末尾处发问,你的轮回中是否有我的身影?诗人的内心是复杂的,希望有亦希望没有,有的话我会向你表达忏悔,又希望没有,这样你就可以忘记这一切悲伤,开始新的生活。
作为“藏族第三代诗人的领军人物”12,嘎代才让以其独特的诗歌之旅闪耀于当代诗坛。他以藏地为精神高地,书写着个体的情怀和民族的展望。他的诗歌具有地域文化与宗教文化的双重特性,正如哈森所言:“嘎代才让血液里的浓浓乡愁,导致他的生命注定沉重。而作为藏民族母亲最疼爱的儿子,他的诗歌,背负着为那片土地、那片天空、为家园为同胞不停书写的重任。”13嘎代才让以其创作,昭示了新生一代年轻的藏族作家对故土和家园的守望与探求。
注释:
1.哈森:《嘎代才让和他的诗歌》,载《文艺报》2010年6月2日。
2.朱万曙:《地域文化与中国文学——以徽州文化为例》,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4年第4期。
3.嘎代才让:《青海 青海》,载《诗刊》2006年5月下半月刊(总第497期),第62页。
4.嘎代才让:《青海》,载《作品》2006年第 7期,第76页。
5.嘎代才让:《我在甘南》,载《诗选刊》2005年第11.12期合刊“中国诗歌年代大展特别专号”,第6页。
6.嘎代才让:《兰州下雨》,载《诗潮》2006年1-2月号,第62页。
7.嘎代才让:《不能再把兰州喝醉》,载《诗潮》2006年1-2月号,第62页。
8.嘎代才让:《暮色:黄河边漫步》,载《诗潮》2006年1-2月号,第63页。
9.嘎代才让:《赞丹呗嘛》,载《民族文学》2015年第6期。
10.嘎代才让:《谶书》,载《中国诗歌》2012年第7期。
11.嘎代才让:《对一只小绵羊的怀念》,载《民族文学》2009年第7期,第112-113页。
12.邱婧:《嘎代才让与属于他的西藏——嘎代才让诗歌创作论》,载《扬子江评论》2011年第4期,第59页。
13.哈森:《嘎代才让和他的诗歌》,中国作家网,http://www.chinawriter.com.cn/bk/2010-06-01/44526.html。
节选自《文化地理视域中的当代藏族文学研究》第十章第八节

徐琴,女,陕西汉中人。中山大学文学博士,西藏民族大学文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致力于现当代文学研究和藏族文学研究,在《当代作家评论》《当代文坛》《小说评论》《民族文学研究》《青海社会科学》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70余篇,其中多篇论文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全文转载。出版学术专著《文化身份的建构与书写——当代藏族女性文学研究》《文化地理视域中的当代藏族文学研究》等。主持 “当代藏族文学与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建构研究”“文化地理视域下的当代藏族文学研究”“当代藏族女性文学研究”等三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嘎代才让,藏族,生于1981年9月,中国作协会员、鲁迅文学院第十届高研班学员。在《人民文学》《民族文学》《诗刊》《星星诗刊》《章恰尔》等刊物发表大量汉藏双语诗作,作品入选六十余种重要诗歌选集,被译为英、法、德、日、朝鲜等多种语言文字。著有诗集《西藏集》等多部。曾荣获“全国十大少数民族诗人”、“滇池•80后十家诗人”、《民族文学》年度诗歌奖、“诗选刊•2005中国年度先锋诗歌奖”、首届“安康诗歌奖”、甘肃省第五届少数民族文学奖一等奖、第六届甘肃省少数民族文学奖、“岗尖梅朵文学奖”、“唐蕃古道文学奖”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