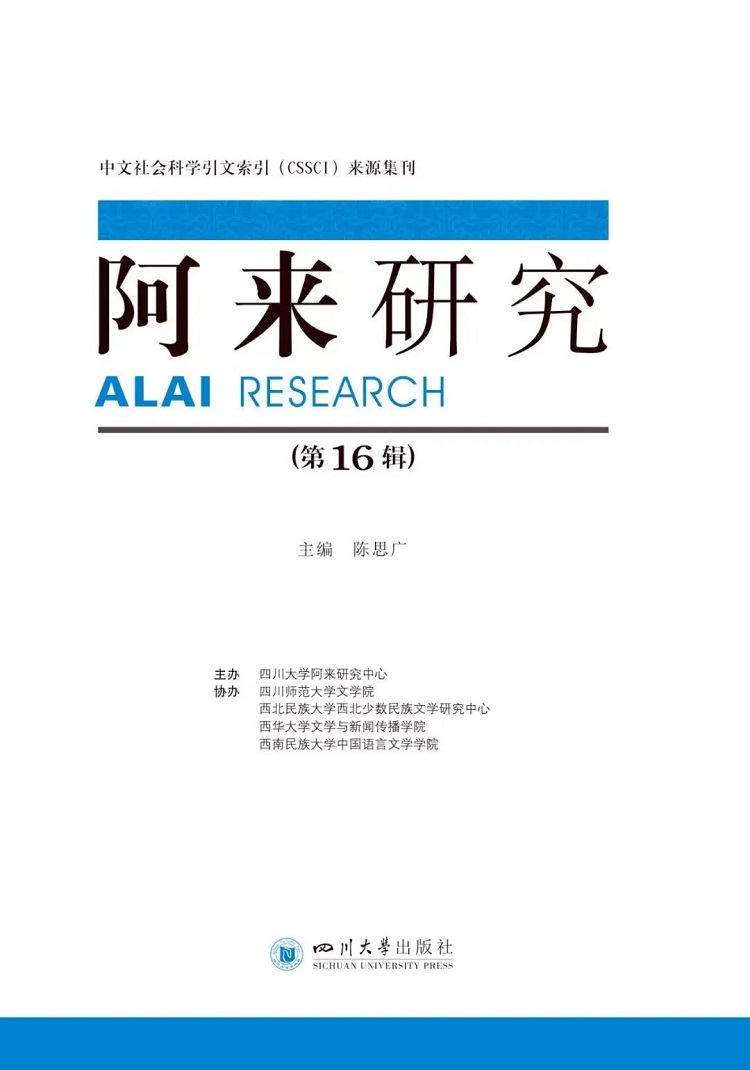
阿来的大量演讲都谈到这样一个问题——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普遍面临诸多困境:怎样充分发掘民族文化资源以形成富有特色的文学风貌;如何在本民族文学叙事的基础上,面向整个人类社会的基本问题进行发言,呈现出开阔的视野;以何种文学表达方式走进世界文坛,平等地参与文学交流;等等。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展现出阿来独特的文学观念,以及“倾听一种腔调”的小说艺术追求。然而,阿来通过演讲表达出的这些观点一直没有被专门研究过。所谓“腔调”,是指“一种叙事的格调”①。对于藏地来说,百年来因外部世界闯入而发生的历史变迁、人的精神信仰与思想面貌的迷茫与更新、由于时间轨道上的发展失衡而产生的边地状态,与特有的地域文化交融,形成了具有鲜明特征的历史风貌,对其进行文学化表达,就带来了独具一格的叙事格调。阿来对这种腔调的“倾听”,是要发掘其中能够反映历史独特性的典型性格和典型环境,从对社会表象的观察进入深层思考,追寻一种恰当的艺术化呈现方式。“倾听”过程特别强调作家的体验者和经历者身份,是以置身于内的姿态进行文学书写。这与我们现在对阿来小说艺术风貌与创作动因的认识存在很大差异。更重要的是,藏地独特的历史风貌和社会变迁将一直延续,这决定了阿来的“倾听”状态没有止境,从而使他的作品普遍具有未完成性。这一开放式文学创作特征为其小说艺术世界带来无限的可能性,孕育出了延展式创作现象,使其笔触伸向多种维度,在神话传说、民族历史和现实社会之间纵横,既可以一线贯穿完整故事,又可以散点聚焦与故事相关的诸多元素,甚至突破文体限制,以更加灵活自由的方式建构一个丰富的艺术世界。这是阿来小说创作的独特之处,也是中国当代少数民族作家在汉语写作方面值得研究的宝贵经验。
一
阿来是擅长演讲的。从目前已经以各种形式发表或出版的17篇演讲稿中可以看到,他的演讲主要围绕文学创作观念与技法展开,而且产生了很大影响力。这17篇演讲稿多数被当作散文结集出版,只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出版了一本《当我们谈论文学时,我们在谈些什么—阿来文学演讲录》,专门将这些文字资料视为演讲稿,区别于一般散文而单独成集。这一现象可以从两方面分析。
一方面,阿来的演讲具有很强的文学性,这是其演讲稿被视为散文的重要原因。阿来的演讲旁征博引且具有故事性,注重对各种例证中的故事情节展开详细讲述,尤其擅长将故事情节中最吸引人、打动人的部分展现出来,使例证中的故事与整个演讲的氛围融合在一起,与演讲中的观点阐发、说理论证融合在一起,形成了演讲稿的文学化表达。同时,阿来的演讲还特别善于运用比喻的修辞手法,这是他自身艺术修养使然,也是为了实现良好的演讲效果。对这一修辞手法大量的、恰当的运用,增强了他的演讲稿的文学性。比如《文学的叙写抒发与想象—在四川2015年中青年作家高级培训班上的演讲》中,为了区别“叙写”和“叙述”两个概念,他将叙述比喻为“一条人工渠道”,将“叙写”比喻为“一条山溪”,比喻一出,听众就明白了,山溪肯定比人工渠道更美、更自然、更富有变幻,于是,“好的小说文本”应该是什么样的,就清晰明白地阐发出来了。②
阿来演讲的故事性和丰富的比喻手法,建立在深入浅出的语言表达和流畅的逻辑基础上,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文本,严谨且富有深度的理性思考得到酣畅淋漓的挥洒,抽象的文学观念得到生动有趣的阐述,在思辨性和艺术性之间达到了巧妙的平衡状态。对文学创作问题的持续思考进一步丰富并加深了演讲的内涵和深度,面向当代文学发言又增强了现实针对性,这是一种紧随文学发展进程的发言,呈现出学者散文的风貌。
另一方面,演讲稿毕竟不是叙事抒情型的散文,而是说理性文本,收录在散文集中是不合适的。由于演讲具有一人对多人说理的特点,如何尽可能有效地说服每一位听众,就成了首先要考虑的问题。演讲的环境、听众的基本情况、演讲的类型、现场的反馈等各种因素都会直接影响演讲内容。因此,并不是演讲稿规定了演讲者说什么,而是演讲现场的状态规定了演讲者需要怎么说。这是一种交互性传播,“演讲者和听众之间的消息传送是同步的,双方同时作为消息源和接收者。传播是受情境约束的,在解释内容和信息构成部分的关系的时候,每个人的理解力都很重要”③,所以,演讲者必须根据现场信息的内容和关系构成不断调整自己的语言表达。事先准备的演讲稿有时候可以被演讲者一字不易地讲出来,但大多数情况下,演讲稿往往并不是一场演讲实际所讲的内容,它只是一份提纲,或者一个起点,甚至很多人并不事先准备演讲稿,而是即兴发挥。事后整理并由演讲者亲自确认的记录稿才是最接近实际演讲内容的文字稿。已经出版的阿来演讲稿,大多数都是事后整理的现场记录稿。
演讲的特点和性质决定了演讲稿是以理服人,同时具有审美价值,“使听众在听的一瞬间,感动起来,心悦诚服地接受一种主张,同意一种见解,改变一种观念、一种感情、一种态度,并且延伸到演讲之后的行为中”④。可见,演讲稿是我们探索演讲者精神世界的重要途径。
二
阿来的演讲多是围绕小说创作观念和方法展开的,其中独到的见解可以概括为“倾听一种腔调”。这一概括来自他的《文学的叙写抒发与想象(上)—在四川2015年中青年作家高级培训班上的演讲》。这次演讲主要谈的是“整个文学艺术上的普遍性问题”,包括“小说的演进”“小说形式的革新”“小说新语言的创造过程”“小说观念的嬗变跟递进”等,其中引用了他非常喜欢的英国女作家多丽丝·莱辛的话:“那么多丽丝·莱辛是怎么讲的,她说我有一个巨大的困难,当我需要写作一个小说的时候我总是在倾听,写作的时候在倾听,在倾听什么呢?它的中文翻译是:我在倾听一种腔调。”这里所说的“腔调”,是“一种叙事的格调……不是写在纸上的,是听得见的,语言都是要发出声音的”,对这种腔调的“倾听”需要创作者成为“事件的体验者、经历者、观察者”。⑤
这就与我们现在对阿来小说创作的认识和研究思路出现了差异。目前学界所形成的普遍性认识和研究思路,可以用第七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二〇〇八年度杰出作家”授奖词概括:“阿来是边地文明的勘探者和守护者。他的写作,旨在辨识一种少数族裔的声音,以及这种声音在当代的回响……阿来持续为一个地区的灵魂和照亮这些灵魂所需要的仪式写作,就是希望那些在时代大潮面前孤立无援的个体不致失语。”⑥然而,这一认识和思路将阿来与他作品中所表现的内容对立起来,似乎阿来是一位探索者,记录了一种特殊化甚至神秘化的“少数族裔的声音”,从而将这一地区作为时代大潮面前弱势的一方。虽然很多学者是从阿来的藏族身份出发,研究这位少数民族作家如何书写少数民族地区的历史、人文与生活,但基本思路仍然会回到这种普遍性认识中。这些都与阿来演讲中表达的创作动机和文学观念相悖,是仅着眼于作品艺术风貌层面的判断,也是在汉族文学和西方文学长期熏陶下形成的审美习惯和研究思维惯性所致。
阿来在第七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二〇〇八年度杰出作家”获奖演讲中,表达了不同的观点:“我的写作不是为了渲染这片高原如何神秘,渲染这个高原上的人们生活得如何超然世外,而是为了祛除魅惑,告诉这个世界,这个族群的人们也是人类大家庭中的一员。”“我自己就曾经生活在故事里那些普通的藏族人中间,是他们中的一员。”⑦
可见,阿来确实在故事中表现出了藏地生活和文化的独特性,但他不是一位探秘者,也不是一位守护者,他并不致力于刻意展现藏地的文化异质性,而只是为了展现这一文化氛围中的人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所做出的特有价值取向和灵魂挣扎。这种文化氛围、特定历史条件、价值取向等都是他所熟悉的,他在习以为常的文化氛围和生活环境中观察和表现他所熟悉的人,用他这次演讲的题目来概括,即“人是出发点,也是目的地”。这种创作状态在很大程度上与汉族作家书写汉族地区的故事无异。
基于这种小说观,他坚决反对东方主义式的藏地叙事,他在多次演讲中都详细谈过,并且为此专门做了《地域或地域性讨论要杜绝东方主义—在中澳文学第三届高峰论坛上的演讲》,提出西藏被视为“异域”,导致文学对藏地的书写受到了一种“先验的规定性”,西藏成为纯粹想象中的神秘地域,“一个祥云缭绕的宗教之国,一个遗世独立的香格里拉”,文学不再正视这里实际存在的问题,形成一种探秘式表达。⑧作为一个在藏地生活的人,阿来从最初走上文学道路至今,一直致力于书写最真实的藏地状态,以此进入更宏大的历史审视与反思。他清醒地意识到,如何表达青藏高原上的藏人的生活,如何将藏人真实的声音艺术化,是重要问题。
由此形成的阿来的边地意识很独特,并不是相对于中原文化或者某种中心文化而自居于边缘地带,不是一种空间意义上的感受,而是转换成了时间意义上的感受,如他在演讲中所说:“苏醒过来的人们,看到自己居然置身在一个与其他世界有着巨大时间落差的世界里。”⑨在他眼中,藏地千百年来滑行于一个既定的历史轨道,外界社会的高速发展使世界突然闯入藏地,虽然都处于同一个空间中,但社会发展程度却使藏地落后于外界,并促使藏地加速发展,产生了时间意义上的落差和激流。阿来在演讲中最常谈论的是“时间落差”,是“落后”与“进步”的对立,是一个“闭锁的社会”突然被打开,面对已经高度发达的世界,所产生的惊异与不知所措。在讲中国人对“落后就要挨打”这句话的认同感时,阿来说:“作为一个中国的少数族裔的作家,这种经验无疑更加牢固。”⑩充分体现了他基于时间意义产生的边地意识。
三
在时间意义上产生的落差与激流之宏大声音,以及其中交响着的藏地普通人之复杂心声,是藏地近百年来最独特的“腔调”,它迥异于其他地区,其中的震颤,是世界先进文明在历史变革时期所远不能及的,是藏地千年历史滑行轨道与突然闯入的世界文明进程相撞击的声音,是藏地宗教文化与共产主义信仰相撞击的声音,是藏地土司制度与新的人民政权相撞击的声音,是历史大变革进程中农奴翻身之喜悦声音以及诸种其他声音相交织的“腔调”。阿来敏锐地捕捉到这种“腔调”,并将之艺术化为小说作品。然而,如此巨大的历史震颤不会一蹴而就,百年时间在历史长河中不过是片刻光阴,由此,这种“腔调”注定将会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延续。随之发生的人的精神变迁不仅长期延续,而且是复杂多面的,很难用纸面上的文字穷尽,由此这种“腔调”注定由无数声部组成,即使以文学的方式将其抽象概括,被典型化的声部也难以历数。阿来所倾听的“腔调”,在其小说作品中是无法完成描绘的,始终处于一种“未完成”状态。
六卷本长篇小说《机村史诗》是非常典型的例子。一方面,这部作品能够呈现出这样宏大的规模,在故事中塑造如此多的人物形象,但又不冗长乏味,正缘于这种未完成性。作品每一卷都在一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展开故事,而每一卷的故事都无法完成对村民精神变化的描绘,于是就需要展开下一卷的故事。从新中国成立之初藏地纯朴民风并未发生太大变化,到1967年,从人性和自然环境两个方面,分别围绕达瑟与达戈的故事、泥石流对机村土地的影响,讲述民风与信仰的改变。这是一个随时代变化而继续发展的进程,在第五、六卷中,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进入机村,一部分年轻人在新的历史环境下开始迷失于金钱的漩涡,精神世界逐渐被异化,在传统价值体系面临崩溃的情况下,机村成了“空山”。但这六卷本故事仍然无法完成对这一历史进程的描绘,正如作品后记中所说:“这半个世纪,中国进行了史无前例的社会实验—从政治到经济。……在政治运动的冲击下,在经济潮流的激荡中,乡村不断破碎,又不断重组。断裂,修复,再断裂,再修复……这个过程,至今还在继续。”⑪
另一方面,这一进程中的声音是复杂多面的,而六卷本故事只能按照叙事逻辑一环一环地讲述,每个故事在自身的艺术世界中是立体丰富和相对完整的,但是无法将阿来倾听到的“腔调”全部容纳进去,仍然处于未完成状态中,于是出现了《机村史诗》的延展式写作。六卷的故事是作品主体,“这样写完了觉得还不够,我又写了十二个小故事。六个关于新的事物,六个关于与新社会适应或者不相适应的人物”⑫。对于六个主体故事而言,这十二个小故事具有注释性,是作者在生活中更仔细深入地“倾听”之体现,目的在于进一步描绘和阐释主体故事中蕴含的“腔调”。马车、报纸、水电站、脱粒机、电话和喇叭,是这六个时代中出现在藏地的新鲜事物,是社会生活在时间意义上发生突进的诱因。瘸子嘎多、秤的新主人、马车夫麻子、自愿被拐卖的卓玛、丹巴喇嘛和番茄江村,这六个人物是时代转折期迷茫与彷徨的典型形象。无论是六个事物还是六个人物,其实都是在解释藏地百姓在特定时代下,面对新境遇和新思想时表现出的无所适从及其原因,是与主体故事密切相关却又属于不同侧面的人的命运交响曲。这十二个小故事虽然外在于主体故事,却呼应着每个主体故事的内在精神,以更自由灵活的方式诠释着作者倾听到的“腔调”,不追求有始有终,甚至可以把人物姓名都省略,只做剪影化素描,以不完整的方式书写无法完成的故事,而这种不完整,正是被时代洪流打破后努力重组的传统乡村图景,这种形式本身也成了一种隐喻。
《尘埃落定》同样具有未完成性,主要表现在延展式写作方面。作品中最能反映藏地“腔调”的,除了傻子少爷之外,还有行刑人尔依和银匠,由于这两个职业是世袭罔替的,从他们的言行举止中能窥见藏地特有的古老文化韵味,他们身上充满了藏地千百年历史中的传统美德,也夹带着无数代传承下来的灵巧和野蛮。然而,为了使故事内在逻辑顺畅,防止无效情节旁逸斜出,傻子少爷、行刑人尔伊和银匠成为“当时未能写的完全的人物”⑬。因此,阿来在《尘埃落定》完成后,又继续围绕行刑人和银匠两个人物形象,创作了两篇短篇小说,分别是1996年发表于《人民文学》上的《月光里的银匠》和发表于《花城》上的《行刑人尔依》。另外,在创作《尘埃落定》之前,阿来于1986年已经完成了短篇小说《阿古顿巴》,可以视为他在寻找小说灵感过程中的实验,“本身就是对故事可能性的探索”⑭。这三篇小说于2021年由浙江文艺出版社结集出版,书的副标题是“《尘埃落定》外篇”,意味着它们都是《尘埃落定》的延展式创作成果,并对这部长篇小说起到注释作用,比如对《尘埃落定》中重要的“罂粟花战争”,在《行刑人尔依》中以行刑人的视角进行了不同侧面的描绘和解读,又比如《尘埃落定》中土司权力的传承,在《月光里的银匠》中通过银匠家族的骄傲折射出来。
从未完成性的角度来看,《云中记》这部作品比较独特,它似乎已经完成了对地震后藏地灾民心理变化的展现,而且目前尚无延展式作品出现,但是,“之所以在汶川地震十年后,我才动手写《云中记》,并不是因为我缺少材料、没有故事,或者不能意识到故事所蕴含的意义,而是因为莱辛所说的‘腔调’尚未被听见”⑮。从小说内容来看,阿来所要倾听的“腔调”,并不是灾后重建过程中百姓的种种不适和思想转变,而是永远无法改变的藏地灾民对“根”的向往,是透过生活表象倾听到的富有文化意蕴的心声。小说中时间意义上的激荡来自外力,一场地震突然改变了云中村的生活轨迹,使村民们被迫迅速转移并开启新生活,从山间古老村落跨越式快进到现代化乡村。而阿巴执意回云中村,折射出时间快进过程中藏地灾民对“根”的精神依恋,他“突然昂起头来说:还有死去的人,还有山神”⑯,这正是大灾难中属于这片少数民族聚居地的独特“腔调”。作品中大量篇幅描绘阿巴在云中村如何招魂,如何行使祭师使命,其实是植根于本土的原始精神信仰对纯朴人性的召唤。云中村消失了,而这种原始精神信仰一直存在,不仅牵引着阿巴,还牵引着所有从云中村转移出来的人。从这个意义上讲,《云中记》是把一个深沉丰厚的话题浓缩成了安魂曲式的故事,它仍具有延展的可能性。
四
阿来小说的未完成性使其艺术世界具有了开放式特征,以长篇小说为主体,不断延展出一系列短篇小说,延展作品既是对主体作品的有效补充与艺术化诠释,又与主体作品互相辉映。延展创作的过程,实际是阿来不断倾听特定社会历史语境下藏地独特“腔调”的过程,不断的倾听带来了不断深入、持续更新的认识,从而为一个已经自足的艺术世界不断注入新的元素,使之越来越生动细腻,甚至出现了跨文体的延展,在散文创作中继续对小说里未完成的,或者无法用小说形式完成的内容进行艺术展现。比如散文《灯火旺盛的地方》对小说《机村史诗》中的伐木场和觉而郎峡谷的现实原型——203伐木场和纳觉山沟进行描绘,既有对“以建设的名义,以进步的名义”⑰使蓊郁森林消失的反思,又有对纯朴美好历史一去不返的失落,甚至有作者的童年回忆。在小说中作为场景而存在的伐木场和峡谷,在散文中成为直接抒情的对象。又如散文《德格:湖山之间,故事流传》对小说《格萨尔王》进行了延展,对小说中雪山、湖泊、城堡、兵器、部落等的现实原型以抒情的方式进行了艺术表现,并借助散文文体自由灵活的优势,与小说内容多次穿插,有效丰富了小说故事的细节,并实现了情感升华,尤其是散文最后一部分对格萨尔王故乡阿须草原的抒情,更是小说无法传达的英雄故事之悠长余韵和沧海桑田之诗意回味。由此既可以反观小说《格萨尔王》作为英雄史诗在情感抒发方面的未完成性,又可以看到阿来的散文如何与其小说实现了辉映。
阿来在小说创作过程中对藏地独特“腔调”的倾听,以及由此带来的作品未完成性,为中国少数民族作家进行汉语写作提供了一种值得借鉴的文学经验。
从文学发展的角度来看,小说的未完成性及其带来的延展式创作现象是边地文学创作的需要。阿来多次在演讲中谈道:“真正面对甘孜、阿坝今天的社会现实时,会发现在中国过去的文学经验里,对其是缺乏书写和表达的。这一缺乏表达和书写的现象,用苏联作家肖洛霍夫的一部小说的名字来概括叫作‘未开垦的处女地’。”⑱在这片“未开垦的处女地”上,最宝贵的是本土民间资源,而由于从来没有开掘过,这些资源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处于自由生长状态,以口头传播的形式一代一代地传承着,每一位传播者都会有意无意地进行一些加工,生发出多种多样的版本,由此形成了深厚而陌生的文学“富矿”,具有丰富的文学化的可能性,虽然也曾有书面文学出现,但是大多封存于寺院之中,并且成为宗教传播的手段,被人为地神秘化了,脱离了社会生活。在这种情况下,“倾听”就成了文学创作的第一步,持续地“倾听”就成了开垦处女地、积累边地本土创作经验的必要手段。在创作过程中,始终以未完成的态度保持一个开放式的艺术世界,不断以延展的方式将持续“倾听”的结果文字化,有利于尘封千百年的民间资源的激活。阿来正是以这种方式激活了阿古顿巴的传说,塑造出《尘埃落定》中的傻子少爷形象;激活了格萨尔王的传说,完成了长篇史诗小说《格萨尔王》;激活了嘉绒藏语中泛神泛灵的感知方式,转移到汉语中创作了《云中记》。
在对边地本土文学资源进行发掘的基础上,还要用恰当的语言文字进行创作。对于少数民族作家来说,用本民族语言写作是得心应手的,而用汉语写作,则会面临一定的困难。阿来对此深有感受,他说:“我是一个用汉语写作的藏族人。”⑲这意味着他在文学创作过程中要穿行于汉语和藏语之间,而困境并不在于汉语运用不娴熟,他说:“我的困境就是用汉语来写汉语尚未获得经验来表达的青藏高原的藏人的生活。”汉语对边疆的书写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并不多见,“这样零星的经验并不足以让我这样的非汉语作家在汉语写作中建立起足以支持漫长写作生涯的充分自信”⑳。这或许是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在汉语写作中普遍存在的困难。阿来以一种“未完成”的方式,对他所“倾听”到的每一种藏地独特“腔调”的不同侧面分别进行文学书写,使每一部作品在保持自身艺术世界完整丰富的同时,不断延展出新作品,最终以作品群的创作规模实现了文学表达的成功。同时,在持续不断的“倾听”中,从藏族民间口耳传承的各类神话传说里汲取营养,逐渐捕捉到最具藏地特色的“腔调”,自然就能够在汉语写作过程中选择最恰当的语言风格和叙事方式,有效抵消语言方面的巨大困难。
从更深层次来说,阿来为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走出“边缘化”困境提供了一种有效方法。由于民间资源开发不足,汉语书写经验匮乏,加之文化的现代化发展起步较晚、起点较低等原因,少数民族文学作品普遍处于中国文坛的边缘地带。有学者统计,关于最近一届骏马奖获奖作品,“普通读者和大众传媒对骏马奖花落谁家的结果并无关注的意兴,更无购买和争相阅读这些作品的意图。或许对骏马奖的遇冷情状早已司空见惯,所以出版社没有对获奖作品进行加印,网上和各地实体书店亦没有‘囤货’和‘码垛’的促销行动”㉑,足以反映这种“边缘化”困境。阿来的作品能够被读者广泛认可,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始终对藏地独特“腔调”保持“倾听”状态,追寻藏地社会变迁的深层原因,以文学创作活动深度解析外部世界与雪域高原之间的历史互动。《尘埃落定》描绘了近代历史变局在藏地的反映,以及藏地土司制度瓦解过程中藏族人民对外来入侵者的绝地反抗,在两者间的相互猜疑与拉锯过程中,折射出以傻子少爷形象为代表的荒蛮却纯朴的藏地传统文明不得不终结的无奈。《机村史诗》的大故事透视出历史大变革时期藏地百姓走进新时代的曲折历程及其原因,这是一种双向反思,对雪域高原的传统文明和外部世界的全新制度同时发出追问。《云中记》描绘了灾难后藏地百姓的心灵漂泊,以及在汉藏杂居环境中对故土的依恋和寻根—新的居住地固然好,但离开故土之后,方知魂牵梦萦的旧居才是自己的精神寄托。阿来深度解析过程的“未完成”状态为进一步探索留出余地,从而以具有高度开放性特征的艺术世界不断吸纳新的思想内涵,广泛吸收现代文化潮流,并实践新的叙事技巧,增强了文学创作面向现实世界多种侧面和多重维度的能力,这不仅丰富了阿来作品的艺术表现力,而且使作品叙事在更宏大的视角下展开,使外部世界能够充分进入作者视野。阿来的作品虽然讲述的是藏地故事,但回应的是中国社会乃至人类社会共同的命题,从而站在了更高的层面观察雪域高原,有助于化解藏地与外部世界之间的隔膜,进而获得了阐释的多种可能性,并推动作品走出了“边缘化”困境。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现代文学文体理论整理汇编与研究(1902—1949)”(17ZDA275)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阿来:《文学的叙写抒发与想象(上)—在四川2015年中青年作家高级培训班上的演讲》,《当我们谈论文学时,我们在谈些什么—阿来文学演讲录》,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17年版,第74页。以下引文若出自此书则只标篇名、页码,不再标明出处。
②阿来:《文学的叙写抒发与想象(上)—在四川2015年中青年作家高级培训班上的演讲》,第67页。
③史蒂芬·R.布莱顿、迈克尔·D.斯科特:《演讲学:第7版》,嵇美云、陈一鸣、周冬敏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1页。
④唐涤非:《演讲学简明教程》,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01页。
⑤阿来:《文学的叙写抒发与想象—在四川2015年中青年作家高级培训班上的演讲》,第65、73-74页。
⑥谢有顺:《第七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专辑》,《当代作家评论》2009年第4期。
⑦阿来:《人是出发点,也是目的地—第七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获奖词》,《阿来散文》,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58、159页。
⑧阿来:《地域或地域性讨论要杜绝东方主义—在中澳文学第三届高峰论坛上的演讲》,第232-233页。
⑨阿来:《地域或地域性讨论要杜绝东方主义—在中澳文学第三届高峰论坛上的演讲》,第231页。
⑩阿来:《文学和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在罗马亚非学院“中意文学论坛”上的演讲》,第239页。
⑪阿来:《一部村落史,几句题外话—代后记》,《机村史诗Ⅵ·空山》,浙江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255-256页。
⑫阿来:《一部村落史,几句题外话—代后记》,《机村史诗Ⅵ·空山》,浙江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257。
⑬阿来:《行刑人·银匠—<尘埃落定>外篇》,浙江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第2页。
⑭阿来:《行刑人·银匠—<尘埃落定>外篇》,浙江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第5页。
⑮阿来:《关于<云中记>,谈谈语言》,《以文记流年》,作家出版社2021年版,第4页。
⑯阿来:《云中记》,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第14页。
⑰阿来:《灯火旺盛的地方》,《从拉萨开始》,华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157页。
⑱阿来:《文学观念与文学写作问题—在四川省中青年作家培训班上的演讲》,第2-3页。
⑲阿来:《我只感到世界扑面而来—在渤海大学的演讲》,《阿来散文》,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66、167页。
⑳阿来:《穿行于异质文化之间—在国际比较文学学会上的演讲》,《阿来散文》,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52页。
㉑乌兰其木格:《当代少数民族散文写作的创作理路及其问题—以第十二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五部获奖作品为中心》,《民族文学研究》2021年第1期。
原刊于《阿来研究》第16辑

周循,女,山东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主要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已在《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数篇,参与山东省高等学校社科规划项目研究1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