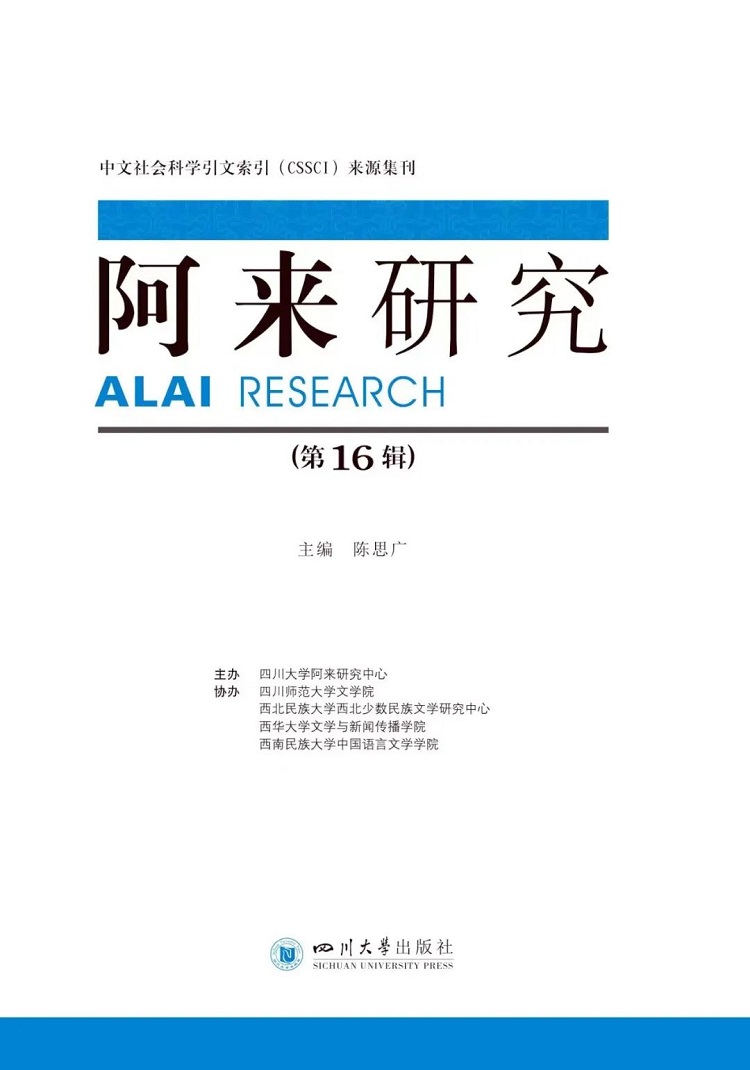
我愿意写出生命所经历的磨难、罪过、悲苦,但我更愿意写出经历过这一切后,人性的温暖和闪光。①
在这个新的时代,我以为文学还应该有一种建构能力,也就是说,在说什么不对与不是的同时,还要同时具有说对和说是的能力,要为建构新的价值观与新的精气神而作出自己的努力。②
——阿来
一、作为建构的文学:传统与时代的共同要求
关于文学的作用,美国作家威廉·福克纳1950年在诺贝尔文学奖授奖仪式上曾说过:“这是我毕生为之呕心沥血的工作,不是为了名,更不是为了利,而是要以人类精神为原料,创造出前所未有的东西……诗人和作家的责任就是写这些。他的特殊光荣就是使人类的心灵得到升华,使人类回忆起曾经引以为荣的勇气、荣誉、希望、自尊、同情、怜悯和牺牲精神,从而帮助人类继续生存。诗人的声音不只是人类的记录,它还可能成为帮助人类永存和走向胜利的支柱和栋梁。”③
观察福克纳的作品,我们可以发现,虽然他的小说看似呈现出各种各样的主题,如《喧哗与骚动》旨在展现美国南部地主家庭的没落,《熊》则体现了福克纳对白人文明的反思,但是它们全都统一在一个更深层的主题之下,那就是“苦难”。作为美国文学史中公认的最会书写苦难的作家之一,加缪称赞他:“梅尔维尔之后,还没有一个美国作家像福克纳那样写到受苦。”④而正是这样一位执着于书写生活苦难和人性丑恶的作家,在获得文学界最具影响力的奖项时,还致力于表达自己对文学重塑人的精神,帮助人类重新确认自身价值的强烈愿望,可见,如同“人的精神”对“苦难”的超越,文学对人的精神的建构,也是各时代永恒不变的议题。
较之福克纳时期,当下文学的外部语境已经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对于这种变化的理解也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其中,马尔库塞对科学技术的社会学批判具有一定的启发性意义。他指出,在今天发达的工业社会中,科学技术已不再满足于仅仅作为社会生产任务的承担者,它已经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新的社会控制形式。而这种社会控制形式新就新在它是在绝对的效率优势和不断提高的生活标准的双重基础上,依靠技术,而不是依靠恐怖,来完成对人的奴役和对离心的社会力量的征服。⑤不仅如此,这种控制如今已经扩散至最危险的领域,即对人的理性的压抑。在技术理性的操纵下,人们爱社会之所爱,恨社会之所恨,个体主动且完全屈从于社会强加给他的生活方式,人们很难认识到自己本性的和真实的需求,也就更不可能提出具有批判性质(对主流价值的反思)的要求。因此,在今天,尽管科学技术一再宣称是它将人从传统的苦难中解放出来,但实际上,它也不过是召唤了一种新的苦难而已。
不仅如此,我们还应该认识到,现代社会的高速发展还带来了对其自身的反抗,许多以往用来解决经典工业社会问题的治理方法不但不再适用,反而可能招致新的冲突。而这些都构成了对文学表达的挑战。或者换一种表述,在未来的文学语境中,“简单现代化”和“自反性现代化”将同时构成写作者思考的对象,并将持续很长一段时间。而文学若想突破或超越这种现象,以确保同一时期的思想价值体系不致沉沦,则需要展现出超越常规的思想力。
然而,现实的复杂性决定了这种“超验”很难得到广泛的实践。因此,每当我们去探索文学表达在当下可能触及的思想边界时,“返魅”的声音总是格外的强烈。这其中包含着大量脱离当下现实背景的文学作品。而对于这种声音,暂且不论科技社会所塑造的“缓冲的自我”还能否实现向“巫魅世界”时期的“渗透的自我”的转换,仅从可能性上来说,“祛魅”就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人类对于“返魅”的渴望只能带来另一个过程,虽然这个过程也许会再创造一些与传统“巫魅世界”相似的特征,但绝不是对其简单意义上的重建。⑥换句话说,一定时期人类存在的意义并不会因为“祛魅”就受到削弱,相反,人为的“返魅”,虽然可能带来一时的抚慰,但若真的将其放到现实中,大概也会一碰就碎。
因此,不论是从传统还是现代性的层面上看,重启文学的建构性议题在今天来说都显然十分有必要。也正是在这一层面上,阿来的《云中记》显示了突出的意义。
《云中记》的情节很简单,简而言之,它写的是一个叫作阿巴的藏族祭师在震后独自一人冒险回村祭奠亡灵,并在二次山体滑坡之际,陪同村子一起消失的故事。之所以说这部作品具备可讨论性,很大程度上是缘于故事发生的背景,即2008年发生在中国四川省的那场地震。地震所造成的生命困境赋予了小说苦难的性质,也赋予了人的自我超越更大的阐释空间。《云中记》虽然并未脱出苦难书写的大范围,但相较于传统的苦难书写,它显示出了对复杂题材的出色的处理能力,以及思想内涵上的深刻意义。
谈到苦难书写,中华文化几千年的文学史很大程度上就是一部苦难的书写史,作为一种总体性的情感,苦难几乎构成了文学所涉及的所有生活的本质,甚至人类历史惯用的社会形态和阶级秩序等分野,在苦难的面前都显得模糊而不可辨。几乎可以这样说:苦难就是一种永远都无法克服的生存的本质,而正是这种无法克服性,引发了人类对终极价值关怀的追求,从而建构起人类精神的历史。因此,直到现在,苦难书写的题材仍在持续地更新,这其中,包括人与工业生产之间的抵牾,还有女性的生存困境,都为苦难题材的丰富做出了贡献。但是,与苦难题材的日渐发展相对应的写作者对苦难题材的处理,却呈现出一定程度的滞后性。这主要表现为:当写作者企图通过文学的批判性功能为所谓的“受难者”代言时,往往会忽略“批判性是一种现代性的预设,同时也是一种总体性的思维方式,它有赖于叙述者在历史总体化的过程中占有主体性的地位”⑦。而正是这种历史的主体地位,使得批判者在为某一阶级代言的同时,能够将一种较为明确的社会理念和变革诉求作为目标。但事实上,现今社会发展阶段中的写作者已经很难具备这样宏大的视野,更不要说主体性地位,因此,作为逐渐脱出历史主流的边缘性群体的写作者看似充满正义的发声,很可能只是生产了一种普遍情绪,这种情绪虽然也暗示了社会结构中存在着某种失衡,却无助于建立新的与社会形态相适应的思想力量,导致这些作品看起来似乎是费了很多心思,也倾注了很多情感,却将问题弄得更复杂了。
而在对题材的具体处理上,如果说传统写作模式中“揭示—批判肇因”的逻辑在处理人类社会的苦难时还有用武之地,那么对于《云中记》所书写的那种更为困难的苦难题材—天灾,这种写作模式则完全丧失了它的作用。毕竟天灾的特殊性就在于苦难的发动者是自然,是一个无法提供情绪以及消化情绪的抽象的主体,因此,对无妄之灾的注解就更容易发展为无根的控诉,当全部的情绪被强制执行为人的个体义务时,写作者就只能继续向“伤痕文学”的阵地退守,或是对这种情绪做战略上的转移—比如转而关注灾难中的人性善恶。
不同于简单化的退守或转移,阿来的《云中记》向着这道难关发起挑战,作品对天灾的阐释以及对人的尊严、信仰和其他人性中固有的美好品质的建构,与传统的灾难书写形成了显著的差别,从而为当代文学批评提供了很大的讨论和重新阐释的空间。
二、尊严的丧失与重建:关于“阿巴之死”的再讨论
作为灾难语境下文学的精神建构,《云中记》最主要的贡献就在于它重新建立起了人的尊严。
在古罗马,尊严这一概念最初被发明来指代个人在社会中具有一种相对其他人而言的优越性。后来西塞罗将这种优越性扩大到全体人类身上,并将尊严的依据诉诸自然赋予人类的理性。到了近代,康德继承了西塞罗和皮科·米兰多拉等人的传统尊严观,将尊严的根据进一步固定在理性上。康德认为,理性是每个人拥有的先天的能力,作为理性存在者,人生来配享尊严。此外,康德还将尊严作为一种内在价值和绝对价值来看待。他在《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中说道:“在目的王国中,一切东西要么有一种价格,要么有一种尊严。有一种价格的东西,某种别的东西可以作为等价物取而代之;与此相反,超越一切价格、从而不容有等价物的东西,则具有一种尊严。”⑧可见,作为一种内在价值和绝对价值,人的尊严是人人平等且不可取代的。
那么,《云中记》如何建立人的尊严?或者说,尊严何以需要重建?
好多人死了,还留在山上。还有一些受重伤的人,断了腿的人,折了胳膊的人,胸腔里某个脏器被压成了一团血泥的人,还躺在全国各地的医院,或者在某个康复中心习惯假肢。⑨
这是阿来《云中记》中为数不多的对于地震中人的状态的描写。关于地震对人类生活的毁灭,尽管小说在题记和叙事中都一再强调“大地震动,只是构造地理,并非与人为敌”⑩,但在自然的绝对力量中,人类注定只能是被动的,不仅如此,人所遭到的打击还是无差别、没有预兆的。在这种打击下,人类社会中一切用来区分阶级的标准都在一瞬间被抹去,房屋、财产、亲人,甚至肢体都在顷刻间化为乌有,取而代之的是废墟,而废墟意味着一切物的积累的丧失。
如果我们将文明看作一种演进,那么那些随着时间的推进而逝去的文明,便是废墟的一种,比如埃及的金字塔、我们的三星堆遗址,便是这种废墟在物质实体上的呈现。但它们毕竟是由时间缔造的废墟,是自然的演进。“充斥着自然力量的地震却不是,它是顷刻间将文明打倒在地,而使其成为名副其实的废墟的一种作为,在没有任何的时间性的过渡之中,文明转变成为了一种废墟”⑪,而这种时间上的极度压缩,也使得文明与废墟之间的转换变得极端,从而构成了对人的理性的巨大挑战。
因此,对着冒险上山的干部仁钦,有人扑上去抓住他拼命摇晃:“怎么就只来了你一个人?!”⑫而面对无法用云中村传统办法医治、疼得大呼小叫的村民,“阿巴就流着泪骂人。阿巴心里有火,因为他拿那些骨头碎成了渣的人没有办法。他拿断骨都戳破了皮肉,白生生露在外面的人没有办法”⑬。
在这样的灾难中,人无法用理性要求自己,理性作为人类的天然能力,其实现的场所在这场名为地震的灾难中彻底沦陷。被掩埋在废墟中几天几夜的人们,只能让渡自己作为理性存在者的尊严,满足作为动物的最基本的求生欲和各项官能上的需求。因此,当象征着生机的直升机降落时,“云中村人脸容悲戚,衣衫破碎,像是一群刚从地狱走出来的鬼魂,向着直升机奔跑而去”⑭。
作为一种能力,理性在生物层面仍然存蓄于人们的身上,但在现实层面却无法发挥作用,尊严也是一样。当一种价值时刻处于一种隐身的状态,失去了实现的场所时,这种价值还是否具有意义?阿来意识到这种悖论:人的尊严在灾难面前沦为最不具价值的价值,隐身的价值,人在灾难中被迫丧失了作为人的尊严。
不仅如此,灾后的生活一样艰难,尤其是对于整体迁移到另一个村子的云中村人来说,搬迁并不仅仅是地理上的移动,更意味着原有的生活方式的失去,以及情感模式的转变。尤其是对刚刚从死亡的危险中脱身出来的幸存者而言,他们一方面要面对亲人离世的痛苦,一方面还要被迫去适应新的生活,抵触的情绪是铺天盖地的。
自身的抵触尚且可以克服,尊严却无比脆弱。云中村集体搬迁后,拥有刺绣技艺的巧手姑娘,因为误将有着宗教意味的莲花绣在了旗袍上,面临被刺绣坊解雇的危机;而原来的老村长在新的移民村中失去了原有的社会地位,从事起清洁队的工作;相较他人,阿巴虽然被任命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但也一直无法摆脱移民村人心中的“老乡”身份。
他们叫我们老乡。几年了,他们还是叫我们老乡。
那是乡亲的意思。
那不是乡亲的意思。要是那是乡亲的意思,他们为什么不叫他们自己人老乡?⑮
在决意回到云中村的时候,阿巴对身为乡长的仁钦抱怨新村的村民叫他作“老乡”,可见阿巴认为自己在新村并未受到真正的接纳。不仅如此,移民村所象征的现代人的生活方式也让他找不到归属感。在原来的云中村,阿巴过的是自给自足的生活,虽然村民们偶尔也需要从山下购入一些生活用品,但大多数时间,他们播种、放牧,遵循着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自然法则。但是在移民村中,小说中提到了一个细节,阿巴在向云丹买马的时候说自己很有钱,他将在家具厂打工的钱全部攒了起来。可以推断,孤身一人的阿巴,在移民村除了基本的生存需求以外,基本不消费,因此,他的生活应该是极度无聊的,是丧失了生活的意义的。所以,阿巴回到云中村的念头并非突如其来,只是在听到老村长说自己已经失去云中村的“味道”的时候,这种念头变得更强烈了,于是经过了一年的思考,阿巴毅然踏上了上山的道路。而阿巴对自己尊严和价值的找寻,也是在他从上山到与云中村一起消失这一过程中逐渐展开的。
“阿巴这个人物的命运一开始我并没有明确的定位。在写作的过程中,我跟他一起经历、一起成长,到最后,他通过自己的行动和思考了悟了生死,参透了其中的关系和秘密。”⑯其实,对于上山之后具体做些什么,初期的阿巴自己也不确定,他不确定回到云中村后应该做些什么,甚至他连是否真的存在鬼魂都不能确定,他只是出于一个祭师的责任,想着万一真的有鬼魂怎么办。相比于家具厂的工人,祭师是凝聚了阿巴更多的自我体认的职业,也是阿巴借以实现自身价值的身份,因此万一真的有鬼魂,那么安抚鬼魂便是阿巴的使命,是他身为云中村最后一代祭师应该担负起的责任。
但是当阿巴真正脚踏云中村的土地的时候,一切都变得自然而然了,他打扫房屋,祭祀山神,走过云中村的每一所房屋,将乡民对亲人的思念带到这里,尤其是在与云丹、央金和仁钦等越来越多的人的接触后,阿巴逐渐意识到,比起作为地理结构的村庄,更重要的是云中村中的每一个人。不管是死去的阿介、祥巴一家……还是活着的央金姑娘、云丹,只要他们是云中村的人,或者曾经是云中村的人,不论他们生前如何行事,或是当下怎样谋生,阿巴都希望他们能过上美满的生活。因此他将超出两匹马价值很多的积蓄给了云丹,帮助他为女儿置办嫁妆;将自己的房子留给了央金,为了有朝一日她回来时能有个地方住,即使她曾经为了包装自己而消费云中村的情怀。这是阿巴自己选择的自我价值,就是尽自己所能让云中村中不论死者还是生者都得到安慰。
其实说到底,安抚亡魂这项活动从被创造出来起就不仅是对死者的安慰,它同时也是生者自己的需求,为了更好地安顿自己的生活。如同阿来在自我阐释时所说的“纪念亡灵,与其说是信仰不如说是情感的需要”⑰。因此,只有云中村的亡灵得到安慰,活着的人才能振作起来继续新的生活。认识到这一切的阿巴找到了作为祭师的真正意义,因此阿巴的死是从容的,他是为了自己以及云中村的每一个人而去迎接死亡,与云中村一起消失是他在参悟了死的意味后的主动选择。
不仅如此,阿巴的死还意味着一种反叛,即人对自然的无差别、无目的的打击的回应。在第二次山体滑坡中拥抱死亡的阿巴用他的行动证明了,人在面对自然的死亡通告时虽然没有选择,但同时也存在着一种没有选择的选择,那就是选择体面的死亡。这就是阿巴的选择,作为一种对自然的绝对力量的回应,阿巴不仅要回到云中村,葬身云中村,而且要选择在地震所造成的山体滑坡中死去。他要重新回到那个场景,那个当初他和所有村民们一同经历过的场景,并在其中宣布:虽然地震不能为人所掌控,但人可以选择有尊严地死去;虽然地震不能创造任何的价值,但人可以通过行动为自身以及世界上千千万万的人创造价值。这是阿巴对地震的回应,也是阿来对人的尊严的回应。
需要说明的是,有学者将作为小说高潮的“阿巴之死”看作一种献祭行为,并指出在这种献祭中阿巴完成了从人性到神性的转变。这种说法虽然肯定了传统族群的宗教神性及其影响力,却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阿巴作为一个人而不是文化的附庸的价值的实现与完满,尤其是在《云中记》这样一个神灵始终未得到确证的文本中,阿巴选择死亡更多的是来源于个人(相对于神)的思考,是人的理性作用的结果,即人作为理性的载体自由地选择实现自己的本质需求。从仁钦和云丹对阿巴的选择的理解上也可以看出人对于人类整体尊严的拥护,而这种拥护也反过来确证了人类尊严还广泛地存续于人的身上。
三、价值体系的延伸:《云中记》的文学及文化意义
虽然“阿巴之死”在小说的叙述中占主体位置,但《云中记》所试图思考和建构的却远不止此。在阿巴和云中村那里,阿来不仅寄托了对人之所以为人的价值期许,更寄托了对中国文化的思辨和期望,这其中不仅包含对死亡意义的思考,还有对历经磨难后人性的闪光和温暖的歌颂。
首先是对死亡意义的思考。纵观中外哲学发展的历史,大凡著名的哲学家,在构建自身的哲学体系时,都对死亡问题有所涉及。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资源,早期的儒家和道家都提倡对待死亡采取“乐生安死”的态度,而出身于社会底层的墨家也从自身的需求出发,创造了“尚力非命”生命观。然而遗憾的是,这些观点在处理死亡在生命中的位置时,都倾向于仅将死亡看作生命的终点,是人在客观意义上的结束,从而忽视了死亡作为一种“伴随态”对个体的生命体验所造成的影响。不仅如此,在讨论死亡的意义时,我们的文化也往往倾向于对死亡作“舍生而取义”或“泰山与鸿毛”式的价值评判,而这种战略性的思维模式实际上挤压了对死亡的非功利讨论,由此导致了我们的文化一直未能深入死亡的哲学意义,给予生命本身应有的观照,这对我们的文化来说无疑是一项缺憾。在日复一日的文化实践中,这种缺憾还逐渐变得习焉不察,直到地震再一次将这项议题摆到我们的面前。
阿来率先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讲道,在地震造成的铺天盖地的悲痛中,还存在着“一点点崇高的洗礼性的东西。至少在那段时间里,好像人都一下子变好了”⑱。这种“好”正是来源于对死亡的思考。大地的轻轻摇晃迫使人陷入直面死亡的极端境遇,但同时也提供了一种反思的可能性。在突如其来的灾难面前,人们认识到了死亡的无常,也更新了关于生的价值定位,所谓的“人一下子变好了”,其实就是人在经历了死亡的威胁后的自我觉知和觉醒,并以此为基础生发出更自觉的人性意识。
而对于阿巴,阿来也让他在这种反思中走上了成为真正的祭师的道路。在阿巴的身上,死亡不再是惯常生命意义上的终点,而是一个起点,一个指引人生方向的航标。生与死在阿巴的身上完成了交汇和融合,使阿巴的生命具有了永恒的意义,而这也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对死亡的新的理解,对死亡的终极思考有时候也可以反过来指导存在的价值。
其次,如同阿来自己阐释的那样,《云中记》还实现了对历经磨难后的人性温暖的歌颂。在以往的文学观念里,强调文学的批判性往往是和追求表达的深刻性相关联的。发展到当下,深刻已经逐渐成为衡量一部作品是否成功的标准之一,而一部歌颂真善美的作品,似乎很难与深刻挂钩;不仅如此,对人性的歌颂也很容易沦为一种精神口号,往往抒情有余,但力量不足。也因此,越来越少有作家愿意在歌颂人性温暖上耗费精力。余华的新作《文城》是当下歌颂人性温暖的作品的典型代表,但学界对余华的这一新作的评价似乎并不高,也许是因为对余华的期待阻碍了对其作品的客观评价,也许是因为“指认某物为‘好’,必须有完备且系统的建构,而否定性的意见只需找到一点瑕疵,就足以激发共鸣,令辛苦建筑的肯定性大厦摇摇欲坠”⑲。近来关于余华《文城》的批评较为多见,这里不再赘述,但无论如何,这都反馈给我们一种信息:即使是余华这样颇具资历的作家,其歌颂人性正义与温情的作品也未能取得较好的效果。
《云中记》的创作正是建立在藏族人民善良淳厚的伦理认同之上的,地震的灾难背后隐含着作家对于人性的温暖与闪光的执着追求。其中,最令人动容的就是仁钦。作为云中村的孩子,地震暴发了,他临危受命,冒险上山,哪怕满脸是血,也要肩负起领导救灾工作的责任。作为干部,他沉静的指挥不仅安抚了灾民,还为云中村带来了生的希望;但作为儿子,在得知自己的母亲很可能已经不在人世时,他却没有为之分心的机会,只能倚靠在舅舅的肩头,和舅舅分享片刻的悲伤。不仅如此,地震结束后,他一面要说服村民搬迁到移民村,一面又要承担着来自上级的压力,即便这样,他对阿巴的执意上山仍然表示出了理解,尽管在这件事上他要面临失职的风险。作为沟通云中村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桥梁,仁钦的身上闪烁着理性的光芒,而他的每一个选择背后,都不仅是干部的责任,更有来自人性的要求,是人在灾难面前被唤起的勇气、怜悯心和自我牺牲精神在发挥作用。
不过,不能忽视的是,在《云中记》纯粹而朴实的人性表达中,少数民族的文化语境提供了更为丰沃的精神土壤,从而使得阿来的叙事更加稳健有力。但这无形中也对作品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褪去边地题材的陌生性和修辞性,写作者是否实现了对人物情感和动机的有效把握。在这一点上,不少学者对此提出了质疑。如对于小说中作为“醒悟者”的央金和中祥巴,李长中就称“人物的内心情感发掘有余而人物行为的合理性经不住推敲”⑳,指出他们身上所存在的人物类型化和机械化问题;刘琼更是直接表示“我觉得央金和祥巴的类型化较为明显,不如阿巴、仁钦和云丹那么丰满,那么有文学复杂性、可信度”㉑。我们不能否认这样的批评的价值,反而应该欢迎这样的声音参与到文学批评的讨论中来,但是,我们也不能因此否定阿来这部小说的成就,甚至认为“《云中记》只有木偶活动,没有成功的艺术形象”㉒,那就显得有些本末倒置。正如我们不能苛求一部小说的每个方面都尽善尽美,阿来《云中记》的个别瑕疵,并不能构成对其为文学精神建构所做出的贡献的遮蔽。阿来向着人性光辉的写作适时地向大众证明了:不存在天然让人退却的题材,作品的深刻与否只在于作家是否进行了合适的表达。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对阿来的《云中记》做建构性的阐释,并非只是想提供一种美学鉴赏,而是试图回到文本开端所提及的文学功用问题。简单地说,就是面对时代精神困境,文学能做些什么?㉓我们观察21世纪以来的文学创作,无论是执意用自然主义手法展现生活本质的非虚构写作,还是带有地域特色的工业题材叙事,无不是沉浸于工业化带来的伤痕中不能自拔,并没有提供作为当代文学创作的与现实相匹配的新的质料。一些新锐青年作家本应为文学表达找到更广阔的空间以及新的美学起点,但是他们中的多数并没有选择延续先锋性的创作策略,而是转去寻求个体经验的支持,在对历史的和西方的不断模仿和搜集中找寻着个人风格。在他们的手中,文学与当下呈现出从未有过的亲近而又遥远、复杂而又表面的关系。局面是显然的,即作为历史余数的文学创作已经无法为现实构建新的想象关系,而文学一直赖以获取思想资源的意识形态实践推论也显得有些疲惫,这都使得文学在面对时代的困境时,除了焦虑,还是焦虑。㉔
就像阿来在自我阐释中所说的那样:“科学时代,神性之光已经黯淡。如果文学执意要歌颂奥德赛式的英雄,自然就要脱离当下流行的审美习惯。近几十年来,受西方现代派文学和后现代派文学的全面影响,文学充满了解构与反讽,荒诞、疏离与怀疑成为文学前卫的姿态。我们已经与建构性的文学疏离很久了。”㉕在这种背景下,尤其是疫情发生后,面对公众对文学期待的不断提高,此时进行对阿来《云中记》的建构性讨论,也许可以提供一些有效经验。
疫情发生后,在被追问是否会书写此次疫情带来的灾难时,作家李修文曾经说过:“写灾难的目的,就是要去反思灾难,从灾难中得到精神上的成长。”㉖作为一种精神写作,阿来的《云中记》真正做到了让灾难生发出意义,让死亡指引存在。如同康德将人的尊严看作一种绝对价值,如果文学能够依赖一种价值永远留存于世间,那么那种价值就体现在这里。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百年乡土小说与乡村文化变迁的关系、启示研究及文献整理”(19ZDA273)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阿来在《云中记》“新书发布会”上的发言,2019年5月25日于北京,htps://mp.weixin.qq.com/s/CdnQQ8D_1L2WFp9_NSqsIw.
②阿来在《云中记》分享会上的发言,2019年6月15日于济南,htps://mp.weixin.qq.com/s/7RS0c7kPMp1CpSLFgXARcw.
③威廉·福克纳:《人类必胜》,《美国演说名篇》,王建华等编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95年版,第245-249页。
④转引自威廉·福克纳:《我弥留之际》,李文俊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5页。
⑤赫伯特·马尔库塞:《批评的停顿:没有反对派的社会》,《单向度的人》,刘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2页。
⑥见查尔斯·泰勒:《祛魅—返魅》,乔治·莱文编,《世俗主义之乐》,赵元译,译林出版社2019年版,第62页。
⑦陈晓明:《表意的焦虑——历史祛魅与当代文学变革》,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412页.
⑧伊曼努尔·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康德著作全集》(第4卷),李秋零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43页。
⑨阿来:《云中记》,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第4页。
⑩阿来:《云中记》,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插页。
⑪赵旭东:《地震十年祭—来自一位人类学家的手稿记述》,《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18年第2期。
⑫阿来:《云中记》,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第37页。
⑬阿来:《云中记》,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第38页。
⑭阿来:《云中记》,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第39页。
⑮阿来:《云中记》,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第10页。
⑯行超:《<云中记>:灾难的安魂曲》,《文艺报》2019年11月15日。
⑰舒晋瑜:《阿来:我敢说世界上还没有这样的小说》,《中华读书报》2019年11月20日。
⑱傅小平:《阿来:我一直在学习,相信我还能缓慢前进》,《文学报》2019年7月11日
⑲丛治辰:《余华的异变或回归—论<文城>的历史思考与文学价值》,《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1年第5期;王鹏程:《奇外有奇更无奇—余华<文城>的叙事艺术及其问题》,《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评论》2021年第5期。
⑳李长中:《写出生命所呈现的意义—以阿来的<云中记>为中心》,陈思广主编,《阿来研究》(第11辑),四川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33页。
㉑伊仁:《<云中记>作品研讨会速记》,陈思广主编,《阿来研究》(第11辑),四川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203-204页。
㉒白草:《<云中记>:一个犹疑、矛盾且诚意不足的仪式》,《文学自由谈》2020年第2期。
㉓见贺仲明:《论高科技时代的文学意义》,《文艺争鸣》2021年第3期。
㉔见陈晓明:《表意的焦虑—历史祛魅与当代文学变革》,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308页。
㉕阿来:《关于<云中记>,谈谈语言》,《以文记流年》,作家出版社2021年版,第5-6页。
㉖李修文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说:“对于灾难文学,我所理解的基本信条没有发生变化:写灾难的目的,就是要去反思灾难,从灾难中得到精神上的成长。当然,因作家自身气质相异,理解也会不同。”http//www.chinawriter.com.cn/n1/2020/0301/c405057-31611443.html.
原刊于《阿来研究》第16辑

贺仲明,文学博士,暨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广东省作协副主席,《大湾区文学评论》主编。兼任中国新文学学会副会长,《新文学评论》副主编。入选教育部2006年度“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广东省“珠江学者”特聘教授。已出版学术著作《中国心像——20世纪末作家文化心态考察》、《一种文学与一个阶层——中国新文学与农民关系研究》等,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文艺研究》《读书》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和乡土小说研究,以及当代文学批评。

吕子涵,女,暨南大学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