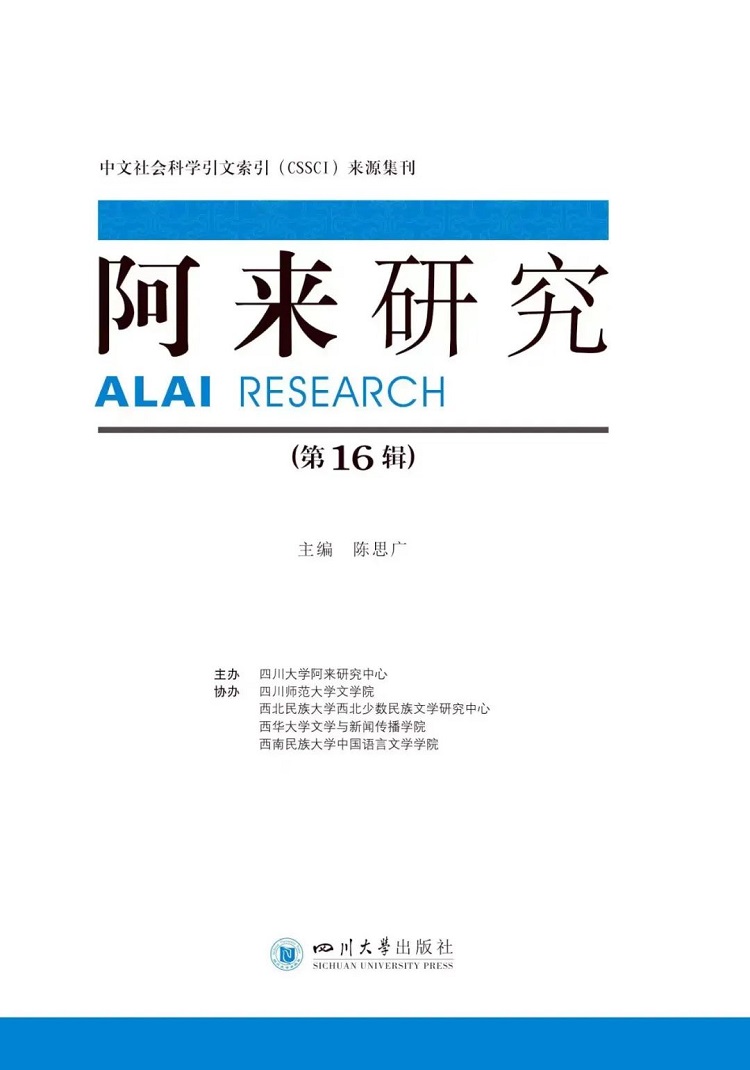
1982年6月20日,时年23岁的阿来以“杨胤睿”为名在《新草地》第2期发表诗歌《丰收之夜》,这是阿来发表的第一篇文学作品。时至今日,阿来的文学创作已经整整走过了四十年。在这四十年的文学旅程中,阿来并不能算是一个高产的作家,但他至今依然笔耕不辍,让我们惊异于他似乎不会枯竭的创作生命力。不仅如此,他的文学成就也有目共睹。他获得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等重量级的文学奖项,也是迄今为止最年轻的茅盾文学奖得主;他的作品被大量译介到国外;《尘埃落定》出版二十多年来,累计销量达到数百万册;2014年5月由四川大学阿来研究中心创办的《阿来研究》,是国内第一个以一位当代作家名字命名公开出版的学术集刊。2021年12月,阿来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所有这些,都让我们清楚地看到阿来在中国当代文学发展中举足轻重的地位。
当然,提到阿来,我们无法规避的还有他的族别。一位藏族作家的汉语书写,的确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挖掘与思考。阿来用汉语书写他的家乡—嘉绒藏地,让带有异域风情的地域书写,脱胎换骨为我们能够感同身受的历史、文化与现实,在“特殊”与“普遍”之间搭建起某种奇妙的“通约性”,同时,也“构成了当代文学叙事中的一种陌生化的新美学”①。阿来曾借用佛经上的一句话表达他的写作梦想:“声音去到天上就成了大声音,大声音是为了让更多的众生听见。要让自己的声音变成这样一种大声音,除了有效的借鉴,更重要的始终是,自己通过人生体验获得的历史感与命运感,让滚烫的血液与真实的情感,潜行在字里行间。”②回顾阿来文学创作的40年,尽管他写作的轨迹也在发生着变化,但那种对“大声音”的追求,对普遍性的执着,以及以诗意的目光对现实的审视始终是引领我们进入他文学世界的路标。其中,有很多值得我们思考的东西。比如,一位用汉语写作的藏族作家何以征服了广大的读者?他的跨族别写作为我们当下的多民族文学共同发展提供了怎样的借鉴,对国际视野下“中国故事”的讲述有着怎样启示?我想,所有这些都是我们今天研究阿来的意义所在。其实,一位作家的全部努力就是要在整体的文化脉络中获得意义。
一
阿来是一位对故乡有着特殊情感的作家。在他文学创作的40年里,他的目光始终没有离开过嘉绒藏地,他用所有的文字书写故乡。他以“低机位”的视角,摄取故乡土地上人与事的变化,在日常生活中呈现时代沧海桑田的巨变,最终将“历史的细语”汇聚成时代的黄钟大吕。
阿来的文学创作始于诗歌。年轻的阿来,在诗歌中歌唱故乡广阔的大地,绵延的群山,肥沃的草原和辽远的星空,饱含着对自由的渴望和生命的激情。然而,随着写作的深入,阿来表现出越来越强的使命感,他不再止步于激情的抒发,诗歌越写越厚重,“他笔下的神话传说和历史民俗都负载着丰富的象征意义。阿来的诗是与一个民族的心路历程联系在一起的,他即使写个人的心史和心事,也不刻意脱离民族的生存背景,而是带着深深浅浅的民族的心理烙纹”③。1989年,他以行吟诗人的姿态漫游若尔盖大草原,写下二百多行的长诗《三十岁时漫游若尔盖大草原》。这首诗在阿来以后很多次的访谈中屡屡被提起,它为阿来的诗歌创作画上了一个休止符。在此之后,尽管他依然有过少量的诗歌创作,但他的创作旨趣已经完全转移到叙事文本中。我认为,阿来创作的这种变化与他追求“大声音”的文学诉求息息相关。在提到这一创作转型时,阿来说:“(诗歌)写到后来……突然你发现一首诗歌的容量是如此有限,这个形式本身局限了你做这些表达。那么最自由的方式是什么方式?小说。”④
实际上,阿来的小说创作几乎是与诗歌同步的。1984年,阿来在《民族文学》第九期上发表短篇小说《红苹果,金苹果……》。在今天看来,这是一部像“青苹果”一样的作品,无论叙事策略还是艺术手法都非常青涩。文本中的藏族少女玛姬始终纠结于自己的族别、语言和藏民族服饰;而另一个重点刻画的人物,干部子弟“他”,更是试图规避自己的藏族族别而向汉族靠拢。整体上来看,小说存在着许多概念化的东西。但是,这篇并不算成功的作品却反映了当时藏地的主要社会问题,那就是藏地青年所产生的强烈的身份认同的焦虑。他们既被外面的世界所吸引,又因自己的民族身份而困惑。我想,在一定程度上,这也是阿来自身生命体验的折射,他曾说:“少年时代,我们一起上山采挖药材,卖到供销社,挣下一个学期的学费。那时,我们总是有着小小的快乐。因为那时觉得会有一个不一样的未来。而不一样的未来不是乡村会突然变好,而是我们有可能永远脱离乡村。”⑤或许,《三只虫草》中那个坐在山坡上眺望远方的少年桑吉,正是阿来的“自画像”。这种困扰始终缠绕在阿来早期的小说创作中,《远方的地平线》《守灵夜》《永远的嘎洛》《环山的雪光》《猎鹿人的故事》等或多或少都蕴含着相关主题。
显然,阿来在开始文学创作之初就表现出了书写“大声音”的宏大抱负。20世纪以来,对身份认同的困惑和焦虑是备受人们关注的问题之一。从个体认同到集体认同,从自我认同到社会认同,以及由此引发的中心与边缘、压制与抵抗、主体与从属,都是困扰我们这个时代最深刻的精神痼疾。可以说,阿来是在中国当代文学中最先表达这种精神困惑的作家之一,由此显示出阿来作为一位优秀作家对现实的敏锐捕捉力和深度思考能力。但是,这一阶段的作品还不够成熟。由于这种情感表达的热切,作品尽管呈现出单纯、朴素、流畅的线条,但整体上较为刻板机械,有时甚至流露出主题先行的意味。
尽管阿来改变了早期的叙事策略,但他对“大声音”的追求始终是不变的创作理念。尤其是当藏地面对现代性、全球化、消费主义等一次次“扑面而来”的冲击,阿来总是能立足于藏民族的历史与现实,对“新”“旧”文明之间的冲突进行深度思考。如果说,在早期的作品中,这种冲突更多地表现为个体对身份认同的困惑,那么,到了创作《尘埃落定》阶段,阿来则开始在立足藏地的基础上,以极具个性的叙事风格,走进更为宏阔的人类文化视域。《尘埃落定》通过一个土司家族的兴衰,刻画了20世纪上半叶在现代性的冲击下土司制度的土崩瓦解。土司制度开始于唐代的“羁縻制度”,主要是封建王朝中央统治阶级利用少数民族中的贵族对其所在地域进行统治。这一制度盛行于明代,到了清代开始衰落。《尘埃落定》讲述的是20世纪初期嘉绒地区麦其土司家族的故事。文本的开篇,麦其土司家族已经败落,连惩处一个叛逃的头人都做不到,为此,麦其土司不得不“从一个镶银嵌珠的箱子里取出清朝皇帝颁发的五品官印和一张地图,到中华民国四川省军政府告状去了”①。麦其土司的珠宝换回了现代化的武器和装备,轻而易举地杀了叛变的头人,打败了接纳头人的汪波土司。这是现代与前现代较量中毫无悬念的胜利。从此,麦其土司为他的领地打开了通向现代的大门。他成为所有土司中真正拥有一支现代军队的人,各种西洋的新鲜玩意儿也接踵而至:英国的镀金电话、美国的收音机、德国的照相机,还有令见多识广的书记官都赞叹不已的钢笔。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也被打破,傻子少爷还在边境建立了贸易市场。然而,“扑面而来”的新世界在给麦其家族带来极大物质享乐的同时,也激发了他们贪婪的欲望。尤其是特派员带来的罂粟种子在原野上绚烂盛开,点燃了人们骨子里的疯狂,引发了战争、饥荒,扼杀了人们的理智和善良,最终导致了麦其家族的毁灭。
从《尘埃落定》开始,对现代性以及“新”“旧”文明冲突的思考始终贯穿于阿来的文学创作。随后的《空山》三部曲以及阿来在“机村”的精神漫游中采撷碎片重组的“机村系列”短篇小说,延续了《尘埃落定》中的“大声音”。《空山》讲述的故事始于20世纪50年代,这是现代性对藏地发起又一次猛烈冲击的时期。外界的新事物、新思想、新概念扑面而来:
人们不断地被告知,每一项新事物的到来,都是幸福生活到来的保证或前奏,成立人民公社时,人们被这样告知过。第一辆胶轮大马车停到村中广场时,人们被这样告知过。年轻的汉人老师坐着马车来到村里,村里有第一所小学校时,人们也被这样告知过。第一根电话线拉到村里,人们也被这样告知过。⑥
一次又一次的“被告知”让机村人呈现出惶恐的神情。长久以来,他们还沿袭着维科所说的“诗性思维”的认知方式,即一种“以己度物”的思维方式。维科认为,原始人在认识不到产生事物的自然原因,而且也不能拿同类事物进行类比来说明这些原因时,他们就把自己的本性移加到那些事物上去,例如俗话说“磁石爱铁”。在《空山·轻雷》中,拉加泽里向他的母亲形象地讲述避雷针的作用,告诉母亲那些地质勘探员会“用避雷针把雷电的愤怒引入土里”⑦。这时,“老太婆不但激动,还有些愤怒:‘避雷针也是太聪明的东西吗?人太聪明神会发怒的。’在机村,有些顽固的老人,把一些新发明归类为‘太聪明’的东西。电话太聪明,发电机太聪明,收音机和录音机太聪明。降雨的火箭当然也太聪明了”⑧。老母亲的诗性思维在现代科学理性面前显得滑稽可笑,但细细想来,又是何等悲哀!其实,老母亲貌似不可理喻的思维,在格拉、多吉、索波、达瑟、达戈、驼子、拉加泽里等机村人的脑袋里也曾瞬间定格,无言地诉说机村在现代性进程中悲喜交加的一切。“机村”这个阿来文学版图中的醒目地标,让我们在民族文化的特异性中找到了人类普遍的记忆和生存秘密。可以说,机村是阿来文学“大声音”中那个最为响亮的音符,通过机村,我们抵达的是整个世界。
二
2009年,阿来在大连理工大学做了题为“世界向我扑面而来”的讲座。他提道:“对我来说,在拉美大地上重温拉美文学,就是重温自己的80年代,那时,一直被禁闭的精神之门訇然开启,不是我们走向世界,而是世界向着我们扑面而来。外部世界精神领域中的那些伟大而又新奇的成果像汹涌的浪头,像汹涌的光向着我们迎面扑来,使我们热情激荡,又使我们头晕目眩。”⑨的确,像藏地这样的边缘地带,她的每一次前行都是在仓皇中应对“扑面而来”的外部世界,手忙脚乱,应接不暇,是被动又被迫的。阿来在此,并不想从政治学或哲学的层面去探讨“文明冲突论”,他关心的是社会变迁历程中普通人的境遇,这使得他的创作带有朴素的人道主义色彩。“人”是阿来关注与书写的终极目的。面对计划经济、全球化、消费主义、信息化这些一次又一次的“扑面而来”,生活在藏地的普通人做出了怎样的选择,遭遇了怎样的生活变故,是阿来“大声音”的原初生发地。
“山珍三部”非常集中地呈现出生活在藏地的人们面对时代转型的境遇与选择。谈到“山珍三部”,很多评论家从生态文学的角度展开,探究消费主义时代我们对自然生态的保护问题。这一视角也的确符合阿来的创作初衷,但是,阿来并没有因此以理念化的主题压制人的存在。他指出“三本书虽然写的是三种不同的事物,是引发狂热消费的不同事物,而且它们也关涉不同人物的不同命运”⑩。“山珍三部”正是通过书写桑吉、斯炯、王泽周这些人物的命运,让我们去感受在现代性的再一次冲击中藏地与时代之间关系。
在《蘑菇圈》中,阿来以60年的时间跨度书写了斯炯的一生。从1955年工作组进村,到“反右”“四清”“文革”,一次次大的政治运动建构了斯炯前半生的生命空间。在此,阿来无意于关注这些历史大事件,这些事件仅仅是人物的活动背景,人物在时代变化中的生存样貌才是他目光的焦点。我认为,斯炯这个人物具有一定寓言性,她是嘉绒藏地的一种精神象征。她的生命之根深深扎在蘑菇圈,蘑菇圈是她抵御外界侵扰的精神圣地。所以,再浩大的政治运动,再艰难的生存环境,再丑恶的人性,都无法“黑化”善良的斯炯。“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是她豁达面对一切的人生态度。她以宽容的心态从容淡定地原谅了一切丑恶,因为蘑菇圈是给予她精神能量的生命之根。可是,随着消费主义时代的到来,蘑菇作为城里人饭桌上的“山珍”,几乎被采挖殆尽,不断有人来打听她的蘑菇圈,此时的斯炯不再像往昔那样气定神闲了。她“不知道自己脾气为何这般不好”⑪,“她的眼睛里失去了往日的亮光”⑫,“心头溅起一点愤怒的火星”⑬。她始终期望能够守护蘑菇圈不被发现,这样“等你们把所有蘑菇都糟蹋完了,我的蘑菇圈就是给这座山留下的种”⑭。可是,人心的叵测和高科技的威力岂是斯炯这样的“原生态”思维能够预料的,伴随着欺骗和GPS定位,蘑菇圈最终还是被发现,斯炯的精神支柱坍塌了,她离开村子时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的蘑菇圈没有了”⑮。而她的离开也意味着藏地孕育的那种原始生命力在消费主义市场逻辑面前的崩塌。
《河上柏影》中的故事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王泽周是村子里出来的第一个大学生。为此父亲给他做了一个纯柏木的书箱,连村子里的活佛都说:“大学里的那些书,配得上装在这么馨香的箱子里。”⑯可是这只土里土气的笨重箱子却让王泽周非常难堪,他生怕受到城里同学的嘲笑。谁想,时过境迁,几年后,稀有的柏木化身为城里人财富和地位的象征,在现实中印证了王泽周在书本上读到的城市消费乡村的文化现象。此时已经读到硕士研究生的王泽周,随着知识的增长,对自己的出身和民族已经不再自卑,反而对家乡的历史和文化充满了探究的热情。尽管他在城市是个边缘人,但故乡给予他精神的力量,让他始终坚守自己的道德准则和价值立场。他结婚坚持要找一个藏族老婆,“这样我的儿子就是比较纯粹的藏族人了”⑰。我认为,阿来通过王泽周这个人物,想要言说的是,从藏地走出去的一代知识分子在接受了现代科学文化后,反而能够更透彻地理解藏文化灵魂的深度,表达出对藏民族身份的致敬和回归。他们想要努力搭建现代科学文化与家乡传统文化之间的通道,这种努力或许是徒劳的,毕竟,这两种文化生发、存在于完全不同的语境之中,但是,他们的回归本身就意味深长,其中蕴藏着许多值得我们深思的东西。
《三只虫草》中的桑吉出生在消费主义时代,尽管他还是个小学生,但已经知道“一株虫草可以换到三十块钱”⑱。不过,他也知道“这是一个美丽的奇妙的小生命”⑲。桑吉纠结的是,“是该把这株虫草看成一个美丽的生命,还是看成三十元人民币,这对大多数人来说也许根本不是一个问题,但对这片草原上的人们来说,常常是一个问题”⑳。作为一种意象,虫草兼具了物质与精神双重属性。一方面,它是人与自然、故乡之间的精神之根;另一方面,它又是连接故乡与外部世界的物质通道。桑吉的三只虫草,用自己的物质价值实现了桑吉对亲情、友情的美好期待。在文本的最后,它们在被算计和欺骗中开启了通往外部世界的“旅行”,这在一定意义上也暗示了桑吉未来的命运。
“山珍三部”中的斯炯、王泽周、桑吉分别代表了藏地三代人在消费主义大潮冲击下的不同生命轨迹。斯炯是生命之根摧毁下绝望的出走;王泽周是出走之后的回归;桑吉呢,他在《百科全书》中看到一个广阔的世界,再回望他生活的小村庄,“心里禁不住生出一种凄凉之感”㉑。于是,最终走出去是桑吉必然的选择。他们三人用自己的人生绘制出了一道圆形的循环轨迹:出走—回归—出走。这是阿来对藏地再一次遭遇世界“扑面而来”的思考,这种思考不做形而上的论道,而是在一个个普通人的命运轨迹中展开。我认为,这就是阿来文学创作的辩证法。他总是通过最普通甚至边缘的小人物的命运,审视藏地在一次又一次面对现代化进程时的遭际。
实际上,早在写作《尘埃落定》时,阿来的辩证法便已然清晰可辨。《尘埃落定》虽然写的是一个土司家族,但叙述者却是一个傻子。阿来通过这个边缘人的视角来揭示其家族的没落以及土司制度及其文化的衰亡。正是因为被排除在家族权力机制的核心之外,傻子才能够更为冷静地观察思考,从而在时代的沧桑巨变中做出自己的选择。傻子的选择是顺势而为,由此体现了“进”与“退”、“取”与“舍”之间的藏地民间智慧和文化精神。除傻子外,斯炯、王泽周、桑吉,还有机村中的格拉、拉加泽里、多吉、索波,以及《云中记》中的祭师阿巴,他们的人生轨迹都与藏地现代性的进程紧紧联系在一起,他们不同的人生选择和人生道路汇聚起来,便钩沉出嘉绒这片土地面对时代巨变的集体记忆,刻印着一个民族或者整个人类的沉浮与兴衰的印记。这些小人物晃动的身影,让我们看到阿来对族群性和地域性的超越,以及对普遍性和共通性的追求。
三
阿来文学创作中的“大声音”还表现为对自然的关注。2018年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的阿来国际研讨会就命名为“边地书、博物志与史诗”。“博物志”的确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阿来“大声音”的一个频段。阿来“博物志”的集中书写莫过于散文集《草木的理想国·成都物候记》。2010年,阿来因为旧病复发,手术后无法远行,只能在成都市区四处游走。那时恰逢腊梅绽放的季节,明丽的花朵吸引了阿来,阿来便背起相机四处拍摄。随后,成都市内的玉兰、海棠、梅、桃、杏、李次第开放,阿来便一发不可收拾,决定“要把自己已经居住了十多年的这座城中的主要观赏植物,都拍过一遍,写上一遍”㉒,于是,便有了《草木的理想国》一书。从表面上看,《草木的理想国》成书似乎源自阿来偶然的生活经历,但是,从另一面看,这部书的创作也是阿来将内心一直蕴藏的对大自然的热爱与敬畏尽情释放的结果。腊梅、梅、贴梗海棠、早樱、玉兰、李、梨、苹果属海棠、紫荆、桃、迎春、桐、丁香……这些按照自然节气依次开放的花朵,在阿来笔下获得了别样的生机,他以工笔画的巧密和精细勾勒出每一株花朵的细部神采:(海棠花)“绸子般肥厚且色彩明丽同时沉着的质感”㉓;(樱花)“中间二三十支细长的雄蕊顶着金黄色花药,几乎要长过花瓣,簇拥着玉绿色矮壮的雌蕊”㉔;(梨)“花将开未开之时,花蕾松动开了,就要绽放的花蕾边上晕着一线浅浅的红”㉕。能够静心驻足,对花朵观察得如此细致入微,一定是一个热爱自然、热爱生命的人。《草木的理想国》让那些在我们日常的步履匆匆中被忽略的美一下子绽放出来,赋予庸常人生绚丽的诗意!或许,这些“小文”的格局并不大,但正是一花一世界,让我们在钢筋水泥土打造的现代都市中,发现了一个敞亮的自然,它就在我们的生活中,需要我们去打量,去了解,去感受。它用原生态的美感,唤醒我们灵魂的记忆。阿来曾说:“我们文学当中更加缺失一个东西,就是我们跟自然的关系。”㉖在此,阿来并不是说,中国文学中缺少书写自然的东西,而是说缺少一种书写自然的视角。他指出了中国文学一个突出的特点:自然在文学中只是作为一种参照的背景存在。的确,早在先秦时期,“比德说”就是儒家美学最重要的特点之一,即自然之所以美,是因为其中蕴藏某种人格美。这种“比德说”始终贯穿着中国文学的审美历程,即便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山水诗,也并非是发现自然,而是在自然中发现了人自己。正因为如此,阿来这些貌似轻盈的文字负载着厚重的力量。在一定意义上,阿来为中国当代文学创作打开了一个新的审美视域。
基于对自然的关注与热爱,阿来的小说对人与自然的关系有着深刻的反思和批判。这一点在他早年的作品中就已初露端倪,《蘑菇》《槐花》《银环蛇》《狩猎》《鱼》《遥远的温泉》《已经消失的森林》等作品以及“机村”系列,都涉及现代化进程中人与自然之间的紧张关系。“山珍三部”更是消费主义时代人类贪婪的物质占有欲对自然生态毁灭性打击的集中展示,呈现出的是与“人类中心主义”对抗的生态观。其实,尽管无数人文学者反复警告人类要警惕自然的报复,但是,人类贪欲似乎随着科技的进步、现代化的进程而加速度膨胀,符号经济的背后,大自然报复的声音必然会导致“寂静的春天”。所以,阿来在“山珍三部”之后,便在长篇小说《云中记》中预言了大自然的报复。2018年出版的《云中记》以汶川地震为背景,此时,距离那场人类的浩劫已经过去整整十年了。在汶川地震发生不久,很多作家都记录了那场惨痛的灾难。但是,阿来始终没有动笔。他拒绝“即时性”的文字,他要在时间的沉淀中让记忆的伤口愈合,从而更加冷静地反思灾难,重新审视人的自然观和生死观。文本开篇就在祭师阿巴的回忆中再现了那场灾难:大地轰鸣,地裂天崩,大地的裂口如同一道闪电,万物崩塌。阿来的文字像湍急的瀑布,一泻而下,失去了往昔一贯的从容淡定,让我们感受到大自然末日审判令人战栗的残酷与威力。随后,阿来并没有延续一般灾难小说的写作范式,没有用大量的文字去书写抗震救灾的感人场面,没有重笔描摹灾后人们的生存样态,而是出乎意料地以“倒计时”去逼近又一次灾难的临近。文本中的阿巴是一个“半吊子”祭师,他并不具备与神沟通的“技艺”,甚至无法确定是否真有鬼魂。但是,阿巴明白在那个特殊时期,安抚鬼魂也就是安抚人心。即使所有人都已经迁离了村庄,阿巴依然固执地坚守在云中村,为死去的乡亲们安魂。此时,出人意料的是,杳无人烟的云中村竟勃发出自然的生机,一切都摆脱了人为的规约,恢复了自然的本性。在这样的环境里,阿巴渐渐形成了“万物有灵且平等”的朴素自然观。人、亡灵、自然界的一草一木都是平等的,阿巴在对自然的观照中获得了人的尊严。我认为,这是一种博大的“宇宙意识”,人将自己的内心与宇宙万物融为一体,将自己置身于巨大的时空体中,由此将整个生命意识无限拓展。正如张若虚《春江花月夜》中的“江畔何年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这是人与自然的对话,人向月亮叩问自然的起源、人类的诞生这些宏阔的命题,探索宇宙的生命本质。李白更是阔大地写出“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真正达到了“天人合一”以及庄子说的“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的境界。可以说,宇宙意识是“盛唐之音”的一个重要审美特征。但是,盛唐之后,这种宇宙意识在中国文学史上始终没有再发出响亮的声音。从这一角度来看,阿来自然书写中蕴含的宇宙意识无疑是极为可贵的。他在《云中记》的“题记”中写道:“大地震动/只是构造地理/并非与人为敌/大地震动/人民蒙难/因为除了依止于大地/人无处可去。”㉗这种宇宙意识显然没有将自然置于人类的对立面,而是以一种悲壮的情怀让人与自然融为一体,由此在自然面前彰显人的尊严。正如张学昕所指出的:“我感到,阿来在小说结尾处,写到阿巴与山体、村庄化作一处做最后的殉道时……差不多是完美地体现了文学叙述浩瀚的品质,它让我们体验到美好灵魂和生命及内心宽广的无边无际。”㉘
四
吉狄马加在谈到阿来的写作时曾说:阿来“已经以一种他独有的方式构建了一个名字叫‘阿来的世界’”㉙。在我看来,“阿来的世界”始终是属于藏地的,他书写藏地的历史、文化,描摹藏地在遭遇现代性时惶恐的表情,也写出了藏地人民的日常生活以及他们的生存境遇。所有这些书写都带着阿来独特的气质,也就是说,“大声音”并非空洞而抽象,而是阿来特有的生命气息和艺术特质的回响。
阿来的文学创作从总体上看是现实主义书写,但阿来的现实主义又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现实主义,有学者将其称为“诗意的现实主义”㉚。我认为,这确实是阿来文学创作独特的艺术风格,也是“大声音”独有的腔调。虽然书写的是现实问题,可是他的阐释却充满诗意。比如《尘埃落定》中一段关于傻子二少爷与塔娜讨论生育问题的描写,塔娜嫌弃傻子,所以吃避孕药,明确表示不愿为傻子生孩子。这在现实生活中是非常令人痛苦而有伤尊严的事情,但文本中这样写道:
风从背后推动着,我们骑在马上跑了好长一段。最后,我们站在了小山岗上。面前,平旷的高原微微起伏,雄浑地展开。鹰停在很高的天上,平伸着翅膀一动不动。这时,具体的事情都变得抽象了,本来会引起刻骨铭心痛楚的事,就像一颗灼热的子弹从皮肤上一掠而过,虽然有着致命的危险,但却只烧焦了一些毫毛。我的妻子说:“看啊,我们都讨论了些什么问题啊!”㉛
现实的痛苦依然存在,但面对整个大自然的浩瀚,个体的痛苦被抽象化了。抽象化了的痛苦像是子弹掠过皮肤烧焦了毫毛,这是多么诗意的阐释!生命由此在宏阔的背景中变得轻盈起来,一如《春江花月夜》在澄澈晴朗的明月中将撕心裂肺的“伤别离”转化为淡淡的哀愁。正是有了如许的哀愁,才有了如许的美和生命。阿来也正是在现实的诗意化中缔造了独特的“阿来的世界”,呈现出“诗意的现实主义”。
阿来小说的这一叙事特色与其早年的诗歌创作有很大关系。在谈到自己的诗歌创作时,阿来曾动情地说:“这些诗不仅是我文学生涯的开始,也显露出我的文学生涯开始的时候,是一种怎样的姿态。……这些诗永远都是我深感骄傲的开始,而且,我向自己保证,这个开始将永远继续,直到我生命的尾声。”㉜我认为,阿来在骨子里是一个诗人,诗意的情怀始终绵延在他的叙事文本中。他早年的叙事就明显表现出这一点,大量的自然意象,如雪山、森林、草木、河流等参与叙事,阿来在诗意的情境中睹物寄情,不大注重故事性情节的营造,是典型的诗化叙事。周克芹评价阿来早期小说创作时曾说:“他好像不是在写小说,而是在写诗。他在试图对他的民族历史作一种诗意的把握。”㉝可见,在小说创作伊始,阿来就将“诗意的现实主义”作为他独特的叙事策略。随后的《尘埃落定》《空山》《云中记》以及“机村系列”“山珍三部”始终充盈着寓意深远而充满诗意的境界。
阿来小说中的诗意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的语言。第五届茅盾文学奖评委会给予《尘埃落定》的评语写道:《尘埃落定》的语言“轻巧而富有魅力”,“充满灵动的诗意”。㉞吉狄马加也曾指出:“《尘埃落定》的成功,与其说是叙事的成功,不如说是语言的成功,说到底就是诗性和异质性表达的成功。”㉟作为用汉语写作的少数民族作家,阿来的叙事语言是藏民族思维与汉语表达融合的产物,带有明显的异质性成分,正是这种异质性搭建了别样的诗意,由此形成语言的陌生化效果。可以说,阿来的语言是有声音的,有触感的,有嗅觉的,他往往在感官的盛宴中让我们体悟现实世界的丰盈和内在律动:
日子就像一条绳子套住的腿一样,再也不肯前进了。㊱
银匠也从屋子里出来,干起活来。锤子声清脆响亮,叮咣!叮咣!叮叮咣咣!㊲
她把几颗蚕豆喂进嘴里,这回,不管她把小嘴闭得有多紧,一动牙齿,就又发出老鼠吃东西的声音来了,嚓嚓,嚓嚓嚓嚓。㊳
这些语句与我们的感官产生了强烈的碰撞,让我们感受到一个丰盈的生命世界。不仅如此,阿来还大量使用感性事物进行隐喻,让语言在“可视化”中更接近事物的本质。比如,《尘埃落定》中红色的罂粟花是暴力、淫欲、鲜血的隐喻;白色作为雪域高原的生命底色,在藏地象征着吉祥和好运,但在《尘埃落定》中,阿来用罂粟白色的液体作为罪恶的隐喻,由此形成了一种反讽的效果。“而我,又看见另一种白色了。浓稠的白色,一点一滴,从一枚枚罂粟果子中渗出,汇聚,震颤,坠落”㊴,“白色的浆汁被炼制成了黑色的药膏”㊵。在此,带有生命色彩的白色的原意被转化了,暗示着白色已经无法给麦其土司家族带来生机,反而潜藏着毁灭的灾害。再如紫色,这是血液凝固之后的色彩,隐喻着杀戮与仇恨。“河流、山野、官寨、树木、枯草都蒙上了一层紫色的轻纱,带上了一点正在淡化,正在变得陈旧的血的颜色”㊶,“杀手一刀下去,黑暗中软软的扑哧一声,紫色衣服上的仇恨就没有了”㊷。这些色彩呈现出的感性的隐喻效果,明显淡化了现实中的丑恶、血腥和阴鸷,杂糅进了朦胧迷离的诗意。
实际上,阿来小说的诗意还表现为带有浓郁藏地气息的诗性精神。这一点在阿来笔下的人物阿古顿巴身上得到了完美的诠释。阿古顿巴是藏民族传说中的智者,他常常以自己的智慧帮助贫苦农奴获得权益,是集智慧、善良、除恶扶贫于一身的理想人物。这个人物的智慧在阿来笔下不仅仅用于扶弱济贫,更多的是用于自我生命的醒悟。在民间故事中,阿古顿巴虽然身份多变,诸如奴隶、小商人、用人等,但总体来看都属于社会底层。阿来则彻底改写了阿古顿巴的出身,让他成为一个富裕领主的儿子,但他放弃了领主的继承权,走上了寻找智慧以及真理的道路。他以自己的智慧惩治了权贵,把富商的财产全部分给了贫苦百姓,最终以永远在路上的方式,找到了生命的终极意义。阿来在谈到阿古顿巴时曾说:“他有点像佛教的创始人,也是自己所出身的贵族阶级的叛徒。他背弃了握有巨大世俗权力与话语权力的贵族阶级……用质朴的方式思想,用民间的智慧反抗。”㊸所以,阿古顿巴这个人物既体现了一种思维方式、一种人生智慧,更体现了一种诗性的精神境界。这一点,在傻子少爷、阿巴、王泽周、斯炯等一系列人物身上都能看到。正是因为有着诗性精神,所以这些人物既从现实中走出,又与现实保持一定的距离。他们大巧若拙,以一种超越世俗的智慧俯瞰人生,在博大的悲悯中挖掘生命原生态的质地,建构起具有原点意义的人物形象。无疑,阿来的“诗意的现实主义”建立了一种别样的美学风格,丰富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方式。
回顾阿来四十年的文学创作,他的目光始终没有离开过故乡的土地,他几乎所有的作品都是在书写嘉绒藏地。阿来在他的文学世界里用自然、民族和文化为故乡建立三维坐标,他在宏阔的“宇宙意识”下对自然的审视,以及对身份政治与文化认同的思考、对康巴百年历史的回顾,都让他的作品呈现出对普遍性和共通性的追求,挣脱了族群性和地方性的羁绊。所有这些,都让我们感受到了作家想要书写一个时代的使命感。同时,“诗意的现实主义”的叙事策略更让我们意识到,阿来始终在努力营造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阿来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我们听到了发自人性深处的大声音。
注释:
①张清华:《阿来的多重文本》,陈思广主编,《阿来研究》(第10辑),四川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页。
②阿来:《穿行于异质文化之间—在1999年国际比较文学学会上的演讲》,《就这样日益丰盈》,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94页。
③陈思广:《阿来诗歌的意义—读<阿来的诗>》,陈思广主编,《阿来研究》(第10辑),四川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22页。
④梁海:《阿来文学年谱》,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7、38页。
⑤阿来:《有关<空山>的三个问题》,《扬子江评论》2009年第2期。
⑥阿来:《空山1》,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7页。
⑦阿来:《空山3》,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0页。
⑧阿来:《空山3》,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0页。
⑨阿来:《看见》,湖南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175页。
⑩阿来:《我为什么要写“山珍三部”》,陈思广主编,《阿来研究》(第6辑),四川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79页。
⑪阿来:《蘑菇圈》,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63页。
⑫阿来:《蘑菇圈》,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83页。
⑬阿来:《蘑菇圈》,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82页。
⑭阿来:《蘑菇圈》,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76页。
⑮阿来:《蘑菇圈》,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84页。
⑯阿来:《河上柏影》,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5页。
⑰阿来:《河上柏影》,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59页。
⑱阿来:《三只虫草》,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3页。
⑲阿来:《三只虫草》,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3页。
⑳阿来:《三只虫草》,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4页。
㉑阿来:《三只虫草》,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71页。
㉒梁海:《阿来文学年谱》,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51页。
㉓阿来:《草木的理想国·成都物候记》,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4页。
㉔阿来:《草木的理想国·成都物候记》,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2页。
㉕阿来:《草木的理想国·成都物候记》,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9页。
㉖阿来:《我为什么要写“山珍三部”》,陈思广主编,《阿来研究》(第6辑),四川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81页。
㉗阿来:《云中记》,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题记。
㉘张学昕、梁海:《阿来论》,四川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41页。
㉙吉狄马加:《在自我、他性以及跨文化之间》,李敬泽主编,《边地书、博物志与史诗—阿来作品国际研讨会文集》,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20年版,第10页。
㉚李莎:《我和阿来:现在相遇也不晚》,陈思广主编,《阿来研究》(第10辑),四川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68页。
㉛阿来:《尘埃落定》,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10页。
㉜阿来:《阿来的诗》,四川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9页。
㉝周克芹:《在历史与现实的交汇点上—序阿来小说集<远方的地平线>》,《民族文学》1989年第1期。
㉞徐希平:《阿来汉语写作的文化意义及其启示》,陈思广主编,《阿来研究》(一),四川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65页。
㉟吉狄马加:《在自我、他性以及跨文化之间》,李敬泽主编,《边地书、博物志与史诗—阿来作品国际研讨会文集》,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20年版,第11页。
㊱阿来:《空山1》,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5页。
㊲阿来:《尘埃落定》,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02页。
㊳阿来:《尘埃落定》,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06页。
㊴阿来:《尘埃落定》,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9页。
㊵阿来:《尘埃落定》,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71页。
㊶阿来:《尘埃落定》,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79页。
㊷阿来:《尘埃落定》,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93页。
㊸阿来:《文学表达的民间资源》,《民族文学研究》2001年第3期。
原刊于《阿来研究》第16辑

梁海,女,博士,大连理工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负责人,主要从事文学评论和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等多项国家级科研项目。出版《小说的建筑》《天道酬技》《阿来文学年谱》等多部学术专著,在《光明日报》《人民日报》《当代作家评论》《文艺争鸣》《南方文坛》《文艺理论与批评》《小说评论》《长篇小说选刊》《中国作家》等发表文学评论百余篇。获第七届辽宁文学奖·文学评论奖,第十四届、十五届大连市社会科学进步奖等。

阿来,当代著名作家,藏族,1959九年生于四川省马尔康县。中国作协副主席,四川省作协主席。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尘埃落定》《空山》《机村史诗》《格萨尔王》《云中记》,长篇非虚构《瞻对》,诗集《梭磨河》,小说集《旧年的血迹》《月光下的银匠》,散文集《大地的阶梯》《草木的理想国》,以及中短篇小说多部。2000年,长篇小说《尘埃落定》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2009年,获得第七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杰出作家奖”;2018年,《蘑菇圈》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2019年,长篇小说《云中记》获第十五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