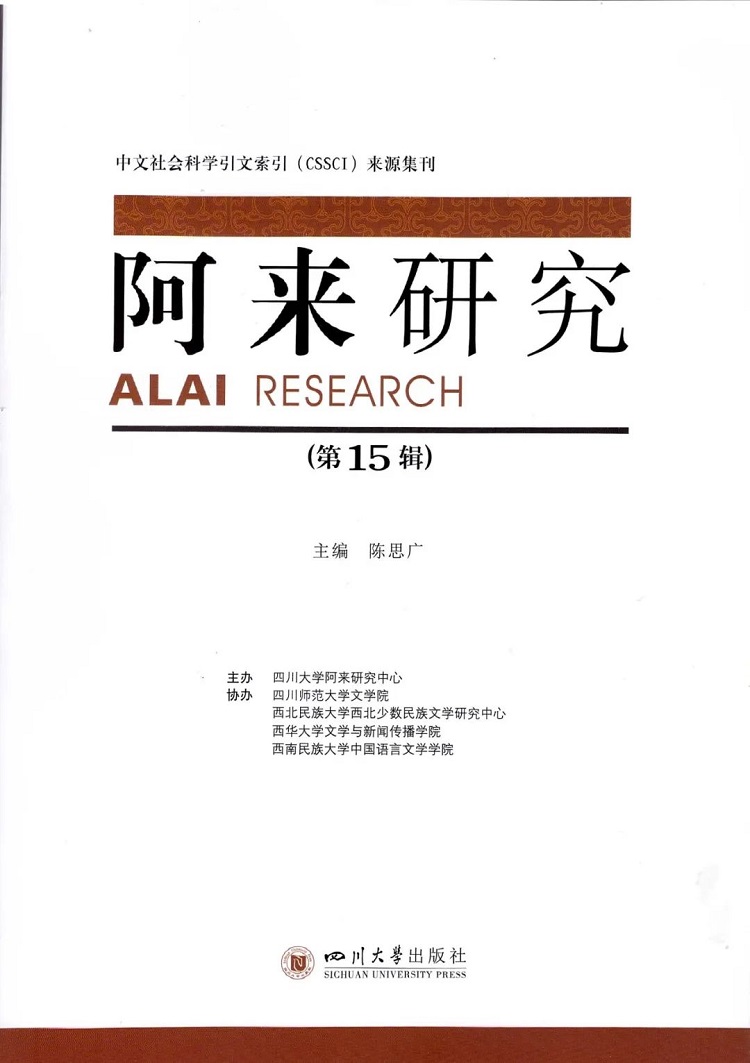
伊扎坐落在青藏高原东部,是个半农半牧的美丽地方,作家梅卓的祖辈就生活在这片山地中,过着简单而平凡的生活。虽然梅卓的出生地距离伊扎有千里之遥,但是其对祖辈居住之地的向往却从没有因为遥远而中止过。①发生在20世纪前半期的伊扎部落与周边部落频仍纷争、最终为马步芳军阀部队剿灭的惨剧自然会进入她的视野中,并在她笔下一再复现。其1997年获第五届骏马奖的长篇小说《太阳石》(初名《太阳部落》)和发表在2005年11期《中国作家》上的中篇小说《珊瑚在岁月里奔跑》就翻开了这沉重的一页历史,这既是浓重的故乡情结使然,也是其正视历史的必然。对照阅读这两部对伊扎部落同一历史事件进行不同书写的小说,我们不难发现作家在重返历史现场时所蕴蓄着的别样复杂用心。
这两部小说中,不论是太阳石(《太阳石》),还是珊瑚(《珊瑚在岁月里奔跑》),都是伊扎部落头人重要的权力象征物,而围绕太阳石和珊瑚进行的财富、土地与权力的争夺正是这两部小说的核心内容。两部小说中所出现的人物众多,他们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可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要将其梳理清楚,颇费一番笔墨,基本意味着要重述一番小说的情节。
先来看《太阳石》。这部小说着重讲述的是伊扎部落与西临的沃赛部落之间的恩怨情仇。这两个部落因为草山等纠纷而常年不睦,正是为了解决矛盾,两个部落一直采取和亲政策。多年前,伊扎千户把自己心爱的妹妹下嫁给了沃赛部落头人,从而确保彼此之间的相安无事。沃赛部落头人夫妇去世后遗留下来的索白、丹麻两个男孩被部落的新头人——他们的叔叔沃赛送还给了伊扎千户。伊扎千户夫妇去世后,部落权力没有依规由自己的亲生儿子嘉措继承,而是旁落到了外甥索白手里。索白要向沃赛部落发动战争,沃赛夫人为消除仇恨而将自己的妹妹耶喜许配给了索白。丹麻做了活佛,常常在伊扎部落和沃赛部落之间游走,甚而一次险些遭到伊扎部落的埋伏袭击。嘉措在与桑丹卓玛结合并生下女儿香萨后离家出走,落草为寇,因杀富济贫而深得普通百姓爱戴。他带人缴获了马步芳军阀部队严总兵手下士兵的枪支,索白借机嫁祸于沃赛部落,和严总兵联手向沃赛部落发动进攻。沃赛战死,其妻自杀。桑丹卓玛与已有妻室的洛桑达吉私下里真心相爱并生下了又一个女儿阿琼。洛桑达吉和妻子豕金并没有生育子女,豕金嫌贫爱富,离过一次婚,和前夫生有夏仲益西和森巴仁庆两个儿子。索白对桑丹卓玛产生情愫,却始终不能得其芳心。索白和耶喜先后生有两个儿子,大儿子阿莽爱上了香萨并向其求婚,香萨因为对其产生误解而拒绝,阿莽因此郁郁寡欢,终跳崖而死。后悔不已的香萨先是长途跋涉寻找父亲嘉措未果,继而上山在密室里苦修,而后不知所终。索白上山打猎,在香萨苦修的密室中避雨,不期然发现了一个襁褓中的女婴,带回去认作女儿,起名为安,安四岁时常常独自进山,在那座密室中待上三天三夜。索白为给安驱邪而去转神山,途中丢掉一条腿,从此安不再独自出门。后来安被认定是一位西去的女活佛的转世灵童。索白的二儿子才扎不务正业,酗酒成性,在一次醉酒后强奸了雪玛。雪玛是索白家的厨娘万玛措的女儿,万玛措曾是索白的情人,她因为索白对桑丹卓玛情有独钟而愤然离家,与一小贩私奔。雪玛本来和豕金的儿子夏仲益西相爱,但因为遭才扎之害,又被豕金嫌弃防范而发疯,夏仲益西也因此出家做了喇嘛。沃赛的儿子嘎嘎重整旧部,当上了沃赛部落的头人,一直以伊扎部落为仇敌。一次,他抓获了洛桑达吉,但并没有杀他,而是让他待在自己庄园里干活。洛桑达吉好容易逃出来,却不慎掉进了深沟里,临死前得知自己有亲生女儿阿琼后感到特别欣慰。阿琼在一年一度的赛马会上与嘎嘎相爱,嘎嘎求婚,遭到桑丹卓玛的拒绝,之后采取了抢亲方式。桑丹卓玛向索白求助,应允只要救回阿琼,就答应索白任何条件。为爱情迷住双眼的索白再度与严总兵联手向沃赛部落发动袭击,却不料严总兵利用两个部落之间的仇杀坐收渔翁之利,在毁灭沃赛部落的同时,也灾难性地打击了伊扎部落。小说结尾是索白将象征伊扎部落权力的太阳石戒指托付给在藏地教书的汉人章子文先生,要他转给阿琼,阿琼和嘎嘎夫妇准备带着这枚太阳石戒指一同去寻找父亲嘉措。
再来看《珊瑚在岁月里奔跑》。小说中,伊扎部落的千户抱养了儿子拉甲,拉甲五岁时就被认定为某位活佛的转世灵童。拉甲离开后的第二年,千户又生育了一对龙凤胎——儿子南甲、女儿珠玛。千户死后,部落权力和祖传的宝石珊瑚被一同移交给了南甲,南甲为迎娶果保百户的女儿秀吉玛而将珊瑚作为聘礼。为了睦邻友好,南甲还将心爱的妹妹珠玛许配给了巴勒蒙旗的巴雅特王爷,尽管珠玛实际上所爱慕的对象是临近的德仓部落头人的儿子一西。德仓部落在和政府的较量中逐渐衰败,在此过程中,伊扎部落采取了明哲保身的做法。马步芳的义子马海买对伊扎部落横征暴敛,南甲不堪压迫而奋起反抗,兵败被俘,管家罗拉为救南甲而被马海买开枪打死,其妻妩姆闻声哭着奔过来,也遭枪杀;妩姆的妹妹色姆被马海买关在后院遭到百般蹂嘛,伊扎部落的财富悉数落入马海买手中。马海买临撤兵时放话要伊扎部落出重金赎回南甲。秀吉玛带着珊瑚和拉甲活佛筹措来的元宝去向巴雅特王爷求助,贪心的巴雅特王爷昧心收下了财物,虚情假意地答应下来,却作壁上观,而马海买因为没有收到赎金而将南甲活活折磨至死。在收拾完伊扎的残局后,早就对巴勒蒙旗的财富和那颗珊瑚觊觎已久的马海买又带兵直奔巴勒蒙旗而来,巴雅特王爷至死也没有交出珊瑚,侥幸逃过一劫的珠玛带着珊瑚和腹中的胎儿回到伊扎,却饱受伊扎人的仇视。珠玛将珊瑚献给了拉甲活佛,自己带着儿子远走他乡。儿子长大成人后主动放弃县城生活而来到伊扎部落,入赘部落人家,辛苦工作、研读经文以赎罪。新中国成立后,拉甲活佛弃教还俗,在省城当上政协委员,一直未嫁的色姆带着姐姐的遗孤兰措共同生活,色姆还一度作为拉甲活佛的信徒和管家和拉甲同在一个屋檐下生活了五年,但二人从来就不是夫妻。1966年,拉甲所在单位要求拉甲和色姆领取结婚证,成为合法夫妻。色姆认为只有兰措的纯洁才配得上拉甲的高贵,遂做主让二人领取结婚证。此时拉甲43岁,兰措17岁。“文化大革命”中,拉甲受到迫害,和兰措在牢房中有了人生唯一一次夫妻生活,其后死于狱中。兰措生下女儿茜若,茜若长大后在民族学院读书,和同学巴马相爱,当茜若得知巴马居然就是巴雅特王爷和珠玛的孙子时,她毅然斩断情丝。数年后,茜若在广州遇到马海买的孙子——外商马依不拉,他答应资助茜若去美国读书,出资买下了茜若手中的那颗珊瑚。这篇小说虽然只有3.5万字,篇幅不过《太阳石》的八分之一,但因为不仅仅讲述伊扎惨剧,还关联到伊扎后人的人生命运,时间跨度更大——上自20世纪20年代末,下到改革开放。
很显然,人物之间这种复杂的血缘、亲缘和情感关系构成了这两部小说情节发展的重要力量。梅卓习惯于通过结构如此复杂的人物关系网络来营造她独特的小说天地,小说中人物之间的关系剪不断、理还乱,多年前的情感之“因”结出了多年后的行为之“果”,人物可叹可惋的命运以及一段段残缺不全的爱情不时冲击着读者的情感神经。而在编织这一张张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网时,梅卓能够做到从容不迫,这是值得称许的。
需要看到,《太阳石》似乎有意识地对故事的发生时间进行了模糊处理,并没有明确时间指向。当然,小说必然要碰触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即伊扎惨剧,这就不可能完全不露出时间痕迹来。小说一共十章,在前四章中,读者如果细心,可以从间或出现的“省府”“县长”“保安司令”“秘书”“军政要员”“学校”等字样意识到小说所讲述的事件应该是发生在民国年间。到了第五章,小说提到朵义才是“现任省府主席马步芳在香房街的公馆的警备大队长”②,读者若是对青海历史掌故有所了解,则可以据此大体上判断故事发生时间应该是在20世纪30年代前后。值得提及的是,较早先的《太阳部落》,《太阳石》在开篇增加了一个六七百字的“楔子”:
唐松赞干布将与其有隙的一位兄弟贬谪到安多地区,其弟遂在此地安家落户,成为一方领袖。后来松赞干布心系兄弟,想要召回弟弟,但其弟留意甚坚,松赞干布为表悔意封其为大如巴王。大如巴王育有三个儿子,三个儿子共有子女29人,29人又生子286人,这286人各据一方,形成三百余部落,伊扎部落就是这三百余部落之一。③
在有了这样一个前情交代之后,小说才开始讲述伊扎部落的故事。这个后加进来的“楔子”在对时间的交代上仍然做了冷处理。在一部讲述历史的长篇小说中,梅卓为何如此不情愿点明具体时间?在我看来,作家可能是基于这样的考虑:藏地一直以来都是比较封闭的,像伊扎、沃赛这些部落,千百年来放牧牛羊、种植庄稼、繁衍生息乃至部落争战,都比较随性自然,完全可以做到自给自足,也似乎是自生自灭,时间的流转、统治阶层的变化似乎对这些自成天地的部落构不成巨大的冲击。即使没有军阀政权的凌虐,小说所浓墨重彩所书写的诸多不完满的令人伤感的男女爱情故事也照样会发生,或缘起于上一代人的恩怨情仇,或缘起于阴差阳错、造化弄人,或缘起于人性的贪婪与放纵。而到了现代,原本封闭的伊扎等部落又不可能是独立存在的“桃花源”,社会的变迁、异质文明的渗入还是难免会渐次从各个角落显现出来,就像小说“吞吞吐吐”地诉说的那些有着鲜明时间印记的现代词汇和历史人物那样,这些现代因素会从不同方面、不同角度对小说中人们的爱情故事、对伊扎部落的覆灭起到强大的催化作用,甚至产生决定性影响。就小说所专注叙写的伊扎部落、沃赛部落的覆灭这一事件而言,马步芳军阀是最大的利益赢家,罪责难逃。
至于《珊瑚在岁月里奔跑》,虽然只是一部中篇小说,但是因为既涉及伊扎部落的灭亡惨剧,还关联伊扎后人在改革开放时期的爱情故事,所以明确提到了1929年、1966年这样具体的年份。前者指向的是马海买军阀消灭伊扎、德仓、巴勒蒙旗等部落的惨剧,而后者指向的是直接影响人物命运走向的整体社会变革。而作为伊扎部落圣物的珊瑚的辗转易主恰好能折射出岁月变化之于主人公命运和情感选择的作用,从而比较贴切地吻合了小说题目“在岁月里奔跑”。小说所涉及的不同时代、不同政权、不同文化是具有翻天覆地的力量的,足以让原本各行其是、各得其所的人的命运突转。一句话,无论是否情愿,伊扎人、伊扎文化都必然要融入时代的洪流并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还要看到,梅卓在《太阳石》中特意添加的有关大如巴王在安多地区繁衍子孙后代的背景介绍应该是别有用意,其意在说明小说中的伊扎部落和相互仇视的沃赛部落其实是同一祖先,即令单纯从《太阳石》中的人物关系来看,伊扎与沃赛两个部落之间的姻亲关系、血缘关系就千丝万缕,无法斩断。对于这种部落之间的手足相残,梅卓是有着深深的隐痛的,而“楔子”中的松赞干布与大如巴王之间的兄弟关系恰好起到非常好的喻示作用。虽然松赞干布与大如巴王曾彼此怨恨,但后来兄弟二人又能和好如初,大如巴王随遇而安、自得其乐,松赞干布对大如巴王每年都有大量封赏。“楔子”中兄弟相亲相爱的美好关系,实则隐含着梅卓对往昔藏族历史的缅怀和对未来的美好期望。而小说结尾,伊扎和沃赛这两个相互仇杀的部落最终在军阀的屠刀下认清了真正的敌人,两个部落重新携手,尤其是嘎嘎和阿琼超越了部落仇恨的爱情的实现以及他们最终投奔父亲嘉措的人生选择,都让读者欣悦地意识到,太阳石将要真正物归原主了。而且,小说中索白这个人物起始通过贿赂政府官员而窃取了伊扎部落的权力,得到了太阳石戒指,后来屡屡对沃赛部落大动干戈,他显然是一个令人深恶痛绝的权力窃取者、民族罪人,但梅卓并没有将其脸谱化。索白对嘉措的妻子桑丹卓玛动了真情,却始终没有“霸王硬上弓”,而是每天晚上守在门外,期待爱情之门为他打开,甚至还因此冷落了旧情人;在村人们因为桑丹卓玛不明不白地生养了阿琼这个私生女而要驱赶她时,索白挺身而出保住了桑丹卓玛的小窝和尊严;索白在后来会为自己窃取部落权力而自责,在收养了安这个女孩后更是发誓不再杀生,在与沃赛部落最后一战前,主动派人将太阳石戒指送还阿琼,意味着将权力归还给部落的真正主人嘉措及其后人……显然,梅卓对索白的书写渐渐释放出了善意,或者可以这样认定,梅卓是通过索白的自我道德完善来表达自己对伊扎部落权力和平更迭的一种美好期待,事实上也是希望部落之间以及部落内部的仇恨和残杀能就此消弭。比较耐人寻味的是梅卓在这当中的爱情书写。年老身残的索白可以冲冠一怒为红颜,发动对沃赛部落的攻击,承诺照顾好桑丹卓玛,并将太阳石戒指交还阿琼,这一系列情节事实上肯定了爱情力量的强大。还要看到,在阿琼一方来说,其生身父亲洛桑达吉可以说是间接死于嘎嘎之手的。照以往情势来说,部落之间的这种仇恨应该是不共戴天的,但阿琼和嘎嘎这两个年轻人的爱情却能战胜两个部落之间的仇恨,让人看到了光明与希望。爱情,或者说爱,最终战胜和超越了仇恨。在回眸历史时,梅卓显然有着很美好的愿望,尽管这一切并不容易实现,但她还是在小说中表现了出来,让读者由索白的幡然醒悟以及阿琼和嘎嘎的最终选择看到一线希望,感到一种安慰,从而能自伊扎部落覆灭的悲哀中走出来。这样一个光明的结尾实则是梅卓理想主义精神的表现。
而在《珊瑚在岁月里奔跑》中,爱情的结局就完全不同了。茜若、巴马本来同是伊扎千户之后,确切来说是拉甲活佛、珠玛这对义兄妹的后人,彼此沾亲带故,但是就因为巴马身上有着四分之一的巴雅特王爷的血统,哪怕珠玛实际上是委曲求全,哪怕珠玛的儿子(巴马的父亲)为巴雅特王爷的罪过真心忏悔赎罪,仇恨的力量依然无比强大,一旦茜若知道真相,巴马还是被无情地逐出了爱情天堂。不过,匪夷所思的是,前辈人为争夺珊瑚而血流成河、反目成仇,茜若竟然会在数年后如此轻而易举地放弃它,而且是让觊觎珊瑚已久的仇人之孙不费吹灰之力就得到了它,这又该如何理解?如果说《太阳石》中太阳石物归原主算皆大欢喜,体现着作家的美好理想,那么《珊瑚在岁月里奔跑》所给出的残酷而具有嘲弄意味的结局可能就更加接近真实生活。换言之,《太阳石》的那个温情脉脉而且昭示着希望的开放性结局是梅卓手下留情,实际上,她清醒地意识到了太阳石(珊瑚)的命运,更认同伊扎精神圣物终将随同伊扎部落的覆灭而消亡的事实。
再看同属于伊扎题材之列的短篇小说《幸福就是珍宝海》,它书写的是祖孙三代伊扎女人的婚恋故事,折射出数代伊扎人从故乡出走的命运。“我”的阿布为逃避被马步芳军阀抓兵的命运而出走草原,一去不复返;“我”的阿依在无望的等待中度过余生;“我”的阿爸被迫离开草原,小说有意没有交代原因,但从时间上推算,很可能也与政治事件有关,他唯有在阿依去世时才匆匆赶回来一次;“我”的阿妈同样在伊扎草原上无望地等待自己的男人归来;“我”和爱人夏洛则是在浮华的城市生活的吸引下而先后主动离开伊扎草原的。军事、政治、商业等诸种现代因素造成了伊扎草原人去帐篷空的凄凉景象,伊扎草原的盛景遂只存在于“幸福的妈妈是珍宝海”的古老歌谣中了。从《太阳石》《珊瑚在岁月里奔跑》《幸福就是珍宝海》等小说给出的让人哑然、启人深思的结局来看,梅卓小说的曲终奏雅事实上源自其对伊扎部落文化风流云散的落寞景象的凝视和由此感到的哀婉。
梅卓另有一些书写藏族现实生活的中短篇小说,尽管与伊扎题材无关,但结局同样令人唏嘘,与伊扎叙事一同互文性地道明了包括伊扎文化在内的藏族部落文化的衰败情形。《唐卡》中,省博物馆古唐卡发掘收集小组成员桑杰才让历经千辛万苦收集到了公元7世纪的无比珍贵的古唐卡,同一小组的张教授等人早就打起了私下出卖文物的歪主意,不断向桑杰才让抛出成就功名、出国深造等诱饵,而且情节隐约暗示桑杰才让一旦答应,爱情之花也会结果。小说以桑杰才让离开酒桌走在路上时脑子逐渐清醒而收尾:“关于唐卡,关于钱,关于美国,关于前途,关于爱,此时此刻,都在心头乱糟糟地晃动着,跳跃着,像路边的五色霓虹灯,毫无章法和规则,却不失亮堂地拥挤到了他的眼前……”④与其说这是梅卓要给读者留下回想的空间,不如说是她不忍心给出另一个结局,不愿意点破社会现实中唯私利是图的一面。《秘密花蔓》中,画唐卡是卓玛的家传绝学,身怀绝技的父亲已经离世,丈夫虽曾是父亲的得意门生,却早就不务正业,荒废了技能,卓玛辛辛苦苦完成的巨幅唐卡更被丈夫以欺骗的方式盗走。中篇小说《佛子》中,像才让奶奶那样虔诚的佛教信徒越来越少,祖孙二人在转海途中感受到了无处不在的浓重商业文化气息对佛教的包围、侵袭,年轻人的不敬神和渎神行为屡见不鲜:才让在转海之后剃度出家,也并非出于对佛教的虔诚,而是为了借机席卷信众的善款。芸芸众生中,究竟还能有多少真正的“佛子”?
“文学创作与作家的内心世界不可分割”⑤,从上述几篇梅卓小说的情节设定来看,她清醒地意识到了类似太阳石(珊瑚)这样的伊扎部落文物遗存及其代表的精神遗存不容乐观的命运,藏族古老部落文化的式微在所难免。如果说梅卓在20世纪80年代初涉文坛时的写作还带有玩票性质因而更多在个人情感天地低回的话,那么随着眼界的开阔,梅卓对文学、生活和社会的理解的加深,有了创作的自觉并意识到了自己写作意义之所在:“文学的篇章虽由个人书写,却注定是一个时代、一个社会的事业。这是一项神圣的事业⑥也正是因为此,她近些年来在藏地不断游走、观察、体验,先后著有散文集《吉祥玉树》《藏地芬芳》《走马安多》,还有对格萨尔史诗进行重述的神魔小说《神授•魔岭记》等。作为一个深深热爱藏族文化的当代藏族代表性作家,梅卓用自己所擅长的文笔来重现往日藏族风土人情、人文景观和民间文化的荣光,让藏族文化由此绽放出永恒的光芒,承担起了一个文字工作者无可回避的文化责任。显而易见,当梅卓专注于对藏族文化记忆的延续和传承之时,她的写作路径将会变得越来越宽,而其作品也注定会给读者留下无限回味的空间。
注释:
①梅卓:《走马安多》,青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0页。
②梅卓:《太阳石》,太白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109页.
③梅卓:《太阳石》,太白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楔子,第1页.
④梅卓:《麝香之爱》,西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10页.
⑤梅卓:《游走在青藏高原(代后记)》,《走马安多》,青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17页.
⑥梅卓:《青海文学:丰收的时节已经到来》,《青海日报》2009年9月25日.
原刊于《阿来研究》第15辑

乔世华,男,1971年生,辽宁大连人。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辽宁省作家协会特聘评论家。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及中外文学关系研究。

梅卓,女,藏族。一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青海省作家协会主席,《青海湖》文学月刊主编,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青海省优秀专家。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太阳部落》《月亮营地》,诗集《梅卓散文诗选》,小说集《人在高处》《麝香之爱》,散文集《藏地芬芳》《吉祥玉树》《走马安多》《乘愿而来》等,作品入选多种选集。曾获全国百千万人才工程奖、全国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拔尖人才、全国第五届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全国第十届庄重文文学奖、中国作家百丽小说奖、青海省首届青年文学奖、第四、五、六届省政府文学作品优秀奖、青海省四个一批拔尖人才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