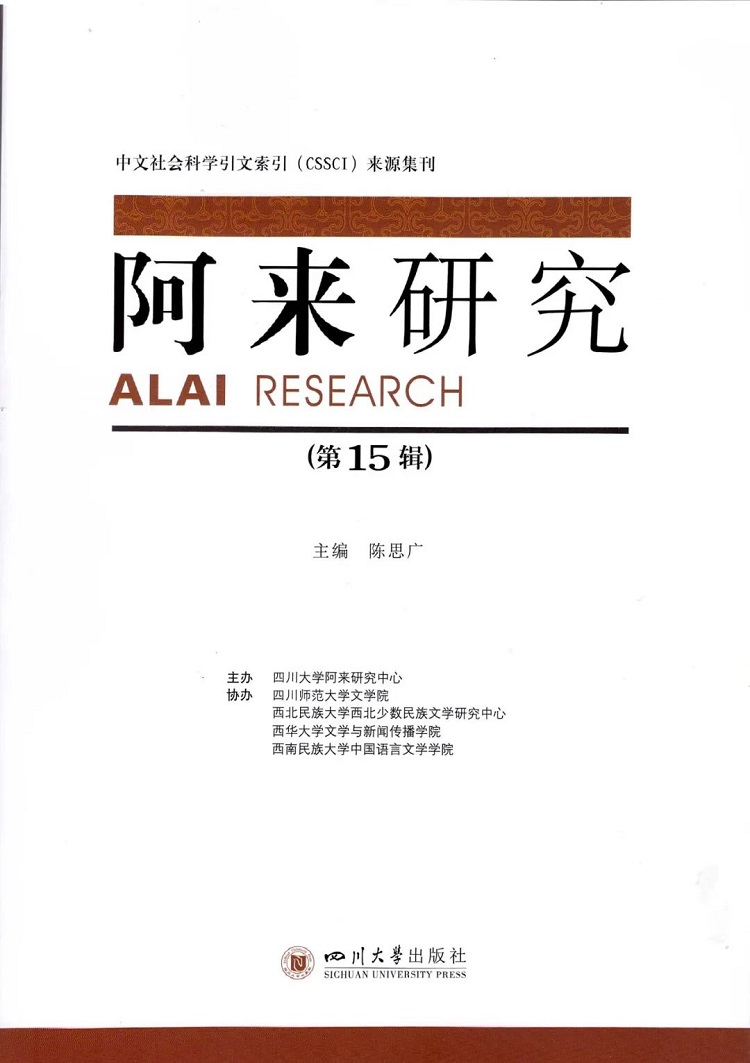
少数民族作家的书写表达不同于大多数汉族作家的创作风格,给我们带来一种不同的阅读体验。其特异的表达关联着陌生的图景,将读者引入神异之所,那些出奇的人间之思冲刷着我们日益固化的认知。聚焦少数民族作家的文学创作,藏族女作家梅卓无疑是一个独特的存在。自20世纪80年代登上藏族文坛以来,她先后创作了《太阳部落》《月亮营地》《人在高处》《麝香之爱》《藏地芬芳》《吉祥玉树》《走马安多》《乘愿而来》《珊瑚在岁月里奔跑》《出家人》《魔咒》《梅卓散文诗选》等小说及散文。无论是散文还是小说,梅卓的文本都彰显出独特的藏族色彩。
我们知道,藏族文化语境最显著的特征乃现实写作与神话、宗教故事的关联。就梅卓创作所提供给世界的图景而言,藏族文化在其文学世界中蕴含着太多的内容,故乡、历史、人性、自然、传说等多种记忆同时也是作家身份的一种参照。可以说自走上文坛起,梅卓就将藏地作为自己诗学和精神上的故乡。
一位作家要写出遥远的故事,需要与故事保持一种遥远的距离。梅卓的《神授•魔岭记》对现实世界便保持着一种远观。该篇以格萨尔史诗“四大降魔篇”中的魔岭大战原叙事为背景,将现实与神话、真实与虚幻、现代与历史、人与神等在文本中有机结合起来,通过魔幻现实主义的叙事手法,将带有超现实色彩的文本与格萨尔史诗构成了互文本,暗中形成了神话与现实的同一性,形成了独特的叙事风格和审美特质。
《神授•魔岭记》以东查仓部落13岁少年阿旺罗罗为主人公,描述了其成长为格萨尔神授艺人的神奇生命历程。小说共13章、39节,创作历时十年,向我们呈现的是对藏民族格萨尔史诗的“故事新编”。小说的意义在于重新找到了史诗在当下的呈现方式,其内部有着非常复杂的结构组成,迥异于汉族作家的表达,表现出藏文化的神奇魅力。
一
毫无疑问,作为藏族作家,梅卓对藏文化的认同有自己独特的视角,这可能与作家本人经历和性格有关,也未必不是一种自觉的文化选择。梅卓的整个创作都彰显其对藏族历史的追溯和现实精神世界的探讨,毋庸赘言,她的小说都是以藏族的文化和历史为背景的。
作为藏文化经典的格萨尔史诗是西藏当代作家文学创作的源泉和灵感,古老的说唱艺术在现当代作家笔下有了独异的创作技巧和现代性因子,因此“以艺人说唱为主体内容的史诗原叙事更多地成为作家文学的叙事背景和创作素材,源于民族集体记忆的格萨尔史诗成为故事中的故事被不断演绎而生发出更多新的故事”①。梅卓的《神授•魔岭记》讲述的是格萨尔史诗中一段关于魔岭大战的故事,作为民族史诗,“格萨尔”生成和流传有着特定的文化土壤。在《神授•魔岭记》中,作者从自然、历史、民俗、禁忌、心理习惯、生活方式等多维层面体悟和描述格萨尔史诗说唱、格萨尔英雄崇拜以及山神崇拜与东查仓部落人们日常生活相濡相融的关系,小说很明显地体现了梅卓自觉的民族创作意图。
作者通过小说中的各种人物,如爷爷、闸宝大师、兰顿大师、精灵扎拉、康珠玛大师、卓玛本宗、阿尼卓嘎等,不断地渲染、传达、讲解着东查仓部落的史诗说唱传统、神灵信仰、民俗事项、禁忌仪式、历史人物、文化掌故等有关民族(或部族)根性的故事。正如题记所言:“若无人类神灵佑助谁?若无神助怎能成人事?若要随心两者需相依。”②在“东查仓部落,美丽的草原牧场,作为神灵的格萨尔与牧人的日常生活有着千丝万缕、休戚与共的关系——无论是生活还是思维”③。西藏是人神共居的世界,也是神话与现实共存的土壤,每一片土地都弥漫着自然的气息和神灵的气息,人供奉神灵,神灵护佑人,人与神灵互惠共存,神山和圣湖都是有着神性的存在,作为藏人心中的圣地得到膜拜,人与自然相得益彰,记录藏民族的共同记忆。
同是藏族作家的阿来在谈到创作时认为:“我们所面临的真正问题是,在面对历史、面对当下社会、面对自己的生活体验时,作为一名作家要通过这些内容表达什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④梅卓在《神授•魔岭记》的写作中似乎也面临一种类似的困惑,即藏族作家的书写应秉持一个什么样的写作立场直面现实。如何面对藏族文化,不同的藏族作家选择不同的方式,对藏地的文学书写就面临着一个如何表达的问题:“我们在一个没有用现代文学手段书写过的地方开始书写和表达的时候,就面临一个问题:我们很难有直接的经验可以沿用。”⑤因此,我特别留意梅卓小说以什么样的艺术方式直面藏族文化的现实。鲁迅开创的“为人生”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中就有着非常清晰的“直面现实”理念,并深刻影响着不同时期的中国作家的写作取向,成为汉语作家遵循的传统和参照。
分析格萨尔史诗之于《神授•魔岭记》的意义,并不是说史诗给了这部小说的形式和内容以什么样的影响。《神授•魔岭记》并不是重新用现代文学形式演绎格萨尔史诗,而是在重构这部史诗,在方法论意义上受到史诗叙事的启示。众所周知,鲁迅的《故事新编》记载了许多神话和传说,究其创作意图,并非通常人们认为的发思古之幽情,而是借中国上古传统文化体系探索现实意义,表达当下的思想旨归,即回归早年《文化偏至论》所提及的“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⑥。因此在鲁迅看来,“虽然明知道过去已经过去,神魂是无法追蹑的,但总不能那么决绝,还想将糟粕收敛起来,造成一座小小的新坟,一面是埋藏,一面也是留恋”⑦。如果说西方小说起源于古希腊神话,那么正如有关研究者认为的那样,中国小说与神话之间缺少一个文学的中介,神话文体是一个无法讨论的问题。
梅卓的神话故事拓展了藏族文学的想象版图,这些文本提供了一种“在别处”的风景,使我们得以看到别样的人和事。无论就梅卓本人以前的创作,还是新时期以来的藏族文学,《神授•魔岭记》都具有经典价值。这是一部不可多得的长篇小说。小说最初的故事发生在藏历六月的第二个火曜日,由一个姻亲联盟引发:
这也正是阿旺罗罗今天比往日起得更早的原因。所谓姻亲联盟他不甚明了,但格萨尔神授艺人将要到来的消息让他激动万分,这是他记事以来一直默默向往着的。爷爷说格萨尔大王出自藏地四大姓氏的东氏,他是千百年来东氏人的骄傲,我们东查仓部落的每个人身上都流着格萨尔的血液,因此我们每个人都肩负着一个责任,那就是要让格萨尔的英雄事迹世世代代传唱下去。⑧
就创作题材和形式而言,梅卓打开了书写藏族文化的新空间,这是梅卓之前未曾尝试过的,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启示后继的创作。
二
关于史诗,梅卓有着怎样的笔致?对格萨尔史诗中的魔岭大战的重构以及为写作《神授•魔岭记》所做的各种准备,让梅卓对藏民族的文化以及神话思维有了全新认识,这激活了她观察和书写藏民族文化的热情并转换为写作中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说到底,文学作品归根结底书写的是人,阿来说过,“好的文学作品大多对人、对人物会有三个维度的考量:一是个体的人;二是作为国或族的文化的或政治性的人;第三个维度也是需要考量的,这就是一个更大的概念,人类的人,普遍人性中的人”⑨。《神授•魔岭记》涉及人、魔、神,归根结底还是写人,人从来就是现代小说的中心。
当我说在藏族历史文化叙事中有一位叫梅卓的女性时,我并非意在突出作家的性别,与其以前作品比较,我怀疑女性主义批评策略面对梅卓的《神授•魔岭记》时的有效性。许多作家在文坛创作中一路走来都有着自己的节奏。事实上,梅卓的创作不是传统的现实主义,而是经过现代主义洗礼,汲取了先锋派的写作技巧。我想,梅卓的创作在题材选取方面一定有过内心的犹豫、困惑甚至怀疑,这种内心状态无法通过任何他者指点或者在他者影响下而有所改变。
有研究者认为,“梅卓对藏文化的再现,有自己独特的想象路径,最重要的一条是:在反思藏族历史、呼唤民族复兴的大叙事长篇小说中,生死爱欲往往成为结构故事、推动情节、塑造人物的原动力、想象源”,这样的描写导致“梅卓的叙事在矛盾犹疑中摇摆不定:一方面,梅卓沉醉于火热情欲的生命宣泄,似乎时常忘记民族大义、历史责任,宁愿让欲望书写牵引自己对青藏高原自然人性、野性爱情的传奇想象;另一方面,梅卓反思藏族遭受异族欺压凌辱、侵略蚕食的悲惨历史,对藏族固执盲目、狭隘愚昧、自相残杀的民族劣根性痛心疾首,寻找民族出路的焦虑充塞在爱欲纠葛的空隙里,使原始欲望的挥洒因饱含大祸临头的毁灭感而显得湿淋淋沉甸甸”。⑩这样的评述如果放在其《太阳部落》《月亮营地》,以及《佳姆萨朵黛》《转眼就是夏天》等小说中倒是切中真意,但从《神授•魔岭记》中似乎可以看到鲁迅笔下的末庄和鲁镇,文本的背后有着批判意识,在精神倾向上接近鲁迅。
在当下题材层面,梅卓曾经用她的文字记录下了爱情与藏文化宗教思想的碰撞与结合,表现当代都市白领的物质生活和感情风波,呈现出藏族女性丰富驳杂的文化身份和当代悲欢。梅卓在表现爱情主题的书写中,将藏文化的魔幻现实以及充满野性的情爱描写得淋漓尽致,在生死爱欲的激情书写中赋予藏族文化以现代性因子。梅卓的小说为藏族文学,也为汉语文坛带来一种迥异而迷人的风景。日本学者柄谷行人从“言文一致”角度谈到风景与人的关系,认为“现代的自我”只有通过某种物质性成为制度性的东西,才有存在的可能,由此“风景不是由对所谓外界具有关心的人,而是通过背对外界的'内在的人'发现的”⑪。作为一部藏族传奇小说,《神授•魔岭记》呈现出了许许多多杰出的神奇景观,这些景观浸透着深沉的民族寓言,展现着远比景观本身丰富的文化信息。
《神授•魔岭记》这部小说融入了作家的生命体验,以及民族或族群的集体记忆,形成独特的自然崇拜和文化记忆景观。转山可以获得山神的佑护,人们对此深信不疑。在东查仓部落,人们敬奉格萨尔,听格萨尔史诗说唱、诵经、祈祷、挂经幡、煨桑、点酥油灯、供奉神灵,这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种信仰习俗和心理需要。从文化史意义而言,“风俗和人之间的关系是互动的,风俗是集体的历史的生成,风俗一旦生成,作为一种文化范式,就会反过来规约人们的思想和行为”⑫。这种源自一个民族记忆深处的文化遗传因子与自然息息相关,形成朴素的自然生态意识,人们赋予一切自然物以神性品格,并与之达成心灵默契一一神灵无处不在,而且直达人们的内心。这种信仰民俗在《神授•魔岭记》中俯拾即是。
信仰之于心灵的加持力十分强大,人们信仰格萨尔,因为格萨尔是正义的化身,代表了慈悲善良、勇敢无畏等一切正能量,成为民族的象征和民众崇拜的对象。这信仰为自然景观赋予了宗教意义上的人性和神性:
阿尼玛卿,这座梦幻般的神山,向阿旺罗罗展示着壮观的自然景象和奇异的神秘传说。阿旺罗罗看到雪山在幻化,渐渐化作一位武士。武士身色雪白,右手拿着白藤鞭,左手拿着珍宝,身穿金制的盔甲,骑在一匹金鞍的白马上。大师说:“这位就是神圣的阿尼玛卿山神,他居住在富丽堂皇的白玉琼楼宝殿之中,有英姿勃勃的九儿九女,还有三百六十位眷属,以及忠实勇武的卫士和侍从一千五百多个。如果向他祈祷,他能满足世间一切愿望。”⑬
在《神授•魔岭记》中,人们将一切美好与善行赋予格萨尔,将所有丑陋与恶行赋予魔王路赞,这反映了藏民族朴素的伦理观和世界观。在光明与黑暗之间,在魔性与神性之间,梅卓都借助神话探问“人”的深度和广度。格萨尔是藏族的保护神,每个藏族人心中都有不一样的格萨尔想象:
雄狮大王格萨尔永远骑着他的江。葛佩布宝马,昂首阔步地奔向前方,他的前方恢宏深邃,那里有雪山的伟岸,草原的博大;那里万物生长,所有的生命都郁郁葱葱;那里男人视死如归,鲜血铸造的英雄冠冕千古流芳……⑭
格萨尔代表着藏民族的英雄形象,成为藏民族的保护神,格萨尔的故事则成为藏族文学中的母题。他离开人间的时候,将保护众生的使命交给了神授艺人,神授艺人乃格萨尔在俗世的代言人,因而享有无上的荣光。对藏族文化的认同感是当下所有藏族作家共同的精神特征,从比较意义上看,梅卓的小说所塑造的主人公承担着在历史跌宕和现实冲突中延续文化和凝聚部落的使命,她通过这样的人物表现出对藏族文化的强烈认同,表现出对藏族文化传承重任的担当。
《神授•魔岭记》塑造的阿旺罗罗则是承担着格萨尔史诗说唱传承重任的文化英雄,整篇小说都围绕着这位格萨尔史诗说唱艺人的现实或梦幻进行叙事。可以认为,这位说唱艺人是《神授•魔岭记》塑造得最成功的形象。这位英雄的格萨尔讲述者经历无数磨难,在“末法时代”打败魔王,终于修成正果。在这个意义上,不妨说《神授•魔岭记》是一部当代的史诗。
三
作为藏族女作家,梅卓既受传统藏文化影响,同时也吸收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写作技巧,其小说表现出浓郁的藏文化特色和魔幻色彩。
《神授•魔岭记》中的成人礼、神箭之路、聚石成灵、圆光镜等,都充满了魔幻神秘色彩,这来自作家自身的民族身份界定和民族主体性的自我定义,而这是藏族作家梅卓的自主选择,并非主流文化强加的,因此她作为少数民族作家,是自觉秉持着这种文化自觉的写作策略的。
作家基于本民族的文化传统进行创作,不仅有意识地放大、渲染藏文化的神奇魅力,还在民族文化的魔幻现实中寄寓象征,使其成为一种身份认同的自觉选择。从文学层面来看,藏族文学的神话叙事丰富了汉语言的表达,打破了现实和虚幻的边界。
正如鲁迅通过文学介入现实,通过杂文、小说进行社会批评和文化批评那样,“其实,无论是马尔克斯的魔幻叙事还是昆德拉的哲理叙事,它们都具备与现实社会政治话语保持适度距离的审美风范,它们都以潜在的反讽而不是显在的批判见长”⑮。
神话不仅仅是“英雄时代”的原始文化现象,也是人类本原生存意义的元叙事。梅卓在其叙事中许多时候是与自己对话,这样的方式有时将自己局限于单一的时空,限制了精神的开拓,但也避免了无病呻吟、泛泛而谈。“依据史诗元叙事的散韵体,构成了不同文本或单一文本之间多向度平行交叉的异质同构与复调织体思维,彰显了集体记忆与民族精神的总体信念。”⑯
藏民族文化中呈现给外界的是诗与歌,格萨尔史诗以说唱的方式传承藏民族的历史寓言。
格萨尔史诗是藏民族世代传唱的活态史诗,不同的说唱艺人会说唱不同的内容,梅卓重构了史诗中的魔岭大战,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她也是神授说唱艺人。《神授•魔岭记》对格萨尔史诗及其说唱艺人的观察和体悟,捕捉到神话世界的现实根源,古老的史诗神话与先锋书写相映成趣,呼应了当代文学的某些思潮。梅卓的创作或许是受到博尔赫斯的影响,学识与诗显得颇为重要。在文本的深层脉络中,海德格尔式的哲学也弥漫在时空之中,存在的问题被提升到很重要的层面,这样的诗性语言使古老的神话重构走向了审美维度。梅卓的史诗故事丰富了中国文学的想象版图,这些文本提供了一种“在别处”的风景,我们借这些故事看到别样的人生形态。《神授•魔岭记》以一种极具魔幻色彩和个性化的笔调丰富了我们的感觉世界,使当代人的视野得到了更新和再生。
尽管我们永远无法重返古老的史诗时代,但我们总还是可以凭借梅卓的文字,去短暂地设想那个现实与梦幻、神与人互相依存的世界。我们几乎可以听到梅卓在写这些文字时的叹息,那是一种对于“永恒失落”的追悼,梅卓就这样把宗教情怀融入人生感悟,为写作引入民族文化的源头活水。
梅卓的边地书写总让我不自觉地联想到鲁迅的《故事新编》《野草》等作品,一次次的书写、抵达,凝固成一篇篇似真亦幻的“传奇文本”。那些高远的空间寄托了作家对真与美的理想追求,那种魔幻又不悖乎人性的故事,足以表露出现代性降临带来的惆怅和乡愁。正如鲁迅写出《狂人日记》《故乡》,梅卓写出了《魔咒》《麝香》,现代性的幽灵就在这乌托邦与现实之间彷徨、游荡。在现代社会,田园牧歌已然远去,梅卓凭借书写不断地重新召回已经逝去的美好,从这个层面来说,那些浪漫、忧伤正是抵抗虚无、守护美好的方式。
梅卓散文、小说中时隐时现的激情和感伤是本色的、独特的,“很多时候,中国人所有的边缘焦虑和生存痛感,不仅基于'生活在别处'的不习惯与不方便,还基于文化身份的失落,包括由此引出的被'他者化'的痛苦和被'妖魔化'的困惑”⑰。梅卓在《走马安多》中曾谈到她自己的生活经历:“我出生并生长在草原、群山之中,最美的莫过于万里长云蓝天,青翠苍茫草原,红墙金顶的寺院群落,曲径通幽的静修之地,这种与世无争的宁静平和,时时刻刻警示并安慰着我,这是与我息息相关的土地我的文学创作源于游走并感动于游走的地方。”⑱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重读梅卓,就会发现她赋予了“崇拜”和“信仰”一种新的关系。在中华文化圈中,对故土的眷念与热爱已然成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果将其移置于更大的社会历史语境来看,藏族聚居地区在现代性实践进程中遭遇了一种巨大的失落感,藏族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也在经历着转型。“在历史的转型期,女作家的敏感使她们能够捕捉时代的脉动,无论是宏阔的外部世界还是微细的内心世界,她们都精心描摹。革命的冲突与变动、内心的寂寥与焦灼,在'革命的第二天',一切如期而至⑲梅卓对藏族文学的抒情传统用个人话语进行现代转化,将其变成了关怀和抚慰,女性个人话语的现代性维度因此显现,个人意识与人间意识并存,在众声喧哗中又留下了个体自我独语。
梅卓在《神授•魔岭记》这部小说中不仅重构了史诗,还在史诗重构中反省了当下的西藏文化的传统,将神话和现实融汇,从而对藏族的宗教信仰和民族根性问题做出了新的诠释。我们在小说中读到藏族的民谣、神山崇拜、藏人、宗教信仰、经师、魔王、寺院,以及许多我们在汉文化语境中未曾体验的一切,这些元素给我们一种迥异的审美感受。我觉得,这是《神授•魔岭记》最独特之处。
结语
日本学者柄谷行人认为,那些看似不证自明的现代文学都是形成于特定时期的关于文学的意识形态。他进一步指出:“在追溯文学起源时,我们只是在那里寻找文学、文字而已。”“对于我们来说,那个不证自明的'国文学史'其实是在'风景之发现'中形成的。为了考察'风景之发现'这一被忘却的颠倒,我们必须扭转这个时间上的顺序。所谓风景乃是一种认识性的装置,这个装置一旦成形出现,其起源便被掩盖起来了。”⑳
就藏族小说缘起而言,其发生过程似乎同样证明了柄谷行人所谓的“风景之发现”的颠倒一一藏族文学最终归复于中国现代文学传统。不过,藏族作家在中国当代文坛的写作也带来了别样的经验与启示:重构的史诗传说与现实叙述同样重写着汉文化视野下的藏地想象,现代社会在某一阶段确立起来的话语方式在发明出一种特殊的文学主流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种执拗的低音,是后者而非前者,构成了中国文学现代性之无限趋新求变的永恒动力。正如梅卓的《神授•魔岭记》,在契合外来者的藏地想象同时,追求的是那种神话、史诗、信仰三合一的艺术表达。
20世纪末,受域外思潮的影响,魔幻书写开始进入当代作家的视野,作品风格完全不同于以往。这一切使得当代文学的天地更加开阔,使当下文坛拥有更多彩的景观。梅卓从藏族格萨尔史诗中寻找传统资源并进行现代性转化,体现了少数民族作家为民族文化立传的多重叙事探求,也为藏族作家的创作开启了多种可能性。在汇流于汉文学传统的同时,亦昭示了其作为地域写作的多元性与开放性,这才是以阿来、梅卓等为代表的少数民族作家及其创作的真正价值之所在。
*本文为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鲁迅与中国现代文学新范式形成关联研究"(AHSKY2O19D125)阶 段性成果.
注释:
①丹珍草:《女性叙事•个人话语•集体记忆——以梅卓长篇小说〈神授•魔岭记〉为例》,《西藏大学学报》 2020年第2期。
②梅卓:《神授•魔岭记》,青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题记.
③丹珍草:《女性叙事•个人话语•集体记忆——以梅卓长篇小说〈神授•魔岭记〉为例》,《西藏大学学报》 2020年第2期。
④阿来:《阿来文学演讲录》,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17年版,第2页.
⑤阿来:《阿来文学演讲录》,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17年版,第3页.
⑥鲁迅:《坟•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7页。
⑦鲁迅:《坟•题记》,《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页。
⑧梅卓:《神授•魔岭记》,青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9页。
⑨阿来:《阿来文学演讲录》,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17年版,第39页。
⑩张懿红:《生死爱欲:梅卓小说的民族想象》,《南方文坛》2007年第3期。
⑪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赵京华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年版,第66页。
⑫吴玉杰、刘巍等:《中国现代女作家的女性文学意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98页。
⑬梅卓:《神授•魔岭记》,青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129页。
⑭梅卓:《神授•魔岭记》,青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455页。
⑮李遇春:《中国文学传统的复兴》,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178页。
⑯丹珍草:《女性叙事•个人话语•集体记忆——以梅卓长篇小说〈神授•魔岭记〉为例》,《西藏大学学报》 2020年第2期。
⑰汪涌豪:《文明的垂顾》,中西书局2014年版,第145页。
⑱梅卓:《走马安多》,青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17页。
⑲吴玉杰、刘巍等:《中国现代女作家的女性文学意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61页。
⑳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赵京华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年版,第12-15页。
原刊于《阿来研究》第15辑

蔡洞峰,安徽桐城人,苏州大学文学博士,副教授,安庆师范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研究生导师。在《鲁迅研究月刊》《东岳论丛》《绍兴鲁迅研究》《上海鲁迅研究》《北方论丛》等刊物已发表50余篇学术论文,部分论文被《人大复印资料》转载。先后主持省部级、厅级课题4项。

梅卓,女,藏族。一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青海省作家协会主席,《青海湖》文学月刊主编,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青海省优秀专家。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太阳部落》《月亮营地》,诗集《梅卓散文诗选》,小说集《人在高处》《麝香之爱》,散文集《藏地芬芳》《吉祥玉树》《走马安多》《乘愿而来》等,作品入选多种选集。曾获全国百千万人才工程奖、全国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拔尖人才、全国第五届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全国第十届庄重文文学奖、中国作家百丽小说奖、青海省首届青年文学奖、第四、五、六届省政府文学作品优秀奖、青海省四个一批拔尖人才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