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次仁罗布的小说创作立足于本民族传统文化和当代文化语境,试图从民族传统文化中衍生出具有普适性意义的艺术题旨。他的小说创作过程,是关注人的生命存在,不断弘扬民族传统文化精髓的艺术实践过程。在创作初始阶段,他的小说就表现出了对人的精神世界与情感世界的关注,这也是他小说创作的原点。在此后的小说创作中,次仁罗布没有拘囿于特定的民族和地域,而是聚焦于对生命的深切关怀,并向着一种最高的生存境界迈进,更加关注人的精神力量的强大和心灵世界的广阔,这也是次仁罗布小说创作的独特之处。
【关键词】次仁罗布;民族文化;宗教;苦难
1992年,次仁罗布小说处女作《罗孜的船夫》发表于《西藏文学》第4期。这是一篇带有习作性质的作品。小说主题清晰、单一,学习、借鉴的痕迹比较明显。仅就主题而言,这篇小说承袭、接续的是新时期以来,西藏文坛上以扎西达娃、色波等为代表的作家一开始创作时所表达的社会主题,即生活在新的社会历史环境中的人们,对现实幸福生活的向往与追求。当然,这种艺术表达也是当时西藏当代文坛的主流。即使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扎西达娃、色波、通嘎等人为代表的作家转变文学路向,追求现代主义艺术表现的那个阶段,西藏当代文学的主流其实依然是现实主义。因此,把这篇小说放置在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西藏当代文学背景中来考察,就会发现,它所表现的也是一种带有主流倾向的社会文化主题。对次仁罗布来说,选择这样一种创作取向,可能与他的艺术经验和生活阅历有关。次仁罗布刚从大学毕业,走上社会不过五六年,文学阅读多局限于带有社会学意味的作品,对社会人生的认识不够广博深入。这种相对单一狭窄的阅读和生活经历,自然会影响其创作视界。之后的十多年,他断断续续发表了一些小说,如《朝圣者》《秋夜》(又名《笛手次塔》)《炭笔素描》《情归何处》《传说在延续》《焚》《尘网》《泥淖》《前方有人等她》《雨季》《杀手》《界》《奔丧》等。这些作品从题材上看,主要关注现实生活中人的生存境遇,具有比较鲜明的写实特色。其中的差别只在于,有些作品倾向于描写人们在物质追求中的努力与挣扎,有些小说则侧重于揭示人在情感漩涡里的冲突与煎熬。这些小说中有个别篇目已经显现出了次仁罗布创作独有的艺术特质,如《雨季》《界》《前方有人等她》等,在小范围内产生了一些影响,也获得了一些奖项,但却没有在更大范围内引起反响。对于次仁罗布此阶段的小说创作,大致可以做出这样的判断:以聚焦社会现实境遇中的现实人生和情感纠葛为主要题材内容,以表现普通人因现实生活中某些需求的无法满足和情感的缺失而伤感、失落和郁郁寡欢为主导性取向,主题略显单一,人物形象的审美意蕴较为薄弱,能够让人产生情感激荡和心灵颤动的作品不多。
尽管此阶段次仁罗布的不少小说从主导性方面看,更多地聚焦、关注人的现实追求和世俗欲望的满足,在主题上带有鲜明的反映世俗生活和表现人的现实欲求的意向,但与众不同的地方在于,他同时也给这种非常世俗化的生活景象设立了一个对立面。当然,这个对立面并没有否定人们世俗化、物质化的现实渴望与追求,而是对人的超凡脱俗的精神世界的表现和肯定,对真挚的人伦亲情的维护。因此,在作品中,他往往会以一种辩证的眼光来审视世俗欲望与精神追求之间的悖论。正是在这种辩证的认识逻辑中,次仁罗布表现出对人的精神世界和情感世界的重视。换句话说,虽然次仁罗布并没有在作品中否定人的物质化的世俗追求,也不否定人的合理的世俗欲望,但他在创作的初始阶段就表现出对人的精神世界和情感寄托的格外关注。这种倾向在他的第一篇小说《罗孜的船夫》中就已有所显露。之后,这种艺术取向随着其艺术经验的积累、人生阅历的增加和思想认识的提升与艺术思维的多维化,变得越来越明显和稳定,从而使他的小说显现出一种与众不同的精神风貌和品格。
《罗孜的船夫》讲述的是一对父女在人生观、价值观方面的矛盾与冲突;展现了在新的时代背景中,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各种文化观念的交流撞击,人们固有的思想观念和生活观念的逐渐转变。女儿为了不让年老的父亲孤身一人在山村孤寂地生活,劝说父亲离开山村,跟随自己到拉萨生活,享受所谓的幸福日子。但父亲拒绝了女儿的请求,独自留在了偏僻的山村。父亲看不惯女儿只追求现实物质利益和生活享受的功利主义做法,对她只知道追求物质生活的富裕而不遵从传统伦理道德规范的做法感到失望和不满。在父亲的观念意识中,对于人的生命而言,金钱和现实物质利益并不是最重要的,人活着最重要的是精神上的满足和恪守古训。
在具体叙述中,次仁罗布并没有简单地否定船夫女儿追求现实幸福的动机和做法,也没有旗帜鲜明地颂扬老人精神世界的清洁高贵。在这篇略显稚嫩的处女作中,次仁罗布表现出了思想意识方面的矛盾。在这种矛盾中,次仁罗布的情感意向和价值判断还是表现出了一定的倾向性。这种倾向性就是对人的精神世界的重视。而这种倾向主要是通过小说的叙事语调体现出来的。在整个叙事过程中,叙述者对老人给予了很大的理解和同情。结合次仁罗布后来小说创作在精神维度上的主导性取向,可以说,《罗孜的船夫》中的这种倾向,为其后面的创作设立了一个标识,这是其艺术精神里的一种类似“生命基因”的元素,它在次仁罗布此后的创作中有迹可循,且越来越明晰。体现在创作主题的追求上,是对现实物质追求的有意回避,对精神世界和情感世界的选择性关注。回溯其创作踪迹,梳理其创作线索,可以说这篇小说就是其艺术踪迹的原点。它为其之后的小说无意识中定下了一个基调,那就是:对人的精神世界和情感世界的精心呵护和深沉关切。这样总结当然不是说次仁罗布不关注现实生活,也不是认为他的文学世界有意拒斥世俗人生。事实是,从始至终,他的小说创作都没有表露出逃离世俗的倾向。他只是在描写人的现实生存境遇时,更倾向于关注具有形而上意味的精神领域和情感世界。具体来说,次仁罗布试图追求这样一种艺术表达和审美境界:即肯定、伸张人的宽容坚韧的精神信念和向善求美的美好情愫,并以此彰显这种信念和情愫,使人们能够在并不美好的现实遭遇中坚韧顽强地生活下去,让人们能在充满着诸多意想不到的困苦磨难的人生道路上乐观地生活下去。这种艺术追求,影响、决定了次仁罗布小说创作的基本审美指向:心怀善念,以真挚的情爱去面对生活和生命个体,为孱弱残缺的生命祈祷,给每一个生命以尊严。这一艺术追求,在上面提及的一些小说中已经得到了初步表现,如《雨季》《界》《杀手》等。
2009年,短篇小说《放生羊》在《芳草》第4期发表,之后被《小说月报》第9期转载,入选该年度多个小说作品集。2010年,《放生羊》获得第五届鲁迅文学奖,为次仁罗布赢得了全国性的文学声誉,次仁罗布的创作也因此被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和评论家关注。以《放生羊》为典型文本,人们对次仁罗布的创作展开了广泛评说和研究。由于《放生羊》鲜明的地域文化色彩和浓郁的宗教气息,在围绕它展开的评说和研究中,除了从叙事学的角度分析、解读外,很大一部分都是关于“宗教书写”的。结论大致是:这篇小说表达了作者深厚广阔的慈悲(或悲悯)、怜悯的宗教情怀。2015年,次仁罗布的长篇小说《祭语风中》出版后,又一次引起了人们对次仁罗布的广泛关注。而论者们对《祭语风中》文化主题层面的评述,其认识范围和评价定位,也没有超出之前人们对以《放生羊》为代表的次仁罗布小说世界的认识和定位。慈悲、体恤、宽容、灵魂叙事等,是评论界对《祭语风中》,乃至次仁罗布整个小说创作的基本认知和定位。论者们大多认为,次仁罗布的创作之所以产生这种审美效果,根本原因在于其深厚博大的宗教文化背景和深广真挚的宗教情怀。持这种论点或类似观点的文章主要有《苦难的承担与救赎的温暖——读次仁罗布的短篇新作》[1]《揭示现代文明冲击下藏族生活的常与变——评次仁罗布小说集<放生羊>》[2]《一世沧桑谱心经——评次仁罗布的<祭语风中>》[3]《将灵魂安放于风中——次仁罗布的<祭语风中>》[4]《苦难岁月的灵魂记忆——评次仁罗布的长篇小说<祭语风中>》[5]等。
对于这种高屋建瓴式的分析和陈述,笔者的基本判断是,它们大体符合次仁罗布的文学世界所提供的题材内容和所折射的一些文化艺术精神。其基本依据是次仁罗布的小说中经常出现与地域文化和民族宗教现象有关的细节描述和场景展现,而许多人物的心理意识和日常生活行为也与宗教现象密切相关,甚至是融为一体的。鉴于次仁罗布作品的宗教文化背景和题材内容,对其小说创作展开一种地域文化层面和宗教文化视野内的解读阐释,自然是顺理成章的研究路径。在这一路径上,评论者、研究者们也确实做出了值得肯定的努力,尽可能发掘、揭示了次仁罗布代表性作品的“宗教书写”及其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和审美价值。
但笔者的疑惑是,这种基于创作主体鲜明的地域宗教文化背景而对其作品主题意向所做的归纳和概括,是否把次仁罗布文学世界所包含的更为重要的内涵做了尽可能周全的描述与提炼;是否真正凸显了次仁罗布小说创作的独特性。换句话说,这种归纳概括,是否把次仁罗布创作对宗教现象、宗教文化心理的种种描写,与那些和他有着相同的文化背景的藏族作家的宗教书写做了有效的区分,是否发现并描述出了次仁罗布宗教书写的独特性。如果没有达到这样的目的,或者说还没有发现次仁罗布小说创作的独特之处,那次仁罗布的小说创作,可能就是对众多具有相同题旨和审美取向的地域文学创作的重复。
如果不能发现这种独特性,就会让次仁罗布这样一位可能具有自身个性的作家淹没在中国当代文学的洪流之中而面目不清。因为一个非常明显的事实是,关于文学创作中“慈悲、怜悯、体恤、宽容的精神内涵,以及这种精神内涵所体现的宗教情怀”这样一种文化审美取向,在绝大多数藏族作家的作品中都是存在的,在中国现当代小说中也不鲜见。在当代藏族作家的创作中,只要涉及宗教书写,几乎都会不同程度地体现出“慈悲、宽容、怜悯”等宗教情怀,即使是那些批判宗教的作品,也包含着上述内涵。无论是小说家,还是诗人;无论是散文,还是其他类型的文学作品,甚至是一些文化史料类的著作,都会显现出上述宗教情怀。如果我们的阅读视野再扩大一些,就会发现,即使是那些不信仰宗教,没有宗教文化背景的作家,他们的作品同样蕴含着悲悯、怜悯、慈悲、体恤的崇高情怀。事实上,一个作家在作品中是否表现了所谓的宗教情怀,问题的关键并不是他是否具有宗教文化背景,不在于他是否信仰宗教,而在于他是如何表达宗教情怀的,更重要的是,他所表达的宗教情怀到底处于哪个层面?他与其他同类作家的创作有何不同?因为,只有这些因素才能体现出他创作的独特性。面对次仁罗布这样一位成绩显著且颇具艺术个性的作家,我们有必要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了使这一问题更具针对性和可比性,我们尝试把次仁罗布放在当代藏族文学发展进程和文化语境中加以考察。这也许会对我们认识这一问题有些帮助。
对于绝大多数藏族作家来说,佛教文化是一种与生俱来的精神文化资源,尽管他们也会遭遇、接受其他类型的文化资源,会借鉴、吸收其他类型的文化资源和精神,但在他们的文化结构体系内,佛教文化却是根源性、基础性的。因此,当代藏族作家的创作中,关于佛教文化的书写一直存在,就像血液在血管里流淌一样。这种情形,我们可以从当代藏族文学不同代际的作家创作那里得到印证。而从不同代际作家不同方式和目的的宗教书写中,我们又能够大致看到次仁罗布宗教书写的独特性所在。
从当代藏族文学发展的历史进程来考察,当代藏族文学的发展历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以益西卓玛、恰白·次旦平措、擦珠·阿旺洛桑、饶阶巴桑、伊丹才让、格桑多杰等为代表的一批作家创作为主。第二阶段以新时期之后登上文坛的作家创作为主,代表性的作家包括德吉措姆、尕藏才旦、丹增、扎西达娃、阿来、色波、端智嘉、伍金多吉、列美平措、才旺瑙乳等。第三个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逐渐崭露头角,占据文坛主流的新生代作家,这批作家在新世纪以来逐渐成了当代藏族文坛的中坚力量,他们以创作小说的梅卓、白玛娜珍、次仁罗布、尹向东、格央、格绒追美、江洋才让、达真、严英秀、罗布次仁、万玛才旦、旦巴亚尔杰、普布次仁、扎巴、拉加先和以诗歌创作为主的班果、扎西才让、完玛央金、单增曲措、旺秀才丹、东主才让、日吉梅朵,以及一些更为年轻的诗歌创作者为代表。这三个阶段中,都存在着宗教书写。就笔者的阅读经验来看,在三个阶段中,宗教书写有着不同的审美取向和文化意味。以益西卓玛、伊丹才让、饶阶巴桑、格桑多杰等人为代表的第一代作家,他们的宗教书写倾向于用谨慎的眼光审视宗教现象,对其表现出一种“疏离”态度。这批作家出生、成长于革命年代,见证或经受过旧制度的腐朽黑暗,对政教合一的政治制度的不合理性有过切身的体察,因此,他们在文学创作中对宗教现象的描写,大多带有审慎的态度。由于受所要表达的“反映革命历史和社会主义建设”这一主导性主题的制约,他们的文本对宗教现象的描写自然不那么细致、深入。这也为后来的创作在这方面的发展、开拓留下了巨大空间。这批作家在新时期之后,仍然断断续续地坚持创作,但基本的艺术路向变化不大。也有一些作家有所突破,但值得言说的方面并不显著。
第二代作家中以益希单增、意西泽仁、德吉措姆、扎西达娃、阿来、色波、通嘎、端智嘉、梅卓、伍金多吉、央珍、列美平措等为代表。这批作家中的大多数出生于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成长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新时期初开始逐步走上文学创作道路。相对开放的社会文化语境,多维的文学创作视野,多样化的题材和文学观念的选择,以及多样化的表现手法的运用,使这批作家的创作相对老一代作家来说更加自由开放。因此,他们的创作风格有着很大不同。对宗教现象的书写,自然也有着各自不同的偏好之处和艺术聚焦点。尽管如此,综观他们的创作,也有一些大致相同的侧面。其中一个侧面则是,他们的宗教书写都带有一定的反思、重构意识。其中扎西达娃和阿来最具代表性,影响也最大。他们从民族传统文化更新重构的角度,从民族传统文化适应新的社会发展环境,发挥正面功用的角度出发,以冷静开放的眼光审视民族传统文化,通过艺术表达的方式构想民族传统文化重构的可能图景。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扎西达娃停止了文学创作;阿来坚持自己的艺术追求,随着创作的深入,他的这种反思、重构态度也更为明确和坚定。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一批出身于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和70年代的作家开始崭露头角。新的文化语境和时代环境,给他们提供了开阔的创作空间,他们的人生经历、教育背景都使得他们比前辈作家有了更多的文学选择。人生经历方面,他们有机会拥有更为丰富纷繁的生活体验,因为他们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可以利用求学、参加各类文化活动的机会离开故乡,到内地许多省区,甚至到国外接触崭新的事物和观念。教育背景方面,随着中国现代教育的普及和涉藏省区现代教育的发展,他们获得了到全国各地不同高等院校学习的机会,从而很早就建构起了较为广博的知识体系。上述经历和教育背景,无疑会为他们的创作带来一些独特的气质和风貌。相对于之前的作家,他们的创作更加趋于多样化。就宗教书写而言,他们的创作呈现出多元态势。大致可以划归为三个向度。一是更倾向于把宗教文化现象作为纯粹的审美元素纳入作品之中,让它们发挥审美功能。当然,所谓的纯粹化的审美元素,是理想化表述,进入文学作品的文化现象,总会表现出一定的社会文化内涵,不可能是纯粹的审美元素。这种倾向在诸多作家的创作中均有不同程度的表现。第二是所谓的文化认同倾向。这类宗教书写表现出的是作家较为明显的对民族宗教文化的追忆与皈依倾向,以在作品中颂扬、讴歌传统文化中的一些稳定的精神观念为表征。代表性的作家主要有才旺瑙乳、白玛娜珍、格央、班果等。第三是通过宗教书写,力图追求一种具有超越地域和民族局限的普遍性价值。这类作家中以次仁罗布最为典型。他的创作以追求和表达对生命无条件的关爱和对人性弱点的宽容为主旨,同时表现一种忏悔、救赎的精神高度。而这种精神追求和表达在其小说中更多地是以超越既定的宗教理念和宗教伦理的方式来完成的。这使得他的宗教书写表现出了与其他作家不同的质地和气象。
阅读次仁罗布的作品,我们能够感受到,虽然他的文本世界与许多作家的作品一样,涉及诸多的宗教现象和宗教文化心理,但他的宗教书写明显有一种与众不同的审美取向。他的宗教书写,没有将注意力仅仅停留在描绘具象化的宗教现象和表现固有的宗教观念上,也没有拘囿在特定的民族和地域上,而是聚焦于着力表现对生命的深切关怀上。在此意义上来说,次仁罗布的小说创作所表现的精神向度,与作家有没有宗教文化背景似乎没有必然的联系,尽管他的宗教文化背景是与生俱来的,也确实影响了他的精神观念和文学创作。决定次仁罗布小说蕴含强大艺术感染力和震撼力的根本性因素,并不必然是他的宗教文化背景,也不是因为他的作品涉及宗教因素,而是作者的人生观、生命观和生活态度。当然,这样说并不意味着作家的人生观、生命观、生活态度与他的宗教文化背景没有关系。而是想指出,同样是受宗教文化影响的宗教书写,与其他作家相比,次仁罗布的宗教书写是有自己的独特之处的。而这种独特之处就在于,不是让宗教精神拘囿于某个地域和民族的文化范畴内,而是让它越出了民族文化的既定范畴,成了一种跨越地域边界的精神意识和生命力量。
那么,次仁罗布的宗教书写所体现出来的超越性内涵到底体现在哪些方面呢?他又是如何让自己的宗教书写达到这样一种审美效果的呢?我们不妨以他的最具代表性,也是在中国文坛上产生影响最大的短篇小说《放生羊》和长篇小说《祭语风中》来做一些分析。
毫无疑问,《放生羊》能够在当时众多候选的中短篇小说中赢得评委的青睐,并最终获得鲁迅文学奖,与它鲜明突出的地域宗教文化特色不无关系。作品所借用的民族宗教文化内容和所表现的感人至深的生命情怀,是这部小说在内容主题方面获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同时,作者选择的第二人称叙事视角也为这样的主题表达找到了非常恰切的表现方式。《放生羊》除了如一些评论文章所说,具有浓厚的悲悯、体恤的宗教情怀外,亦有着超越惯常的宗教意旨的主题。这个主题就是亲情伦理之爱和万物平等的生命意识。
在一般的理解中,认为《放生羊》中的主人公年扎老人遵循佛教生命轮回和因果报应观念,为了让死去的妻子桑姆早日投胎转世,坚持诵经拜佛,并为此从羊贩子手里买了一只即将被送往屠宰场的绵羊来放生。无论是对妻子桑姆,还是对放生羊,年扎都心怀慈悲、怜悯之情,为他们的受苦受难而感到难过,并希望通过自己承受苦难来完成救赎,这是一种深厚的宗教情怀。从小说所讲述的故事和它的文化背景来看,这样的理解固然没有错。但笔者认为,这篇小说其实蕴含着更为深广的内涵,这种内涵超越了特定的宗教观念和意识,或者说它包含着上述宗教内涵,但又不仅仅只是一种简单的宗教内涵。一直关注次仁罗布创作的藏族评论家普布昌居的一种见解具有很好的启发意义。她在评述次仁罗布的小说创作时,除了强调次仁罗布作品蕴含着悲悯、怜惜、宽容、忍耐等文化内涵,同时还指出,“次仁罗布的小说借助爱的资源高扬人的高尚德行,正是在这些美好精神的照耀下,生存的坚冰一点点消融,让我们于严酷现实之中看见米兰·昆德拉所说的‘美丽世界的影子’”[6]。普布昌居在更为开阔的视野中发掘出次仁罗布小说创作更为深广的精神品质——爱,这是对次仁罗布小说主题意蕴相当深刻地开掘,当然也是比较妥帖地开掘与解读。尽管在笔者看来,她还没有指出其中另外一些同样重要的内涵。
仔细研读《放生羊》就可以发现,潜藏在小说内部的,促使主人公年扎一切行动的根本性动因是亲情伦理之爱和众生平等的意识。正是这种亲情之爱和众生平等的意识,使得年扎不但为妻子桑姆的生命归宿感到担忧,从而甘愿为之诵经祈祷,并毫不犹豫地花费自己不多的积蓄买一只羊放生,以求妻子桑姆获得救赎。这一情节中包含的亲情之爱自不待言,而最值得关注的是年扎对羊的生命存在的爱怜与尊重,因为它体现了佛教众生平等的伦理观念。从而显示了作者超越一般的善恶观念和简单的悲悯情怀的思想意识。
如果说年扎的初始动机是以购买绵羊这一善行为妻子桑姆赎罪,此时的绵羊仅仅是为达到赎罪目的而被利用的工具;那么,在日后与绵羊相处的过程中,年扎则把绵羊视为与人类有着同等的生命尊严和平等地位的生命存在。这种转变,充分表现出了年扎心理意识中“生命至上、万物平等”的观念。《放生羊》的大部分内容都在讲述年扎与放生羊相依为命的亲密关系。而其中所表现出的平等友爱的关系,是最值得关注的主题旨向。小说在叙述上采取了第二人称视角,这给小说的主题表达带来了深刻的意蕴。用第二人称“你”来指代羊,这本身就蕴含着对作为与人类相异的物种的羊的尊重,而小说中叙述人“我”(年扎)对羊的一视同仁的态度,则体现出主人公对所有生命的尊重和关爱。小说中放生羊有时甚至是以年扎爱人的化身而存在的。尽管在“我”的心目中,也有借此来为妻子换取善的报业,从而让她早日投胎转世的“功利”目的;但“我”对放生羊的那份真挚之情,以及周围人对羊的关心、关爱,还是能够让我们感受到,作为生命物种的羊所得到的尊重与平等待遇。放生羊与年扎所建构的这种友爱平等的生存关系,是次仁罗布宗教书写最有价值的部分。因为它背后蕴藏的是作者对一切生命的关爱。这是一种超越一切鸿沟与隔阂的大爱。
小说中值得关注的情节还有年扎与羊一起转经、朝佛的过程,这也是小说用力最多最为集中的地方,它生动地表现了“生命至上、万物平等”的主题内涵。它同样体现了作者对生命的爱怜之情。在当代藏族文学中,转经、朝佛是一个极为普遍的文化现象和故事要素。在《放生羊》中,次仁罗布也描写了这些现象,只不过值得关注的是,小说描写这些日常行为时,特别突出了年扎与放生羊一起相互陪伴、如影随形、不离不弃地转经、朝佛的情景。在此过程中,小说通过叙述人(也是小说主人公)说明,之所以让羊也去转经、朝佛,是为了让它超脱——获得一个好的报应。小说中年扎对放生羊有这样一些“劝告”:
我突然想带你去小昭寺,让你拜拜释迦牟尼佛,争取来世有个好去处。
我提醒你,好好拜佛,用心祈求。你顺从地跟随我,你的目光落在慈祥的神佛和面目狰狞的护法神上,一种胆怯的虔诚表现出来,身子微弓,步伐轻柔。我从你的眼神里,发现你是一头很有灵性的绵羊,相信你跟着我会积很多的功德,这些以小积多的功德,最终会给你好的报应。[7]
在年扎的心目中,放生羊也可以通过修行积德而获得好的报应,从而在轮回转世中避免不幸的命运。把羊视作与人平等的物种,认为它可以与人一样,通过今生的修炼达到超脱,无疑有着极为深刻的文化内涵。佛教所倡导的众生平等,在这里得到了形象地体现。它让我们意识到,所谓的“众生平等”,不仅仅是人与人的平等,而是整个宇宙万物之间的平等。可以说,放生羊这一独特的艺术形象的刻画,既应和了佛教生命轮回的观念,也彰显了佛教“众生平等”的至高境界。在此,我们看到次仁罗布的宗教书写,最终指向是对生命的关爱,是对生命的一视同仁。显然,这种观念意识比那些简单地表现对人的苦难命运心怀怜悯的书写,更能体现出作家的广阔胸襟与宏伟视野。
小说的结尾,以一种带有象征意味的特写,强化了这种文化意蕴。
翌日,我们又从昨天停顿的地方开始磕长头。发现身边有几十个磕长头的人,从穿着来看,他们一定来自遥远的藏东。在嚓啦嚓啦的匍匐声中,我们一路前行,穿越了黎明。朝阳出来,金光哗啦啦地散落下来,前面的道路霎时一片金灿灿,你白色的身子移动在这片金光中,显得愈加的纯净和光洁,似一朵盛开的白莲,一尘不染。[7]
结合这一片段,我们有理由做出这样的判断,在广博深厚的人性之爱的指引下,《放生羊》把在藏族文化背景上展开的艺术创作的文化境界,提升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当然,《放生羊》并不是唯一能体现次仁罗布这种文化取向的小说。他的一些重要的中短篇小说都蕴含着这种文化伦理主题,比如《雨季》《界》《绿度母》《前方有人等她》等。即使是那些看上去没有涉及宗教现象的小说,次仁罗布也多倾向于表达“爱”对人生命存在的重要意义,比如《焚》《秋夜》《尘网》《八廓街》等。在这些小说中,《雨季》和《尘网》《界》以鲜明的主题显示了次仁罗布小说创作所追求的以“爱”为生命核心价值的主导性题旨。
《雨季》描写了一个不幸家庭的种种苦难,以此表现了家庭成员之间至亲至真的伦理之爱。小说中值得关注的是主人公旺拉在面对亲人一个接一个死亡时的态度。一方面,他把真挚的爱给予父亲、儿子、妻子;另一方面,他以坚强乐观的态度面对生活,以此来表达他对亲人的爱。这种生活态度,也与许多描写不幸遭遇或苦难的小说有着根本性的区别。它没有让主人公在“人生即苦”观念的促使下选择消极的生活方式,而是以“好好活着”的信念直面现实生活。在“人生即苦”的宗教文化背景中,这种主题表达显然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因为它表达的是对现实人生和人的生命价值的关爱和尊重,是对生命尊严的肯定和维护。《尘网》的视点集中在纯粹的世俗生活上,但表达的主题依然是“爱”对于人的生命质量和情感世界的重要价值。瘸子郑堆无论在情感上,还是在物质生活上,都没有获得过幸福感。在五十多岁的时候,他无意间获得了一次爱情,并因此而有了自己的孩子,他为此而焕发出了生命活力。尽管郑堆因意外去世,没来得及更长久地享受生命的快乐,但他感到很满足。小说结尾描写了郑堆死后他的灵魂所感受到的情景:
“跛子的灵魂如空气般,紧紧贴在女人的肚皮上,感受那小孩蠕蠕地动。跛子想:在这世上最好的莫过于爱。
跛子的亡灵不由自主地被喇嘛们的铃声牵引着,走出屋子,走向一片漆黑的夜幕里。
跛子一点都不惧怕,因为他想到尘世间自己曾经爱过人,而且爱的是那样彻骨。有了爱什么都不惧怕。”[8]
在作者的笔下,跛子(郑堆)的灵魂之所以能够安然地离去,是因为他在人间有过爱。有了这种珍贵的情感体验,郑堆获得了强大的精神力量,也就无所畏惧了。这正是次仁罗布小说在宗教文化背景中所追求的超越单纯的“怜悯、慈悲”等宗教情怀的主题意蕴。而这种主题意蕴在长篇小说《祭语风中》里得到了更为全面的深刻表现。
从题材上看,《祭语风中》是关于历史的叙述,演绎的是西藏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至20世纪90年代的历史进程,但叙述历史并不是它的主要目的。小说的题旨在于通过表现主人公遭遇种种苦难之后的精神世界,来彰显一种超越生死和苦难的高贵品质——博大宽广的爱,以及在这种爱的指引下对芸芸众生无常生命的救赎。
苦难叙事是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主题。古今中外,具有此类主题意向的作品不胜枚举。就中国当代文学来说,苦难叙事也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文学现象。出现了不少影响巨大的作家,比如余华、阎连科、莫言等的创作。次仁罗布的苦难叙事以西藏的当代历史为背景,描述了在宏大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个体生命所遭遇的种种苦难;在此基础上,表现个体生命博大开阔的精神视界和宽厚仁爱的胸怀,从而展示人的精神品质的高贵。而这些又是通过主人公晋美旺扎对生命存在的关爱和个人精神的不断反省表现出来的。在具体叙事中,次仁罗布让人的精神世界占据主导位置,发掘、揭示人的精神世界的矛盾与焦灼。通过揭示苦难的现实意义与展示生命个体承受苦难的能力,来彰显人的精神品质的高贵和完美。苦难在次仁罗布笔下蕴含着提升人的精神境界的审美力量,同时也是警示和促使人走向精神完美和心灵饱满的中介。生命个体正是在承受苦难和化解苦难的过程中,一步步领悟生命的真谛和价值,并逐渐明白无私的关爱和真诚的尊重,是生命应该具有的高贵品质。正是在这一点上,《祭语风中》延续和丰富了次仁罗布一贯的审美追求,使其作品显示出了独特的文化品格。
在中国当代藏族文学的宗教书写中,在关涉到人间苦难的时候,往往把苦难的产生归结于人的欲望难以满足,认为是人太执着于自我,太执着于自我欲望的满足,才导致人生的苦难;除此之外,还把苦难的产生归结于世事难料。这种认识和理解与佛教经典典籍中的“人生即苦”“人生无常”观念一致。毫无疑问,这种认识和理解有其现实根据和心理依据。但又不完全正确,至少与现实生活的复杂纷繁,与人性的复杂多面并不完全相符。因此,这样的宗教书写即使没有问题,也是有偏差的。次仁罗布的宗教叙事在这方面做出了摆脱既定的思维定势的努力。他所体认的苦难,其来源并不一定源自于人的欲望的难以满足,也不仅仅局限在现实可见的苦难上,而是指向个体生命的精神领域、心灵世界,是个体生命意识觉醒的必然结果,是体味到生命缺憾与人性弱点后的洞察。因此,在他笔下,即使是现实苦难,也会经过艺术转化,成为构建、锻造精神世界的烈焰。而这种由苦难燃放出的烈焰,淬变、熔铸出的是人物对生命无条件的关爱。
《祭语风中》的主人公晋美扎巴的一生,是与苦难相伴的一生。经历苦难是他理解“关爱生命”至高意义的中介,也是成就他人生价值的桥梁。因此,他对苦难采取了一种特别的方式,那就是积极面对、毫不回避。他所面对的诸多苦难,一开始都是外在的,物质上的、肉体上的、生活上的。对他而言,这些苦难并不是不能克服或回避。但他的做法是通过肉体上的煎熬,接纳、吸收化解此类苦难,试图把苦难当做精神升华的历练过程。从始至终,晋美扎巴没有摆脱过苦难,根本原因在于,对他而言,真正的苦难不是肉体上的疼痛或物质上的贫乏,而是精神上的无所依托和心灵上的不安焦灼。这种精神性的苦难,是潜藏于灵魂深处的,是隐秘的,是他人看不到的,只有自己才能感受到。它甚至是无法向他人倾诉的。而这种苦难的根源,则源自于他对人生缺憾和人性弱点的洞察和正视,来自于他对芸芸众生不幸命运的同情与爱怜。正因为此,他在经受过现实种种苦难后过上相对稳定安逸的生活时,内心却越发感到不安和惶恐。在他看来,消除这种不安和惶恐的唯一方法是为那些死去的和活着的人们祈祷,通过自己的身体力行——做一个天葬师,来超度人们的灵魂,完成精神的救赎。通过做天葬师,晋美扎巴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心理和精神上的平静,也算是完成了自我救赎。对晋美扎巴这一形象的塑造,是次仁罗布宗教书写所表现出来的独特之处,也是其过人之处。出于对每一个生命的关爱,他既对现实苦难予以关注,同时也肯定现世人生价值;又能超越具体可见的苦难,把苦难当做审视的对象,在心怀大爱的基础上,对苦难进行形而上的思索,探索苦难的意义,并寻求化解苦难的路径与方法,让人物以积极的态度面对苦难无边的现实生活,而不是简单地重复“人生即苦”“人生无常”的主题。尽管这种积极的态度和救赎的路径也不可能解决一切现实困境和生命难题,但晋美扎巴以对自我和他人的“关爱”为出发点,通过宗教方式进行自我救赎和救赎他人的行为,却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一形象的强大艺术力量。很显然,在次仁罗布的艺术逻辑里,宗教书写不仅仅只是描写宗教文化现象和宗教仪式,不是简单地描写与之相关的生活习俗;宗教书写不是描述一种远离世俗的生活方式,宣扬一种清静无为的心理状态,也不是追求精神上的超凡脱俗。次仁罗布的创作所追求的宗教书写,是一种向着人的最高的生存境界迈进的尝试。那就是:面对世俗,但又尝试着超越具体的世俗事务的羁绊,以超越个人的大爱去怜惜芸芸众生的苦难遭遇,从而完成对每一个生灵的救赎。而这种超越和救赎,其坚实的情感基础就是对世间万物的爱怜。这种爱怜的存在,使次仁罗布小说中的宗教书写穿越既定的宗教范畴,让人感受到人的精神力量的强大和心灵世界的广阔。
参考文献:
[1]尤其林.苦难的承担与救赎的温暖——读次仁罗布的短篇新作[J].小说评论,2009(5).
[2]欧阳澜,汪树东.揭示现代文明冲击下藏族生活的常与变——评次仁罗布小说集《放生羊》[J].阿来研究,2016(4).
[3]杨艳伶.一世沧桑谱心经——评次仁罗布的《祭语风中》[J].阿来研究,2016(4).
[4]叶淑媛.将灵魂安放于风中——次仁罗布的《祭语风中》[N].文艺报,2016-06-06.
[5]徐琴.苦难岁月的灵魂记忆——评次仁罗布的长篇小说《祭语风中》[J].当代作家评论,2016(6).
[6]普布昌居.让爱照亮生命——对藏族作家次仁罗布 2009年作品的研读[J].西藏研究,2010(6).
[7]次仁罗布.放生羊[J].芳草,2009(4).
[8]次仁罗布.尘网[J].西藏文学,2003(4).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改革开放40年藏族长篇小说研究(1978-2018)”(项目号:19BZW180)的阶段性成果。
原刊于《西藏民族大学学报》2021年第6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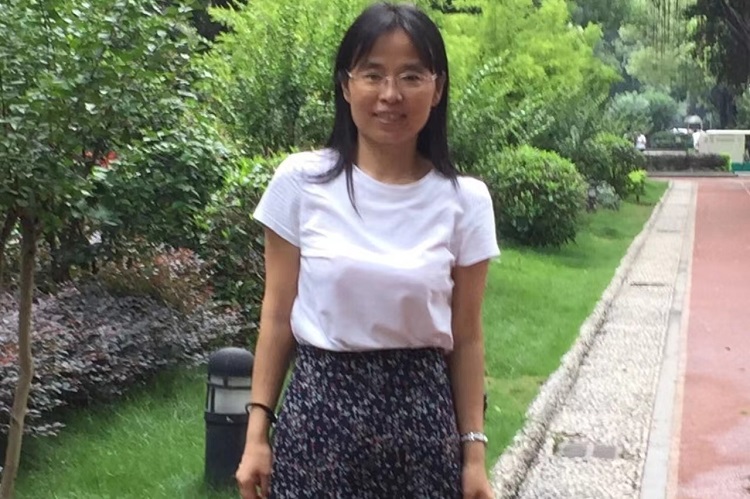
卢顽梅(1976~),陕西礼泉人。西藏民族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与西藏当代文学。

次仁罗布,藏族,西藏拉萨市人,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西藏作家协会常务副主席,《西藏文学》主编,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代表作有《杀手》《界》《阿米日嘎》《放生羊》《神授》《八廓街》等小说,《放生羊》获第五届鲁迅文学奖,长篇小说《祭语风中》获中国小说协会2015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第三名。作品被翻译成了英语、法语、西班牙等多种文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