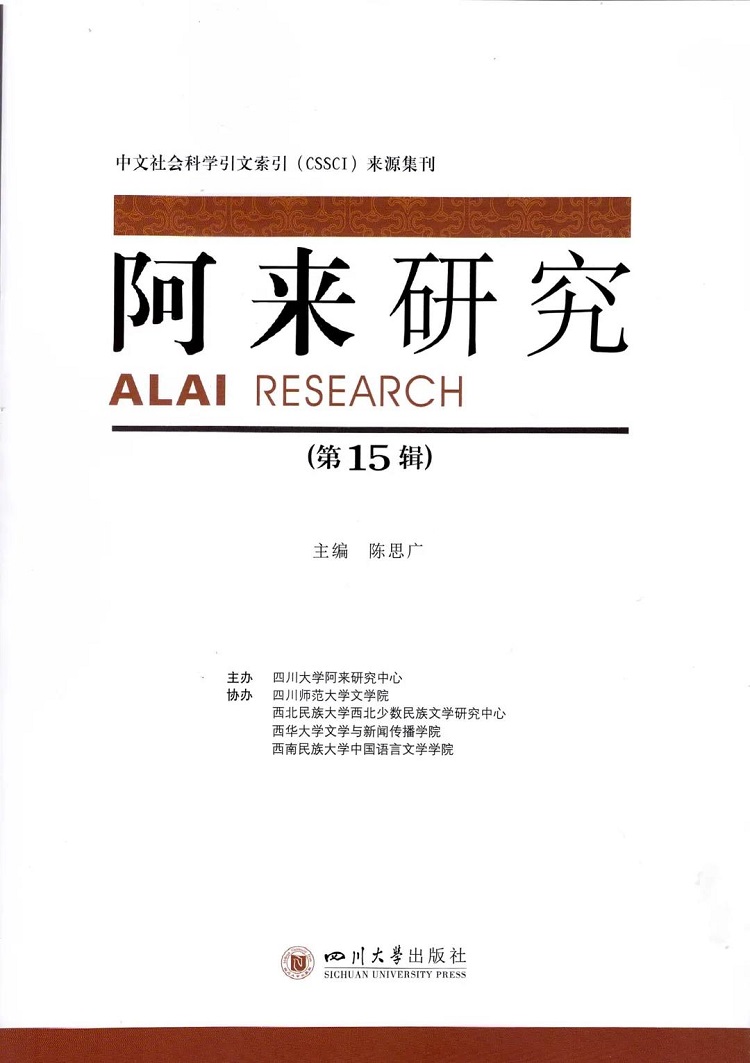
诸多藏族女作家中,梅卓别具特色。她的作品有着女性作家唯美灵秀的风格,清澈洗练,行云流水,亦不乏苍凉凝重、幽邃深沉的笔力,历史透视的深邃感和民族文化的忧思使她的多部长篇小说有着史诗般的苍凉雄壮。雪域文化的浸染更使她的作品洋溢着藏地神异色彩。
对于梅卓的创作,既有研究从多种角度进行了丰富、精彩的论析。本文拟从“气氛”审美的视角切入,期望从新的视域观照、分析梅卓的藏地书写。
“气氛美学”(The Aesthetics of Atmosphere)这一概念是20世纪80年代末德国哲学家、美学家格诺特•波默(Gernot Bohme)首次提出的。格诺特•波默从生态学角度进行美学论析,将“气氛”作为其生态自然美学研究的核心概念,进而又将气氛美学拓展至对自然环境、人文环境、审美环境等的研究。他打着“重返鲍姆加登感性学”的旗号,以身体现象学为基,对传统美学进行重构,形成了其独具特色的“气氛美学”。在他看来,“气氛本身却并不是物,它毋宁说是漂游不定的居间,介于物和知觉着的主体之间”①。但是审美“气氛”的存在、制造审美“气氛”的实践显然并非始自格诺特•波默,而是由来已久,源远流长。如果说中国古典文化中不乏关于审美气韵、基调、气氛、神韵创造的范例,那么,在当代少数民族文学艺术中,“气氛”审美同样大量存在。因此,借鉴格诺特•波默的“气氛美学”,并整合古往今来与之相关的各种理论资源,对梅卓的藏地书写进行探究,当是可行的。
纵观梅卓的藏地书写,不难发现其中不乏诗性气氛、神性气氛、沧桑气氛、边地气氛、寓言式气氛、女性性情四溢的“伊甸园”气氛、生态气氛、家族气氛与亲情气氛的营构。在梅卓创造的艺术化境中,这些气氛不是单一、孤立存在的,并非泾渭分明、相互区隔的并列式呈现。相反,多种气氛盘根错节,缠搅在一起,它们互相生发,互相渗透,互相作用,形成一种境界层深的“星云”格局。从中,我们可体察到以梅卓为代表的青海藏族作家藏地书写的独特韵味。
从1987年开始创作以来,梅卓在多个领域勤奋耕耘,在长篇小说、中篇小说、散文、诗歌等多方面不断结出硕果,已出版了《太阳部落》《月亮营地》《藏地秘史》等长篇小说,《佛子》《青稞地》等中篇小说,《梅卓散文诗选》《土伯特香草》等诗集,《藏地芬芳》《吉祥玉树》《走马安多》等散文集。作为一个接受过系统高等教育、长期在城市生活、有现代意识的视野开阔的作家,梅卓在她的创作实践中不可能一味沉潜在故乡的历史往事中,不可能仅仅专注于藏地乡野人生。作为一个处于汉藏文化交界点的藏族作家,梅卓又不可能不对藏民族的历史、未来与文化传统进行深沉的反思和热切的瞻望。作为一名女性作家,梅卓更不会缺少丰盈的女性生命体验,对情恋、人物心灵悸动的细腻入微的体察和摹写。在众多作品中,梅卓着眼于藏地的一草一木,潜心于藏地的日常人生,细腻而敏感地体察日常人生中的悲欢离合。或钩沉吊古、文化寻根、追思历史、思古忧今,批判性地审视如漫漫岁月飘落下来的层层尘埃般绵延不尽的民族传统文化;或针砭当代人对自然生态的破坏、现代文明的负面效应,对城市化进程中藏民族文化传统的失落进行反思自省……这客观上使民族历史记忆、女性个体情思、现代性批判话语、藏地神幻叙事在梅卓的作品中交错叠合,难以分割。而女性作家的独特体验、审美偏好和倾注整个生命灵肉浑合地进行创作的天然倾向更使她在创作中自然地把眼、耳、鼻、舌、身、意融为一体,沉浸在女性特有的富有血肉感的写作中,这也势必使她的作品中洋溢的“气氛”审美呈现出多元一体的浑然状态。
一
进入梅卓的文学世界,我们马上就会感受到无处不在的诗性气氛。
藏族是一个长于歌舞,有着悠久诗乐舞传统的民族。藏歌藏舞使雪域高原跃动着诗意的旋律,寺院的讲经说法也有着诗的清灵悦耳,既教化众生,又怡人情性。“格萨尔艺人带着世界上最长的史诗吟诵在高远的山冈,曼陀铃琴手弹着世界上最美的情歌吟唱在低回的河谷,他们代表着藏族的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中的民间精华。”②青藏高原也本是一片充盈着诗意的大地。梅卓曾说她出生并成长的草原群山、万里长云蓝天、青翠苍茫草原、红墙金顶寺院群落、曲径通幽静修之地正是她文学创作的灵感之源。在气氛美学家格诺特·波默看来,“美学研究的是周遭世界的各种质与我们的处境感受之间的关联”,“当我进入某个空间,我就以某种方式被这个空间所规定了。此空间所带有的气氛对我的处境感受来说是决定性的。可以说,只有当我处在气氛中,我才能知觉和识别这个或那个对象”③。诗意的藏乡、诗乐舞传统悠久的藏文化熏陶势必使梅卓浸染于这种诗意的气氛,女性作家长于抒情的天性更使她倾向于以诗心观照万物。在她的作品中,这种诗意的气氛俯拾即是。
置身诗意的气氛,梅卓的“处境感受”也充盈着诗情画意。她眼中所见、笔下所绘,尽皆化境。
雪山、草原、静静流淌的河流,牦牛、羊群、静静飘散的炊烟,是初入理塘的最好写照。
——《走马安多》④
山上白雪皑皑,冰川满布,山下是浓郁的森林,八座白塔面向喀瓦嘎博依次而立,白色的煨桑台里桑烟缭绕,五彩的经幡在风中飘扬,这是人间圣境,是一幅绝美的画卷。
——《藏地芬芳》⑤
午后的阳光倾泻在湖水中,反射出星星点点的光斑,那么耀眼,水色在阳光下变幻莫测,一会儿青绿、一会儿深蓝,岸畔茂密的冬草也变成了金色,天空依然那么蓝,远远飘着几朵白云,仿佛远道而来的问候,北岸的冈仁波切雪峰,南岸的那木那尼雪峰,在碧绿幽蓝的湖面投射下高贵的身影,这是怎样一幅瑰丽的画面,难怪她是藏区神圣的湖泊之一。
——《走马安多》⑥
“气氛”使得“材料”不再是纯然的物理存在,而是充盈着情感,获得了灵性和生气,如行云流水,涌动着生命的活力。语言材料由此不再以二维平面形式存在,语象由此获得了兰色姆所谓的“构架”和“肌质”,成就了一种鲜活的气氛。梅卓的散文如此,小说亦如此。梅卓的小说中也不乏温馨柔婉、感性诗意的抒情气氛。难怪一些学者甚至认定“抒情”是梅卓文学创作的核心,说她以其大气、感性和诗情感应着世间万物的抒情性。梅卓的小说善于融汇眼、耳、鼻、舌、身、意多种感官,营造一种浑合的抒情气氛。在《神授•魔岭记》中,抒情性的文字与视觉、听觉、嗅觉、触觉、感受贯通,与情思意绪息息相通,通感效应明显。“远方连绵的雪山上一层薄薄的雾霭正在舒缓的散开,深蓝色的天空渐次明朗”等视觉化抒情语句总是与意绪深度化合,相互生发;“山是活的,风吹过来,山就开始奔跑;水也是活的,风吹过来,水也开始奔跑;山水之间的白唇鹿在奔跑,大树也活了……”视、听、触、嗅、意也常常融会贯通,形成一种诗意的气氛。“喇嘛的金刚铃声一响,犹如微风掠过长天,大地一片清凉”,听觉、触觉、意绪交融;“白海螺的音质呈现出纯粹的美,那是久远的声音,仿佛很久以来就铭刻在心灵当中,那是熟悉而又陌生的大海的回响。多少个清晨醒来,听到远方的天籁之音,与白海螺的声音相叠相印,成为生命里的一部分,这重要的一部分,从父辈接来,再传给子孙”,听觉、意绪交融;“阿旺罗罗在晨光中舒展着呼吸,这种混合着青草和露珠香味的气息和他十三年来呼吸的一样充满了宁静和甘美,使他倍觉安全”,嗅觉、意绪交融。⑦在此,“通感特征并非物的属性,而是能通过各种各样的感官特质制造出来的气氛之特征”⑧。
小说集《麝香之爱》同样不乏诗情画意,麝香气息渗透在男女情爱世界中,凄婉而艳烈。其中的《转眼就是夏天》更有着浓郁的散文诗格调,呓语般的叙事风格,将男女爱情演绎得回肠荡气。
二
在梅卓的作品中,神性气氛也无处不在。和其他藏族作家一样,梅卓的作品中同样氤氲着浓郁的神性气息。梅卓说:“安多,是众神居住的地方。人们崇敬、畏惧、信仰,为娱神而谱写诗篇,传扬神话。”⑨青海的藏族自治地方,神性气氛无处不在。迎风飘的各色经幡,独具特色的藏家庄廓,认定转世活佛灵童的仪式,桑烟缭绕的丧葬仪式,身着奇特服饰、法力神奇的民间巫师,磕长头,转山转经,口耳相传、代代吟唱的神话和英雄史诗……总是让我们恍如嗅到了菩提的气息,沐浴着西天佛地的神奇气韵。这里是一个神灵到处栖息的世界,是一个人与神灵朝夕共处的所在。“神与人同在这一片蓝天白云之下,互以慰籍,互以生存”⑩,这种西天佛地独有的神奇灵动的神性气氛深深浸染着梅卓的作品。梅卓的散文,寥寥数笔,就能激扬起这种藏地特有的神性气氛,“到理塘的时候,天上飘下瑞雪,正是吉祥时刻。理塘县城所在地为高城镇,飞雪中,看到高挂着的路牌:欢迎来到世界高城……雪山环绕中的理塘,一派银装素裹,清洁静雅,理塘河纵贯全境,为这片开阔的高原山地带来了灵气。”⑪
在她的小说世界中,同样随处可见洋溢着神秘气息的山光水色、充满灵性的意象、神异的人物际遇、三生三世缠绵悱恻的因缘轮回。这种神性气氛使她的个人文学言说与更为久远的藏民族文化记忆、藏地神幻叙事传统紧密地联结在了一起。即使是世俗人生的日常图景描摹,也总是笼罩着神秘的祥瑞气息,隐喻着佛教的灵动启示,写实笔法与神幻叙事难以断然分割。梅卓同样擅长综合运用视、听、触、嗅、意多种感知去营造神性的气氛。在《神授•魔岭记》中,当阿旺罗罗抱着靴子光脚走出帐篷时,他不仅看见了远方连绵的雪山、氤氲的雾霭,还恍然目睹山水之间的白唇鹿在奔跑。喇嘛的金刚铃声如微风掠过长天,使大地一片清凉。远方的天籁之音与白海螺发出的久远的声音一齐融入生命深处,唤起亘古绵延的民族集体记忆。在此,情绪的场景化、嗅听触感知的视觉化呈现使读者情不自禁以神性的心灵体察大千世界,感应天地幽微,使自然的、人文的、感觉的、意绪的、神幻的各种意蕴在梅卓的作品中熔于一炉。⑫
三
女性与男性的心性差异客观上使女性文学在男性主导的文学传统中始终独树一帜,为文学史带来一股清新的风。在工具理性、消费主义甚嚣尘上的现代社会中,女性的感性化、直觉化的心性,重情感生活和人际交流的生活取向,柔和温婉的处事方式,更成了刚性的男性社会的软化剂、润滑剂。相比于男性作家,女性作家对爱情书写情有独钟,爱情书写俨然是女性作家生命存在和达成的重要方式。“与男性大师们注重寻求社会、民族的理想——政治社会的乌托邦恰成映照,女性寻求的是爱——情感的乌托邦。”⑬
如同其他女性作家,梅卓也对女性情感纠葛情有独钟。但梅卓书写的是有着雪的质地和山的性格,因“双重生产的强度过早地透支了身体”⑭的藏族女人的婚姻爱情、人生命运,这使她彩绘的女性性情四溢的“伊甸园”气氛有着独有的色质。
和内地作家笔下含蓄、平和、理性的人物不同,梅卓笔下的男男女女性情率真、粗犷,热情似火,敢爱敢恨,有着野泼的情性、野性的生命活力、旺盛的情欲、坚毅隐忍的性格。《太阳部落》中的桑丹卓玛就是典型代表。桑丹卓玛是太阳部落的英雄嘉措的妻子,在身负家仇的嘉措被迫远走他乡之际,她与洛桑达吉坠入爱河不能自拔,并生下了女儿阿琼萨。然而洛桑达吉还是离开了桑旦卓玛,贫困而孤寂的桑旦卓玛遭受着世人的鄙夷,独自抚养着两个缺乏父爱的女儿,坚强隐忍地艰难度日。
梅卓营构的女性的乌托邦、伊甸园在很大程度上其实是一种反乌托邦、反伊甸园。爱情在她的笔下表现得更为幽怨凄婉,盘根错节,令人欲罢不能。在《太阳部落》《月亮营地》《麝香之爱》等作品中,梅卓塑造了耶喜、桑丹卓玛、香萨、雪玛、尼罗、茜达、阿•吉、阿•玛姜、吉美等众多女性形象。她们的爱情都带有悲剧色彩。在梅卓笔下,爱情就像青藏高原上的牧歌一样百转千回,灵动而缠绵,美丽而惨烈,炽烈又隐秘,直露又幽婉。
在《月亮营地》中,甲桑的母亲尼罗曾是一个亭亭玉立的少女,她与阿•格班倾心相爱,然而,命运作祟,在权势与财富的诱惑下,阿•格班最终还是抛弃了尼罗,入赘阿家而成为月亮营地炙手可热的权贵,尼罗只能郁郁而终。在《麝香》中,吉美同样是一个痴迷于爱情梦幻的无望的守望者。“吉美就在这间一张床、一张小桌、一条躺椅的小屋中这样度过最美丽的青春时光。这是什么时候开始的?为什么?吉美曾不止一次问过自己,她是清楚的,她这样打发时间,只是为了某一天迎接她等待着的甘多。”⑮而短篇小说《出家人》里转世轮回中的两度爱情悲剧尤其令人扼腕叹息,在这篇小说中,男孩曲桑与女孩洛洛前世青梅竹马,然而终因曲桑父母将曲桑送去出家,有情人未成眷属。洛洛在分别之际将木质念珠作为信物赠给曲桑,约定来世再会。然而来世两人再度无缘牵手:城市姑娘曲桑与偶遇的草原男子洛洛一见钟情,分别后,曲桑写信给洛洛,附上念珠,然而信件却因邮递员的失误而永远无法寄到洛洛手中。
小说集《麝香之爱》中,梅卓在书写她的爱之悲歌的同时,也表达出她的爱之反思。《秘密花蔓》中的卓玛不乏才华和热情,但是唐卡画家父亲还是坚持传男不传女,把唐卡技艺传给了女婿而不是女儿,然而丈夫洛桑不务正业,无心作画,承受着生活重担的卓玛只能在丈夫不归之夜默默面对着巨幅唐卡。小说《魔咒》中的达娃卓玛更显示出梅卓对爱情和人生的新的思考和展望。这个像“达娃”(月亮)一样的女孩在追逐寻找真爱失败后,坚定地走出了爱情的阴影,宽恕了伤害她的人,开始主宰自己的命运,形塑全新的自我。
梅卓立足雪域高原的日常人生,对爱情和人生进行了多元化书写,展现了独特地域的独特情恋景观。她对女性欲望、情感生活的复杂性、扭曲性给予了尊重与宽容,对人性的复杂性、恶人心中一闪的善念、浪子回头的悔悟、背叛者临终的忏悔、失足者晚年的悔恨,都沉静而善意地进行了充分展现。
四
梅卓有着自觉的生态意识,这在她的诗文小说中均有表现。在《诗与自然的距离》中,梅卓区分了两类诗人:文字诗人和行动诗人,她更推崇的无疑是行动诗人,“行动诗人往往更贴近自然。或许他们的标志就是与大自然融为了一体”,而这种离星空最近的行动诗人得益于“大自然赋予藏族人的信仰模式”,“对藏人来说,大自然是所有生物的母体,它的每一种创造都有其因果关系,从大到人类、小到蚁类,所有生物的生命价值对母亲而言是完全一样的,母亲从不以你强而赋予你更多,也从不以你弱而赋予你更少,生命等值、生命等价的观念已深入人心。因此,藏人的自然观中,有一个世界独有的生命体系,每座山峰和每片湖泊都是人格化的神灵。”⑯这种藏地信仰恰恰就是素朴的生态意识。在长篇小说《神授•魔岭记》中,在充满神幻色彩的格萨尔史诗的外衣下,美丽祥和的生态气氛随处可见。美丽的草原牧场、东查仓部落的人神共欢有赖于雄狮大王格萨尔的护佑,格萨尔返回天界时,赋予了神授艺人传唱格萨尔史诗以压制妖魔鬼怪、保护苍生乐土的使命。在作品中,当格萨尔神授艺人们到处传唱时,草木丰茂,飞禽走兽生机勃勃,当神授艺人们中断了歌唱时,山川失色,魔性张扬。小说借扎拉之口表达了对“末法时代”的忧思,少年阿旺罗罗正是在这种情势下担负起了保护生命和家园的神圣使命。⑰
优美和谐的自然生态总是令梅卓心向往之,当她写到雪山、蓝天、草场、田野时,自然的山光水色在她的笔下总是熠熠生辉,赏心悦目。
“这是一座壮丽的雪山,山下青松连绵,杨树已变成秋天的金黄,有红色的灌木丛,在残雪中显现各种色彩,蓝天蓝得那么醉人,就像女儿的脸庞,那么洁净,那么令人沉醉。”
行文至此,我们也不禁沉浸在梅里雪山这澄净明澈的气氛中。然而接着,梅卓笔锋陡转,
“很快却看到有很大很大一片林子被伐光,残根令人触目惊心地裸露着,整整一片山冈”。⑱
自然生态惨遭破坏的景象就像是给壮丽的梅里雪山划了一道伤口,也在人的心中烙下一块伤疤。
梅卓除了关注藏地自然生态的破坏和环境恶化,也高度关注精神生态的问题。小说集《麝香之爱》表现了梅卓对民族信仰、现代藏族青年精神生态的忧思。它所展现的灯红酒绿的现代都市气氛与我们印象中的传统藏族聚居地大相径庭。小说里的藏族青年一代已远离了他们祖辈生长的草原,远离了骏马和藏袍,走进了钢筋水泥的现代都市,摇身一变,做起了工人、导游、作家、编辑,过着典型的城市生活,和内地青年已无多大区别。甚至大量的藏地城镇也为现代都市化的潮流所裹挟,藏式酒吧、藏式KTV如雨后春笋般次第涌现,藏式饭店林立,居民衣着时尚。在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中,古老的藏族民俗风情渐行渐远,传统的生活方式、精神信仰在一点点地流失、消解。
本雅明说人“呼吸灵气”,格诺特•波默在评析本雅明这一观点时也强调“人身体性地吸纳灵气”,“人让这种气氛贯穿着自己”。⑲在长篇小说《神授•魔岭记》中,“整理好藏装腰带的阿旺罗罗在晨光中舒展着呼吸,这种混合着青草和露珠香味的气息和他十三年来呼吸的一样,充满了宁静和甘美,使他倍觉安全”⑳。宁静优美的生态气氛直接影响和塑造了少年阿旺罗罗的精神状态,也显示了生态气氛对于精神生活、人类文明的重要性。
五
梅卓的文学世界里也不乏寓言式的气氛。在她的小说世界里不乏人神、人魔、人兽、人与自然同构的寓言,亦不乏卡夫卡式的现代人生寓言。信仰、追求,都市人的生存状态,情感与精神的异化,人性与文明的异化,都一一得到反思和呈现。这种寓言书写有着卡森•麦卡勒斯式的“表达性写作”的意味,它直面创伤,书写创伤,也在某种意义上成为走出创伤的通道。蛇钻香囊、飞蛾扑火式的女性爱情寓言在梅卓笔下既是藏族女性的宿命,也俨然是人类历史上女性的宿命。由此,梅卓的爱情书写、女性书写获得了超越时空的寓言意蕴。梅卓的长篇小说《太阳部落》《月亮营地》《神授•魔岭记》有着悲凉深沉的历史反思,别有一种历史沧桑感,沧桑气氛在她的小说中比比皆是。雪域高原、雪域文化是梅卓和她的藏地书写植根的沃土,梅卓的作品散发出浓郁的青海藏族气息。藏族长期以来聚族而居,家族血缘纽带在人际交往、人物命运归宿、情感纠葛与婚姻生活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也使得梅卓作品中家族气氛与亲情气氛挥之不去,女性特有的母性也使梅卓更倾向于关注和展现家族亲情。限于篇幅,这些气氛,不再一一赘述。
注释:
①格诺特•波默:《气氛美学》,贾红雨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64页。
②梅卓:《诗与自然的距离》,《民族文学》2007年第11期。
③格诺特•波默:《气氛美学》,贾红雨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4页。
④梅卓:《走马安多》,青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3页。
⑤梅卓:《藏地芬芳》,青岛出版社2006年版,第102-103页。
⑥梅卓:《走马安多》,青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40页。
⑦参看杨霞:《集体记忆与个人话语的诗性书写——评梅卓长篇小说〈神授•魔岭记〉》,《青海湖》2020年 第10期。
⑧格诺特•波默:《气氛美学》,贾红雨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64页。
⑨梅卓:《走马安多》,青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9页。
⑩梅卓:《走马安多》,青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9页。
⑪梅卓:《理塘:洁白的仙鹤永在飞翔》,《福建文学》,2006年第3期。
⑫参看杨霞:《集体记忆与个人话语的诗性书写——评梅卓长篇小说〈神授•魔岭记〉》,《青海湖》2020年 第10期。
⑬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0页。
⑭梅卓:《走马安多》,青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12页。
⑮梅卓:《麝香之爱》,西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页。
⑯梅卓:《诗与自然的距离》,《民族文学》2007年第11期。
⑰梅卓:《神授•魔岭记(节选)》,《青海湖》2020年第10期。
⑱梅卓:《走马安多》,青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3页。
⑲格诺特•波默:《气氛美学》,贾红雨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6页。
⑳梅卓:《神授•魔岭记(节选)》,《青海湖》2020年第10期。
原刊于《阿来研究》第15辑

何志钧,文学博士,南昌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同行评议专家、山东省智库高端人才、山东省首批签约文艺评论家。在《文学评论》《人民日报》等报刊发表学术论文、评论200余篇,发表论文30余次被人大复印资料等出版物转载。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等出版专著3部,主编、副主编、参编著作7部。已主持结项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数字化语境中新世纪以来的文艺审美实践研究”1项、中国博士后基金项目和省社科规划项目等6项。主持在研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数字美学理论话语建构研究”1项、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点项目“网络文艺发展研究”子课题1项。

梅卓,女,藏族。一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青海省作家协会主席,《青海湖》文学月刊主编,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青海省优秀专家。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太阳部落》《月亮营地》,诗集《梅卓散文诗选》,小说集《人在高处》《麝香之爱》,散文集《藏地芬芳》《吉祥玉树》《走马安多》《乘愿而来》等,作品入选多种选集。曾获全国百千万人才工程奖、全国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拔尖人才、全国第五届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全国第十届庄重文文学奖、中国作家百丽小说奖、青海省首届青年文学奖、第四、五、六届省政府文学作品优秀奖、青海省四个一批拔尖人才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