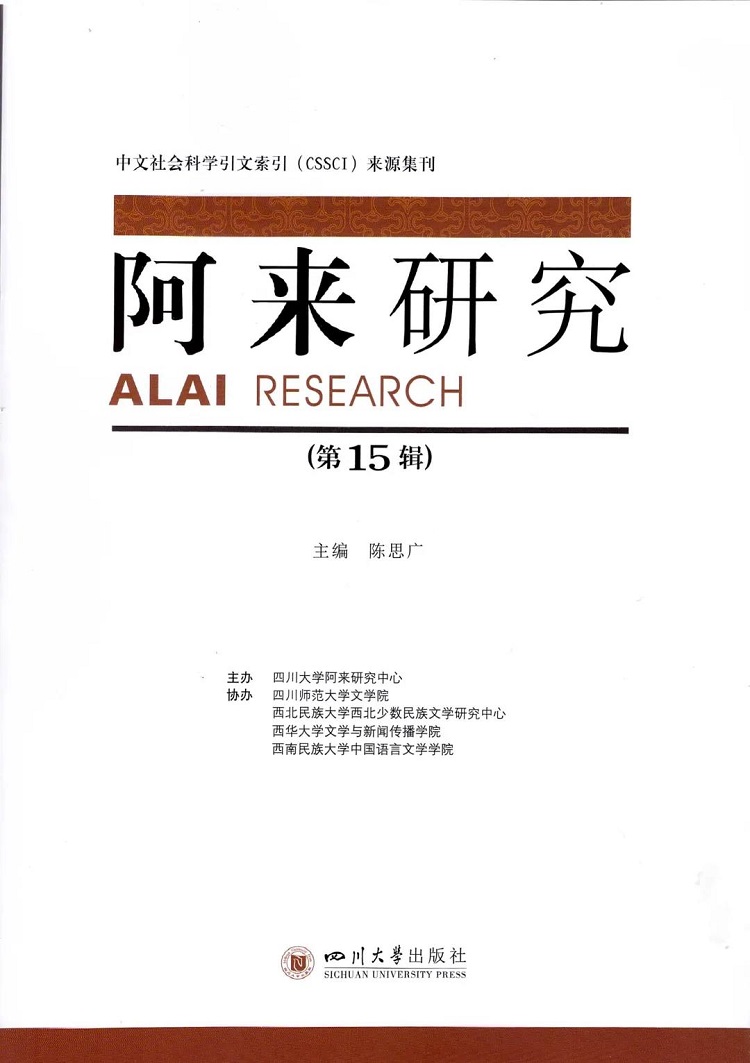
2020年2月,北京师范大学的张莉率先提出了“新女性写作”的概念,并与北京大学的贺桂梅对“当代女性写作”作品与理论进行了重新梳理,由此引发了“新女性写作专辑”的推出和学界对“新女性写作”现象的相关讨论。张莉指出,“新女性写作”是与“私人化写作”“身体写作”“中产阶级写作”等有着重要区别的概念:
“新女性写作”强调写作者的社会性别,它将女人和女性放置于社会关系中去观照和理解而非抽离和提纯。它看重在日常生活中发现隐秘的性别关系,它认识到,两性之间的性别立场差异其实取决于民族、阶层、经济和文化差异,同时,它也关注同一性别因阶级/阶层及国族身份不同而导致的立场/利益差异。“新女性写作”强调写作的日常性、艺术性和先锋气质,而远离表演性、控诉式以及受害者思维;“新女性写作”看重女性及性别问题的复杂性,它应该对两性关系、男人与女人以及性别意识有深刻认知。这是一种理想意义上的女性写作——真正的女性写作是丰富的、丰饶的而非单一与单调的,它有如四通八达的神经,既连接女人与男人、女人与女人,也连接人与现实、人与大自然。①
“新女性写作”的提出可以看成是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女性主义理论思潮之后一次本土化的探索,它是立足于新时代中国性别话语的现实探讨与理论建构。
几乎与张莉她们提出“新女性写作”的时间相去不远,藏族女作家梅卓在2019年9月完成了《神授•魔岭记》的创作,在新作中,她再次站在藏民族的文化立场之上,对传唱千年的格萨尔史诗进行女性特有的解读与审视,在书写着藏民族共同记忆的同时,用当代文学的形式再现了神话与现实的交融。梅卓的新作将目光投向民族文化的历史讲述,超越了时空界限,打破了现实主义的束缚,更加有力地回应着张莉等人提出的“新女性写作”。从《太阳石》到《神授•魔岭记》,梅卓的小说创作不沉迷于个体的呐喊或身体的迷醉,而是始终坚持将女性放置在民族文化与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去加以关注,把性别问题的讨论同民族精神的承续关联。新作中,她更是转向对史诗中的女性个体命运、情感纠葛的再认识,延续着她把对本民族口头文化的理解置于书写文化中的尝试,体现了日常性与艺术性的结合,为我们提供了新女性写作的另一种可能。
1、回到历史中去
纵观藏族历史,在传统藏族社会中,书写的掌握、运用与传播,更多集中在上层贵族和寺院僧侣手中,这一现象直到新中国成立,西藏和平解放后才得以改变。这也意味着以梅卓为代表的一批藏族女作家们在开始自己的文学创作活动之前,除了口头传统中“听到”的内容之外,几乎是无法“看到”女性自己书写的历史的。因此,如何挖掘潜藏在藏民族书写历史背后的女性,赋予她们以大写的“人”的权利,还原女性真实面貌,成为藏族女作家们共同思考的问题。
梅卓的小说创作向来对男女两性给予同样的关注,既不因为藏族传统社会中男性的家长地位而忽视女性的存在,也不因为女性在社会生活、宗教活动等领域的边缘地位而指责男性,这与20世纪90年代以陈染、林白为代表的“私人化写作”和后来以卫慧、棉棉为代表的“身体写作”渴望建立女性自己的精神和肉体世界,颠覆传统社会中男权话语的统治有着明显的不同。梅卓似乎更深谙中庸之道,以女性价值在民族历史书写中的讨论,来化解民族文化前进发展中可能遇到的难题,这可以视作她女性写作的策略之一。那么如何确立这种女性价值?梅卓首先想到的是要回到民族历史的现场。
梅卓对传统的历史叙事方式进行解构,积极吸收藏族文化中的精华,开辟出当代藏族女性历史书写的特殊路径,在用女性视角全面展现历史的基础上对民族历史进行重建。有学者指出,“表现民族历史文化题材的......小说也具有改革的意识流向,但它与改革题材小说不同的是前者贯注着创作者民族意识的强化。作家从现代意识的高度对本民族历史现状予以重新审视,加深对本民族自身形象的思考,表现出一种庄严的民族责任感”②。早在《太阳石》《月亮营地》中,梅卓就尝试通过部落纷争史的讲述,来开辟女性书写民族历史的可能,无论是前者关涉的伊扎部落和沃赛部落间的矛盾与冲突,还是后者所营造的月亮营地里发生的故事,着力关注的正是民族历史发展进程中部落文化的特征,以及女性在其中的地位和个性展现。不同于阿来在《尘埃落定》中以土司家的傻子二少爷为核心讲述家族/部落史,其他人物的设置都是为了衬托这位男性的“假傻”与“真智”,一方面,梅卓塑造代表着族群希望的索白千户、甲桑、云丹嘉措等男性,他们一步步成为部落守护者、捍卫者;另一方面,桑丹卓玛、茜达甚至尕金这些女性形象都有着鲜活的特征,她们绝不是作为男性的附属而存在,尤其当文本中男性缺席时,这些女性能够主宰文本,影响着部落历史文化的进程。像在《太阳石》中,部落最后的希望落在了英雄嘉措身上,然而能够引领族人找到嘉措的“钥匙”却是他的女儿阿琼,换句话说,没有阿琼这位女性的出现,整个部落历史将难以续写。这里,女儿与父亲的关系是潜在的,作家巧妙地通过将父亲设置为不在场,凸显女儿的作用,这就打破了女性遵从父权话语体系的陈规,强调了女性在历史中的重要性。梅卓想呼吁的正是,藏族女性在历史进程中的价值是有待浮出历史地表的。她也主动为笔下的女性代言——无论是对感情坚持自我选择的桑丹卓玛、茜达,对家庭、部落充满责任感的阿•吉,对爱情坚守执着的尼罗,抑或是其他女性,都被梅卓塑造成“内心坚忍顽强,敢于爱己所爱”的女性。女作家不仅重构了藏族历史发展中女性存在的价值,展现她们面对情感、责任时的态度,而且通过塑造不同性格的藏族女性,揭示出她们的精神特质。梅卓的创作摆脱了民族/国家叙事模式的影响,建构起部落—性别叙事框架,以自己成长的安多地区为背景,将女性命运同部落历史发展紧密关联。
在新作《神授•魔岭记》中,梅卓在部落历史书写模式的基础上,以东查仓部落为现实讲述的落脚点,对代表着民族历史的格萨尔史诗进行了大胆创编尝试。史诗本身是用诗歌体裁记录重大历史事件或英雄传说的长篇叙事作品,格萨尔史诗作为古代藏族社会历史百科全书式的记录,虽然不像《红史》《西藏王统记》《西藏王臣记》《安多政教史》等历史文献那样客观真实地展现朝代更迭、历史事件、人物事迹等,却通过格萨尔王这样一个民族英雄南征北战、降妖除魔的亦真亦幻的事迹,利用散韵结合的方式,再现了岭国始归一统的历史。梅卓在延续着史诗故事讲述该有的模式的同时,以史诗中魔岭大战的情节为小说的内在线索,围绕格萨尔王、王妃珠姆、魔王路赞、魔王之妹阿达拉姆之间的纠葛展开,此外,她还独辟蹊径地设置了一个外在线索,落在东查仓部落13岁的神授艺人阿旺罗罗身上,让他站在当下时空来讲述格萨尔故事,借此,梅卓将民族史诗与魔幻现实有机结合。在这部作品中,梅卓没有过多去塑造现实的女性主人公,而是以格萨尔史诗中出现的几位重要女性为对象,还原她们在史诗中的应有地位和作为女性的情感需求。比如描述格萨尔王出征魔国之前,森姜珠姆王妃依依不舍,梅卓不惜笔墨去描述王妃“泪水婆娑”“悲泣”之状,甚至当格萨尔狠心扬鞭出发时,珠姆依旧拖着马缰,直到自己被拖倒在地。一边是格萨尔接旨降妖除魔,珠姆无奈,必须和大王一样摒弃个人的“小家”;一边是作为伴侣的女性当丈夫离开后的无依与牵挂。因此珠姆发愿:“曾经发誓不相离,现在活活抛下我,格西转告三句话,该做事情我已做,该跑路程我跑完,今生情缘已完结,来生空行中相见。”③这种复杂、微妙的情感被梅卓捕捉,并投递到了文本中,梅卓借格萨尔故事的讲述者阿旺罗罗表达对这位王妃的怜悯,同时,也表达对王妃顾全大局的由衷钦佩。同样的还有魔王路赞的妹妹阿达拉姆,在梅卓笔下,依照史诗原样呈现了格萨尔王降服阿达拉姆的情节,其中对阿达拉姆的聪慧、勇敢不乏描写。得知王兄要抢夺梅萨时,阿达拉姆就看出孰对孰错:“生在魔地会堕地狱,可怜我不知今后路,若遇雄狮王大丈夫,要离苦得乐走正道……”④另外,梅卓也别出心裁地借用侧面描写的手法来烘托阿达拉姆的美,如同古希腊人眼中的海伦一样,在三头羊的眼中,阿达拉姆就是“海伦”:“我默默地记住了她的名字,这世上最好听的名字,双唇微启,叹息一般地呼出,然后舌尖轻轻弹向上颚,卷起的舌尖舒展开来,让气息从两侧穿出,最后将充满敬意的上下唇温柔地合拢,她的名字的发音就完美地呈现了出来——阿达拉姆!”⑤单单一个名字,作家就用了如此大段的描述,可见阿达拉姆是一位多么美妙的人儿。而且,在阿旺罗罗眼中,阿达拉姆归顺格萨尔王,助其统一,是当之无愧的女英雄,这则带有作家明显的褒扬立场。《神授•魔岭记》可以视为是梅卓挑战民族史诗当代书写的尝试,而其中她对女性内心活动的探索、情感特征的呈现,正是她渴望将史诗女性更多还原为真实女人的努力。
2、在民族文化中求索
在当代藏族女作家中,梅卓一直秉持着自己独特的气质与特征。早在1987年她就开始发表作品,率先涉足诗歌领域,尤擅散文诗创作。贵州人民出版社曾出版过一本《梅卓散文诗选》,扉页上写道:“梅卓女士散文诗的结集出版,将使更多的人在单调重复的生活里忽然听到来自雪域高原充满人性和人情的呼唤。”⑥足可见其创作的立足点和出发点。早期的梅卓,创作还略显青涩,“雪域”“寺庙”等是她自我确证的标识,“虔敬”“温柔”是她情感的归宿。从1995年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太阳石》问世,到后来的《月亮营地》,再到2019年的《神授•魔岭记》,以及中篇小说《佛子》《魔咒》,短篇小说《麝香之爱》《出家人》等不同篇幅的作品,梅卓在小说创作领域很快打上了自己的烙印,对民族文化的坚守成为她创作的持久动力和源泉。
对于梅卓的民族身份而言,在开始文学创作之初,她拥有的最大财富无疑是民族口头文化传统中的宝贵遗产。梅卓曾提到过,她的父母很早就离开了家乡的草原牧区而外出工作,所以她的成长历程中唯一能够建立起与带有神秘色彩的家乡的联系的,就是口头传承,通过家中长辈讲述藏族史诗、神话、谚语等,她习得了滋养她文学创作的宝贵知识。梅卓的童年和少年时期其实都是在汉文化圈中度过的,在海北藏族自治州的首府,她接受了各种汉语方言的熏陶,这直接导致了她在以后的创作中有了以汉语书写为主的自觉。当然,在同时具备文化素材和语言工具之后,梅卓的文学创作还需要一个契机——和母亲回到伊扎草原。这片土地带给梅卓的认识与情感上的冲击,恰恰与潜藏在一个少数民族女性心中的创作欲望相碰撞,梅卓从那时起就暗下决心,要把对这片土地的感情诉诸文字。就像米兰•昆德拉在被问及为何他的小说故事全部发生在捷克斯洛伐克的时候,他总结道:“发现生命的前半部分对我们多么根深蒂固,这是非常有趣的。我们注定扎根于生命的前半部分,即使生命的后半部分充满强烈而动人的经历。”⑦民族文化带来的认同感与自豪感,给予了梅卓写作的动力,她则利用自己的女性身份以及口头文化滋养的独特情感体验,在文本内外开辟出藏族女性写作的新气象。
梅卓的作品,无论是现实还是历史题材,都极富藏文化的魅力,努力寻找并再现民族文化精神成为她创作持之以恒的内在动力。后殖民主义理论认为,一种文化一旦处于边缘,便不可避免地将处于弱势地位,虽然这种文化或多或少保留了自己的话语权,但这种话语权往往成为被忽略乃至淹没的“少数人”的声音。梅卓正试图利用自己的作品,将民族文化的声音传递出来。正如有研究者指出,“梅卓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与热爱是从血脉中生长出来的,对它的呵护发自本能,充满无可辩驳、不可动摇的自豪感、自信心。也因此,她对本民族的文化积弊深恶痛绝,对民族的衰落痛心疾首,总是给予尖锐的批判针砭,长歌当哭地呼唤民族振兴”⑧。从第一部长篇小说《太阳石》开始,梅卓就立足藏地,以藏族文化为叙事背景,紧紧围绕藏族人民历史的或是当下的生活状况展开叙述,其藏族文化特征外在体现为四个方面。第一,作品中大部分出场人物都是藏族,无论从外貌特征、服装配饰还是性格习惯上来看都有着典型的藏族特征,如《魔咒》中安多女子达娃卓玛和她爱上的康巴汉子尼玛才让,各自身上具有所在藏地的鲜明特征,这说明作家在她的文本创作中给予笔下人物充分的关注,没有脱离本族的文化特征进行创作;他民族的人物形象往往作为配角出现,甚至有些是对立角色,以辅助完成文本叙述,如《唐卡》中的张教授,严总兵、马步芳等封建军阀。第二,文本的叙事空间几乎都在藏族聚居地区,或牧区或城市,即便一些具有现代意义的场所,如酒吧、歌厅,也都是藏族人开的,有浓郁的藏式风格,像“快乐酒馆”那样。所以,环境的渲染使梅卓的小说民族特征明显。第三,作品中如天葬台、风马旗、寺院、喇嘛等藏族文化的特殊标识非常明显,像《太阳石》中的太阳石戒指和木刻风马,《珊瑚在岁月里奔跑》中的红珊瑚,《出家人》中的木质念珠,《神授•魔岭记》中的魔戒、圆光镜等民族文化的信物更是在小说叙事中承担起贯穿全文的线索作用。第四,文本中的叙事语言充满藏式风格。梅卓虽然采用的是汉语写作,但她充分调动了藏语思维,将史诗故事、格言、谚语、藏戏等内容融入人物的语言中,丰富了作品的文化性,如《神授•魔岭记》借阿旺罗罗之口,大量再现了格萨尔史诗的演唱。上述要素体现了民族文化对梅卓的影响,使得她的创作具有了深深的民族烙印。
藏族传统社会所形成的诸多文化观念对女性有着重要影响,例如认为女性身上有某种不洁的东西,因而女性被限制参与佛事;在日常生活中,总是忙于烹饪饭菜的女性永远无法取代男人成为大厨师,因为男性是饮食洁净最基本的保证。在对待生育问题的态度上,藏族文化认为生育是女人的重要职责,不能生育的女人会受到歧视;然而即便是生育,因为藏族传统观念视生育为不洁净的事,所以也只能在草房或牛棚中完成,而且刚生产的女人第二天就要继续投入繁忙的劳动。在日常生活中,女性只能承担播种、施肥、收割、挤奶、打酥油、上山砍柴、炒青稞、磨糌粑等体力劳动,而永远无法承担技术性工作。⑨这些观念上的束缚使得身为女性的梅卓渴望塑造独立的藏族女人,超越民族文化中存在的性别偏见,还原女性成长、生活的内在心路历程。卢小飞等人在为西藏女性做口述实录时发现,“西藏女性中的大多数人是没有或者较少功利心的,眼花缭乱的世俗生活没有迷倒她们,官场的八股和名利场上的虚伪客套,没能演变她们,难得保留下西藏人文烙印下的那份纯真”⑩。面对世俗的纷争,梅卓发现藏族文化在爱情方面显得较少有束缚,因此她选择在小说中通过爱情主题来展现女性的地位。在梅卓看来,女性不仅需要爱情,而且看重爱情,因为爱情,女性才会心甘情愿成为她爱的那个人的妻子。典型如《太阳石》,作家以桑丹卓玛与嘉措、尕金与洛桑达吉、阿琼与嘎嘎等多对夫妻关系为着眼点,强调藏族女性对爱情的格外看重。桑丹卓玛面对常年离家的嘉措,尕金面对拥有情人的洛桑达吉,阿琼面对部落灭亡的头人嘎嘎,均仍然坚持维系着家庭,无怨无悔地承担起家务劳动,同时照看老人、抚养子女,尽到做妻子的义务。这并不是对男权中心文化的妥协,而是在藏族文化影响下女性对爱情责任的主动承担。同样,藏族文化中的女性对于爱情欲望的表达也是积极主动的。在还原女性最原始、最简单的爱欲时,作家没有掺杂过多的情色描写来博人眼球,而是尽可能客观展现,如写到长期独守家中的尕金面对丈夫归来时那种肉体的欲望。而在表现女性间对爱情的争夺保卫时,作家也直截了当,如尕金在得知桑丹卓玛是洛桑达吉的情人后,表露出作为妻子的本能的讽刺与嫉恨。同样鲜活的例子,在梅卓其他小说中也能找到,她这种立足民族文化立场的创作,摆脱了物化的人性,避免了男权中心对女性的刻板印象。她塑造出女性丰满的形象和血肉之躯,在个人情感表达的过程中,让她们勇敢诉说自己的需求和欲望,而非借助男性或通过男性的话语方式来言说,这是梅卓女性写作的另一策略。
3、作为女性的反思
在对藏族文化与历史关系的策略性建构之外,梅卓深入思考了本民族文化的多样性特征,从口头文化的继承、传播到文学书写的开展,她善于借助历史材料与民族口头文化内容相互佐证,大胆想象,用发自肺腑的热情书写对雪域高原上女性的礼赞,试图找寻民族文化中女性精神的宝贵品质并重建女性家园。《太阳石》中的桑丹卓玛、《月亮营地》中的茜达都是这种精神品质的代表。桑丹卓玛对索白千户的冷颜拒斥、对洛桑达吉的疯狂热恋、对丈夫嘉措的责任与义务,茜达敢爱敢恨地跟随外乡人云丹嘉措离开,这些无不是藏族女性自觉自主选择的结果,梅卓用女性的实际行动重塑了传统中总是默默无闻的女性形象。
正如美国黑人女作家托妮•莫里森对历史叙事的改写“不仅再现了被湮没的历史、难以表达的精神创伤,而且还重新铭刻了黑人的身体,重构了黑人历史记忆,为黑人建构自主、自信的主体精神清扫了阵地,体现了其身份认同策略和政治目的”⑪,梅卓通过她的小说创作,改写着女性在部落战争时期、解放时期以及当下社会中生存的面影,不仅还藏族女性以真实的身体和自主的意识,而且建立起关于女性表述的体系。她的作品在某种意义上消解了传统意识形态的父性霸权,重建起一种基于母性的、情绪化的文化理念。
针对民族发展现状,梅卓进一步做出了冷静反思。面对现代性的冲击,藏族知识女性不仅关注自身命运,更是对民族命运表现出独特的关怀。有学者指出:“而对这些现象,人们大都早已司空见惯,常是习焉不察麻木不仁。而文学女性在以性别视角观察和体验生活,以现代意识和女性立场烛照素材时,会以超出一般人的敏感,从现实的物质存在和精神存在中格外深切地感受到身为女性所受到的来自生活方方面面的压抑。”⑫物质和精神是现代人生活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对于藏族人来说,受传统文化和宗教文化的双重影响,他们具有重精神而轻物质的文化观念,因此,梅卓才会将文学写作看成一种“慈悲的事业”,以超越阶级、性别、文化等差异的关怀来观照藏族社会中的各类人群,疏离文化中心主义的同时,借助汉语书写来确立自己的文化身份,并努力实现话语转换,将处于相对边缘的文化带入主流文化圈。文化的融合与碰撞弥补了本民族文化不足的同时实现了超越,这体现为梅卓笔下关于精神的讨论以及面对物质世界时所做出的有效反应。因此,梅卓的小说创作不是单纯站在性别立场的颂扬,她基于民族历史、文化等综合因素考量,还原藏族女性的真实面貌,并通过民族性的考察、民族精神的凝练,反思当下文化发展的种种问题,这恰恰是新女性写作的题中应有之义。
注释:
①张莉主编:《美发生着变化》,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第5页。
②向云驹、尹虎彬:《历史嬉变中的自足与突奔——〈民族文学〉一九八五年小说述评》,《民族文学》1986 年第1期。
③ 梅卓:《神授•魔岭记》,青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177页。
④梅卓:《神授•魔岭记》,青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135页。
⑤梅卓:《神授•魔岭记》,青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301页。
⑥梅卓:《梅卓散文诗选》,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勒口。
⑦转引自孙妮:《V.S.奈保尔小说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98页。
⑧ 张懿红:《梅卓:民族立场与民族想象》,《青海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
⑨参见格央:《雪域的女儿》,西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27页。
⑩ 卢小飞主编:《西藏的女儿:60年60人口述实录》,中国藏学出版社2011年版,前言,第3页。
⑪ 唐红梅:《种族、性别与身份认同:美国黑人女作家艾丽丝•沃克、托尼•莫里森小说创作研究》,民族出版社2006年版,第191页。
⑫乔以钢:《中国当代女性文学的文化探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2页。
原刊于《阿来研究》第15辑

徐寅,文学博士,1986年生于安徽安庆,天津财经大学人文学院讲师。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会员、中国女性文学学会会员、天津作家协会会员。先后在《民族文学研究》《阿来研究》《青海社会科学》《西藏研究》《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西藏文学》等刊物发表文章二十余篇,参与编写《文苑撷英:新时代大学语文读本》等。博士论文《当代中国藏族女作家汉语写作研究》曾获中国妇女研究会第七届妇女/性别研究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二等奖。

梅卓,女,藏族。一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青海省作家协会主席,《青海湖》文学月刊主编,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青海省优秀专家。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太阳部落》《月亮营地》,诗集《梅卓散文诗选》,小说集《人在高处》《麝香之爱》,散文集《藏地芬芳》《吉祥玉树》《走马安多》《乘愿而来》等,作品入选多种选集。曾获全国百千万人才工程奖、全国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拔尖人才、全国第五届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全国第十届庄重文文学奖、中国作家百丽小说奖、青海省首届青年文学奖、第四、五、六届省政府文学作品优秀奖、青海省四个一批拔尖人才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