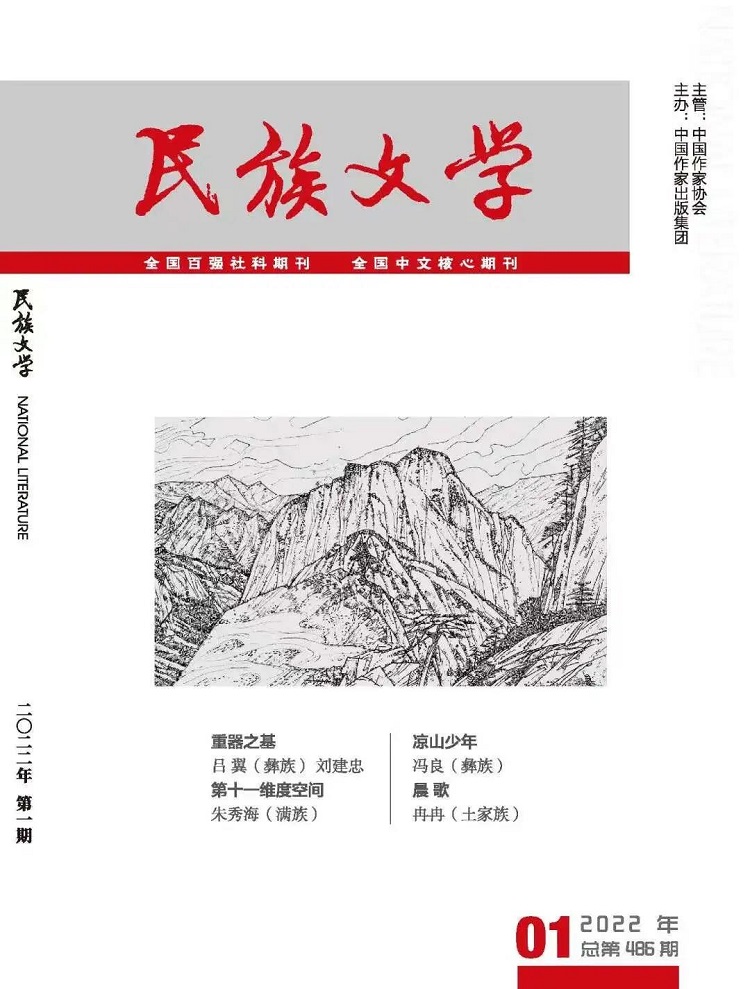
一、时代感与总体性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也是《民族文学》创刊40周年。四十春秋,《民族文学》的百花园竞艳争芬、繁枝硕果,值得隆重祝贺,“白手起家,京南一隅陶然亭。/安营扎寨,后海南沿大翔凤。/四十春秋,兄弟各族携手共风雨。/肝胆相照,文学园地齐心同耕种。”(查干《祝酒词》)
在新时代的背景下《民族文学》所刊发的少数民族诗歌展现出新的诗学气象、思想深度和精神流变,凸显了诗歌写作的时代感和总体性趋向。这印证了诗人(作家)既是社会公民又是语言公民,这涉及的不仅是现实正义和社会良知而且是诗性正义和语言的求真法则。
作为这方面的主题写作,舒洁(蒙古族)的组诗《山河大地上的信仰》(其中收录了《溯源:致敬马克思》)让我想到了他在2021年出版的一部8000多行的颂体长诗《卡尔·马克思》,“他的人格,他的诗歌,他的建构在人类之思中的缜密的理论,他代表一个庞大阶层所发出的宣言,无不说明他是一个立体的、杰出的、不朽的人。他对人类世界的影响和引领,在时间中就是丰碑与旗帜。在我的观念里,他是一个真实的男人,一个充满血性的英雄,一个深刻阐释了世界无产者内心声音的先哲。”(舒洁《我写〈卡尔·马克思〉》)整首长诗时时充溢着类似于蒙古“长调”的深沉之爱和哲性之思,更准确地说这是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高度的“精神导师传记”“信仰之诗”和“历史升阶书”。石才夫(壮族)的长诗《千秋百年》站在不无深刻而宏阔的“历史时间”的高度,展现出关于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在线性的重要时间节点和历史事件的交会处诗人也展现出较为深刻的历史总结能力。时代和现实总是由个体构成的,弦河(仡佬族)直接呈现个体的现实经验,当然这并不纯然是事实的直接折射而是精神透析的能动结果,“在滚动的湖水里/他在看鱼,我的父亲,他失明多年的右眼/现在终于坏死了/我看见一只白色眼球的父亲/他不是我的父亲了//他的腿最近瘸了/疼痛。但是他没有说,没有说”(《父亲在嵊泗的海对岸看鱼》)。巴音博罗(满族)的主题组诗《晨光中升起的炼钢厂》让我们关注工业题材诗歌的时代经验和美学经验深度融合的诗学命题和社会学命题。新世纪尤其是新时代以来,在新工业加速度发展的过程中涌现出了一大批的产业工人以及代表性的诗歌作品,而工人的社会境遇和工人诗歌的丰富性和崭新经验以及精神质素亟须从作品、评论、出版和传播的各个领域予以观照和总结。巴音博罗以“炼钢厂”为深度意象和中心场域,真切而深邃地反映了个体命运的激荡和整体时代境遇的变迁,从精神空间、时间维度和诗歌内部机制出发重新激活了语言和技艺,在崭新经验的淬炼中抒写着工业时代的“启示录”和“命运史诗”——
黄昏,那是时间这伟大、沉默的导师!
他在指引人们阔步前进,就像北方的荒野
铜号在召集,群山向钢铁厂汇涌、波动
使肉体中坚强的部分,慢慢变为不朽……
——《不要在炼钢厂面前谈论大海》
“炼钢厂”成为开放式和吸附力并存的精神共时体结构,它被转换为“机器”“一匹马”“一根针”“一头苍老的狮子”……由此,“炼钢厂”既是时代的又是超越时代的,既是具象化、经验的又是想象力介入和智性提升的产物。工业迭代升级的景观折射出复杂的现代性经验、工业文明生态机制和后工业时代产业工人心理的嬗变。由此,诗人必须具有强大消化能力的胃来处理当代的新题材、新主题和新经验。这印证了真正的诗歌,无论其处理的是什么题材和主题,那些能够一次次打动读者甚至能够穿越时代抵达未来的作品往往让我们在人类精神共时体和命运共同体的意义上看到人性、命运以及大时代的斑驳光影、炫目奇观和真实面貌。
在碎片化、即时性的日常个体经验越来越被强调的写作语境下,诗歌也越来越成为窄化的自我遣兴和封闭的修辞练习,很多诗人不再是引领时代精神的灯塔和风向标,不再是民族、国家和人类整体意识高度的精神表征。由此,我们亟需的则是总体性的诗人和“诗人中的诗人”。尤其是在长诗创作中诗人主体精神的建构和诗歌话语谱系的达成更易于得到验证、累积和完成。在一定程度上长诗可以作为一个时期诗歌创作的综合性指标,也最能考察诗人全面的写作能力,这是对语言、智性、精神体量、思想能力、想象力、感受力、判断力甚至包括体力、耐力、心力在内的最彻底、最全面的考验。从一个更长时效的阅读时期来看,长诗与总体性诗人往往是并置在一起的,二者在精神深度、文本难度以及长久影响力上都最具代表性。由此,我们可以格外关注2021年刊发在《民族文学》上的小长诗。
雪舟(回族)的《西峡山中》展现了祁连山、陇山的沟壑褶皱以及植被的自然物候和时令景观,而更为深入之处则在于自然物转换为与个体、族裔、历史、时代深度关联的时空体和命运结构,诗人丰卓的想象力和一次次的精神叩访以及深度细描是邃远而直抵生命本里、生态本体和文化根底的。阿顿·华多太(藏族)也写到了祁连山,他尽可能地将历史、文化、宗教和时间的光晕投注到这连绵不尽的山体上,“历史像吹过岩石的阵风/吹动黑白不同的棋子/你来我往,在时间的棋盘里”(《嘉峪关印象》)。彝族诗人阿赫长江则在小长诗《燎原》中重塑了凉山的文化基因,在“火塘”“法铃”“披毡”“羊角”“鹰”“火把”“群山”等民族深度意象中加深着元素化写作的精神牵引功能。杨荟是云南彝族,她的《老山兰——致敬为祖国牺牲的英雄》让我们看到诗人个人化历史想象力和求真意志的重要性。对于这首诗而言,最为重要的是它的出发点、立足点,比如一个个数字在这首诗中所承载的巨大精神重力,“从山顶到山脚共21排/960个土堆960块墓碑/960具忠魂埋骨南疆/他们平均年龄不到20岁/百分之三十是党员/百分之四十二是共青团员/百分之九十九没有结婚没有儿女/这样的烈士陵园在这边境上有24座”。这是历史时间和生命时间以及求真意志同时降临与猝然相遇的过程,它们激活和碰撞出来的场景以及词语本身更具有长效的生命力和活力。这是人与历史的重逢,是词语和时间的交锋。这也是个体时间在现实时间和历史场域之间的交互往返,是立足于战争但又最终超越了战争对过往以及未来的对视,是“英雄史诗”和“命运交响曲”。对历史和战争以及命运的重新思考需要一个诗人具备精神能力和思想能力以及与此对应的词语能力、细部处理能力、整体构造能力和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只有对历史、战争以及诗歌自身有着极其完备而独特的认知者,才能在相关写作实践中有所作为。
二、基调、生长点与精神关照方式
无论现代诗的体式、技艺和表现方式如何丰富和发展,少数民族诗人总是抹不去“民歌”的源头和言说基调,那实际上是他们天生的嗓音和特有的发声方式。确确实实,在一部分少数民族诗人的文本中我总是能听到一副副歌唱的喉咙,“诗”和“歌”在他们这里往往是合二为一、融为一体的。是的,天生的歌唱天性和音乐本能在整饬的形式、清悦的耳感和韵律中得到了强有力的回响,比如萨仁图娅(蒙古族)的《一路追云》、塔里木(维吾尔族)的《天空之上》、吴颖丽(达斡尔族)的《我曾被春天温柔以待》、郑刚(藏族)的《西里往事》、额·宝鲁德(蒙古族)的《大草原那边》(哈森译)、宝音塔米尔(蒙古族)的《飞鸟》、马英(蒙古族)的《风暴中的苍狼》,以及第8期柯尔克孜族作品专辑中帕米尔·阿斯勒别克的《草原亲如母亲》、托尔坤·莎依特的《故乡哈拉峻》、努尔托乎托·杜巴纳勒的《白鹿》、克里木·铁木尔的《生活就是奋斗》、祖拉·拜先纳里的《无锡深秋》等等。
一个刊物要不断关注甚至推动文学生长点。就近几年的少数民族诗歌创作群体而言,年轻的写作者不仅成长速度加快,而且呈现出特殊的诗歌风貌和语言质地,而这也离不开《民族文学》侧重青年诗人的推介,比如“本刊新人”栏目和“90后作品专辑”。其中第4期“本刊新人”栏目推出的90后韩金月(撒拉族)就是代表之一,她的诗句“永恒内部/落下的雨和鼓声”(《百花园》)代表了诗人永恒的责任和要义,即在瞬间的、即时性和表象的背后最终发现时间永恒的秘密和世界的法则,即真正意义上的诗人要具备“芥子纳须弥”般的精神视野和襟怀。诗人独语、对话,说出祷辞和启示录,他们不仅关乎个体情感的潮汐和命运的仪轨,而且指涉时间的内在奥义和人类永恒的命运共同体的语言之途和精神之境。质言之,诗人的襟怀、视角以及取景框对于写作来说非常关键,“我在田埂上猜想收成/与得失无关/我在池塘边怀念故人/与悲喜无关/我把它们想象成静物/唯有如此,才感受到时间的重量”(马季《异质之美》)。正是得益于差异性的眼光、取景框和精神观照方式,娜夜(满族)的写作突破了一般意义上的“女性写作”,她的诗歌因为语言节制、智性突出、质地深邃而形成了不可替代的个人风格。娜夜的组诗《云端之上》在突出空间背景所具备的精神景深前提下——梭磨河、阿来书屋、罗吾楞寺、斯古拉、溶洞、白帝城——展现了亘古般的伟大召唤和不可解的未知力量的影响,“每个生命都有量子纠缠的另一个自己”(《火苗最旺的地方》)。娜夜的诗从与细小和幽微之物的一次次凝视、对话和擦亮开始,它们与人性、母体、生态、时间、存在、记忆等构成的人类终极命题直接关联。这样的诗不只是与个人有关,更指涉精神共振层面的“我们”,进而也能够赢得更多的倾听者。康若文琴的《曼扎》《空杯》也体现了诗人作为精神修行者观看世界以及自我的特殊方法,同样也是一个诗人的眼光、视野和方法论的体现。
曼扎内,火焰和海水相安无事
都来自远古
她假设没有真正的死亡
出生只是一次次出发
每一轮回,她都放下些许尘埃
一点,一点点
然后,她大步走进尘埃
——《曼扎》
这些极其微观的空间却足以支撑起一个强大的无限延展的本质性的精神空间与幻象世界,这是精神和心髓模型与灵魂证悟的微观缩影。其重心在于观照方式、认知角度和取景框位置,在于感受和想象的时时深度参与。
三、空间、坐标与族裔想象
奥斯卡·米沃什说过:“我们的所有想法都源自于地点的概念。”在文学家、考古学家以及田野考察者这里,地图对应的并不是平面空间,而是具象化的自然和历史融合的构造,甚至是生命化的对应。
晓雪(白族)的组诗《西部诗抄》更接近于伟大恒久的自然元素与精神世界的一次次深度对话和沉思。娜夜(满族)写到了“梭磨河”,“我可以分辨三只鸟的叫声/一只在黎明叫醒我/窗前雨雾缭绕/梭磨河日夜流淌”(《火苗最旺的地方》)。康若文琴(藏族)的诗中也出现了“梭磨河”,它显然是藏地文化的母体般的原始象征,“梭磨河眼里含着整个夜空/匍匐到尘土里/七里,白湾,莫斯都岩画/直波碉楼,还有四大丘的蚂蚁/静默,一句真言/与星辰的碎屑和解”。对于族裔和居民而言,家乡地图还意味着他们最后的精神依托和记忆坐标。每一个写作者都有自己现实故乡的地图和记忆图式。这些点、线、面、体联缀成了想象的共同体,进而维持了记忆的根基和往昔的景象。“地图”是属于记忆的,是全息的,整体的信息包含在每一个线条中。这些地图不只是一个个点和一条条细线,而是实体和记忆结合的产物,是想象的共同体。这既是地理上的又是精神上的标识——最后的标识,“常常是用来标识与所有作品或生产者相关的最表面化的和最显而易见的属性。词语、流派或团体的名称专有名词之所以会显得非常重要,那是因为他们构成了事物:这些区分的标志生产出在一个空间中的存在”。(皮埃尔·布尔迪厄《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和结构》)。对于返乡者或精神漫游者而言,“地图”不是平面的而是立体的有生命力的,可以一次次重返、凝视、抚摸和漫游。
鲁若迪基(普米族)的《车过二郎山隧道》规避了一般意义上的“观光诗”和“风景诗”的惯性危险,而是在主体性认知装置中注入了家族的命运,充溢着人与世界不可逾越的命定式距离的慨叹而令人沉思。多年来,鲁若迪基一直是一个反“风景化”的写作者,“所谓风景乃是一种认识性的装置,这个装置一旦成型出现,其起源便被掩盖起来了”(柄谷行人《风景之发现》)。在鲁若迪基这里不存在外在的观光化的“风景”,而是主体和空间交互之后产生的“内在化景观”。阿卓务林(彝族)的《指路经》等诗指向了彝族的精神母体和文化源头,在山、河、路以及“父亲”构成的循环式的命运交响中凸显出亘古未变的终极景象,这在越来越强调现代性经验的整体语境下反倒是获得了特殊的诗学、民族学的精神重力和思想载力。在咏叹式的抒写中,阿卓务林在母体般的召唤中一次次回到他诗歌写作的起点和源头,即彝族人的生死观念、族裔信仰、属地性格、精神图谱、地方性知识以及整体性层面对人的本质问题的终极对话和思想盘诘。同为彝族诗人的邱墨则在组诗《把你捧在手心上》热切地欢呼、赞颂着高速的现代景观时代和新时代的到来,刚好与阿卓务林的“凝视”形成了不同的精神向度。牙韩彰(壮族)的“花山”则蕴含了传统、先祖和新时代的对话,而个人与地方性知识的深度介入,凸显了生生不息的族裔密码和精神档案。蔡晓龄(纳西族)、安然(满族)、姚茂椿(侗族)都在新的时间序列里担任了回溯者和母语的梦想家的角色,他们在诗歌中寻找族裔的根系,探询那些被日常浮土和现代性力量所隐藏或忽视的深沉根底,“从根以下开始/干脆从家谱上的祖先名讳开始/从大雾中开始发芽/从不知名的一天起步/从你的一根黑发泅渡大渡河/上空的桥散发铁锈味/跨过你的地界气息就变了/天空采不完的菌子藏着吃不完的虫子/一个亲人埋进去/世上的眼神不一样了/那是我的至亲一个梦想家/在梦中避开我去死/事先没问过我一句/现在我拔起任何一截草根/都听见他的呓语/对我耳语/那种模糊与真切/刚好等于与云南的那段距离”(蔡晓龄《与云南的一段距离》)。陈润生(仡佬族)以“雷家坝”为切入点关注的仍是田园和“乡愁”,在乡村日常之物的描摹中他既是沉静的、满足的,也是掺杂了悲悯、不安和忧伤的。雄黄(侗族)则在“湘西”和“雪峰山”下打捞时光的倒影和岁月的流年,使得诗歌承担了记忆功能,“忍不住潜入水中,反复打捞自己/那几两浑浊而散乱的命”。(《桥下倒影》)。嘎代才让(藏族)等诗人的写作一再确认了诗歌如果 要承担记忆的功能,就得一次次探询原有的精神坐标,要一次次深入到事物隐秘的内部,必须通过现象学的还原说出褶皱里面的真相,“风的形状没法形容,俯身前行/据说有雨夹雪,雷电,人们蓄意告别/盛大的筵席/这座小镇拥有/让人偏爱的一面:民族的,世界的/都经这里保持着/正常的体温,和一尘不染的表情/我爱这样简单的地方”(《倒淌河》)。
四、原型象征与家族抒写
在阅读2021年《民族文学》所刊发的诗作中,我一次次与诗人笔下的那些“父亲”“母亲”以及家族形象的抒写相遇。显然,他们具有原型象征的因子,而原型象征在现代诗中常常以人格模式和情结模式的方式来达成。原型象征是指诗人在写作中直接从神话原型(archetype)或仪式、种族记忆等母题中找到象征体。由此,我一次次想到当年威廉·福克纳所说的一句话:“他的父亲不仅肉体上为他播下种子,而且往他身上灌输了做一个作家必须具备的那种信仰,那就是相信自己的感情是很重要的,父亲另外还灌输给他一种欲望,迫切希望把自己的感情诉说给别人听。”(《舍伍德·安德森》)“父亲”“母亲”总会成为诗人、作家们叙述道路中绕不开的关键形象,有时他们是具体的、命运的、家族的,有时则带有时代整体的象征,而后者更像是一个个精神寓言所支撑起来的族谱、档案。
那么,什么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与时代和个体都密切相关的真实的“父亲”“母亲”?也许,“真实”这个词已经变得越来越可疑,不仅每个人的生活和命运差异巨大,而且每个作家通过文字来再现或虚构的方式颇为不同。由此,我们只能从精神现象学的角度来观看那些多侧面的镜像之中的由碎片、点阵或拟像所建立起来的复数的“父亲”和“母亲”。
由“父亲”“母亲”形象我们总会直接想到土地、家族以及大地伦理。这些“父亲”“母亲”显然不再单单是诗人个体的具象化的“亲人”,而是融合了不同个体的差异性经验之后的“我们的”“想象的”“寓言化的”以及命运共同体的“象征”。正是借助这一复合体的“父亲”“母亲”结构,诗人得以一次次如此艰难异常地完成对人、人性、家族、命运、现实以及历史的综合考察和内在挖掘。在诗人的文化根性和精神胎记中,“母亲”更多指向了个体和族群的“母体”,指向了源头,而“名字”则直接与身份、家族、基因和血脉连缀成一条历史、现实和命运相掺杂的河流,“关于这一称号/有人说背负青天,苍茫千里/我没有认同/而是竭力分解//让姓飘入大海/带着爱的信札/在细沙与泡沫之间/看缪斯的背影//让名飞向天空/借着鹰鹫的眼睛/坐在漫天的阴霾里/窥探宙斯和七个女人的秘密”(海翔《我的名字》)。撒拉族诗人韩金月笔下的“母亲”“新娘”和女性则指向了复杂难解的时间命题本身——当然也是人的本质命题,“衰老”是万物的共用词,这个单向度的过程是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挡的,“晚间和母亲坐在椅间/她如同一座坍塌的雕塑/泛着年迈的困意/母亲手上的戒指是绿宝石的/但头上的绿盖头却变成了黑色/时间不经意间就把几十个年头/从母亲青春的脸庞挪至别处”(《母亲》),“像一只被时间的手在岁月的烧炉里/烘烤的陶器,一寸一寸,烧制出/一个女子最动人的姿态/我知道多年后,你身上艳丽的光泽会日渐黯淡/正如一棵在早春灿然绽放的树/在暮春时节缓缓熄灭灯盏/或者在未来,你将体内的几尾鱼放生/竹影似的身影便不断弯下去”(《新娘》)。值得注意的是韩金月对时间命题和女性精神世界的观照是审慎的,并没有附着太多的伦理化、民俗学和社会学的符号,而是还原为一个个场景、细节、精神现场以及携带了心理势能的核心意象,它们不需要阐释和评说,它们自身就具有不必言说但却能感染旁人的心理轴心和共情的精神空间,“薄雾如同夜晚的桂冠,缭绕在我/年老村庄的上空/一些面容姣好的女子在秋天出嫁,如落叶至水/随流水向远而逝/而在穹顶深处,星火轻燃/我看到无数银质的光粒悄然坠落于/人间所有的街市和河岸/黎明时分,昨夜跋山涉水而来的清霜/在白昼的眉间,落雪”(《霜降》)。鲁娟为80后彝族诗人,她的《拉布俄卓及女人群画像》则以“女性”“母亲”“祖母”“小女孩”为生发个体情感、族裔命运和地方性知识的“金色”轴心,这些诗歌文本中的女性既是自画像又是女性群像。她们是复合式载体,美丽、隐忍、热烈、朴素、勤劳、狂野,一起汇聚成了女性家族图谱和母语般的基因密码,“给你,/这些历经痛苦和艰辛浮出来的,/是黄连是苦楝是甘露是蜜汁,/是由黑暗转向光亮的全部!”(《礼物》)值得注意的是鲁娟的这组诗出现了高密度的“对话”,它们既是深度理解的产物又正好是绵延不绝的族裔母体的衍生、循环。人生一世,草木一秋。土族诗人绿木诗歌中的“母亲”“父亲”被还原为如同“一株草”般的真切、坚韧、朴素而沉默、卑微的命运,但是他们自然如同大地和大山一样让人温暖,让人永生铭记,“蹲在山梁上抽烟的我俩/多像两株一青一黄的蒿草/父亲,风吹过来又吹过去/岁月何曾放下过刀子//人世艰辛/我们并没有发出声音/只是内心的波澜像云朵一样/一会儿乌黑一会儿洁白/但从不曾落过雨水”(《与父书》)。彝族诗人丁丽华笔下的“母亲”(《周六,陪母亲透析》《中元节之夜》《礼物》)以及朱良德(侗族)的“母亲”都是与身体、衰老、疾病、失语等日常情境紧密牵扯在一起的,作为“疾病的隐喻”而出现的“母亲”更增添了命运的阵痛感和现场压抑、沉暗的基调,“这样吧,给你说说我的母亲/一个曾经不懂汉话今天忘记彝语的女人/刚从医院透析回来。小女儿守在她身边/守着她荒凉的晚年,守着她的余生/小心翼翼地过着每一天”(丁丽华《在盛夏等你》),“一阵叮嘱后,母亲正要进屋/在翻门槛的时候,母亲在家门口摔了一跤/重重地,就在我眼前/地上流了一些血/我把母亲抱在怀里的时候/才发现母亲如此瘦小/后来,我把母亲送到了医院/在去医院的途中,我才发现/母亲的眼里,含着一些晚年的泪水/却没有喊疼”(朱良德《去年除夕》)。对于高若虹(满族)来说,个人化的家族想象力指向了更为真切的个体命运,指向了围绕着“黄河滩”展开的一段真实不虚的过往,比如《六岁我登上了天台山》并非是传统的登高诗、景物诗,而是“命运之诗”,“在半山腰我看见一群咩咩叫的云/有两朵正在吃奶/那是一个艰苦的年代我听见饿得面黄肌瘦的日子/在妈妈背上咕咚咽了一口口水/而满山打坐的石头/闭目入定喉结没有滚动”。
五、大地伦理与共同体的碎片
“大地”与“天空”是彼此映照的垂直共同体,失去了任何一方都会导致世界秩序的瓦解。基于此,“大地”并不单是空间维度的,而是对应了时间、文化和心理体系的,所以“大地伦理”既是生态环境伦理又是民族文化伦理。在固态的封闭社会,大地对应于人与环境之间的血肉脐带和命运关联,“康巴,每一片草原都犹如一只大鼓,四周平坦如砥,腹部微微隆起,那中央的里面,仿佛涌动着鼓点的节奏,也仿佛有一颗巨大的心脏在咚咚跳动。而草原四周,被说唱人形容为栅栏的参差雪山,像猛兽列队奔驰在天边。”(阿来《格萨尔王》)关于“大地”的本源性写作曾一度成为世界文学的重要传统,“大地共同体”的提出对应了人们深层的原初的心理结构和精神视界。
从整体来看,高若虹(满族)的组诗《在黄河滩陪一棵枣树坐坐》体现了对“乡土秩序”“大地伦理”的维护,正如那些秋风一遍遍冷峭地刮过滩涂、石头、土地、庄稼、枣树、土豆、蚂蚱、院子、红木门、土墙、轮椅以及一个个无名的乡村妇女一样。顺着秋风扫过“黄河滩”之后的痕迹,我们注意到它们是“大地伦理”或“大地共同体”的表现物、剩余物以及最后的证物,“那块石头记得当年他就像一块石头/被命运狠狠地从家门口一脚一脚地踢走/他踢石头时发出的沉闷的响声/就像他被踢走时压抑的抽泣哽咽/一声一声听得我也压抑心一下一下抽紧//一块家门口的石头被他踢走了/留下巴掌大的一团空白/反倒让院子和家空旷孤独起来”(《踢石头的人》)。蔡晓龄(纳西族)的“田野”、朱良德(侗族)的“坡背村”、黄秋(瑶族)的“伊犁河”以及马克(回族)的“作物”书写,都道出了一个长久以来形成的传统和共识,“大地”“河流”以及“山谷”直接对应了地区经验以及相应的体验方式和文学叙述方式,也就是说描写地区经验的文学是区域文化生成和消亡过程中的一部分,“青藏故里早已冰天雪地/你发来的视频里,一群牛羊/踯躅于一场又一场风雪中/我差不多已经忘记了/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和孤寂//空落落的老宅门口,这个时间/再也不会有晚归者轻轻浅浅的脚印了/那盏蝴蝶形的蓝色太阳能路灯/悄然隐没于无声的黑暗之中”(刚杰·索木东《夜读》)。正如迈克·克朗所说,“它们是历史发展过程中空间被赋予意义的时刻”(《文化地理学》)。大地是精神依托和记忆标识,尤其是在地方性知识和大地伦理遭遇挑战的时刻。在这个意义上,高若虹(满族)的“黄河滩”与葛·呼和少布(蒙古族)“遗失的马鞭”“荒芜的草原”“猎人的子孙”,以及龙金永(苗族)的“村庄”一样,都对应了“大地共同体”的碎片,“马鞭已经丢失,梦想也不是驰骋/细碎的黄花是温馨的寄托/绽放的却是无奈的殷红/女儿呢?牛羊依然在她的心里茁壮”(葛·呼和少布《遗失的马鞭》)。这是“遥远的目光”般的真切和恍惚,而“遥远的目光”已被匆促的现代性世界景观所终止。为此,列维-斯特劳斯不得不发布警告,“人类的一切作为,即使都避免不了失败的命运,也并没有能扭转整个宇宙性的衰亡程序,相反的,人类自己似乎成为整个世界事物秩序瓦解过程最强有力的催化剂,在急速地促使越来越强有力的事物进入惰性不动的状态,一种有一天将会导致终极的惰性不动状态。从人类开始呼吸开始进食的时候起,经过发现和使用火,一直到目前原子与热核的装置发明,除了生儿育女以外,人类所做的一切事情,就只是不断地破坏数以亿万计的结构,把那些结构支解分裂到无法重新整合的地步。”(《忧郁的热带》)
值得强调的是真正意义上的少数民族诗人并不是孤闭的“地方主义者”,而是以“土著”“人”“诗人”的三重眼光来看待、审视这一特殊的精神结构,从而既有特殊性、地方性又有人类性和普遍性,由此个人经验、族裔经验才能够进而提升为历史经验和语言经验,“属于世界文学的作品,尽管它们所讲述的世界完全是另一个陌生的世界,它依然还是意味深长的。同样,一部文学译著的存在也证明,在这部作品里所表现的东西始终是而且对于一切人都具有真理性和有效性。”(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在此前提下产生的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诗,也许还是终极之诗。
原刊于《民族文学》汉文版2022年第1期(责任编辑 郭金达)

霍俊明,河北丰润人,研究员、博士后,供职于中国作协《诗刊》社,中国作协诗歌委员会委员、中国现代文学馆首届客座研究员,著有《转世的桃花——陈超评传》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