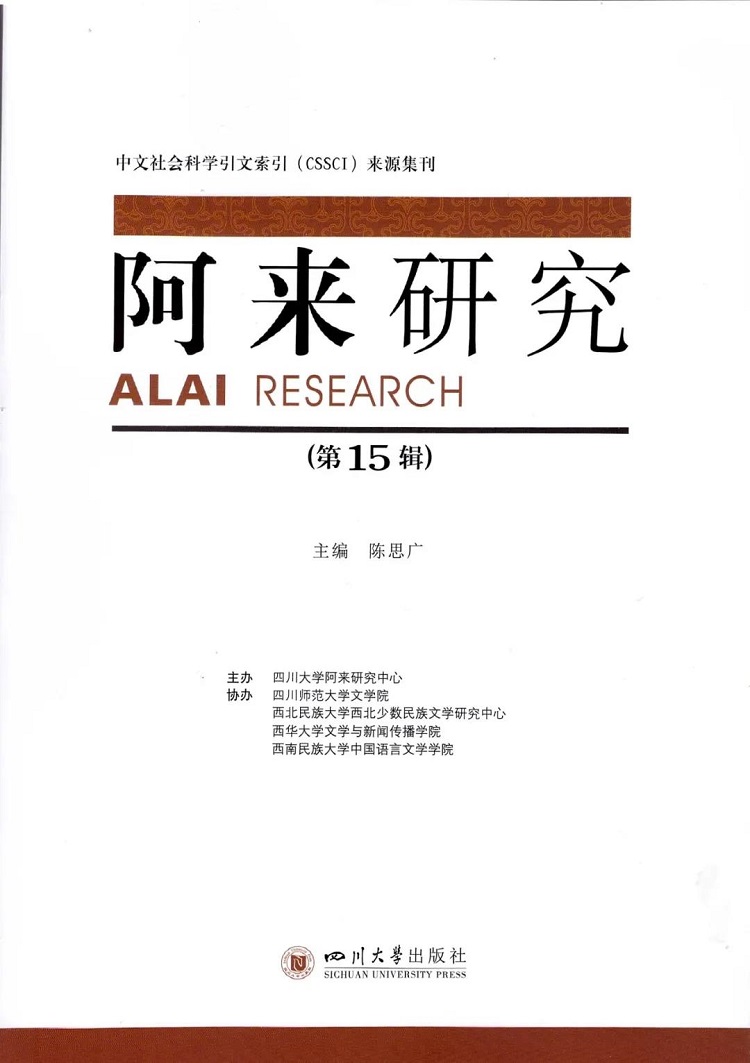
阿来,“一个用汉语写作的藏族人”①,一个生活在藏族文化边缘地带的双重混血儿,一个深受西方文艺作品影响的中国作家。民族身份的复合性使得阿来的创作始终以某种徘徊的姿态穿行于汉藏文化之间。多重文化资源的滋养为阿来提供了更为宽广的写作视野,有学者称之为“跨文化写作”或“跨族别写作”,强调其创作资源、身份立场的异质性,但如何处理民族性与普遍人性的关系对作者而言仍然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难题。相对于汉藏文化的双重中心,阿来试图以一种剥离的视角、游离的目光,在历史与现代之间创造一种广义的“大声音”②,这声音从个人体验出发去到天上让众生听见,但听到的目的并不在于彰显声音之宏大。“大音希声、大象无形”,作者所追求的是一种融合了民间传统、悲悯情怀及知识分子责任感的普遍人性书写。因而,阿来小说的创作主题也由早期的边地家族史写作逐步向民族志创作方向转型,史料的挖掘、观点的密集输出是对当下现实提出的严峻反思。如阿来在谈到非虚构作品《瞻对》时认为,写作不应以娱乐大众为目的,文学创作应当关注社会问题,表达作家对社会现状的观察与思考,也就是说书写历史的目的在于回应今天的困境。③
作为一名自觉抵抗庸俗趣味的严肃作家,这样的努力是值得肯定的,但文学创作的学者化转向也引起了评论界的广泛争议。郜元宝以“不够破碎”为题批评阿来后期的长篇创作丢失了原本的文字灵性,知识的堆砌、过于强大的理性思维压抑了小说本身的叙事逻辑,白浩、邵君燕、李建军等学者也表达了同样的忧虑。争议点大致如下,首先在于阿来的民族身份。郜元宝称其为“从小就失去本族文化记忆而完全汉化了的当代藏边青年”④,邵燕君则对阿来的“纯文学”作家属性进行了补充说明⑤。如何通过文学的形式书写本民族文化、关照历史、回答现实的确是一个困境,但将阿来视为“藏地密码”或“藏族文化”的代言人,于作者和读者而言都是有失偏颇的。阿来出生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古称“嘉绒”,嘉绒藏族是指生活在甘孜、阿坝部分地区以农耕、狩猎为主要生产方式的嘉绒人,嘉绒藏语是一种只有语音没有文字的藏语方言,其内部形态变化丰富,语言现象复杂,保留了许多古代先民部族的语音、词汇。因而,与其将阿来的创作理解为狭义的藏文化书写,不如从地域视角切入,仅将其视为嘉绒藏区生产生活、民族文化的地方性知识书写。⑥
另一争议在于阿来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姿态,大致可以理解为对其“纯文学”书写、“知识崇拜”、启蒙话语以及矛盾的人文主义立场的批评。从“山珍三部曲”到《机村史诗》,再到以汶川地震为题材的《云中记》,反思现代性始终是阿来小说的重要主题之一。作者想要表达的从来都不仅仅是少数民族视角下的地方性经验,而是希望通过书写一个村庄的历史达到某种普遍性的启示,从个别的乡村到所有的乡村,管中窥豹,一叶知秋。但是,思想输出的强大意图部分地压制了小说本身的艺术价值,以《蘑菇圈》为例,作者对于书中主人公阿妈斯炯不加批判的赞美式塑造反而损害了人物的真实性与复杂性,肥胆与丹雅疑似“乱伦”的情节设定则略显多余,通过渲染丹雅对于金钱毫不掩饰的贪婪以及将其与阿妈斯迥可持续发展式的自然观念进行对比来表达作者对于消费主义的批判,也是比较粗糙的。因而,我们需要探讨的并非阿来作为一名藏族作家能否书写“中国经验”或进一步剖析其写作立场的问题,而是少数民族作家如何书写地方性经验以及现代化视野下城乡矛盾的问题。从这一角度来看,相较于名声大噪的《尘埃落定》,学界与市场对于《空山》的关注仍显不足。《空山》以藏族传统村落“机村”为空间背景,在某种悠长的民间曲调中将串联起当代历史记忆,对于传统生活方式的回望也并非仅停留在无尽的缅怀与叹息中。阿来深知历史无法倒退,但面对旧文化的消逝以及那些跟不上时代的个体的悲剧,仍然坚持用一种悲悯且浪漫的笔调缓缓叙述。阿来曾说:“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不悲悼文化的消亡。但我希望对于这种消亡,就如人类对于生命的死亡一样,有一定的尊重与悲悼。悲悼旧的,不是反对新的,而是对新的寄予了更高的希望。”⑦那些认为《空山》的创作理念过强从而丢失了本民族文化的批评或许过于苛刻了。首先,阿来的藏地书写并非狭义概念上的西藏隐秘岁月,相较于书面藏语,嘉绒方言、民间口传资源、地方志、官方史书、翻译佛经、个人化记忆才是阿来关于藏地知识的主要来源。其次,人文主义立场与民族性表达也并非一组矛盾的概念,正如阿来笔下的宗教体验是一种混合了原始苯教信仰与藏传佛教的自然神性,相对于以寺庙、喇嘛、转经筒为核心意象的藏地想象,阿来更愿意创建一种摈弃了“东方主义”式幻想的真实藏地。而所谓“人文主义”立场本身就是复杂的,既可以指向科学与文明,也可以以“人性”为关键词对科学与现代化提出质疑。
一、民间资源与神话的力量
阿来的小说大多取材于嘉绒大地星罗棋布的神话传说、部族史诗、家族历史以及现代化视野下当地居民日常生活的变迁与心灵逆境。有关“嘉绒”一词的来源说法众多,其中有两种说法流传最广:一是地缘说,指大渡河流域靠近河谷或汉人聚居区的温热地带,二是和苯教信仰相关。嘉莫墨尔多神山是藏区四大神山之一,嘉莫在苯教信仰中是神山护法斯贝嘉莫的简称,嘉莫嚓瓦绒则是斯贝嘉莫的居所,雀丹先生在《嘉绒藏族史志》中将“嚓瓦”解读为居民区,“绒”是低湿温暖的河区,也有学者认为“嚓瓦”是炎热的意思,“嘉绒”一词保留了嘉莫嚓瓦绒的首尾部分,后逐步发展为区域名称。汉藏混居的历史传统,相对温热的气候条件,物产丰饶的地理环境,多种宗教相互融合的信仰体系,这一系列因素形成了阿来笔下不同于拉萨藏文化中心的边缘藏地想象。阿来文学创作的民间资源(而非民间立场)可以分为外在与内在两个层面,外在资源包括藏族口头文学传统、歌谣、民间故事、英雄神话、当地生产生活习惯以及宗教信仰等多重内容。此外,民间资源并非仅限于口头传说,也包括书面作品等,如格萨尔说唱艺术就包括托梦、顿悟和掘藏等多种形式。内在资源则是指藏民族的集体记忆或集体潜意识,也就是一种类似于神话力量的内在召唤。即使在现代科技已然代替原始图腾、宗教仪式成为全新信仰模式的今天,神话仍以碎片化的形态深埋于人们的内部信仰体系。如果说梦是个人潜意识的显现,那么神话就是集体潜意识的原型,它教导我们如何将个人生命与更宽广的社群生活、历史传统联系起来,指引我们发现自我,体验生命的内在价值。
不同于现代作家对于语言、技巧的个人追求,神话故事的情节设置通常较为单一,语言古朴,想象力丰富,对于创作者的有意隐藏则在于召唤某种更为久远且伟大的记忆与传统。“召唤”作为一种神秘体验,经由仪式的外部形态进入内在心灵世界,从而将个人与族群历史联结在一起,教导众人经由死亡体验生命。因而,阿来小说中的神性因素并非某种具体的宗教体验、宗教仪式,而是一种精神意象。神话学学者坎贝尔将神话的功能分为神秘性、物理宇宙观、社会性和教育四种。神秘性使人类对世界始终保持一种敬畏心理,类似于科学理性意义上的物理宇宙观,神话中的宇宙观同样强调一种无法证“有”的超越性,强调在人类世界之外有一个更伟大的世界。但是,探寻的方向不在外部,而在个体的心灵深处,我们必须超越具体的形象层面,将其视为一种象征,同时不将这种“超越”当作高于自然的绝对理性或终极精神。上帝说“我与你同在”,所要表达的正是这样一种永恒的慈悲。从这一角度来看,神性也就是人性。社会性是指神话的地方性差异,生活在不同地域的人类社群将会产生不同的伦理规范,这些规范经由神话的形式得以传播。神话的想象方式与该地区民众的生产生活范式紧密相连,雪域高原的藏族与生活在河谷地带的藏族必然信奉着不同的神灵。但这并不代表信仰之间的不可通约性,地方性知识的意义与神性的终极奥秘的关系并非对立,而是彼此相通,此处即别处,边缘即中心,死亡即出生,片刻即永恒。而神话的教育意义不仅限于远古时期,即使在现代社会也同样重要,它涉及生命本身,指导我们如何生活。
神话的力量是一种泛神论概念上的智慧,它随着讲述的历史被一次次加工再创造,并在咒语般的仪式中不断复活。作为神话的故事不同于系统性的宗教信仰,它以意象作为呈现方式,隐喻而非议论是其主要的叙事手法。与之最为相近的体裁是诗歌,我们无法从实在的角度对诗歌进行解读,只能经由意象与隐喻以期达到无限的靠近。小说《云中记》中,阿来借由祭司阿巴的返乡之旅想要完成的正是一场灵魂的对话与召唤。首先我们注意到的是名字的隐喻,作为苯教非物质文化传承人的阿巴是一名不合格的祭司,却在汶川地震发生四年后孤身一人回到摇摇欲坠的家乡,肩负起超度亡灵、抚慰生命的伟大使命。此外,“失忆”与“回忆”作为小说叙事的核心结构于时空之间串联起云中村的历史变迁,同时承载着精神返乡的重要隐喻。寻找记忆的旅程正是阿巴唤醒自我的旅程,也是带领族人回到故乡的精神之旅。于是,当阿巴穿上法衣,拿起祭铃,那深埋于血液中的咒语终于苏醒:
祖宗阿吾塔毗,保护神阿吾塔毗,收下你子孙的魂灵吧!
给他指回去的路!
给他指回去的路!
给他指光明的路!
给他指光明的路!
让他看见你的灵光!
让他看见你的灵光!
上路了!
上路了!
飞升了!
飞升了!
光芒啊!
光芒啊!⑧
“回去”、“光明”、“灵光”、“上路”、“飞升”、“光芒”,阿来借用祭祀词的肃穆语调,史诗般的复沓韵律,将读者带入了一种壮大且威严的广阔情景。宣读一种大恐惧,大怜悯。这一刻,地动山摇,在祖先的遥远呼唤中,个体仿佛坠入了幽深的记忆深处。面对神圣的远古召唤,所有逝去的、活着的灵魂都将再次汇集,庄严得回应道:“我们在!我们在!”一场向死而生的伟大仪式终于完成。仁钦问舅舅阿巴,这算是死了吗。舅舅回答道,不是死,是消失。最后一名祭司终于在“那一天”和云中村一起坠落,一起飞升,但这并不是死亡,而是大地拥抱其子民的古老方式。它壮烈且辉煌,正如《空山》中巫师多吉与原始森林一同消亡于天火的昭示。我们必须理解到,相较于身体的死亡,精神层面的“死亡”更具有启示意义,也就是招魂仪式中的死亡与飞升,更有启示意义。死亡作为人类最恒常的苦难,是古典神话学中所要解释的根本问题,也是生命的终极奥秘。而涅槃的意义并不指向对死亡的超越或蔑视,它不是拒绝,而是接受。接受死亡是接受生命的第一步,只有理解了这一含义,才能真正理解“飞升”的意义。云中村末日般坠落的景象如同死亡的盛大典礼,这让我们联想到《空山》中给的那把席卷天地的天火:“天火说,机村人听好,如此天地大劫,无论荣辱贵贱,都要坦然承受,死犹生,生犹死,腐恶尽除的劫后余晖,照着生光日月,或者可以于洁净心田中再创世界。”⑨叙述人借用神启般的语言想要传递正是一种深刻的怜悯与反思,救赎的声音不在天国,而在灾难来临的时刻,也就是劫后余生的觉醒时刻。当然,每个人的觉醒时刻并不相同,那是属于个人的心理体验。
此外,藏族民间资源为阿来的写作提供了丰富多彩的传说故事,生动独特的人物形象原型。如小说《阿古顿巴》中的讽喻智者阿古顿巴、《尘埃落定》中的傻子二少爷,《鱼》中的遗腹子鱼眼夺科,《达瑟与达戈》中的书呆子达瑟等。这些人物兼具“智者”与“白痴”的双重象征,仿佛古老寓言中的人间使者,穿过历史的尘埃对人类施以警戒,荒诞的外部形态是神谕的必要伪装,其实在则如《红楼梦》中那面錾着“风月宝鉴”的镜子,直指人心、直指人性。又如《格萨尔王》中的英雄神子,《月光里的银匠》中骄傲自尊、技艺非凡的银匠达泽,《行刑人尔依》中通过穿戴亡者衣物获取力量、最终以死亡打破其命运闭环的小尔依等人物。这些原本流传于民间传说中的人物形象在阿来的拼贴下逐步清晰,他们勇敢地与既定命运对抗,终于走向自己的命运,并将自己隐藏在故事中,获得永生。民间的智慧就在于赋予了每个人成为英雄的可能,经久不衰的冒险故事教导我们,迷失与苦难是通往命运窄门的必经之路,而结局则隐含着坠入深渊或迎接荣耀的双重可能。这是一个有关成长的经典母题,在成长的旅途中,离开母亲,寻找父亲意味着离开生活的既定轨迹,遵循自我意志的召唤,正如小说《猎鹿人的故事》的结尾,当少年桑蒂找到父亲的遗骸时,他终于找到了自己,找到了自己的幸福。
二、自然神性与神山信仰
阿来在与陈晓明的对话中曾说道,对于“宗教”他是持怀疑态度的,并非质疑宗教本身,而是质疑作为宗教代言人的僧侣阶级,认为宗教与政治的结合必然导致权力的滥用,神性的消解。⑩正如阿来在《格萨尔王》中将僧人送回寺庙的隐喻,《河上柏影》中老柏树的死亡,白云寺的兴起,信仰变迁反映的正是人心的变化历程,从自然崇拜到宗教,再到以“寺庙”“佛像”“上师”为核心意象的神秘感,金碧辉煌的寺院在金钱的加持下日益兴盛,所谓信仰已然沦为物欲时代的绝妙反讽。相较于宗教意识形态,阿来想要书写的是一种源自大自然的“自然神性”,陈晓明将其解读为“没有宗教的宗教性”⑪。不同于宗教场所、宗教仪式对于信仰的实体化下沉,自然神性强调的是人与自然的精神交流,个体对于生命本身的领悟以及宇宙力量带给心灵的震撼体验。因此,阿来将目光投向远古藏族先民的信仰方式,从民间视角切入藏族地区的民俗文化及心理结构。以僧人与巫师形象为例,阿来在塑造二者时呈现出截然不同的两种态度。阿来笔下的僧人往往未能摆脱俗世的困扰,具有许多人性的缺点,而巫师、祭司的形象则更加正面,更具灵性。巫师不同于僧侣阶级,他的权威来自于个人化的神性体验而非社会角色的扮演,是一种内在的信仰模式。巫师所代表的是一种更为古老的传统,继承的是阿来小说中那个野马和家马未曾分离的远古记忆。从这一角度看,小说《云中记》中苯教祭司阿巴对于佛教传道的拒斥应当作为一种象征姿态来理解,代表了作者本人面对信仰、民族问题时的思想转轨。
嘉绒大地先后受到苯教、佛教、儒道思想等多元文化的渗透影响,以松潘县的东日神山,也就是著名的黄龙景区为例,原本是一座重要的苯教神山,后受到藏传佛教、道教的影响,如今已成为一处汇集多重宗教文化的圣地。阿来小说中的生命观也具有佛、苯互渗的鲜明特点,相较于体系成熟的印度佛教,苯教融合了大量原始宗教的信仰方式,如自然崇拜、万物有灵、祖先崇拜等观念,占卜祈福、祭祀亡灵、驱鬼降神等仪式,以及名目繁多的地方性神邸鬼怪;佛教在发展过程中也吸取了部分苯教术语、仪轨。如果说佛教经典给予阿来更多的是理性思考,那么民间信仰的探寻则帮助阿来打来了一条更为广阔的生命旅程。需要强调的是,在阿来的藏地书写中,对于藏传佛教和苯教的记录更多是作为一种民间资源而非宗教教义。阿来试图描绘的是一种流传于嘉绒藏区的自然神性或者说地方心理结构,其中以神山信仰最为重要。神山信仰广泛存在于各藏族聚居地区,嘉绒地区由于苯教信仰保存较为完整,对于神山、圣湖等自然创造物的崇拜观念则更为突出。神山信仰作为藏区文明的文化内核,与远古藏人的宇宙观、生命观,社群内部的政治结构,伦理禁忌紧密相关,发展出等级森严的神山体系以及与之相对应的祭祀文化。如小说《云中记》中详细记载了山神节时祭祀地方山神阿吾塔毗的仪式过程。祭祀活动通常在每年的固定时段举行,其中巫师或活佛担任主持祭祀的重要角色,带领族人一同煨桑熏烟、插箭立杆、献祭风马,以祭拜山神,祈祷神灵的庇佑。久而久之,祭祀山神的活动已成为当地居民重要的民俗文化和节日庆典,是凝聚族群力量、守护一方安宁的精神寄托。又如《空山》中将灵魂寄托于山中神树的传统习俗,再现了藏族人民将生命与自然万物紧密相连的信仰模式,告诫人类对自然始终要保持敬畏之心,从而起到了引发读者反思人类命运与生态保护的教育意义,也就是作者所说的文学的现实关照。
从早期作品《猎鹿的故事》中将雪山阿吾塔毗命名为“父亲的神山”到《云中记》《蘑菇圈》将其称作“祖先神阿吾塔毗”,再到《空山》中对于圣湖色嫫措的守护,作者对自然、生命的态度有着明显的转向。从征服自然到守护家园,阿来倡导的是从“剑”的传统到“圣杯”传统的精神回溯。美国人类学家艾斯勒在其著作《圣杯与剑—我们的历史,我们的未来》中认为人类社会在以剑为代表的统治关系之前,其组织模式是以圣杯为象征的合作关系。圣杯作为女性生殖器的象征代表了一种母系社会传统,意味着生产、给与和创造,是大自然孕育生命、繁衍生命的象征,而剑作为战争的武器,代表了男性统治下侵略、暴力与杀戮历史的开端。人类社会从圣杯到剑的转向不仅是社会结构的转向,更是意识形态的堕落,从此,夺取生命的力量毅然凌驾于创造生命的力量之上,而女神崇拜为代表的合作关系则如伊甸园中上帝对蛇的诅咒一般遭到统治阶级的弃绝与玷污。《空山》中阿来借喇嘛江村贡布止口说道,人类社会正是有了分别心,才失去了远古的混沌和谐,走向纷争、仇恨与不安。⑫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会将远古先民的生活想象成无忧无虑的乌托邦社会,或者将神山信仰当作一种早于父权社会的女神崇拜。大部分神山都以男性神邸命名,神湖则以女神命名,神山之间往往具有复杂的亲属关系,这与藏区部落之间的入侵历史或宗教之争紧密相关。作为地方保护神、部落始祖神的神山,其庇佑范畴在一定意义上等同于藏区社会的区域结构划分,也就是藏区四大神山或九大神山说。南文渊依据信仰等级将其分为全藏神山 、大区神山、小区神山与部落神山四种⑬。阿来小说中的阿吾塔毗应属小范围的部落神山。作为本土传统信仰的自然神性崇拜类似于荣格学派所说的种族记忆,以民间传说、禁忌祭祀等形式隐藏在藏族人民的心理结构和日常生活中。笔者用圣杯传统作为自然神性书写的象征,想要强调的正是阿来小说中创造生命、接纳生命的力量,与之相对应的剑则代表了一种狂热且贪婪的暴力倾向,它无视自然规律与传统信仰,肆意破坏生态环境,吞噬人心,在现代社会则表现为金钱、权利、名望的诱惑。
藏族信仰中对待生命的敬畏态度来源于一种不同于进化论意识的传统神性思维,“万物有灵”意味着将所居住地的整体景观神圣化,并与部落神话相连接,赋予空间精神指引的力量。如《空山》中的圣湖色嫫措,《云中记》中的神山阿吾塔毗都被当作部落先祖受到供奉。占有土地并将土地神圣化的心理动机并非仅限于藏族神山信仰,而是一种广泛存在的家园意识,如《旧约·创世纪》中以色列人先祖亚伯拉罕宣布以上帝之名拥有流着奶和蜜的“应许之地”。圣杯传统或者说自然神性认为世界本身就是神圣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并非征服和掠取,而是合作与交换。小说《空山》中的猎人与猎物共享着亲密的共生关系,因为在狩猎文化中,动物不仅是猎人可敬的敌人,更是教导其生命原则的伟大导师。而猎杀的目的不在于享受生命,而是维持生命。生命的奥秘就在于必然经历其他生命的死亡,无论是动物还是植物,在原始先民信仰体系中杀生是一种类似于牺牲的庄严时刻,这来源于将人类融入自然循环、世界整体的思维模式。原始苯教信仰中的血祭仪式所隐含的正是这样一种交换思维,通过向自然献祭寻求神灵的庇佑。所以《蘑菇圈》中阿妈斯炯对待山神的馈赠是那么地珍惜,望着正在生长的袍子,如同呵护新生婴儿般幸福喜悦;《河上柏影》中母亲依娜的衰老才会随着五棵老柏树的死亡一同到来;《空山》中,阿来将村民猎杀猴子的行动被描述为一场残忍的屠杀。圣杯传统不同于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暴力原则,是一种倡导同情、关心和爱的古老美德。来自于藏族民间的神性意识与20世纪80年代再度兴起的人文主义思潮不谋而合,呼唤人性、人情,人的尊严与藏地书写相融合,成为阿来小说的又一重要主题。
三、人文主义立场
《人是出发点,也是目的地》是阿来获得“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时所作的发言,也是其创作理念的基本阐释。早在多年以前,阿来就曾表达过他无意再去渲染雪域高原的奇特与神秘,而是希望借由文学的形式越过民族与地域,让更多的人了解这片高原上的人与生活,书写普通人的命运故事。阿来认为小说家的任务不在于制造陌生,创造奇观,而是消解误会,传递消息,真实且真诚的书写“人”的故事。面对强大的汉语传统,阿来,作为一名不会书面藏语且用汉语写作的藏族作家,其对“普遍人性”的追求往往被解读为对自身民族语言的贬低、对民族传统的消解,进而引起了广泛的争议。邵燕君以韩少功的《马桥词典》和阿来的《空山》为例,论述了二者在处理命名问题时的立场差异,认为《马桥词典》是以反启蒙的姿态庄严得面对不同于汉语普通话的地方语言传统,《空山》则讲述了一个老套的启蒙故事,缺乏边缘文化面对主流知识时应有的态度。但因此判断阿来放弃了本民族文化身份,屈从于汉语传统,仍是草率的。首先我们应当将作家阿来与公众人物阿来进行区分,也就是说在阅读文本时避免过度带入媒体报道中的“阿来”形象或其自我阐释。新闻报道中的叙事策略过于强调观点的倾向性,部分的破坏了对于文本的开放性解读。其次,无论是阿来自己,还是读者、评论家都无需将其创作视为雪域高原的整体化书写或者一种“奇观”进行实证性研究。另外,正如后殖民理论学者霍米·巴巴所批评的那样,少数族裔的强烈认同必然产生自人的流动,所谓“身份”的确定性本身就是一个值得怀疑的伪命题。阿来在《新京报》的一次访谈中曾说道,文学创作应该在个人观点,国家、民族观点之外加入人类的概念,如果过度强调独立身份、独立价值则会造成更多的隔阂与误解。⑭拒绝任何形式的本质主义或二元对立,从多元视角进入阿来的小说创作或许更为有效。
人文主义或人道主义的概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定义,具有复杂的多义性和含混性。因而对阿来小说中人文主义立场的剖析也因保持一定的开放态度,其中兼具科学启蒙、人性书写以及对所谓“科学神谕”的质疑等多个对立矛盾的层面。以小说《云中记》为例,祭司阿巴基于传统生活经验所获得的民间知识与地质学家的科学知识体系似乎是两种不同的认识方式、价值观念,但事实上二者并不矛盾,反而相互成为一种有效的补充。对待同一世界,从不同角度出发将会获得完全不同的认知经验,合作而非统治的“圣杯”传统所倡导的正是一种经验的共享。知识之于阿来,正如同《桃花源记》中的那句“仿佛若有光”。百科全书作为一种象征在阿来的小说中反复出现,在《三只虫草》中指引着少年桑吉走向更广阔的世界,《空山》中则是达瑟抵抗“非理性”狂热的重要武器。但这并不代表作者没有反思,回到村里的桑吉看着那些新修的定居点,心想:“这些房子是对百科全书里的某种方式的一种模仿。因而住在这些房子里的人并没有另外的世界中住着差不多同样房子里的人那样相同的生活。”⑮桃花源的美丽秘境只是局外人的奇观化想象罢了,对于当地原住民来说,犹豫、艰难、无所适从的现实困境才是生活的真相。阿来的藏族文化身份并非以“坚守”民族传统的姿态呈现,而是化作对历史的自觉反思,化作一种更为深沉的记忆。这与怀旧不同,阿来无意将青藏高原描述为与现代生活对立的美好家园,也无意对现代化进程中的乡村图景进行表象呈现,而是从人的境况出发,直面矛盾,书写边地人民的心灵困境。生活在雪域高原的人们和生活在其他地域的人们并无不同,追求尘世间的幸福是大多数人的首要目标,从这一角度看,“城乡矛盾”才是近年来阿来小说创作的主要主题。
“外面”一词,仅凭其本身就代表着某种巨大的诱惑,一个富饶且宽广的世界,一种更加文明、进步的生活方式。当作者在《云中记》中借阿巴之口感慨道:“我们自己的语言怎么说不出全部世界了,我们云中村的语言怎么说不出新出现的事物了” ⑯时,并非意味着对本民族语言传统的抛弃,或者说边缘文化向主流文化的投怀送抱,而是遭遇乡村荒芜这一现实问题时发出了沉重叹息。在现代化进程中,传统乡村生活是十分脆弱的,就像阿来所言:“对于乡村,或者对于边疆地带,其实在商业链条上就是对它的盘剥。这种盘剥,我更愿意把它看成是城市对乡村的盘剥,而不将其归结为民族与民族的关系。”⑰机村,这个位于青藏高原的藏族村庄在庞大的消费体系中与其他任何村庄事实上并无区别,只是供给链条上个微不足道的输出环节,在资源消耗殆尽之后,继续通过出卖自然风光或山珍特产吸引城市的关注,机村的经验正是无数乡村生活的共同经验。《自愿被拐卖的卓玛》中的藏族姑娘卓玛和王安忆笔下的“小镇娜拉”们⑱对于城市生活拥有着同样热烈的向往,因而小说讲述的仍然是“娜拉出走”的经典母题。但值得肯定的是阿来并没有将这次出走渲染成一场堕落的行动或者粗暴得用“金钱”或“物欲”作为其出走动机。朴拙的语言、诗意化的日常生活形态让阿来的写作在处理命运主题时少了份戾气,多了份宽容。阿来将卓玛的渴望描写成一场甜蜜的醉酒,在梦中,她飞了起来,穿过村庄、穿过高山,义无反顾的飞向远方。那滴醒来时的泪水如同包裹在糖果里的酒精,是飞翔必须付出的“甜蜜”代价。在小说的最后,阿来写道,机村人并不好奇卓玛卖掉自己的原因,反而更愿意讨论卓玛去了哪里,把自己卖给了什么样的一个人。一种朴素却真挚的善意始终充盈着文本,给与沉重的现实飞翔的力量,对于人本身的关怀与理解始终是阿来小说中最为动人的地方。
最初的人文主义起源自古罗马,也就是与野蛮状态相对立的文明教化。文艺复兴时期以来,现代人文主义逐渐衍生出以抵抗中世纪神学的“人的尊严”“人的价值”等核心要素。而当代的人文主义用法则不仅包括基于人类概念之上的人道主义关怀,对人性美、人情美的歌颂,同时也是对人性弱点与复杂性或者说“人的过失”(humanerror)的重新评估。雷蒙·威廉斯分析道:“过去将‘过失’视为人类(humanity)犯错的明证,现在则被认定为——这种认可未必带来讽刺或默许的含义——人之常情(human)的一项例证(因此,human——人之常情与likeable——人之可爱,二次的意涵便相距不远)。”⑲阿来对藏族英雄神话传说格萨尔史诗的改写体现的正是这种基于“人之常情”之上的当代人文主义立场。小说《格萨尔王》中,神子崔巴噶瓦因无法安然面对人类的苦难,下凡化作王子觉如立志斩妖除魔,解救苍生,最终成为万人敬仰的战神格萨尔王。但连年的征战却让格萨尔王陷入长久的困惑与倦怠。说唱艺人晋美因梦见了格萨尔王的忧郁,试图制止掘藏喇嘛继续开掘格萨尔的故事,终止这无尽的命运,却被愤怒地指责为“渎神”。但当关于神的叙事成为不可撼动的神圣信仰时,原本处于负面意义的“渎神”行为则被赋予了解放的意义。阿甘本曾提到“宗教”(religio)一词的词源事实上并非来自于拉丁语“religare”,指人神之间的联结之物,而是源于“relegere”:“它指的是在于众神的关系中必须采取的小心翼翼、殷勤专注的姿态,以及在为尊重神圣与神圣之外之间的分隔而必须遵守的形式—以及公式—面前的,不安的踌躇。”⑳晋美的追问、怀疑与探索,阿古顿巴的戏谑反讽,格萨尔王的忧郁,这些“人”的行动使得原本坚固稳定的英雄神话故事产生了变异与扩张,在彼此重叠的意义之中完成了一次“渎神”。但“渎神”并非意味着超越分隔或恢复到分隔以前的不受限制的使用状态,也就是回复到“家马与野马不分”的时代,而是拒绝分隔的形式,从而使既定权力装置失效,保持开放以期获得新的使用。正如强权的对立面不是抗拒,而是“疏忽”(negligenza),是一种不合时宜的严肃戏仿,也就是阿古顿巴的“帽子戏法”。阿古顿巴藏身于故事的结尾以悬置分隔的形式成为了同时代的例外。因而阿来的人文主义立场与其说是关于“是什么”的故事,不如将其作为一种否定性意见的提出,即将故事从无穷无尽的神圣领域解放出来,再次回归混沌的人的领域,给与其复杂的探讨空间。
结 语
本文从民间资源、自然神性以及人文主义立场三个角度出发分析了阿来的小说创作及其创作动机,并尝试回应有关作者民族身份与知识分子写作的质疑。虽然阿来的小说的确存在主题先行,以启蒙姿态压制艺术表现,史料堆砌破坏作品结构等问题,但将其归因为民族身份的丧失仍是粗暴的。首先,阿来小说中的民族身份并非一种对抗性的民族立场,而是民间资源、民族文化及民族心理的混合型表述。相对于奇观式的藏地想象,阿来试图呈现的是处于现代化历史进程中的当代藏地境况,也就是作者所说的“面向今天的写作”。因而,小说中的藏地元素可以理解为一种表现作者价值理念的“引用”或“召唤”,通过书写藏地历史变迁,回望古老的自然神性崇拜,进而反思现代性,关注当下生活。其次,民族间的矛盾在阿来看来中并不是血缘或族群问题,而是身份认同问题。正如《空山》中所言:“比如林军这样的机村人,他是地道的汉族。但走出机村,他就是藏人。他也以为自己是藏人。只有回到机村,他又感到自己是个孤独的汉人。”㉑身份认同不仅和族群文化、地域文化等要素相关,更是一种流动且相对的心理归属。霍米·巴巴认为在物理世界所代表的第一空间和象征世界所代表的第二空间之外还存在着超越二元对立的第三空间,主导第三空间的原则不是隔离与分隔,而是互动的“混杂”状态,“混杂”通过消解身份的严格界限进而达到不同族群间的和谐共融。在阿来的小说中,汉藏双重血缘经由隔绝走向共融的个人命运故事正是重要主题之一。同样,普遍人性的追求与地方性书写的关系也不是矛盾对立的,而是统一于人文主义关怀之下的“人的故事”。俄罗斯诗人茨维塔耶娃曾说过:“对于诗人来说,母语是不存在的”㉒,成为诗人即意味着成为所有民族的诗人。相信这也是阿来的写作追求,因为:“我是我自己/我也不是我自己/是我的兄弟,我的情侣/我的儿子,我的一切血亲。”㉓
注释:
①阿来:《穿行于异质文化之间》,陈思广主编,《阿来研究资料》,四川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4页。
②阿来:《穿行于异质文化之间》,陈思广主编,《阿来研究资料》,四川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6页。
③阿来、童方:《〈瞻对〉“国际写作计划"及其他--阿来访谈》,陈思广主编,《阿来研究》(第1辑),四川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8-32页。
④郜元宝:《不够破碎--读阿来短篇近作想到的》,陈思广主编,《阿来研究资料》,四川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94页。
⑤邵燕君:《“纯文学”方法与史诗叙事的困境—以阿来〈空山〉为例》,陈思广主编,《阿来研究资料》,四川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186-196页。
⑥丁增武在其论文《“消解”与“建构”之间的二律背反—重评全球化语境中阿来与扎西达娃的“西藏想象”》中认为阿来的书写无法代表整个藏区文化,但相对于“被劫持了的西藏”这样的批评,丁增武表示更愿意称其为“被替换了的西藏”。
⑦阿来:《有关〈空山〉的三个问题》,陈思广主编,《阿来研究资料》,四川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14页。
⑧阿来:《云中记》,北京十月出版社2019年版,第346—347页。
⑨阿来:《空山》,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51页。
⑩阿来、陈晓明:《藏地书写与小说的叙事—阿来与陈晓明的对话》,陈思广主编,《阿来研究资料》,四川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39页。
⑪阿来、陈晓明:《藏地书写与小说的叙事—阿来与陈晓明的对话》,陈思广主编,《阿来研究资料》,四川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40页。
⑫阿来:《空山》,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38页。
⑬南文渊:《藏族神山崇拜观念浅述》,《西藏研究》2000年第2期。
⑭江楠:《阿来,我不是写历史,我就是写现实》,《新京报》2014年1月14日。
⑮阿来:《蘑菇圈》,长江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161页。
⑯阿来:《云中记》,北京十月出版社2019年版,第203页。
⑰朱又可、阿来:《疯狂的虫草,疯狂的松茸和疯狂的岷江柏—专访作家阿来》,陈思广主编,《阿来研究资料》,四川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18页。
⑱程光炜:《小镇的娜拉:读王安忆小说〈妙妙〉》,《当代作家评论》,2011年第5期。
⑲雷蒙·威廉斯:《关键词 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刘建基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版,第259页。
⑳吉奥乔·阿甘本:《渎神》,王立秋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27页。
㉑阿来:《空山》,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70页。
㉒茨维塔耶娃:《茨维塔耶娃致里尔克》,刘文飞译编,《刘文飞译文自选集》,漓江出版社2013年版,第46页。
㉓阿来:《群山,或者关于我自己的颂辞》,《阿来的诗》,四川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第5页。
原刊于《阿来研究》第15辑

彭岚嘉,1964年出生于甘肃景泰县,兰州大学文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西部文化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兼全国文化艺术资源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文化产业协作体专家委员会委员、甘肃省文化发展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甘肃省黄河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甘肃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甘肃省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入选甘肃省领军人才(第一层次)、甘肃省555创新人才、甘肃省宣传文化系统拔尖创新人才和甘肃省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主持完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两项,省部级科研项目二十余项。发表文章近120多篇,出版著作10余部,主要有《中国西部文化发展战略研究》《西北文化资源大典》等。获甘肃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两项、二等奖两项,省厅级奖励多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