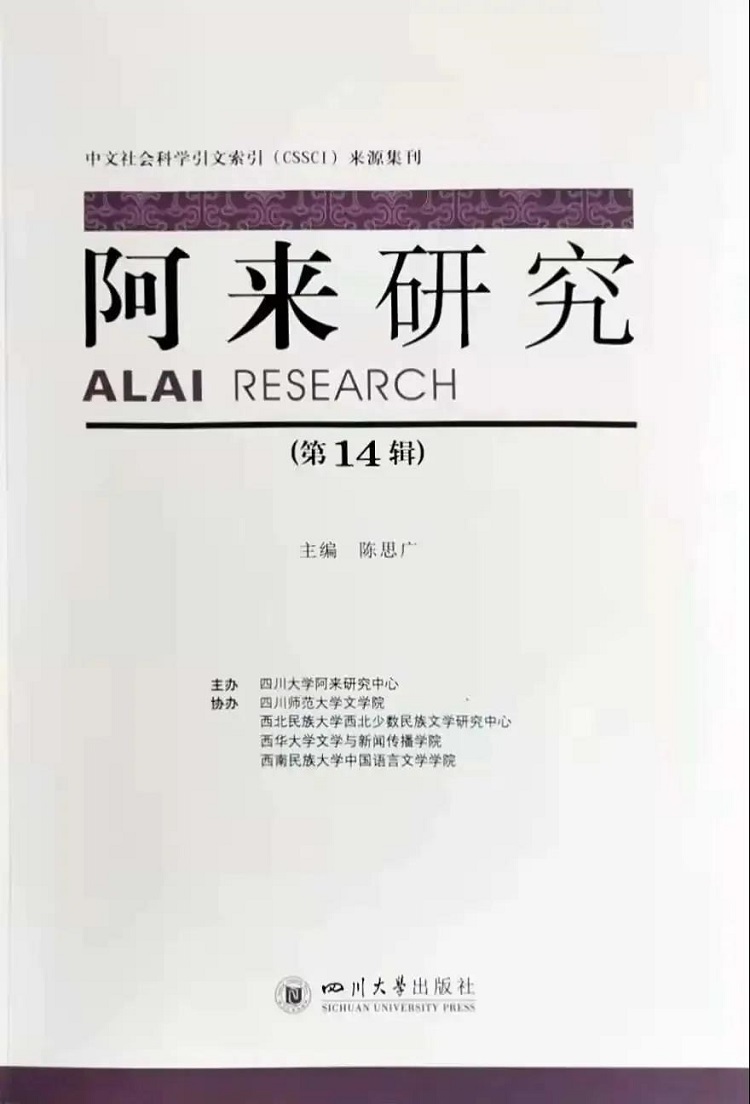
新时期作家很少有与外国文学相隔绝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对外的窗口打开,外国文学大量涌入中国,这使中国作家的广采博览、对外借鉴成为可能。为了充实自己的文学库存或者在创作中达成创新求变的目标,许多作家积极阅读和师法外国文学,阿来也不例外。从80年代起,阿来就开始大量阅读外国文学作品,“这一习惯,至今没有间断”①。不过,面对色彩斑斓、风格各异的外国文学,阿来有自己的兴趣点和择取对象,他推崇和喜欢的主要是欧美文学和拉美文学,对福克纳、托妮•莫里森、卡尔维诺、马尔克斯、鲁尔福等作家的作品尤其熟悉,也有自己的理解和看法,这些作家也都在不同程度上带给阿来启迪和影响。从阿来的小说创作来看,无论是注重民族生活书写与民间文化开掘的创作理念,还是重视形式技法创新、强调兼收并蓄的文学思想 与创作追求,抑或是“魔幻”技法的尝试,以及人物形象的塑造与描写,无不体现出外国文学的影响和阿来在外国文学接受上的特征。
一
作家必须注重民族生活的书写与民间文化的开掘,以获得属于自己的本土气质,这是阿来的创作理念,也是他从拉美文学和欧美文学中获得的重要启示。
我们注意到,在阿来阅读与接受的外国文学中,拉美文学占据了醒目的位置。阿来之所以青睐拉美文学,是因为拉美大陆的神奇性和拉美文学的民族 性,使得从神秘藏地走来、有着独特族群身份的阿来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和认同感,阿来也曾多次走访拉美国家,在拉美大地上的行走使他对拉美大陆与拉美文学有了更深的认识和体悟。这些决定了他对拉美文学的选择与接受。他先是拉美诗人聂鲁达推崇有加,视其为自己的文学导师,之后他又大量阅读拉美小说,包括魔幻现实主义作家和其他拉美作家的小说。从20世纪80年代起,阿来就开始阅读拉美小说,不仅读魔幻现实主义作家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家长的没落》《迷宫里的将军》和鲁尔福、卡彭铁尔、阿斯图里亚斯等人的小说,还读很多其他拉美作家的作品,据他自己说,他“读过一百多位拉美作家的作品”以及“许多拉美作家的访谈与对话”②。阿来非常重视、欣赏拉美文学的“本土气质”,提到魔幻现实主义作家的 献与成就,阿来说:“马尔克斯这一批魔幻现实主义作家,真正了不起的成就在于,他们让拉丁美洲文学,开始摆脱欧洲文学框架,真正有了本土民族气质。”③这里阿来所说的“本土民族气质”,指的是拉丁美洲文学的本土特征,即立足于拉美的民族生活与土著文化来展现美洲特色,这一特征在魔幻现实主义文学中体现得尤其突出。比如阿斯图里亚斯的《危地马拉传说》《总统先生》《玉米人》等小说对美洲印第安文化有出色表现,阿斯图里亚斯正因作品“深深植根于美洲民族气质和印第安人的传统之中”(诺奖授奖辞)在1967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卡彭铁尔的《埃古•扬巴•奥》《这个世界的王国》对美洲黑人文化的审视也颇有代表性,其中描写了美洲黑人的宗教仪式、“伏都教”信仰、泛灵论以及黑人与自然的神秘关系,鲁尔福的《佩德罗•巴拉莫》一方面揭示了战后墨西哥农村荒凉破败的社会现实,另一方面通过阴魂亡灵的故事和鬼魂游走的科马拉村的描绘,展现了墨西哥人的“死人国”信仰和鬼神文化的特征,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对拉美的文化历史加以全方位的扫描,展示了拉美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混杂性”特征,即拉美本土的印第安文化、黑人文化和外来的欧洲文化、阿拉伯文化交织的特征,马尔克斯也因对拉美历史和文化的出色表达而在198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拉丁美洲作家这种将本土文化与现代小说技法融合在一起的创作特点,使拉美文学成功地走向了世界。
拉美作家虽然写的是带有鲜明本土特征的地方性的题材,但又不被地方性束缚,这让阿来钦佩不已。在拉美文学的启发下,阿来走向了对本民族生活及民族文化的大力书写。他的小说总是围绕着他熟悉的藏地生活和文化习俗来展开叙述。比如《尘埃落定》写的是嘉绒地区的生活风情与土司制度衰落的历史,也呈现了藏族人的神灵信仰和神话传说,《空山》写的是藏族村落中传统文化受到现代的异质文明影响之后,藏族人精神无处可依的处境,《瞻对》在讲述瞻对两百年来的历史的同时,也描绘了这段绵长历史中康巴人独特的生存境况与强悍野性的民族性格,展现出康巴民族的生活史与精神史。从这些方面,我们可以看到阿来小说与拉美文学的精神融通之处。
其次,阿来对民族民间文化的重视与开掘,既有拉美文学对他的启示,更得益于欧美作家及其创作对他的影响。在这方面,拉美作家马尔克斯、阿斯图里亚斯,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美国作家托妮•莫里森等人给予他的影响尤其明显。
阿来曾说,“我的创作重视民间传统,就是受拉美文学作家的影响”④,“我准备写作自己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尘埃落定》的时候,就从马尔克斯、阿斯图里亚斯们学到了一个非常宝贵的东西……我自己得出的感受就是一方面不拒绝世界上最新文学思潮的洗礼,另一方面却深深地潜入民间,把藏族民间依然生动、依然流传不已的口传文学的因 素融入到小说世界的构建和营造”⑤。从他的小说创作中,可以看出这一创作理念及其 所受到的外来影响。比如《尘埃落定》就是以藏族民间传说为依托,来讲述末世土司的故事,《瞻对》在观照瞻对康巴藏族的生活时,既纳入有关贡布郎加的种种传说,又展 现了康巴人特殊的习俗,包括特定历史时期康巴人的“夹坝”风习,瞻对地区藏族人的 饮食习惯、居住习俗、丧葬习俗等。民间文化的开掘与展现不仅丰富了小说的内涵,也使阿来在创作中能够在现实世界与幻想世界间自由穿梭,获得艺术表达的自由。
在阿来的外国文学接受史中,卡尔维诺也是个不容忽视的人物。卡尔维诺是一位深受民间文学影响的意大利作家,在20世纪50年代,他曾花费大量心血搜集整理出《意大利童话》,获得巨大成功。阿来熟知卡尔维诺整理意大利童话的轶事,作为一名藏族作家,阿来也注重“从藏族民间口耳传承的神话、部族传说、家族传说、故事和寓言中吸收营养”,在他看来,“那些在乡野中流传于百姓口头的故事反而包含了更多的藏民族 原本的思维习惯与审美特征,包含了更多世界朴素而又深刻的看法”⑥。阿来坦言他创作的源泉是民间文化,阿坝的神秘文化和丰富传说给阿来带来了源源不断的创作灵感。“阿来一直试图在他的作品中,通过对藏族人的历史、传奇、生活点滴和悲欢离合的讲述,由点及面地展现了藏族地区近百年来的沧桑变迁。在他的笔下,无论是康巴土司,还是说唱艺人、藏族牧民,在这些鲜活的人物身上,既能看到藏族人的豪迈和血性,也有面对平淡生活的柔情和恬淡。”⑦
不过,相比于卡尔维诺,美国作家对阿来的影响更为巨大。阿来曾说:“对我影响最大的是美国文学,我主要关注美国文学的三个领域,一是黑人文学。黑人在美国算是异族,是美国的少数民族……第二个影响是犹太文学,犹太人在美国也是异族,当然也包括一些流亡作家,纳博科夫、米沃什,索尔•贝娄……第三是美国南方文学。代表当然是福克纳,还有南方女作家,奥•康纳尔。”⑧阿来之所以接受美国文学,主要是 “因为我长期生活其中的那个世界的地理特点与文化特性,使我对那些更完整地呈现出地域文化特性的作家给予更多的关注”⑨,而美国黑人文学、南方文学在阿来看来就是极具“地域文化特性”的文学。从创作实践来看,在民族民间文化的表达方面,美国黑人文学的代表作家托妮•莫里森对阿来的影响较为显著。阿来十分欣赏莫里森的作品,“认可黑人女作家托里•莫里森的《娇女》、《所罗门之歌》”⑩,在他的眼里,托妮•莫 里森的小说“艺术高超” “意旨深刻”,“揭示个别命运的同时也预示了人类普遍遭遇”⑪。阿来还说,美国犹太作家和包括托妮•莫里森在内的黑人作家给了他“更持久的影响与启发”⑫。
也许是因为与托妮•莫里森有着相似的身份(少数民族作家)和欣赏托妮•莫里森的创作,阿来的创作理念与作品都表现出与托妮•莫里森的精神契合,比如注重民间文学文化的创作理念及其创作实践就与托妮•莫里森的理念与创作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托妮•莫里森的小说注重吸纳黑人的民间故事与传说,她说:“《所罗门》可说是通过男人写人生的不同阶段,因此需要一种民间传说的格调。《沥青娃娃》也有传说意味,但比《所罗门》更直接,更大胆。”⑬托妮•莫里森的《所罗门之歌》穿插了众多的民间故 事、神话传说与歌谣,比如保存祖先遗骨的故事、黑人会飞的民间传说、民间歌谣《所罗门之歌》等,以此弘扬了黑人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表现了回归黑人文化传统的渴望。小说《柏油娃娃》(亦译《沥青娃娃》)以黑人民间故事“柏油娃”为基础,“柏油娃”讲的是狐狸欲抓住兔子饱餐,做了个柏油玩偶试图粘住兔子,而兔子机智逃脱的故事。莫里森对这个民间故事加以创造性改写,通过黑人青年桑(兔子)、脱离黑人文化的乔丁(柏油娃)的爱情故事及其和白人糖果大王(狐狸)之间的关系,来探索黑人文化和白人文化的关系,探讨了黑人如何摆脱白人的控制,保持自身的民族特色和种族文化的问题。从上述作品来看,神话和传说帮助莫里森重构了美国黑人的文化记忆,也为她的小说蒙上了一层神秘面纱。
阿来也深受民族文化的熏陶并自觉吸纳民族神话传说资源。如阿来的《格萨尔王》 以格萨尔的史诗为底本,从现代人的视角对格萨尔王的性格命运进行诠释,这部“重述神话”的小说可以说是阿来对本民族文化的一次致敬。小说《阿古顿巴》则是阿来直接根据藏族民间智者阿古顿巴的民间传说创作的。此外,小说《灵魂之舞》中索南班丹老人死前让灵魂自由行走,以体验嘉绒藏族的独特死亡方式——“要死的人让灵魂去经历一下过去的事情”。还有《蘑菇》中古老部族的祖先传说、《宝刀》中孽龙的故事、《尘埃落定》中的土司起源神话等,也都是阿来自觉开掘、利用民间文化资源的例证,这些作品将藏族民间文化中的神秘成分编织进现实的内容中,充分体现了阿来关注族群文化、“向民间学习”的创作理念。
值得注意的是,阿来对本民族的生活、文化的关注与展现并没有使他的创作走向“自我窄化”,相反,他在民族生活与文化的表达中寄寓了对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关切和对人与世界的一些普遍性问题的思考。正如马尔克斯用马孔多的历史来反映拉美大陆的历史、福克纳写美国南方乡镇生活又超越了南方一样,阿来的小说创作也抵达了外国文学大师们那种“以小见大”、由地方性写出世界性的创作境界。
二
阿来重视想象力,也注重在兼收并蓄中获得小说形式、手法的创新,对“魔幻”技法也有所尝试。阿来这方面的文学思想与创作追求也体现了他与外国作家、外国文学的某种精神联系。
想象力,是一个作家最基本的能力。阿来重视想象力,也欣赏那些富有想象力的外国作家,比如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阿来称他为“富于幻想的卡尔维诺”。在阿来看来,想象或者幻想是作家也是文学的可贵品质,“一个人所以要成为一个作家,绝非仅仅要对现实作一种简单的模仿,而是要依据恢弘的想象,在心灵空间中用文字建构起另外一个世界”⑭,曾几何时,中国文学因过于强调现实主义的真实性而排斥想象与幻想。对此,阿来深感重建中国文学的幻想传统的必要,但重建不仅涉及文学观念的变革和对纵向传统的继承的问题,还须放眼世界,海纳百川,兼收并蓄,所以阿来说:“中国文学幻想传统的重建,除了纵向的接续,还有大量的横向的比较,只有站在与世界对话的意义上,这种重建才是一种真正的重建。”⑮也就是说,文学不是在一个封闭的系统中繁荣起来的,文学的发展或者某种文学传统的发扬光大与重建,都离不开和世界文学的对话与交流。
实际上,无论是重建中国文学的幻想传统,还是作家个人的创新,都需要和世界文学进行对话与交流,都需要向他人学习。这是新时期作家的共识,也是阿来从马尔克斯等作家那里得到的启示。创新是文学的生命,也是每个作家孜孜以求的目标。相对于题材内容的创新,阿来更看重形式的创新,而要在文学形式上创新求变,就必须敞开心胸,向别人学习,马尔克斯等拉美作家给予阿来的启示就是“不拒绝世界上最新文学思潮的洗礼”⑯,所以阿来认为,不仅要学习本国作家,也要研究外国作家,从中获得宝贵的经验和创新的灵感,阿来指出,“我们常说的艺术敏感,对小说家来说,首先就是对小说形式要有一种敏感。其次,当然也要对别的小说家,就是那种在艺术创新上一直有很好能力的小说家,对他们的东西进行充分研究”,“国外小说它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些经验”。⑰由于注重对富有创新能力的中外作家的作品的研究,阿来为自己的每一篇小说寻找到了恰切的表达方式,比如短篇小说《鱼》围绕一次钓鱼的经历,主要从心理角度表现藏族传统文化中的禁忌对人的控制以及人对禁忌的反抗,像是一部心理小说,中篇小说《遥远的温泉》以诗意的笔墨来呈现自然的美和“我”对美好事物的向往与寻找,带有诗化小说的特征,长篇小说《空山》采用开放性的“花瓣式”结构,通过六个“既独立又相互联系”的中篇小说来呈现一个村庄的变迁史,它就像一幅富有想象力的拼图,多线索、多中心叙述了不同历史时期一个叫“机村”的藏族村落的历史变迁。与此同时,在《空山》中,散文、日记、诗歌、笔记、素描等多种文体的杂糅也体现出创新性特征。而长篇小说《瞻对》在文体上则以“非虚构”为艺术追求,以史料文献为基础,对康巴地区的瞻对近两百年的历史展开真实叙述,在讲述瞻对的故事时,时常采用多角度交替叙述的方式,使得瞻对的人与事显得立体多姿。可以说,阿来的每一篇小说几乎都有各自不同的写法与艺术风采。从上述作品可看出阿来在多方学习他人(包括外国作家)的创作经验后在小说艺术上的成熟和匠心独运。
阿来重视中国文学的幻想传统,在创作手法上,阿来也曾借鉴、接纳拉美的“魔 幻”技法。阿来坦言,“我读过很多魔幻现实主义作品及其理论”⑱,魔幻现实主义对他产生影响似乎也顺理成章。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不仅植根于民族的历史与文化,在艺术手法上也有着鲜明的特征,其中之一便是“打破了生与死,人与鬼的界限”和“鬼魂出现”⑲。比如《百年孤独》中有普鲁邓希奥•阿基拉尔与布恩迪亚的人鬼情缘;《佩德 罗•巴拉莫》中普雷西亚多进入的科马拉村是个充斥着鬼魂的村庄,一个鬼魂到处游荡、幽灵窃窃私语的神秘世界,《幽灵之家》中克拉腊活着时可以和鬼魂交往,死后则可以和生者往来,她的幽魂不时出现在亲人身边……魔幻现实主义的这一打破人与鬼、生与死之界限的手法在中国新时期作家的小说中被大量借鉴使用,在阿来的小说中也较为常见。在阿来看来,魔幻现实主义的成功,就在于找到了与本土文化相匹配的文学样式和手法。阿来也找到了用来表现不无神秘色彩的藏族文化的一个技法,那就是打破生死界限、人鬼界限或人神界限的“魔幻”技法。考察阿来的小说可以发现,魔幻技法时有运用。《旧年的血迹》写彩芹的父亲开小差被枪毙,其后父亲的鬼魂夜夜骑马回家, 《月光里的银匠》中的活佛则是个神一般先知先觉的人,他能够凭借超凡的神力和作法仪式知道银匠的远方主子——老土司已死的事实,《尘埃落定》中,神魔鬼怪也可以参与活人的争战,当麦其土司与汪波土司之间爆发罂粟花战争时,双方的喇嘛、神巫们设坛作法,邀集神灵与魔鬼,驱使风雨雷电打击对方,《空山》中,格拉死去后形散神不散,幽魂还在林子里捕猎,还在等待尘世里猜忌与仇恨的消失……这些神秘诡异的人与事,无不带给我们魔幻般的感受。在上述作品中,阿来“以魔幻现实主义为表达方法, 建构了一个复杂而又神奇的文学世界”⑳,这些打破生与死、人与鬼、人与神界限的描写把现实的事物与非现实的事物交织在一起,虽然神神鬼鬼,但并没有抛弃现实,而是以鬼神事写人事、观现实,使小说在凸显现实精神的同时获得了亦虚亦实、亦真亦幻的艺术效果,正如茅盾文学奖评委严家炎在《尘埃落定》的评语中所说的那样,“轻淡的一层魔幻色彩增强了艺术表现开合的力度”㉑。
三
从人物形象的塑造来看,阿来的小说也不乏受外国文学影响的例子。在阿来的小说中,有两个重要的人物形象,一个是《尘埃落定》中的傻子二少爷,一个是《空山》中行为“另类”的书痴达瑟。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两个形象的塑造是中外文学影响的结果。
从与本土文学形象的精神联系看,《尘埃落定》中的傻子是个有深刻寓意的人物,他似傻非傻,在他身上既有着藏族民间智者阿古顿巴的影子,也与鲁迅《狂人日记》中的狂人有某种相似之处。阿来指出,《尘埃落定》之所以着意塑造傻子二少爷形象,“这也许就是受像阿古登巴这样智慧的‘笨办法’的影响”㉒,两相对照,我们不难发现: 傻子二少爷和藏族民间智者阿古顿巴一样从来没有复杂的计谋和深奥的盘算,他具有淳朴的智慧,并常常在出其不意中战胜狡猾的对手。也有论者将傻子二少爷形象与鲁迅笔下的狂人形象相提并论㉓,鲁迅《狂人日记》中的狂人一方面确实有着“迫害妄想”的种种症状,另一方面又是那个世界看现实最清醒的人。《尘埃落定》中的傻子二少爷也是如此,一方面傻里傻气,另一方面又时有大智慧显现。傻子二少爷是麦其土司酒后所生,所以免不了痴傻与慈拙,他生下来后一个月不会笑,“两个月任何人都不能使我的双眼对人和事做出反应”他每天早晨起来必然要问的两个问题是“我是谁”“我在哪里”;他满官寨地找人打他,为的是验证被仇恨自己的人打会不会感到痛。但有时他又是一个超常聪明的人,身上常常有灵光闪现:他命令卓玛在饥民面前炒麦子并施舍给饥民,以一片仁慈之心为麦其家赢得了新臣民,他娶了最漂亮的女人塔娜做妻子,并在北方边境建立贸易市场,与别的土司和汉人进行贸易往来,获得了巨大的利润。傻子二少爷还有先知先觉的特性,他能预先知道客人的到来,知道父亲派哥哥和他去南北边境的真实意图,也早早预知了土司末日的到来。傻子二少爷那种既疯傻又理智、大智若愚的精神特质,无疑与狂人、阿古顿巴等形象有着某种相似之处。
而从与外国文学的联系来看,阿来以傻子做主人公,也离不开福克纳《喧哗与骚 动》的启示,这也是人们常常把《尘埃落定》中傻子二少爷形象与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中的白痴班吉形象相联系的原因。美国作家福克纳对中国作家的影响是巨大的,莫言、阎连科等作家都曾坦言自己对故乡的书写无不受到福克纳执着书写“邮票那样大小的故乡”的启发。福克纳的名作《喧哗与骚动》也对一些中国作家的创作产生了具体的 影响,其影响之一就是,在中国作家的小说文本中也出现了类似于班吉的人物,比如韩少功《爸爸爸》中的白痴丙崽、阿来《尘埃落定》中的傻子二少爷、贾平凹《秦腔》中疯疯癫癫的引生,等等。阿来阅读了不少福克纳的作品,包括《喧哗与骚动》《我弥留之际》以及一些中短篇小说,他说,福克纳的小说非常棒,“像美国蓝调那样有力,自由而悲伤,我非常喜欢”,还说福克纳“教会了我如何描绘与表达苦难”㉔。
如果把《尘埃落定》中的傻子二少爷与《喧哗与骚动》中的班吉比较,可以发现二 者的相似之处。一是他们的智力都存在着缺陷,班吉尽管33岁了,智力却相当于3岁孩童,他的意识混乱无逻辑,语言含糊不清,行为表现像一个孩童;傻子二少爷出生很 久都不会笑,13岁才开始记事,心智也不成熟,在对事物的认知判断有欠缺,比如他成年了才知道女人有漂亮和不漂亮的区别,他还丢掉了松巴头人献上的能治好他的灵药,做了命该如此的傻子。二是他们在傻的同时都有超凡的一面,比如班吉有超常的嗅觉,能闻到铁门“冷的气味”,闻到死亡的气味,闻到姐姐凯蒂的失贞。他也有一定的感情,喜欢有“树一样的香味”的姐姐凯蒂,对姐姐十分依赖,凯蒂离开家后,班吉拿着凯蒂的脏拖鞋或是看着炉火来怀念姐姐。傻子二少爷也有超常的感知能力和预言能力,他还干了几件聪明事,比如在北方边境建立贸易市场,制服拉雪巴土司,等等。只不过,班吉是真傻,而傻子二少爷是似傻非傻。
而从傻子形象的功能作用来看,《尘埃落定》《喧哗与骚动》也有相似之处。首先, 在《喧哗与骚动》中,福克纳借助白痴班吉的形象及其意识流动,对南方世家康普生家族的衰落史进行了展示,《尘埃落定》也借助傻子形象讲述了麦其土司家的故事和土司制度的衰落。其次,两部小说都以傻子作为叙述者,使得作者“可以超越现实逻辑,可以把生活现实的逻辑全部打乱进行重组,拼贴出离奇的、怪诞的或许是本真的生活”㉕。当然,阿来笔下的傻子形象也有着阿来的独创性,在小说中,傻子既是历史的见证人,又是预言家和无奈的殉葬者,其形象内涵更加丰富复杂。阿来以傻子作为故事的叙述者和亲历者,既有利于展现藏地的神奇,也使小说染上了魔幻色彩。
如果说阿来与他经常提到的福克纳产生了精神遇合,成功构造出傻子二少爷的形象的话,《空山》中的达瑟形象则是卡尔维诺对阿来产生影响的结果。阿来说,《空山》的主要内容是“写值得一说的人与事”㉖,达瑟就是其中值得一说的人之一。喜欢住在树上的达瑟是《空山》中一个重要的人物,阿来塑造这一形象的灵感显然来自卡尔维诺的 《树上的男爵》。阿来虽然很少公开提到或赞美卡尔维诺,但他熟悉卡尔维诺并受其影响,却是事实。他笔下的达瑟就让人联想到卡尔维诺《树上的男爵》中的柯希莫。
《树上的男爵》中12岁的柯希莫因为与家人发生争执,一气之下爬到了树上,从此,在树上生活了一辈子。柯希莫的选择既带有青春期的叛逆意味,也体现出他对庸常生活的拒绝与逃离。柯希莫是个有着独立思想的人,在他看来,要看清地面上的生活就要和它保持距离,所以他选择了树上的生活。但他并不因此把自己与人世相隔绝,他“待在树上听树下的神父讲课”,在树上看人们干活,“并询问肥料和种子的情况”,当他独自在森林里转悠时,结识了一些到森林里安身的烧炭工、锅匠、玻璃工,还有因饥荒而拖家带口、背井离乡的人。父亲死后,柯希莫继承了爵位,但“他的生活没有改变”, 他在树上经管着家里的产业,在树上与田庄管家和佃户见面,当他的妈妈生病后,“柯希莫留在树上守护她,树上挂一盏小灯,使她能够在黑暗中看见他”。他在树上读书、 打猎,与女人谈情说爱也在树上,是个名副其实的“树上的男爵”。
受“树上的男爵”的奇特形象的启迪,阿来在《空山》中也描绘了一个喜欢生活在树上的书痴达瑟。阿来作品中的主人公“时常给人一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孤独感”㉗, 达瑟就是这样一个独醒者。达瑟在机村最初是一个辍学的人,后来接到在外做官的叔叔的来信,得以去州里的民族干部学校上学,但他还是未能完成学业。当时,达瑟碰巧捡到了一本植物图谱,他从那一刻起爱上了书,中了书本的魔法,于是他连续几天都去图书馆,收捡了十几箱书。之后达瑟离开令人羡慕的干部学校,带着一马车的书回到了机村,开始了在树上看书的生活。达瑟一直守护着这些书,守护着知识和文化。他向村民们解释什么是“胳驼”,什么是“杠杆原理”,自己也写了一本关于植物学的书。达瑟希望别人也相信书上的知识,因为书中的知识能让人洞悉世界某一角落的生存规律,学会尊重自然规律。这些书给他带来了满足感,但当好朋友达戈死去,达瑟的树屋也被索波带人拆毁后,达瑟觉得了无生趣,变得爱喝酒,爱骂人,那个过去沉默寡言的读书人最终变成了浪荡不羁的酒鬼和等死的行尸走肉。
无论是上树以后一生再未落地的柯希莫,还是时而待在树屋读书,时而行走在机村的达瑟,都同样热爱大地和人间:柯希莫在树上依然关注着世人的生活,并多次帮助人们摆脱困境;达瑟关注着机村的一切,他用知识作导引,思考、感悟着世事,他为机村人滥杀猴群、砍伐森林而痛心,也从机村遭遇的泥石流看到了大自然的惩罚。虽然达瑟与柯希莫都被视为另类的“怪人”,但其实他们才是纯真并坚守着初心的人。
上述分析表明,阿来笔下的傻子二少爷形象和达瑟形象的塑造及其傻子叙述视角的采用,的确带有外国文学影响的痕迹,他们和《喧哗与骚动》中的白痴班吉、《树上的 男爵》中的柯希莫均有着某种相似之处,但又绝不是对福克纳和卡尔维诺笔下人物的复制,而是鲜明地体现了阿来在借鉴中的生发与创造。
总之,阿来所选择、接受的外国文学主要来自两大板块——拉美文学和欧美文学, 阿来对外国文学的择取和接受有自己的喜好和审美标准,尤其着迷于那些既有本土性又有世界性的文学作品。阿来对外国文学的接受不是为了复制某一外国文学作品,而是广采博览,强大自我,找到自身的文学路径。阿来所受的外国文学的影响也是丰富、复杂的,既有显在的影响如傻子、达瑟形象塑造上的影响和魔幻技法上的影响等,又有潜在的对创作理念、文学思想和创作追求的影响,这些影响的来源有时是单一的,有时则是多元混杂的。阿来对外国文学的择取与接受,其积极意义毋庸置疑,在当今全球化的语 境下,开放视野、向外学习借鉴对一个作家来说特别重要,事实上,也只有虚心学习外国作家的创作经验,在相互交流、取长补短、兼收并蓄的基础上写出的作品,才有与不同国度、不同族群对话的可能性。
注释:
①阿来、吴道毅:《文学是温暖人心的东西》,《上海文学》2014年第9期。
②阿来、吴道毅:《文学是温暖人心的东西》,《上海文学》2014年第9期。
③张杰:《阿来:不应把马尔克斯简化为一本书》,《华西都市报》2014年第9期。
④阿来、吴道毅:《文学是温暖人心的东西》,《上海文学》2014年第9期。
⑤阿来:《我只感到世界扑面而来——在渤海大学“小说家讲坛”上的讲演》,《当代作家评论》2009年第1期。
⑥吴怀尧:《阿来:文学即宗教》,《延安文学》2009年第3期。
⑦《阿来:读懂藏族人的眼神》,国际在线2010年4月13日,http://gb.cri.cn/27824/2010/04/13/110s2815915.htm。
⑧吴怀尧:《阿来:文学即宗教》,《延安文学》2009年第3期。
⑨阿来:《穿行于多样化的文化之间》,《中国民族》2001年第6期。
⑩ 冉云飞、阿来:《通往可能之路——与藏族作家阿来谈话录》,《西南民族大学学报》1999年第5期。
⑪阿来:《局限下的写作》,《当代文坛》2007年第3期。
⑫阿来:《我只感到世界扑面而来——在渤海大学“小说家讲坛”上的讲演》,《当代作家评论》2009年第1期。
⑬〔美〕查尔斯•鲁阿斯:《托尼• 莫里森访谈录(二)》,斯默译,《外国文学动态》1994年第2期。
⑭阿来:《民间传统帮助我们复活想象》,《看见》(阿来散文集),湖南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205页。
⑮阿来:《重建文学的幻想传统》,《新闻晨报》2010年9月13日。
⑯阿来:《我只感到世界扑面而来——在渤海大学“小说家讲坛”上的讲演》,《当代作家评论》2009年第1期。
⑰姚霏、符二:《阿来:文学的高贵在于优雅》,《春城晚报》2013年3月13日。
⑱卫玮:《以美学为信仰——河北青年作家与阿来对话》,《文艺报》2014年8月6日。
⑲参见陈光孚:《魔幻现实主义》,花城出版社1986年版,第68、96页。
⑳权绘锦、李骁晋:《魔幻现实主义的西藏本土化表达——兼论阿来小说中的神秘叙事》,《北方文学(下旬刊)》2014年第5期。
㉑《第五届茅盾文学奖评委会委托部分评委撰写的获奖作品评语》,《文艺报》2000年11月11日。
㉒冉云飞、阿来:《通往可能之路——与藏族作家阿来谈话录》,《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99年第5期。
㉓参见贺绍俊:《说傻•说悟•说游——读阿来的〈尘埃落定〉》,《当代作家评论》1998年第4期。
㉔吴怀尧:《阿来:文学即宗教》,《延安文学》2009年第3期。
㉕陈晓明:《当代文学主潮》,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27页。
㉖吴怀尧:《阿来:文学即宗教》,《延安文学》2009年第3期。
㉗吴怀尧:《阿来:文学即宗教》,《延安文学》2009年第3期。
原刊于《阿来研究》第14辑

曾利君,女,文学博士,重庆合川人。西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现当代文学教研室主任。中国老舍研究会理事,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理事,重庆市现当代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重庆市比较文学学会理事。已出版专著4部,在《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学术月刊》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项、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2项,主研或参研国家级重大项目、省部级项目共5项。

阿来,藏族,1959年生于四川阿坝藏区。四川省作家协会主席。著有诗集《棱磨河》,小说集《旧年的血迹》 《月光下的银匠》《蘑菇圈》,长篇小说《尘埃落定》《空山》《格萨尔王》《云中记》,非虚构作品《瞻对》《大地的阶梯》,散文集《大地的语言》等。曾获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