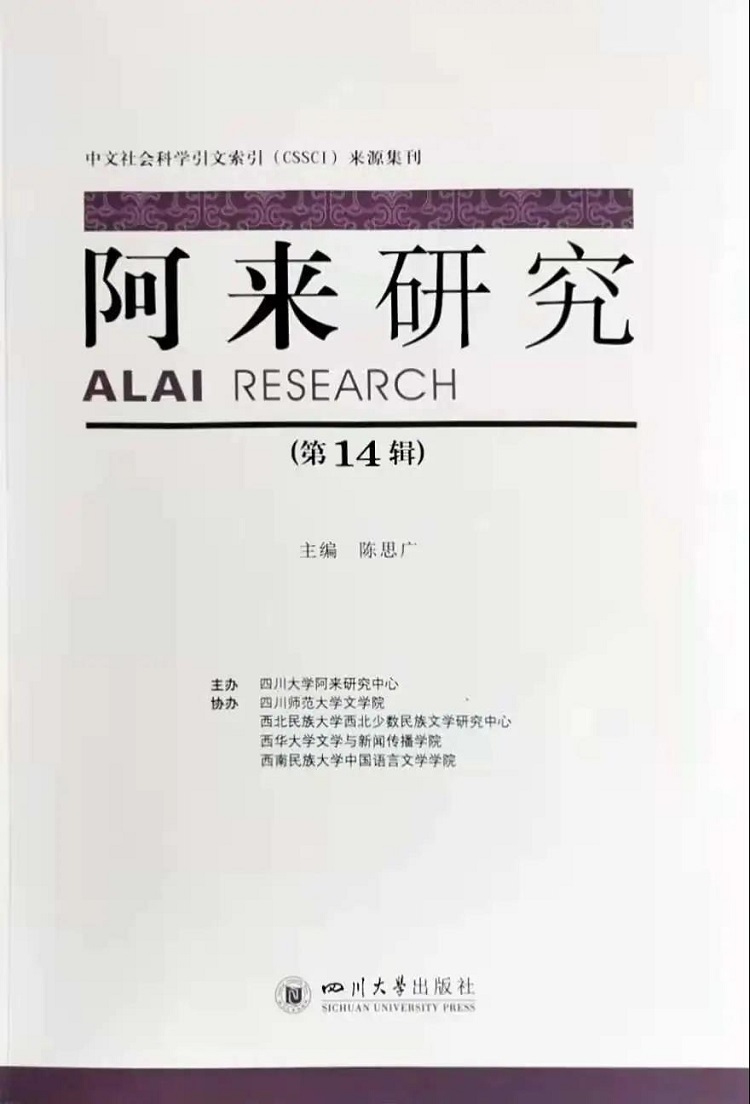
从阿来的作品《尘埃落定》《蘑菇圈》《三只虫草》《河上柏影》《空山》以 及2019年出版的《云中记》来看,现代性一直是阿来深切关注的问题。在阿来以往的创作中,时空总是以传统社会的封闭与现代社会的开放之间的对比来呈现的。而在《云中记》中,阿来呈现了传统社会、现代社会、神性世界三个不同的时空,各种时空“相互渗透,可以共处,可以交错,可以接续,可以相互比照,互相对立,或者处于更为复杂的相互关系之中”。阿来既沿袭以往对古老社会和现代世界所代表的两个不同时空相互碰撞的书写,又建构了一个 勾连过去、现在、未来的神性世界。他用永恒的神性世界弥合前两个时空的断裂,并以此探讨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以及现代社会中传统的出路。在这个过程中,阿来表现出对传统与现代共融的尝试与努力,表达了对人性至善至美力量的信任。这是阿来发出的新声音。
一、传统的消逝与温情的怀念
在传统社会中,人们由于封闭、内敛的生活而对土地产生了强烈的共依存感,这种共依存使得人们形成了“生于斯,死于斯”“重死而不远徙”的重土观念,同时也就不可避免地“被安静地束缚在一片固定的土地上,人们根据这片土地确定自己的认同,确定自己的语言、风俗和起源。没有人、没有权力机构、没有内心要求也没有外在动力促使他们流动,促使不同土地上的人彼此之间交流,促使它们发生戏剧性的变化和运动”。久而久之,传统社会便形成了以静止、封闭为主要特征的时空形态。村落的封闭空间以及原始的生活方式作为传统社会的符号表征不断得到文学书写。
首先是封闭的村落空间。胡彬彬等人在《中国传统村落蓝皮书》中指出, 传统村落是“中国古代先民在农耕文明进程中,在族群部落的基础模式上,因 ‘聚族而居的生产生活需求而建造的、具有相当规模、相对稳定的基本社会单元” 。由此观之,村落是传统社会的产物。阿来在创作的过程中始终将自己的视野放在对村庄的书写之中。从《旧年的血迹》《永远的嘎洛》等中短篇小说中的 “色尔古村”,到《机村史诗》六部曲和短篇小说《蘑菇圈》中的“机村”,到《尘埃落定》中的“土司官寨”、《河上柏影》中的“老家”以及新作《云中记》中的“云中村”, 阿来一直以村庄作为叙述视角来展现传统社会的面貌特征。正因为村庄的空间形态已成为传统社会的符号表征,被作为指代传统社会的场域而不断出现,所以云中村空间书写的背后是对传统社会的暗喻。作为传统社会的“村庄”带着封闭和静止的特点,活动在这一块土地上的人们对世界、对自我本体的认识仅仅局限在村庄的狭小范围内。正如阿来自己小时候被地质队员的一张航拍图震撼一样,以这个村庄为中心的人们还不知构成自己全部童年世界和大部分少年世界的那个以一个村庄为中心的“广大”世界其实非常渺小,人们在鲜少与外界交流的过程中过着相对不变和静止的生活。
其次是原始的生活方式及其意象。传统社会的生活方式以简单生产、手工劳作为主要特征。在《云中记》中云中村的人们使用石磨坊磨面,使用火把照明,骑马出行,利用自然界便于获取的资源满足基本的生活需求——抹的头油是动物的脂油,喝的水是山后的泉水。文本中出现的意象如马、火等将传统社会具象地呈现出来。
《云中记》中,伴随阿巴重返云中村的两匹马贯穿整个文本的叙述,使我们不能不对它们加以注意。在云中村甚至整个瓦约乡,很久之前就没有马了,现代化的拖拉机、 卡车等交通工具代替了原始的动物劳力。两匹马向云中村走去,实则是阿巴向传统社会的缓缓回归。阿来在《尘埃落定》《格萨尔王》《行刑人尔伊》《奥达的马队》等多部作品中都书写了传统社会中的日常事物——马,马作为一种主要的交通工具而成为表征传统的符号。试想今天若是有谁再骑马出行,定会成为一个奇异的景象而被围观吧。
《云中记》书写了阿巴取火、用火的行为。在祭祀山神的时候,阿巴从腰间悬挂的麂皮点火包中拿出一块石英石,然后他用一块弯月状的铁片使劲剐擦那块石英石。阳光过于强烈,火没有点着。阿巴转过身,用自己的身体挡住阳光,再次用铁片剐擦石英石的表面。这次,他看到火星飞溅起来,火点着了。《韩非子•五蠹》中有这样的记载::“上古之世……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说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可见阿巴采用的取火方式是原始的。同时,阿巴还使用火把照明,生火做饭。借用文本中仁钦的话来说,阿巴真真正正回到了火所代表的石器时代。
逝去的传统社会是在阿巴从移民村回到云中村重新践行传统生活方式的过程中呈现出来的。在这个过程中,阿巴的生活在时间之流中得以显现。在传统的生活中,时间呈现出循环往复、周而复始的特点。阿巴重返云中村,从第一天起,便随着日升日落而作息。第二天、第三天以至几个月之后,文本都是从阿巴醒来开始叙述。每一天太阳的升起是阿巴开始活动的信号,同时阿巴也依据植物的荣枯得知季节的更替。到了云中村滑落的那一天,生活结束了,阿巴的生命也终结了,不再迎来崭新的一天。阿来总是在深切的怀念中构建这样一个即将要消亡的过去时空,他的其他作品也是如此。在《空山》中,这个饱受变化之苦的机村最终以所有人的搬离、乡村的消失为结局,所有复现传统的尝试都被现实打败。在《蘑菇圈》中阿妈斯炯最后对她的蘑菇圈的消失的悲切诉说,隐喻的便是传统社会走向消亡的悲歌。在《河上柏影》中王泽周所在的村庄以及父辈辛 苦建造的房子,还有濒危的岷江柏,都随着现代化的推进而走向消亡。
二、现代的发展与人性的异化
相比于传统社会循环往复的时间,现代社会的时间是一条单向度的射线,具有明确的方向,它有始有终,始于过去,穿越现在,奔向未来。在人们对时间均匀而精确的把控中,过去、现在、未来呈现出清晰的演进脉络。因此,现代社会的线性时间观决定了现代社会以发展进化、求新求变为主要特征的社会形态。现代社会的发展日新月异,工业文明推动了生产力、生产方式的飞跃,人们的生活方式随之发生巨大改变。但是,现代社会的精神发展却没有呈现与物质发展同步的态势。人们深受拜物教、消费主义、拜金主义的毒害,丧失了心灵的清醒。现代社会的发展模式代表的是人类社会的希望,还是发展的陷阱?阿来通过现代社会的构建来表达自己对现代化进程的认识。
现代社会是一个物质文明不断进步与发展的时空。在《云中记》中,阿来书写了水电站、电视、汽车、无人机等一些依靠科学而产生的代表先进生产力的事物。一方面, 阿来通过这些意象来巧妙区分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另一方面,阿来也通过这些意象体 现着社会不断进步与发展的趋势。纵观阿来的众多作品,类似的意象符号同样存在,如在《机村史诗》中出现的拖拉机、脱粒机、电话等。无疑,正是这些事物的出现增进了当地与外界的联系,打破了以往的封闭性,使传统社会逐步转化为现代社会。
《云中记》中也出现了工厂、超市、天然气、自来水、洗发水等现代生活的意象。这些碎片化的现代要素呈现了人们生活的巨变。人们做饭不再生火,而是使用天然气; 喝水不再沿溪而饮,家家户户接上了自来水;不再家家事农桑,而是进入工厂上班;不再自给自足,而是去超市购物。人们生活在一个极度便利的工业文明时代,同时我们不禁想起阿来在《大地的阶梯》中所引利奥波德的一句话:“人们在不拥有一个农场的情况下,会有两种精神上的危险,一个是以为早饭来自杂货铺,另一个是认为热量来自火炉。”诚然,杂货铺的早饭与火炉的热量带来的便捷与舒适是毋庸置疑的,但是离开了传统土地的人们在迷醉于物质时,再来审视一下自身精神是否丰盈,怕是会感到难堪吧。
阿来说他从不持有一种文化保守主义的立场,相反,他对现代化进程不是抵制而是肯定的。他正视现代化给人们带来的好处以及它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但是他更要去体现在这样一个过程人们发生的改变与付出的代价。在现代化进程的辐射下,乡村原有的经验早已断裂,“当全球化的进程日益深化时,这个世界就不允许有封闭的经济与文化体存在了。于是,那些曾经在封闭环境中独立的文化体缓慢的自我演进就中止了。从此,外部世界给他们许多的教导与指点,他们真的就拼命加快脚步,竭力要跟上这个世 界前进的步伐。正是这种追赶让他们失去自己的方式与文化”。现代社会以“新”为 衡量的尺度。在云中村,人们在现代化的冲击下认为凡是新的就是进步的,云中村古老的一切都是落后的、赶不上时代潮流的。人们盲目追赶,想要走在前面,成为进步的代表,但也为此付出代价阿巴的父亲因为修机耕道而被炸死,水电站滑坡使阿巴失去记忆。村民搬迁到发展更为迅速、更加开放的移民村,现代化进程迅速推进,新的事物代替了所有旧的存在,然而,正如阿多诺所言,“新之真理,未受侵犯者之真理,处于意图的缺席之中”。“新”无疑成为整个现代社会的标准,却造成了人们与传统越来越深的决裂,使得传统社会中人们长期以来的观念和见解难以为继。
人们的精神世界呈现出焦虑、空虚,甚至被异化的境况。在移民村新出生的孩子已经不会再讲云中村的语言了,人们敬神的心也慢慢淡化。人们供奉祖师的画像前不允许点长明灯,因为长明灯容易引起火灾。古老的文化与信仰在现代的禁令下不断消失。人们只是一味趋利,追求金钱:农家乐敲诈游客,一份极其普通的野菜鹿耳韭被卖到了200元的高价,中祥巴返乡,提出要建设家乡,发展热气球旅游项目,可是却利用灾后云中村的废墟景色,计划直播云中村的消失,以村落的灾难作为观赏噱头,央金姑娘时隔四年重返云中村,却是由公司操纵的悲情表演,借灾难博取同情,获取利益。在《机村史诗》中人们为了利益而残杀山上的猎物,甚至不惜违背千年来与猴群和平共存的约 定,大开杀戒。《蘑菇圈》中人们为了追求松茸的高利益,在松茸还没长成时便开始大肆采摘,丹雅甚至偷偷在阿妈斯炯身上安装了摄像头以展览“生态蘑菇”的生长环境,达到炒作的目的。《三只虫草》《河上柏影》中人们对虫草和岷江柏的掠夺同样如此。在现代社会中,人们陷入了异化的巨大漩涡而难以挣脱。
三、神性的救赎与精神的觉醒
狄尔泰认为神性世界体现为有宗教信仰的人们“在与不可见世界的交往中寻求最高 的和绝对有效的生命价值,从这种交往的不可见的对象中寻求绝对有效的最高的效应价值,从中寻求一切幸福和喜悦”。换句话说,神性世界是一个不可见的世界,人们在信仰它的过程中实现了对真善美的精神追求。神性世界在传统社会中普遍存在,随着社会的发展,其领域逐渐缩小,在现代社会中神性世界被视作科学的对立物而遭受排斥,神性逐渐被理性与科学所遮蔽。
但在《云中记》里,有神性的苏醒。在过去,阿巴是一名发电员。在水电站滑坡的事故中,他失去了记忆,过着懵懵懂懂的生活。几年之后,他又因为电的震撼而醒来,但这只是肉体上的唤醒,只是让他恢复了过去的记忆。他真正意义上的顿悟来自老喇嘛 手中清澈的泉水。在《新约》中,基督徒只有受洗之后,才算真正进入了教会,印度教认为,人一生之中必须要有一次用恒河之水洗涤自我、洗净罪恶,在佛教中,观世音菩萨手托柳枝净瓶,点化众生。在宗教中,水常常能够洗涤人肉体与灵魂的双重罪恶。喇 嘛用清水洗涤了阿巴尘世的脏垢,让他得以净化,唤醒了他身上的神性。
神性世界不是外部世界的具体呈现,而是在人的心灵中经过长久磨砺才形成的。阿巴身上的神性苏醒之后,他依旧沿着不可逆的时间轨迹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从云中村到移民村的过程中,他越来越坚定地信仰那个有鬼魂存在的世界。对阿巴而言,时间具有了“无时间性”,达到了静止的永恒。于是,他按照四年前地震的时间进行安魂仪式;又按照四年前约定的时间祭祀山神。同时,阿巴重返云中村,实际上是回归那个万物有灵的不可见的神性世界。
对于阿巴这些信仰苯教的人来说,他们意识中主观的存在即为客观的、真实的东西。他们相信人死了,肉体消失,灵魂尚存。地震中丧生的人,他们的鬼魂还在村庄里四处飘荡,无人照顾。正因为如此,独自回到云中村的阿巴并不孤单,他和这些鬼魂对话,告诉他们“我回来了”。他要让鬼魂听到他的声音,给他们投放粮食,让他们不再孤零,真正得以安宁。同时他怀着悲悯,对所有的人都一视同仁。不管这户人家生前的善恶如何,也不管是什么民族,他都予以安抚。这是他神性的显现,宽容而仁慈。阿巴对待鬼魂如此,对待生活中的其他生命也是如此。
神对生命充满了平等的博爱。对阿巴而言,万物有灵,自然界的一切都有生命。他和花草树木对话,亲切地关爱它们。在祭祀的时候,他将枸子网状的枝条移到一边,不想烫着它们。对人们眼中的禁忌之物——罂粟,阿巴一样没有差别。在很久之前,云中村的鹿群就消失了,但是阿巴回来后,鹿群重新出现,它们与阿巴和两匹马融洽地生活着,阿巴并没有想杀死它们去获得物质回报。阿巴让生命自在地生长与凋零,其中也包括他自己。在这个过程中,他超越了有限而短暂的生命,获得了无限与永恒的新生。他没有对死亡的恐惧,他甚至预演死亡,让死亡早日来临,同那些鬼魂一起上路。对阿巴而言,死亡只是获得新生的必经之路,他将以另一种方式达到永恒。
“神性不是对人性的否定,而是人性中最高尚、最通神、最接近神的位置、并放射光辉的那个部分。”阿巴身上的神性苏醒的时候,他身上人性的光芒也相伴而生,合而为一。在对鬼魂履职以及对生命宽宥的过程中,他拥有的真善美的品质使得他对死去的魂灵充满悲悯:他包容了央金回到云中村的表演,把自己在移民村的房子留给了她,对中祥巴的热气球表演也不再计较。阿巴获得了精神的丰盈,他身上散发出的人性光芒打动了那些迷途的人,让他们幡然醒悟。央金离开舞台,回到移民村,中祥巴放弃了直播云中村消失的热气球表演。阿巴最终用神性完成了对沉沦之人的救赎。沈从文在《烛虚》中说“神存在于生命本体”,神性是以美与爱为内质的人性。神性的回归能够让沉 沦的人重新“神智清明,灵魂放光,恢复情感中业已失去甚久之哀乐弹性”,它,让人的精神觉醒。
四、传统与现代的关系
阿来在《云中记》中呈现了传统社会、现代社会、神性世界三个不同的时空,用饱含深情的笔触书写了阿巴在不同时空的体验。这种文化体验,不仅仅属于阿巴个人,更属于藏族人民以及身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每个人。通过三个时空的建构,小说表达了对传统与现代社会关系的深刻思考。
(一) 传统与现代的对抗
现代社会在制度、观念、文化、科技等方面呈现出同传统社会的对立性,甚而有人说现代就是作为传统的敌对方而存在的。“长期以来,人们始终将‘传统的’和‘现代的’对立起来,更不用说现代性或现代主义了 :凡‘现代的’就是与‘传统的’决裂, 凡‘传统的’便是对‘现代的’拒斥。”阿来认为,在少数民族地区,包括在汉族的相对落后和偏远的乡村,“走向现代性的进程不是一个主动追求的过程,始终都是外部强加给它们的,它们自己并没有这种自觉和主动,它的现代性的完成是被迫驱动的”。阿来在书写藏族乡村这种被动的现代性的过程中,表现出对传统与现代的对抗关系的思考。
其他作家在写到少数民族生活时也会流露出对被强加的现代性的忧思。迟子建在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中写了最后一个萨满的消失,写了现代性冲击下人们离开千百年 来赖以生存的家园,走向现代化的城市。扎西达娃在小说《西藏,隐秘岁月》《朝佛》《地脂》等作品中书写了传统生活在现代入侵过程中的分崩离析。在《空山》中阿来也展现了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某种断裂。在金钱的诱惑面前,人们大肆伤害动物,破坏自然。《云中记》在书写物质生活断裂的同时也呈现了藏族人民精神生活的伤痕。地震发生后,云中村人死伤无数,巨大的心灵苦痛围绕着人们。现代强大的救援力量拯救了人们的生命,却无法治愈人们的心灵,是阿巴安抚鬼魂的仪式让人们回归正常生活。阿巴把自己做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补助金捐给孩子们时,他认为那是政府给山神的钱, 孩子们应感谢山神。云中村处于滑坡体上,不久要随山体滑坡而消失,政府动员村民相信科学,集体搬迁。人们最初说不认识那个“科学”,最终又同意集体搬迁,人们发出了“山神抛弃了他们,阿吾塔毗抛弃了他们”的哭喊。在《三只虫草》中人们对现代生活的事物充满迷惑,不懂电视剧里的消费购物,疑惑虫草到底是三十块钱还是生命,最终人们向他们信赖的山神寻求答案,他们认为“山神有一千只一万只眼睛,山神什么都能看见”。人们在现代化进程中依旧遵循着过去的思维逻辑,用过去的信仰与观念解释他们面对的未知。在这个过程中,传统与现代从未达成融合,只是各自在彼此的系统里迎着时代的洪流奔跑。
(二) 传统与现代的共融
在《云中记》中,阿来尝试从文化层面对断裂的传统与现代关系进行弥合,这种尝试通过阿巴与余博士的多次对话来显现。阿来借用文本中两个人物的口吻来表达自己对传统与现代关系的理解:余博士是科学理性的代表,阿巴是传统文化的象征,双方运用彼此的知识系统来阐释对世界的认识。余博士没有像洛伍一样对阿巴回村安抚鬼魂加以指责,没有对阿巴进行现代思想的强行灌输,而是在尊重的基础上平等交流。正是因为相互的包容与接纳,余博士对阿巴的文化系统有了深刻的认识,而同时阿巴也对科学有了客观的认识。当阿巴发出感叹“科学和神一样,一点不可怜人”时,余博士告诉阿巴,科学可以让人们少受些灾难。受余博士影响,阿巴在坚守自己文化信仰的同时,对科学充满了希望,他对云丹说,要对科学有信心。科学的阐释在某种程度上是能够被传统文化的理解与接受的,而传统文化的阐释又在一定程度上给极度理性的现代社会注入了诗意和希望。传统与现代可以从对抗转向共融,传统文化可以尝试以再生的方式破解与现代断裂的难题。
在《云中记》中,传统与现代共融共生,产生独特的力量。这种力量表现在人性的 温暖与光芒中。阿来说:“现代文明只是让人醒来,但不足以获得智慧,只有在获得传统的加持中,人才可以得到清明。”阿巴便是如此,他在电的照耀下醒来,却通过喇嘛手中清澈的泉水获得了顿悟。阿巴在临死之前对仁钦深切叮嘱,希望他能够善待并且关爱所有乡亲。他希望仁钦不管是对改变信仰的人,还是对依旧信仰苯教的人,不管是对心地善良的人,还是对犯了错误的人,都要关心爱护。这正是阿巴经历传统文化的洗 礼之后把传统文化注入现代社会的表现。这种注入最终体现为人性的温暖与闪光,它通过仁钦的延续而走向未来。阿来阐释了传统文化与现代发展融合共生的力量,歌颂了 “生命在经历磨难、罪过、悲苦之后,人性的温暖和闪光”。
结语
通过《云中记》的时空建构,阿来表达了现代化进程不能离开传统的观点。正如卡林内斯库在书中所言,我们不过是站在古代巨人肩膀上的现代侏儒。同时阿来也探讨了 传统与现代在未来发展中共融共生的可能性。这样的文学阐释对我们而言是有醍醐灌顶之功的。但是传统与现代如何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更好地交融,以发挥力量,仍然是一 个难题。我们不禁会问:“对于传统与现代的融合,仅仅是神性系统与科学系统某些概念的相互理解与尊重是否足够?”阿来在让我们看到了力量的同时,又让我们面对最后 一位祭师的消亡并质疑:传统已然逝去,现代性最终会留下什么?现代社会的出路问题留给我们更多的思索,但是正如彼特拉克所说“这种遗忘的沉睡不会永远持续下去。当黑暗被驱散之后,我们的后代又能沐浴在从前清纯的光辉中。”我们应当对现代社会的抱有希望。
原刊于《阿来研究》第14辑

唐昌华,女,山东理工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

陈晶晶,女,山东理工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