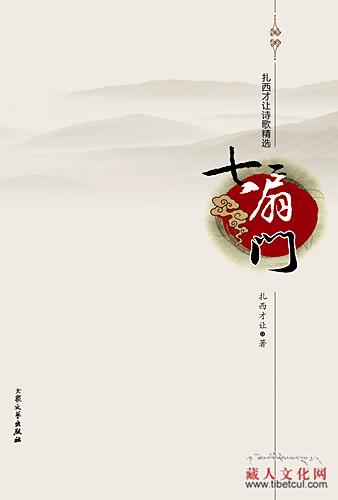
иҜ—жӯҢпјҡжӣІеҫ„йҖҡе№Ҫзҡ„йқҷдҝ®д№Ӣең°
——з®ҖиҜ„жүҺиҘҝжүҚи®©иҜ—йӣҶгҖҠдёғжүҮй—ЁгҖӢ
еҸІжҳ зәў
еӣ дёәеңЁйқ’и—Ҹй«ҳеҺҹе·ҘдҪңз”ҹжҙ»дәҶ20дҪҷе№ҙпјҢзҺ°еңЁиҷҪ然з”ҹжҙ»еңЁеҶ…ең°пјҢдҪҶеҝғеҚҙдёҖзӣҙжІЎжңүеёҰеӣһжқҘпјҢе®ғе·Із»ҸеғҸи—Ҹең°йӣӘиҺІе’Ңж јжЎ‘иҠұдёҖж ·пјҢеңЁйқ’и—Ҹз”ҹж №пјҢеӯЈеӯЈз»Ҫж”ҫпјҢиҝҷе°ұдә§з”ҹдёҖдёӘеҘҮжҖӘзҡ„зҺ°иұЎпјҢжҲ‘дёҚеӨ§е…іжіЁиҮӘе·ұз”ҹжҙ»зҡ„иҝҷдёӘеҹҺеёӮйҮҢеӨ§дәӢе°Ҹжғ…пјҢжҜ”еҰӮиҜҙеҜ’еҶ¬йҮҢеҚ–зғӨзәўи–Ҝзҡ„д№ЎдёӢиҖҒдәәиў«еҹҺз®Ўжү“дјӨгҖҒзӮүзҒ¶жҺҖзҝ»еҗҺжҖҺж ·дәҶпјҢжҜ”еҰӮиҜҙзҰ»е®¶дёҚиҝңзҡ„йӮЈжқЎи·ҜпјҢиҝҷеҮ е№ҙдҝ®дәҶжҢ–пјҢжҢ–дәҶдҝ®пјҢеғҸеӯ©еӯҗ们зҺ©жІҷеңҹдёҖж ·жқҘеӣһжҠҳи…ҫпјҢжҜ”еҰӮиҜҙе°ҸеҢәй—ЁеҸЈеҚ–ж°ҙжһңзҡ„д№ЎдёӢе°ҸеӨ«еҰ»пјҢд»ҠеӨ©жҷҡдёҠ23зӮ№жҳҜеҗҰеҮҶеӨҮжү“зғҠпјҢиә«ж—ҒеңЁеӨ§зәёз®ұйҮҢзқЎи§үзҡ„е°ҸеҘіеӯ©дјҡдёҚдјҡж„ҹеҶ’гҖӮзӣёжҜ”иҝҷдёҖеҲҮпјҢжҲ‘еӨ©еӨ©ж”¶зңӢи—Ҹең°ж–°й—»пјҢйӮЈйҮҢзҡ„жё…зәҜгҖҒжҶЁеҺҡгҖҒйӮЈйҮҢзҡ„з»Ҹе№ЎгҖҒжЎ‘зғҹпјҢйӮЈйҮҢзҡ„еҸҳиҝҒгҖҒи„үжҗҸпјҢйӮЈйҮҢзҡ„ж–Үеӯ—е’ҢиҜ—жӯҢпјҢйғҪжҳҜжҲ‘е…іжіЁзҡ„еҜ№иұЎгҖӮж—¶й—ҙд№…дәҶпјҢдёҖдёӘдәәзҡ„ж–Үеӯ—е’ҢиҜ—жӯҢпјҢжҖ»жҳҜеӨҡж¬Ўиө°иҝӣжҲ‘зҡ„и§ҶйҮҺпјҢд»–е°ұжҳҜз”ҳеҚ—зҡ„и—Ҹж—ҸдҪң家жүҺиҘҝжүҚи®©пјҢд»–зҡ„дҪңе“Ғж•Ји§ҒдәҺгҖҠиҜ—еҲҠгҖӢгҖҒгҖҠж°‘ж—Ҹж–ҮеӯҰгҖӢгҖҒгҖҠдёӯеӣҪиҜ—дәәгҖӢгҖҒгҖҠдёӯеӣҪиҜ—жӯҢгҖӢзӯүж•°еҚҒз§ҚжҠҘеҲҠпјӣе…ҘйҖүеӨҡз§ҚйҖүжң¬пјҢеӨҡж¬ЎиҺ·зңҒзә§д»ҘдёҠеҘ–йЎ№пјҢ2015е№ҙе…ҘйҖү“第дәҢеұҠз”ҳиӮғиҜ—жӯҢе…«йӘҸ”гҖӮд»–зҡ„гҖҠдёғжүҮй—ЁгҖӢпјҢиҷҪеҸӘжҳҜи–„и–„зҡ„дёҖеҶҢпјҢдҪҶеҚҙжҳҜиЎЁзҺ°иҜ—дәәе‘ҪиҝҗжҲӘйқўгҖҒжғ…ж„ҹеҪ’е®ҝе’ҢзҒөйӯӮзҡҲдҫқзҡ„дёҖйғЁиҜ—йӣҶгҖӮеҖҹеҠ©иҝҷйғЁиҜ—йӣҶпјҢжҲ‘жғіи°Ҳи°ҲжүҺиҘҝжүҚи®©еңЁиҜ—жӯҢж–Үжң¬дёӯе‘ҲзҺ°зҡ„д№ЎеңҹгҖҒдәІжғ…е’ҢеҹәдәҺж°‘ж—Ҹдј з»ҹзҡ„еҶҷдҪңгҖӮ
д№Ўжғ…пјҢд»–зҡ„з”ҳеҚ—
еңЁиҝҷдёӘиў«зү©иҙЁеЎһеҫ—ж»Ўж»ЎеҪ“еҪ“зҡ„дё–з•ҢдёӯпјҢдәә们еҸ‘иҙўеҝғеҲҮпјҢеҲ°еӨ„ж·ҳйҮ‘пјҢдёҚжӢ©жүӢж®өпјҢеқ‘и’ҷжӢҗйӘ—гҖҒе…ӯдәІдёҚи®ӨпјҢжәҗиҮӘдәәзұ»жң¬жҖ§зҡ„еҜ№ж¬Ізҡ„жёҙжұӮдјҡиў«ж— йҷҗеҲ¶зҡ„ж”ҫеӨ§гҖӮдҪҶжҳҜзңӢжүҺиҘҝжүҚи®©зҡ„иҜ—дҪңпјҢд»–еҝғдёӯе§Ӣз»ҲжңүдёҖдёӘжңҖзҫҺдёҪзҡ„ең°ж–№пјҢйӮЈе°ұжҳҜз”ҳеҚ—пјҢе°ұжҳҜ家乡пјҢзҫӨеұұд№ӢдёӯпјҢдёҮйҮҢзҷҪдә‘и“қеӨ©пјҢйқ’зҝ иӢҚиҢ«зҡ„иҚүеҺҹпјҢзәўеўҷйҮ‘йЎ¶зҡ„еҜәйҷўпјҢз»ӣзәўиүІзҡ„еғ§иўҚпјҢжӣІеҫ„йҖҡе№Ҫзҡ„йқҷдҝ®д№Ӣең°пјҢжҳҜд»–з”ҹдәҺж–ҜгҖҒй•ҝдәҺж–Ҝзҡ„зҲ¶жҜҚеңҹең°пјҢд»–жҠҠиЎҖи„үе’Ңе‘јеҗёиһҚе…ҘдәҺжӯӨпјҢжҠҠжӯҢеЈ°е’Ңж–Үеӯ—иһҚе…ҘдәҺжӯӨпјҢжқҘзңӢгҖҠз”ҳеҚ—дёҖеёҰзҡ„йқ’зЁһзҶҹдәҶгҖӢпјҡ“з”ҳеҚ—дёҖеёҰзҡ„йқ’зЁһзҶҹдәҶвҲ•жңүдәәд»Һиҝңж–№жҸЈзқҖжҖҖеҝөеӣһжқҘвҲ•жңүдәәеңЁйҒ“и·ҜжҲӘдҪҸд№қжңҲпјҢеҚёдёӢйӘЁзҒ°е’ҢжіӘж°ҙвҲҘз”ҳеҚ—дёҖеёҰзҡ„йқ’зЁһзҶҹдәҶвҲ•жҲ‘зҡ„дәІдәәж•Јеёғз”°йҮҺвҲ•еҗ¬еҲ°з®ҖеҚ•зҡ„з”ҹжҙ»иҗҪзұҪзҡ„еЈ°йҹівҲҘеҗ¬еҲ°з§ӢеӨ©зҡ„е’іе—Ҫиў«йңңиҰҶзӣ–вҲ•з§ӢеӨ©зҡ„еӯ©еӯҗпјҢд»Һ葬иҝҮзҘ–зҲ¶зҡ„ж°ҙйҮҢвҲ•жҚһеҮәиў«иӢҰйҡҫжөёжіЎзҡ„з§ҚеӯҗвҲҘз”ҳеҚ—дёҖеёҰзҡ„йқ’зЁһзҶҹдәҶвҲ•и°ҒдёҖиҝӣй—Ёе°ұжәҳ然иҖҢйҖқвҲ•и°Ғе°ҶдёҖдёӘе©ҙе„ҝпјҢжүҳз”ҹеңЁйқ’зЁһзҡ„жўҰйҮҢ”гҖӮеҶҚзңӢ“йЈҺеҗ№иҚүдҪҺпјҢдёҖдёӣжӮІж„ӨиҖҢиҗҪйӯ„зҡ„зҹўиҪҰиҸҠвҲ•д»ҝдҪӣеҪ’д№Ўд№Ӣи·ҜдёҠзҡ„жіЁе®ҡзҡ„зҢ®иҫһвҲҘжҳҜд»Җд№ҲйҡҗеңЁжҲ‘зҡ„зңјйҮҢи¶ҠжқҘи¶Ҡж·ұвҲ•жҳҜд»Җд№Ҳе°ҒдҪҸжҲ‘зҡ„еҳҙе”ҮжӢ’з»қжў—е’ҪвҲҘдҪ пјҢиөӨиә«иЈёдҪ“зҡ„з”ҳеҚ—пјҢиҙ«з©·зҡ„з”ҳеҚ—вҲ•жҲ‘зҲұдҪ иҝҷеҰӮйҘҘдјјжёҙзҡ„з”ҳеҚ—вҲҘжҲ‘зҲұдҪ й«ҳжӮ¬зҡ„д№іжҲҝпјҡж—Ҙе’ҢжңҲвҲ•зҘһз§ҳиҖҢжё©зғӯзҡ„еӯҗе®«йҮҢж –жҒҜзҡ„з”ҳеҚ—вҲҘжҲ‘зҲұдҪ йҮ‘зҝ…зҡ„еӨӘйҳіпјҢи“қзңјзҡ„жңҲдә®вҲ•жҲ‘зҲұдҪ й«ҳеӨ„зҡ„иЎҖжҖ§жІіжөҒпјҢдҝЎд»°дҪ иҝңж–№зҡ„зҷҪ银йӣӘеұұ”пјҢгҖҠзҢ®иҫһгҖӢгҖӮдёҚи°ҷдё–дәӢзҡ„з«Ҙе№ҙпјҢеҝғжҜ”еӨ©й«ҳзҡ„е°‘е№ҙпјҢй©°йӘӢеӣӣж–№зҡ„йқ’е№ҙпјҢе”ҜдёҖдёҚеҸҳзҡ„жҳҜжқ‘еә„е°ҸеұӢйҮҢйҮ‘й»„зҡ„зҒҜе…үпјҢжҳҜйҖҡеҗ‘еұұеӨ–дё–з•Ңзҡ„д№Ўй—ҙе°Ҹи·Ҝе’Ңи·Ҝж—Ғзҡ„е–ңй№ҠзӘқпјҢжҳҜз“·е®һгҖҒжҶЁеҺҡгҖҒеңҹеҫ—жҺүжёЈзҡ„д№ЎйҹіпјҢжҳҜжё©жҡ–гҖҒз®ҖйҷӢдјјд№Һиҝҳж•ЈеҸ‘зқҖиғҺиЎЈе‘ійҒ“зҡ„еңҹзӮ•……жүҺиҘҝжүҚ让笔дёӢзҡ„з”ҳеҚ—гҖҒе”җе…Ӣй•ҮгҖҒи…ҫеҝ—иЎ—гҖҒиҚүеҺҹгҖҒдә”йҮҢеұұжІҹгҖҒеҚ—еұұгҖҒжёЎеҸЈпјҢйғҪйӮЈд№ҲзҫҺпјҢйӮЈд№ҲдәІпјҢи®©дәәеҝғйҶүпјҢи®©дәәеҗ‘еҫҖпјҒ
“зҫҠзҫӨеҮәзҺ°пјҢжҲ‘е–„иүҜзҡ„е…„ејҹе§җеҰ№вҲ•еёҰжҲ‘жқҘеҲ°дәІзҲұзҡ„иҚүеҺҹвҲ•иҝҷеҹӢзқҖиЎҖиӮүе’ҢйӘЁеӨҙзҡ„иҚүеҺҹ”пјҢгҖҠжҲ‘зҡ„иҜ—жӯҢеҢ—ж–№гҖӢгҖӮ“жҲ‘зҡ„жқ‘еә„йҮҢиғҪз№Ғж®–дәәзұ»гҖҒ家з•ңвҲ•е’ҢдёҖдәӣжңүи¶Јзҡ„ж•…дәӢвҲ•д№ҹиғҪз№Ғж®–дёҖдәӣжҳҶиҷ«пјҢдёҖдәӣйЈҺвҲ•дёҖдәӣй•ҝзқҖзҝ…иҶҖйЈһиЎҢзҡ„дёңиҘҝ”пјҢгҖҠжҲ‘зҡ„жқ‘еә„гҖӢгҖӮеҶҚзңӢзңӢ他笔дёӢж•…д№Ўзҡ„иӢҰпјҡ“д№Ўжқ‘йҮҢзҡ„ж ‘еҸ¶й—ӯзқҖзңјзқӣвҲ•жҲ‘ж„ҹи§үеҲ°жҲ‘дҫқ然еӯҳеңЁвҲ•дҪҶеҚҙйқўеҜ№зқҖжӣҙдёәзңҹе®һзҡ„иҙ«з©·”пјҢгҖҠжё…жҳҺеүҚеҗҺгҖӢгҖӮдёҖйҳөйҳөжӯҢеЈ°дјҙзқҖжё…йЈҺгҖҒзӮҠзғҹе’ҢеҘ¶йҰҷпјӣдёҖжңөжңөзҷҪдә‘еғҸеңЈиұЎеӨ©й—ЁпјҢжҠҠиӢҚй№°зҡ„зҝ…иҶҖ收еӣһеҺ»гҖҒж”ҫеҮәжқҘпјҢеҒҢеӨ§зҡ„иҚүеҺҹпјҢиҠіиҚүзў§иҝһеӨ©пјҢйҮҺиҠұзӮ№зӮ№пјҢзҷҪзҡ„зҫҠзҫӨпјҢй»‘зҡ„зүҰзүӣгҖӮиҝҷе°ұжҳҜз”ҳеҚ—пјҢе®ғжңүжё…жҫҲзҡ„зҫҺпјҢжңүж·іжңҙзҡ„дәІпјҢжңүйҡҗйҡҗзҡ„з—ӣгҖӮиҜ»зқҖжңүдёҖз§ҚзңӢеҲ°жқ‘еҸЈжҹіж ‘зҡ„дәІеҲҮпјҢжңүдёҖз§Қй—»еҲ°йҳҝеҰҲзӣӣйҘӯеҮәй”…зҡ„йҰҷе‘іпјҢжңүдёҖз§ҚзңӢеҲ°зҲ¶дәІжҠҪзқҖж—ұзғҹзҡ„жё©йҰЁпјҢжңүдёҖз§ҚйёЎйёЈзҠ¬еҗ зҡ„жқӮд№ұгҖӮ
жҹ”жғ…пјҢеғҸз»Ҹе№ЎйЈһиҲһ
дёҺеҫҲеӨҡзҹҘеҗҚиҜ—дәәзҡ„дҪңе“ҒдёҖж ·пјҢжүҺиҘҝжүҚи®©зҡ„иҜ—жӯҢд№ҹжңүеҫҲеӨҡжҠ’жғ…зҡ„жҲҗеҲҶпјҢж…ўж…ўе“Ғе‘іпјҢжҖ»жңүдёҖз§Қжҹ”жҹ”иҪҜиҪҜзҡ„дёңиҘҝиө°иҝӣжҲ‘们еҝғжүүпјҢи®©дәәйҷ¶йҶүпјҢеғҸдёҖзј•еӨҸеӨңзҡ„еҮүйЈҺпјҢеғҸдёҖжі“жё…йҖҸзҡ„ж¶ҹжјӘпјҢеғҸдёҖжқҹд»Һиҝңж–№йЈҳжқҘзҡ„зҗҙеЈ°пјҢжҜ”еҰӮпјҡ“еҶ¬еӨ©еҲ°дәҶпјҢеұұеқЎдёҠе°ҶеҮәзҺ°иў«зҢҺжһӘеҮ»дёӯзҡ„е…”еӯҗвҲ•иҖҢеңЁжҳҘеӨ©пјҢдёҮзү©еӨҚиӢҸпјҢжҲ‘дјҡеј•йўҶзқҖжҲ‘зҡ„еҘідәәжқҘеҲ°иҝҷйҮҢвҲҘжҲ‘们иәәеңЁиҚүең°дёҠпјҢд»°жңӣзқҖеӨ©з©әвҲ•д»Җд№ҲиҜқд№ҹдёҚиҜҙвҲҘжңүж—¶еҘ№дјҡз»Ҷеҝғең°жӢ”еҺ»жҲ‘鬓角зҡ„зҷҪеҸ‘вҲ•жңүж—¶жҲ‘д№ҹдјҡжҠҡе№іеҘ№зңји§’зҡ„зҡұзә№”пјҢгҖҠеҺ»е№ҙеӨҸеӨ©гҖӢгҖӮиҝҷжҳҜиҜ—дәәеңЁеҶҷ“жҲ‘зҡ„еҘідәә”гҖӮдәә们既йңҖиҰҒзү©иҙЁз”ҹжҙ»еҸҲйңҖиҰҒзІҫзҘһеҜ„жүҳпјҢж—ўеҗ‘еҫҖзӨҫдјҡиҝӣжӯҘеҸҲжёҙжңӣеӣһеҲ°еҺҹз”ҹжҖҒзҡ„еӨ§иҮӘ然пјҢзәҜжңҙгҖҒжӮ 然пјҢеҮҸеҺ»дё–дҝ—зҡ„жһ·й”ҒпјҢеҝғж— жҢӮзўҚпјҢеҰӮжһңз»ҸеёёеёҰзқҖ“жҲ‘зҡ„еҘідәә”пјҢ“иәәеңЁиҚүең°дёҠпјҢд»°жңӣзқҖеӨ©з©ә”пјҢиҝҷдёӘж—¶еҖҷдёҚжғіжҲҝдә§иӮЎзҘЁгҖҒдёҚи°Ҳе·ҘдҪңеҖәеҠЎгҖҒдёҚжҸҗи®©дәәеӨҙз–јзҡ„еҗ„з§ҚиҜҒ件гҖҒиҜҒжҳҺеҠһзҗҶе’Ңеӯ©еӯҗзҡ„ж•ҷиӮІпјҢеҸӘжҠҠеҝғдәӨз»ҷиҚүеҺҹпјҢдәӨз»ҷжңҲе…үе’Ңжҳҹиҫ°пјҢеӨҡеҘҪпјҢеӨҡзҫҺпјҢеӨҡжғ¬ж„ҸгҖӮ
еҶҚзңӢ他笔дёӢзҡ„е°‘еҘіпјҢ“ж јжЎ‘зӣӣејҖеңЁиҝҷжқ‘еә„вҲ•иў«и—ҸиҜӯй—®еҖҷзҡ„жқ‘еә„пјҢжҳҜжҲ‘жҳјеӨңзҡ„еҪ’е®ҝвҲ•жҖҖжҠұзҫ”зҫҠзҡ„еҚ“зҺӣе‘ҖвҲ•жңүзқҖж—ҘжңҲдёӨдёӘд№іжҲҝпјҢжҳҜжҲ‘йӮӮйҖ…зҡ„姑еЁҳвҲҘй»‘еӨңйҮҢжҲ‘дәІдәҶеҚ“зҺӣзҡ„жүӢвҲ•е°‘еҘіеҚ“зҺӣе‘ҖпјҢдҪ жҳҜжҲ‘еҲқе«Ғзҡ„ж–°еЁҳвҲҘйҒ“и·ҜдёҠжҲ‘иҝңзҰ»ж јжЎ‘зӣӣејҖзҡ„жқ‘еә„вҲ•иҝңзҰ»й»‘иҖҢз§ҖзҫҺзҡ„е°‘еҘіеҚ“зҺӣвҲ•зңјеҗ«еҝ§дјӨзҡ„姑еЁҳе‘ҖвҲ•зқЎеңЁж јжЎ‘дёӯеӨ®пјҢжҳҜжҲ‘дёҖз”ҹзҡ„ж•…д№Ў”пјҢгҖҠж јжЎ‘зӣӣејҖзҡ„жқ‘еә„гҖӢгҖӮеңЁиҝҷдәӣеҜҢжңүйҹөеҫӢзҡ„иҜ—иЎҢйҮҢпјҢз®ҖжҙҒгҖҒиҪ»зҒөгҖҒжҳҺеҝ«пјҢиҠӮеҘҸеҰӮеҗҢйғЁйҳҹиЎҢиҝӣдёҖж ·пјҢй“ҝй”өжңүеҠӣпјҢдҪҶиҜ—дәәеҸҲдёҚж”ҫејғеҜ»жүҫдёҺиҜ—жҖ§еўғз•ҢзӣёйҖӮеә”зҡ„иҜӯиЁҖпјҢеҶҷзү§дәәзҡ„зҲұжғ…пјҢеҶҷе°‘з”·е°‘еҘіеҪјжӯӨзҡ„еҖҫжғ…дёҺеҘҪж„ҹпјҢеҶҷеӨ§иҮӘ然иөӢдәҲе№ҝиўӨиҚүеҺҹдёҠдәә们зҡ„иҮӘз”ұе’Ңе№ёзҰҸгҖӮ
еҶҚж¬ЈиөҸд»–зңјйҮҢзҡ„зҲ¶дәІпјҡ“еҺ»е№ҙжӯӨеҲ»д»–е°ұиҖҒдәҶпјҢи№ІеңЁеўҷи§’еҗёзғҹпјҢи„ёиүІеҸ‘й»„вҲ•жҠҪ第дә”ж №зғҹж—¶пјҢд»–зҡ„жүӢйўӨжҠ–зқҖпјҢеҲ’дёҚзқҖзҒ«жҹҙвҲ•жҲ‘е°ұз«ҷеңЁд»–зҡ„иә«еҗҺпјҢеҸӘйҡ”зқҖдёҖе өеўҷпјҢжҲ‘её®дёҚдёҠд»–зҡ„еҝҷвҲ•еӨӘйҳіз…§еңЁд»–зҡ„иә«дёҠпјҢеғҸз…§зқҖдёҖдёӘеҪўиІҢиЎ°иҖҒзҡ„е©ҙе„ҝ”пјҢгҖҠзҲ¶дәІгҖӢгҖӮиҝҷдёӘзҲ¶дәІпјҢжҳҜжҲ‘们йғҪеҫҲзҶҹжӮүзҡ„зҲ¶дәІпјҢд»–жҳҜзү§дәәгҖҒеҶңж°‘гҖҒзҡ®еҢ жҲ–иҖ…иў«еҹҺз®Ўиө¶еҫ—еғҸжғҠеј“д№Ӣйёҹзҡ„е°Ҹз”ҹж„ҸдәәпјҢ他们жҷ®йҒҚзҡ„и§ӮеҝөжҳҜеӨ©дёҠдёҚдјҡжҺүйҰ…йҘјпјҢ他们е…ұеҗҢзҡ„жғіжі•жҳҜжҢЈдёҖеҲҶпјҢж”’дёҖеҲҶпјҢж—¶еёёжҠҠдёҖеҲҶй’ұж”ҘеңЁжүӢеҝғзӣҙеҲ°еҮәжұ—пјҢеӯҳеҲ°дёҖе®ҡзҡ„ж•°еӯ—е°ұеҜ„з»ҷдёҠеӯҰзҡ„еӯ©еӯҗпјҢжҲ–иҖ…зІҫжү“з»Ҷз®—з»ҷ他们дҝ®жҲҝгҖҒеЁ¶еӘіеҰҮпјҢ他们дҝЎиө–иҮӘе·ұзҡ„и„ҡжӯҘпјҢеҸҢжүӢзҡ„еҺҡиҢ§пјҢжҖ»д№ҹж“ҰдёҚе№Ізҡ„жұ—ж°ҙ……еҶҚж¬ЈиөҸгҖҠжқ‘еә„йҮҢзҡ„еҘідәәгҖӢпјҡ“жқ‘еә„йҮҢзҡ„еҘідәәвҲ•еҲҡеЁ¶иҝӣжқҘпјҢж–°йІңеҰӮжЎғвҲ•жө‘иә«ж•ЈеҸ‘зқҖйҶүдәәзҡ„йҰҷж°”вҲҘз”ҹиҝҮеӯ©еӯҗеҗҺпјҢж—§еҫ—еҺүе®івҲ•еӨұеҺ»дәҶеҫҖж—Ҙзҡ„е…үжіҪвҲ•еңЁиҠӮж—ҘпјҢеңЁе®¶йҮҢпјҢеңЁи·ҜеҸЈпјҢйғҪжҳҫеҫ—з–Іжғ«вҲ•д»ҝдҪӣиў«жІ№жұЎжөёйҖҸзҡ„жҠ№еёғвҲҘдҪҶеҘ№д»¬иҝҳеңЁз»ҷжҲ‘们жҢЎйЈҺйҒ®йӣЁвҲ•еғҸжҲ‘们еӨҙйЎ¶зҡ„и“қеӨ©пјҢдёҖзӣҙеӯҳеңЁзқҖвҲ•дёҚдјҡеғҸеӨ§жЎҘйӮЈж ·зӘҒ然еһ®еЎҢвҲ•д№ҹдёҚдјҡеғҸз©әж°”йӮЈж ·зӘҒ然ж¶ҲеӨұвҲҘи®ёеӨҡе№ҙдәҶпјҢеҘ№д»¬е…»иӮІзқҖе„ҝеҘівҲ•еҝҚеҸ—зқҖз”·дәә们зҡ„иғҢеҸӣпјҢжҠҠиҮӘе·ұзңӢеҫ—йӮЈд№ҲдҪҺ”гҖӮиҝҷжҳҜжқ‘йҮҢзҡ„еҘідәәпјҢд№ҹжҳҜжҲ‘们еӨ§е®¶зҶҹжӮүзҡ„жҜҚдәІпјҢеҘ№жӣҫиүіиӢҘжЎғиҠұпјҢеҘ№жӣҫ笑声еҰӮй“ғпјҢеҘ№жӣҫзәӨи…°еҰӮжҹіпјҢжӯЈеӣ дёә“з”ҹиҝҮеӯ©еӯҗеҗҺпјҢж—§еҫ—еҺүе®і”пјҢеҘ№д»¬жҠҠйҮҚеҝғиҪ¬з§»дәҶпјҢжҠҠдёҖеҲҮж”ҫејғдәҶпјҢеҸӘеӣ дёәеҘ№д»¬жҳҜжҜҚдәІпјҢжҳҜеҺҹз”ҹжҖҒж·ұи—Ҹд№ӢдёӢзҡ„йҒ“еҫ·еҠӣйҮҸпјҢжҳҜдёҖдёӘж°‘ж—Ҹзҡ„з”ҹеӯҳзҠ¶жҖҒеҸІпјҢжҳҜдёҠеёқиөҗдәҲеҘ№д»¬иҝ‘д№Һжғ©зҪҡиҲ¬зҡ„жң¬иғҪпјӣжүҺиҘҝжүҚ让笔дёӢзҡ„жҜҚдәІпјҢжҳҜжҲ‘们жңҖе®үзЁізҡ„еҹәеә§пјҢжҳҜжҲ‘们иә«еҗҺж°ёиҝңзҘқзҰҸзҡ„зӣ®е…үпјҢжҳҜжҲ‘们е“ӯжіЈдёӯгҖҒжҢ«жҠҳдёӯгҖҒиӢҰйҡҫдёӯжңҖе…Ҳжғіиө·зҡ„дёҖзј•ж•‘иөҺзҡ„еҠӣйҮҸе’ҢжҠӨдҪ‘жҲ‘们еүҚиЎҢзҡ„дҪӣе…үгҖӮ
жЎ‘зғҹпјҢеңЁиҚүеҺҹйЈҳйҖё
е…іжіЁжүҺиҘҝжүҚи®©е’Ңд»–зҡ„ж–Үеӯ—пјҢжңҖи®©дәәж·ұеҲ»зҡ„жҳҜд»–еҶҷдҪңзҡ„ең°еҹҹжҖ§е’Ңж°‘ж—ҸжҖ§пјҢ“дҪңдёәдёҖеҗҚз”ЁжұүиҜӯеҲӣдҪңзҡ„и—Ҹж—ҸдәәпјҢз”ҹй•ҝеңЁи—ҸжұүдәҢе…ғж–ҮеҢ–дәӨиһҚгҖҒзү§дёҡж–ҮжҳҺе’ҢеҶңдёҡж–ҮжҳҺдәӨзӣёиҫүжҳ зҡ„з”ҳеҚ—еӨ§ең°пјҢжүҺиҘҝжүҚи®©“иҫ№зјҳдәә”зҡ„иә«д»ҪеёҰз»ҷд»–еҫҲеӨҡеӣ°жү°пјҢдҪҶдёҺжӯӨеҗҢж—¶пјҢд№ҹз»ҷдәҶд»–еҸҰдёҖеҸҢе®Ўи§ҶжҜҚж—ҸгҖҒж•…еңҹе’Ңж–ҮеҢ–зҡ„зңјзқӣпјҢеҸҰдёҖж”Ҝи®°еҪ•еӨ§ең°е’ҢжҜҚж—Ҹзҡ„еӯҳеңЁгҖҒйҖқеҺ»е’ҢжңӘжқҘзҡ„笔”гҖӮпјҲеҲҡжқ°•зҙўжңЁдёңпјүгҖӮеңЁжүҺиҘҝжүҚи®©зҡ„иҜ—дҪңдёӯпјҢиғҪйҡҸж—¶йҡҸең°зў°и§ҰдёҖдәӣеҸҘеӯҗпјҢиҝҷдәӣзҘһеҘҮзҡ„зІҫзҒөпјҢи®©дәәжғҠеҸ№зҡ„жҳҜпјҢиҝҷдәӣж–Үеӯ—еә”иҜҘжҳҜд»Һй«ҳеғ§еӨ§еҫ·еңЁжЎ‘зғҹиў…з»•дёӯгҖҒеңЁзғӣе…үй—ӘиҖҖдёӯгҖҒеңЁжі•еҷЁдјҙеҘҸдёӯзј“зј“еҗҹиҜөеҮәжқҘзҡ„пјҢжңүдёҖз§ҚзӣҙжҠөеҝғзҒөзҡ„ж’һеҮ»пјҢз»ҷдәәд»ҘйҖҡйҖҸзҡ„еҗҜиҝӘпјҢи®©дәәж·ұжҖқпјҢз”ҡиҮізҒөе…үдёҖзҺ°пјҢжҜ”еҰӮпјҡ“еұұдёҠеҮәзҺ°дәҶзҘһзҘ—вҲ•д»–们жқҘиҮӘејӮеҹҹвҲҘж№–иҫ№иҜһз”ҹдәҶзҷҪеЎ”вҲ•е»¶зј“дәҶж—¶й—ҙжөҒйҖқзҡ„йҖҹеәҰ”пјҢгҖҠжӯӨж—¶гҖӢпјӣиҫ№иҜ»иҫ№е“ҒпјҢиғҪе“ҒеҮәеҫҲеӨҡе“ІзҗҶпјҢжңү“йҖқиҖ…еҰӮж–ҜеӨ«пјҒдёҚиҲҚжҳјеӨң”зҡ„ж„ҹеҸ№пјӣжңү“дәәз”ҹеҰӮжўҰпјҢдёҖе°Ҡиҝҳй…№жұҹжңҲ”зҡ„еӨ§жӮҹеӨ§еҪ»гҖӮеҶҚзңӢ“еңЈең°зҡ„еҶ°йӣӘд№ӢиҠұиҜһз”ҹзҡ„йӮЈе№ҙвҲ•дёҖдёӘеғ§дәәеңЁдҪӣе…үйҮҢйЎҝжӮҹдәҶз”ҹжӯ»вҲ•дёҖеә§еҜәйҷўе»әжҲҗдәҶпјҢеұұеҚ—зҡ„йӮЈеә§зҷҪеЎ”вҲ•дҪҝи·Ӣж¶үиҖ…еҒңжӯўдәҶиҝҒеҫҷвҲҘйӮЈж—¶жҲ‘иҝҳжІЎжңүеҮәз”ҹвҲ•жҲ‘зҡ„жӣҫзҘ–зҲ¶еӣ зҪӘеӯҪиҖҢ被葬дәҺж°ҙеҹҹ”пјҢгҖҠиҗҪжҲ·гҖӢгҖӮ“еғ§дәәгҖҒдҪӣе…үгҖҒйЎҝжӮҹгҖҒеҜәйҷўгҖҒзҷҪеЎ”гҖҒзҪӘеӯҪгҖҒ幡然гҖҒж јиҗЁе°”зҺӢ”пјҢиҝҷдәӣе»әзӯ‘зү©гҖҒиҝҷдәӣй«ҳеғ§пјҢиҝҷдәӣд»ӘејҸпјҢиҝҷдәӣи—Ҹең°зү№жңүз¬ҰеҸ·е’ҢеҗҚз§°пјҢжҲ‘жҳҜеӨҡд№ҲзҶҹжӮүпјҢеҮ д№ҺжүҖжңүзҡ„и—Ҹж—ҸеҗҢиғһпјҢеҸ—ж°‘ж—Ҹдј з»ҹж–ҮеҢ–зҡ„еҪұе“ҚпјҢеҗ‘зңҹгҖҒеҗ‘зҫҺгҖҒеҗ‘е–„пјҢ他们еҝғжҖҖж…ҲжӮІпјҢжҖңжғңдёҮзү©пјҢзӣёдҝЎиҪ®еӣһпјҢеңЁгҖҠиҗҪжҲ·гҖӢиҝҷйҰ–иҜ—дёӯпјҢе®Ңе…ЁиғҪзңӢеҲ°жүҺиҘҝжүҚи®©зҡ„иҝҷдёҖзғҷеҚ°пјҢжҲ–иҖ…иҜҙиҝҷдёҖзғҷеҚ°е·Із»ҸиһҚе…Ҙд»–зҡ„иЎҖж¶ІгҖӮ
жҺҘзқҖзңӢ“еҒҢеӨ§зҡ„иҚүеҺҹвҲ•еңҹең°ж·ұеӨ„жөҒеҠЁзқҖиЎҖи„үвҲ•зҹіеұұдёӢеҹӢзқҖдәәзұ»йҖҗж—Ҙж—¶вҲ•йҒӯйҒҮиҝҮзҡ„йӮЈзүҮжЎғжһ—вҲҘиӢҘжҲ‘еғҸиқјиҡҒз”ҹжҙ»дәҺиҚүеә•вҲ•е°ҶиғҪзӣ®зқ№еңЈеғ§зҡ„иўҲиЈҹвҲ•д№ҹйҒ®дёҚдҪҸзҡ„ж—ҘеҮәвҲҘиӢҘжҲ‘зқЎеңЁең°еә•дёӢвҲ•д№ҹиғҪеңЁжёҗжёҗе–§еҡЈиө·жқҘзҡ„дё–з•ҢйҮҢвҲ•иҒҶеҗ¬еҲ°еӨ§ең°зҡ„жё…йҹі”пјҢгҖҠжё…жҷЁгҖӢгҖӮиҝҷдәӣж·ұйӮғзҡ„иҜ—иЎҢпјҢиҝҷдәӣйҒҘиҝңзҡ„йҹіз¬ҰпјҢеңЁе…¶д»–иҜ—дәә笔дёӢжІЎжңүпјҢиҝҷдәӣз»Ҹж–ҮдёҖж ·зҡ„ж–Үеӯ—пјҢдёҚжҳҜеңЁд№ҰжҲҝйҮҢеҶҷзҡ„пјҢдёҚжҳҜеңЁдәәеҝғиҶЁиғҖгҖҒж¬ІеЈ‘йҡҫеЎ«гҖҒе°”иҷһжҲ‘иҜҲзҡ„зҺҜеўғдёӯе°ұиғҪеҶҷеҮәжқҘзҡ„пјӣе®ғдә§з”ҹдәҺйқ’и—Ҹй«ҳеҺҹпјҢйӮЈйҮҢжңүзҘһеұұгҖҒзҷҪеЎ”гҖҒеҜәйҷўгҖҒзҺӣе°је ҶгҖҒз»Ҹе№ЎгҖҒдҪӣзҸ гҖҒз»ҸиҪ®……йӮЈйҮҢзҡ„дәә们зҹҘйҒ“еӨ©ең°зҡ„еӨ§пјҢиҮӘиә«зҡ„е°ҸпјӣйӮЈйҮҢзҡ„дәәзҹҘйҒ“жңүйҷҗзҡ„зҙўеҸ–пјҢжҲҗеҖҚзҡ„еӣһжҠҘпјӣ他们йҡҗеҝҚи¶Ӣе–„гҖҒзҡҺ然жҫ„жҫҲгҖҒ敬з•ҸдёҖеҲҮпјҢеҝғиЈ…иҸ©жҸҗгҖӮ
иҜ»жүҺиҘҝжүҚи®©зҡ„дҪңе“ҒпјҢйӮЈд»ҪзңҹпјҢйӮЈд»ҪзәҜпјҢйӮЈд»ҪдёҚеҠ жҺ©йҘ°зҡ„иҙЁжңҙпјҢйӮЈд»ҪеӨ©зұҒд№ӢйҹіиҲ¬зҡ„йЎҝжӮҹпјҢи®©жҲ‘们зјұз»»еӣһе‘ігҖӮи®°еҫ—д»–еңЁжҺҘеҸ—дёҖж¬ЎйҮҮи®ҝж—¶иҜҙиҝҮпјҡ“з”ҹжҙ»еңЁз”ҳеҚ—иҝҷеқ—зҘһеҘҮзҡ„еңҹең°дёҠпјҢжҲ‘з”ЁиҮӘе·ұзҡ„ж–№ејҸеҗҹе”ұзқҖдёҖдёӘиҫ№зјҳдәәзҡ„ж°‘ж—Ҹи®ӨеҗҢд№ӢжӯҢпјҢиЎҖзјҳеҪ’еұһд№ӢжӯҢпјҢиҝҷдәӣжӯҢеЈ°жңүзқҖеҸ‘иҮӘеҶ…еҝғзҡ„еӯӨзӢ¬е’ҢеҜӮеҜһ”гҖӮжҲ‘еҶ’жҳ§зҡ„зҗҶи§ЈиҝҷжҳҜжүҺиҘҝжүҚи®©иҮӘе·ұз»ҷиҮӘе·ұеҙҮй«ҳзҡ„дҪҝе‘ҪпјҢиҮӘе·ұз»ҷиҮӘе·ұжІүз”ёз”ёзҡ„жӢ…еҪ“пјҢд»–зҡ„иҜ—жӯҢеҲӣдҪңпјҢжӯЈжҳҜдёәе®һзҺ°иҝҷз§ҚжӢ…еҪ“зҡ„йҒ“и·ҜдёҠзҡ„жҺўзҙўпјҢд»–зҡ„иҜ—жӯҢпјҢд№ҹжҲҗдёәд»–зҡ„жӣІеҫ„йҖҡе№Ҫзҡ„зҒөиӮүйқҷдҝ®д№Ӣең°гҖӮжҲ‘зӘҒ然жғіиө·жіўе…°дјҹеӨ§зҡ„еҘіиҜ—дәәиҫӣжіўж–ҜеҚЎзҡ„дёҖеҸҘиҜқпјҡ“жҲ‘и§үеҫ—жҲ‘еҸӘиғҪжӢҜж•‘иҝҷдёӘдё–з•ҢдёҖдёӘеҫҲе°Ҹзҡ„йғЁеҲҶгҖӮеҪ“然иҝҳжңүеҲ«зҡ„дәәпјҢеёҢжңӣжҜҸдёӘдәәйғҪиғҪеӨҹжӢҜж•‘иҝҷд№ҲдёҖдёӘеҫҲе°Ҹзҡ„йғЁеҲҶгҖӮ”жүҺиҘҝжүҚи®©пјҢжӯЈйҖҡиҝҮд»–зҡ„еҶҷдҪңпјҢдёә“жӢҜж•‘иҝҷд№ҲдёҖдёӘеҫҲе°Ҹзҡ„йғЁеҲҶ”иҖҢеҒҡзқҖеҠӘеҠӣгҖӮ
гҖҗдҪңиҖ…з®Җд»ӢгҖ‘еҸІжҳ зәўпјҢи—ҸеҗҚеІ—ж—ҘзҪ—еёғпјҢеңЁгҖҠиҜ—еҲҠгҖӢгҖҠи§Јж”ҫеҶӣжҠҘгҖӢгҖҠж–ҮиүәжҠҘгҖӢзӯүеҸ‘иЎЁиҜ—ж–Ү900дҪҷзҜҮпјҲйҰ–пјүпјӣи‘—жңүгҖҠе®ҲжңӣйҰҷе·ҙжӢүгҖӢзӯүиҜ—йӣҶеӣӣйғЁпјӣжҜ•дёҡдәҺйІҒиҝ…ж–ҮеӯҰйҷўз¬¬еҚҒд№қеұҠй«ҳз ”зҸӯпјҢдёӯеӣҪиҜ—жӯҢеӯҰдјҡгҖҒиҘҝи—ҸдҪңеҚҸдјҡе‘ҳгҖ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