绵延历史中,青海自古就是北方各民族交流融合的前沿地带,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创造了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和灿烂的文明,为世人展示出了独特的人文内涵与无穷的精神魅力。人口超过百万的藏族是青海少数民族中人口最多的一个民族,他们分布在青海全境,集中于牧区草原,草原的宽广与牧人的经历使他们形成了旷达的心胸与性格。藏民族在其繁衍发展的历程中,继承和发展了本民族深厚的传统文化,形成了他们独特的审美心理。在格萨尔史诗弥漫的这片土地上,到处散溢着诗歌的芳香。藏族诗人格桑多杰,就是从这片土地走来并全身心感受这片土地的老一代优秀的诗人。
格桑多杰是藏族当代诗坛上成长起来的第一代诗人,但这并不代表着他的诗在当下已失去了某种所谓的“现代性”意义,相反,他的诗作中表现出的对时代脉搏的强烈感知、国土家园的无比热爱、民族文化的深情传达、诗情诗意的执著追求,正是当下诗歌在喧闹中所缺乏的一种精神所在。现代诗歌发展到今天被人们称为垃圾,确实使所有爱好诗歌的中国人民,读者或者作家包括诗人们痛心疾首。但事实上,当我们回过头去审视当代诗坛从第一代到如今第四代的成长轨迹,不难发现,尽管今天的诗歌面临这样或那样的生存困境,但我们谁也无法否定诗歌在这个历史时代或者是在更早更远的历史长河中曾有过的辉煌与对时代的一种感召。而格桑多杰的诗,正是站在高原这片诗性的土地对时代、对民族所发出的一种感召。
阅读格桑多杰的大量诗篇,我们能明显感觉到他对整个时代脉搏的强烈感知与民族文化的深情传达。五十年代的单纯与热烈、六十年代的艰难与迷狂、七十年代的反思与探求、八十年代的开放与复兴、九十年代的快速发展以及进入新世纪以来向着更高的和谐目标进取的整个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过程,在他饱含深情的笔触都有深深的印迹可寻。
例如创作于70年代末的组诗《北海抒情》中, 诗人称北海为“摇篮”,并在“那一年”的标题下,忆起了二十六年前在中央团校学习、生活和工作时的情景“那一年——二十六年前一个明媚的春天,/老师教我举桨划船。/我落过牧主皮鞭的手臂呀,/第一次掀动你平静的碧波,/青春的胸怀顿时成为幸福的大海。/……我看惯悲凉野蛮的双眼呀,/第一次眺望中南海的楼房,/青春的血管顿时流淌幸福的火焰。”诗所表达的寓意十分明显而感情炽热真诚。在北京中央团校的生活虽然对诗人来说是短暂的,但却是他受党的培养和教育的缩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他在新中国下的健康成长。而诗人所得到的,正是整个历史跨入70年代后整个民族所得到的。因而,他在诗中有着对党最深情的赞美和最热烈的表白。“共产党的恩情/用十八座昆仑山也载不完/用十八条大河的歌声也唱不完”在《喳曲的传说》和长诗《黎明分娩的新城》中,他也形象地对新旧两种生活作了深情对比。他写道:“巨斧般绿色的新城……/把身上的桎梏劈碎,/伸出双臂昂然站起,/让熬寒的胸膛里热血重流,敢把敲骨吸髓的“法典”火焚。/面对沉沉黑夜从不彷徨阔步地走来,/不愧是黎明的儿女,/旧与新的两条路子断然分离,/两重天的经历就从你的生辰划线。”这些新旧交替的欣喜与对新生活、新道路的肯定正是他从历史走来的心路历程。整个诗都洋溢着一股投身新生活的激情与诗人对踏上新征程的昂扬斗志。
在格桑多杰延续至今的大量的诗歌作品中,像这样深情讴歌伟大祖国、展现新旧生活巨大反差的作品比比皆是。共产党领导下整个民族生活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激荡着格桑多杰一颗对祖国充满深情、对人民充满挚爱的诗心。因而,循着祖国前进的步伐,他从未停止对祖国和人民的歌唱。创作于1995年的长诗《大千何处存豪气欲觅赤城问昆仑》更是以荡气回肠的故事给我们叙述了在和平年代,也就是全国人民正如火如荼投身于改革的大潮各尽其能之际,在一些犯罪分子却极其嚣张、盗猎分子极度猖獗的情况下,为了国家的资源不受破坏、为了国家的法律不被人践踏而不顾个人生命危险、与犯罪分子展开英勇斗争最终献出宝贵生命的英雄索南达杰的一生。他用朴实的语言和直白的感情在心痛地陈述这个英雄故事时,不刻意修饰的词语和真情流露的表白打动了所有读者,使我们在他诗的语境中,看到了一个大写的高原藏族汉子以铮铮铁骨永久地矗立于高原之高的伟岸形象,整首诗充满了震撼力。正如他在诗中所写:“立一躯巍巍忠魂的形象;/站一身浩浩正气的威姿,/壮丽的人生何惧血洒颅断。/你的精神明净如秋日的高空,/你的心底清澈如西海的涟漪。/你所踩出的路坦荡于可可西里的劲风,/你的汗珠洒在布满黄金和梦想的土地。/你的风尘抖落于五万里的生命禁区,/你的热量抛洒于海拔五千米的苍茫高地。”一路走来,格桑多杰都是用他敏感和细腻的情怀紧紧伴随着时代前进的步伐。
一
2008年,5·12大地震悲剧的发生深深牵动了所有中国人的心。已年过七旬的格桑多杰作为中华儿女的一员,也深深为之动容,在病榻完成了组诗《汶川松叶》,以诗人的名誉表达了对同胞最深情的抚慰。看到自己的同胞在废墟上的绝望恸哭,他写下了“我断肠的腹腔,/如刀搅碎了肺叶”这样感同身受的诗句,同时也将自己和全国人民对于灾区的关爱以及灾后重建的信心进行了表达。他“坚信万众一心的躯干,/能顶住无情降临的灾祸,/民族自生的血液耿直,/流循似铁如钢的信念,/能扫荡猖狂的患难”。同样,在2010年4月14日一场突如其来的地震灾难降临美丽玉树后,老诗人写下了《奋攀昆仑寒涯——捧致肝脾勇救三江源的啼婴(通天河的叙说)》这一组长诗。从“超越时空,美丽的玉树,你我举燃一盏明灯,钢铁的臂膀,亲人金珠玛米,谁在构筑,英雄的人民子弟兵,将军您太辛苦了,强大的凝聚力,可贵的行动,格拉丹东托起蓝色九天”这十一首诗完整叙写了玉树从地震到救灾以及迅速启动重建的整个过程,写下了“玉树曾长青于世界的眼眸/长青于三江源清澈的渏涟/奔驰于夏日的草原波浪/歌舞于蓝天彩虹的大地”这样美丽的玉树;写下了“4月14日7时49分/满目疮痍/玉树结古镇群众陷入灾难/揪痛了巴颜喀拉山的心脉/惊刺了三江源碧清的泉眼/震碎了清明如镜的期望”这样满目疮痍的玉树;同样也写下了“翻开日日夜夜奋战的日历/多少个夜夜日日更替的朝夕/战斗在重灾区的最前沿/金珠玛米是人间的神军/金珠玛米是人民的救星”和“问大地/是谁啊/在危难关头/日夜难眠/萦怀玉树受灾的群众/山崩地裂的时刻/是谁啊/是谁日夜难眠/牵挂玉树遇难的灾民/为万山之崇/寻找拯救灾害的力量”这样被大爱包裹的玉树。大爱同心、无私奉献的民族精神在灾难面前得到进一步升华,一脉相承的抗震救灾精神再次迸发。大灾大难后喷薄而出的民族大爱,这正是中华民族从悠长的历史走来,全国各民族兄弟始终荣辱与共、同甘共苦永远是一家的历史见证。
二
散文诗《雪魂》中,他以精练的语言叙说了藏民族由过去走向未来的艰难历程,以及在历史的长河中对祖国所作的文明贡献。而雪魂,就是民族之魂。“雪魂登临茫茫的环宇放眼纵观咏北来南往的本土传说。”雪魂在向人们诉说着自一千多年前的唐蕃联姻以来,汉藏人民和睦相处、亲如一家的悠久历史。作者还在诗作中诉说了藏民族在前进的历史中所创造的文明财富。作为民族历史的见证者,诗人在对自己民族的过去与现在的对照中有着鲜明而强烈的震撼,并且对本民族所创造的灿烂文化与历史文明有着很深的感触。因而他在诗中毫不避讳地展露着自己的骄傲。《名门浩雪》一诗中,我们也足见他对生在高原的自豪:“浩雪生来乾坤之门,/巨豪名门的后嗣。/它以寒冷的沉迷爱情,/征服了多少座峰峦。/善性柔轻圣洁和委婉,/但无疑它耿直坦白而冰冷。/峰峦心悦诚服地仰望、仰望,/忘掉了飞雪纷纷后的冷酷。/残酷的洁白,/寒骨的柔软。/划出4千米的高度,/翘首8千米的空阔。”但理性的格桑多杰为民族自豪的同时,并没有满足于藏族人民已有的成就,而是清醒地感知到了藏民族所要面临的现代化问题,因而他又对藏民族的明天充满了希冀,希望他在祖国的大家庭中,同其它民族携手并进,大胆地探索。“雪魂在千年的历程中反躬思虑却并未在凝固的漩涡中停步渴盼兄弟间继续挽手再创更高文明的甘露。”事实上也正是这样,当改革的春风吹拂整个雪域草原时,高原人民正以前所未有的激情,精神焕发地向历史的新纪元迈进。作为民族代言者的格桑多杰,正是通过自己激情四溢的诗句在向人们展示这个民族在新时代所具有的新面貌。
如果说作者在《雪魂》中以豪迈的情调抒写了自己民族的辉煌历史,那么,在同样是散文式表述的《辉煌的诞辰》中,作者则是冷静地在雪山下伫立沉思。民族辉煌的诞生,不是轻轻松松就能取得的,而是在血与火的磨练中取得的,因而,一个民族要发展就不能忘记民族的历史。格桑多杰通过对往昔苦难岁月的回忆反衬了藏族人民今天美好生活的来之不易。因此,在《深邃天涯》一诗中,他抒发着一个老革命家从历史走来的爱国挚情和一个民族从历史走来的感恩之情,期待着祖国在民族团结中繁荣昌盛。写下了“……一个良辰驾驭着永恒的光芒,/共同升起/一位伟大的爱国者的尊荣,/晨曦灿灿,/一条大河万里清明,/一切富于明朗/一切富于真善美。……北京拉萨拉萨北京/千里迢迢,/谁的足迹印上了/一层又一层?/层层脚印都是最深沉的爱的凝聚。……/如果确认山鹰的性格能锻铸铠甲,/宝驹的豪情也定能触感鲲鹏的金翼,/黄河弯弯/讴歌赞美女娲补天的赤胆,/愿苍天不要扭曲/晨晨丹露报捷破晓的定律。/从喜马拉雅的心田到黄河弯的拂柳,/爱国的基石密密实实地铺垫。”这样袒露心迹的赤诚诗句。
历史走过的诸多岁月都在格桑多杰的诗作中留下了痕迹,而藏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也同样在他的诗中得到深情地传达。他的诗不仅大量撷取雪域高原藏民族熟悉的山水草木和生活中非常熟悉的事物作为诗歌意象,而且他还善于从藏族的民歌、谚语和格言以及神话传说中汲取营养,并加以发展,适时用于某个境象中并赋予它新的内涵。这样,他的诗就在一种别具一格的韵味中凸显了其创作上的民族特色。而我们也常常能在他“鸽子蓝天下飞翔,/嫩柳微风中荡漾;/峻岩向鸽子传情,/引诱来矫健的翅膀。”和“不掀开碧波群山要抱怨,/不矫健高旋小雀也会怨恨。”“观世音菩萨点化的猕猴,/将砍劈亲骨肉的刀斧何时放下?/岩魔女孕育的后代,/把相杀凶衅的魔影何时埋葬?”这样的诗句中深切感受藏民族的文化特色,在格萨尔的叙述中感知这块史诗的土壤。还有《鲁协》两首,也让我们在“别轻信鹦鹉的舌头,/模仿人话全是半句;/我们虽临别一时,/但确不违背太阳导向的心颗。”和“能照澈人心的明月,/透显伴侣是否终生如一?/却流云遮蔽了月容,/千万别愁肠,/月亮为世人圆明。”这样的诗句中感受着别样的韵味。正如他自己所说:“民族的文艺形式,民族的语言特色,是我习作的第一本教科书。后来,眼界渐渐地开阔了,我也开始向古典诗歌,向白话体新诗学习,但希望的是,能在藏族民歌这个‘砧木’上嫁接新的枝条,结出更香甜的民歌的果子来。”
三
热爱人民,赞美家乡,是古今中外诗人创作的传统题材。而事实上,格桑多杰也一直以民族的歌者形象出现,用饱含深情的诗来赞誉自己的民族和家乡。他及时地捕捉到在特定的时期里和特定的条件下民族心理的特殊变化,在写出引导人们弃旧图新的诗篇的同时,也将自己对国土家园的无比热爱和诗意的追求作了淋漓尽致地表达。
格桑多杰的诗能带你到连绵起伏的雪山脚下,到广袤无垠的绿色草场,到景色迷人的江河湖海,到勤劳朴实的藏家帐篷,也能使你在他的笔端遨游于祖国大好河山如长城、山海关、新疆吐鲁番和大美敦煌中并葆有盎然兴致。如诗《垛妮达山的清露》《情系无声的地方》《饮马松疆》《山岩大佛》《曙光的赞歌》《意趣敦煌》,散文《阿尼玛卿雪山》等等作品,不仅能使你领略到雪山草原、藏地风情、昆仑野马、哈达锅庄的独特韵味,而且也能使你深深感怀作为生长在这块土地并对这块土地有着无比深情的格桑多杰的一片赤子之情。他写昆仑的云:“紧贴峰峦,/像静卧的羊群,/缭绕草原,像洁白的鲜奶;/亲吻野花,爱抚山草,/献出它无比的温存。”他描绘高山雪莲:“雪山的女儿——卡瓦班玛/传说中她是雪山的供花/是遥远瀚海的使者仙鸟吐出的金籽/云女把金籽拾来埋进深情的雪线/培育出炽焰般的热情/繁忙绚丽的姿容/山崖一样坚强的本色/雪山因她而变得洁白”。他描写骏马:“它是疾驰的风暴/它是燃烧的彩霞。”为故乡赞美和焦灼的语言,为民族呼唤和歌唱的诗句,都将格桑多杰拳拳赤子之心跃然纸上。他的诗,不仅有着深邃的情感、悠深的意境,而且唱出了整个藏民族的心声。格桑多杰不但热爱自己的家乡,他更热爱祖国的山山水水。他说:“我不仅喜欢青藏高原的雪莲,也同样喜欢江南的翠竹;我不仅仰慕雪山的挺拔,我同样仰慕长城的气势;我不但赞美黄河,同样赞美大海的涛声。不管哪个海里捞出的珍珠,都是一样地闪光。”因而在他笔下,长城“……述致一条稀世的概念/筑坚艺术史的古典/载体于东方硬韧的墙线/见龙体升华于莽原的长云/勇牵一个浩瀚的东海出征/于是/青山澎湃蓝天汹涌/从容地横越万里千峰/护卫灿星和睦/平安黎明”。山海关“启迪远见的人们/遥望得更远/创举立体文明的起点”。而写敦煌时又有“佛法叹为观止/留下永世审美的写生铭记/人与佛的迂途如此遥遥/佛与人的塑造如此相近而静默/中华——东方的古国凝重的容纳/黄河长江博大的胸膛荡漾无边”的诗句。
作为雪域高原的歌者,格桑多杰像许多生长在这片土地上的少数民族一样,自觉匍匐于家乡丰沃的土壤,深情地讴歌和赞美家乡的山山水水。在他这个诗人的心里和眼里,家乡到处都是可以为诗的事物,家乡到处都是诗意的氛围。正如他自己所说:“我曾苦苦探求,什么是诗?诗在哪里?我不懂诗,但我觉得生活的主流是美的,美好的生活就是诗。这种美,在我的胸怀里化作了永不枯竭的泉,涌流不息,我终于找到了:诗在藏族姑娘挤奶的咝咝声中,那洁白、鲜净的乳汁就是诗;诗在山涧清澈见底的流泉里,那迸涌淌泻的溪流就是诗;那群峰之巅的风涛雪浪,那广袤草原的千顷绿波,那点缀绿野的牛羊,那陪衬山色的天鹅……藏家人丰富多彩的生活,青藏高原绚丽无比的自然风貌,都充满诗情画意。我找到了诗的源头,也找到了诗。”正是在他这种自觉的诗意氛围中,我们不但在他时而幽婉如溪流浅唱、时而深情如心灵呼唤的诗作中强烈感觉到了属于民族和这块高地的一种诗意,而且也在他时而雄浑如草原奔马、时而精辟如哲人警策的诗作中同样感觉了他本人对诗的一种追求和营造。因而,我们不难发现,在格桑多杰自觉有意识地将自己发现的美和崇高作为一种诗的艺术表达出来时,他丰富的想象、奇丽的构思和质朴的语言构筑了他整个行文的风格,再加上他对本民族文化尤其是藏族人民生动的口语、民歌的比兴等艺术手法的兼收并蓄,他的诗在浓郁的民族特色中有着强烈的感染力与渲染力。
真正优秀的诗歌是那种指向生命可能的诗歌,它使我们能看到一种坚定、宽阔,充满爱和存在感,在苦难与挫折人生中,富有痛感或者不屈不挠地活着的生命,它应对着我们文明中最鲜活、最不可更改的部分。而真正的诗人是时代寄予厚望、人民投以信赖的歌手。格桑多杰这位立足于雪域高原这块诗性土地上的深情歌者,一路走来正是用他诗人的心,去捕捉诗情,用画家的眼,去撷取画意,用乐师的耳,去品赏韵味,更用人民之子的情,去感谢人民。因而他在诗作中展现的民族精神,以及与人民息息相通、心心相印的挚情,使他的一些早期诗作即使是在远离了某个特定时代的今天看来,依旧有着沉甸甸的分量。在这个诗人自主写作的年代,老诗人朴素、透彻的诗,更让人在一种饱满的深情里回味无穷……
原发于《青海湖》2015年第1期

格桑多杰,藏族,青海贵德人,中共党员。毕业于北京中央团校。曾任中共中央委员、青海省人大常委、中国作家协会第四届理事、中国文联第五届委员、青海省文联主席、新闻出版局局长等职。上世纪60年代开始发表作品,著有诗集《牧笛悠悠》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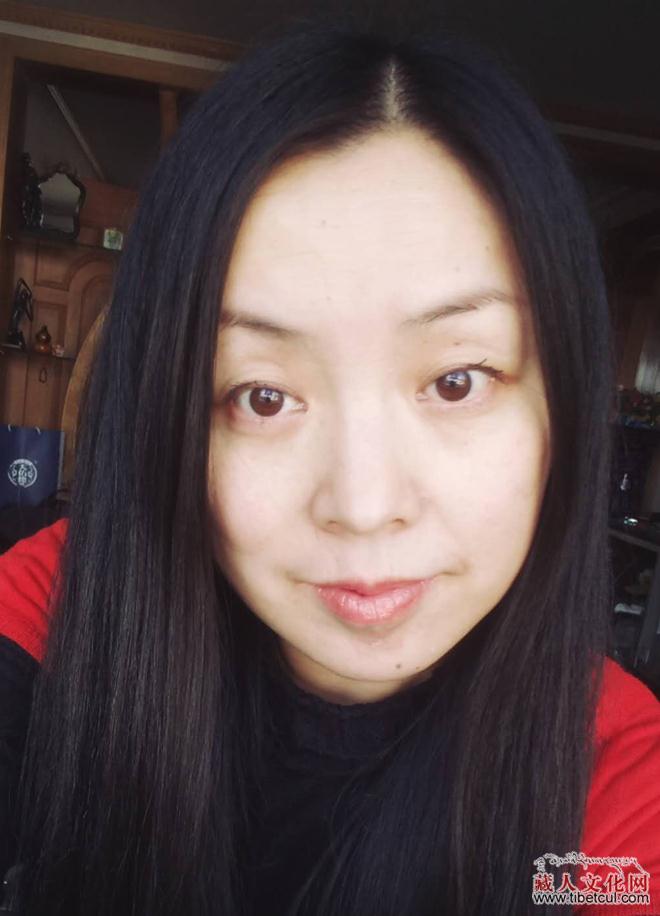
毕艳君,女,青海贵德人,青海省社会科学院文史研究所文学副研究员,青年评论家。长期从事文学评论与民族文化研究工作,先后在省内外公开刊物和报纸上发表成果百余项。合著有《古道驿传》《文成公主与唐蕃古道》《青海民族文化与旅游开发》《三江源文化通论》等著作。作品曾获第五届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三等奖,青海省首届文艺评论奖二等奖,第四届青海青年文学奖,青海省第六届(建国60周年)文学艺术创作奖,青海省哲学社会科学三等奖,全省优秀调研报告奖等奖项。2014年获得青海省“三八红旗手”荣誉称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