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空寓言的民族化书写
——江洋才让小说简论 ①
毕艳君
不可否认,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不管是不是本民族的创作者,一些作家对藏族文化神秘和魔幻的一种展示,曾使藏族文学以其独特的一种文化气质和魅力蜚声文坛,这种状态使民族文学尤其是藏族文学在当代文学的开枝散叶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时日一长,人们开始对那种大量描写奇幻、神秘事物,表现力仅仅停留在表层的作品开始产生审美疲劳。相反地,在这种大量表层所裹绕的外衣之下,人们开始对这个民族生命价值的追寻和人类命运的历史关怀产生了一种探究的欲望。于是,进入21世纪以后,一种以日常生活叙事的细碎、杂乱和雁过无声的生命痕迹来表现边地的、藏民族的历史的小说跃入读者视野并被广泛认可。其中最为重要的代表就是2000年获得茅盾文学奖的藏族作家阿来。他在《尘埃落定》、《空山》以及后来的《格萨尔王》中为我们塑造的瑰丽雄奇的边地世界,成为边地藏民族文化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有机和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阿来小说中塑造的边地世界既是文学艺术的创造,同时也因其巨大的社会容量成为解读当代藏民族历史与文化的范本 。②
众所周知,优秀的作家总能在其作品中为我们营造出别具一格的艺术审美空间,一如沈从文与湘西 ,贾平凹与商州,莫言与高密,阿来与藏族边地等等,无一不在说明一个独创性的小说世界对于作品而言是何等重要。它既是一个作家的艺术选择同时也是成就一个作家的文化选择。从青海藏地走出来的作家江洋才让,正是在长期的本民族文化浸透中,在历史的时空中大量汲取了本民族的文化养分后,以玉树康巴的民族历史书写展现了康巴藏族在这方水土之下的生命足迹。无论世界如何改变,这里的同胞生活的从容淡定,无论生命发生什么意外,这里的同胞依旧朴实自信。从《康巴方式》、《马背上的经幡》到《灰飞》,他不断以自己越来越娴熟的创作技巧和生命感悟在向人们展示自己富有生命力的创作,同时也将青海美丽藏地上的玉树康巴人以民族志的书写方式近乎完整地呈现了出来。“他拒绝一种简单的利用边地来反思现代化进程的态度,淡化了汉民族作为现代性的示范作用,康巴人的生活方式,不再既是落后的又是自由的,而是展现出一种文化人类学式的历史细节的主体性作用。” ③
一、民族志式的历史传奇
在藏族传统的文化观念里,生命是永恒不变,无尽轮回的。因此,在传统的笃信藏传佛教的藏族人眼里,时间的概念是模糊的、不确定的,即使是在某年某月的某日发生了生命中重大的需要铭记的事件,也通常是用另一个确切的物品的存在或是故事来表现,一如《康巴方式》中,铊珈的再次出现是斡玛家老屋拆除的日子一样。《马背上的经幡》也是如此,作家所要叙述和展现的故事从一场草原赛马会来开端,从而引出了作为牧人的卡开和扎洛,曾经在一次赛马会上有过生活交集和力量交锋的两个人自此之后不同的生活际遇和生命轨迹。然而充满意味的命运,在他们生活的广阔空间里弥漫着无法言说的不确定性,因此,两个牧人最终又因为彼此都很钟爱的一匹马而在生命的历程中会和,谁知最后的相遇却成为最后的诀别。可以说,在江洋才让整个的创作书写中,游牧文化的自然浸透、现实主义的深沉关照,以及其精确细致的刻画,使他的小说在表现民族文化例如宗教仪式、民族习性、丰富的民间故事和传说中充满了文化人类学的解读与阐释,诸种人物和事件的历史演绎顿时饱满清晰起来。富有意蕴、耐人寻味的哲理化表述使小说充满了令人回味的想象空间。这种叙述,脱离了广泛意义上的传奇的刻意构建,而是以过往历史中生命痕迹的展演,为读者勾勒了一幅生动鲜明的藏地文化志书。叙事的绵长与细致更有利于其民族志式的铺展。
生活在此的平凡康巴人,深刻鲜明地呈现着他们对于自然、对于人类的认识与接收。他们平凡而伟大,普通而深刻。在他们的生命历程中,即使触碰到不可知的暗礁,他们也是从容拐弯后继续毫无畏惧地如一条静静而流的长河一般向前、向前、继续向前。即使日子过得琐碎、细小,充满了困难与疑惑,也透露出生命本质的韵味:活着就是生活,就是不断的前进,即使遇到生命中的许多不确定,生命的脚步也从不停息,因为他们知道:“等不来的时候,思念就干了。”
发表在2013年《钟山》第3期的长篇小说《灰飞》,更是将他的边地民族志式的书写推向了一个高峰。在《灰飞》中,江洋才让的才情不乏显见的倾泻而出。整个小说的叙述从十岁的普布、一个普通的生长在康巴藏族家庭,却又享受了诸多牧人所不能享受的成长历程的孩子的生长记录,见证了一段长达50(生于1960年,故事结束于2010年)年的历史轨迹。生命在诸多往日里闪闪发光却又历经沧桑。《灰飞》的叙述虽然依旧保留着江洋才让惯常的表达方式与情感演绎,但读者能明显感到与以往作品最大的不同,那就是他在叙事中用时间加强和演绎了每一段历史和每一个事件。从普布生于1960年5月24日、妹妹巴拉姆生于1962年6月18日、普巴生于1963年的记录,到1960年5月22日普布出生前和1962年巴拉姆出生前的一个倒叙,再到1971年时对妹妹巴拉姆那天生邪乎的描述,以及再后来对于父亲嘎玛仁青从1976年1月到9月的几次哭泣、1983年10月20日夏加校长荣升为教育局长、1986年6月11日土登桑丘离世的描写,以及小说快结尾时的2007年4月8日、2008年4月、2009年5月6日,等等有关于时间的点缀,使我们读者深切地感知到,康巴人的生活,并非是一种脱离主体的纯粹的自我存在,其实在整个中华历史的每段历史中他们也都有主体性的演绎,他们的历史,就是整个中华历史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一种共同的历史所在。尤其是在《灰飞》的结尾,2010年4月13日和14日的确切记录,让我们触目惊心感知了这片大地上无可抗拒的一场来自自然的特大灾难。正是有别于其它作品的这种对于时间的特殊强调性,让我们在这部作品的阅读后更加肯定了作家江洋才让对于长篇小说历史叙事的一种驾驭能力。
在时间的确定性表达上,《灰飞》比其他作品更具细节性和表达性,具有很强的感染力,更像是一个民族浩浩历史的志书纪录。内容精确细致、广瀪驳杂,感情细腻真挚、意蕴深厚绵长。而这种真实,正是民族志所要表达的历史同在。突出事件的历史时间,在于更真切地让人体味历史的真实存在。可见,这片土地并未因处于“边地”而脱离历史行进的轨迹,相反,它的细致、琐碎更是与历史的一种紧密联系。正如小说中所说的:“个人的历史就是由这些琐屑似米粒、油菜籽粒、更小的草籽粒、沙粒的事情构成的。不要否定,历史上那些大人物的琐碎事,往往是被忽略了。”宏大的历史,其实也正是这些琐屑、细小的历史所构成的而已。
中国历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统一国家,从来就有复数和复线的文化文明史,而江洋才让叙述的历史就是以小说为表现手法的藏地文化史的一部分。其意义不仅仅是文学艺术上所取得的成绩,还应该是以民族志式的传奇来表现出的一种对自己熟捻于心的文化的深切关怀与阐释。即人物在现场,作者也在现场的一种从容表述,从而试图达到从历史出发即而抵达哲学的书写深度。正如巴尔扎克认为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一样,江洋才让在不同的作品中或重或轻叙述历史和展现历史,显现出其在政治叙事线索中的人性关怀与 民俗叙事细节中的文化关怀,利用他的创作技巧饱满小说世界的同时,也丰富了读者的阅读世界,让读者对一个民族从历史走到今天有了更为广阔的了解空间。
二、民间立场与民间身份的确定
作为一部藏族作家写自己母族历史的作品,江洋才让的作品中不可置疑地就会有许多有关家乡传统文化与民俗民风的描摹与阐释,因此,从一开始,作家就给自己确定了一个民间的立场与身份。即前面所说人物在现场,作者也在现场的一种从容表述,而非他者的介入性描述。这样,作品在细微、独特中更趋于真实和自然。这种立场的确定与身份的定位,使作家在叙事风貌、审美情趣、价值选择和言语特征上具有了自己独特的风骨。
众所周知,即使在漫漫文学史中难以寻觅文人大批创作的鲜明足迹,文人作品孱弱无力、难撑大局的的时候,浩繁丰富的民间文学也依旧以它世代口耳相传的生命力在广袤的大地上生生不息、绚烂多姿。作为有着最可称道的《格萨尔》史诗的藏民族,更是在诗歌芳香弥漫的大地上散发着藏民族传统文化的无穷魅力。丰富的民间故事和传说、谚语等都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成为与本民族生活息息相关的一种文化依存,如唇齿之依般活跃在每个民族作家的作品中。因此,无论是《康巴方式》《马背上的经幡》还是《灰飞》,萦绕和包裹在江洋才让长篇小说中的有关民族的文化气息随处可嗅,却又意味深长。正如江洋才让自己说的:“我在每一个乡间穿梭,流连在被微风吹拂的青稞地------如果说我的舌苔上有一片青稞地,那么额头上就会有一片草场。”正是在这种无法剥离的依存之下,有关宗教的、生活习性的东西在作家笔下以一种充满了生活情趣的叙述深情而真挚地流淌,汩汩而出的是作家自己对这片青青草地、神山圣水满满的敬畏与尊崇。
在《康巴方式》和《灰飞》中,作家江洋才让都有着关于神山的描述。就像《灰飞》中十岁的普布觉得“山是见证了好多事情的。万物荣枯、季节流转,即使石头开花也逃不过它的眼睛。”而在《康巴方式》中,卡瓦神山在这个康巴农庄的传说里是被指认为伏藏之山的。“有了这座神山,村民们的心灵就有了一种很空灵的寄托。村民们有事没事地总是要在一天当中朝着它叩几个头。响头磕过了,心里才会踏实。”而这神山不同于其它神山的地方,还是因为山脚下的好多石头里都含着铁。因此守护神山的南卡婆婆似乎有了更大的权利,来决定含有铁的石头的去向。有康巴人的地方就离不开马和刀子,于是在《康巴方式》中,“我”因为终于拥有了一把属于自己的刀而欢喜,而母亲也因为我把刀子高举起来的肃穆而想到“自己的儿子虽然瘦弱,但是支撑肉体的骨头却根根坚硬,随便甩出一块,就会打裂岩石。”而哥哥为了得到一匹烈马,独自一人追寻野马足迹而苦守九天。在《灰飞》中,则是父亲嘎玛仁青与三匹马为伴,运输着学校里需要的一切物资。而在《马背上的经幡》里,故事更是以一场草原上的盛会赛马会为开场,整个故事却又以一匹好马经历两个主人为纵线展开了卡开和扎洛两个各自不同的生命个体的生活轨迹。在康巴人的生命中,就像《马背上的经幡》中洛扎的感觉一样,人的命运,马的命运,牛羊的命运,多多少少会有点相似。不光是自然中的山水富有灵性,其实,包括牛羊在内的世间万物皆有灵性,皆有所通之处。
而对于事情和事件的讲解,康巴人天生就有一种叙述的欲望,讲故事的能力。于是,在江洋才让的笔下出现了很多次的叙述场景。就像我们在听一个熟悉的“很久很久以前”的类型故事一样,充满了好奇与期待,共鸣与遐思。《康巴方式》中,阿爸讲得关于驮脚汉给康巴部落带来了好运,是狗为康巴人衔来金贵的青稞种子的时候,还有阿妈白拉姆讲述王子历经千辛最终救出美丽公主的故事的时候;《马背上的经幡》中卡开的老丈人讲述自己路遇一匹雌狼,却因为自己称呼了它为姐姐后安然无恙回来的时候,努丁讲述路遇三个奇怪的人的时候,色达湖自然保护区管理员亚玛讲述色达湖的心脏是一条青鱼,千年不死并且没有一只水鸟会去吃它的时候;《灰飞》中“接下来的故事是河水告诉了河岸。河岸又告诉了岸边的鹅卵石。鹅卵石又告诉了一双脚。那双脚带着这个故事满生产队里游走。讲故事的人就是生产队队长。”等等诸如这样讲故事和听故事的场景以及描述有很多次,似乎“康巴”天生就与传奇有关。然而正是在这种传奇外衣的包裹之下,我们在江洋才让民族化的书写和语言中看到了康巴人最真实的生活场景。而任何讲述者,在开讲时都必须使自己处在一种平和的状态,心平气和,缓缓道出,可见,这种娓娓道来的叙事更接近读者的心灵。“就像我的一个前辈说的,我说出一切,因此我干净,世界吉利。”“康巴人信奉道理就像信奉自己的父母一样!” 江洋才让在康巴大地上痴迷于讲述的一种描写,在促成他民间身份的形成与民间立场的确定的同时,也完成了他小说中的一种记述上的艺术转换(即叙述视角的多样转换,第三人称和“我”的叙述常常是交互出现),显现了他对自己民族生存之地上的诸事诸物的洞若观火。
本民族传统文化的浸润,使江洋才让在叙事语言上有着鲜明的民族特点和民族风格。清新明快、意蕴深厚、富有哲理的诗意表达常常使人流连于他所建构的一时一景与之下的人物。《康巴方式》中,在描述哥哥寻找野马时他说:“希望只是一种使人变得虚妄的气体,他的弥漫总是选择你头脑发热的时刻。它的深入最终会使你身心交瘁,疲惫不堪。” 而在全村人壮观的收割青稞时,他又说道:“这不是劳动了,而是在舞蹈。”一些充满了智慧的俚语与谚语也时刻在提醒读者,这不但是个不容小觑的群体,更应该是个值得人们敬仰、学习的民族。在江洋才让的笔下,他们是生活在边地的一个群体,但他们是真正呈现自己本真生活状态、热爱生命与生活的人。“在康巴人的诉说里,时间向来是一种可以打败一切的不可思议的伟大的力量。”“康巴人的发梢所指的地方就是风要前往的地方。”“你认为可怕的其实就像泥土般容易解体。”“忘了故乡,就是忘了生命的由来”。“事情经不住想,木头经不住烧,泥地经不起挖。”“光滑,会让行走的人摔跤,失去自己的脊梁。而且是一寸一寸地断掉。“父亲总对他说,不要低着头走路,这样会撞到别人的胸口。”“他的笑比穿过县城的吉曲河拐弯还要宽阔。” 而“阿爸说”、“阿妈说”,这样类似的开场白带出来的关于古老民族的历史记忆更是有着真理般的闪光点,一次次跌落在孩子们的心上,也跌落在读者的心上。
三、宗教叙事与政治叙事中的人文关怀
任何一个民族作家在以文学的形式来表现本民族的历史文化时,民俗的介入是不可规避的。因此,在许多民族作家的作品中,我们通常都会透过人物、情节和故事的发展舒展一卷属于读者自己的民俗画卷。在江洋才让的作品中也是如此,从《康巴方式》《马背上的经幡》到《灰飞》,去除我们通常认为的最为直观的服饰以及饮食和生活习惯以外,我觉得最大的看点在于对喇嘛,或者说是宗教的一种理解性阐释。
《康巴方式》里,年轻的喇嘛在久旱无雨的情况下出现了,这个看见村里人向他脱帽致敬时脸上会飞过红晕的喇嘛,在太阳的炙烤下念了整整6个小时的经以后,羞怯地拒绝了50元钱的布施而只拿了10元钱后转身离去。在喇嘛的身影在村道上渐行渐远,直至融入远山以后,在场的村里人都愣在原地,有人发出声息:“是佛?!”然而在接下来的等待中,村里并没有如喇嘛喻示的那样在十天之内出现人们期盼已久的雨水,倒是在15天时,哥哥带人从山上引水回来了。一时间,人们欣喜若狂,只可惜雪水有限,越用越少。但就在几天后,人们祈盼已久的雨水终于如痴而来。虽然它与喇嘛喻示的时间不相吻合,但“我”却在如痴的雨声里陷于对那个喇嘛的深深怀念之中。《灰飞》中,有着洞察世事的敏锐与聪慧的普布在经历了出人意料的成长历程,尤其是在经历了忘年交才文的触电身亡(因为寻找夜不归宿的自己)后,他知道,他再也没有了这个朋友,没有了给他讲逻辑、讲哲学的朋友。加上之前传言中的弟弟普巴和“黑弟弟”两个人的死亡,在他看来是跟他有很大关系的,因此他深深陷入一种巨大的困惑中,然而就是在这个时候,也就是在1983年的6月16日,他在河边遇到了一个老阿卡。老阿卡“你是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佛菩萨,还是深陷在毫不容你的世俗”的声音萦绕在他耳边三天后,23岁的普布下定决心进入佛门。于是1983年9月3日,普布当了阿卡,成为一名在册僧人。原来以为普布的一生从此就会在庄重的念经声中度过,谁知,难以捉摸的世事总会降临。因为多尼的养父去世,多尼又变成无依无靠,而她对普布的示爱和一场食物中毒的意外竟像是冥冥中的某种安排似的,于是普布还俗了,并且顺理成章地和多尼结为夫妻了。
故事看到这,我们就不能不感慨于世事的无常与生命的不确定性了。藏传佛教作为边地世界最主要的意识形态,长久以来深刻地影响着当地人们社会、精神生活的一切领域。这种宗教信仰的外化,体现在藏族人民对于佛事、寺院的宗崇与敬仰乃至膜拜。然而,在江洋才让的让的叙述下,我们看到了别样的喇嘛,也看到了还俗的阿卡。这都源于佛教一切“慈悲利他”的思想,慈悲利他教人学会的是与他人、与社会、与宇宙和谐共处的本来智慧与方便,能极大地有利于将陷落和禁锢于私我的小圈子里的残缺的灵性解放出来。正因为此,我们看到的祈雨喇嘛虽孤独无助、青涩羞怯但却令人怀念,而还俗的普布也因多尼的生活能重新焕发光彩而被众人所理解和接受。即使最后他们的婚姻破裂,作者赋予他的也是最深切的一种人文关怀。无论是对祈雨喇嘛的细节描写,还是对普布与多尼婚姻的完整表述,江洋才让都在有限的一种宗教叙事中表达了他对僧人的一种常态下的理解与关怀。这种氤氲在人文关怀之下的叙事读来会让读者看见一个更接近于自己的现实,有助于作品的真实性表达。同时,也透露出作家自己最朴实和最原始的一种精神和价值取向,即对一切至真至纯至善至美理想的信仰和追求。
在江洋才让的长篇作品中,最能突出政治叙事的应该是《灰飞》。《灰飞》所描写的故事就像书名一样,似乎一切皆有可能灰飞烟灭。普布的父亲嘎玛仁青作为一个学校的马车工,在那样的年代是极其不易的。因此我们看到,这个牧人的儿子竟然能在县城小学里工作,据说就是因为他天生篮球打得好。他的步伐是羚羊的步伐。他闪展腾挪就像是受过专业训练。在过去的年代,尤其是在少数民族的作品陈述中,篮球这个物件似乎是新鲜而又不可触及的,而在《灰飞》中,篮球是陪伴嘎玛仁青一生,也是他最钟爱的一件物品,因此他说“篮球是鹰!撞向篮板,或冲进篮网,义无反顾的鹰。”而他拿起篮球时,他的目光里就有了一个比房子还宽敞的地方。就是这样一个鹰一样的人物,也在经历用篮球做饲料袋,吃马吃的玉米饲料的历史;也在经历挖野菜的历史,而在他经历与篮球有关或者说是篮球见证了某些历史的时候(他与某些造反派在篮球场上相遇),普布和巴拉姆却在学校里经历着小红卫兵们对校长的造反和批斗,妹妹巴拉姆对于小红卫兵的羡慕与效仿丝毫没有动摇普布帮助朋友的心。在这里,作家给我们叙述的是一段旁观的历史,小说中接受批斗的人似乎与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关系不大,但朋友间的友谊却使普布展现了自己最大的善良,与那些恶毒的落井下石的人相比,善良的人带出了特殊历史时期最美好的一面。而在普布亲历的一场批斗中,作家还着重描写了藏医苦巴桑,“他战战兢兢地站在愤怒的中央,低眉顺目地迎接着发狂的质问。……普布从大人的两腿间钻到苦巴桑前,他看到,苦巴桑哭了。涕泪俱下,最后他站不住了,竟然跪在了地上。……一次又一次的批斗总是在前面等着他,终于有一天,有人看到他口吐白沫死在家里了。”这个场景的描述不仅将那个年代人们失去理智变得疯狂的一面真实的进行了再现,也将隐含在小普布内心的巨大同情与深刻怜悯表述了出来。于是他又说:“人们在生病的时候,才开始想到苦巴桑的好。”
作为现实主义的写实小说,除了呈现特殊年代的历史面貌外,《灰飞》这部作为民族志式书写的故事,就时间跨度而言也是一部宏大的叙事小说。除了前面说到的特殊历史背景下的往事以外,他的笔触还延伸到了现代世界里的严打和改革开放以后的自主创业。而这里的主角,变成了希西拉多德。一个曾经被叫做大嘴巴的有着令人糟糕记忆的人物。在世事变幻后,竟然成为引领这个县城现代潮流的人。而普布的儿子尼玛在自己和多尼结束十一年的婚姻之后,竟然成长成了一位除了背着装爷爷篮球的网兜四处游荡而无所事事的年轻人,至少在普布眼里是这样的。故事的行进似乎越来越不能让人按常规判断,也许这就是作家最真实的生命叙述,人生无常,时时刻刻充满了不确定性,就像灰飞一样。
无论是蕴藉着浓浓民族色彩的宗教,还是无法回避的历史政治背景,江洋才让都在他的小说中运用了一种精神共通中的互勉与互解。这是因为作者无论用怎样转换的视角来叙述这个绵长而细致的历史长河中的故事,他都有一个历史细节的筛选与甄别,都因他自己的融入而变得得心应手,由此,他的关怀与深情不难感知,也不难理解。这样的关怀,使《灰飞》的结局显得格外精彩,一切的变幻都已发生,就连离不开普布的多尼已经在别人的怀抱里享受幸福,那么,还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发生?果然,在经历了好多的出人意料和变化后,更大的变化接踵而至。2010年4月14日,突然而来的一场灾难,让一切灰飞烟灭。在无法预知的灾难中,废墟、杂乱、灰飞土扬中传来了“布鲁鲁……布鲁鲁”的哨声,那正是挂在普布脖子上不吭不哈的那根被细小的链子拴着的裁判哨,在这个节骨眼上,终于派上了用场。
结语
民族文学说到底就是以其民族特色为基本特征,展现本民族性格和智慧的文学。因此,江洋才让这几年,尤其是在经历了地震变故以后的书写,可以说是藏族文学尤其是展现位于青海高原康巴这个群体的藏族文学中的佼佼者。他在汉藏两个民族之间穿行的文学敏感与对文学的虔诚,以及他对自己“康巴”这个标签的认可与传承,家乡故土再建的经历与认识,使他在艺术上有着不断尝试的创新精神和对本民族历史文化内蕴的深入挖掘与生活的真实再现,从而使其作品显现出少数民族创作的旺盛生命力和高超的艺术感染力。
他用驾驭长篇的高强能力,用自己民间立场和身份的确定,以富有诗意的语言刻画着藏民族历史上不同的生活细节;用民族志式的书写以琐碎细致的记录,来展现自己本民族的“地方性记忆”;用传统藏族文化观念中的乐观、坚韧、执着引领故事发展的方向,保持着人性深处最美的悲悯情怀。同时,他也用自己最饱含深情的文化传承毫无保留地呈现着这个民族的一切,喜怒哀乐、生离死别以及生生不息的生命活力。
位于青海省西南青藏高原腹地的三江源头,有一片天然美丽的草原名字叫玉树,这里世代生活着雄性、果敢、朴实的康巴藏人。但这里的康巴人并不仅仅是人们想象中的“血管里响着马蹄的声音”的人,于是我们看到了身为这片土地主人的康巴汉子江洋才让给我们记录的别样的《康巴方式》,而坚韧执着的康巴人又与马和刀有着不解之缘,于是又有了《马背上的经幡》。而在2010年的4月,一场地震灾害使这片大地上的一切在瞬间灰飞烟灭。于是我们在作家的沉淀中看到了厚重历史的再现,看到了《灰飞》。江洋才让用生活记录的方式,在大量的写实(当然,也有想象的参与和构建)中力图将一个民族完整而不是片段式的历史呈现给读者,给读者还原一个真实的康巴。因此,江洋才让的这类小说多着力于普通而细小的日常生活。在这里,有着康巴人最平实却温暖的生活轨迹,而其主旨却是更关注藏族人物形象作为普通人的人间情怀,既有民族性特征,更有普适性价值。那一个个人物和场景在情感表达上的精准和到位,那隐忍中澎湃的激情,那痛苦中些微的甜蜜,都流淌着作家对故乡母亲最真诚的热爱和忠诚。
【注释】
①文中所引小说情节皆出于江洋才让小说《康巴方式》(《钟山》长篇小说专号2010年A卷)、《马背上的经幡》(青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3月版)、《灰飞》(《钟山》2013年第3期),文内不再一一注释。
②龙其林:文化血脉精神原乡——透视阿来小说中的边地世界,《美与时代》2005年11月下
③赵林云:一部民族志式的边地奇书——评江洋才让的边地小说《康巴方式》,《钟山》2010年第2期
原刊于《青海湖》2013年第11期

江洋才让,中国作协会员,青海省作协副主席,曾就读于鲁迅文学院少数民族作家班。荣获青海省第四届、第五届、第六届文学艺术政府奖,获紫金•首届《钟山》文学奖长篇小说奖,《作品》第十二届短篇小说奖,《十月》“牦牛文化”专刊短篇小说奖,首届青海湖文学奖、青海青年文学奖。作品《康巴方式》入围第八届茅盾文学奖,首届唐蕃古道文学奖。多部作品入选《长篇小说选刊》《小说月报》《小说选刊》《散文选刊》《中华文学选刊》《西部散文百家》等选刊和选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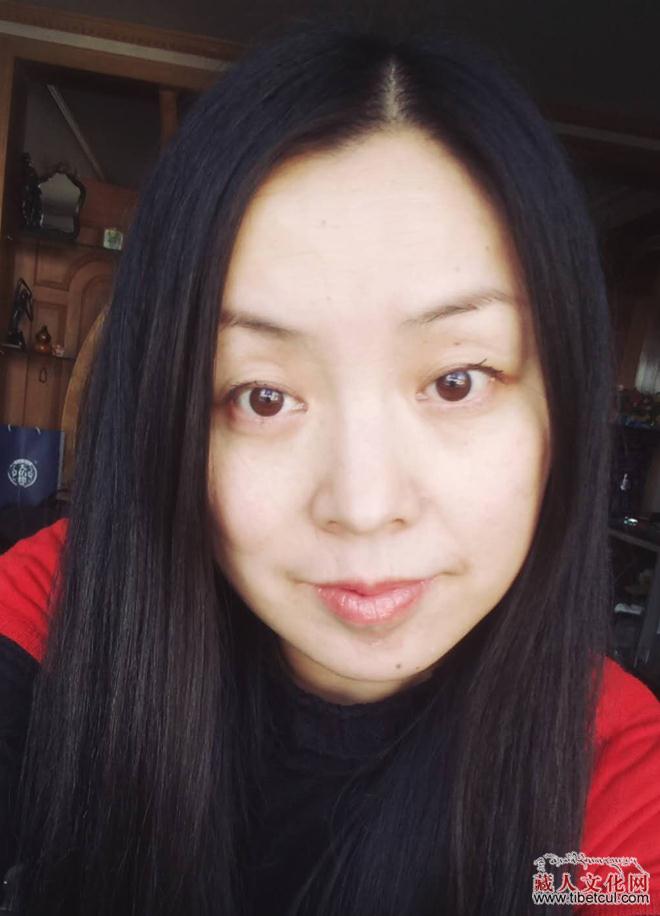
毕艳君,女,青海贵德人,青海省社会科学院文史研究所文学副研究员,青年评论家。长期从事文学评论与民族文化研究工作,先后在省内外公开刊物和报纸上发表成果百余项。合著有《古道驿传》《文成公主与唐蕃古道》《青海民族文化与旅游开发》《三江源文化通论》等著作。作品曾获第五届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三等奖,青海省首届文艺评论奖二等奖,第四届青海青年文学奖,青海省第六届(建国60周年)文学艺术创作奖,青海省哲学社会科学三等奖,全省优秀调研报告奖等奖项。2014年获得青海省“三八红旗手”荣誉称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