й•ҝзҜҮе°ҸиҜҙгҖҠе‘Ҫе®ҡгҖӢжҳҜиҫҫзңҹ“еә·е·ҙдёүйғЁжӣІ”пјҲгҖҠеә·е·ҙгҖӢгҖҠе‘Ҫе®ҡгҖӢгҖҠ家еӣӯгҖӢпјүдёӯзҡ„第дәҢйғЁгҖӮиҫҫзңҹеңЁи°ҲеҲ°иҝҷйғЁе°ҸиҜҙзҡ„еҲӣдҪңж—¶пјҢжӣҫиҜҙпјҡ“еӣҪдәәеҝ…йЎ»ж„ҸиҜҶеҲ°пјҢеӨ§йҮҸиҘҝж–№зҹҘиҜҶдҪ“зі»дёӯзҡ„иҜ„еҲӨ规еҲҷеҫҲеӨҡжҳҜдёҚйҖӮеҗҲиҜ„д»·дёӯеӣҪзҡ„гҖӮеӣ дёәпјҢиҝҷдёӘжңүзқҖдә”еҚғе№ҙеҺҶеҸІзүҲеӣҫдёҠзҡ„д»»дҪ•дёҖдёӘж°‘ж—ҸпјҢж— и®әз”Ёд»Җд№Ҳж–№ејҸи„ұзҰ»иҝҷдёӘеӨ§зҫӨдҪ“йғҪжҳҜдёҚжҲҗз«Ӣзҡ„пјҢдёӯеӣҪжҳҜеҗ„ж°‘ж—Ҹз»„жҲҗзҡ„еӨ§е®¶еәӯжҳҜе‘ҪдёӯжіЁе®ҡзҡ„пјҢе°ұеғҸжң¬д№Ұзҡ„дё»дәәе…¬д№үж— еҸҚйЎҫең°иө°еҗ‘жҠ—ж—ҘжҲҳеңәйӮЈж ·пјҢжҳҜе‘ҪдёӯжіЁе®ҡзҡ„гҖӮ”жүҖд»ҘпјҢгҖҠе‘Ҫе®ҡгҖӢеҢ…еҗ«дёӨдёӘеұӮйқўзҡ„“е‘Ҫе®ҡ”пјҡ家еӣҪе‘ҪиҝҗдёҺдёӘдәәе‘ҪиҝҗгҖӮ
ж–Үжң¬и®Іиҝ°дәҶдәҢжҲҳжңҹй—ҙпјҢеә·е·ҙз”·е„ҝжұҮе…ҘжҠ—ж—ҘжҙӘжөҒпјҢеҠ е…ҘдёӯеӣҪиҝңеҫҒеҶӣпјҢжҠ—еҮ»ж—ҘеҜҮпјҢдҝқ家еҚ«еӣҪзҡ„ж•…дәӢгҖӮиҝҷж®өеҮ д№Һиў«дәә们еҝҪз•Ҙзҡ„еҺҶеҸІпјҢйҖҡиҝҮеңҹе°”еҗүе’ҢиҙЎеёғдёӨдёӘзғӯиЎҖз”·е„ҝзҡ„зҲұжҒЁжғ…д»ҮпјҢеңЁиЎҖдёҺзҒ«зҡ„ж’һеҮ»дёӢд»ӨдәәиҚЎж°”еӣһиӮ пјҢи®©жҲ‘们ж„ҹеҸ—еҲ°дәҶеҸІиҜ—зҡ„жҒўе®ҸгҖӮе…¶е®һпјҢд»Һ“дёүйғЁжӣІ”дёӯзҡ„第дёҖйғЁгҖҠеә·е·ҙгҖӢејҖе§ӢпјҢиҫҫзңҹе°ұиҜ•еӣҫиөӢдәҲ“дёүйғЁжӣІ”еҸІиҜ—зҡ„еҹәи°ғгҖӮйәҰ家еңЁдёәгҖҠеә·е·ҙгҖӢжүҖеҒҡзҡ„жҺЁд»ӢиҜӯдёӯеҶҷйҒ“пјҡ“иҝҷжҳҜдёҖйғЁеә·е·ҙи—Ҹдәәзҡ„еҸІиҜ—пјҢжҜҸдёҖеӨ„з»ҶиҠӮйғҪеҢ…еҗ«зқҖдәәжҖ§жңҖж·ұеӨ„зҡ„зҫҺеҘҪдёҺж„ҹеҠЁ”гҖӮйҷҲжҷ“жҳҺж•ҷжҺҲи®ӨдёәгҖҠеә·е·ҙгҖӢ“жҳҜжҠҠдј з»ҹзҡ„еҸІиҜ—дёҺзҺ°д»Јзҡ„дәӢдёҡеҠ еңЁдёҖиө·”гҖӮиҫҫзңҹиҮӘе·ұд№ҹиҜҙпјҢеёҢжңӣ“иҝҷдёүйғЁе°ҸиҜҙиғҪйҮҚй“ёж°‘ж—ҸзҒөйӯӮпјҢз»ҷдәәзұ»д»ҘеҝғзҒөе®үжҠҡ”гҖӮжҳҫ然пјҢеҸІиҜ—жҖ§жҳҜиҜёеӨҡеӯҰиҖ…еҜ№гҖҠеә·е·ҙгҖӢзҡ„дёҖиҮҙе…ұиҜҶпјҢд№ҹжҳҜиҫҫзңҹеҲӣдҪң“дёүйғЁжӣІ”зҡ„еҸҷдәӢеҲқиЎ·гҖӮ
然иҖҢпјҢеңЁйҳ…иҜ»гҖҠе‘Ҫе®ҡгҖӢд№ӢеҗҺпјҢжҲ‘еҸ‘зҺ°пјҢиҝҷйғЁе°ҸиҜҙзңҹжӯЈжү“еҠЁжҲ‘зҡ„并йқһжҳҜдј з»ҹж„Ҹд№үдёҠзҡ„еҸІиҜ—жҖ§иҝҪжұӮпјҢиҖҢжҳҜйӮЈдәӣиә«д»ҪеҚ‘еҫ®зҡ„е°Ҹдәәзү©пјҢ他们и·Ңе®•иө·дјҸзҡ„з”ҹе‘Ҫж—…зЁӢпјҢиҝҳжңүз”ҹе‘Ҫзҡ„иӨ¶зҡұдёӯи•ҙи—үзқҖзҡ„еҜ№еҺҶеҸІгҖҒеҜ№е®—ж•ҷзҡ„зҗҶи§ЈгҖӮжҲ‘жғіпјҢжӯЈжҳҜиҝҷдәӣе°Ҹдәәзү©зҡ„“е‘Ҫе®ҡ”и®©жҲ‘们зңӢеҲ°дәҶдёҖдёӘзңҹе®һзҡ„еә·е·ҙпјҢеҰӮеҗҢжқҺ敬жіҪжүҖиҜҙпјҢ“(иҫҫзңҹзҡ„)дҪңе“ҒдёҚд»…д»…еұһдәҺеә·е·ҙзҡ„еҺҶеҸІе’Ңж–ҮеҢ–пјҢжӣҙеұһдәҺеә·е·ҙи—Ҹдәәзҡ„ж·ұеҲ»дәәжҖ§”гҖӮжҲ–и®ёпјҢиҝҷд№ҹжҒ°жҒ°д»ҺеҸҰдёҖдёӘеұӮйқўжһ„зӯ‘дәҶгҖҠе‘Ҫе®ҡгҖӢеҲ«ж ·зҡ„еҸІиҜ—е“Ғж јгҖӮ
дёҖ
гҖҠе‘Ҫе®ҡгҖӢйҮҮз”ЁдәҶеҸҢзәҝеҪ’дёҖзҡ„еҸҷдәӢз»“жһ„пјҢйўҮжңүдёӯеӣҪдј з»ҹе°ҸиҜҙзҡ„йҹөиҮҙгҖӮдёҠзҜҮ“ж•…д№Ў”и®Іиҝ°зҠҜдәҶж·«жҲ’зҡ„е°Ҹе–Үеҳӣеңҹе°”еҗүе’Ңеӣ иөӣ马зә зә·иҖҢжқҖдәәзҡ„иҙЎеёғеҗ„иҮӘеҜҢжңүдј еҘҮиүІеҪ©зҡ„ж•…дәӢпјӣдёӢзҜҮ“ејӮд№Ў”еҲҷе°ҶдёӨдёӘдәЎе‘ҪеӨ©ж¶Ҝзҡ„з”·еӯҗз»‘е®ҡеҲ°дёҖиө·пјҢжңҖеҗҺеңЁе‘Ҫиҝҗзҡ„е®үжҺ’дёӢпјҢ他们д№үж— еҸҚйЎҫең°иө°дёҠдәҶжҠ—ж—Ҙж•‘дәЎзҡ„йҒ“и·ҜгҖӮ
иҙЎеёғжҳҜе…ёеһӢзҡ„еә·е·ҙиЎҖжҖ§з”·е„ҝпјҢж•ўзҲұж•ўжҒЁпјҢдёәдәҶеҫ—еҲ°еҝғзҲұзҡ„еҘідәәйӣҚйҮ‘зҺӣпјҢд»–дёҠжј”дәҶдёҖеҮә“дәәжқҖеҲҖ”зҡ„дј еҘҮж•…дәӢпјҡеҫ’жүӢжҸЎдҪҸжғ…ж•ҢеҲәжқҘзҡ„еҲҖеҲғпјҢдёҖжҺ°дёӨеҚҠгҖӮиҝҷдёӘж•…дәӢдј йҒҚиҚүеҺҹпјҢдёҺж јиҗЁе°”зҺӢгҖҠең°зӢұж•‘еҰ»гҖӢзҡ„ж•…дәӢдёҖж ·йҪҗеҗҚгҖӮеҜ№иҙЎеёғиҖҢиЁҖпјҢзҲұжғ…еӣә然зҸҚиҙөпјҢдҪҶиҝҳжңүжҜ”зҲұжғ…жӣҙзҸҚиҙөзҡ„пјҢйӮЈе°ұжҳҜ“еҚЎжіўзғӯ”пјҲж„ҸеҚідёәдәҶйқўеӯҗд№ҹиҰҒз»ҷиҮӘе·ұдәүеҸЈж°”пјүгҖӮ“д»ҺиҙЎеёғиғҪи®°дәӢзҡ„йӮЈдёҖеӨ©иө·пјҢе°ұйҡҸзқҖе№ҙйҫ„зҡ„жёҗжёҗеўһй•ҝдҪ“дјҡеҲ°еҚ“科йғЁиҗҪзҡ„з”·дәәе’Ңеә·е·ҙз”·дәәеңЁжҹҗз§Қж„Ҹд№үдёҠйғҪжҳҜеңЁдёәйқўеӯҗиҖҢжҙ»зқҖгҖӮзӯүд»–й•ҝжҲҗеӨ§дәәеҗҺпјҢд»–еңЁиөӣ马еңәзңӢеҲ°йӘ‘жүӢ们еңЁдёә‘еҚЎйўҮзғӯ’иҝҷеҸҘиҜқиҫғеҠІпјӣеңЁйғЁиҗҪдёҺйғЁиҗҪй—ҙдёәдәүеӨәж“Қеңәзҡ„иҫғйҮҸдёҠпјҢд№ҹеңЁдёә‘еҚЎйўҮзғӯ’иҝҷеҸҘиҜқиҫғеҠІ……жҖ»д№ӢпјҢ‘еҚЎйўҮзғӯ’иҝҷеҸҘиҜқеңЁжҹҗдёҖ件дәӢжғ…дёҠдёҖж—ҰеңЁеҝғдёӯжҲ–еҳҙйҮҢиҜҙеҮәжқҘд№ӢеҗҺпјҢжҺҘдёӢжқҘзҡ„жј”еҸҳе’ҢеҸ‘еұ•жңүж—¶е°ұж— жі•жҺ§еҲ¶дәҶпјҢе®ғд№ҹи®ёдјҡз»ҷеҪ“дәӢдәәгҖҒ家еәӯгҖҒйғЁиҗҪеёҰжқҘеҘҪеӨ„пјҢз”ҡиҮіеёҰжқҘиҚЈиӘүпјҢеҸҚд№Ӣд№ҹи®ёдјҡеёҰжқҘдёҚеҲ©пјҢз”ҡиҮіжҳҜзҒҫйҡҫгҖӮ”жӯЈжҳҜеӣ дёә“еҚЎжіўзғӯ”пјҢд»–еңЁиөӣ马时жғ…з»ӘеӨұжҺ§иҖҢжқҖдәәпјҢд»ҺиҖҢжҠӣеҰ»ејғеӯҗпјҢиғҢдә•зҰ»д№ЎпјҢиў«еӣӣеӨ„иҝҪжқҖгҖӮеҗҢж ·жҳҜеӣ дёә“еҚЎжіўзғӯ”пјҢд»–еҘӢеӢҮжқҖж•ҢпјҢеұЎз«ӢжҲҳеҠҹпјҢжңҖеҗҺеҸӘиә«зӮёзўүе ЎиҖҢиӢұеӢҮзүәзүІпјҢжҲҗдёәдёҖеҗҚжҠ—ж—ҘиӢұйӣ„гҖӮ
жҲ‘们зңӢеҲ°пјҢиҙЎеёғжңҖеҲқ并дёҚжҳҜжҠұзқҖдҝқ家еҚ«еӣҪзҡ„иҝңеӨ§зҗҶжғіеҸӮеҠ иҝңеҫҒеҶӣзҡ„пјҢеҸӮеҶӣжҠ—ж—ҘеҜ№д»–иҖҢиЁҖпјҢе®һеұһж— еҘҲд№ӢдёҫпјҢеӣ дёәд»ҮдәәиҝҪжқҖжӯҘжӯҘзҙ§йҖјгҖӮд»–еңЁжҲҳеңәдёҠжқҖж•Ңзҡ„еҠЁеҠӣпјҢйҷӨдәҶдёәжӯ»еҺ»зҡ„е…„ејҹ们жҠҘд»ҮеӨ–пјҢжӣҙеӨҡзҡ„иҝҳжҳҜзјҳдәҺ“еҚЎжіўзғӯ”гҖӮеҲқж¬ЎжқҖж•Ңз«ӢеҠҹеҗҺпјҢд»–жғі“еҝ…йЎ»жқҖжӯ»жӣҙеӨҡзҡ„ж—Ҙжң¬й¬јеӯҗжүҚиғҪжңүжӣҙејәеҠӣзҡ„иғҪеҠӣе’ҢйқўеӯҗйҮҚиҝ”ж•…д№Ў……”иҖҢз«ӢеҠҹжҺҲеҘ–зҡ„еҘ–йҮ‘еҸҜд»Ҙи®©д»–иө”еҒҝжқҖдәәзҡ„“е‘Ҫд»·”пјҢдёҺ“еҰ»еӯҗйӣҚйҮ‘зҺӣе’Ңеӯ©еӯҗе°ҸиҙЎеёғеңЁйәҰеЎҳиҚүеҺҹиҝҮдёҠе®үе®Ғзҡ„ж—ҘеӯҗдәҶ”гҖӮ然иҖҢпјҢе°ұжҳҜиҝҷж ·дёҖдёӘ“иғёж— еӨ§еҝ—”зҡ„“еҚЎжіўзғӯ”пјҢжј”з»ҺдәҶеә·е·ҙз”·е„ҝжңҖд»ӨдәәиҚЎж°”еӣһиӮ зҡ„йўӮжӯҢгҖӮд»–еҜ№еҫ…жңӢеҸӢйҮҚжғ…йҮҚд№үпјҢеёёеҜ№еңҹе°”еҗүиҜҙпјҢдёӨдәәжҳҜ“еғҸзӯ·еӯҗдёҖж ·зҡ„е…„ејҹпјҢжқҘж—¶е°ұжҳҜдёҖеҸҢ”пјӣеҝғзҲұзҡ„еқҗйӘ‘йӣӘдёҠйЈһжҲҳжӯ»жқҖеңәпјҢ“д»–жҖҘеҝҷи·ӘдёӢжҠұдҪҸйӣӘдёҠйЈһзҡ„и„–еӯҗпјҢе°ҶеӨҙжҸҪеңЁиҮӘе·ұзҡ„жҖҖйҮҢеӨ§е“ӯиө·жқҘпјҢжӮІеЈ°йӣ·еҠЁгҖӮ……дҪ жӯ»жҲ‘жҙ»зҡ„еҸҢж–№еңЁд»ҝдҪӣеҮқеӣәзҡ„з©әж°”йҮҢзӣ®зқ№дәҶдёҖдёӘдёӯеӣҪеҶӣдәәж„ЈжҳҜз”ЁеҸҢжүӢеҲЁејҖдёҖдёӘеқ‘пјҢзӣҙеҲ°й»‘马зҡ„иә«дҪ“жҺ©еҹӢеңЁеқ‘йҮҢж¶ҲеӨұеңЁең°йқўдёӢдёәжӯў”гҖӮеҪ“ж—ҘеҶӣе Ўеһ’еҲ©з”ЁеӨҙйЎ¶дёҠеҺҡеҺҡзҡ„еІ©зҹіеҸ‘еҮәз–ҜзӢӮзҡ„жү«е°„пјҢдёҖдёӘжҺҘдёҖдёӘзҡ„зҲҶз ҙе°Ҹз»„зә·зә·еҖ’еңЁдәҶе Ўеһ’зҡ„жһӘеҸЈдёӢж—¶пјҢиҙЎеёғ“е°ҶдёҖйқўд»ҝеҲ¶зҡ„еІӯ·ж јиҗЁе°”еҫҒжҲҳж—¶жңҹзҡ„ж——еёңеғҸеӯҗеј№еёҰдёҖж ·еҒ·еҒ·жҚҶеңЁи…°й—ҙпјҢеҶҚж¬ЎеҸ‘еҮәеә·е·ҙз”·дәәзӢӮж”ҫдёҚзҫҒзҡ„еҗјеЈ°——ж №еҳҝеҳҝпјҒеҶІиҝӣжһӘжһ—еј№йӣЁ……”
жҲ‘и®ӨдёәпјҢеңЁдёӯеӣҪеҪ“д»Јж–ҮеӯҰеҸІдёҠпјҢй“ҒиЎҖжҹ”жғ…зҡ„з”·е„ҝеҪўиұЎе№¶дёҚе°‘и§ҒпјҢдҪҶеғҸиҙЎеёғиҝҷж ·жҠҠ“еҚЎжіўзғӯ”дҪңдёәдәәз”ҹдҝЎд»°зҡ„еә·е·ҙз”·е„ҝзҡ„зЎ®еҫҲе°‘гҖӮд»–жңәиӯҰеҸҲйІҒиҺҪпјҢд»—д№үеҸҲеҒҸзӢӯпјҢеҸҜд»ҘиҜҙпјҢд»–зҡ„зјәзӮ№дёҺдјҳзӮ№дёҖж ·йІңжҳҺгҖӮдҪҶеңЁе®¶еӣҪеӨ§д№үйқўеүҚпјҢд»–д№үж— еҸҚйЎҫпјҢд»ҘжңҖдёәиЎҖжҖ§зҡ„ж–№ејҸзҢ®еҮәиҮӘе·ұзҡ„з”ҹе‘ҪгҖӮеңЁд»–иә«дёҠиҜ йҮҠдәҶеә·е·ҙдәәеҜ№з”·жҖ§зҡ„зҗҶжғіе»әжһ„гҖӮд»ҺиҝҷдёӘж„Ҹд№үдёҠжқҘзңӢпјҢиҙЎеёғиҝҷдёҖеҪўиұЎдҫҝе…·жңүдәҶж–ҮеӯҰеҸІж„Ҹд№үгҖӮ
дәҢ
еҰӮжһңиҜҙиҙЎеёғиҝҷдёҖеҪўиұЎд»Һ“еҪўиҖҢдёӢ”зҡ„еұӮйқўпјҢеЎ‘йҖ дәҶжңүиЎҖжңүиӮүзҡ„е…ёеһӢеә·е·ҙз”·е„ҝпјӣйӮЈд№ҲпјҢеңҹе°”еҗүиҝҷдёҖеҪўиұЎеҲҷеңЁ“еҪўиҖҢдёҠ”зҡ„еұӮйқўпјҢиҜ йҮҠдәҶиҫҫзңҹеҜ№и—Ҹдј дҪӣж•ҷе’Ңи—Ҹж°‘ж—Ҹж–ҮеҢ–зҡ„зҗҶи§ЈгҖӮ
еңҹе°”еҗүиҮӘе№јиҒӘж•ҸпјҢжңүж…§ж №пјҢеӯҰд№ з»Ҹж–Үзҡ„иғҪеҠӣжҳҜжғҠдәәзҡ„пјҢжҲҗй•ҝе’ҢиҝӣжӯҘзҡ„йқһеёёеҝ«пјҢжң¬еҸҜд»ҘеғҸзҲ¶дәІйҖҒд»–еҮә家еүҚжүҖеҳұжүҳзҡ„“еҘҪеҘҪеҪ“е–ҮеҳӣпјҢз»ҷ家йҮҢдәүеҸЈж°””гҖӮ然иҖҢпјҢдёҖж¬ЎеҒ¶з„¶зҡ„жңәдјҡпјҢд»–зңӢеҲ°дәҶд»“еӨ®еҳүжҺӘзҡ„жғ…иҜ—гҖӮ“иҝҷдәӣиҜ—еҸҘиҜ»дёҠеҺ»еҫҲзҫҺпјҢйқһеёёиҝҮзҳҫпјҢдҪҶд»–жӣҙжҳҜеҝғз”ҹз–‘й—®пјҡ‘йҡҫйҒ“еғҸд»“еӨ®еҳүжҺӘиҝҷж ·иҮій«ҳж— дёҠзҡ„еӨ§е–Үеҳӣд№ҹж•ўжңүз”·еҘід№ӢзҲұпјҹ’йӮЈдёҖеҲ»пјҢд»–иў«иҝҷжң¬йӣҶеӯҗзҡ„иҜ—еҸҘж•ҙжҮөдәҶпјҢдјјд№Һе…ӯе№ҙжқҘеңЁеҝғйҮҢз”ЁдёҖеҸҘеҸҘз»Ҹж–ҮеЎ‘йҖ зҡ„еңЈж®ҝпјҢйЎ·еҲ»й—ҙиў«еҺҡеҺҡзҡ„дә‘еұӮйҒ®зӣ–дәҶгҖӮ”жӯЈжҳҜд»“еӨ®еҳүжҺӘзҡ„жғ…иҜ—пјҢжү“ејҖдәҶиҝҷдёӘеҲҡж»Ў17еІҒзҡ„е°Ҹе–Үеҳӣжғ…зҲұзҡ„й—ёй—ЁпјҢд»–иў«иӮүдҪ“зҡ„ж¬ІжңӣжүҖзә з»“пјҢз–ҜзӢӮең°зҲұдёҠдәҶеӨҙдәәзҡ„еҘіе„ҝиҙЎи§үжҺӘгҖӮиҝҷж®өжғ…зҲұеҜјиҮҙеҗҺжһңжҳҜеҸҜжҖ–зҡ„гҖӮзҠҜдәҶж·«жҲ’зҡ„еңҹе°”еҗүеҸ—еҲ°дәҶеҜәйҷўдёҘй…·зҡ„жғ©зҪҡпјҢжҺҢеҠҝзҡ„е–Үеҳӣ们еёҢжңӣз”ЁжңҖдёҘй…·зҡ„еҲ‘еҫӢжқҘжғ©жІ»еңҹе°”еҗүгҖӮд»–е’Ңд»–жғ…еҗҢзҲ¶еӯҗзҡ„и®Із»ҸеёҲеӮ…иҫҫжқ°иў«йһӯжү“еҫ—еҘ„еҘ„дёҖжҒҜпјҢйҡҸеҗҺеғҸжӯ»зӢ—дёҖж ·иў«жү”еҲ°еҜәйҷўй—ЁеӨ–гҖӮеңЁжӯӨпјҢжҲ‘们зңӢеҲ°пјҢжң¬еә”д»ҘеӨ§зҲұдёәжң¬гҖҒж…ҲжӮІдёәжҖҖзҡ„еҜәйҷўж— з–‘жҳҜеҶ·й…·зҡ„пјҢеҚідҫҝиҝһжҙ»дҪӣйғҪжё…жҘҡеҮӯеңҹе°”еҗүзҡ„иө„иҙЁпјҢдјҡжҲҗдёәдёҖеҗҚйқһеёёдјҳз§Җзҡ„е–ҮеҳӣпјҢдҪҶ他们дҫқ然没жңүз»ҷеңҹе°”еҗүж¶…ж§ғзҡ„жңәдјҡгҖӮдёҖдёӘе№ҙиҪ»е–Үеҳӣзҡ„еүҚйҖ”е°ұеӣ дёҖж¬Ўе°Ҹе°Ҹзҡ„иҝҮеӨұ被摧жҜҒдәҶгҖӮ“жүҖжңүзҡ„жҠӨжі•зҘһжҲҗдёәжўҰеўғйҮҢзҡ„иҷҡз©әпјҢе°Өе…¶еҸҢдҝ®зҡ„еӨ§еЁҒеҫ·йҮ‘еҲҡжҳҫеҫ—йҷҢз”ҹиҖҢеҶ·жј пјҢеҒҡеҮәдёҖеүҜ‘дәӢдёҚе…іе·ұй«ҳй«ҳжҢӮиө·’зҡ„жЁЎж ·”гҖӮиҖҢиҝҷз§ҚеҶ·жј зҡ„иғҢеҗҺпјҢе…¶е®һйҡҗи—ҸзқҖйҳҙжҡ—зҡ„дәәжҖ§гҖӮеңҹе°”еҗүжё…жҘҡпјҢжҒ°жҒ°жҳҜеӣ дёәиҮӘе·ұиҒӘж…§иҝҮдәәпјҢжҷӢеҚҮиҝҮеҝ«пјҢеј•иө·дј—еғ§еҰ’еҝҢпјҢжүҚдјҡеҜјиҮҙеҰӮжӯӨж®Ӣй…·зҡ„жғ©зҪҡгҖӮдё‘жҒ¶зҡ„дәәжҖ§йҒ®и”ҪдәҶзҘһжҖ§зҡ„е…үиҫүгҖӮ
зӣёеҸҚпјҢеңЁе°ҳдё–й—ҙеҖ’е……ж»ЎдәҶжё©жғ…гҖӮи®©еңҹе°”еҗүдёҮдёҮжғідёҚеҲ°зҡ„жҳҜпјҢжҠҠд»–д»ҺеһӮжӯ»зҡ„иҫ№зјҳж•‘еӣһзҡ„дәәпјҢз«ҹ然жҳҜеёёе№ҙеңЁеҜәйҷўеӨ–иҪ¬з»Ҹзҡ„йҳҝе……пјҢдёҖдёӘд»–еңЁеҒҡе–Үеҳӣж—¶дёҚеұ‘дёҖйЎҫзҡ„еӯӨиҖҒйҳҝе©ҶгҖӮиҖҢзҲ¶жҜҚдёҚд»…ж— еҫ®дёҚиҮіең°з…§ж–ҷд»–зҡ„иә«дҪ“пјҢиҝҳ“е°Ҷеңҹе°”еҗүзқЎи§үзҡ„жҜӣжҜЎж”ҫеңЁеёҗзҜ·зҡ„еҸідёҠж–№и·қдҪӣйҫӣдёҚиҝңзҡ„дҪҚзҪ®пјҢйӮЈжҳҜеңЁдёҖйЎ¶й»‘еёҗзҜ·дёӯжңҖеҸ—е°Ҡ敬зҡ„е–ҮеҳӣжҲ–жҳҜй•ҝиҫҲжүҚиғҪдә«з”Ёзҡ„дҪҚзҪ®”гҖӮиҝҷз»ҷдәҶд»–ејәеӨ§зҡ„зІҫзҘһеҠӣйҮҸгҖӮ然иҖҢпјҢзҲ¶жҜҚзҡ„иҝҷдёҖиЎҢдёәдёҖж—Ұиў«еҸ‘зҺ°пјҢ“еҜәеәҷе’ҢеӨҙдәәйҡҸж—¶еҸҜд»Ҙе°ҶиҝҷдёӘ家еәӯзҡ„иҙўдә§е…ЁйғЁжІЎж”¶пјҢйҖҗеҮәжң¬еҢәеҹҹпјҢдҪҝе…¶еҖҫ家иҚЎдә§гҖӮжғ…иҠӮзү№еҲ«дёҘйҮҚзҡ„иҰҒз”ұйғЁиҗҪеӨҙдәәиҒҡдј—пјҢйӮҖиҜ·еҜәеәҷзҡ„еӨ§е–Үеҳӣеҝөе’’з»ҸпјҢжҢҮе®ҡиҝҷжҲ·дәә家жҳҜйӯ”й¬јпјҢз”ҡиҮіеӨ„д»Ҙз ҚжүӢгҖҒз Қи…ҝгҖҒжҢ–зңјгҖҒеүҘзҡ®зӯүй…·еҲ‘”гҖӮзҙ жңӘе№із”ҹзҡ„иҙЎеёғеңЁеҚұжңәж—¶еҲ»еҶ’жӯ»её®еҠ©д»–йҖғзҰ»дәҶж—Ҹдәәзҡ„иҝҪжқҖгҖӮжүҖжңүиҝҷдәӣдәәй—ҙзҡ„ж— з§ҒеӨ§зҲұпјҢи®©д»–жёҗжёҗйўҶжӮҹеҲ°дәҶдҪӣж•ҷзҡ„зңҹи°ӣгҖӮи—Ҹдј дҪӣж•ҷй«ҳеғ§жӣҫеҰӮжӯӨиҜ„д»·д»“еӨ®еҳүжҺӘпјҢ“е…ӯдё–иҫҫиө–д»Ҙдё–й—ҙжі•и®©дҝ—дәәзңӢеҲ°дәҶеҮәдё–жі•дёӯе№ҝеӨ§зҡ„зІҫзҘһдё–з•ҢпјҢд»–зҡ„иҜ—жӯҢе’ҢжӯҢжӣІеҮҖеҢ–дәҶдёҖд»ЈеҸҲдёҖд»Јдәәзҡ„еҝғзҒөгҖӮд»–з”ЁжңҖзңҹиҜҡзҡ„ж…ҲжӮІи®©дҝ—дәәж„ҹеҸ—еҲ°дәҶдҪӣ法并дёҚжҳҜй«ҳдёҚеҸҜеҸҠпјҢд»–зҡ„зү№з«ӢзӢ¬иЎҢи®©жҲ‘们йўҶеҸ—еҲ°дәҶзңҹжӯЈзҡ„ж•ҷд№үпјҒ”еңЁгҖҠе‘Ҫе®ҡгҖӢдёӯпјҢеңҹе°”еҗүеҚіжҳҜд»“еӨ®еҳүжҺӘзҡ„дәәй—ҙеёғйҒ“иҖ…гҖӮд»–еҗҢж ·з”Ёд»–зҡ„зү№з«ӢзӢ¬иЎҢпјҢдј йҖ’еҮәжңҖзңҹиҜҡзҡ„ж…ҲжӮІгҖӮеҚідҪҝдҫқ然зғӯзҲұиҙЎи§үжҺӘпјҢдҪҶд»–зҡ„еҶ…еҝғж—¶еҲ»еқҡе®ҲзқҖеҜ№дҪӣзҡ„дҝЎд»°пјҢе°Өе…¶жҳҜеңЁд»ҺеҶӣеҗҺпјҢ“жҲҳеЈ«е’ҢдҪӣж•ҷеҫ’зҡ„еҸҢйҮҚиә«д»ҪеңЁж®Ӣй…·зҡ„жҲҳдәүдёӯиҺ·еҫ—дәҶеүҚжүҖжңӘжңүзҡ„дҪ“йӘҢпјҢиҝҷдёӘдҪ“йӘҢеңЁзўҺзүҮдёҠеҶҷзқҖпјҡдёҖдёӘеӣҪ家гҖҒдёҖдёӘж°‘ж—ҸгҖҒдёҖдёӘдёӘдҪ“пјҢдёҖж—ҰйқўдёҙйҮҺе…ҪдёҖж ·зҡ„еҶӣйҳҹзҡ„еҮҢиҫұпјҢж…ҲжӮІдёәжҖҖзҡ„иҸ©иҗЁеҝғйҮҢд№ҹе……ж»ЎдәҶжҶҺжҒЁпјҢзңҹжӯЈиЎЁиҫҫдәҶз”ҹе‘Ҫзҡ„жңҖй«ҳеўғз•Ң——зҲұе’ҢеҸӢе–„”гҖӮ
ж–Үжң¬дёӯеј•з”ЁдәҶдёҖдёӘжөҒдј еңЁзҶҠжңөиҚүеҺҹдёҠзңҹдҝЎдҪӣе’ҢеҒҮдҝЎдҪӣзҡ„ж•…дәӢпјҢжқҘйҳҗйҮҠеҜ№дҪӣзҡ„еҝғиҜҡжҳҜз”Ёдё–дҝ—зҡ„зңје…үйҡҫд»ҘеүҘејҖзңҹдјӘзҡ„гҖӮеҗҢж ·пјҢеңЁеңҹе°”еҗүиҝҷдёӘзү№з«ӢзӢ¬иЎҢзҡ„е–Үеҳӣиә«дёҠпјҢжҲ‘们зңӢеҲ°дәҶд»Җд№ҲжҳҜзңҹжӯЈзҡ„дҝЎд»°пјҢзңӢеҲ°дәҶи—Ҹдј дҪӣж•ҷжңҖдјҹеӨ§зҡ„зІҫзҘһеўғз•ҢгҖӮ
дёү
жҲ‘жіЁж„ҸеҲ°пјҢдёҚе°‘и—Ҹж—ҸдҪң家зҡ„еҸҷдәӢж–Үжң¬жҖ»жҳҜе……зӣҲзқҖжө“йғҒзҡ„иҜ—ж„ҸгҖӮзҝ»ејҖйҳҝжқҘзҡ„гҖҠе°ҳеҹғиҗҪе®ҡгҖӢпјҢжү‘йқўиҖҢжқҘзҡ„жҳҜйЈҳйӣ¶зҡ„жғҶжҖ…дёҺе“Җе©үпјҢејҘжј«гҖҒжөҒиҪ¬зқҖж— еҘҲзҡ„жң«дё–жғ…жҖҖгҖӮеңЁзҺ°д»ЈжҖ§дёҺдј з»ҹдҪ“еҲ¶зҡ„еҶІж’һдёӯпјҢеңҹеҸёзҺӢжңқеёҰзқҖжҢҪжӯҢејҸзҡ„жғ…и°ғпјҢе“ҖеҸ№еҮә“ж— еҸҜеҘҲдҪ•иҠұиҗҪеҺ»”зҡ„ж— йҷҗжҖ…жғӢгҖӮж¬Ўд»ҒзҪ—еёғзҡ„гҖҠзҘӯиҜӯйЈҺдёӯгҖӢд»ҺеҪўиҖҢдёӢзҡ„еұӮйқўеҺ»е…іжіЁзҺ°е®һпјҢжҸӯзӨәз”ҹжҙ»зҡ„иӢҰйҡҫпјҢдҪҶ并дёҚеӣҝдәҺз”ҹжҙ»жң¬иә«пјҢиӢҰйҡҫжң¬иә«пјҢиҖҢжҳҜд»ҘдёҖз§Қи¶…и¶Ҡзҡ„е®—ж•ҷжғ…жҖҖеҺ»зҗҶи§ЈиӢҰйҡҫпјҢжңҖз»Ҳи¶…и¶ҠиӢҰйҡҫпјҢжҠөиҫҫдёҖз§Қи¶…и¶Ҡзҡ„зІҫзҘһй«ҳеәҰгҖӮи—Ҹдј дҪӣж•ҷдёӯи•ҙи—үзҡ„ж…ҲжӮІгҖҒйҡҗеҝҚгҖҒж•‘иөҺзӯүз»ҲжһҒжғ…жҖҖпјҢжЁЎзіҠдәҶеҶ·жҡ–дёӨжһҒпјҢи¶ҠиҝҮиӢҚеҮүпјҢе‘ҲзҺ°еҮәжё©жҡ–зҡ„иҜ—ж„ҸгҖӮеҗҢж ·пјҢиҫҫзңҹд№ҹжҳҜеҰӮжӯӨгҖӮж— и®әжҳҜд»–зҡ„гҖҠеә·е·ҙгҖӢпјҢиҝҳжҳҜгҖҠе‘Ҫе®ҡгҖӢйғҪжңүзқҖеҫҲж·ұзҡ„иҜ—ж„ҸгҖӮ
иҫҫзңҹзҡ„еҸҷиҝ°ж—¶еёёдјҡе°ҶиҮӘ然дёҺдәәиҒ”зі»еңЁдёҖиө·пјҢ他笔дёӢзҡ„дёҮзү©йғҪжІүжөёеңЁе……ж»ЎзҒөжҖ§зҡ„дё–з•ҢдёӯпјҢиҚүеҺҹгҖҒеұұеіҰгҖҒеӨ©з©әж•ЈеҸ‘зқҖз”ҹе‘Ҫзҡ„ж°”жҒҜгҖӮд»–з”ЁжңҖзңҹжҢҡзҡ„жғ…ж„ҹеҺ»жҚ•жҚүжҜҸдёҖдёӘеҠЁдҪңпјҢйЈҺдјјд№ҺеҸҜд»Ҙи§Ұж‘ёпјҢиҚүеҺҹдёҠдёҖеҲҮйғҪиў«иөӢдәҲдәҶ“иҜқиҜӯжқғ”пјҢе°ұиҝһж—¶й—ҙд№ҹеҸҳеҫ—еҰӮжӯӨз”ҹеҠЁпјҢдёҺ他笔дёӢзҡ„дәәзү©е®һзҺ°дәҶзІҫзҘһзҡ„“иҒ”иўӮ”пјҡ
йӮЈдёҖж—¶еҲ»зҡ„йәҰеЎҳиҚүеҺҹеҮәеҘҮең°еҜӮйқҷпјҢиҝһй«ҳиҝҮиҶқзӣ–зҡ„еһӮз©—жҠ«зўұиҚүе…ЁйғҪйҪҗеҲ·еҲ·ең°иҖ·жӢүзқҖиҚүе°–пјҢеҫҲжҳҺжҳҫпјҢйҖ жҲҗз©әж°”жөҒеҠЁзҡ„дҪҝиҖ…——йЈҺпјҢдҫқж—§иҝҳеңЁжү“зӣ№гҖӮ
йЈҺзә№дёқдёҚеҠЁең°иәәеңЁж—¶й—ҙзҡ„жҖҖйҮҢпјҢе”ҜзӢ¬еҗ‘еүҚиө¶и·Ҝзҡ„ж—¶й—ҙжҺЁзқҖеӨ©з©әдёҠйғЁзҡ„иүІеқ—ж…ўж…ўжөёеҮәж·ұи“қиүІпјҢдёӢйғЁзҡ„иүІеқ—дҫқж—§й»‘жҡ—пјҢиүІеқ—зҡ„з»“еҗҲйғЁжҳҜдёҖзүҮжҳҸжҡ—зҡ„е…үеҪұеҲҶз•ҢзәҝпјҢеҘ№еңЁжңҰиғ§гҖҒе№Ҫж·ұдёӯжҡ—зӨәжүҖжңүзҡ„иҚүеҺҹз”ҹзҒөпјҢж—¶й—ҙжӯЈеңЁеҲ»жқҝиҖҢе®Ҳж—¶ең°еңЁе®Ғйқҷдёӯеҗ‘ж–°зҡ„дёҖеӨ©иө°жқҘпјҢиҚүеҺҹзҒөеҠЁзҡ„зҷҪеӨ©еҚіе°ҶејҖе§ӢгҖӮ
иҮӘе№јз”ҹй•ҝдәҺи—Ҹең°зҡ„иҫҫзңҹпјҢе№ёиҝҗең°иҺ·еҫ—дәҶжӣҙеӨҡдёҺиҮӘ然жҺҘи§Ұзҡ„жңәдјҡгҖӮжӯЈжҳҜеңЁдёҺиҮӘ然зҡ„иҖій¬“еҺ®зЈЁдёӯпјҢдә§з”ҹдәҶдёҖз§Қе»әз«ӢеңЁдёҮзү©жңүзҒөи®әеҹәзЎҖдёҠзҡ„иҮӘ然и§ӮгҖӮиҮӘ然дёҮзү©дёҺдәәжңүзқҖзӣёеҗҢзҡ„з”ҹе‘Ҫж №еҹәпјҢеҰӮеҗҢж°ҙд№ідәӨиһҚпјҢиғҪеӨҹиҺ·еҫ—еҝғзҒөдәӨж„ҹгҖӮеӣ жӯӨпјҢж–Үжң¬дёӯдәәзү©и·Ңе®•иө·дјҸзҡ„е‘Ҫиҝҗд№ҹеҫҖеҫҖйҖҡиҝҮиҮӘ然ж„ҸиұЎеҠ д»Ҙе‘ҲзҺ°гҖӮжҲ‘们зңӢеҲ°пјҢеңЁеңҹе°”еҗүдёәдәҶдёҚиҝһзҙҜиҙЎи§үжҺӘиҖҢиҝһеӨңйҖғи·‘зҡ„йӮЈдёӘеӨңжҷҡпјҢдёҖиҪ®жҳҺжңҲе§Ӣз»ҲдёҺд»–дёҚзҰ»дёҚејғпјҡ
жј«й•ҝзҡ„жҠҳзЈЁдҪҝиәәеңЁиҙЎи§үжҺӘиә«иҫ№зҡ„еңҹе°”еҗүж— жі•е…ҘзқЎпјҢе°ұеңЁжҹҙзҒ«зҮғе°ҪдҫқзЁҖеҸ‘еҮәеҷје•Әеҷје•Әзҡ„зӮёиЈӮеЈ°дёӯпјҢжҙһеҸЈеӨ„дёҖйҒ“еҶ°еҮүзҡ„жңҲе…үеӮ¬йҖғдјјзҡ„жі»еңЁжіҘең°дёҠпјҢ“и¶ҒеҘ№зҶҹзқЎпјҢеҖҹзқҖжңҲе…үпјҢйҖғеҗ§гҖӮ”……
……жӯӨеҲ»пјҢеӨңеңЁжңҲдә®зҡ„йҷӘдјҙдёӢеҗ¬и§Ғеңҹе°”еҗүзҡ„еҝғеңЁдёҺжғ…дәәиҜҙпјҡ“еҝғиӮқпјҢи„ӮиӮӘпјҢзӯүжҲ‘еңЁеӨ–й—ҜиҚЎжҢЈеҲ°дәҶй’ұпјҢжҲ‘дјҡиө¶зқҖйӘЎй©¬й©®зқҖйҮ‘银иҙўе®қгҖҒз»«зҪ—з»ёзјҺжқҘиҝҺеЁ¶дҪ зҡ„пјҢжҲ‘дјҡеҸ«дҪ зҡ„еӨҙдәәйҳҝзҲёдёҚеҶҚе°ҸзңӢжҲ‘гҖӮеҰӮжһңдёҚжҲҗпјҢзӯүдёӢиҫҲеӯҗдёҚеҒҡе–Үеҳӣзҡ„ж—¶еҖҷпјҢеҶҚеҒҡеӨ«еҰ»пјҒ”д»–еҖҹзқҖжңҲе…үд»”з»Ҷең°з«ҜиҜҰдәҶеҘ№зҡ„йқўеӯ”пјҢиҜҙдёҖеҸҘз§Өз ЈйӮЈд№ҲйҮҚзҡ„иҜқпјҡ“еҶҚи§ҒдәҶпјҢиҙЎи§үжҺӘпјҒ”
……еҶ°еҶ·еҶ·зҡ„жңҲе…үз…§еңЁеңҹе°”еҗүжҠ•еңЁең°йқўдёҠзҡ„иә«еҪұпјҢеңҹе°”еҗүдјёжүӢжҢүдҪҸжҢӮеңЁи…°й—ҙзҡ„йәҰиӢҰпјҲзҒ«й•°иўӢпјүе’ҢжҙӣзӣҙпјҲеҗҠеҲҖпјүпјҢжҖ•е®ғ们弄еҮәеЈ°е“ҚпјҢеёҰзқҖиҙҹеҝғзҡ„дёҚе®ү蹑жүӢ蹑и„ҡең°ж¶ҲеӨұеңЁеІ©жҙһеӨ–пјҢеғҸи§ҒдёҚеҫ—дәәзҡ„еҒ·зүӣзӣ—马иҙјдёҖж ·ж¶ҲеӨұеңЁжё…иҫүзҡ„жЁЎзіҠеӨ„гҖӮжһҒе…·жӮІеү§ж„ҹе’ҢжөӘжј«иүІеҪ©зҡ„жңҲе…үжңҖиғҪдҪ“дјҡд»–жӯӨеҲ»зҡ„еӨҚжқӮеҝғеўғ……
……еӨҙдёҠзҡ“жңҲзӣҙи§ҶзқҖд»–еғҸдёҖеҢ№жҪңиЎҢзҡ„еӯӨзӢјеңЁжңҲиүІйҮҢжІЎе‘Ҫең°еҘ”и·‘пјҢиә«дҪ“еҗҢз©әж°”ж‘©ж“ҰеҮәжұ—ж¶ІйҖҸеҮәд»–зҡ„жғҠж…ҢзЁӢеәҰпјҢж•ҙдёӘйҖғи·‘д№ӢеӨңпјҢд»–жңҖжӢ…еҝғзҡ„дёҚжҳҜйҘҝзӢјзҡ„иўӯеҮ»пјҢиҖҢжҳҜжӢ…еҝғиҙЎи§үжҺӘзҡ„еҮәзҺ°гҖӮ……
еңЁдҪӣж•ҷж–ҮеҢ–дёӯпјҢжңҲж„ҸиұЎзҡ„ж„Ҹи•ҙйқһеёёдё°еҜҢгҖӮе…¶дёӯпјҢдҪҝз”ЁиҫғеӨҡзҡ„жҳҜд»ҘжңҲж„ҸиұЎе–»жҢҮдҪӣжҖ§жң¬иҮӘжё…йқҷзҡ„ж•ҷд№үгҖӮгҖҠдҪӣиҜҙжңҲе–»з»ҸгҖӢдә‘ пјҡ“зҡҺжңҲеңҶж»ЎпјҢиЎҢдәҺиҷҡз©әпјҢжё…еҮҖж— зўҚ”гҖӮ“зҠ№жңҲиЎҢз©әпјҢжё…еҮҖж— зўҚгҖӮиӯ¬жҳҺзңјдәәпјҢж¶үеұҘиҜёйҷ©пјҢзҰ»иҜёз–‘жғ§гҖӮ”жҢҮеҮәдҪӣжҖ§жң¬иҮӘжё…еҮҖпјҢзҠ№еҰӮжҳҺжңҲиЎҢз©әпјҢдҝ®иЎҢиҖ…дёҖж—ҰжӮҹеҫ—пјҢеҲҷеҸҜдёҚз–‘дёҚжғ§гҖӮиҖҢдёӯеӣҪеҸӨе…ёиҜ—жӯҢеҫҲж—©дҫҝд»ҘжңҲе…ҘиҜ—пјҢеҮ д№ҺжҜҸдёҖдёӘдёӯеӣҪеҸӨд»ЈиҜ—дәәзҡ„иҜ—жӯҢдёӯйғҪдјҡеҮәзҺ°“жңҲ”гҖӮиҝҷз§ҚиҜ—жӯҢзҡ„иЎЁиҫҫж–№ејҸеңЁиҜ—дҪӣдҝұзӣӣзҡ„е”җе®Ӣж—¶жңҹдҝғдҪҝдҪӣзҰ…иЎЁиҫҫж–№ејҸжҳҺжҳҫеҮәзҺ°иҜ—еҢ–гҖҒзҫҺеҢ–гҖҒж„ҸеўғеҢ–зҡ„еҖҫеҗ‘пјҢзҰ…е®—дёӯзҡ„жңҲж„ҸиұЎд№ҹиў«е®ЎзҫҺеҢ–гҖӮд»ҺиҝҷдёӘи§’еәҰзңӢпјҢж–Үжң¬дёӯеңҹе°”еҗүйҖғи·‘иҝҮзЁӢдёӯзҡ„жңҲж„ҸиұЎпјҢ并йқһжҳҜеҸҜжңүеҸҜж— зҡ„зҺҜеўғзғҳжүҳпјҢе®ғж·ұеҗ«зқҖдҪӣжҖ§жң¬иҮӘжё…йқҷзҡ„еҜ“ж„ҸпјҢеҫҲеҘҪең°еҸҚиЎ¬еҮәеңҹе°”еҗүжҢЈжүҺеңЁжғ…ж¬ІдёҺдҪӣжҖ§д№Ӣй—ҙзҡ„еҶ…еҝғж…Ңд№ұдёҺзә з»“пјҢеҗҢж—¶пјҢеҸҲиҗҘйҖ еҮәдёҖдёӘе……ж»ЎиҜ—ж„Ҹзҡ„з©әй—ҙпјҢи®©дәәзү©еңЁиҜ—ж„Ҹзҡ„з»ҙеәҰдёӯеҠӘеҠӣеҺ»иҝҪжұӮдёҖз§ҚзІҫзҘһзҡ„ж°ёжҒ’гҖӮгҖҠе‘Ҫе®ҡгҖӢдёӯеғҸиҝҷж ·йҖҡиҝҮиҮӘ然ж„ҸиұЎжқҘеҲ»з”»дәәзү©гҖҒжҺЁиҝӣжғ…иҠӮзҡ„дҫӢеӯҗиҝҳжңүеҫҲеӨҡпјҢе®ғ们еҰӮеҗҢдёҖеқ—еқ—з”ҹжҙ»жҲ–жғ…ж„ҹзҡ„“зўҺзүҮ”пјҢеңЁиҜ—ж„Ҹзҡ„ж°ӣеӣҙеңәжҷҜдёӯпјҢдёҺдәәзү©д№Ӣй—ҙеӢҫиҝһиө·жҲ–еҫ®еҰҷгҖҒжҲ–жңҙзҙ гҖҒжҲ–еӣ°зӘҳзҡ„е…ізі»пјҢд»ҘеҸҠзӣёдә’й—ҙзңҹиҜҡзҡ„ж„ҹеә”гҖӮеҸҜд»ҘиҜҙпјҢиҫҫзңҹд»ҘдёҖз§Қзӣҙи§үзҡ„жҠҠжҸЎдёәж®Ӣй…·зҡ„зҺ°е®һжҷ•жҹ“дёҠдёҖеұӮиҜ—ж„Ҹзҡ„е…үзҺҜгҖӮ
гҖҠе‘Ҫе®ҡгҖӢзҡ„зЎ®з»ҷжҲ‘们еёҰжқҘж–°йІңзҡ„йҳ…иҜ»дҪ“йӘҢгҖӮж–Үжң¬дёҚд»…еЎ‘йҖ дәҶдёӯеӣҪеҪ“д»Јж–ҮеӯҰеҸІдёҠйІңи§Ғзҡ„е…ёеһӢеә·е·ҙз”·е„ҝеҪўиұЎиҙЎеёғпјҢеҗҢж—¶пјҢд№ҹйҖҡиҝҮеңҹе°”еҗүиҝҷдёӘдәәзү©иҜ йҮҠеҮәи—Ҹдј дҪӣж•ҷзҡ„зңҹи°ӣгҖӮеңЁиҝҷдёӨдёӘе‘ҪиҝҗеқҺеқ·зҡ„е°Ҹдәәзү©иғҢеҗҺпјҢжҳҜдёҖж®өжӣҫз»ҸиҪ°иҪ°зғҲзғҲзҡ„еҺҶеҸІеҚ°и®°пјҢиҖҢе……ж»ЎиҜ—ж„Ҹзҡ„еҸҷиҝ°ж— з–‘еӨҚиӢҸдәҶжҲ‘们дёҖеәҰиҝ·еӨұзҡ„зҘһжҖ§и§Ӯз…§гҖӮйҷҲжҷ“жҳҺеңЁиҜ„д»·иҫҫзңҹзҡ„е°ҸиҜҙгҖҠеә·е·ҙгҖӢж—¶иҜҙпјҡ“пјҲиҫҫзңҹпјүиҺ·еҫ—дәҶж–°зҡ„еҺҶеҸІи§ҶйҮҺгҖӮжүҖд»ҘиҝҷйғЁе°ҸиҜҙжҳҜжҠҠдј з»ҹзҡ„еҸІиҜ—е’ҢзҺ°д»Јзҡ„дәӢдёҡеҠ еңЁдёҖиө·пјҢжүҖд»ҘжңүдёҖдёӘеҫҲй«ҳзҡ„иө·зӮ№гҖӮ……зҺ°д»Јиҝӣе…Ҙи—Ҹж—Ҹж–ҮеҢ–пјҢи—Ҹж—Ҹиҝӣе…ҘзҺ°д»ЈпјҢе®ғе’ҢзҺ°д»ЈзӣёйҒҮзҡ„е‘ҪиҝҗпјҢиҝҷд№ҹжҳҜйқһеёёжңүеҺҶеҸІж·ұеәҰзҡ„дёңиҘҝгҖӮдҪңиҖ…жҠ“дҪҸиҝҷж ·дёҖдёӘеҺҶеҸІзҺҜиҠӮеҺ»еҶҷпјҢиҝҷдёӘз»ҙеәҰжҠҠжҸЎеҫ—йқһеёёеҘҪпјҢе°ұжҳҜеңЁдёҖдёӘеҸІиҜ—зҡ„еҲӣдҪңдёӯжңүдёҖдёӘзҺ°д»Јзҡ„и§ҶйҮҺ”гҖӮеңЁжӯӨпјҢйҷҲжҷ“жҳҺжҸҗеҮәдәҶдёҖдёӘеҖјеҫ—жҲ‘们ж·ұжҖқдёҺжҺўз©¶зҡ„й—®йўҳпјҢеҚіеҸІиҜ—еҲӣдҪңдёӯзҡ„зҺ°д»Ји§ҶйҮҺй—®йўҳгҖӮжҲ‘жғіпјҢжҲ–и®ёеңЁгҖҠеә·е·ҙгҖӢд№ӢеҗҺпјҢгҖҠе‘Ҫе®ҡгҖӢеҜ№иҝҷдёҖй—®йўҳеҒҡеҮәдәҶеҸҲдёҖж¬ЎеҠӘеҠӣзҡ„жҖқиҖғе’Ңе°қиҜ•гҖӮ
еҺҹеҲҠдәҺгҖҠйҳҝжқҘз ”з©¶гҖӢ第дёғиҫ‘

жўҒжө·пјҢеҘіпјҢеӨ§иҝһзҗҶе·ҘеӨ§еӯҰдәәж–ҮеӯҰйҷўж•ҷжҺҲпјҢеҚҡеЈ«з”ҹеҜјеёҲгҖӮдё»иҰҒд»ҺдәӢж–ҮеӯҰжү№иҜ„е’ҢдёӯеӣҪзҺ°еҪ“д»Јж–ҮеӯҰз ”з©¶гҖӮиҝ‘е№ҙжқҘеҮәзүҲеӯҰжңҜдё“и‘—1йғЁпјҢеңЁгҖҠе…үжҳҺж—ҘжҠҘгҖӢгҖҠдәәж°‘ж—ҘжҠҘгҖӢгҖҠж–ҮиүәдәүйёЈгҖӢгҖҠеҪ“д»ЈдҪң家иҜ„и®әгҖӢгҖҠж–ҮиүәзҗҶи®әдёҺжү№иҜ„гҖӢгҖҠеҚ—ж–№ж–ҮеқӣгҖӢгҖҠе°ҸиҜҙиҜ„и®әгҖӢгҖҠеҪ“д»Јж–ҮеқӣгҖӢгҖҠдёӯеӣҪдҪң家гҖӢзӯүеҲҠзү©еҸ‘иЎЁеӯҰжңҜи®әж–Ү80дҪҷзҜҮпјҲе…¶дёӯдёӯж–Үж ёеҝғжңҹеҲҠ58зҜҮпјҢCSSCI收еҪ•30дҪҷзҜҮгҖӮз ”з©¶жҲҗжһңиў«дәәеӨ§еӨҚеҚ°иө„ж–ҷе…Ёж–Ү收еҪ•6зҜҮпјүгҖӮдё“и‘—гҖҠе°ҸиҜҙзҡ„е»әзӯ‘гҖӢиҺ·з¬¬дёғеұҠиҫҪе®Ғж–ҮеӯҰеҘ–гҖ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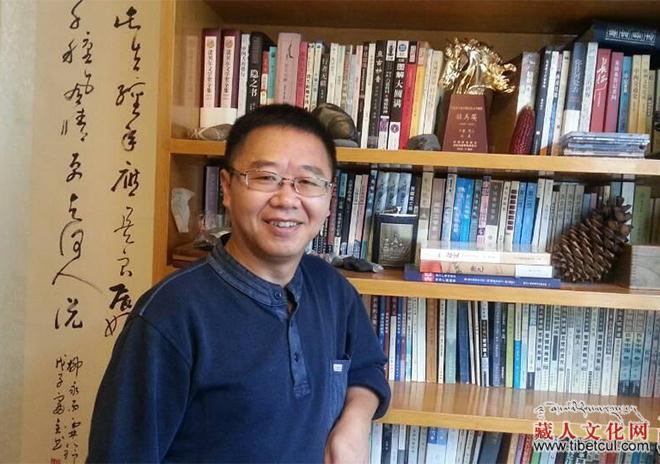
иҫҫзңҹпјҢи—Ҹж—ҸпјҢдёӯеӣҪдҪң家еҚҸдјҡдјҡе‘ҳпјҢдёӯеӣҪе°‘ж•°ж°‘ж—ҸдҪң家еӯҰдјҡзҗҶдәӢпјҢе·ҙйҮ‘ж–ҮеӯҰйҷўзӯҫзәҰдҪң家пјҢи‘—жңүй•ҝзҜҮе°ҸиҜҙгҖҠеә·е·ҙгҖӢгҖҠе‘Ҫе®ҡгҖӢгҖӮе…¶дёӯ,гҖҠеә·е·ҙгҖӢиҺ·з¬¬еҚҒеұҠе…ЁеӣҪе°‘ж•°ж°‘ж—Ҹж–ҮеӯҰеҲӣдҪңй•ҝзҜҮе°ҸиҜҙ“йӘҸ马еҘ–”пјҢж №жҚ®гҖҠеә·е·ҙгҖӢж”№зј–зҡ„еӨ§еһӢе№ҝж’ӯеү§иҺ·з¬¬еҚҒдәҢеұҠе…ЁеӣҪ“дә”дёӘдёҖ”е·ҘзЁӢеҘ–е’Ң2012е№ҙеәҰеӣӣе·қзңҒ“дә”дёӘдёҖ”е·ҘзЁӢзү№еҲ«еҘ–пјҢ并зҝ»иҜ‘жҲҗиӢұж–ҮеҮәзүҲпјӣгҖҠе‘Ҫе®ҡгҖӢиҺ·2012е№ҙеәҰеӣӣе·қзңҒ“дә”дёӘдёҖ”е·ҘзЁӢеҘ–пјҢ并е…ҘйҖү “2012з»Ҹе…ёдёӯеӣҪеӣҪйҷ…еҮәзүҲе·ҘзЁӢ”иө„еҠ©йЎ№зӣ®гҖ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