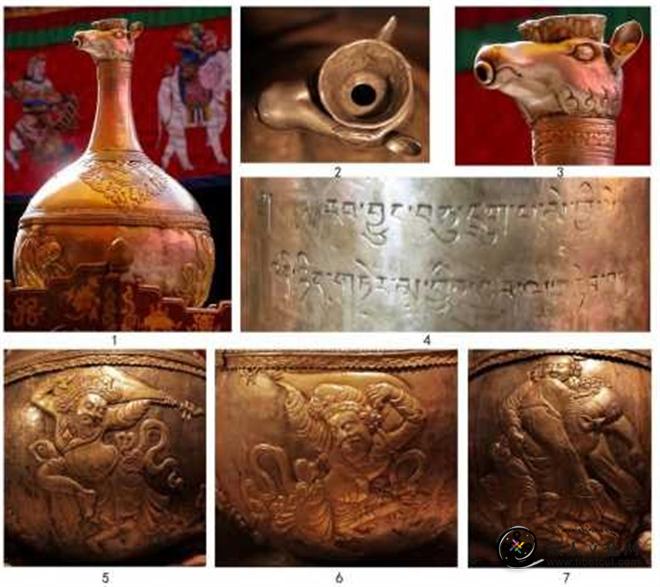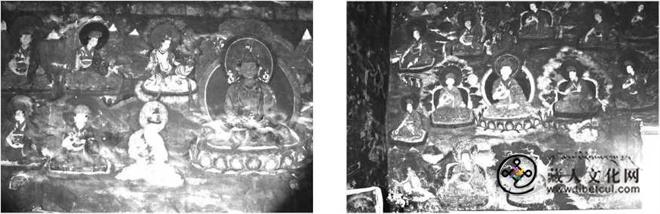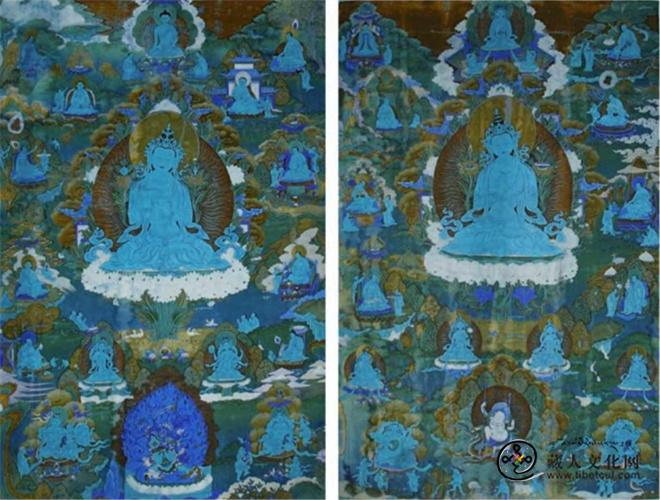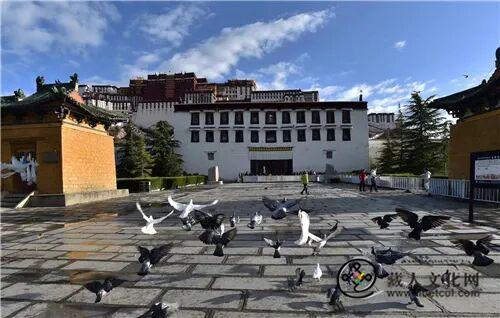摄影:觉果
摄影:觉果
摘要:文章立足现有的中英文史料,以汉藏通婚为考察维度,从汉人移民史的角度梳理了清代民国巴塘汉藏关系的互动进程,即从清初的族际区隔逐步走向民国中后期的深度交融,集中表现在此间巴塘汉藏通婚数量的日益增多,尤其是民国时期当地汉藏文化广泛地相互采借、浸润与融合,而长期浸润其中的巴塘人亦身具汉藏复合文化特质,其中最典型的即通晓汉藏文。在民国时期汉藏存在隔膜的历史背景下,巴塘地方汉藏民族的交往交流的增加和交融的实现不但稳固了内地中央政府在藏地边疆的“治权”与“国防”,更使兼备汉藏文化特性的巴塘青年一跃成为联结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甚至1949年以后汉藏关系的强力纽带之一,并持续推动着汉藏间的沟通与交流。
关键词:巴塘;汉人移民;汉藏通婚;文化交融;汉藏联结
民国时期,因语言差异与政治滞碍,汉藏民族关系整体出现了一定的困难与隔膜,但即使如此,一些爱国的汉藏人士与组织仍努力在宗教、商贸、政治等领域推动汉藏间的沟通与交流。这其中就包括一批在内地从事汉藏语文翻译的巴塘人。对此,曾任西康民众驻京代表办事处代表的陈强立(1911—1985)晚年时曾回忆道:
他[按:格桑泽仁]从西康边远之地招来许多青年在内地就学,这是一件好事,尤其是其中有不少通晓汉藏文的人,如刘家驹、格桑悦希(格桑泽仁之弟,国民党监察委员)、江安西、黄玉兰、邓珠拉姆等,翻译汉藏文件,对汉藏文化交流起了很好的作用。
尽管陈氏本欲指称的对象为西康青年,但其所举诸人却皆为巴塘人,由此更凸显出巴塘青年在其中的代表性与重要性。如引文所示,巴塘人得以“对汉藏文化交流起了很好的作用”,关键在于他们“通晓汉藏文”。而据史料记载,民国时期巴塘人兼通汉藏双语是极为普遍的现象。1947年,蒙藏教育司即指出,巴塘“汉康杂居,男女老幼,皆能操康汉两种语言”。
巴塘位于青藏高原东部,为何民国时期当地人“皆能操康汉两种语言”?前贤指出,这一独特的文化现象是清代民国移民巴塘的汉人与本地藏人经由族际通婚等互动进程而产生的汉藏交融结果。但因材料散佚,加之研究重点不同,既有研究对清代民国巴塘的汉藏关系如何走向交融的历史叙述,尤其是对不同时期当地汉藏通婚的史实呈现,既不系统,史料基础也存有较大的可拓展空间,并且对巴塘汉藏交融的历史影响也未予以充分注意。
有鉴于此,本文广泛搜集包括档案、期刊、日记、回忆录、传记与年谱、文史资料等多种史料,钩沉索隐,以汉藏通婚为考察维度,从汉人移民史的角度对清代民国巴塘汉藏关系的历史演进与阶段特征作长时段的文献梳理与史实分析,以求最大可能地复现这一时段巴塘汉藏互动的历史轮廓,以期从微观/地方的视角丰富对民国时期汉藏民族交流史的整体认识,也为进一步深入理解民国康藏史乃至汉藏交流史提供新的史实基础与思考线索。
一、清初至1905年:从族际区分走向汉藏交融
检视材料,焦应旂所著《藏程纪略》是目前所见最早记载汉人移民巴塘的清代史料。康熙六十年(1721)二月,焦应旂自西藏出发,经川藏道东返内地,途经巴塘时发现,“集市之所,内地汉人亦寓此贸易”F。此后,汉人在巴塘的踪迹时见于文献记载。乾隆十六年八月癸亥(1751年10月18日),四川总督策楞额奏称:“查各省民人在打箭炉以外贸易者,不止西藏一带,如类乌齐、察木多、乍丫及里塘、巴塘、明正土司所属地方在在都有。”《巴塘志略》是巴塘最早的汉文志书,由巴塘粮员钱召棠辑成,经考订,成书于“道光二十四年或次年初”。内载,巴塘“番汉居民数百家”;在竹巴笼,“汉土数十家皆傍水楼居”。道光二十五年(1845),姚莹途经巴塘发现,当地“蛮民数百户,有街市,皆陕西客民贸易于此”。道光二十六年(1846),法国遣使会会士古伯察(Régis-EvaristeHuc,1813—1860)由藏被押解回内地,曾停住巴塘3天,他称:“我们在巴塘的居民中发现了一大批汉人,从事手艺和产业,甚至还有些人从事农业和开发藏族人的庄园。”光绪三十年(1904)五月,巴塘粮员吴锡珍在一份呈禀中写道:“巴塘汉夷杂处,……汉民则多半客籍,且习于经商。”从以上材料来看,汉人早在康熙年间就已居于巴塘,主要从事贸易经商,也有以手艺和农业种植为生者,至于这些早期移民的数量,既有材料皆语焉不详。
除汉商一类的自发移民外,同一时期巴塘还有另一个重要的汉人群体,即由内地派驻于此的清朝文武官弁。为保障川藏大道的畅通,清朝自康熙末年以来就陆续在巴塘等进藏节点设置塘汛,派兵戍守。目前所知最早记载巴塘戍兵数的清代史料是《雍正四川通志》。据载,雍正时期,巴塘戍兵分“兵”与“土兵”两类,其中“兵”即由内地选派至此的绿营兵勇,计有286人。至道光年间,“兵”已大为减少,缺额由“土兵”增补。《巴塘志略》载:“现在随营差遣马步兵八十三名,均由内地操营捡派,三年更换……;乾隆三十三年,添设土马兵一百四十名,土步兵六十五名。”可见,至道光年间,巴塘的绿营兵已从雍正时期的286人锐减至83人。1846年,古伯察在巴塘期间窥察到,“清朝兵站共由300名兵勇组成”。比照《巴塘志略》的记载来看,这一数额应指巴塘汉、土兵弁的总数。同治年间途经巴塘的英国商人库柏(T.T.Cooper)称,当地“一名(汉人)低级军官掌控着一支由180名汉人士兵组成的分遣队”。1900年,游历至巴塘的英国人H.R戴维斯发现,“镇里有三个汉人官员,一个文官,两个武官。后者指挥一支70人的卫戍部队”。综上,在1900年以前,因时局变幻,清代巴塘的汉军驻兵数存在阶段性浮动,并整体呈下降趋势,但最低也维持在数十人的规模。可见,此一时段,汉人官弁一直是巴塘人口中不容忽视的重要存在。
那么,当内地汉人在清初移民至巴塘时,面对这个以藏传佛教为底色的传统藏族社会,他们如何处理与本地社会的关系呢?而随着移民进程的推进,当地的汉藏关系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
关于清朝中前期巴塘的汉藏关系,当前存留下的直接材料非常少,但幸运的是,此间汉人在巴塘的一些活动为我们提供了少许极有价值的讯息。据巴塘地方史志记载,雍正五年(1727),早期到巴塘的汉商曾相约组建汉商公会,又名财神会。乾隆十三年(1748),巴塘“汉民公建”关帝庙于堡东,而在河西岸的龙王堂则由“土民公建”。未久,当地的绿营官兵加入财神会,并分建单刀圣会,与汉商公会并置。1874年,4年前被地震毁坏的关帝庙重建完毕,是时巴塘汉人将财神会扩建为“川陕滇三省同乡会”,并将重建后的关帝庙定名为“川陕滇三省会馆”。从名称不难看出,不论是财神会,还是川陕滇三省同乡会,成员身份与群体规模虽有差别,但两个组织都是严格意义上的汉人组织。这表明尽管汉人自清初就已进到巴塘,并开启与本地藏族的互动进程(经商、雇佣、租佃等),但直到同光之际,汉人移民仍自觉地强调并坚持自身与巴塘藏族之间的族群区分,“汉民公建”的关帝庙就是作为汉藏区分的象征标识而存在的。
但要指出的是,据史料反映,至少在同光时期,巴塘的汉人移民也已表现出融入本地藏族社会的倾向,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倾向越发明显、强烈。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关帝庙在乾隆年间初建时,系“汉民公建”,但同治时期重建关帝庙时,捐资参与者除了当时巴塘的各路汉人外,还包括大营官罗宗旺登。围绕关帝庙这一在藏地极具汉人族群象征意义的建筑物的重建,不论是罗宗旺登的捐资参与,还是汉人移民对其捐资的接受,都在某种程度上显示出巴塘汉藏人民在社会边界、文化心理上对彼此的开放与接纳,这在汉人移民方面尤为如此。其次,也是最为重要的,1877年,英国人威廉・吉尔(William J.Gill)观察到,巴塘“喇嘛庙里还住着些当地出生的、派驻藏区的汉人士兵的孩子们。在士兵返回之际,其藏人妻子和孩子都被留下,孩子一般会进入喇嘛庙”。这是目前笔者所见最早直接记载巴塘存在汉藏通婚现象的清代史料。1900年5月8日,初到巴塘的戴维斯也发现,“当地居民主要是藏人,但有相当一部分是汉人与当地土著结婚的后裔,他们都已藏化”E。汉藏后裔“有相当一部分”,这说明那时巴塘汉藏通婚的数量不在少数。根据刘家驹(格桑群觉,1900—1977)与格桑泽仁(王天华,1904—1946)的出生日期推算可知,二人父亲刘观镛、王兴海正是在此前后迎娶了他们的藏族母亲。据刘家驹的长孙德钦雄勒先生称:“刘观镛的夫人是藏族,刘观镛早期到藏区并和藏区妇女结婚,生了刘家驹。”而与格桑泽仁相识的任乃强曾提到,“格桑泽仁是清末在巴塘经商人娶藏女所生的儿子”,其“父王兴海,母竹玛拉姆”,按照格桑泽仁的朋友陈强立的说法,“其父是云南人”。汉藏通婚的出现深刻地反映出巴塘汉、藏间的族际隔膜已打破、距离正趋缩小。而随着1905年“凤全事件”的爆发,这一汉藏交融的趋势则愈发突出。
二、1905—1912年:川边改革与汉藏交融的加速
“凤全事件”以后,巴塘迎来一股汉人移民的浪潮,以至“城区几全部为汉人”。此说不一定准确,但也是一种当时社会的反映。是年,清廷急调大量清军进剿,事后分兵若干驻守巴塘。尽管当前我们尚不见详载驻军具体数额的官方文献,但美国医生罗富德(Z.S.Loftis,1881—1909)的日记可以提供一些参照。1909年6月17日,罗富德到达巴塘,他在19日的日记中提到,此时约有1200名士兵驻扎在巴塘。可见,当时清军的数额是不少的。按定制,戍边清军3年更换,但在赵尔丰“化出关之兵为民”政策引导下,部分官兵最终选择落籍巴塘,并终老于此,下述邓克成、冯海江即是如此。
勘乱后,清政府在巴塘的权势得到空前的增强,赵尔丰乘势以巴塘为中心开启川边改革,移民即是他借以推行改革的重要策略之一。1908年,四川总督赵尔巽会衔赵尔丰致函军机处,明确提出“安巴、安藏,不外移民政策”的治边思路。后来赵尔丰更是直言道,川边改革“事虽关外之事,人多内地之人”。正因如此,时已荣居“西康之首治”F的巴塘,过去还只是一个“汉夷穷滥百姓一百二十余家”、“既无生意,又无铺户”的“山口荒村”,“一时汉番蚁集,市肆喧阗,由数百户增至一千余户,几成西康第一都会”。1911年4月9日的《成都商报》就曾报道称:在“凤全事件”以前,巴塘“向虽有汉商住此,而铺店无一,故无市廛形式”。勘乱后,“陕滇四川商人,□往设市,……现已有洋广杂货铺三家,滇商六家,陕商五家,酱园一家,茶馆三家,菜馆四家,其余粮食铺,面食铺,均有数家,市肆尚日增无已,而房屋表面亦多改从汉式,竟一变从前蛮荒萧条之况”。汉商铺子的持续扩增以及本地“房屋表面亦多改从汉式”,由此足见当时到巴塘的汉商数量之多。
不过,与垦民相比,在清末巴塘汉人移民中,汉商究属小众。为推进垦务,赵尔丰曾鼓励内地汉人出关垦殖,除提供路费外,还“给以衣、粮、庐舍、牛、种、农具”。在此背景下,加上巴塘“俨如内地”的声誉,以及地处川藏大道的通衢地位,遂引得内地垦民纷至沓来。例如,打箭炉厅在1905—1907年间登记的267名出关垦民中,前往巴塘者就高达118人。而据巴塘粮员董涛在1909年的统计,巴塘“自[光绪]三十二年二月起至三十三年四月止”,“其时新到垦夫二百余名”。1908年,赵尔丰拟将官府招募的800名内地垦夫(“有眷属者三百七十余人”)平均分发至巴塘、定乡、稻城、河口4县,每县200名(未含眷属)。此外,曾任巴塘粮员的陈廉还在1909年回顾道,巴塘自1906年招民垦殖以来,“迄今三年,出关垦夫不下数百名”。这些官方记载显示,不到3年的时间,即有数百名内地垦夫拖家携口前往巴塘,这一数目着实令人惊讶。但要指出的是,实际定居者的数量是低于此数的。在同一份呈禀中,陈廉解释道,部分是因“领垦夫希图侵渔”,“临时雇人应点”所致。比如,宣统元年六月十二日(1909年7月28日),打箭炉厅致电陈廉,“言资阳送来垦夫五十名”,但当陈廉七月初五日(8月20日)点验时,“连老弱妇孺共二十一名”。除这一原因外,董涛还指出,垦夫到巴塘后,也有因“偷窃,或领粮私逃,甚有充清道夫亦不胜任者”而被“知县随时淘汰”者。即便如此,纵然按半数计,清末实际到巴塘的垦夫数量仍不容小觑。
在这一移民浪潮下,其他身份的许多汉人也纷纷出关到巴塘。具体而言,像著名民族学家李绍明先生(1933—2009)的父亲李亨,他到巴塘任职学务局。而曾任甘孜藏族自治州州长的钦饶(王安梁,1928年生人),其父王绍清是四川“邛崃拦河坎的”,因裁缝手艺被招募至巴塘,后定居于此;再如,1983年任巴塘县副县长的格桑旺堆(何多才,1930年生人),其爷爷何正连是从四川(今南充市)蓬安县逃难至巴塘的。尽管川边改革期间巴塘汉人移民的总数现已不可考,但通过对驻军、汉商与垦民的描述,大体已能见其数量之众。
随着汉人大量涌进巴塘,本地的汉藏通婚也愈发普遍,甚至还蔓延至权贵阶层。1911年,英国植物学家金敦・沃德(FrankK.Ward,1885—1958)就敏锐地发现,巴塘“大多数汉族人、商人和军人都与当地藏族部落的女性结婚,一起生活”。从军人来看,为安抚戍边军人,赵尔丰曾鼓励边军迎娶藏女。在巴塘,部分官兵与藏族女性成婚并生儿育女后,就此选择落籍巴塘。例如,1950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8军的马才生,其父籍贯湖南,清末随马维骐进抵巴塘后就在当地娶妻并定居于此。再如,宣统元年六月初三日(1909年7月19日),时任赵尔丰西军中营哨官的袁绍奎与巴塘西松工藏族女性绒贞缔结婚书,结为夫妻。被誉为“藏族第一位女教授”的邓珠拉姆的父亲邓克成与母亲志玛青中亦在此时喜结连理。
作为国民政府时期的风云人物,冯云仙(格桑雀珍,1908—1985)的父母同属汉藏通婚。父亲冯海江于清末随赵尔丰进驻巴塘,母亲阿宗系巴塘人,“生在贵族之家”,是“一位与汉人通婚最早的贵族女子”。冯海江与阿宗的结合表明,汉藏通婚在清末巴塘已出现向本地藏族权贵阶层延展的迹象,而在等级森严的藏族社会,这一迹象已然成为当时汉藏交融深化的一个显著标志。此外,冯云仙在《西康关外日记》中还提到一个清军与巴塘女子成婚的案例:民国时期任炉霍县委员的顶武东,“系赵大帅时大砲队队长,与先父同事多年”,“顶太太系巴安人,与我母亲系姊妹”。
清末,其他身份的汉人选择与当地藏族女性通婚也多。比如,李亨就“在当地找了个藏族结过一次婚,还生了个小男孩”。此外,巴塘传教士芙洛拉·史德文(Flora Beal Shelton)在1912年出版的《西藏边界的光与影》中提到,1908年随其夫妇到巴塘传教的四川大邑县人李国光(Li Guay Gwuang)当时已与一名藏族女子结婚。1914年,李国光的藏族妻子“Candro”去世。他后来又续娶了一位名叫达瓦卓玛的巴塘女子为妻。1939年,金陵大学电影课教师孙明经赴川康考察时,曾为李国光的家庭拍摄照片数张,其中一张即附有“巴安李牧师一家,汉藏融合”的注语。
事实上,除了普遍选择与藏族女性通婚外,据文献记载,当时生活在巴塘的汉人也已开始主动地吸纳藏族文化。1911年,沃德就观察到,巴塘的汉人在“日常生活中,他们即使不穿当地服装,也至少接纳了当地藏族部落的一些风俗习惯”。而前引吉尔称“汉藏后裔一般会进入喇嘛庙”,以及戴维斯对汉藏后裔“藏化”的描述,则表明汉藏后裔对藏族文化的汲取更为广泛、深入。这些事实都清楚地显示出,进入清朝后期,巴塘的汉人移民尤其是汉藏后裔对藏族文化已持更为开放、包容、接纳的态度。与此同时,在川边改革期间,赵尔丰强制推行的官话教育、改汉姓等措施则在很大程度上推动着巴塘藏族接受并学习汉文化。而这一双向的文化采借也为民国时期巴塘的汉藏文化朝着更为深度交融的方向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1912—1949年:“汉藏矛盾几乎无存,民族关系融洽”
民元以来,巴塘虽“频遭变乱,所有垦民大半流离死亡”,但汉人及其后裔在民国巴塘已有相当数量却是不争的事实。1921年,据自称曾“旅行西南各地”的翁之藏估算,巴塘有汉族15000人。I此数显然有夸大的嫌疑。1935年,羊磊在《巴安小志》中引1928年巴塘人口调查数称:“汉回及外籍侨寓者约一百八十四户,丁口约计九百五十余”。羊氏是否将汉藏后裔纳入其中,我们不得而知。而任乃强据“考查后(1930年)之估计”,认为将汉藏后裔计入,巴塘有“汉400(户)、丁口4500人”;而在另一处,任乃强又指出,巴塘时有“汉户300余家”。1938年,一位署名“毅公”的作者撰文称:
巴安治城汉籍之民约十分之六强,故康人呼巴安曰“汉人城”,示人特多之谓,而其真实涵义,即指此为特殊地段,不与康情同也。
仅“治城”而言,汉人已占“十分之六强”,其数不可谓不多,并且“汉人城”这一称号还是由“康人”所呼,更能说明这一事实。1941年,美国传教士丹尼尔·弗赖伯格(H.Daniel Friberg,1908—2005)取道中国西部诸省前往缅甸,路经巴塘时,他观察到巴塘“汉人只占十分之一”。这一比例与毅公的观察相比,看似抵牾,其实不然,因为此“十分之一”是就巴塘全县而言,而据其言,在西康西部,“汉人生活在城镇里”,故两段材料实际是相互证成的。当然,巴塘县城以外也有汉人居住。1939年10月19日,著名人类学家庄学本到竹巴龙(笼),就发现江边“有水手四户系汉人”。1943年,李中定撰文指出,巴塘“汉族占百分之九、五”[按:9.5%]。两相比对,李中定与丹尼尔的数据基本相近,故皆可采信。综合可知,到民国中后期,巴塘的汉人数量实已达到相当规模。
民元以后,得益于大量汉人的存在,巴塘的汉藏通婚并未因川边改革的中断而减缓,反而愈发寻常、普遍。1929年,初到巴塘的刘曼卿询问巴塘人保森“巴安教育近事”时,保森答云:“自赵氏教育摧败后,……女子更多随嫁汉人,流入内地,西康有歌讽之,意谓‘汉人到内地是回转故乡,西康姑娘啊,那是异域尔无往’。”保森所谓“赵氏教育摧败后”,系指民国鼎革以后。因此,这则材料清楚地指明了汉藏通婚在民国巴塘的盛行。对此,川人戴述古的记述可为佐证。戴述古曾于1925年应聘到巴塘华西学校任教员,基于实地观察,他在1936年的一篇文章中称,在巴塘,“汉人军商婚娶于其地者极多”。1939年,8岁的杨岭多吉随父母定居巴塘,据其回忆,当时“巴塘也有一些善良的汉族商人、居民,他们早就同当地有亲密的姻亲关系,汉藏矛盾几乎无存,民族关系融洽”。除了这些整体描述外,下述个案还提供了进一步证明。
1929年,美籍传教士马里恩·邓肯(Marion H.Duncan)以他在巴塘传教时的亲身见闻与经历为基础,撰成并出版《银雪之山》一书,书中曾展示了一张巴塘汉藏家庭的合照,丈夫是一名富裕的汉人银匠,与其藏族妻子以及年老的岳母等居住在一起。作为汉藏通婚的后裔,刘家驹沿着父亲的脚步迎娶了巴塘泽曲伙的藏族姑娘玉珍纳母为妻。此外,格旺的原生家庭同样是典型的汉藏合璧:“以后等于我的爸爸长大了以后呢,就结了婚,我的妈妈是西藏芒康的。”在《进军西藏日记》中,1950年随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8军进藏的新华社记者林田也提到几个巴塘汉藏通婚的案例。例如,担任其藏语翻译的巴塘藏族格桑杨刚,他的一个姐夫就是四川人;1950年参加18军的江正林的妻子同样是藏族。此外,1950年与巴塘籍藏族文学家降边嘉措(张自康)一同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小扎西(汉名曾光祖)、志玛、东秀、陈淑兰等人的“父亲都是汉族,母亲是藏族”。
据降边嘉措回忆,母亲张金莲(汉名为降边嘉措生父所取)一生经历了3次婚姻,其后两任丈夫均为汉族,第二任丈夫是傅德铨的外甥,第三任丈夫即降边嘉措的生父张正伦,系四川雅安人。此外,张正伦的一位川籍王姓同事,“他的妻子也是当地藏族”,并育有两个儿子;而对降边嘉措极好的邓珠娜姆阿姨则在抗战期间嫁给了一位到巴塘任县长的内地汉人,同样育有两个孩子。
民国中后期,汉藏后裔的大量存在同样说明此间巴塘汉藏通婚的广泛。戴述古就曾指出,巴塘“人民大率混血”。降边嘉措曾追忆道,在巴塘读小学时,班上“有几个像我一样半汉半藏的同学”。格旺在巴塘省立小学就读时,虽然同学都自认是藏族(包括像他这样的汉藏后裔亦是如此),但其中“汉族血缘的也有,同学里面也不少。
除了大量的汉藏通婚外,在民国时期,巴塘汉、藏两种文化的相互采借、糅合也更为常见。譬如巴塘关帝庙对藏族宗教要素的吸纳以及藏族参与关帝庙的庆典活动。在服饰上,巴塘人王信隆称,巴塘“汉民服饰同内地,土民居城中者,几与汉民无异”H。另外,当时许多巴塘人或者同时拥有汉、藏两个姓名,或取一个汉藏混合的名字。降边嘉措曾回忆道:
在当时,改汉姓、取汉名在我们那里也成了一时风尚,很多人都有两个名字。……我们那里一些完全没有汉人血统的普通的藏族农牧民,有不少人就叫李扎西、张次仁、王洛桑、赵娜姆、刘央金……。
此外,像格桑泽仁、刘家驹、邓珠拉姆、冯云仙、格旺等作为个案证据,同样证实了汉藏双名在民国巴塘的风靡。需强调的是,巴塘人兼备汉藏双名,除了藏族“改汉姓、取汉名”外,还包括汉人及其后裔取藏名,比如,毫无藏族血统的王安梁就取了一个藏名——钦饶;至于汉藏后裔取藏名,格桑泽仁、刘家驹、冯云仙、邓珠拉姆等人就是其中的典型例子。
当然,最引人注目的,还是民国时期的巴塘人大多兼通汉藏两种语言。除前引蒙藏教育司的记载外,1936年,王信隆介绍巴塘“汉藏两种[语言]均通,与汉人交接用汉语,与藏人交接用藏语”。1950年8月2日,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8军53师副政委的苗丕一(1916—2005)率军进抵巴塘时发现,当地“懂藏、汉两种文字、语言的人不少”。
从个案来看,江安西(洛桑顿珠,1906—2000)称,格桑泽仁“通晓汉藏语文”;曾与刘家驹在《蒙藏周报》(南京)共事的黄奋生称刘氏“精娴汉藏语文”;而江安西更是“通晓藏、汉、英三种语言文字”,其妻巴塘藏族黄玉兰(次仁央宗,1905—1989)亦“精通汉藏语文”。而据巴塘人平措汪杰(闵志诚,1921—2014)回忆,他的舅舅、江安西之弟江新西(洛松吉村)同样“精通英文、汉文和藏文”;他儿时的伙伴阿旺格桑(刘绍禹)也“会藏文、汉文和一些英文”。可见,民国时巴塘人兼通汉藏双语已是寻常现象。
因此,通过对宗教信仰、服饰、姓名、语言等文化要素的描述及汉藏通婚的普遍情况等事实,充分显示出民国时巴塘汉藏文化交汇融合的寻常与深入,足见民国时期的巴塘汉藏关系已实现深度交融。对此,我们还可以提供一个佐证。据江安西回忆,1925年,应时局所需,巴塘的汉人移民及其后裔将“华族联合会”(1924年由“川陕滇三省同乡会”改组而来)更设为“西康巴安国民协进会”,这是一个“没有民族界限的地方性组织”,因为“除三省官商子弟外,凡属巴塘民众不分民族,皆可入会”。这表明延续了近两百年、借以标识汉藏区分的移民组织在当时已不再符合现实需要。此举正揭示出巴塘的汉藏两族到民国时大体已实现族际交融和谐。
四、民国巴塘汉藏交融的历史影响
据史料反映,清代民国巴塘汉藏交融的实现在民国康藏史或汉藏关系史上曾有过不容忽视的重要影响。1929年,任乃强考察西康时发现,“西康各县,汉民较多之地,即治权最固之地,亦即国防最坚之地”,譬如:
巴塘自民八以来,孤悬西陲,逼近藏军;历届汉官,视同弃地;赖有汉户三百余家,遥奉正朔;虽四围境土皆已梗化,惟此一区,始终不渝。
1933年,任氏在中央政治学校蒙藏班发表讲演时,进一步解释这是“因为内地移民较多之处与当地情感融洽,帮助汉军甚大”。“情感融洽”显然就是汉藏交融的同义语。也就是说,按任氏的说法,巴塘的汉藏交融氛围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民国康藏政局的走势,并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起到了稳固内地中央政府在边疆藏地的“治权”与“国防”的重要作用。
此外,在南京国民政府奖掖蒙藏青年赴内地求学任职等政策的推动下,巴塘汉藏交融的成果——兼备汉藏血缘的巴塘人,还通过地理与社会的双重流动一跃成为当时联结汉藏关系的强力纽带之一,并持续推动着汉藏间的沟通与交流。正如陈强立所言,在民国汉藏关系因语言、政治滞碍而长期处于交流不畅的背景下,通晓汉藏语文的巴塘青年在内地“翻译汉藏文件,对汉藏文化交流起了很好的作用”。事实上,除了翻译汉藏文件外,1928年,自东北返回后,通晓汉藏语文的格桑泽仁就一直充任九世班禅与南京国民政府的联络人。刘家驹则“专做班禅对外的翻译”,这在《班禅大师东来十五年大事记》中屡有记载。1938年,邓珠拉姆被聘为西藏驻京办事处藏文秘书,“主要从事口头翻译,此间还曾为噶厦驻京代表与蒋介石当翻译”。江安西与黄玉兰夫妻亦长期在国民政府机关担任汉藏文翻译或汉藏文教师。格桑悦希则“因汉藏语文不同,电码阙如,于消息之传递,文化之沟通上,殊感不便”,于是“穷数年之力”,创编了一套藏文电报码。上述活动均切实地促进了国民政府时期中央与地方间的沟通与理解。当然,身具汉藏复合文化特质的巴塘人对国民政府时期汉藏关系的沟通与联结远不止于此,但限于文章篇幅,需另辟专文予以详述。
事实上,新中国成立初期,兼通汉藏双语的巴塘人仍继续推动着汉藏间的沟通与联结。据降边嘉措称,195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平解放西藏时,在进藏部队“担任主要翻译的,几乎全是巴塘人”。此外,“解放后第一个给毛主席当翻译的是巴塘人;第一个将马列的书和毛泽东的著作翻译成藏文的,也是巴塘人;第一次将《国际歌》和新中国成立后被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义勇军进行曲》翻译成藏文,在广大藏族地区传唱的,也是巴塘人。”窥一斑而见全豹,上述史实已足见清代民国巴塘汉藏交融的形成与深化所具有的深远的历史影响。
五、结语
综上,内地汉人自康熙年间移居巴塘始,有清一代,通过汉藏通婚等族际互动,巴塘的汉藏民族关系逐步从初期的族际区隔走向了中后期的汉藏交融,川边改革则加速了这一进程。民国以后,最终在血缘与文化上实现了广泛且具有深度的族际交融。在民国特定的历史语境下,巴塘汉藏交融的实现不但稳固了内地中央政府在藏地边疆的“治权”与“国防”,还在更高层面推动着国民政府时期汉藏间的沟通与联结。这些事实清楚地表明,民国内地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之间的政治滞碍与军事冲突并未妨碍汉藏关系在微观层面不断地走向和睦融洽,而微观层面的汉藏互动无疑更能揭示此期汉藏关系的内在肌理与鲜活实态,更加贴近汉藏关系的实质与本相。总之,清代民国巴塘汉藏交融的案例不但扩大并深化了对民国汉藏关系和谐交融一面的认识,从现实意义来看,它也从汉藏关系的维度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和发展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参照、论证和启示。而加强该论题涉及相关资料搜罗整理和学术研究,也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作者简介:刘欢,内江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原刊于《中国藏学》2025年第3期(总第170期),注释略,原文版权归作者和原单位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