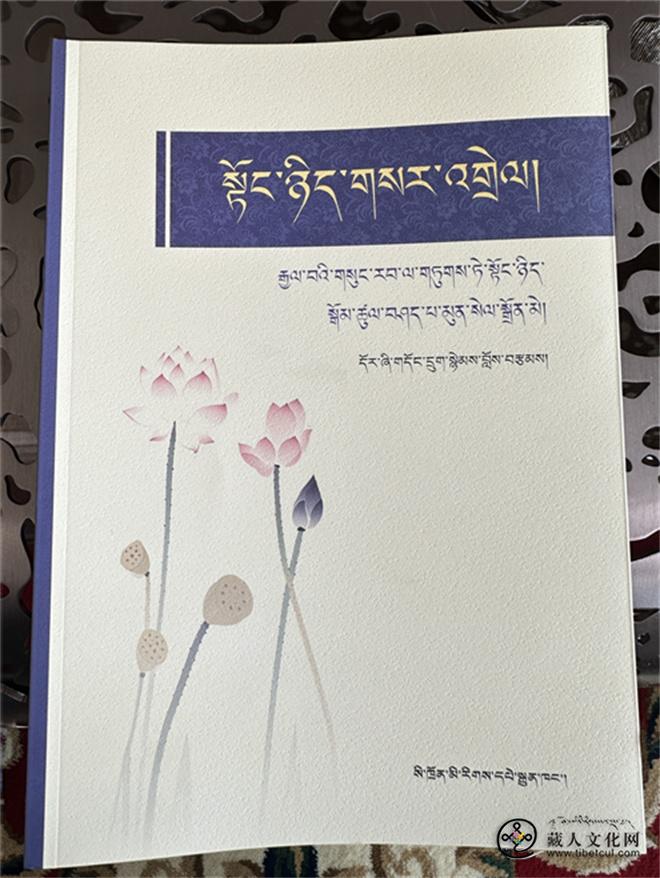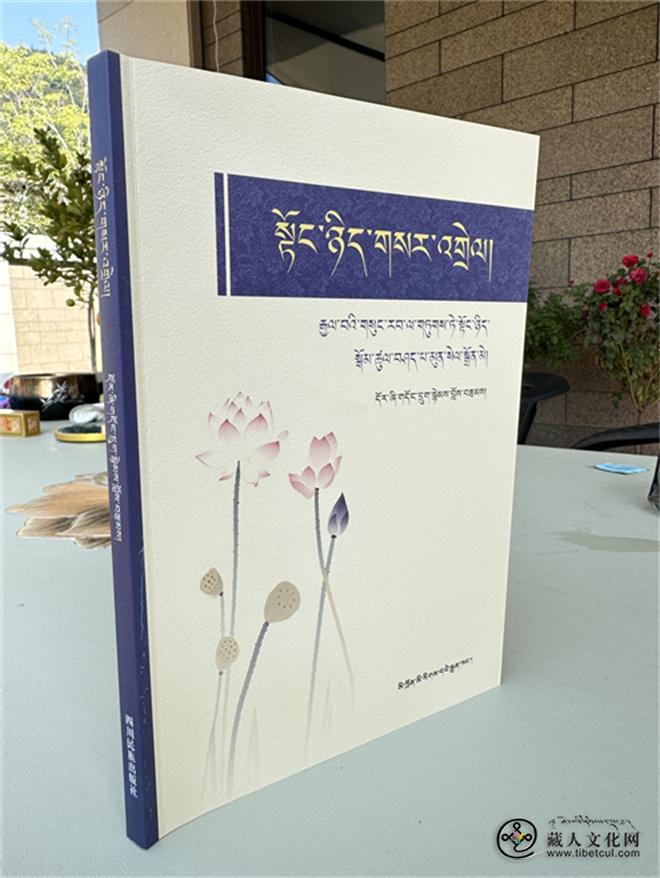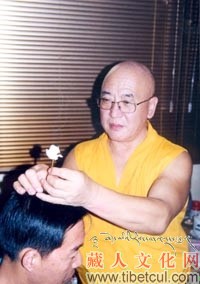[тєЁт«╣ТЈљУдЂ]сђђУ┐Єтј╗ТЏЙТюЅСИђС║ЏтГдУђЁтюетЁ│С║јтЦўУ»ЉсђітЁЦтЏаТўјТГБуљєУ«║сђІСИГТюЅтЄатцёУ»ЉТ│ЋТў»тљдтдЦтйЊуџёжЌ«жбўСИіУ┐ЏУАїУ┐ЄуаћуЕХ№╝їТЈљтЄ║С║єСИђС║ЏТјеТхІсђѓТюгТќЄт░єСЙЮуЁДУ»ЦУ«║уџёТбхУЌЈУ»ЉТюг№╝їт░▒тГдУђЁС╗гтјЪТЮЦуџёТЪљС║ЏТјеТхІу╗ЎС║ѕжЄЇТќ░ТјбУ«етњїУ»ёС╗исђѓтЈдтцќУ┐ўт░єСИЊжЌеТїЄтЄ║У┐Єтј╗уаћуЕХСИГуЋЎтГўуџёСИђтцёжЄЇтцДуќЈТ╝Јсђѓ
тЁ│жћ«У»Ї№╝џсђђтЏаТўјсђђтЁЦтЏаТўјТГБуљєУ«║сђђСйЏТЋЎ
С╝ЌТЅђтЉеуЪЦ№╝їтюеСйЏТЋЎтЁИу▒ЇуџёуаћуЕХСИГ№╝їРђютдѓСйЋТў»тјЪУ«║ТюгТёЈРђЮСИђуЏ┤Тў»СИђСИфтЏ░ТЅ░тГдУђЁС╗гуџёжџЙжбўсђѓУ┐ЎСИфжџЙжбўуџёУДБтє│тіъТ│ЋСИђУѕгСИЇтцќС╣јСИцСИф№╝џСИђУђЁ№╝їТў»С╗јтјЪУ«║тєЁт«╣уџёжђ╗УЙЉу╗ЊТъёТЅЙуГћТАѕ№╝ЏС║їУђЁ№╝їТў»С╗јтјЪУ«║У»ГУеђуџёжђ╗УЙЉу╗ЊТъёТЅЙуГћТАѕсђѓтЅЇУђЁУЙЃтЁ│Т│ет«ЌТЋЎтЊ▓тГдуџёТјбУ«е№╝їУђїтљјУђЁУЙЃУ┐ЉС║јУ»ГУеђтГдуџёуаћуЕХсђѓ
сђітЁЦтЏаТўјТГБуљєУ«║сђІ№╝ѕСИІТќЄуЋЦуД░СИ║сђітЁЦУ«║сђІ№╝ЅТў»тћљ№╝јујётЦўТ│ЋтИѕТЅђУ»ЉтЁХСИГСИђжЃеТЎ«тЈЌТјет┤ЄуџёТ▒ЅС╝аСйЏТЋЎТќЄуї«сђѓт«ЃСИјујётЦўТ│ЋтИѕуџётЈдСИђжЃеУ»ЉуЮђсђіТГБуљєжЌеУ«║сђІ№╝ѕСИІТќЄуЋЦуД░СИ║сђіжЌеУ«║сђІ№╝ЅСИђУхи№╝їУбФТ▒ЅС╝атЏаТўјтГдУђЁС╗гт░іСИ║тЏаТўјтГдСИГуџёРђютцДт░ЈС║їУ«║РђЮсђѓт«ЃС╗гТў»жЋ┐ТюЪС╗ЦТЮЦТ▒ЅС╝атЏаТўјуаћуЕХТЅђСЙЮуџётюГУЄг№╝їУђїСИћ№╝їт«ЃС╗гС╣ЪТў»У┐Єтј╗Т▒ЅС╝атЏаТўјтГдСИГС╗ЁтЈ»СЙЮУхќуџёСИцжЃеТа╣ТюгУЉЌСйюсђѓујётЦўС╗ЦтљјуџёуфЦтЪ║сђЂуЦъТ│░сђЂТќЄУйеуГЅтЏаТўјтцДтИѕ№╝їС╣ЃУЄ│У┐ЉС╗Бу╗ЮтцДжЃетѕєТ▒ЅС╝атЏаТўјтГдУђЁ№╝їТЌаСИЇТў»С╗ЦТГцСйюСИ║уљєУ«║уФІУХ│уџёТа╣Тюг№╝їуаћуЕХтњїтЈЉТЅгТ▒Ѕтю░СИђУёЅуџётЏаТўјС╝аУДёсђѓ
УЄфтЈцС╗ЦТЮЦ№╝їтюеС╝ау╗ЪуџёуаћуЕХСйЊу│╗жЄї№╝їТГцС╣дуџётю░СйЇт┤ЄжФў№╝їС╗јТЌаС║║т»╣тЁХУ»ЉСйютјЪТќЄТЈљтЄ║У┐ЄУ┤еуќЉсђѓуёХУђїтйЊУ┐ЉС╗БС║║С╗јтЇ░т║дуџёУђєжѓБТЋЎтЙњТЅІСИГТЅЙтѕ░С║єСИђСИфсђітЁЦУ«║сђІуџёТбхТќЄуЅѕТюгтљј[1]№╝їСИђС║ЏСИГтЏйтГдУђЁтдѓ
ТюгТќЄС╗ЦСИІт░єт»╣тІўућ▒тЁІС╗ђу▒│т░ћУ»ЉтИѕтљЅуЦЦТіцтњїУЌЈТЌЈУ»ЉтИѕТ│Ћт╣бтљЅуЦЦУ┤цС╗јТбхТќЄУ»ЉТѕљУЌЈТќЄуџёсђітЁЦУ«║сђІ[2]№╝їтЈѕС╗јСИіУ┐░СИЅСйЇтГдУђЁТЏЙТЈљтЄ║уџёТјеТхІТёЈУДЂСИГТІБтЄ║тЄатцёт░цтЈ»тЋєТдиуџётю░Тќ╣жЄЇТЈљУ«еУ«║сђѓтЈдтцќТюЅСИђСИфжЌ«жбў№╝їС╣ЪТў»ТѕЉСИфС║║У«цСИ║Т»ћУЙЃСИ╗УдЂуџёУ»ЉТ│ЋжЌ«жбў№╝їтѕЎТў»СИіжЮбСИЅСйЇтГдУђЁтЮЄТюфТЏЙуЋЎТёЈТїЄтЄ║уџёсђѓ
У┐ЎжЄїТюЅТёЈжЄЄућеУ┐ЎСИфУЌЈУ»ЉТюгтєЇТгАт»╣тІўуџёуљєућ▒ТюЅСИЅСИф№╝џуггСИђсђЂућ▒С║јтјєтЈ▓СИіУЌЈТќЄТў»тђЪжЅ┤ТбхТќЄСИ║ТЉ╣ТюгтѕЏжђатЄ║ТЮЦуџёСИђуДЇТќЄтГЌсђѓт«ЃтюеУ»ГТ│ЋућџУЄ│ућеУ»ЇСИіт║ћУЙЃСИ║ТјЦУ┐ЉТбхТќЄсђѓуггС║їсђЂУЦ┐УЌЈС║║тюеТбхТќЄтЏаТўјУ«║тЁИуџёу┐╗У»ЉУ┐ЄуеІСИГ№╝їтЙђтЙђжЄЄућетЇ░сђЂУЌЈСИцтю░У»ЉтИѕ[3]тљїУ»ЉуџёТќ╣Т│Ћ№╝ѕУ┐ЎуДЇТќ╣Т│ЋтЁХт«ъС╣ЪУбФтцДжЄЈтю░Т▓┐ућетѕ░тЁХт«ЃуџёСйЏтЁИу┐╗У»ЉУ┐ЄуеІСИГ№╝ЅсђѓтЏаТГц№╝їтЁХУ»ЉТќЄуџётЈ»жЮаТђДТюЅС║єУЙЃтцДуџёС┐ЮУ»ЂсђѓуггСИЅсђЂТбхТќЄтЏаТўјтЁИу▒ЇУ»ЉтЁЦУЌЈТќЄуџёТЌХжЌ┤Т»ћУ»ЉтЁЦТ▒ЅТќЄуџёУдЂТЎџ№╝їтюеУ┐ЎТюЪжЌ┤СйЏТЋЎтЏаТўјтГдтюетЇ░т║дТюгтюЪу╗ЈтјєС║єтЁХтЈЉт▒ЋуџётЁеуЏЏТЌХТюЪсђѓС╣ЪтюеУ┐ЎСИфТЌХТюЪжЄї№╝їтјЪТЮЦтюежЎѕжѓБТЌХС╗БтЏаТўјуљєУ«║СйЊу│╗СИГжЂЌуЋЎуџёСИђС║ЏТюфтЈіУ»дУЙеуџёуљєУ«║жЌ«жбўти▓УјитЙЌТЏ┤ТИЁТЎ░уџёУДБжЄісђѓС╣Ът░▒Тў»У»┤№╝їУЌЈТЌЈС║║Т»ћТ▒ЅТЌЈС║║ТЏ┤т«їТЋ┤тю░у╗ДТЅ┐тЇ░т║дС╝аТЮЦуџётЏаТўјтГдсђѓУ┐Ўт┐ЁуёХТюЅтіЕС║јтйЊТЌХуџёТбхУЌЈу┐╗У»Љт«ХС╗гУЃйС╗јТЏ┤тЄєуА«уџётєЁт«╣жђ╗УЙЉТђДСИіТііТЈАтЇ░т║дтјЪтЁИсђѓУ┐ЎТаиуџёт»╣тІўТ»ћУЙЃ№╝їТЌауќЉС╣ЪУЃйСИ║С╗ітцЕуџёТ▒ЅС╝атЏаТўјуаћуЕХТЈљСЙЏТќ░уџёУДєуѓ╣тњїУАЦтЁЁУ»ЂТЇ«сђѓ
СИђсђЂ тЁ│С║јтЦўУ»ЉРђюТГцСИГт«ЌУђЁ№╝їУ░ЊТъЂТѕљТюЅТ│ЋсђЂТъЂТѕљУЃйтѕФ№╝їти«тѕФТђДТЋЁРђЮСИђтЈЦуџёУ»ЉТ│Ћ
У┐ЎжЄїтјЪТЮЦ
ТГцтЈЦУІЦСЙЮУЌЈТќЄУ»ЉТёЈт║ћСИ║№╝џРђютЁХСИГТЅђУ░Њт«ЌУђЁ№╝їТў»С╗ЦТъЂТѕљТюЅТ│ЋсђЂТъЂТѕљУЃйтѕФСйюСИЇтЁ▒ти«тѕФРђЮтЁетЈЦСИГтЈфТюЅСИђСИфтЁиТа╝У»Їgyis№╝їт«ЃуџёСйЇуй«тюеРђюТъЂТѕљТюЅТ│ЋсђЂТъЂТѕљУЃйтѕФРђЮС║їУ»ЇС╣Ітљј№╝їТїЅУЌЈТќЄтЁиТа╝У»Їуџёт║ћућеУДётѕЎт╣Ху╗ЊтљѕУ┐ЎжЄїуџётєЁт«╣тѕєТъљ№╝їУ┐ЎСИфтЁиТа╝У»Їgyisт║ћУ»ЦТў»т»╣РђюТъЂТѕљТюЅТ│ЋсђЂТъЂТѕљУЃйтѕФРђЮУАеУЃйСйюСИ╗СйЊтіЪУЃйуџёУЎџУ»Ї№╝їтдѓУ»┤РђюС║║С╗ЦТќДуаЇТаЉРђЮСИГуџёРђюС╗ЦРђЮтГЌсђѓТЋЁТГцСИГт║ћУ»ЉТѕљРђюС╗ЦТъЂТѕљТюЅТ│ЋсђЂТъЂТѕљУЃйтѕФРђЮсђѓТГцТЌХРђюС╗ЦРђЮтГЌт╣ХСИЇУАетјЪтЏасђѓУ┐ЎжЄїС║ЅУ«║С╣ІтцёУІЦТГБТў»ујётЦўТЅђУ»ЉРђюТЋЁРђЮтГЌуџёУ»Ю№╝їтѕЎтЇ│Сй┐ТѕЉС╗гУЃйУ»ЂТўјтюетЈцТ▒ЅУ»ГуџёС╣аТЃ»СИГРђюС╗ЦРђдРђдТЋЁРђЮуџёућеТ│ЋтЈ»Тјњтц┤Ті╝т░Йтю░УЂћућеТѕќтЇЋуће№╝їуёХУђїујётЦўУ»ЉтЈЦСИГуџёРђюТЋЁРђЮтГЌТјњтюетЁетЈЦС╣Ітљј№╝їТїЅСИГТќЄС╣аТЃ»уџёТюЅТЋѕТдѓТІгУїЃтЏ┤т║ћУ»Цу╗ЪУ«АтЁетЈЦ№╝їтЏаТГцТЌаУ«║тдѓСйЋС╣ЪтЙѕжџЙТЅЙтЄ║уЏИтљїуџёТќГтЈЦУДБжЄісђѓ
Уђїт»╣С║јРђюТђДРђЮСИђтГЌуџёУАеТёЈ№╝їтюетЈцтЁИСйЏТЋЎУЉЌСйюСИГтЙѕтцџТЌХтђЎТў»ућеСйюУАеуц║т╝║У░ЃТЪљуДЇтГўтюеТюгУ┤еуџёТёЈтљЉсђѓтдѓтљїСИІжЮбУдЂУ«еУ«║уџёСИђтЈЦСИГуџёРђюТђДРђЮтГЌСИђТаи№╝їС╗јУЌЈТќЄСИГтЙѕжџЙУ»┤УЃйуЏ┤ТјЦТЅЙтѕ░СИђСИфтдѓnyidуГЅуџёуЏ┤ТјЦтГЌую╝СИјС╣Іт»╣т║ћуГЅУДѓсђѓТѕЉУ«цСИ║У┐ЎтЈ»С╗ЦУбФУДєСйюТў»СИђуДЇУ»ЉУђЁСИфС║║уџёуљєУДБТёЈтљЉ№╝їУІЦтдѓТў»№╝їтѕЎтЙѕжџЙтЇЋу║»ућеТЅђУ░ЊуџёРђют»╣тГЌУ»ЉРђЮуџёУДБтЅќую╝тЁЅТЮЦт»╣тЁХСйютЄ║т«бУДѓуџёУ»ёС╗исђѓ
С║їсђЂ тЁ│С║јРђюжџЈУЄфС╣љСИ║ТЅђТѕљуФІТђДРђЮСИђтЈЦуџёУ»ЉТ│Ћ
У┐ЎтЈЦ
УЌЈТќЄт»╣ТГцСИђтЈЦуџёт»╣т║ћУ»ЉТёЈт║ћСИ║№╝џРђютћ»т»╣УЄфТЅђТѕљуФІСйюТЅ┐У«ИРђЮсђѓС╣Ът░▒Тў»У»┤№╝їу┐╗У»ЉУЌЈТќЄуџёСИцСйЇтЇ░сђЂУЌЈУ»ЉУђЁтњїу┐╗У»ЉСИГТќЄуџёујётЦўтљїТЌХТўјТўЙтю░УДБУ»╗тѕ░С║єУ┐ЎСИфРђютћ»РђЮтГЌсђѓУђїТГцтЈЦтюеУЌЈТќЄтјЪТќЄСИГ№╝їТў»тюеУДБжЄіС╣ІтЅЇСИђтЈЦРђютЁХСИГТЅђУ░Њт«ЌУђЁРђЮуџёСИђСИфжЃетѕє№╝їт«ЃУдЂтѕ░СИІжЮбтЇ│т░єУ«еУ«║уџётЈдСИђтЈЦТЅЇТъёТѕљт»╣Рђют«ЌРђЮуџёт«їТЋ┤УДБжЄісђѓУђїУ┐ЎСИцтЈЦС╣ІжЌ┤Тў»СИђуДЇРђютљїСйЇРђЮуџётЁ│у│╗№╝їтЁХжЌ┤т«їтЁеТ▓АТюЅС╗╗СйЋУАетЏаТъюуџёС╗јт▒ътЁ│у│╗сђѓтЏаТГц№╝ї
СИЅсђЂ тЁ│С║јРђюТў»тљЇСИ║т«ЌтдѓТюЅТѕљуФІтБ░Тў»ТЌатИИРђЮСИђтЈЦуџёУ»ЉТ│Ћ
тЦўУ»ЉРђюТў»тљЇСИ║т«ЌРђЮСИђтЈЦ№╝їтюеУЌЈТќЄТюгсђітЁЦУ«║сђІСИГуА«т«ъС╣ЪТЌатЈ»уЏ┤ТјЦт»╣т║ћуџёУ»ЉТќЄсђѓСйєТў»№╝їУ┐ЎУІЦТў»ујётЦўУ»ЉТќЄТЌХСИ║тіат╝║У»ГТ░ћТЅђСйюуџёТи╗тіауџёУ»Ю№╝їжѓБт░▒УдЂУ«еУ«║у┐╗У»ЉТіђтиДСИіТў»тљдтдЦтйЊуџёжЌ«жбў№╝їСИЇт║ћУ»ЦТў»У┐ЎуДЇт»╣тІўуаћуЕХТЅђт║ћу╗ЎС║ѕУ»ёУ«║уџёсђѓСИјТГцуЏИтЈЇ№╝їТбхТќЄсђЂУЌЈТќЄС║їТюгСИГтЮЄТюЅСИђтЈЦ№╝џРђюСИјуј░жЄЈуГЅТЌатдет«│РђЮ№╝їУђїТЂ░ТЂ░ТГцтЈЦ№╝їтюеујётЦўУ»ЉТюгСИГТЌасђѓуёХтљју┤ДТјЦтљјжЮбуџёСИђтЈЦ№╝џРђютдѓТюЅТѕљуФІтБ░ТЌатИИРђЮ№╝їУЌЈсђЂТ▒ЅСИцСИфУ»ЉТюгтЮЄтљїТЌат╝ѓ№╝їтЈЇТў»Тќ░тЈЉуј░уџёжѓБСИфТбхТќЄТюгСИіУДЂСйюСИ║РђютдѓТюЅТѕљуФІ№╝їтБ░Тў»тИИТѕќТЌатИИРђЮсђѓт»╣ТГц
ТѕЉУ«цСИ║У┐ЎуДЇТјеТхІТў»уЅЄжЮбуџё№╝їу╝║С╣Јжђ╗УЙЉуљєТЇ«уџёсђѓждќтЁѕ№╝ї
тЁХТгА№╝ї
жѓБС╣ѕтђњт║ЋТў»Т▒ЅсђЂУЌЈСИцСИфУ»ЉТюгСИГуџёРђютдѓТюЅТѕљуФІтБ░Тў»ТЌатИИРђЮтњїуЏ«тЅЇТбхТюгСИГРђютдѓТюЅТѕљуФІ№╝їтБ░Тў»ТЌатИИТѕќТЌатИИРђЮтЊфСИђСИфТЅЇТў»ТГБуА«уџё№╝ЪТѕЉС╗гт░єС╗јТюгтЈЦС╗ЦСИІуЅхТХЅуџёТЋ┤Т«хтєЁт«╣у╗ЊТъёСИГ№╝їтЈ»С╗ЦТЅЙтѕ░жђ╗УЙЉСИітЇЈУ░ЃуџёТјеУ«║сђѓС╗јУ┐ЎСИђтЈЦт╝ђтДІ№╝їсђітЁЦУ«║сђІжџЈтљјуџёСИђТ«хтјЪТќЄТГБтюеУ«еУ«║С╗ђС╣ѕТў»т«ЌсђЂтЏасђЂтљїтЊЂсђЂт╝ѓтЊЂуГЅТдѓт┐хсђѓС╗јтЁХтљјТќЄС╗ЦРђюТў»СИЅуЏИРђЮт»╣РђютЏаРђЮСйют«џС╣Ѕ№╝їтЈѕС╗ЦРђюС╗ЦТЅђуФІТ│ЋС╣ІТђ╗тљїС╣ЅРђЮтЈітЁХтЈЇжЮбтѕєтѕФСйюРђютљїтЊЂРђЮсђЂРђют╝ѓтЊЂРђЮуџёт«џС╣ЅТђДТЈЈУ┐░ТЮЦуюІ№╝їУ┐ЎС║ЏтЁХт«ъТў»уюЪтЏасђЂуюЪтљїтЊЂсђЂуюЪт╝ѓтЊЂуџёт«џС╣ЅсђѓТЇ«ТГцТѕЉС╗гтЈ»С╗ЦУ«цСИ║№╝їУ┐ЎжЄїУ«еУ«║уџёт«ЌсђЂтЏауГЅтљЇуЏИ№╝їт«ъУ┤еТў»ТїЄуюЪт«ЌсђЂуюЪтЏауГЅС╣Ѕ№╝їС╗ЦУІЦСИЇуёХ№╝їтјЪТќЄт▓ѓСИЇт░єРђюУЃйт«ЅуФІС║јУ»ЂТўјС╣ІСйЇУђЁРђЮСйюСИ║У┐ЎжЄїРђютЏаРђЮуџёУДБжЄі№╝їтдѓТў»т▓ѓСИЇС╣ЪтЈ»т░єРђюС╝╝тЏаРђЮС╣ЪтїЁтљФУ┐Џтј╗№╝їт░єтЏауџётцќт╗ХТЅЕтцДтѕ░т«ЃуџётГЌжЮбТюгТёЈСИіТЮЦсђѓуёХУђї№╝їСЙЮТЇ«тјЪТќЄуџёТёЈтЏЙТЮЦуюІ№╝їС║Іт«ъТЂ░ТЂ░СИЇТў»У┐ЎТаиуџёсђѓУІЦтдѓТў»№╝їтѕЎСИіжЮбуџёжЌ«жбўтЈ»С╗ЦУ┐јтѕЃУђїУДБС║є№╝џуггСИђсђЂУІЦУ┐ЎжЄїУДБжЄіуџёРђют«ЌРђЮт«ъУ┤еТў»ТїЄРђюуюЪт«ЌРђЮуџёУ»Ю№╝їтѕЎРђюСИјуј░жЄЈуГЅТЌатдет«│РђЮСИђтЈЦу«ђтѕФУ»Гт┐ЁтйЊТюЅжюђУдЂтіатЁЦТќ╣УЃйСй┐С╣ІТюЅТЋѕт«џС╣Ѕ№╝ЏуггС║їсђЂтЁХтљјСИђтЈЦуџёСИЙСЙІУ»┤ТўјС╣Ът┐ЁСИЇтйЊтїЁтљФРђютБ░тИИРђЮС╣ІтЂЄт«ЌсђѓТЇ«ТГцТѕЉСИфС║║тюетЁ│С║јУ┐ЎСИђтЈЦСИіТЏ┤ТјЦтЈЌУЌЈТќЄУ»ЉТюгуџётЈ»жЮаТђДсђѓ
тЏЏсђЂ тЁ│С║јРђютЏаТюЅСИЅуЏИ№╝їСйЋуГЅСИ║СИЅ№╝їжЂЇТў»т«ЌТ│ЋТђДсђЂтљїтЊЂт«џТђДсђЂт╝ѓтЊЂжЂЇТЌаТђДРђЮСИђтЈЦуџёУ»ЉТ│Ћ
У┐ЎСИђтЈЦт«ъУ┤ет║ћУ»ЦтЁ│УЂћтЁХтљјуџёРђюТГцСИГТЅђСйюТђДТѕќтІцтІЄТЌажЌ┤ТЅђтЈЉТђД№╝їжЂЇТў»т«ЌТ│Ћ№╝їС║јтљїтЊЂт«џТюЅТђД№╝їт╝ѓтЊЂжЂЇТЌаТђД№╝їТў»ТЌатИИуГЅтЏаРђЮсђЂРђютљїТ│ЋУђЁ№╝їУІЦС║јТў»тцё№╝їТўЙтЏатљїтЊЂтє│т«џТюЅТђДРђЮС╗ЦтЈіРђют╝ѓТ│ЋУђЁ№╝їУІЦС║јТў»тцё№╝їУ»┤ТЅђуФІТЌатЏажЂЇжЮъТюЅРђЮСИЅтЈЦСИђУхиУ«еУ«║сђѓТѕЉУ«цСИ║У┐ЎТў»тюесђітЁЦУ«║сђІуџёТбхсђЂУЌЈсђЂТ▒ЅСИЅТюгт»╣тІўуаћуЕХСИГТюђтђ╝тЙЌтЁ│Т│еуџёжЃетѕє№╝їСйєУ┐Єтј╗уџёТ▒Ѕтю░уџётГдУђЁС╗гтЇ┤Т▓АТюЅтЈЉуј░тЁХСИГуџёти«т╝ѓсђѓ
У┐ЎжЄїТѕЉтЁѕт░єУ┐ЎтЏЏтЈЦтюеУЌЈТќЄТюгСИГуџётєЁт«╣У»ЉтЄ║ТЮЦ№╝џ
1. тЏаУђЁ№╝їтЇ│Тў»СИЅуЏИсђѓУІЦТюЅжЌ«№╝џУ┐ЎжЄїуџёСИЅуЏИтЈѕТў»С╗ђС╣ѕ№╝Ъ№╝ѕуГћ№╝ЅС╣Ът░▒Тў»т«ЌТ│ЋсђЂтћ»С║јтљїтЊЂСИГтє│т«џТюЅсђЂС║јт╝ѓтЊЂСИГтє│т«џт┐ЁТЌасђѓ
2. тЁХСИГТЅђСйюТђДТѕќТЌатІцтІЄТЌажЌ┤ТЅђтЈЉТђДт«џТЅђУ░ЊТў»т«ЌТ│ЋС╗ЦтЈіС║јТЌаТЅђуФІ№╝ѕТ│Ћ№╝ЅСИГтє│т«џт┐ЁТЌа№╝їТў»ТЌатИИСИіуџё№╝ѕуюЪ№╝ЅтЏасђѓ
3. тЁХСИГтљїТ│Ћтќ╗№╝їтЇ│Тў»УАеуц║СйєтЄАтЏаС╣Ітћ»С║јтљїтЊЂСИГТюЅУђЁсђѓ
4. Уђїт╝ѓТ│Ћтќ╗№╝їтЇ│Тў»УАеуц║СйєтЄАС║јТЌаТЅђуФІ№╝ѕТ│Ћ№╝ЅСИГт┐Ёт«џТЌатЏаУђЁсђѓ[6]
тюеУ┐ЎжЄїТѕЉС╗гтЈЉуј░УЌЈУ»ЉсђЂтЦўУ»ЉСИГТюЅСИЅСИфжЄЇУдЂуџёСИЇтљїС╣Ітцё№╝џ
уггСИђсђЂтЁ│С║јРђютЏаТюЅСИЅуЏИРђЮСИђтЈЦсђѓУ┐ЎТў»ујётЦўуџёУ»ЉТќЄ№╝їСйєС╗јУЌЈТюгуџёТјфУ»ЇТЮЦуюІ№╝їУ┐ЎжЄїт╣ХТ▓АТюЅСй┐ућеРђюТюЅРђЮ№╝їУђїТў»тђЪтіЕу╗ЊТЮЪтЈЦУЎџУ»Ї№╝ѕrtsogs-tshig№╝ЅmoС╗БТЏ┐У░ЊУ»ЇУАеуц║РђюТў»РђЮсђѓтєЇтЈѓУђЃС╣ІтЅЇтЄаСйЇтГдУђЁт»╣ТбхТюгуџётЈЦУДБтѕєТъљТЮЦуюІ№╝їС╝╝С╣јТбхТюгСИГС╣ЪТ▓АТюЅРђюТюЅРђЮтГЌуџёт»╣У»Љ[7]сђѓУ┐ЎСИфжЌ«жбўтюеуЏ«тЅЇуџёТ▒ЅС╝атЏаТўјуаћуЕХСИГС╝╝С╣јС╣ЪтЈфТў»СИђСИфУАеУЙЙТќ╣т╝Јуџёт░ЈСИЇтљїУђїти▓сђѓСйєтюеУЌЈС╝атЏаТўјуџёУЄфуёХУ»ГУеђу│╗у╗ЪСИГ№╝їУ┐ЎжЄїтђњт║ЋућеРђюТў»РђЮућеРђюТюЅРђЮ№╝їТў»тЁ│С╣јРђюуюЪтЏаРђЮуџёт«џС╣ЅУЃйтљдт░▒СИђСйЊСИітљїтЁиСИЅуЏИуџёжЌ«жбў№╝їТў»тЁ│С╣јтЏаТўјСйюСИ║жђ╗УЙЉтиЦтЁитюеУЄфуёХУ»ГУеђт«ъУихт║ћућетЙЌтйЊСИјтљдуџёжЌ«жбўсђѓУ┐ЎТќ╣жЮбуџёУ»ду╗єУЙеУ«║№╝їУ»╗УђЁтЈ»тЈдтцќтЈѓУђЃуЈГудЁу┤бтЇЌТюГти┤уГЅТ│ежЄісђѓ
уггС║їсђЂтЇ│тюеуггС║їтЈЦСИГ№╝їТбхсђЂУЌЈсђЂТ▒ЅУ»ЉТюгуФЪжЃйСИЇуЏИтљїсђѓтЁХСИГ№╝їТбхТќЄТюгТГцтЈЦТюЅтЁ│С║јтљјС║їуЏИуџёТЈЈУ┐░№╝їСйєТ▓АТюЅуггСИђуЏИуџёТЈЈУ┐░№╝Џ[8]УЌЈТќЄТюгтѕЎТюЅуггСИђсђЂСИЅуЏИуџёТЈЈУ┐░№╝їу╝║уггС║їуЏИуџёТЈЈУ┐░№╝ЏУђїујётЦўУ»ЉТюгтѕЎТў»СИЅуЏИуџёТЈЈУ┐░С┐▒тЁесђѓт░▒УАежЮбТќЄТёЈ№╝їт«ъУ«ЕС║║жџЙС╗ЦуА«У«цУ░ЂТЏ┤уюЪуА«сђѓуёХт░▒тјЪТќЄУ┐ЎжЄїТЅђтЄ║уј░уџёТЌХТю║№╝їТў»ТГБтЦйтюеУДБжЄітљїсђЂт╝ѓтЊЂС╣Ітљј№╝їтЈѕтюетЇ│т░єУДБжЄітљїсђЂт╝ѓтќ╗С╣ІтЅЇуџёУ┐ЎСИфСИГжЌ┤СйЇуй«СИісђѓУ┐ЎТЌХтјЪТќЄуЅ╣тѕФТаЄСИЙС╣ЮтЈЦтЏаСИГуџёС║їсђЂтЁФСИцтЈЦТГБтЏасђѓт░▒ТГцТЌХУђїУеђ№╝їТў»тљдТюЅуггСИђуЏИТЈЈУ┐░уџёжюђУдЂУ┐ўжџЙС╗Цу╗ЎС║ѕт┐Ёт«џуџётѕцТќГ№╝їСйєУІЦу╝║уггС║їуЏИтѕЎС╝╝С╣јСИЇтљѕТЃЁуљєсђѓтЏаТГц№╝їТѕЉТјеТхІУЌЈТќЄУ»ЉТюгтюеУ┐ЎжЄїТў»Т╝ЈС║єСИђтЈЦ№╝їСйєтђњт║ЋТў»Т╝ЈУ»ЉУ┐ўТў»ТЅђСЙЮтјЪТюгСИЇтљї№╝їтѕЎТюЅтЙЁт░єТЮЦУЃйтюеУЌЈтї║ТЅЙтѕ░жѓБСИфсђітЁЦУ«║сђІуџёТбхТќЄтјЪТюгТЅЇтєЇС║ѕУђЃт»Ъсђѓ
уггСИЅсђЂтюеујётЦўУ»ЉТюгСИГ№╝їтЁ│С║југгС║їуЏИуџёУ»ЉТ│ЋтЮЄС╗ЦРђюС║јтљїтЊЂт«џТюЅТђДРђЮУ»ЉтЄ║№╝їт«ЃжЁЇтљѕуЮђуггСИЅуЏИуџёРђют╝ѓтЊЂжЂЇТЌаТђДРђЮ№╝їТъёТѕљС║єтљјТЮЦТЋ┤СИфТ▒ЅС╝атЏаТўјуаћуЕХСйЊу│╗т»╣тљјС║їуЏИтЈіС╣ЮтЈЦтЏауџёУДБжЄітЪ║уАђсђѓуёХУђї№╝їС╗јТбхсђЂУЌЈСИцТюгуџётГЌжЮбТёЈТђЮТЮЦуюІ№╝їУ┐ЎжЄїуџёУ»ЉТ│ЋС╝╝С╣јТюЅжЄЇтцДуџётЄ║тЁЦсђѓУ┐ЎС╣ЪТў»СИіТќЄТЈљтѕ░уџёТбхсђЂУЌЈсђЂТ▒ЅСИЅТюгсђітЁЦУ«║сђІт»╣У»╗уаћуЕХСИГТюђУЄ│тЁ│жЄЇУдЂуџёТЅђтюесђѓ
ТѕЉС╗гС╗јТюгУіѓСИђт╝ђтДІуџёУЌЈТќЄУ»ЉТќЄСИГуггСИђсђЂСИЅтЈЦСИГСИЇжџЙуюІтѕ░№╝їУЌЈТЌЈтЏаТўјтГдУђЁС╗гт»╣У┐ЎжЄїуџёуггС║їуЏИуџёУДБУ»╗Тў»Рђютћ»С║јтљїтЊЂСИГтє│т«џТюЅРђЮсђѓУ┐ЎжЄїТюђжЄЇУдЂуџёт░▒Тў»тюеРђютљїтЊЂРђЮС╣ІтЅЇтЄ║уј░С║єСИђСИфжЎљт«џУ»ЇРђютћ»РђЮсђѓУ┐ЎСИфтГЌтюетјЪУЌЈТќЄСИГт»╣У»Љт░▒Тў»жѓБСИфnyidтГЌсђѓnyidтГЌтюеУЌЈТќЄСИГТюЅУАеуц║т»╣тЁХу┤ДТјЦС╣ІтЅЇтЈЦтГљТѕљтѕєУхитіат╝║ТїЄуц║уџёСйюуће№╝їтюеТќЄСИГ№╝їтйЊСИцт║дТЈЈУ┐░уггС║їуЏИуџёТЌХтђЎ№╝їnyidтГЌжЃйу┤ДТјЦС║јРђютљїтЊЂРђЮСИђУ»ЇС╣Ітљј№╝їТЋЁУбФУДБжЄіСйют»╣тљїтЊЂуџёу«ђтѕФСИЊТїЄ№╝їС╣Ът░▒Тў»У»ЉСйюСИГТќЄуџёРђютћ»С║јтљїтЊЂРђЮуџёТёЈТђЮсђѓтюеУЌЈТќЄТюгт»╣уггСИЅуЏИуџёТЈЈУ┐░СИГТѕЉС╗гтљїТаиУЃйуюІтѕ░У┐ЎСИфnyidтГЌ№╝їСйєтюетљїТаиСИцт║дт»╣уггСИЅуЏИуџёТЈЈУ┐░СИГ№╝їnyidтГЌТў»у┤ДТјЦС║јРђюТюЅРђЮтГЌС╣Ітљј№╝їтЏаТГцУ┐ЎТЌХт«ЃУбФуљєУДБСйюСИ║Тў»т»╣РђюТюЅРђЮтіат╝║ТїЄуц║№╝їтЇ│У»ЉТѕљТ▒ЅУ»ГСИГуџёРђют┐ЁТюЅРђЮСИђУ»Їсђѓ
СИЇтЇЋУЌЈТќЄтдѓТў»№╝їтЇ│СЙ┐ТѕЉС╗гт»╣тІўТбхТќЄТюгС╣ЪТюЅуЏИтљїуџёТЃЁтєхсђѓТѕЉС╗гтюеТбхТќЄТюгУ«▓У┐░СИіжЮбУЌЈТќЄТюгУ»ЉТќЄуџёуггС║їсђЂСИЅсђЂтЏЏтЈЦТЌХ[9]№╝їжЃйтЈЉуј░С║єт»╣т║ћуџёжѓБСИфevaсђѓУ┐ЎжЄїуџётЏЏСИфevaтюеТбхТќЄСИГтЄ║уј░уџёТЃЁтєхтњїУЌЈТќЄуџёу┐╗У»ЉТЃЁтєхтјЪт«їтЁеСИђУЄ┤сђѓС╣Ът░▒Тў»У»┤evaтљїТаитюеТЈЈУ┐░уггС║їуЏИТЌХ№╝їСИцт║ду┤ДТјЦтюеРђютљїтЊЂРђЮС╣ІтљјтЄ║уј░сђѓУђїт»╣т║ћтю░№╝їevaС╣ЪтюеТЈЈУ┐░уггСИЅуЏИТЌХ№╝їСИцт║ду┤ДТјЦтюеРђюТюЅРђЮтГЌС╣ІтљјтЄ║уј░сђѓ
У┐Ўу╗ЮСИЇС╝џТў»СИђуДЇТЌаТёЈуџётиДтљѕсђѓтЈ»С╗ЦУ»ЂТўјуџёуљєућ▒ТюЅС║їСИф№╝џ1сђЂсђітЁЦУ«║сђІСйюСИ║жЎѕжѓБуџёсђіжЌеУ«║сђІуџёТ│ежЄі№╝їТў»ТЌетюеСИ║УДБжЄіжЎѕжѓБуџётЏаТўју│╗у╗ЪтјЪуљєсђѓУЎйуёХ№╝їТѕЉС╗гтюесђіжЌеУ«║сђІСИГТюфУЃйуюІтѕ░тЁ│С║јтЏаСИЅуЏИуџётЁиСйЊТЈЈУ┐░№╝їТЌаТ│ЋУхёСйюУ┐ЎжЄїУ«║У»ЂуџёуЏ┤ТјЦСЙЮТЇ«сђѓСйєТў»№╝їжЎѕжѓБтюетЁХтЈдСИђжЃеТЏ┤СИ║жЄЇУдЂуџётЏаТўјтиеУЉЌРћђРћђсђіжЏєжЄЈУ«║сђІуггС║їтЊЂСИГТЏЙСИЊжЌеУ«еУ«║тѕ░У┐ЎСИфжЌ«жбўсђѓТЋЁТГц№╝їРђютћ»С║јтљїтЊЂСИГтє│т«џТюЅРђЮт║ћТЌауќЉТў»жЎѕжѓБТюгС║║уџётјЪТёЈсђѓ2сђЂСйюСИ║тЇ░т║дтљјТЮЦу╗ДТЅ┐жЎѕжѓБтЏаТўјждќУдЂтцДтИѕТ│ЋуД░№╝їтюетЁХУЉЌтљЇуџёсђіжЄіжЄЈУ«║сђІСИГ№╝їТЏЙтюеуггтЇЂСИЃУЄ│уггС║їтЇЂтЏЏжбѓтЈітЁХуЏИтЁ│УЄфжЄіСИГ№╝їтцДу»Єт╣Ётю░У«еУ«║С║єтдѓСйЋТЅЇТў»жЎѕжѓБт»╣уюЪтЏауггС║їсђЂСИЅуЏИУДБжЄіуџёуюЪт«ъТёЈУХБсђѓС╗ќТїЄтЄ║С║є№╝їУІЦСй┐жЎѕжѓБТЅђСИЙтЏаСИЅуЏИуљєУ«║Тў»УЃйС┐ЮУ»ЂТюЅТЋѕТјеуљєтйбт╝ЈуџёУ»Ю№╝їтѕЎтЁХСИГуггС║їуЏИуџётє│т«џт┐ЁтйЊС╗ЦРђютћ»С║јтљїтЊЂСИГтє│т«џТюЅРђЮУЃйтюеуюЪТЋїт«Ќуџёт┐ЃУ»єСИГУјитЙЌтє│т«џСИ║тЅЇТЈљсђѓСИЇС╗ЁтдѓТў»№╝їС╗јтЁХТќЄСИГтєЁт«╣тЈЇТўа№╝їтЇ│СЙ┐Тў»тюеТ│ЋуД░С╣ІтЅЇ№╝їСйюСИ║жЎѕжѓБуџёС║▓С╝ат╝ЪтГљуџёУЄфтюетєЏ№╝їУЎйуёХт»╣тЁХтИѕжЎѕжѓБуџёуггС║їсђЂСИЅуЏИУ«▓Т│ЋТюфУЃйтюєТ╗АуљєУДБ№╝їСйєС╗ќтюетЁ│С║југгС║їсђЂСИЅуЏИтюежђ╗УЙЉУ«цУ»єУ┐ЄуеІСИГтЈ»тафС║њТјеУ┐ЎСИђуѓ╣СИіУ┐ўТў»ТюЅтЁ▒У»єуџёсђѓТЇ«ТГц№╝їТѕЉС╗гС╣ЪТюЅуљєућ▒уЏИС┐А№╝їтљїТаиТў»СИ║жЎѕжѓБт╝ЪтГљуџётЋєуЙ»уйЌ№╝їСИЇУЄ│С║јСИЇТЄѓУ┐ЎСИфтјЪуљєсђѓ
С╗ЦСИіуџёУ┐ЎС║ЏТјбУ«е№╝їУ┐ўТў»ТЇ«уЏ«тЅЇТЅђТюЅУхёТќЎуџёТјеУ«║сђѓтЁХтјЪтѕЎСЙЮуёХТў»СЙЮжЮаУ»ГУеђу╗ЊТъёуџётљѕуљєТђДтњїтєЁт«╣у╗ЊТъёуџётљѕуљєТђДсђѓт»╣ТГцТЏ┤У»ду╗єсђЂТЏ┤Ти▒тЁЦсђЂТЏ┤тЄєуА«уџёТјбУ«еуі╣тЙЁТюфТЮЦС╝џТюЅТЏ┤тцџтЈ»С┐АуџётЈцу▒ЇТќЄуї«уџёжЮбСИќтњїт»╣тЁХтЄєуА«уџёУДБУ»╗сђѓУ┐ЎС║ЏТјбУ«еТЌауќЉС╝џСИ║ТѕЉС╗гТ▒Ѕтю░СйЏТЋЎтЏаТўјтГдуџёуаћуЕХтЈЉт▒ЋТЈљСЙЏТЏ┤т╣┐жўћсђЂТЏ┤ТИЁТЎ░уџёУДєжЄјтњїТЏ┤тцџтЁЃуџёУДњт║дсђѓУђїућ▒ТГцт░єС╝џт╝ЋС╝ИуџёТЏ┤т╣┐Т│ЏуџёуљєУ«║ТјбУ«етњїт«ъУихт║ћуће№╝їТЅЇТў»уюЪТГБуџёТюђу╗ѕуЏ«ТаЄсђѓ
[2] УЌЈТќЄсђітЁЦУФќсђІТюЅтЁЕтђІуЅѕТюгсђѓСИђТў»ТюгТќЄТЅђт╝ЋућеуџёжђЎтђІтЙъТбхТќЄУГ»тЁЦУЌЈТќЄуџёуЅѕТюгсђѓтЈдтцќжѓёТюЅСИђтђІТў»тЙъСИГТќЄУГ»тЁЦУЌЈТќЄуџёуЅѕ№╝ѕтїЌС║гуЅѕ№╝їCeтИЎ№╝їугг84bУЄ│угг
[3] жђЎУБАТЅђУффтЇ░тю░УГ»тИФ№╝їСИ╗С╗ЦуЋХТЎѓУЃйу▓ЙТЊЁТбхТќЄтю░тЇђуѓ║СЙІ№╝їСИдСИЇТў»т░ѕТїЄуЈЙС╗ітю░уљєСИіуџётЇ░т║дтю░тЇђсђѓСИІтљїсђѓ
[4] угг337жаЂсђѓ
[5] угг337жаЂсђѓ
[6] тѕєтѕЦтюесђіСИ╣уЈауѕЙсђІ№╝їугг80bсђЂ
[7] сђіТ│ЋТ║љсђІ№╝їугг338жаЂ№╝ЏсђітЇЌС║ъуаћуЕХсђІ№╝їугг41жаЂсђѓ
[8] сђіТ│ЋТ║љсђІ№╝їугг339жаЂ№╝ЏсђітЇЌС║ъуаћуЕХсђІ№╝їугг41жаЂсђѓ
[9] сђіТ│ЋТ║љсђІ№╝їугг339-341жаЂ№╝ЏсђітЇЌС║ъуаћуЕХсђІ№╝їугг41-42жаЂсђѓ
№╝ѕтцЇТЌдтцДтГд05у║ДуАЋтБФуаћуЕХућЪсђђуйЌті▓ТЮЙ№╝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