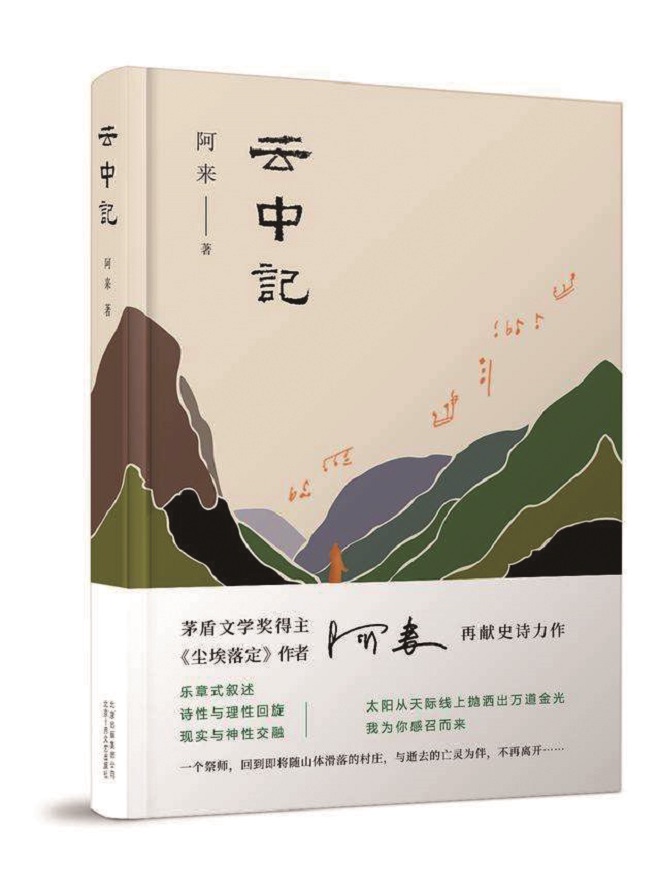
《云中记》(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年4月)的扉页上有这样几行字:“向莫扎特致敬。写作这本书时,我的心中总回想着《安魂曲》庄重而悲悯的吟唱。”某种意义上,《云中记》正是阿来写给5·12汶川地震中逝者们的一首安魂曲。10年之后再次回望,在曾经的巨痛即将被大众遗忘的时刻,阿来用自己极度克制的笔触、平静的讲述和深刻冷静的思考,写出了拥有《安魂曲》般力量和美感的《云中记》。

记 者:《云中记》的写作开始于5·12大地震发生10年之后,这中间经历了一段漫长的沉淀。迟迟没有动笔的原因,是您有意克制、不想被一时浓烈的情绪所裹挟,还是一种自然的失语状态,就像我们面对至亲的突然离开时仿佛丧失表达能力一样?
阿 来:其实这两种原因都有。灾难发生的当下,我也觉得有很多话可以说,当时那种情境下,很多作家都提起笔来书写,表达自己的情绪和所观察到的现实。但是面对这样的写作,我马上产生一种警惕,难道文学就是简单地说出事实吗?难道现实主义就是简单地描绘自己所看到的吗?我觉得在这样重大的现实面前,文学应该写出更有价值的、更值得探索和挖掘的东西。但是这东西究竟是什么,当时我没有想得很清楚。而且的确,如果选择第一时间去写,我也很容易情绪失控,包括我们看到很多及时出现的作品,其实都是失控的、没有节制的表达,你以为自己是在第一时间、在一个最好的状态中去书写的,但是最后发现所达到的不是想要的效果。
记 者:那么,是什么具体的契机让您最终提笔的?
阿 来:我其实没有想过什么具体的契机。我知道这个题材、这个内容对我来说很重要,我也相信自己有一天肯定会去书写它。但是我的写作一向不会做什么具体的规划、准备,也从来不给自己规定什么时候要写什么。其实当时我正在写另一个长篇小说,突然有一天,我的脑海中一下涌现出一种情绪,出现了一个具体的形象,这些都与我当时正在写的长篇完全没有关系。但那个形象又是那么鲜明,在我脑中挥之不去,那就是后来出现在小说《云中记》中的祭师。于是,我停下自己手中正在写的那个长篇,开始了《云中记》的写作。
对我来说,写作常常就是这样的情形。一件事情,如果我对它有兴趣,那么它就一定会存在于我心里,我不会着急去表达,而是先克制住表达和书写的冲动,因为我知道这种冲动有时候是虚假的,或者是短暂的。长篇小说的写作需要有漫长的时间、大量的经历投入,一时的感觉是不够的,你必须有充分的内心准备,不然一口气是没办法支撑自己写到底的。
记 者:您的作品一直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前两年的“山珍三部曲”《蘑菇圈》《三只虫草》《河上柏影》通过珍稀物种的现状反思了当代社会的商业逻辑。在生活中,您也是个非常热爱自然与生灵的“博物学家”。而《云中记》写的是自然灾难,或者说是自然对人的惩罚。通过这部作品,您对人与自然的关系有什么新的理解?
阿 来:刚才提到我在灾难发生的当下没办法马上动手的原因,也是我当时没有想明白的问题,主要是我们到底应该如何处理与死亡、与自然的关系。过去我们所看到的中外文学中的灾难书写,不管是战争灾难还是政治迫害,这些灾难的发生都有具体的原因和对象,我们习惯了对面有个敌人、有一种敌对的力量,这样我们才可以表达情绪,才可以施以仇恨、批判。但自然灾难完全不同,台风、地震、火灾、水灾,这些都是大自然按照自己的规律在运行,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人要生活在大地上,并不是大地发出的邀请,而是人类自己的选择。我们总说“大地母亲”,大自然是我们永远没办法去仇恨的。我们的文学习惯了把所有问题设置出冲突双方,但在自然灾害这里,冲突双方是不存在的,你对面的大自然是没有情感的,它并不是施暴者,因此你也不能把它当作敌人,这个问题是我们此前的灾难文学所不曾面对的,也是我在写作时首先必须想清楚的。
比起“山珍三部曲”,《云中记》对自然与人的关系思考,其实触及的是更加本质性的关系。大自然为人的生存提供了庇护,提供了各种各样的资源,但它也有情绪发作的时候,它一旦发作,人类就将面临灾难,而这时,人的宿命性就出现了。人必须在这个充满灾难的大地上生存,你在享受大自然恩赐的同时就必须承受可能发生的灾难,这一切我们都别无选择。这是人类的宿命,也是悲剧性所在。这个时候,我们才真正深刻意识到人类的无力、渺小,因此,爱护自然绝不是基于狭隘的环保主义,而是一种更根本的宿命论的认识。如果说《云中记》有一点贡献的话,我想主要就是处理和提供了对死亡、对自然这两个方面的新的书写。
记 者:从《尘埃落定》到《机村史诗》,再到今天的《云中记》,可以看出,您对现代文明始终持有一种复杂的思考与审视。小说《云中记》写到灾后重建中出现的一些新情况,尤其是后面几章,央金、祥巴等人本来是灾难的受害者,但他们在商业逻辑的影响下,对家乡和乡亲的做法、行为更让人觉得痛心。您是怎么构思这部分内容的?
阿 来:大地震过去这么些年,其实我还是一直关注着灾区的情况。小说中所写到的这些现象其实在现实生活中都能找到影子,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只不过我用文学的手法进行了改头换面而已。对于自己笔下的人物和现实生活中看到的这些现象,我还是基本秉持着“温柔敦厚”的态度,提出问题的同时也尽量理解他们吧。
对于这场大灾,我关心的不止是当时的灾区和灾民的情况,我更关心的是之后重建中的灾区。一场灾难带来了很多人员伤亡、财产损失,这些伤亡和损失是无法逆转的,发生了就是发生了,触景生情很正常,但是悲天呼号本身并没有价值。更重要的是,在灾难发生之后,我们人的意志体现在哪里、发生了什么变化,之后我们是怎样对生活、对社会进行重建的,在我看来这比一时受灾的情况更重要。所以在《云中记》中,我想写这部分内容。
记 者:就像云中村人所面临的现实一样,在现代化不可抗拒的大趋势面前,云中村这样的古老文明,或者说云中村人所信仰的精神和传统,在今天处于怎样的地位,该如何自处?
阿 来:我并不认为所有旧的东西都应该保存下来,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它的轨迹,与时代脱节之后,消失就是必然的命运。人类文明几千年,这当中不断的进步,其实就是不断发现新的事物、同时不断与旧的事物告别。
我们现在有一种强烈的怀旧情结,这里面其实有两个心理基础。一是我们提倡尊重传统、保护传统的大环境。这个环境是好的,但其中有问题需要辨析。在我看来,我们对传统的理解和保护,更重要的是领会其中的精神,地球空间有限,要不要保存那么多物质的东西,这个问题我还是存疑的。与其去保存那么多具体的物质,不如多读一点我们古代的经典著作,我们民族传统真正精神性的东西其实是记载在文字和书籍中的,而不只是留存在某个老物件上。现代社会出现了拜物主义,很多“怀旧”行为,有时候其实只是对物质的迷恋,而不是对传统的尊重。现在很多人对于传统文化的理解就是老物件、旧仪式,所谓“鉴宝”,最终关注的还是它的商品价值。事实上,我觉得传统文化最重要的是其中的精神,我们传承传统文化,并不是传承一件物品、一些技术上的问题,而应该是传承它真正的内在精神。
还有一个心理基础是,当代社会中的人们在面对新事物时内心有一种焦虑和不确定的、不安全的感觉。过去出现的新事物往往是可感可触的,火车、汽车虽然是新的,但人们还可以把握。但是到现在,我们每天所面对的很多新问题是大家完全无法把握的,比如我们热衷于讨论金融、科技、人工智能等等,大家耳熟能详,但是很少有人能真正说清楚它们到底是什么。对于这些新事物,人们一方面极度依赖,一方面又无法把握。在这种关系中,人类本身会产生焦虑,会时常有缺乏安全感的时刻,所以我们一边急速发展,不停地出现新事物,另一方面又不停地“怀旧”“怀乡”,对旧事物总有一种迷恋。
记 者:小说中阿巴对于传统的态度,其实也代表了您刚才所说的观点。这个人物身上有某种矛盾性,他开始以祭师的身份参加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培训班时,好多东西都记不住,被大家嘲笑为“冒牌的半吊子”,但另一方面,在大灾发生之后,他却成为了对故土和已故乡亲最坚定的守护者,甚至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您是如何定位并把握阿巴这个人物的?
阿 来:阿巴这个人物身上是有普遍性的,在现实生活中,我见到的一些所谓传承人都有点“半吊子”。这当中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文明传统并不是很顺利地传承下来的,“文革”对传统文化形成了强力的阻断,很多传统在当时人们的思想中被切断了。所以,直到今天,我们对传统文化在内心的理解和认可其实并不彻底,很多人都是似懂非懂的。《云中记》中的阿巴就是这样,一开始他对于传统文化是什么其实并不是很清楚,但是灾难的发生唤醒了他,唤醒了他对传统的记忆、对传统文化精神的理解,也唤醒了他作为“传承人”的责任感。
记 者:对作家来说,“穿梭生死”的写作是很不容易的。《云中记》通过阿巴实现了这一点。阿巴是云中村人们与亡人沟通、与彼岸世界沟通的一座桥梁。与西方人不同的是,中国文化中一直缺乏“死亡教育”,对于死亡,我们好像除了恐惧之外一无所知。《云中记》中,阿巴“向死而生”,某种程度上他也教给我们究竟应该如何面对死亡。
阿 来:阿巴这个人物的命运一开始我并没有明确的定位。在写作的过程中,我跟他一起经历、一起成长,到最后,他通过自己的行动和思考了悟了生死,参透了其中的关系和秘密。所以面对自己最后的结局,阿巴的内心是非常平静的,甚至进入了一种伟大的境界。
中国人对待灾难和对待死亡大多有三个阶段的感觉,首先是你说的恐惧,接着是受震动,然后就是遗忘。我觉得“死亡教育”应该有两方面内容,一是对于正在面对死亡的人,如何能够平静坦然地接受死亡,接受这是人的必然命运;还有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当你面对他人的死亡时应该思考什么,如何从别人的经历投射到自己,思考自己的生存和生命价值以及死对生的意义,这是对每一个个体的生者,对整个社会和国家而言都很重要的深层问题。
记 者:十余年过去了,彼时语境中的很多喧嚣如今已经趋于宁静。就像您说的,我们好像已经进入了“遗忘”的阶段。小说《云中记》就像是一场对亡灵的告慰,告慰小说中的阿巴,更是告慰在那场灾难中受灾的灵魂。这次写作,对您个人来说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吗?
阿 来:这样的遗忘我真的看过太多太多了。地震发生之后,我第一时间赶到汶川,此后又去过北川、映秀等地。在现场,我眼见着救灾人员、志愿者的热情一天天退却,遗忘开始发生。最开始的半个月时间内,大家都沉浸在那种巨大的悲痛中,救灾的热情也都很高涨。半个月过去之后,这种热情一天天的退却、递减,救灾的人们每一天都呈现出完全不同的状态。不用说现在已经过去了十余年,我曾经亲身经历的遗忘的速度,是以天为单位计算的。
写作《云中记》,其实我并没有想说告慰什么人。在那场大地震中,受灾的人里面没有一个是我自己熟悉的、身边的人,但是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看,我们人类都处于“生命共同体”之中,所以,他们的受难也是我的受难,他们的经历也是我的经历。因此,这次写作其实就是记录一段我与那些受难的人们、小说中的人们共同的经历,记录我们共同的沉痛的记忆。完成《云中记》的写作对我而言,首先是让自己心中埋伏10年的创痛得到了一些抚慰,是我对自己那段经历、那种感受的一个交代,那段记忆我永远不会忘,但是写完之后我心里释然了很多。
原刊于《文艺报》2019年11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