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В
гҖҖгҖҖж—ҘеүҚпјҢи‘—еҗҚи—Ҹж—ҸиҜ—дәәжүҺиҘҝжүҚи®©ж•Јж–ҮиҜ—йӣҶгҖҠдёғжүҮй—ЁгҖӢеҮәзүҲеҸ‘иЎҢгҖӮиҜ—дәәеңЁд»–зҡ„еҗҺи®°дёӯеҶҷеҲ°пјҡвҖңжҲ‘жғіз»ҷжҲ‘еҚҒе…«е№ҙзҡ„иҜ—жӯҢд№Ӣж—…з”»дёҠеҸҘеҸ·гҖӮиҝҷдёӘж—…зЁӢпјҢиҷҪ然жңүзқҖжІҝйҖ”зҫҺеҘҪзҡ„йЈҺжҷҜеҸҜд»Ҙи®©жҲ‘й•ҝд№…ең°йҷ¶йҶүе…¶дёӯпјҢдҪҶйҒ“и·ҜдёҠзҡ„иү°йҡҫеӣ°иӢҰд№ҹз»ҷдәәеёҰжқҘдәҶйҡҫд»ҘиЁҖиҝ°зҡ„еҝғзҗҶеҺӢеҠӣгҖӮе№ёеҘҪиҝҷдёҖеӨ©з»ҲдәҺд»Ҙиҝҷжң¬ж•Јж–ҮиҜ—йӣҶзҡ„зј–иҫ‘е’ҢеҚ°еҲ·иҖҢжӮ„жӮ„ең°еҲ°жқҘдәҶгҖӮвҖқвҖ”вҖ”иҜ»жқҘдёҚд»…еҝғдёӯй»Ҝ然пјҒ
гҖҖгҖҖеҸҜд»ҘжҜ«дёҚе®ўж°”ең°иҜҙпјҢеңЁйұјйҫҷж··жқӮзҡ„иҜ—еқӣпјҢжүҺиҘҝжүҚи®©д»Ҙд»–иҮӘе·ұзҡ„зӢ¬зү№ж–№ејҸпјҢжё…ж–°еҗҹе”ұдәҶж•ҙж•ҙеҚҒе…«е№ҙпјҒвҖ”вҖ”иҝҷеҜ№дёҖдёӘиҜ—дәәиҖҢиЁҖпјҢжҳҜдҪ•е…¶дёҚжҳ“пјҒ
гҖҖгҖҖиҝ‘ж—ҘпјҢи—Ҹдәәж–ҮеҢ–зҪ‘ж–ҮеӯҰйў‘йҒ“дё»зј–гҖҒи—Ҹж—Ҹйқ’е№ҙиҜ—дәәеҲҡжқ°В·зҙўжңЁдёңеҜ№жүҺиҘҝжүҚи®©иҝӣиЎҢдәҶи®ҝи°ҲгҖӮ
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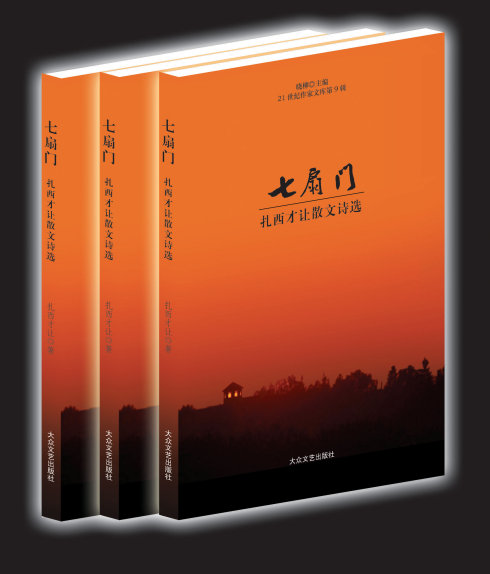
гҖҖгҖҖ
гҖҖгҖҖзҙўжңЁдёңпјҡдҪ еҘҪпјҢиҖҒе…„пјҒйҰ–е…ҲзҘқиҙәдҪ зҡ„иҜ—жӯҢз»“йӣҶеҮәзүҲпјҒиҝҷеҜ№и—Ҹж—Ҹж–Үеқӣе’Ңз”ҳиӮғж–ҮеқӣиҖҢиЁҖпјҢж— з–‘жҳҜ件幸дәӢпјҒ
гҖҖгҖҖжүҺиҘҝжүҚи®©пјҡе‘өе‘өпјҢеқҰзҺҮең°иҜҙпјҢеҜ№жҲ‘иҮӘе·ұиҖҢиЁҖпјҢиҝҷжҳҜ件幸дәӢгҖӮдҪҶеҜ№и—Ҹж—Ҹж–Үеқӣе’Ңз”ҳиӮғж–ҮеқӣжқҘиҜҙпјҢеӨҡдёҖдёӘжүҺиҘҝжүҚи®©пјҢжҲ–иҖ…е°‘дёҖдёӘжүҺиҘҝжүҚи®©пјҢеӨҡеҮәдёҖжң¬д№ҰжҲ–е°‘еҮәдёҖжң¬д№ҰпјҢжҲ‘и®ӨдёәйғҪдёҚеӨӘйҮҚиҰҒгҖӮйҮҚиҰҒзҡ„жҳҜпјҢд»–йҖҡиҝҮж–ҮеӯҰеҲӣдҪңпјҢиЎЁзҺ°дәҶдёӘдәәжүҖе…іжіЁзҡ„дё–з•ҢпјҢиЎЁиҫҫдәҶд»–еҜ№иә«иҫ№дёҮзү©зҡ„жғ…ж„ҹгҖӮ
гҖҖгҖҖжҲ‘дёҖзӣҙи®ӨдёәпјҢеҜ№дәҺдҪң家е’ҢиҜ—дәәжқҘиҜҙпјҢйҮҚиҰҒзҡ„еә”иҜҘжҳҜдҪңе“Ғжң¬иә«гҖӮеҘҪзҡ„дҪңе“ҒиғҪеӨҹжҲҗе°ұеҘҪзҡ„дҪң家иҜ—дәәпјҢдҪҶеҘҪзҡ„дҪң家иҜ—дәәдёҚдёҖе®ҡеҶҷеҮәеҘҪзҡ„дҪңе“ҒгҖӮжҲ‘们зҺ°еңЁиҜ»еҚЎеӨ«еҚЎгҖҒиүҫз•Ҙзү№е’Ңжҷ®йІҒж–Ҝзү№пјҢиҜ»жқҺзҷҪгҖҒжқҺе•Ҷйҡҗе’ҢйҷҲеӯҗжҳӮпјҢиҜ»е…ӯдё–иҫҫиө–д»“еӨ®еҳүжҺӘе’ҢејҳдёҖжі•еёҲжқҺеҸ”еҗҢгҖҒе®һйҷ…дёҠиҜ»зҡ„жҳҜ他们зҡ„дҪңе“ҒпјҢ并且йҖҡиҝҮе…¶дҪңе“Ғи®ӨиҜҶ他们иҝҷдәӣдәәгҖӮжүҖд»ҘпјҢдёҖжң¬д№Ұзҡ„е‘ҪиҝҗпјҢеҪ“е®ғйқўдё–д№ӢеҗҺпјҢдҪңиҖ…дјјд№Һж— жі•еҶіе®ҡе®ғзҡ„е‘ҪиҝҗпјҢжңүж•Ҳзҡ„ж“ҚдҪңе’Ңе®Јдј пјҢеҸӘиғҪеңЁзҹӯжңҹеҶ…дә§з”ҹеҪұе“ҚпјҢиғҪеҗҰйҷӘдјҙдёҚеҗҢзҡ„иҜ»иҖ…еәҰиҝҮ他们зҡ„зҫҺеҘҪж—¶е…үпјҢйӮЈе°ұеҝ…йЎ»зңӢдҪңе“Ғзҡ„йӯ…еҠӣгҖӮжҲ‘зҡ„иҜ—жӯҢжҳҜеҗҰиҝҳе…·еӨҮзқҖиҝҷз§Қйӯ…еҠӣпјҢзҺ°еңЁжҲ‘жҢҒжҖҖз–‘жҖҒеәҰпјҢеӣ дёәжҲ‘们еӣәжңүзҡ„дёӘдәәз§үжҖ§пјҢжҲҗй•ҝзҡ„дәәж–ҮзҺҜеўғпјҢжҺҘеҸ—зҡ„ж–ҮеҢ–зҶҸйҷ¶пјҢзңӢеҫ…дёҮзү©зҡ„зңје…үпјҢзҗҶи§Је°ҳдё–зҡ„зғҰеҝ§зӯүзӯүпјҢжҳҜдёҚе°ҪзӣёеҗҢзҡ„пјҢдҪңдёәиҜ»иҖ…зҡ„дёӘдҪ“пјҢд№ҹеӣ жӯӨиҖҢеҜ№дҪң家иҜ—дәәзҡ„дҪңе“ҒжңүзқҖдёӘдәәзҡ„е–ңеҘҪпјҒ
гҖҖгҖҖжңүзҡ„дҪң家иҜ—дәәиҜҙиҮӘе·ұзҡ„дҪңе“ҒжҳҜеҶҷз»ҷдә”еҚҒе№ҙеҗҺзҡ„иҜ»иҖ…зңӢзҡ„пјҢиҝҷиҜқиҷҪ然жңүдәӣзӢӮеҰ„пјҢдҪҶдјјд№Һйҡҗи—ҸзқҖж·ұж·ұзҡ„ж— еҘҲе’ҢйҒ—жҶҫпјҒ
гҖҖгҖҖ
гҖҖгҖҖзҙўжңЁдёңпјҡзңӢеҲ°дҪ зҡ„еҗҺи®°пјҢеҝғдёӯдёҚзҰҒй»Ҝ然пјҒз”ҡиҮіжңүзӮ№иҗҪеҜһе’ҢеҜӮеҜҘпјҒеңЁдҪ иҜ—жӯҢеҲӣдҪңжӯЈйҖўзӣӣжңҹзҡ„ж—¶иҠӮпјҢжҳҜд»Җд№Ҳи®©дҪ иҗҢз”ҹйҖҖж„Ҹпјҹ
гҖҖгҖҖжүҺиҘҝжүҚи®©пјҡе…¶е®һдёҚжҳҜйҖҖеҮәпјҢжҳҜйҖ”дёӯзҡ„дј‘ж•ҙпјҢжҳҜеҜ№жҲ‘зҡ„иҜ—жӯҢеҲӣдҪңзҡ„е°Ҹз»“е’ҢеҸҚжҖқгҖӮ
гҖҖгҖҖжҲ‘йқһеёёе–ңж¬ўдҪң家йҳҝжқҘпјҢе–ңж¬ўд»–зҡ„иҜ—йЈҺпјҢе–ңж¬ўд»–зҡ„е°ҸиҜҙпјҢе–ңж¬ўд»–зҡ„жҜ…然еҶіж–ӯзҡ„дёӘжҖ§гҖӮеҪ“е№ҙд»–еҶҷгҖҠдёүеҚҒеІҒж—¶жј«жёёиӢҘе°”зӣ–еӨ§иҚүеҺҹгҖӢиҝҷйҰ–й•ҝиҜ—ж—¶пјҢж„Ҹж°”еҘӢеҸ‘пјҢжүҚжғ…жЁӘжәўпјҢдҪҶд»–зӘҒ然еҒңжӯўдәҶиҜ—жӯҢеҶҷдҪңпјҢиҖҢе°ҶзІҫеҠӣиҪ¬еҗ‘зҹӯдёӯзҜҮе°ҸиҜҙеҲӣдҪңгҖӮгҖҠйҳҝе…ӢйЎҝе·ҙгҖӢгҖҒгҖҠжңҲе…үйҮҢзҡ„银еҢ гҖӢгҖҒгҖҠиЎҢеҲ‘дәәе°”дҫқгҖӢзӯүдҪңе“Ғзҡ„иҜһз”ҹпјҢзү№еҲ«жҳҜй•ҝзҜҮе°ҸиҜҙгҖҠе°ҳеҹғиҗҪе®ҡгҖӢзҡ„жЁӘз©әеҮәдё–пјҢд»ҘеҸҠеҗҺжңҹзІҫеҝғжү“йҖ зҡ„гҖҠз©әеұұгҖӢзі»еҲ—дҪңе“Ғзҡ„жҲҗеҠҹпјҢиҜҒжҳҺд»–зҡ„еҶіж–ӯжҳҜжӯЈзЎ®зҡ„гҖӮ
гҖҖгҖҖдҪңдёәеҶҷдҪңиҖ…пјҢжҲ‘们еә”иҜҘжҖқиҖғиҝҷж ·дёүдёӘй—®йўҳпјҡжҲ‘们дёәд»Җд№ҲеҶҷдҪңпјҹжҲ‘们еҶҷд»Җд№ҲпјҹжҲ‘们жҖҺд№ҲеҶҷпјҹиҝҷе…¶е®һе°ұжҳҜдёүдёӘжңүе…іеҶҷдҪңзҡ„еӨ§й—®йўҳгҖӮдёҚжҖқиҖғиҝҷдёүдёӘй—®йўҳзҡ„дәәпјҢж°ёиҝңеҸӘжҳҜдёӘж–ҮеӯҰзҲұеҘҪиҖ…пјҢд»ҺдәӢзҡ„жҳҜзӣІзӣ®еҶҷдҪңгҖӮжҖқиҖғ并иғҪеӨҹи§ЈеҶіиҝҷдёүдёӘй—®йўҳзҡ„дҪң家иҜ—дәәпјҢжүҚиғҪеңЁж–ҮеӯҰеҲӣдҪңйҳҹдјҚдёӯз•ҷдёӢд»–й«ҳеӨ§зҡ„иғҢеҪұгҖӮ
гҖҖгҖҖеҚҒе№ҙеүҚжҲ‘е°ұжҖқиҖғиҝҷдёүдёӘй—®йўҳпјҢдҪҶеҲ°зҺ°еңЁдёҖзӣҙжІЎжңүеӨ„зҗҶеҘҪпјҢеҺҹеӣ еҫҲеӨҡпјҢеӨ–еңЁзҡ„пјҢеҶ…еңЁзҡ„пјҢдё»и§Ӯзҡ„пјҢе®ўи§Ӯзҡ„пјҢйғҪжңүгҖӮжҲ‘дёҚжҳҜдёҖдёӘжҖҖжҠұеӨ§еҝ—зҡ„дәәпјҢеҸҜеңЁеҶҷдҪңдёҠиҝҳжҳҜжңүзқҖдёӘдәәзҡ„зҗҶжғігҖӮиҝҷдёӘзҗҶжғізҡ„е®һзҺ°дёҺеҗҰпјҢдёҖзӣҙеӣ°жү°зқҖжҲ‘пјҢеҪұе“ҚзқҖжҲ‘зҡ„еҲӣдҪңзҠ¶жҖҒгҖӮжҲ‘е§Ӣз»Ҳи®ӨдёәжҲ‘зҡ„еҲӣдҪңиҝҳжңӘеҲ°жүҖи°“зҡ„зӣӣжңҹпјҢжҲ‘еңЁж–ҮеӯҰеҶҷдҪңд№Ӣи·ҜдёҠиҫ№иө°иҫ№жӯҮгҖҒиҫ№жӯҮиҫ№иө°пјҢе°ұиҝҷж ·ж…ўеҗһеҗһең°иө°дәҶдёҖеҚҒе…«е№ҙгҖӮеҚҒе…«е№ҙпјҢеӨҡеҘҪзҡ„дёҖж®өе…үйҳҙе•ҠпјҢе©ҙе„ҝеҸҜд»Ҙй•ҝжҲҗеё…е“ҘзҫҺеҘіпјҢ家еәӯеҸҜд»Ҙз»„дәҶеҸҲе»әе»әдәҶеҸҲзҰ»пјҢдәӢдёҡеҸҜд»Ҙеі°еӣһи·ҜиҪ¬еҸҲйҷ·дәҺжІүжәәпјҢиҖҢжҲ‘е‘ўпјҹеҪ“е№ҙжҳҜдёӘйЈҺеҚҺжӯЈиҢӮзҡ„иҜ—жӯҢеҶҷдҪңиҖ…пјҢиҖҢд»ҠеҚҙе§Ӣз»ҲеғҸдёӘжү¶еўҷиө°и·Ҝзҡ„зһҺеӯҗпјҒеӣ жӯӨжҲ‘иҗҢз”ҹдәҶдёӯйҖ”жӯҮжҒҜзҡ„жғіжі•пјҢжӯҮжҒҜд№ӢеҗҺж•ҙиЈ…еҫ…еҸ‘иҝҳжҳҜз»қе°ҳиҖҢеҺ»пјҢиҝҷдёӘе°ұиө°зқҖзңӢеҗ§пјҒ
гҖҖгҖҖеҸҰеӨ–пјҢжҲ‘жіЁж„ҸеҲ°пјҢдёҺжҲ‘дёҖж ·еӨ„еңЁиҝҷз§ҚзҠ¶жҖҒдёӯзҡ„иҜ—дәәе’ҢдҪң家пјҢжҳҜжҜ”иҫғеӨҡзҡ„гҖӮдҪ жҜ”еҰӮиҜҙжҲ‘们з”ҳиӮғзҡ„и‘—еҗҚиҜ—дәәжЎ‘еӯҗгҖҒиЈ•еӣәж—ҸиҜ—дәәиҙәдёӯгҖҒи—Ҹж—ҸиҜ—дәәзҳҰж°ҙгҖҒж ЎеӣӯиҜ—дәәиҗ§йҹігҖҒеӣһж—ҸиҜ—дәәж•ҸеҪҰж–ҮзӯүзӯүпјҢдҪ иҜҙйғҪжңүжүҚеҗ§пјҢйғҪдјјд№Һж— жі•ж‘Ҷи„ұеӣ°еўғпјҢдёҺж–ҮеӯҰе§Ӣз»ҲдҝқжҢҒзқҖдёҖз§ҚиӢҘеҚіиӢҘзҰ»зҡ„и·қзҰ»гҖӮ
гҖҖгҖҖ
гҖҖгҖҖзҙўжңЁдёңпјҡи®°еҫ—йӮЈжҳҜ1994е№ҙз§ӢеӨ©пјҢеҲҡиө°еҮәз”ҳеҚ—иҚүеҺҹгҖҒеҲҡеҲҡеӯҰзқҖеҶҷиҜ—зҡ„жҲ‘пјҢеңЁиҘҝеҢ—еёҲеӨ§зҡ„ејҖеӯҰе…ёзӨјдёҠеҗ¬ж Ўй•ҝеңЁи®ІиҜқдёӯжҸҗеҸҠеҗҢд№ЎеҗҢж—Ҹзҡ„дҪ пјҢйӮЈж—¶жҳҜдҪ•зӯүзҡ„д»°ж…•е•ҠпјҒд»ҺйӮЈеӨ©ејҖе§ӢпјҢиҜ—жӯҢзҡ„еҠӣйҮҸе’Ңйӯ…еҠӣпјҢеҶҚж¬Ўж·ұж·ұеҮ»дёӯдәҶжҲ‘зҡ„еҝғзҒөпјҒд»ҠеӨ©пјҢдҪ иғҪеӣһеҝҶдёҖдёӢдҪ зҡ„иҜ—жӯҢд№Ӣи·Ҝеҗ—пјҹ
гҖҖгҖҖжүҺиҘҝжүҚи®©пјҡеҘҪпјҢе°ұйЎәзқҖдҪ зҡ„иҝҷдёӘй—®йўҳйҡҸдҫҝжүҜдёҖжүҜгҖӮзҺ°еңЁжғіжғіпјҢиҘҝеҢ—еёҲеӨ§зЎ®е®һжҳҜдёҖдёӘиғҪеӨҹиҜһз”ҹиҜёеӨҡиҜ—дәәзҡ„еӯҰеәңгҖӮжҲ‘们з”ҳиӮғиҜ—жӯҢеҲӣдҪңйҳҹдјҚдёӯзҡ„дҪјдҪјиҖ…пјҢж— и®әжҳҜеҠҹжҲҗеҗҚе°ұзҡ„пјҢиҝҳжҳҜеҰӮж—ҘдёӯеӨ©зҡ„пјҢиҝҳжҳҜжӯЈеңЁиҜ•еӣҫеҶІејҖдёҖжқЎиЎҖи·Ҝзҡ„пјҢеӨ§еӨҡжҜ•дёҡдәҺиҘҝеҢ—еёҲеӨ§пјҢиҝҷдјјд№ҺдёҺиҝҷжүҖеӯҰеәңзҡ„ж–ҮеҢ–з§Ҝж·Җжңүе…іпјҢдёҺж–ҮеӯҰеҲӣдҪңж°ӣеӣҙжңүе…іпјҢдёҺе®Ҫжқҫзҡ„ж Ўеӣӯдәәж–ҮзҺҜеўғжңүе…ігҖӮжҲ‘еңЁиҝӣе…ҘеёҲеӨ§д№ӢеҲқпјҢе°ұејәзғҲең°ж„ҹеҸ—еҲ°дәҶиҝҷдёҖзӮ№гҖӮйӮЈж—¶еҖҷеёҲеӨ§жңүдёүдёӘж–ҮеӯҰзӨҫпјҢз»ҷдәәеҚ°иұЎеҫҲж·ұпјҢдёҖдёӘжҳҜвҖңжҲ‘们вҖқпјҢиҗ§йҹігҖҒеҫҗе…ҶеҜҝ他们еңЁеҠһпјҢеңЁж ЎеӣӯйҮҢжңүзқҖе№ҝжіӣзҡ„еҪұе“ҚпјӣдёҖдёӘжҳҜвҖңе…Ҳй”ӢвҖқпјҢдёӯж–Үзі»еҠһзҡ„пјҢжҲ‘们称д№Ӣдёәдёӯж–Үзі»жүҚеӯҗжүҚеҘізҡ„иҠіиҚүең°пјӣдёҖдёӘжҳҜвҖңжҷЁжҳ•вҖқпјҢж”ҝеҸІзі»еҠһзҡ„пјҢжҳҜжҲ‘иө°дёҠиҜ—жӯҢеҶҷдҪңд№Ӣи·Ҝзҡ„еҠ жІ№з«ҷгҖӮжҲ‘е…ҲжҳҜеңЁиҝҷдёүдёӘеҶ…йғЁдәӨжөҒеҲҠзү©дёҠеҸ‘дҪңе“ҒпјҢеҗҺжқҘе°ұеңЁгҖҠиҘҝеҢ—еёҲеӨ§жҠҘгҖӢгҖҒгҖҠйҳіе…ігҖӢгҖҒгҖҠзәўжҹігҖӢгҖҒгҖҠж јжЎ‘иҠұгҖӢгҖҒгҖҠйЈһеӨ©гҖӢгҖҒгҖҠиҘҝи—Ҹж–ҮеӯҰгҖӢгҖҒгҖҠиҜ—зҘһгҖӢгҖҒгҖҠиҜ—жӯҢжҠҘжңҲеҲҠгҖӢгҖҒгҖҠжҳҹжҳҹиҜ—еҲҠгҖӢзӯүеҲҠзү©дёҠеҸ‘пјҢиө°зҡ„и·Ҝеӯҗеҹәжң¬дёҠжҳҜдј з»ҹејҸзҡ„пјҢе°ұеғҸж•ҷеёҲдёҠиҒҢз§°дёҖж ·пјҢз”ұж•ҷе‘ҳеҲ°еҲқзә§пјҢз”ұеҲқзә§еҲ°дёӯзә§пјҢз”ұдёӯзә§еҲ°й«ҳзә§пјҢдёҖжӯҘдёҖдёӘеҸ°йҳ¶пјҢдёҖжӯҘдёҖдёӘи„ҡеҚ°гҖӮеҲ°еӨ§еӯҰжҜ•дёҡж—¶пјҢдёҚзҹҘдёҚи§үз«ҹ然混жҲҗдәҶдёҖдёӘж ЎеӣӯиҜ—дәәгҖӮеӨ§еӯҰжҜ•дёҡеҗҺпјҢеҶҷдҪңжңүдәҶж–№еҗ‘жҖ§пјҢдёңиҘҝд№ҹеҸ‘еҫ—жӣҙеӨҡпјҢдёҠдәҶгҖҠиҜ—еҲҠгҖӢгҖҒгҖҠж°‘ж—Ҹж–ҮеӯҰгҖӢгҖҒгҖҠж•Јж–ҮиҜ—гҖӢгҖҒгҖҠж•Јж–ҮиҜ—дё–з•ҢгҖӢзӯүжқӮеҝ—пјҢдҪңе“Ғе…ҘйҖүеӨҡжң¬иҜ—жӯҢйҖүжң¬пјҢиҺ·дәҶдәӣе…ЁеӣҪжҖ§зҡ„гҖҒзңҒзә§зҡ„еӨ§еҘ–пјҢд№ҹжңүе№ёиў«и—Ҹдәәж–ҮеҢ–зҪ‘гҖҒиҘҝи—ҸдҝЎжҒҜдёӯеҝғгҖҒз”ҳиӮғдҪң家зҪ‘зӯүзҪ‘з«ҷд»Ҙдё“йЎөеҪўејҸжҺЁиҚҗз»ҷдәҶиҜ»иҖ…пјҒ
гҖҖгҖҖ
гҖҖгҖҖзҙўжңЁдёңпјҡдҪңдёәдёҖдёӘеңЁиҜ—жӯҢд№Ӣи·ҜдёҠзҡ„и·өиЎҢиҖ…пјҢжҲ‘ж·ұж·ұзҹҘйҒ“пјҢдёҖдёӘиҜ—дәәпјҢиғҪеҪўжҲҗиҮӘе·ұзӢ¬зү№зҡ„йЈҺж јпјҢжҳҜдҪ•е…¶дёҚжҳ“пјҒиҖҢдҪ еҒҡеҲ°дәҶпјҒеҚҒе…«е№ҙжқҘпјҢдҪ зҡ„жҜҸдёҖиЎҢж–Үеӯ—пјҢйғҪж·ұж·ұең°жү“дёҠдәҶдёҖдёӘзғҷеҚ°вҖ”вҖ”вҖңжүҺиҘҝжүҚи®©вҖқпјҒд»ҠеӨ©пјҢдҪ дёәиҜ—жӯҢе’ҢиҜ—дәәпјҢжңҖжғіиҜҙзӮ№д»Җд№Ҳпјҹ
гҖҖгҖҖжүҺиҘҝжүҚи®©пјҡжғіиҜҙзҡ„еҫҲеӨҡгҖӮдё»иҰҒиҜҙдёӨзӮ№пјҡ
гҖҖгҖҖ第дёҖпјҢиҜ—йЈҺзҡ„еҪўжҲҗе§Ӣз»ҲжңүдёҖдёӘжЁЎд»ҝвҖ”вҖ”еҖҹйүҙвҖ”вҖ”еҗёж”¶вҖ”вҖ”еҲӣж–°вҖ”вҖ”иҝ”жңҙеҪ’зңҹзҡ„иҝҮзЁӢгҖӮиҝҷе…¶е®һжҳҜиҜ—жӯҢеҶҷдҪңзҡ„дә”дёӘйҳ¶ж®өпјҢиҖҢиҝҷдә”дёӘйҳ¶ж®өпјҢжҜҸдёҖйҳ¶ж®өиҝҳеҸҜд»Ҙз»ҶеҲҶпјҢеҸҜд»ҘеҲ’еұӮгҖӮиҝҷдјјд№ҺжҳҜеәҹиҜқпјҢдҪҶеҚҒеҲҶйҮҚиҰҒпјҒжҜҸдёӘеҶҷдҪңиҖ…пјҢйғҪе°ҶжҲ–еӨҡжҲ–е°‘ең°жңүжүҖдҪ“йӘҢгҖӮеӣ жӯӨжҲ‘们иҰҒжё…йҶ’ең°и®ӨиҜҶеҲ°иҮӘе·ұжүҖеӨ„зҡ„дҪҚзҪ®пјҢдёҚиғҪеҰ„иҮӘе°ҠеӨ§пјҢзӣ®дёӯж— дәәпјҢеҗҰеҲҷдјҡи·Ңи·ҹеӨҙпјҢдјҡеҸ—дјӨпјҢдјҡиө°зҒ«е…Ҙйӯ”гҖӮзңӢйҮ‘еәёзҡ„жӯҰдҫ е°ҸиҜҙпјҢдәҶи§Јжңүеү‘дёҺж— еү‘пјҢжңүжӢӣдёҺж— жӢӣпјҢе…ҘйҒ“дёҺеҮәйҒ“пјҢе°ұиғҪжҳҺзҷҪиҝҷдёӘйҒ“зҗҶгҖӮзӣ®еүҚжҲ‘жүҖеҲ°иҫҫзҡ„йҳ¶ж®өпјҢд»…д»…жҳҜеҲҡеҲҡи·Ёе…ҘеҲӣж–°йҳ¶ж®өзҡ„й—Ёж§ӣпјҢжүӢдёӯжҸЎдёҖжҠҠе№іеёёд№Ӣеү‘пјҢеӯҰзҡ„жҳҜеӨ§еёҲзҡ„жӢӣж•°пјҢиө°зҡ„жҳҜзҫҠиӮ е°ҸйҒ“пјҢиҝҳжІЎжңүиө°еҮәдёҖжқЎеӨ§и·ҜжқҘгҖӮжҲ‘们и—Ҹж—Ҹзҡ„йғЁеҲҶжҲҗеҗҚиҜ—дәәпјҢеҰӮдё№зңҹиҙЎеёғгҖҒз»•йҳ¶е·ҙжЎ‘гҖҒдјҠдё№жүҚи®©гҖҒеҲ—зҫҺе№іжҺӘзӯүпјҢиҝҳжңүз”ҳиӮғзҡ„иҜ—еқӣеӨ§и…•д»¬пјҢеҰӮжқҺиҖҒд№ЎгҖҒдҪ•жқҘгҖҒеӨҸзҫҠд»ҘеҸҠеҗҺжқҘиҖ…еҸӨ马гҖҒе”җж¬ЈгҖҒеЁңеӨңгҖҒйҳҝдҝЎгҖҒзҺӢиӢҘеҶ°гҖҒзүӣеәҶеӣҪзӯүпјҢеӨ§еӨҡд№ҹеӨ„еңЁиҝҷдёӘйҳ¶ж®өпјҢдёҚиҝҮеұӮж¬ЎжҜ”жҲ‘й«ҳеҫ—еӨҡгҖӮеҲ°иҫҫ第дә”йҳ¶ж®өзҡ„иҜ—дәәе°‘д№ӢеҸҲе°‘пјҢеңЁж”ҫзңјеӣҪеҶ…иҜ—еқӣпјҢеҜҘеҜҘж— еҮ гҖӮ
гҖҖгҖҖ第дәҢпјҢжҲ‘们дёҖзӣҙеңЁеӨёеӨ§зҺ°еҪ“д»ЈиҜ—жӯҢзҡ„еҠӣйҮҸпјҢе…¶е®һиҜ—жӯҢзҡ„еҠӣйҮҸжҳҜжңүйҷҗзҡ„гҖӮжҲ‘дёӘдәәи®ӨдёәзҺ°еҪ“д»ЈиҜ—жӯҢзҡ„дҪңз”Ёе’Ңд»·еҖјпјҢжҜ”дёҚдёҠе°ҸиҜҙпјҢжӣҙжҜ”дёҚдёҠеҪұи§ҶдҪңе“ҒгҖӮжңүж—¶дёҠзҪ‘зҺ©жёёжҲҸпјҢеҸ‘зҺ°иҝҷзҪ‘з»ңжёёжҲҸиҰҒжҜ”иҜ—жӯҢеҸҜжҖ•еҫ—еӨҡпјҢејәиӣ®еҫ—еӨҡгҖӮеҰӮжһңзңҹиҰҒжғіиҜ—жӯҢзҡ„еҠӣйҮҸејәеӨ§иө·жқҘпјҢжҲ‘们е°ұеә”иҜҘеҒҡеҘҪдёүдёӘж–№йқўзҡ„е·ҘдҪңпјҢдёҖжҳҜйҖ еҠҝпјҢд»ҘиҜ—дёәеӨ©пјҢд»ҘиҜ—дёә马пјҢд»ҘиҜ—дёәжўҰпјҢе”ҜиҜ—дёәдёҠгҖӮиҝҷдёҖзӮ№пјҢеғҸжӮЁиҝҷж ·зҡ„жҙ»и·ғеңЁзҪ‘з»ңдёҠзҡ„иҜ—дәә们еҒҡеҫ—еҘҪпјҢжҲ‘иҮӘе·ұе§Ӣз»Ҳз»ҷдёҚдёҠеҠІгҖӮдәҢжҳҜдә®зӣёпјҢжңүиҮӘе·ұи§үеҫ—ж»Ўж„Ҹзҡ„дҪңе“ҒпјҢиҰҒеҸҠж—¶зҡ„жҠ•зЁҝпјҢеҸҠж—¶еҸ‘иЎЁпјҢдёҚиҰҒй”ҒеңЁжҠҪеұүйҮҢпјҢжҗҒеңЁз”өи„‘йҮҢпјҢдёҖе№ҙеҚҠиҪҪпјҢдёҚи®©еҮәдё–гҖӮжҲ‘еҚҒеҲҶеҸҚеҜ№е°Ғй—ӯејҸеҶҷдҪңпјҢз»ҷдәәдёҖз§ҚеҚҒе№ҙзЈЁдёҖеү‘зҡ„ж„ҹи§үпјҢзӯүеү‘зЈЁеҘҪдәҶпјҢжҢәиә«иҖҢеҮәжӢ”еү‘еӣӣйЎҫпјҢдәә家已з»ҸдҪҝз”ЁдёҠеҺҹеӯҗеј№дәҶпјҒиҜ—жӯҢдёҚжҳҜеҸӨи‘ЈпјҢдёҚдјҡеӨҡе°‘е№ҙд»ҘеҗҺжӢҝеҮәжқҘиҝҳиғҪеҚ–дёҠеӨ§д»·й’ұпјҢеҖјй’ұзҡ„еҸӘжҳҜе°‘ж•°дәәзҡ„е°‘ж•°зҜҮз« гҖӮжҲ‘们д№ҹдёҚиғҪзӣёдҝЎвҖңжҳҜйҮ‘еӯҗе°ұдјҡеҸ‘е…үвҖқиҝҷеҘ—й¬јиҜқпјҢеӣ дёәйҮ‘еӯҗж··еңЁжіҘжІҷйҮҢпјҢжіҘжІҷдҝұдёӢпјҢйҮ‘еӯҗд№ҹдёӢгҖӮдёүжҳҜжҺҘиҪЁпјҢдёҺж•Јж–ҮжҺҘиҪЁпјҢдёҺе°ҸиҜҙжҺҘиҪЁпјҢдёҺз”өи§ҶжҺҘиҪЁпјҢдёҺеӨ§дәӢжҺҘиҪЁгҖӮеңЁдёҺж•Јж–Үе’Ңе°ҸиҜҙзҡ„жҺҘиҪЁж–№йқўпјҢиҜ—дәәеҮәиә«зҡ„ж•Јж–ҮеӨ§е®¶е‘Ёж¶ӣгҖҒдҪң家йҳҝжқҘгҖҒе°ҸиҜҙ家йҹ©дёңпјҢе·Із»ҸжҲҗдёәжҲ‘们зҡ„жҘ·жЁЎгҖӮдёҺз”өи§Ҷз”өеҪұжҺҘиҪЁж–№йқўпјҢй…Қд№җиҜ—жң—иҜөгҖҒиҜ—жӯҢдҪңе“ҒеҲ¶дҪңгҖҒиҜ—жӯҢиөҸжһҗиҠӮзӣ®гҖҒиҜ—дәәдј и®°зұ»еҪұи§ҶзӯүпјҢе·Із»ҸеҒҡдәҶеӨ§йҮҸзҡ„е°қиҜ•пјҢжҲҗж•Ҳжңүзӣ®е…ұзқ№гҖӮдёҺеӨ§дәӢжҺҘиҪЁж–№йқўпјҢеңЁ2008е№ҙеҚ—ж–№йӣӘзҒҫгҖҒвҖң5В·12вҖқжұ¶е·қеӨ§ең°йңҮгҖҒвҖң4В·14вҖқзҺүж ‘еӨ§ең°йңҮе’ҢвҖң8В·7вҖқиҲҹжӣІжіҘзҹіжөҒзӯүйҮҚеӨ§иҮӘ然зҒҫе®ідёӯпјҢдёәжҢҜе…ҙж°‘ж—ҸзІҫзҘһгҖҒе”ӨйҶ’жҠ—дәүж„ҸиҜҶгҖҒе“ҖжӮјйҒҮйҡҫеҗҢиғһпјҢиҜ—жӯҢдјјд№ҺеҸ‘жҢҘеҮәдәҶе®ғзҡ„зңҹжӯЈзҡ„дҪңз”ЁеҸҠж„Ҹд№үгҖӮ
гҖҖгҖҖ
гҖҖгҖҖзҙўжңЁдёңпјҡдҪңдёәеӣҫеҚҡзү№е„ҝеҘіпјҢжҲ‘们зҡ„иЎҖж¶ІдёӯпјҢеӨ©з”ҹжөҒж·ҢзқҖз”ҹд№ӢдәҺж–Ҝзҡ„иҜ—ж„Ҹйҹіз¬ҰпјҒеҲӣдҪңеҚҒе…«е№ҙпјҢдҪ и§үеҫ—жҜҚж—Ҹж–ҮеҢ–е’Ңж•…д№ЎзғӯеңҹпјҢз»ҷдҪ жңҖеӨҡзҡ„жҳҜд»Җд№Ҳпјҹ
гҖҖгҖҖжүҺиҘҝжүҚи®©пјҡжҲ‘еңЁгҖҠдёғжүҮй—ЁгҖӢвҖң第дёҖжүҮй—Ёй—ЁеүҚжҸҗзӨәвҖқдёӯеҶҷиҝҮиҝҷж ·дёҖж®өиҜқпјҡвҖңжқҺеҹҺе…Ҳз”ҹеңЁе…¶иҮӘдј дҪ“ж•Јж–ҮгҖҠж°ёз”ҹдёҺдҪ зӣёдјҙиҖҢиЎҢгҖӢдёӯиҝҷж ·дәӨд»ЈиҮӘе·ұзҡ„ж°‘ж—ҸеҮәиә«пјҡвҖҳжҲ‘зҡ„зҲ¶зі»жҳҜжҳҺ代移民иҖҢжқҘзҡ„жұүж—ҸпјҢиҖҢжҜҚзі»жҳҜеҪ“ең°еңҹи‘—и—Ҹж°‘гҖӮиҜҙжҲ‘зҡ„жҜҚзі»дёәи—Ҹж—ҸпјҢд№ҹеҸӘжҳҜеӨ§жҰӮзҡ„еҪ’зұ»иҖҢе·ІпјҢиӢҘиҰҒеҜ»ж №жәҜжәҗпјҢеҲҷйңҖеӣһеҲ°е…¬е…ғе…«дё–зәӘпјҢйӮЈж—¶еҘ№зҡ„ж—Ҹдәәд№ҹи®ёз§°дёәе…ҡйЎ№жӢ“жӢ”пјҢжҳҜз”ҹжҙ»дәҺйқ’и—Ҹй«ҳеҺҹдёңйғЁпјҢиҮӘе·ұ并没жңүд»Җд№Ҳж°‘ж—ҸеҪ’еұһж„ҸиҜҶзҡ„зү§дәәгҖӮвҖҷеңЁз”ҳеҚ—пјҢеғҸиҝҷж ·зҡ„еңЁж°‘ж—ҸеӨ§иһҚеҗҲйҮҢиҜһз”ҹзҡ„жңүзқҖж–°йІңиЎҖж¶Ізҡ„дәәеӯҗпјҢжҳҜж•°дёҚиғңж•°зҡ„пјҢ他们жҲ–йўҶзқҖжұүж—Ҹиә«д»ҪпјҢжҲ–йўҶзқҖи—Ҹж—Ҹиә«д»ҪпјҢжҲ–йўҶзқҖеңҹж—ҸгҖҒеӣһж—Ҹе’Ңи’ҷеҸӨж—Ҹиә«д»ҪпјҢжІүйқҷиҖҢеқҡйҹ§ең°з”ҹжҒҜеңЁе®үеә·еӨ§ең°дёҠгҖӮвҖқ
гҖҖгҖҖжҲ‘е’ҢжҲ‘зҡ„е…„ејҹе§җеҰ№пјҢдёҺжқҺеҹҺ他们жңүзқҖзұ»дјјзҡ„ж°‘ж—Ҹиә«д»ҪпјҢжҚўеҸҘиҜқиҜҙпјҢжҲ‘们зҡ„иә«дҪ“йҮҢд№ҹжҒ’д№…ең°жөҒеҠЁзқҖи—ҸжұүдёӨиӮЎиЎҖж¶ІгҖӮиҝҷз§ҚеӨҡж°‘ж—ҸиЎҖж¶ІеңЁдёӘдҪ“иә«дёҠзҡ„жӮ„然жұҮйӣҶпјҢдҪҝеҫ—жҲ‘们既йӘ„еӮІпјҢеҸҲж— еҘҲпјҢж— жі•йҖғи„ұе‘Ҫиҝҗзҡ„дё»е®°пјҢжҲҗдёәжёёзҰ»еңЁеҮҶж°‘ж—Ҹд№ӢеӨ–зҡ„еҗҚеүҜе…¶е®һзҡ„иҫ№зјҳдәәгҖӮеҪ“然пјҢжҳҜеҗҰжңүеҮҶж°‘ж—ҸпјҢиҝҷиҝҳжҳҜдёҖдёӘйңҖиҰҒиҖғиҜҒе’Ңе•ҶжҰ·зҡ„й—®йўҳгҖӮ
гҖҖгҖҖ и‘—еҗҚи—Ҹж—ҸиҜ—дәәгҖҒеӯҰиҖ…гҖҒзӨҫдјҡжҙ»еҠЁе®¶жүҚж—әз‘ҷд№іе…Ҳз”ҹеңЁгҖҠи—Ҹж—ҸеҪ“д»ЈиҜ—дәәиҜ—йҖүгҖӢпјҲжұүж–ҮеҚ·пјүеүҚиЁҖдёӯеҰӮжҳҜиҜҙпјҡвҖң(жҲ‘们)жј«жӯҘеңЁеҸӨиҖҒзҡ„еӨ§ең°дёҠпјҢж•Ҹж„ҹең°дјёзј©зқҖиүәжңҜи§Ұи§’пјҢдҪ“е‘ізқҖжёҗжҳҫеҶ°еҮүзҡ„дәәжғ…пјҢж„ҹжӮҹзқҖеӨҡдҪҷдәәгҖҒеұҖеӨ–дәәгҖҒиў«ејӮеҢ–иҖ…зҡ„еҜӮеҜһе’ҢеӯӨзӢ¬пјҢиҝӣиҖҢй©ұзӯ–иҮӘе·ұжҲҗдёәеҝғзҒөж”ҫйҖҗзҡ„жөҒжөӘиҖ…гҖӮвҖқзңҹжҳҜиҝҷз§ҚеҝғзҒөжөҒжөӘиҖ…зҡ„иә«д»ҪпјҢдҪҝжҲ‘жҲҗдёәдёҖдёӘжүҖи°“зҡ„иҜ—дәәгҖӮеҚҒе…«е№ҙжқҘпјҢз”ҹжҙ»еңЁз”ҳеҚ—иҝҷеқ—ж·ұжғ…зҡ„еңҹең°дёҠпјҢжҲ‘з”ЁиҮӘе·ұзҡ„ж–№ејҸеҗҹе”ұзқҖдёҖдёӘиҫ№зјҳдәәзҡ„ж°‘ж—Ҹи®ӨеҗҢд№ӢжӯҢпјҢиЎҖзјҳеҪ’еұһд№ӢжӯҢпјҢиҝҷдәӣжӯҢеЈ°жңүзқҖеҸ‘иҮӘеҶ…еҝғзҡ„еӯӨзӢ¬е’ҢеҜӮеҜһгҖӮ

гҖҖгҖҖ
гҖҖгҖҖзҙўжңЁдёңпјҡиҜ—жӯҢдәҺжҲ‘пјҢиҮӘд»ҘдёәжҳҜдёҖдёӘиҒҠд»ҘиҮӘж…°зҡ„и§Ји„ұд№Ӣй—ЁвҖ”вҖ”ж— йқһжҳҜеңЁе№іеәёзҡ„з”ҹжҙ»дёӯз»ҷиҮӘе·ұдёҖдёӘдёҚе№іеәёжҙ»зқҖзҡ„еҖҹеҸЈе’ҢзҗҶз”ұпјҒйӮЈд№ҲпјҢдҪ иғҪи°Ҳи°ҲиҜ—жӯҢдәҺдҪ жҳҜдёҖдёӘд»Җд№Ҳж ·зҡ„зҠ¶жҖҒеҗ—пјҹ
гҖҖгҖҖжүҺиҘҝжүҚи®©пјҡиҝҷдёӘзңҹдёҚеҘҪиҜҙпјҢжҲ‘дёҚжӣҫз»Ҷз»ҶжғіиҝҮгҖӮзҺ°еңЁпјҢ既然жӮЁй—®еҲ°иҝҷдёӘй—®йўҳпјҢжҲ‘жғід»ҺдёӨж–№йқўжқҘи°ҲгҖӮ
гҖҖгҖҖйҰ–е…ҲпјҢжҲ‘е…ҲиҜҙиҜҙиҜ—жӯҢиҝҷз§Қж–ҮдҪ“еҜ№жҲ‘з”ҹеӯҳзҠ¶жҖҒзҡ„еҪұе“ҚгҖӮеҸҜд»Ҙиҝҷд№ҲиҜҙпјҢеңЁйқ’жҳҘжңҹпјҢзғӯзҲұиҜ—жӯҢе°ұеғҸзғӯзҲұеҘіеӯ©дёҖж ·иҮӘ然пјҢйӮЈз§ҚзғӯзҲұе’Ңз—ҙиҝ·д»ҝдҪӣжҳҜи—ҸеңЁиЎҖж¶ІйҮҢзҡ„пјҢдёҖе‘је–Ҡе°ұеҮәжқҘдәҶпјҢе°ұеғҸйҳҝжқҘиҜҙзҡ„пјҡвҖңд»ҺйӘЁеӨҙйҮҢеҶ’жіЎжіЎе„ҝпјҒвҖқйӮЈж—¶еҖҷзңҹе–ңж¬ўжҠ’жғ…пјҢжғіе”ұпјҢжғіи·іпјҢжғіеңЁиҚүеҺҹдёҠзӢӮеҘ”пјҢжғіз”Ёж–Үеӯ—и®°дёӢиҮӘе·ұзҡ„йҡҗз§ҳзҡ„жҖқжғігҖӮд№ӢжүҖд»ҘйҖүжӢ©иҜ—жӯҢеҶҷдҪңпјҢжІЎжңүеӨӘеӨҡзҡ„зҗҶз”ұпјҢеҸӘжҳҜдёҖз§ҚжғіиЎЁиҫҫзҡ„еҶІеҠЁгҖӮеҗҺжқҘеҸ‘иЎЁдәҶпјҢ收еҲ°иҜ»иҖ…жқҘдҝЎдәҶпјҢејҖе§ӢеҸӮеҠ 笔дјҡдәҶпјҢиҝҷдёҖеҲҮеҸҳеҢ–йғҪи®©жҲ‘и§үеҫ—ж¬Је–ңпјҢйӮЈеҠІеӨҙе°ұжӣҙи¶ідәҶгҖӮе…¶е®һиҝҷе°ұжҳҜдёҖз§ҚиЎЁжү¬пјҢдёҖз§ҚиӮҜе®ҡпјҢдёҖз§Қйј“еҠұпјҢдёҖз§Қж–№еҗ‘зҡ„жҢҮеј•гҖӮеҜ№дәҺдёҖдёӘзғӯиЎҖйқ’е№ҙжқҘиҜҙпјҢжҲ‘еӨӘйңҖиҰҒиҝҷз§ҚеҸҰдёҖз§ҚеҪўејҸзҡ„жҺҢеЈ°дәҶпјҒд»ҘиҮідәҺиҜ—жӯҢеҶҷдҪңеҪұе“ҚдәҶжҲ‘зҡ„еӨ„дәӢж–№ејҸгҖҒз”ҹжҙ»иҝҪжұӮе’Ңе“ІеӯҰжҖқиҫЁпјҢдҪҝжҲ‘ж„ҹзҹҘдәҶзңҹжғ…зҡ„еҸҜиҙөпјҢзңҹзҲұзҡ„е”ҜзҫҺпјҢзңҹеҝөзҡ„иҝ·йҶүпјҢжҲ‘еқҡдҝЎпјҡжҙ»зқҖиҷҪ然иү°иҫӣпјҢдҪҶз”ҹжҙ»жң¬иә«зЎ®е®һе……ж»ЎзқҖиҝ·дәәзҡ„иүІеҪ©пјҒ
гҖҖгҖҖе…¶ж¬ЎпјҢиҜ—жӯҢеҶҷдҪңиҝҮзЁӢпјҢз»ҷжҲ‘зҡ„ж„ҹи§үпјҢе°ұжҳҜдёҖдёӘжҖқжғіжҲҗзҶҹзҡ„иҝҮзЁӢпјҢи§ӮеҝөеҸҳеҢ–зҡ„иҝҮзЁӢпјҢз”ҹе‘Ҫе®Ңе–„зҡ„иҝҮзЁӢгҖӮжҲ‘жӣҫз»ҸеҶҷиҝҮиҝҷж ·дёҖйҰ–иҜ—пјҡвҖңе“ҰвҖ”вҖ”еҶҚд№ҹдёҚиғҪиҜҙеҮә/е°‘еҘіеҰӮиҠұпјҢе°‘еҰҮдјјжһңпјҢиҖҒеҰҮд»ҝдҪӣйЈҺдёӯиҙҘзө®/еҶҚд№ҹдёҚиғҪиҜҙеҮә/зҲұиҝҮпјҢжҒЁиҝҮпјҢз”ҹж®–иҝҮпјҢжҲ‘е·Іе®Ңе–„дәҶжҲ‘иҮӘе·ұ/ жҲ‘зҡ„ж№®жІЎжӮ„ж— еЈ°жҒҜвҖқгҖӮиҝҷз§Қи®ӨиҜҶпјҢиҝҷз§Қжғ…ж„ҹпјҢе°ұжҳҜеҖҹиҜ—жӯҢеҶҷдҪңжқҘеҜ№иҮӘиә«з”ҹжҙ»зҡ„иҝӣиЎҢжҖ»з»“пјҢеҜ№дёӘдәәжғ…ж„ҹиҝӣиЎҢж•ҙзҗҶпјҢеҜ№дёӘдҪ“з”ҹе‘Ҫзҡ„иҝӣиЎҢи®ӨзҹҘгҖӮеңЁгҖҠдёҖеӨ©гҖӢдёӯпјҢжҲ‘иҝҷж ·еҶҷйҒ“пјҡвҖңиҖҢд»ҠеҸӘиғҪдёҖзқ№йҶүй…’иҖ…еңЁйҳҙжҡ—и§’иҗҪйҮҢз•ҷдёӢжұЎзү©пјҢжҲ–иҖ…зһҘи§ҒеҘідәәжқҫжқҫеһ®еһ®зҡ„иҮҖйғЁпјҢе’Ңе©ҙеӯ©з»қжңӣзҡ„зҘһиүІгҖӮеҸҜжҳҜпјҢеҪ“зңҹжӯЈзҡ„ж—¶еҲ»еҲ°жқҘпјҢз–ҜзӢӮзҡ„иҖҒдәәе°Ҷи¶Ӣеҗ‘е№ійқҷпјҢе •иҗҪзҡ„е°‘е№ҙе°ҶиҜ•еӣҫж–°з”ҹгҖӮйӮЈдәӣе…ҲзҹҘ们记иҪҪдёӢжқҘзҡ„з–ҫз—…дёҺеҒҘеә·пјҢз”ҹдёҺжӯ»пјҢйғҪе°ҶжҳҜиӮүдҪ“иҝӣиЎҢзҡ„йқ©е‘ҪгҖӮеӣ жӯӨпјҢиҜ·еҜ№йқҷеҖҷеңЁз—…еәҠиҫ№зҡ„й»‘иЎЈдҫҚиҖ…еҰӮжӯӨе‘је–ҠпјҡжҲ‘иҰҒзңӢйӮЈеӨ§е…үжҳҺпјҒжҲ‘иҰҒзңӢйӮЈз”ҹе‘Ҫдёӯзҡ„иҪ»дёҺйҮҚпјҢзҡҶеҪ’дәҺж»”ж»”жұҹж°ҙпјҒвҖқжӮЁзңӢпјҢиҜҙзҷҪдәҶпјҢжҲ‘зҡ„иҜ—жӯҢеҶҷдҪңжң¬иә«пјҢе…¶е®һе°ұжҳҜе®Ңе–„иҮӘжҲ‘зҡ„иҝҮзЁӢгҖӮ
гҖҖгҖҖ
гҖҖгҖҖзҙўжңЁдёңпјҡиҝҷдәӣе№ҙжқҘпјҢеңЁејӮд№ЎжјӮжіҠзҡ„еҚҒе…ӯе№ҙйҮҢпјҢжҲ‘ж—¶еёёж„ҹеҲ°дёҖз§Қйҡ”зҰ»е’Ңж–ӯеҘ¶еҗҺзҡ„ж— жүҖйҖӮд»ҺпјҒиҝҷдәӣеӣ°йЎҝе’Ңж— еҘҲпјҢдҪҝиҮӘе·ұзҡ„еҲӣдҪңйҷ·е…ҘдәҶдёҖдёӘеғөеұҖпјҒдҪ еңЁд»–д№ЎжұӮеӯҰ4е№ҙеҗҺйҮҚж–°еӣһеҲ°з”ҳеҚ—пјҢеңЁеҲӣдҪңдёҠпјҢдҪ жңүиҝҮжҖҺж ·зҡ„еӣ°йЎҝе’Ңж— еҘҲпјҹ
гҖҖгҖҖжүҺиҘҝжүҚи®©пјҡжӮЁиҜҙзҡ„вҖңдёҖз§Қйҡ”зҰ»е’Ңж–ӯеҘ¶еҗҺзҡ„ж— жүҖйҖӮд»ҺвҖқзҡ„ж„ҹи§үпјҢжҲ‘д№ҹж·ұжңүж„ҹи§ҰгҖӮжҲ‘дёӘдәәи®Өдёәдё»иҰҒеҺҹеӣ еңЁдәҺпјҡжҲ‘们еҜ№жҲ‘еүҚиҫ№жүҖжҸҗеҲ°зҡ„дёҺеҶҷдҪңиҖ…зӣёе…ізҡ„дёүдёӘй—®йўҳпјҢиҝҳжҳҜзјәе°‘ж·ұе…ҘиҖҢеҶ·йқҷзҡ„жҖқиҖғпјҢжүҖд»Ҙдјҡдә§з”ҹеӣ°йЎҝе’Ңж— еҘҲпјҢдҪҝиҮӘе·ұзҡ„еҲӣдҪңйҷ·е…ҘдәҶеғөеұҖпјҒдҪҶиғҪиӮҜе®ҡзҡ„жҳҜпјҢдҪ жҲ‘йғҪжҳҜз”ҳиӮғ70еҗҺиҜ—дәәпјҢеңЁиҝҷдёӘдјјжҳҜиҖҢйқһзҡ„з•Ңе®ҡдёӯпјҢжҲ‘们еҒҡзҡ„иҝҳжңүжңүдёҖдәӣж„Ҹд№үзҡ„пјҢе°Өе…¶жҳҜдҪ гҖҒйғӯжҷ“зҗҰгҖҒжқҺж»ЎејәгҖҒжј йЈҺе’ҢзҺӢејәзӯүдәәпјҢеҗ„иҮӘеңЁдёҚеҗҢзҡ„ж–ҮеҢ–йўҶеҹҹе®һзҺ°зқҖиҮӘе·ұзҡ„дәәз”ҹд»·еҖјгҖӮе°ұжӢҝжӮЁжқҘиҜҙеҗ§пјҢдҪңдёәи—Ҹдәәж–ҮеҢ–зҪ‘ж–ҮеӯҰйў‘йҒ“зҡ„дё»зј–пјҢдҪ еҜ№и—Ҹж—Ҹж–ҮеӯҰзҡ„е®һи·өгҖҒе®Јдј е’ҢжҖ»з»“жңүзӣ®е…ұзқ№пјҢеҜ№и—Ҹж—ҸдҪң家е’ҢиҜ—дәәзҡ„еҸ‘жҺҳгҖҒжўізҗҶгҖҒжҺЁеҮәе’ҢеҪ’зәіеҒҡеҮәдәҶдёӘдәәзҡ„еҠӘеҠӣпјҢеҸ–еҫ—дәҶдёҖе®ҡзҡ„жҲҗж•ҲгҖӮзҺ°еңЁжғіиө·иҝҷдәӣпјҢзңҹжҳҜж„ҹж…ЁдёҮеҚғпјҒ
гҖҖгҖҖжұӮеӯҰеӣӣе№ҙд№ӢеҗҺжҲ‘йҮҚиҝ”з”ҳеҚ—пјҢжҳҜеӣ дёәж•…еңҹжғ…з»“гҖҒж°‘ж—Ҹжғ…з»“е’ҢдәІжғ…жғ…з»“жүҖиҮҙгҖӮеҪ“然пјҢйӮЈж—¶еҖҷпјҢд№ҹе°ұжҳҜеҚҒе…ӯе№ҙеүҚпјҢдәәжүҚзҡ„жөҒеҠЁиҝҳжІЎжңүзҺ°еңЁиҝҷд№ҲиҮӘз”ұиҖҢйў‘з№ҒгҖӮеӣһеҲ°ж•…еңҹпјҢеҸҜиғҪжҳҜжңҖеҘҪзҡ„йҖүжӢ©гҖӮеҚҒе…ӯе№ҙжқҘпјҢеңЁе№ІеҘҪжң¬иҒҢе·ҘдҪңзҡ„еҗҢж—¶пјҢжҲ‘дҫқ然ж·ұзҲұзқҖиҜ—жӯҢеҲӣдҪңпјҢжҠҠе®ғеҪ“еҒҡдёҖ件иҰҒдәӢжқҘеҒҡпјҢеҗҢж—¶д№ҹе…јйЎҫж–ҮеӯҰиҜ„и®әе’Ңе°ҸиҜҙеҲӣдҪңгҖӮж–ҮеӯҰиҜ„и®әзҡ„еҜ№иұЎпјҢдё»иҰҒй’ҲеҜ№з”ҳеҚ—зҡ„дҪң家е’ҢиҜ—дәәпјҢдҪңе“Ғж•Ји§ҒдәҺгҖҠз”ҳеҚ—ж—ҘжҠҘгҖӢгҖҒгҖҠз”ҳеҚ—з”өи§ҶжҠҘгҖӢгҖҒгҖҠе…°е·һж–ҮиӢ‘гҖӢе’ҢгҖҠиҜ—еҲҠгҖӢзӯүжҠҘеҲҠгҖӮе°ҸиҜҙдё»иҰҒеҸ‘иЎЁеңЁгҖҠиҘҝи—Ҹж–ҮеӯҰгҖӢе’ҢгҖҠж јжЎ‘иҠұгҖӢдёҠпјҢйғҪжҳҜзҹӯзҜҮпјҢе°Ҹжү“е°Ҹй—№ејҸзҡ„гҖӮдё»иҰҒзІҫеҠӣиҝҳжҳҜж”ҫеңЁиҜ—жӯҢеҶҷдҪңдёҠпјҢдҪҶжҖ»жҳҜж—¶ж–ӯж—¶з»ӯпјҢеҒңеҒңиө°иө°пјҢжІЎжңүиҝһз»ӯжҖ§пјҢзјәд№ҸеӢҮеҫҖзӣҙеүҚз ҙйҮңжІүиҲҹзҡ„йӯ„еҠӣгҖӮеҺҹеӣ еҳӣпјҢжҲ‘дёӘдәәи®Өдёәдё»иҰҒеңЁдәҺдёӨж–№йқўгҖӮдёҖжҳҜжҲ‘дёӘдәәзҡ„жҖ§ж јжҜ”иҫғж•Јжј«пјҢжңүзҗҶжғіпјҢе°‘и®ЎеҲ’пјҢзјәжҜ…еҠӣпјҢд№ҸжҒ’еҝғгҖӮдәҢжҳҜжҲ‘ж— жі•жңүж•Ҳең°еӨ„зҗҶеҶҷдҪңе’Ңе·ҘдҪңд№Ӣй—ҙзҡ„е…ізі»гҖӮеңЁжҲ‘зңӢжқҘпјҢеҶҷдҪңе’Ңе·ҘдҪңдјјд№ҺжңүзқҖдёҚеҸҜи°ғе’Ңзҡ„зҹӣзӣҫпјҢиҝҷзҹӣзӣҫзҡ„еӯҳеңЁпјҢд№ҹи®ёжҳҜеӣ дёәж—¶й—ҙе®үжҺ’зҡ„дёҚеҰҘеҪ“пјҢд№ҹи®ёжҳҜеӣ дёәеҚ•дҪҚйўҶеҜјзңӢеҫ…еҶҷдҪңиҖ…зҡ„жҖҒеәҰпјҢд№ҹи®ёжҳҜеӣ дёәдёӘдәәеҶ…еҝғзҡ„еҶІзӘҒпјҢеҸҚжӯЈеҗ„з§ҚеҺҹеӣ йғҪжңүгҖӮе·ҘдҪңеҚҒе…ӯе№ҙжқҘпјҢдә”еҲҶд№Ӣдёүзҡ„ж—¶й—ҙж®өд»ҺдәӢзҡ„дёҖзӣҙжҳҜж•ҷиӮІж•ҷеӯҰпјҢд»ЈиҜҫеӨҡпјҢдҪңдёҡеӨҡпјҢиӮ©дёҠеҸҲеҺӢзқҖзҸӯдё»д»»зҡ„йҮҚжӢ…пјҢиө·еҫ—жҜ”е…¬йёЎж—©пјҢзқЎеҫ—жҜ”зҡ„е“ҘжҷҡгҖӮжңүж—¶еҖҷзңӢдҪң家зҡ„дј и®°пјҢеҸ‘зҺ°еҘҪеӨҡдҪң家йғҪжҳҜиҪ»е·ҘдҪңйҮҚеҲӣдҪңзҡ„пјҢеҗғжғҠд№ӢдҪҷпјҢж јеӨ–иүізҫЎгҖӮеҶҚд»”з»ҶжӢңиҜ»пјҢеҸ‘зҺ°дј и®°дҪңиҖ…жҖ»е–ңж¬ўе°Ҷи®°еҸҷзҡ„йҮҚзӮ№е§Ӣз»Ҳж”ҫеңЁдҪң家зҡ„жғ…ж„ҹз”ҹжҙ»е’ҢеҶҷдҪңз”ҹж¶ҜдёҠпјҢиҖҢеҜ№дҪң家жүҖд»ҺдәӢзҡ„е·ҘдҪңпјҢд№ҹжҳҜиҚүиҚүеҮ 笔пјҢеҸӘиҜҙжҳҺиҮӘе…¶дҪ•е№ҙдҪ•жңҲиҮідҪ•е№ҙдҪ•жңҲеңЁдҪ•еҚ•дҪҚе№ІиҝҮпјҢеҚҙеҫҲе°‘еҶҷеҲ°е…·дҪ“е№Ід»Җд№Ҳе·ҘдҪңгҖӮиҝҷе°ұи®©жҲ‘зӘҒ然жҳҺзҷҪдәҶдёҖдёӘйҒ“зҗҶпјҡдҪңдёәдҪң家иҜ—дәәиә«д»Ҫзҡ„дәәпјҢд»–пјҲеҘ№пјүзҡ„дәәз”ҹж Үеҝ—пјҢдёҚжҳҜд»–пјҲеҘ№пјүжүҖд»ҺдәӢзҡ„жҹҗдёҖйЎ№дёҺеҶҷдҪңж— е…ізҡ„е·ҘдҪңпјҢиҖҢжҳҜдҪң家пјҲиҜ—дәәпјүжң¬дәәзІҫзҘһйЈҺиҢғе’ҢдҪңе“Ғжң¬иә«пјҢжҲ‘з§°д№ӢдёәвҖңдәҢжң¬дё»д№үвҖқгҖӮжҲ‘еҫҲжғіжӢҘжңүеұһдәҺиҮӘе·ұзҡ„вҖңдәҢжң¬дё»д№үвҖқпјҢз»ҸиҝҮеӨҡз§ҚеҠӘеҠӣпјҢжҜ”еҰӮйҮҚжӢ©еІ—дҪҚпјҢжҚўдёӘзҺҜеўғпјҢеҲ°ж–ҮеҢ–йғЁй—Ёд»Җд№Ҳзҡ„пјҢи°ӢдёӘй—Іе·®пјҢиөўеҫ—й—Іж—¶пјҢд»Ҙдҫҝд»ҺдәӢеҶҷдҪңпјҢеҚҙжңӘиғҪеҰӮж„ҝпјҒд»ҘдёҠжүҖи°Ҳзҡ„дёӨеӨ§ж–№йқўжҲҗдёәжҲ‘еҲӣдҪңдёӯйҒҮеҲ°зҡ„жңҖеӨ§зҡ„еӣ°йЎҝе’Ңж— еҘҲпјҢиҮід»Ҡж— жі•жңүж•Ҳең°еҫ—д»Ҙи§ЈеҶігҖӮ
гҖҖгҖҖ
гҖҖгҖҖзҙўжңЁдёңпјҡжҲ‘жғіжҠҠиҜқйўҳжүҜиҝңдёҖзӮ№пјҒеҜ№дәҺеҪ“дёӢзҡ„и—Ҹж—Ҹж–ҮеӯҰпјҢдҪ и®ӨдёәжҳҜдёҖдёӘд»Җд№ҲжҖҒеҠҝпјҹ
гҖҖгҖҖжүҺиҘҝжүҚи®©пјҡеҜ№дәҺеҪ“дёӢзҡ„и—Ҹж—Ҹж–ҮеӯҰеҲӣдҪңпјҢжҲ‘иҝҳжҳҜжҜ”иҫғд№җи§Ӯзҡ„гҖӮиҖҒдҪң家们已еҘ е®ҡдәҶеҹәзЎҖпјҢйғЁеҲҶдёӯе№ҙдҪң家еҲӣдҪңеҠҝеӨҙеҰӮж—ҘдёӯеӨ©пјҢиҖҢйқ’е№ҙж–°й”җеҸҲеұӮеҮәдёҚз©·гҖӮиҝҷйғҪжҳҜдёҚеҸҜеҗҰи®Өзҡ„дәӢе®һпјҢдҪҶз§°дёәеӨ§еёҲзҡ„иҝҳжҳҜдёҚеӨӘеӨҡпјҒж јиҗЁе°”зҺӢзҡ„дј е”ұиҖ…们жҳҜеӨ§еёҲпјҢеҶҷгҖҠзұіжӢүж—Ҙе·ҙйҒ“жӯҢйӣҶгҖӢгҖҒгҖҠиҗЁиҝҰж јиЁҖгҖӢгҖҒгҖҠж°ҙж ‘ж јиЁҖгҖӢгҖҒгҖҠж јдё№ж јиЁҖгҖӢгҖҒгҖҠз”ҳдё№ж јиЁҖгҖӢгҖҒгҖҠеӨ©з©әж јиЁҖгҖӢе’ҢгҖҠзҒ«зҡ„ж јиЁҖгҖӢзҡ„жҳҜеӨ§еёҲпјҢиҮҙеҠӣдәҺдҪӣеӯҰз ”з©¶е’Ңдј ж’ӯзҡ„д»ҒжіўеҲҮ们жҳҜеӨ§еёҲпјҢдҪҶиҝҷдәӣйғҪжҳҜеңЁеӨ§ж–ҮеҢ–жҰӮеҝөе’ҢеӨ§е®—ж•ҷйўҶеҹҹдёӯзҡ„дҪјдҪјиҖ…гҖӮеңЁи—Ҹж—Ҹж–ҮеӯҰеҲӣдҪңдёҠпјҢзү№еҲ«жҳҜи—Ҹж—Ҹж–ҮеӯҰжұүиҜӯзұ»ж–Үеӯ—еҲӣдҪңдёҠпјҢдёҡе·ІеҸ–еҫ—жҲҗе°ұзҡ„пјҢеұҲжҢҮз®—жқҘпјҢд№ҹе°ұжҳҜдё№зңҹиҙЎеёғгҖҒйҘ¶йҳ¶е·ҙжЎ‘гҖҒйҳҝжқҘгҖҒжүҺиҘҝиҫҫеЁғгҖҒзӣҠиҘҝеҚ“зҺӣгҖҒе°•и—ҸжүҚж—ҰгҖҒдјҠдё№жүҚи®©гҖҒиҙЎеҚңжүҺиҘҝгҖҒзҷҪеҚҺиӢұгҖҒз«ҜжҷәеҳүгҖҒе”ҜиүІгҖҒиүІжіўгҖҒе®ҢзҺӣеӨ®йҮ‘гҖҒеҲ—зҫҺе№іжҺӘгҖҒзҷҪ马еЁңзҸҚгҖҒжүҚж—әз‘ҷд№ігҖҒж—әз§ҖжүҚдё№гҖҒж¬Ўд»ҒзҪ—еёғгҖҒжў…еҚ“гҖҒж јеӨ®гҖҒеӨ®зҸҚзӯүдҪң家е’ҢиҜ—дәәгҖӮиҝҷйҮҢиҫ№пјҢйҳҝжқҘгҖҒзҷҪеҚҺиӢұгҖҒе”ҜиүІгҖҒж¬Ўд»ҒзҪ—еёғ他们еҶҷеҮәдәҶиҫғдёәз»Ҹе…ёзҡ„дҪңе“ҒпјҢиҖҢжүҺиҘҝиҫҫз“ҰгҖҒиүІжіўгҖҒдјҠдё№жүҚи®©е’Ңе°•и—ҸжүҚж—ҰпјҢж–Үжң¬жҺўзҙўзҡ„ж„Ҹд№үеӨ§дәҺдҪңе“ҒиЎЁзҺ°зҡ„еҶ…е®№гҖӮеҪ“然пјҢеңЁиүҜеҘҪзҡ„зҺҜеўғдёӯпјҢжҲ‘们иҝҳжңүе…¶д»–ж ‘жңЁеңЁжҲҗй•ҝзқҖпјҢ并且жңүзқҖжҲҗдёәеӨ§ж ‘зҡ„еҸҜиғҪжҖ§пјҢдҪ жҜ”еҰӮиҜҙеҳҺд»ЈжүҚи®©гҖҒзҺӢе°Ҹеҝ гҖҒзҙўжңЁдёңгҖҒжүҺиҘҝгҖҒзҺӢеҝ—еӣҪгҖҒжЎ‘дё№гҖҒйҫҷд»Ғйқ’гҖҒдә‘жүҚи®©гҖҒжүҺиҘҝе°јзҺӣгҖҒзҺӢжӣҙзҷ»еҠ зӯүдәәпјҢйғҪжңүзқҖеҫҲејәзҡ„еҸҜеЎ‘жҖ§пјҢе’ҢеҸҜд»Ҙйў„зҹҘзҡ„еҸ‘еұ•еүҚжҷҜгҖӮи—Ҹж–Үеӯ—жҲ‘дёҚзҶҹжӮүпјҢжүҖд»Ҙж— жі•еҜ№д»Ҙи—Ҹж–Үеӯ—иҝӣиЎҢеҲӣдҪңзҡ„дҪң家е’ҢиҜ—дәәеҒҡеҮәиҜ„еҲӨпјҢйҒ“еҗ¬йҖ”иҜҙжқҘзҡ„пјҢдёҚиғҪд»ЈиЎЁжҲ‘зҡ„зңӢжі•гҖӮж— и®әжҖҺд№ҲиҜҙпјҢжҲ‘еҜ№и—Ҹж—Ҹж–ҮеӯҰеҲӣдҪңжҢҒд№җи§ӮжҖҒеәҰпјҢзү№еҲ«еҜ№йҳҝжқҘгҖҒжүҺиҘҝиҫҫеЁғгҖҒе°•и—ҸжүҚж—ҰзӯүдҪң家пјҢжңүзқҖжҷҜд»°д№Ӣжғ…пјҢеӣ дёә他们зҡ„еҲӣдҪңжңүзқҖжҳҺжҳҫзҡ„зӣ®зҡ„жҖ§гҖҒиҙЈд»»ж„ҹе’Ңй•ҝиҝңзҡ„зңје…үпјҢ他们已з»ҸжүҫеҲ°дәҶеұһдәҺиҮӘе·ұзҡ„ж–ҮеӯҰзҹҝи„үгҖӮеҰӮжһңдёҚи°Ҳж”ҝжІ»еӣ зҙ пјҢе”ҜиүІзҡ„ж–ҮеӯҰеҲӣдҪңд№ҹдёҚеҸҜеҝҪи§ҶпјҒжҲ‘еҜ№ж¬Ўд»ҒзҪ—еёғгҖҒзҷҪ马еЁңзҸҚгҖҒж јеӨ®гҖҒеӨ®зҸҚгҖҒеҳҺд»ЈжүҚи®©гҖҒзҺӢе°Ҹеҝ гҖҒзҺӢеҝ—еӣҪзӯүдәәд№ҹжҳҜе……ж»ЎдҝЎеҝғпјҢжҲ‘и®Өдёә他们жҳҜеҪ“д»Ји—Ҹж—Ҹж–ҮеӯҰеҲӣдҪңдёӯдёҚеҸҜдҪҺдј°зҡ„ж–°й”җеҠӣйҮҸгҖӮиҝҷеҮ иӮЎеҠҝеҠӣзҡ„ејӮеҶӣзӘҒиө·пјҢдёҚд»…д»…дјҡдҝғдҪҝеҪ“д»Ји—Ҹж—Ҹж–ҮеӯҰеҲӣдҪңиҝӣе…ҘеҲ°еӨ§з№ҒиҚЈгҖҒеӨ§еҸ‘еұ•зҡ„ж—¶жңҹпјҢжӣҙдјҡеҜ№жҲ‘еӣҪеҪ“д»Јж–ҮеӯҰеҲӣдҪңеёҰжқҘдёҖе®ҡзҡ„еҪұе“ҚгҖ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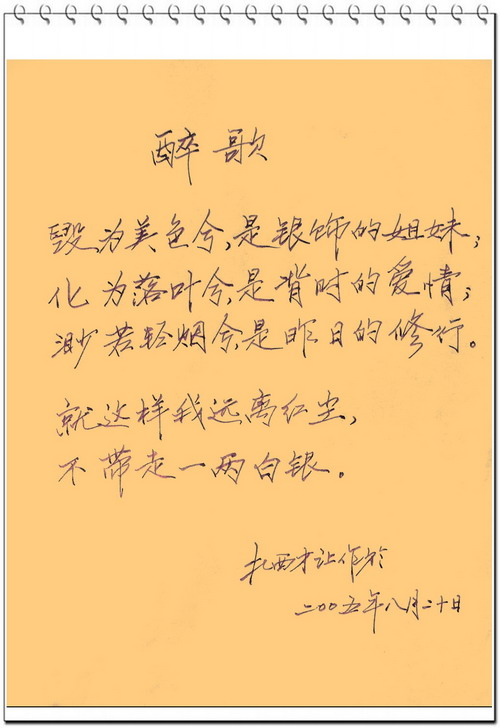
гҖҖгҖҖ
гҖҖгҖҖзҙўжңЁдёңпјҡвҖңж—§дәӢе·ІеҰӮжәӘжөҒпјҢжіЁе…ҘдҪ зҡ„иЎҖж¶Іпјӣж•…ең°е·ІеҰӮзІҫзҒөпјҢеҢ–дёәдҪ зҡ„йӯӮйӯ„гҖӮдҪ зңҹзҡ„иғҪеӨҹиҝңзҰ»еҘ№еҗ—пјҹвҖқе…„ејҹ们жҳҜиҜ»зқҖдҪ дјҳзҫҺзҡ„иҜ—жӯҢжҖҖеҝөдҪ жҶЁеҺҡзҡ„笑容呢пјҢиҝҳжҳҜе’ҢдҪ дёҖиө·иҜ»зқҖдҪ дјҳзҫҺзҡ„иҜ—жӯҢжҖҖеҝөзҫҺеҘҪзҡ„иҜ—жӯҢеІҒжңҲе‘ўпјҹ
гҖҖгҖҖжүҺиҘҝжүҚи®©пјҡеә”иҜҘиҝҷд№ҲиҜҙпјҡи®©жҲ‘们иҜ»зқҖжӣҙеӨҡдјҳз§ҖиҜ—дәәзҡ„дјҳзҫҺиҜ—жӯҢпјҢжҖҖеҝөжҲ‘们зҫҺеҘҪзҡ„иҜ—жӯҢеІҒжңҲпјҒ
гҖҖгҖҖж— и®әжҲ‘们жҳҜеҗҰиҝңзҰ»иҜ—зҘһпјҢжҲ‘们йғҪеә”е…іжіЁдјҹеӨ§зҘ–еӣҪе’ҢеҸӨиҖҒж°‘ж—ҸеҶ…еҝғзҡ„з§ҳеҸІпјҢжҜ”еҰӮж–°ж—¶д»ЈејҖеҲӣиҖ…еүҚиЎҢйҒ“и·ҜдёҠзҡ„жӣҷе…үе’ҢиҗҪж—ҘпјҢзҘһеҘҮеңҹең°дёҠиҜһз”ҹзҡ„зҘһиҜқе’Ңдј иҜҙпјҢдәҳеҸӨй•ҝжІійҮҢй—ӘиҖҖзқҖйҮ‘银е…үиүІзҡ„ж–ӯд»ЈеҸІгҖӮз”ҡиҮіиҝҳеҸҜд»Ҙе…іжіЁдёӘдҪ“зҡ„еҶ…еҝғдҪ“йӘҢпјҢжҜ”еҰӮйӮЈдәӣеҫҖжҳ”ж—ҘеӯҗйҮҢзҡ„зҲұдёҺжҒЁгҖҒжіӘдёҺз—ӣпјҢйӮЈдәӣзҒҝзғӮйҳіе…үе’Ңз§ҳеҜҶжғ…дәӢпјҢйӮЈдәӣеҝғзҒөзҡ„иҪ»еҫ®йңҮйўӨпјҢжҝҖжғ…йҷҚдёҙж—¶иҺ«еҸҜеҗҚзҠ¶зҡ„ж¬ўж„үвҖҰвҖҰи°ҰйҖҠи®Өзңҹең°дҪ“е‘іжҜҸдёҖж®өдәәз”ҹпјҢеңЁзІҫзҘһе’ҢжҖқжғіжҺҖиө·е·ЁеӨ§жіўжөӘзҡ„еӨ§жө·дёҠйўҶеҸ—еҶ…еҝғзҡ„йЈҺжҡҙпјҢжІүйҶүдәҺйӣЁиҝҮеӨ©жҷҙеҗҺзҡ„зҘҘе’ҢдёҺе®үе®ҒгҖӮ
гҖҖгҖҖ
гҖҖгҖҖзҙўжңЁдёңпјҡвҖңд»Җд№Ҳд№ҹжқҘдёҚеҸҠеҒҡ/жҲ‘ж¬ІжҠҪиә«зҰ»ејҖ/е°ұе·ІйҡҸйЈҺйЈҳйӣ¶вҖқвҖ”вҖ”дёҚиҝҮеҘҪеңЁдҪ зҡ„ж–Үеӯ—з•ҷз»ҷдәҶжҲ‘们пјҢз•ҷз»ҷдәҶиҝҷдёӘж—¶д»ЈпјҢиҝҷе·Із»Ҹи¶іеӨҹпјҒ
гҖҖгҖҖжүҺиҘҝжүҚи®©пјҡжҲ‘жҳҜдёӘжӮІи§Ӯдё»д№үиҖ…пјҢеёёеёёи®ӨдёәвҖңжҲ‘зҡ„ж№®жІЎжӮ„ж— еЈ°жҒҜвҖқгҖӮеҜ№дәҺжҲ‘зҡ„иҜ—жӯҢжқҘиҜҙпјҢд№ҹжҳҜеҰӮжӯӨгҖӮеҲӨж–ӯдёҖдёӘдәәзҡ„ж–Үеӯ—жҳҜеҗҰз•ҷз»ҷдәҶдёҖдёӘж—¶д»ЈпјҢйӮЈжҳҜйңҖиҰҒж—¶й—ҙзҡ„иҖғйӘҢзҡ„гҖӮж—¶й—ҙе°ұжҳҜдёҖжқЎжІіпјҢиў«жІіж°ҙеёҰжқҘзҡ„дёңиҘҝпјҢиҰҒд№ҲжјӮжө®дәҺжІійқўпјҢиҰҒд№ҲжІүдәҺжІіеә•пјҢиҰҒд№Ҳиў«ж°ҙзЁҖйҮҠгҖӮжІүдәҺжІіеә•жҲ–иҖ…иў«ж°ҙзЁҖйҮҠпјҢйғҪжҳҜиў«ж·ҳжұ°пјҒиҖҢжө®дәҺжІійқўзҡ„пјҢеңЁжІіж°ҙеҘ”жөҒзҡ„иҝҮзЁӢдёӯпјҢд№ҹжңүзқҖжҲӘ然дёҚеҗҢзҡ„з»“еұҖгҖӮжҲ‘дёҚеҘўжңӣжҲ‘зҡ„иҜ—жӯҢиғҪеӨҹеҫ—еҲ°жөҒдј пјҢеҸӘеёҢжңӣиҝҷдәӣж–Үеӯ—иғҪи®©дәәдә§з”ҹжғ…ж„ҹе…ұйёЈпјҢз»ҷйҳ…иҜ»е®ғзҡ„дәәеёҰжқҘзүҮеҲ»зҡ„и§ҰеҠЁгҖҒж„ҹеҠЁе’ҢжҝҖеҠЁгҖӮиғҪеҒҡеҲ°иҝҷдәӣпјҢжҲ‘е°ұеҝғж»Ўж„Ҹи¶ідәҶгҖӮ
гҖҖгҖҖдҪ зһ§пјҢдҪ з»ҷдәҶжҲ‘дёҖдёӘиҜҙзңҹиҜқзҡ„жңәдјҡпјҒ
гҖҖгҖҖж„ҹи°ўдҪ еҜ№жҲ‘зҡ„йҮҮи®ҝпјҢд№ҹж„ҹи°ўи—Ҹдәәж–ҮеҢ–зҪ‘еҜ№жҲ‘зҡ„е®Јдј дёҺжҠҘйҒ“пјҢжӣҙиҰҒж„ҹи°ўиҜ»иҖ…жңӢеҸӢй•ҝжңҹд»ҘжқҘеҜ№жҲ‘зҡ„е…іжіЁпјҒ
гҖҖгҖҖжңӢеҸӢ们пјҢи°ўи°ўдәҶпјҒ
гҖҖгҖҖ
гҖҖгҖҖдәҢгҖҮдёҖгҖҮе№ҙе…«жңҲе…°е·һ
пјҲж‘„еҪұпјҡжқҺеҹҺпјү
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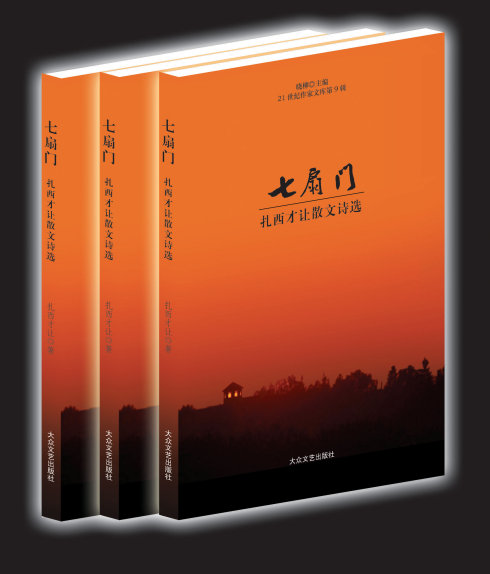
гҖҖгҖҖ
гҖҖгҖҖзҙўжңЁдёңпјҡдҪ еҘҪпјҢиҖҒе…„пјҒйҰ–е…ҲзҘқиҙәдҪ зҡ„иҜ—жӯҢз»“йӣҶеҮәзүҲпјҒиҝҷеҜ№и—Ҹж—Ҹж–Үеқӣе’Ңз”ҳиӮғж–ҮеқӣиҖҢиЁҖпјҢж— з–‘жҳҜ件幸дәӢпјҒ
гҖҖгҖҖжүҺиҘҝжүҚи®©пјҡе‘өе‘өпјҢеқҰзҺҮең°иҜҙпјҢеҜ№жҲ‘иҮӘе·ұиҖҢиЁҖпјҢиҝҷжҳҜ件幸дәӢгҖӮдҪҶеҜ№и—Ҹж—Ҹж–Үеқӣе’Ңз”ҳиӮғж–ҮеқӣжқҘиҜҙпјҢеӨҡдёҖдёӘжүҺиҘҝжүҚи®©пјҢжҲ–иҖ…е°‘дёҖдёӘжүҺиҘҝжүҚи®©пјҢеӨҡеҮәдёҖжң¬д№ҰжҲ–е°‘еҮәдёҖжң¬д№ҰпјҢжҲ‘и®ӨдёәйғҪдёҚеӨӘйҮҚиҰҒгҖӮйҮҚиҰҒзҡ„жҳҜпјҢд»–йҖҡиҝҮж–ҮеӯҰеҲӣдҪңпјҢиЎЁзҺ°дәҶдёӘдәәжүҖе…іжіЁзҡ„дё–з•ҢпјҢиЎЁиҫҫдәҶд»–еҜ№иә«иҫ№дёҮзү©зҡ„жғ…ж„ҹгҖӮ
гҖҖгҖҖжҲ‘дёҖзӣҙи®ӨдёәпјҢеҜ№дәҺдҪң家е’ҢиҜ—дәәжқҘиҜҙпјҢйҮҚиҰҒзҡ„еә”иҜҘжҳҜдҪңе“Ғжң¬иә«гҖӮеҘҪзҡ„дҪңе“ҒиғҪеӨҹжҲҗе°ұеҘҪзҡ„дҪң家иҜ—дәәпјҢдҪҶеҘҪзҡ„дҪң家иҜ—дәәдёҚдёҖе®ҡеҶҷеҮәеҘҪзҡ„дҪңе“ҒгҖӮжҲ‘们зҺ°еңЁиҜ»еҚЎеӨ«еҚЎгҖҒиүҫз•Ҙзү№е’Ңжҷ®йІҒж–Ҝзү№пјҢиҜ»жқҺзҷҪгҖҒжқҺе•Ҷйҡҗе’ҢйҷҲеӯҗжҳӮпјҢиҜ»е…ӯдё–иҫҫиө–д»“еӨ®еҳүжҺӘе’ҢејҳдёҖжі•еёҲжқҺеҸ”еҗҢгҖҒе®һйҷ…дёҠиҜ»зҡ„жҳҜ他们зҡ„дҪңе“ҒпјҢ并且йҖҡиҝҮе…¶дҪңе“Ғи®ӨиҜҶ他们иҝҷдәӣдәәгҖӮжүҖд»ҘпјҢдёҖжң¬д№Ұзҡ„е‘ҪиҝҗпјҢеҪ“е®ғйқўдё–д№ӢеҗҺпјҢдҪңиҖ…дјјд№Һж— жі•еҶіе®ҡе®ғзҡ„е‘ҪиҝҗпјҢжңүж•Ҳзҡ„ж“ҚдҪңе’Ңе®Јдј пјҢеҸӘиғҪеңЁзҹӯжңҹеҶ…дә§з”ҹеҪұе“ҚпјҢиғҪеҗҰйҷӘдјҙдёҚеҗҢзҡ„иҜ»иҖ…еәҰиҝҮ他们зҡ„зҫҺеҘҪж—¶е…үпјҢйӮЈе°ұеҝ…йЎ»зңӢдҪңе“Ғзҡ„йӯ…еҠӣгҖӮжҲ‘зҡ„иҜ—жӯҢжҳҜеҗҰиҝҳе…·еӨҮзқҖиҝҷз§Қйӯ…еҠӣпјҢзҺ°еңЁжҲ‘жҢҒжҖҖз–‘жҖҒеәҰпјҢеӣ дёәжҲ‘们еӣәжңүзҡ„дёӘдәәз§үжҖ§пјҢжҲҗй•ҝзҡ„дәәж–ҮзҺҜеўғпјҢжҺҘеҸ—зҡ„ж–ҮеҢ–зҶҸйҷ¶пјҢзңӢеҫ…дёҮзү©зҡ„зңје…үпјҢзҗҶи§Је°ҳдё–зҡ„зғҰеҝ§зӯүзӯүпјҢжҳҜдёҚе°ҪзӣёеҗҢзҡ„пјҢдҪңдёәиҜ»иҖ…зҡ„дёӘдҪ“пјҢд№ҹеӣ жӯӨиҖҢеҜ№дҪң家иҜ—дәәзҡ„дҪңе“ҒжңүзқҖдёӘдәәзҡ„е–ңеҘҪпјҒ
гҖҖгҖҖжңүзҡ„дҪң家иҜ—дәәиҜҙиҮӘе·ұзҡ„дҪңе“ҒжҳҜеҶҷз»ҷдә”еҚҒе№ҙеҗҺзҡ„иҜ»иҖ…зңӢзҡ„пјҢиҝҷиҜқиҷҪ然жңүдәӣзӢӮеҰ„пјҢдҪҶдјјд№Һйҡҗи—ҸзқҖж·ұж·ұзҡ„ж— еҘҲе’ҢйҒ—жҶҫпјҒ
гҖҖгҖҖ
гҖҖгҖҖзҙўжңЁдёңпјҡзңӢеҲ°дҪ зҡ„еҗҺи®°пјҢеҝғдёӯдёҚзҰҒй»Ҝ然пјҒз”ҡиҮіжңүзӮ№иҗҪеҜһе’ҢеҜӮеҜҘпјҒеңЁдҪ иҜ—жӯҢеҲӣдҪңжӯЈйҖўзӣӣжңҹзҡ„ж—¶иҠӮпјҢжҳҜд»Җд№Ҳи®©дҪ иҗҢз”ҹйҖҖж„Ҹпјҹ
гҖҖгҖҖжүҺиҘҝжүҚи®©пјҡе…¶е®һдёҚжҳҜйҖҖеҮәпјҢжҳҜйҖ”дёӯзҡ„дј‘ж•ҙпјҢжҳҜеҜ№жҲ‘зҡ„иҜ—жӯҢеҲӣдҪңзҡ„е°Ҹз»“е’ҢеҸҚжҖқгҖӮ
гҖҖгҖҖжҲ‘йқһеёёе–ңж¬ўдҪң家йҳҝжқҘпјҢе–ңж¬ўд»–зҡ„иҜ—йЈҺпјҢе–ңж¬ўд»–зҡ„е°ҸиҜҙпјҢе–ңж¬ўд»–зҡ„жҜ…然еҶіж–ӯзҡ„дёӘжҖ§гҖӮеҪ“е№ҙд»–еҶҷгҖҠдёүеҚҒеІҒж—¶жј«жёёиӢҘе°”зӣ–еӨ§иҚүеҺҹгҖӢиҝҷйҰ–й•ҝиҜ—ж—¶пјҢж„Ҹж°”еҘӢеҸ‘пјҢжүҚжғ…жЁӘжәўпјҢдҪҶд»–зӘҒ然еҒңжӯўдәҶиҜ—жӯҢеҶҷдҪңпјҢиҖҢе°ҶзІҫеҠӣиҪ¬еҗ‘зҹӯдёӯзҜҮе°ҸиҜҙеҲӣдҪңгҖӮгҖҠйҳҝе…ӢйЎҝе·ҙгҖӢгҖҒгҖҠжңҲе…үйҮҢзҡ„银еҢ гҖӢгҖҒгҖҠиЎҢеҲ‘дәәе°”дҫқгҖӢзӯүдҪңе“Ғзҡ„иҜһз”ҹпјҢзү№еҲ«жҳҜй•ҝзҜҮе°ҸиҜҙгҖҠе°ҳеҹғиҗҪе®ҡгҖӢзҡ„жЁӘз©әеҮәдё–пјҢд»ҘеҸҠеҗҺжңҹзІҫеҝғжү“йҖ зҡ„гҖҠз©әеұұгҖӢзі»еҲ—дҪңе“Ғзҡ„жҲҗеҠҹпјҢиҜҒжҳҺд»–зҡ„еҶіж–ӯжҳҜжӯЈзЎ®зҡ„гҖӮ
гҖҖгҖҖдҪңдёәеҶҷдҪңиҖ…пјҢжҲ‘们еә”иҜҘжҖқиҖғиҝҷж ·дёүдёӘй—®йўҳпјҡжҲ‘们дёәд»Җд№ҲеҶҷдҪңпјҹжҲ‘们еҶҷд»Җд№ҲпјҹжҲ‘们жҖҺд№ҲеҶҷпјҹиҝҷе…¶е®һе°ұжҳҜдёүдёӘжңүе…іеҶҷдҪңзҡ„еӨ§й—®йўҳгҖӮдёҚжҖқиҖғиҝҷдёүдёӘй—®йўҳзҡ„дәәпјҢж°ёиҝңеҸӘжҳҜдёӘж–ҮеӯҰзҲұеҘҪиҖ…пјҢд»ҺдәӢзҡ„жҳҜзӣІзӣ®еҶҷдҪңгҖӮжҖқиҖғ并иғҪеӨҹи§ЈеҶіиҝҷдёүдёӘй—®йўҳзҡ„дҪң家иҜ—дәәпјҢжүҚиғҪеңЁж–ҮеӯҰеҲӣдҪңйҳҹдјҚдёӯз•ҷдёӢд»–й«ҳеӨ§зҡ„иғҢеҪұгҖӮ
гҖҖгҖҖеҚҒе№ҙеүҚжҲ‘е°ұжҖқиҖғиҝҷдёүдёӘй—®йўҳпјҢдҪҶеҲ°зҺ°еңЁдёҖзӣҙжІЎжңүеӨ„зҗҶеҘҪпјҢеҺҹеӣ еҫҲеӨҡпјҢеӨ–еңЁзҡ„пјҢеҶ…еңЁзҡ„пјҢдё»и§Ӯзҡ„пјҢе®ўи§Ӯзҡ„пјҢйғҪжңүгҖӮжҲ‘дёҚжҳҜдёҖдёӘжҖҖжҠұеӨ§еҝ—зҡ„дәәпјҢеҸҜеңЁеҶҷдҪңдёҠиҝҳжҳҜжңүзқҖдёӘдәәзҡ„зҗҶжғігҖӮиҝҷдёӘзҗҶжғізҡ„е®һзҺ°дёҺеҗҰпјҢдёҖзӣҙеӣ°жү°зқҖжҲ‘пјҢеҪұе“ҚзқҖжҲ‘зҡ„еҲӣдҪңзҠ¶жҖҒгҖӮжҲ‘е§Ӣз»Ҳи®ӨдёәжҲ‘зҡ„еҲӣдҪңиҝҳжңӘеҲ°жүҖи°“зҡ„зӣӣжңҹпјҢжҲ‘еңЁж–ҮеӯҰеҶҷдҪңд№Ӣи·ҜдёҠиҫ№иө°иҫ№жӯҮгҖҒиҫ№жӯҮиҫ№иө°пјҢе°ұиҝҷж ·ж…ўеҗһеҗһең°иө°дәҶдёҖеҚҒе…«е№ҙгҖӮеҚҒе…«е№ҙпјҢеӨҡеҘҪзҡ„дёҖж®өе…үйҳҙе•ҠпјҢе©ҙе„ҝеҸҜд»Ҙй•ҝжҲҗеё…е“ҘзҫҺеҘіпјҢ家еәӯеҸҜд»Ҙз»„дәҶеҸҲе»әе»әдәҶеҸҲзҰ»пјҢдәӢдёҡеҸҜд»Ҙеі°еӣһи·ҜиҪ¬еҸҲйҷ·дәҺжІүжәәпјҢиҖҢжҲ‘е‘ўпјҹеҪ“е№ҙжҳҜдёӘйЈҺеҚҺжӯЈиҢӮзҡ„иҜ—жӯҢеҶҷдҪңиҖ…пјҢиҖҢд»ҠеҚҙе§Ӣз»ҲеғҸдёӘжү¶еўҷиө°и·Ҝзҡ„зһҺеӯҗпјҒеӣ жӯӨжҲ‘иҗҢз”ҹдәҶдёӯйҖ”жӯҮжҒҜзҡ„жғіжі•пјҢжӯҮжҒҜд№ӢеҗҺж•ҙиЈ…еҫ…еҸ‘иҝҳжҳҜз»қе°ҳиҖҢеҺ»пјҢиҝҷдёӘе°ұиө°зқҖзңӢеҗ§пјҒ
гҖҖгҖҖеҸҰеӨ–пјҢжҲ‘жіЁж„ҸеҲ°пјҢдёҺжҲ‘дёҖж ·еӨ„еңЁиҝҷз§ҚзҠ¶жҖҒдёӯзҡ„иҜ—дәәе’ҢдҪң家пјҢжҳҜжҜ”иҫғеӨҡзҡ„гҖӮдҪ жҜ”еҰӮиҜҙжҲ‘们з”ҳиӮғзҡ„и‘—еҗҚиҜ—дәәжЎ‘еӯҗгҖҒиЈ•еӣәж—ҸиҜ—дәәиҙәдёӯгҖҒи—Ҹж—ҸиҜ—дәәзҳҰж°ҙгҖҒж ЎеӣӯиҜ—дәәиҗ§йҹігҖҒеӣһж—ҸиҜ—дәәж•ҸеҪҰж–ҮзӯүзӯүпјҢдҪ иҜҙйғҪжңүжүҚеҗ§пјҢйғҪдјјд№Һж— жі•ж‘Ҷи„ұеӣ°еўғпјҢдёҺж–ҮеӯҰе§Ӣз»ҲдҝқжҢҒзқҖдёҖз§ҚиӢҘеҚіиӢҘзҰ»зҡ„и·қзҰ»гҖӮ
гҖҖгҖҖ
гҖҖгҖҖзҙўжңЁдёңпјҡи®°еҫ—йӮЈжҳҜ1994е№ҙз§ӢеӨ©пјҢеҲҡиө°еҮәз”ҳеҚ—иҚүеҺҹгҖҒеҲҡеҲҡеӯҰзқҖеҶҷиҜ—зҡ„жҲ‘пјҢеңЁиҘҝеҢ—еёҲеӨ§зҡ„ејҖеӯҰе…ёзӨјдёҠеҗ¬ж Ўй•ҝеңЁи®ІиҜқдёӯжҸҗеҸҠеҗҢд№ЎеҗҢж—Ҹзҡ„дҪ пјҢйӮЈж—¶жҳҜдҪ•зӯүзҡ„д»°ж…•е•ҠпјҒд»ҺйӮЈеӨ©ејҖе§ӢпјҢиҜ—жӯҢзҡ„еҠӣйҮҸе’Ңйӯ…еҠӣпјҢеҶҚж¬Ўж·ұж·ұеҮ»дёӯдәҶжҲ‘зҡ„еҝғзҒөпјҒд»ҠеӨ©пјҢдҪ иғҪеӣһеҝҶдёҖдёӢдҪ зҡ„иҜ—жӯҢд№Ӣи·Ҝеҗ—пјҹ
гҖҖгҖҖжүҺиҘҝжүҚи®©пјҡеҘҪпјҢе°ұйЎәзқҖдҪ зҡ„иҝҷдёӘй—®йўҳйҡҸдҫҝжүҜдёҖжүҜгҖӮзҺ°еңЁжғіжғіпјҢиҘҝеҢ—еёҲеӨ§зЎ®е®һжҳҜдёҖдёӘиғҪеӨҹиҜһз”ҹиҜёеӨҡиҜ—дәәзҡ„еӯҰеәңгҖӮжҲ‘们з”ҳиӮғиҜ—жӯҢеҲӣдҪңйҳҹдјҚдёӯзҡ„дҪјдҪјиҖ…пјҢж— и®әжҳҜеҠҹжҲҗеҗҚе°ұзҡ„пјҢиҝҳжҳҜеҰӮж—ҘдёӯеӨ©зҡ„пјҢиҝҳжҳҜжӯЈеңЁиҜ•еӣҫеҶІејҖдёҖжқЎиЎҖи·Ҝзҡ„пјҢеӨ§еӨҡжҜ•дёҡдәҺиҘҝеҢ—еёҲеӨ§пјҢиҝҷдјјд№ҺдёҺиҝҷжүҖеӯҰеәңзҡ„ж–ҮеҢ–з§Ҝж·Җжңүе…іпјҢдёҺж–ҮеӯҰеҲӣдҪңж°ӣеӣҙжңүе…іпјҢдёҺе®Ҫжқҫзҡ„ж Ўеӣӯдәәж–ҮзҺҜеўғжңүе…ігҖӮжҲ‘еңЁиҝӣе…ҘеёҲеӨ§д№ӢеҲқпјҢе°ұејәзғҲең°ж„ҹеҸ—еҲ°дәҶиҝҷдёҖзӮ№гҖӮйӮЈж—¶еҖҷеёҲеӨ§жңүдёүдёӘж–ҮеӯҰзӨҫпјҢз»ҷдәәеҚ°иұЎеҫҲж·ұпјҢдёҖдёӘжҳҜвҖңжҲ‘们вҖқпјҢиҗ§йҹігҖҒеҫҗе…ҶеҜҝ他们еңЁеҠһпјҢеңЁж ЎеӣӯйҮҢжңүзқҖе№ҝжіӣзҡ„еҪұе“ҚпјӣдёҖдёӘжҳҜвҖңе…Ҳй”ӢвҖқпјҢдёӯж–Үзі»еҠһзҡ„пјҢжҲ‘们称д№Ӣдёәдёӯж–Үзі»жүҚеӯҗжүҚеҘізҡ„иҠіиҚүең°пјӣдёҖдёӘжҳҜвҖңжҷЁжҳ•вҖқпјҢж”ҝеҸІзі»еҠһзҡ„пјҢжҳҜжҲ‘иө°дёҠиҜ—жӯҢеҶҷдҪңд№Ӣи·Ҝзҡ„еҠ жІ№з«ҷгҖӮжҲ‘е…ҲжҳҜеңЁиҝҷдёүдёӘеҶ…йғЁдәӨжөҒеҲҠзү©дёҠеҸ‘дҪңе“ҒпјҢеҗҺжқҘе°ұеңЁгҖҠиҘҝеҢ—еёҲеӨ§жҠҘгҖӢгҖҒгҖҠйҳіе…ігҖӢгҖҒгҖҠзәўжҹігҖӢгҖҒгҖҠж јжЎ‘иҠұгҖӢгҖҒгҖҠйЈһеӨ©гҖӢгҖҒгҖҠиҘҝи—Ҹж–ҮеӯҰгҖӢгҖҒгҖҠиҜ—зҘһгҖӢгҖҒгҖҠиҜ—жӯҢжҠҘжңҲеҲҠгҖӢгҖҒгҖҠжҳҹжҳҹиҜ—еҲҠгҖӢзӯүеҲҠзү©дёҠеҸ‘пјҢиө°зҡ„и·Ҝеӯҗеҹәжң¬дёҠжҳҜдј з»ҹејҸзҡ„пјҢе°ұеғҸж•ҷеёҲдёҠиҒҢз§°дёҖж ·пјҢз”ұж•ҷе‘ҳеҲ°еҲқзә§пјҢз”ұеҲқзә§еҲ°дёӯзә§пјҢз”ұдёӯзә§еҲ°й«ҳзә§пјҢдёҖжӯҘдёҖдёӘеҸ°йҳ¶пјҢдёҖжӯҘдёҖдёӘи„ҡеҚ°гҖӮеҲ°еӨ§еӯҰжҜ•дёҡж—¶пјҢдёҚзҹҘдёҚи§үз«ҹ然混жҲҗдәҶдёҖдёӘж ЎеӣӯиҜ—дәәгҖӮеӨ§еӯҰжҜ•дёҡеҗҺпјҢеҶҷдҪңжңүдәҶж–№еҗ‘жҖ§пјҢдёңиҘҝд№ҹеҸ‘еҫ—жӣҙеӨҡпјҢдёҠдәҶгҖҠиҜ—еҲҠгҖӢгҖҒгҖҠж°‘ж—Ҹж–ҮеӯҰгҖӢгҖҒгҖҠж•Јж–ҮиҜ—гҖӢгҖҒгҖҠж•Јж–ҮиҜ—дё–з•ҢгҖӢзӯүжқӮеҝ—пјҢдҪңе“Ғе…ҘйҖүеӨҡжң¬иҜ—жӯҢйҖүжң¬пјҢиҺ·дәҶдәӣе…ЁеӣҪжҖ§зҡ„гҖҒзңҒзә§зҡ„еӨ§еҘ–пјҢд№ҹжңүе№ёиў«и—Ҹдәәж–ҮеҢ–зҪ‘гҖҒиҘҝи—ҸдҝЎжҒҜдёӯеҝғгҖҒз”ҳиӮғдҪң家зҪ‘зӯүзҪ‘з«ҷд»Ҙдё“йЎөеҪўејҸжҺЁиҚҗз»ҷдәҶиҜ»иҖ…пјҒ
гҖҖгҖҖ
гҖҖгҖҖзҙўжңЁдёңпјҡдҪңдёәдёҖдёӘеңЁиҜ—жӯҢд№Ӣи·ҜдёҠзҡ„и·өиЎҢиҖ…пјҢжҲ‘ж·ұж·ұзҹҘйҒ“пјҢдёҖдёӘиҜ—дәәпјҢиғҪеҪўжҲҗиҮӘе·ұзӢ¬зү№зҡ„йЈҺж јпјҢжҳҜдҪ•е…¶дёҚжҳ“пјҒиҖҢдҪ еҒҡеҲ°дәҶпјҒеҚҒе…«е№ҙжқҘпјҢдҪ зҡ„жҜҸдёҖиЎҢж–Үеӯ—пјҢйғҪж·ұж·ұең°жү“дёҠдәҶдёҖдёӘзғҷеҚ°вҖ”вҖ”вҖңжүҺиҘҝжүҚи®©вҖқпјҒд»ҠеӨ©пјҢдҪ дёәиҜ—жӯҢе’ҢиҜ—дәәпјҢжңҖжғіиҜҙзӮ№д»Җд№Ҳпјҹ
гҖҖгҖҖжүҺиҘҝжүҚи®©пјҡжғіиҜҙзҡ„еҫҲеӨҡгҖӮдё»иҰҒиҜҙдёӨзӮ№пјҡ
гҖҖгҖҖ第дёҖпјҢиҜ—йЈҺзҡ„еҪўжҲҗе§Ӣз»ҲжңүдёҖдёӘжЁЎд»ҝвҖ”вҖ”еҖҹйүҙвҖ”вҖ”еҗёж”¶вҖ”вҖ”еҲӣж–°вҖ”вҖ”иҝ”жңҙеҪ’зңҹзҡ„иҝҮзЁӢгҖӮиҝҷе…¶е®һжҳҜиҜ—жӯҢеҶҷдҪңзҡ„дә”дёӘйҳ¶ж®өпјҢиҖҢиҝҷдә”дёӘйҳ¶ж®өпјҢжҜҸдёҖйҳ¶ж®өиҝҳеҸҜд»Ҙз»ҶеҲҶпјҢеҸҜд»ҘеҲ’еұӮгҖӮиҝҷдјјд№ҺжҳҜеәҹиҜқпјҢдҪҶеҚҒеҲҶйҮҚиҰҒпјҒжҜҸдёӘеҶҷдҪңиҖ…пјҢйғҪе°ҶжҲ–еӨҡжҲ–е°‘ең°жңүжүҖдҪ“йӘҢгҖӮеӣ жӯӨжҲ‘们иҰҒжё…йҶ’ең°и®ӨиҜҶеҲ°иҮӘе·ұжүҖеӨ„зҡ„дҪҚзҪ®пјҢдёҚиғҪеҰ„иҮӘе°ҠеӨ§пјҢзӣ®дёӯж— дәәпјҢеҗҰеҲҷдјҡи·Ңи·ҹеӨҙпјҢдјҡеҸ—дјӨпјҢдјҡиө°зҒ«е…Ҙйӯ”гҖӮзңӢйҮ‘еәёзҡ„жӯҰдҫ е°ҸиҜҙпјҢдәҶи§Јжңүеү‘дёҺж— еү‘пјҢжңүжӢӣдёҺж— жӢӣпјҢе…ҘйҒ“дёҺеҮәйҒ“пјҢе°ұиғҪжҳҺзҷҪиҝҷдёӘйҒ“зҗҶгҖӮзӣ®еүҚжҲ‘жүҖеҲ°иҫҫзҡ„йҳ¶ж®өпјҢд»…д»…жҳҜеҲҡеҲҡи·Ёе…ҘеҲӣж–°йҳ¶ж®өзҡ„й—Ёж§ӣпјҢжүӢдёӯжҸЎдёҖжҠҠе№іеёёд№Ӣеү‘пјҢеӯҰзҡ„жҳҜеӨ§еёҲзҡ„жӢӣж•°пјҢиө°зҡ„жҳҜзҫҠиӮ е°ҸйҒ“пјҢиҝҳжІЎжңүиө°еҮәдёҖжқЎеӨ§и·ҜжқҘгҖӮжҲ‘们и—Ҹж—Ҹзҡ„йғЁеҲҶжҲҗеҗҚиҜ—дәәпјҢеҰӮдё№зңҹиҙЎеёғгҖҒз»•йҳ¶е·ҙжЎ‘гҖҒдјҠдё№жүҚи®©гҖҒеҲ—зҫҺе№іжҺӘзӯүпјҢиҝҳжңүз”ҳиӮғзҡ„иҜ—еқӣеӨ§и…•д»¬пјҢеҰӮжқҺиҖҒд№ЎгҖҒдҪ•жқҘгҖҒеӨҸзҫҠд»ҘеҸҠеҗҺжқҘиҖ…еҸӨ马гҖҒе”җж¬ЈгҖҒеЁңеӨңгҖҒйҳҝдҝЎгҖҒзҺӢиӢҘеҶ°гҖҒзүӣеәҶеӣҪзӯүпјҢеӨ§еӨҡд№ҹеӨ„еңЁиҝҷдёӘйҳ¶ж®өпјҢдёҚиҝҮеұӮж¬ЎжҜ”жҲ‘й«ҳеҫ—еӨҡгҖӮеҲ°иҫҫ第дә”йҳ¶ж®өзҡ„иҜ—дәәе°‘д№ӢеҸҲе°‘пјҢеңЁж”ҫзңјеӣҪеҶ…иҜ—еқӣпјҢеҜҘеҜҘж— еҮ гҖӮ
гҖҖгҖҖ第дәҢпјҢжҲ‘们дёҖзӣҙеңЁеӨёеӨ§зҺ°еҪ“д»ЈиҜ—жӯҢзҡ„еҠӣйҮҸпјҢе…¶е®һиҜ—жӯҢзҡ„еҠӣйҮҸжҳҜжңүйҷҗзҡ„гҖӮжҲ‘дёӘдәәи®ӨдёәзҺ°еҪ“д»ЈиҜ—жӯҢзҡ„дҪңз”Ёе’Ңд»·еҖјпјҢжҜ”дёҚдёҠе°ҸиҜҙпјҢжӣҙжҜ”дёҚдёҠеҪұи§ҶдҪңе“ҒгҖӮжңүж—¶дёҠзҪ‘зҺ©жёёжҲҸпјҢеҸ‘зҺ°иҝҷзҪ‘з»ңжёёжҲҸиҰҒжҜ”иҜ—жӯҢеҸҜжҖ•еҫ—еӨҡпјҢејәиӣ®еҫ—еӨҡгҖӮеҰӮжһңзңҹиҰҒжғіиҜ—жӯҢзҡ„еҠӣйҮҸејәеӨ§иө·жқҘпјҢжҲ‘们е°ұеә”иҜҘеҒҡеҘҪдёүдёӘж–№йқўзҡ„е·ҘдҪңпјҢдёҖжҳҜйҖ еҠҝпјҢд»ҘиҜ—дёәеӨ©пјҢд»ҘиҜ—дёә马пјҢд»ҘиҜ—дёәжўҰпјҢе”ҜиҜ—дёәдёҠгҖӮиҝҷдёҖзӮ№пјҢеғҸжӮЁиҝҷж ·зҡ„жҙ»и·ғеңЁзҪ‘з»ңдёҠзҡ„иҜ—дәә们еҒҡеҫ—еҘҪпјҢжҲ‘иҮӘе·ұе§Ӣз»Ҳз»ҷдёҚдёҠеҠІгҖӮдәҢжҳҜдә®зӣёпјҢжңүиҮӘе·ұи§үеҫ—ж»Ўж„Ҹзҡ„дҪңе“ҒпјҢиҰҒеҸҠж—¶зҡ„жҠ•зЁҝпјҢеҸҠж—¶еҸ‘иЎЁпјҢдёҚиҰҒй”ҒеңЁжҠҪеұүйҮҢпјҢжҗҒеңЁз”өи„‘йҮҢпјҢдёҖе№ҙеҚҠиҪҪпјҢдёҚи®©еҮәдё–гҖӮжҲ‘еҚҒеҲҶеҸҚеҜ№е°Ғй—ӯејҸеҶҷдҪңпјҢз»ҷдәәдёҖз§ҚеҚҒе№ҙзЈЁдёҖеү‘зҡ„ж„ҹи§үпјҢзӯүеү‘зЈЁеҘҪдәҶпјҢжҢәиә«иҖҢеҮәжӢ”еү‘еӣӣйЎҫпјҢдәә家已з»ҸдҪҝз”ЁдёҠеҺҹеӯҗеј№дәҶпјҒиҜ—жӯҢдёҚжҳҜеҸӨи‘ЈпјҢдёҚдјҡеӨҡе°‘е№ҙд»ҘеҗҺжӢҝеҮәжқҘиҝҳиғҪеҚ–дёҠеӨ§д»·й’ұпјҢеҖјй’ұзҡ„еҸӘжҳҜе°‘ж•°дәәзҡ„е°‘ж•°зҜҮз« гҖӮжҲ‘们д№ҹдёҚиғҪзӣёдҝЎвҖңжҳҜйҮ‘еӯҗе°ұдјҡеҸ‘е…үвҖқиҝҷеҘ—й¬јиҜқпјҢеӣ дёәйҮ‘еӯҗж··еңЁжіҘжІҷйҮҢпјҢжіҘжІҷдҝұдёӢпјҢйҮ‘еӯҗд№ҹдёӢгҖӮдёүжҳҜжҺҘиҪЁпјҢдёҺж•Јж–ҮжҺҘиҪЁпјҢдёҺе°ҸиҜҙжҺҘиҪЁпјҢдёҺз”өи§ҶжҺҘиҪЁпјҢдёҺеӨ§дәӢжҺҘиҪЁгҖӮеңЁдёҺж•Јж–Үе’Ңе°ҸиҜҙзҡ„жҺҘиҪЁж–№йқўпјҢиҜ—дәәеҮәиә«зҡ„ж•Јж–ҮеӨ§е®¶е‘Ёж¶ӣгҖҒдҪң家йҳҝжқҘгҖҒе°ҸиҜҙ家йҹ©дёңпјҢе·Із»ҸжҲҗдёәжҲ‘们зҡ„жҘ·жЁЎгҖӮдёҺз”өи§Ҷз”өеҪұжҺҘиҪЁж–№йқўпјҢй…Қд№җиҜ—жң—иҜөгҖҒиҜ—жӯҢдҪңе“ҒеҲ¶дҪңгҖҒиҜ—жӯҢиөҸжһҗиҠӮзӣ®гҖҒиҜ—дәәдј и®°зұ»еҪұи§ҶзӯүпјҢе·Із»ҸеҒҡдәҶеӨ§йҮҸзҡ„е°қиҜ•пјҢжҲҗж•Ҳжңүзӣ®е…ұзқ№гҖӮдёҺеӨ§дәӢжҺҘиҪЁж–№йқўпјҢеңЁ2008е№ҙеҚ—ж–№йӣӘзҒҫгҖҒвҖң5В·12вҖқжұ¶е·қеӨ§ең°йңҮгҖҒвҖң4В·14вҖқзҺүж ‘еӨ§ең°йңҮе’ҢвҖң8В·7вҖқиҲҹжӣІжіҘзҹіжөҒзӯүйҮҚеӨ§иҮӘ然зҒҫе®ідёӯпјҢдёәжҢҜе…ҙж°‘ж—ҸзІҫзҘһгҖҒе”ӨйҶ’жҠ—дәүж„ҸиҜҶгҖҒе“ҖжӮјйҒҮйҡҫеҗҢиғһпјҢиҜ—жӯҢдјјд№ҺеҸ‘жҢҘеҮәдәҶе®ғзҡ„зңҹжӯЈзҡ„дҪңз”ЁеҸҠж„Ҹд№үгҖӮ
гҖҖгҖҖ
гҖҖгҖҖзҙўжңЁдёңпјҡдҪңдёәеӣҫеҚҡзү№е„ҝеҘіпјҢжҲ‘们зҡ„иЎҖж¶ІдёӯпјҢеӨ©з”ҹжөҒж·ҢзқҖз”ҹд№ӢдәҺж–Ҝзҡ„иҜ—ж„Ҹйҹіз¬ҰпјҒеҲӣдҪңеҚҒе…«е№ҙпјҢдҪ и§үеҫ—жҜҚж—Ҹж–ҮеҢ–е’Ңж•…д№ЎзғӯеңҹпјҢз»ҷдҪ жңҖеӨҡзҡ„жҳҜд»Җд№Ҳпјҹ
гҖҖгҖҖжүҺиҘҝжүҚи®©пјҡжҲ‘еңЁгҖҠдёғжүҮй—ЁгҖӢвҖң第дёҖжүҮй—Ёй—ЁеүҚжҸҗзӨәвҖқдёӯеҶҷиҝҮиҝҷж ·дёҖж®өиҜқпјҡвҖңжқҺеҹҺе…Ҳз”ҹеңЁе…¶иҮӘдј дҪ“ж•Јж–ҮгҖҠж°ёз”ҹдёҺдҪ зӣёдјҙиҖҢиЎҢгҖӢдёӯиҝҷж ·дәӨд»ЈиҮӘе·ұзҡ„ж°‘ж—ҸеҮәиә«пјҡвҖҳжҲ‘зҡ„зҲ¶зі»жҳҜжҳҺ代移民иҖҢжқҘзҡ„жұүж—ҸпјҢиҖҢжҜҚзі»жҳҜеҪ“ең°еңҹи‘—и—Ҹж°‘гҖӮиҜҙжҲ‘зҡ„жҜҚзі»дёәи—Ҹж—ҸпјҢд№ҹеҸӘжҳҜеӨ§жҰӮзҡ„еҪ’зұ»иҖҢе·ІпјҢиӢҘиҰҒеҜ»ж №жәҜжәҗпјҢеҲҷйңҖеӣһеҲ°е…¬е…ғе…«дё–зәӘпјҢйӮЈж—¶еҘ№зҡ„ж—Ҹдәәд№ҹи®ёз§°дёәе…ҡйЎ№жӢ“жӢ”пјҢжҳҜз”ҹжҙ»дәҺйқ’и—Ҹй«ҳеҺҹдёңйғЁпјҢиҮӘе·ұ并没жңүд»Җд№Ҳж°‘ж—ҸеҪ’еұһж„ҸиҜҶзҡ„зү§дәәгҖӮвҖҷеңЁз”ҳеҚ—пјҢеғҸиҝҷж ·зҡ„еңЁж°‘ж—ҸеӨ§иһҚеҗҲйҮҢиҜһз”ҹзҡ„жңүзқҖж–°йІңиЎҖж¶Ізҡ„дәәеӯҗпјҢжҳҜж•°дёҚиғңж•°зҡ„пјҢ他们жҲ–йўҶзқҖжұүж—Ҹиә«д»ҪпјҢжҲ–йўҶзқҖи—Ҹж—Ҹиә«д»ҪпјҢжҲ–йўҶзқҖеңҹж—ҸгҖҒеӣһж—Ҹе’Ңи’ҷеҸӨж—Ҹиә«д»ҪпјҢжІүйқҷиҖҢеқҡйҹ§ең°з”ҹжҒҜеңЁе®үеә·еӨ§ең°дёҠгҖӮвҖқ
гҖҖгҖҖжҲ‘е’ҢжҲ‘зҡ„е…„ејҹе§җеҰ№пјҢдёҺжқҺеҹҺ他们жңүзқҖзұ»дјјзҡ„ж°‘ж—Ҹиә«д»ҪпјҢжҚўеҸҘиҜқиҜҙпјҢжҲ‘们зҡ„иә«дҪ“йҮҢд№ҹжҒ’д№…ең°жөҒеҠЁзқҖи—ҸжұүдёӨиӮЎиЎҖж¶ІгҖӮиҝҷз§ҚеӨҡж°‘ж—ҸиЎҖж¶ІеңЁдёӘдҪ“иә«дёҠзҡ„жӮ„然жұҮйӣҶпјҢдҪҝеҫ—жҲ‘们既йӘ„еӮІпјҢеҸҲж— еҘҲпјҢж— жі•йҖғи„ұе‘Ҫиҝҗзҡ„дё»е®°пјҢжҲҗдёәжёёзҰ»еңЁеҮҶж°‘ж—Ҹд№ӢеӨ–зҡ„еҗҚеүҜе…¶е®һзҡ„иҫ№зјҳдәәгҖӮеҪ“然пјҢжҳҜеҗҰжңүеҮҶж°‘ж—ҸпјҢиҝҷиҝҳжҳҜдёҖдёӘйңҖиҰҒиҖғиҜҒе’Ңе•ҶжҰ·зҡ„й—®йўҳгҖӮ
гҖҖгҖҖ и‘—еҗҚи—Ҹж—ҸиҜ—дәәгҖҒеӯҰиҖ…гҖҒзӨҫдјҡжҙ»еҠЁе®¶жүҚж—әз‘ҷд№іе…Ҳз”ҹеңЁгҖҠи—Ҹж—ҸеҪ“д»ЈиҜ—дәәиҜ—йҖүгҖӢпјҲжұүж–ҮеҚ·пјүеүҚиЁҖдёӯеҰӮжҳҜиҜҙпјҡвҖң(жҲ‘们)жј«жӯҘеңЁеҸӨиҖҒзҡ„еӨ§ең°дёҠпјҢж•Ҹж„ҹең°дјёзј©зқҖиүәжңҜи§Ұи§’пјҢдҪ“е‘ізқҖжёҗжҳҫеҶ°еҮүзҡ„дәәжғ…пјҢж„ҹжӮҹзқҖеӨҡдҪҷдәәгҖҒеұҖеӨ–дәәгҖҒиў«ејӮеҢ–иҖ…зҡ„еҜӮеҜһе’ҢеӯӨзӢ¬пјҢиҝӣиҖҢй©ұзӯ–иҮӘе·ұжҲҗдёәеҝғзҒөж”ҫйҖҗзҡ„жөҒжөӘиҖ…гҖӮвҖқзңҹжҳҜиҝҷз§ҚеҝғзҒөжөҒжөӘиҖ…зҡ„иә«д»ҪпјҢдҪҝжҲ‘жҲҗдёәдёҖдёӘжүҖи°“зҡ„иҜ—дәәгҖӮеҚҒе…«е№ҙжқҘпјҢз”ҹжҙ»еңЁз”ҳеҚ—иҝҷеқ—ж·ұжғ…зҡ„еңҹең°дёҠпјҢжҲ‘з”ЁиҮӘе·ұзҡ„ж–№ејҸеҗҹе”ұзқҖдёҖдёӘиҫ№зјҳдәәзҡ„ж°‘ж—Ҹи®ӨеҗҢд№ӢжӯҢпјҢиЎҖзјҳеҪ’еұһд№ӢжӯҢпјҢиҝҷдәӣжӯҢеЈ°жңүзқҖеҸ‘иҮӘеҶ…еҝғзҡ„еӯӨзӢ¬е’ҢеҜӮеҜһгҖ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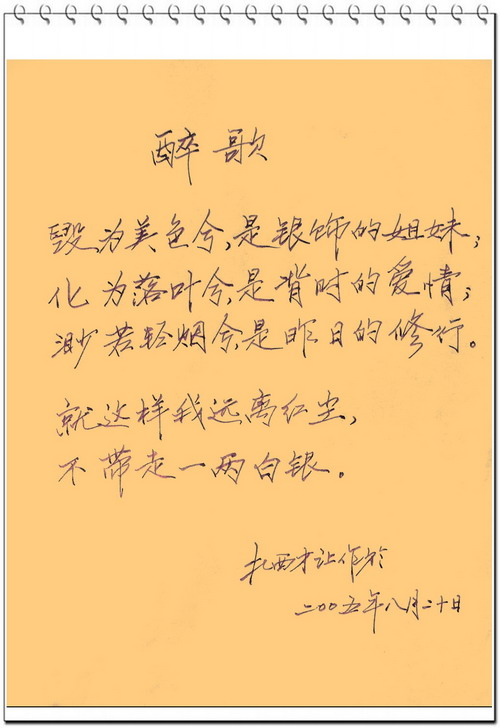
гҖҖгҖҖ
гҖҖгҖҖзҙўжңЁдёңпјҡвҖңж—§дәӢе·ІеҰӮжәӘжөҒпјҢжіЁе…ҘдҪ зҡ„иЎҖж¶Іпјӣж•…ең°е·ІеҰӮзІҫзҒөпјҢеҢ–дёәдҪ зҡ„йӯӮйӯ„гҖӮдҪ зңҹзҡ„иғҪеӨҹиҝңзҰ»еҘ№еҗ—пјҹвҖқе…„ејҹ们жҳҜиҜ»зқҖдҪ дјҳзҫҺзҡ„иҜ—жӯҢжҖҖеҝөдҪ жҶЁеҺҡзҡ„笑容呢пјҢиҝҳжҳҜе’ҢдҪ дёҖиө·иҜ»зқҖдҪ дјҳзҫҺзҡ„иҜ—жӯҢжҖҖеҝөзҫҺеҘҪзҡ„иҜ—жӯҢеІҒжңҲе‘ўпјҹ
гҖҖгҖҖжүҺиҘҝжүҚи®©пјҡеә”иҜҘиҝҷд№ҲиҜҙпјҡи®©жҲ‘们иҜ»зқҖжӣҙеӨҡдјҳз§ҖиҜ—дәәзҡ„дјҳзҫҺиҜ—жӯҢпјҢжҖҖеҝөжҲ‘们зҫҺеҘҪзҡ„иҜ—жӯҢеІҒжңҲпјҒ
гҖҖгҖҖж— и®әжҲ‘们жҳҜеҗҰиҝңзҰ»иҜ—зҘһпјҢжҲ‘们йғҪеә”е…іжіЁдјҹеӨ§зҘ–еӣҪе’ҢеҸӨиҖҒж°‘ж—ҸеҶ…еҝғзҡ„з§ҳеҸІпјҢжҜ”еҰӮж–°ж—¶д»ЈејҖеҲӣиҖ…еүҚиЎҢйҒ“и·ҜдёҠзҡ„жӣҷе…үе’ҢиҗҪж—ҘпјҢзҘһеҘҮеңҹең°дёҠиҜһз”ҹзҡ„зҘһиҜқе’Ңдј иҜҙпјҢдәҳеҸӨй•ҝжІійҮҢй—ӘиҖҖзқҖйҮ‘银е…үиүІзҡ„ж–ӯд»ЈеҸІгҖӮз”ҡиҮіиҝҳеҸҜд»Ҙе…іжіЁдёӘдҪ“зҡ„еҶ…еҝғдҪ“йӘҢпјҢжҜ”еҰӮйӮЈдәӣеҫҖжҳ”ж—ҘеӯҗйҮҢзҡ„зҲұдёҺжҒЁгҖҒжіӘдёҺз—ӣпјҢйӮЈдәӣзҒҝзғӮйҳіе…үе’Ңз§ҳеҜҶжғ…дәӢпјҢйӮЈдәӣеҝғзҒөзҡ„иҪ»еҫ®йңҮйўӨпјҢжҝҖжғ…йҷҚдёҙж—¶иҺ«еҸҜеҗҚзҠ¶зҡ„ж¬ўж„үвҖҰвҖҰи°ҰйҖҠи®Өзңҹең°дҪ“е‘іжҜҸдёҖж®өдәәз”ҹпјҢеңЁзІҫзҘһе’ҢжҖқжғіжҺҖиө·е·ЁеӨ§жіўжөӘзҡ„еӨ§жө·дёҠйўҶеҸ—еҶ…еҝғзҡ„йЈҺжҡҙпјҢжІүйҶүдәҺйӣЁиҝҮеӨ©жҷҙеҗҺзҡ„зҘҘе’ҢдёҺе®үе®ҒгҖӮ
гҖҖгҖҖ
гҖҖгҖҖзҙўжңЁдёңпјҡвҖңд»Җд№Ҳд№ҹжқҘдёҚеҸҠеҒҡ/жҲ‘ж¬ІжҠҪиә«зҰ»ејҖ/е°ұе·ІйҡҸйЈҺйЈҳйӣ¶вҖқвҖ”вҖ”дёҚиҝҮеҘҪеңЁдҪ зҡ„ж–Үеӯ—з•ҷз»ҷдәҶжҲ‘们пјҢз•ҷз»ҷдәҶиҝҷдёӘж—¶д»ЈпјҢиҝҷе·Із»Ҹи¶іеӨҹпјҒ
гҖҖгҖҖжүҺиҘҝжүҚи®©пјҡжҲ‘жҳҜдёӘжӮІи§Ӯдё»д№үиҖ…пјҢеёёеёёи®ӨдёәвҖңжҲ‘зҡ„ж№®жІЎжӮ„ж— еЈ°жҒҜвҖқгҖӮеҜ№дәҺжҲ‘зҡ„иҜ—жӯҢжқҘиҜҙпјҢд№ҹжҳҜеҰӮжӯӨгҖӮеҲӨж–ӯдёҖдёӘдәәзҡ„ж–Үеӯ—жҳҜеҗҰз•ҷз»ҷдәҶдёҖдёӘж—¶д»ЈпјҢйӮЈжҳҜйңҖиҰҒж—¶й—ҙзҡ„иҖғйӘҢзҡ„гҖӮж—¶й—ҙе°ұжҳҜдёҖжқЎжІіпјҢиў«жІіж°ҙеёҰжқҘзҡ„дёңиҘҝпјҢиҰҒд№ҲжјӮжө®дәҺжІійқўпјҢиҰҒд№ҲжІүдәҺжІіеә•пјҢиҰҒд№Ҳиў«ж°ҙзЁҖйҮҠгҖӮжІүдәҺжІіеә•жҲ–иҖ…иў«ж°ҙзЁҖйҮҠпјҢйғҪжҳҜиў«ж·ҳжұ°пјҒиҖҢжө®дәҺжІійқўзҡ„пјҢеңЁжІіж°ҙеҘ”жөҒзҡ„иҝҮзЁӢдёӯпјҢд№ҹжңүзқҖжҲӘ然дёҚеҗҢзҡ„з»“еұҖгҖӮжҲ‘дёҚеҘўжңӣжҲ‘зҡ„иҜ—жӯҢиғҪеӨҹеҫ—еҲ°жөҒдј пјҢеҸӘеёҢжңӣиҝҷдәӣж–Үеӯ—иғҪи®©дәәдә§з”ҹжғ…ж„ҹе…ұйёЈпјҢз»ҷйҳ…иҜ»е®ғзҡ„дәәеёҰжқҘзүҮеҲ»зҡ„и§ҰеҠЁгҖҒж„ҹеҠЁе’ҢжҝҖеҠЁгҖӮиғҪеҒҡеҲ°иҝҷдәӣпјҢжҲ‘е°ұеҝғж»Ўж„Ҹи¶ідәҶгҖӮ
гҖҖгҖҖдҪ зһ§пјҢдҪ з»ҷдәҶжҲ‘дёҖдёӘиҜҙзңҹиҜқзҡ„жңәдјҡпјҒ
гҖҖгҖҖж„ҹи°ўдҪ еҜ№жҲ‘зҡ„йҮҮи®ҝпјҢд№ҹж„ҹи°ўи—Ҹдәәж–ҮеҢ–зҪ‘еҜ№жҲ‘зҡ„е®Јдј дёҺжҠҘйҒ“пјҢжӣҙиҰҒж„ҹи°ўиҜ»иҖ…жңӢеҸӢй•ҝжңҹд»ҘжқҘеҜ№жҲ‘зҡ„е…іжіЁпјҒ
гҖҖгҖҖжңӢеҸӢ们пјҢи°ўи°ўдәҶпјҒ
гҖҖгҖҖ
гҖҖгҖҖдәҢгҖҮдёҖгҖҮе№ҙе…«жңҲе…°е·һ
пјҲж‘„еҪұпјҡжқҺеҹҺпј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