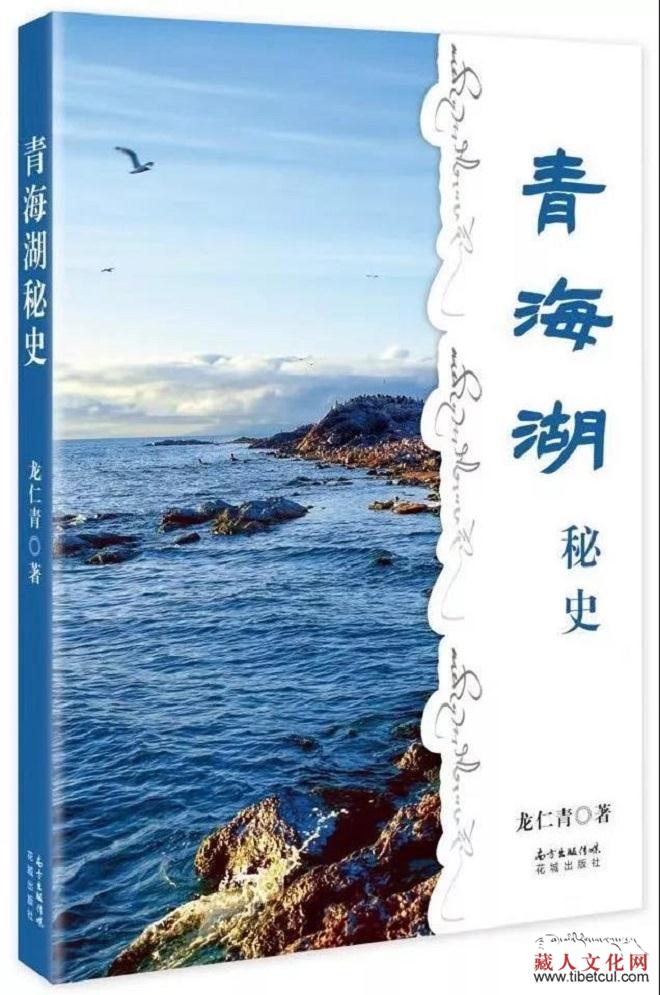
и®° иҖ…пјҡйҫҷд»Ғйқ’иҖҒеёҲпјҢжӮЁеҘҪпјҢжҲ‘们з•ҷж„ҸеҲ°пјҢжӮЁзҡ„дҪңе“Ғдё»иҰҒжңүе°ҸиҜҙгҖҒж•Јж–ҮгҖҒиҜ‘и‘—е’Ңеү§жң¬д»ҘеҸҠдёҖдәӣжӯҢиҜҚзӯүпјҢе®ғ们еӨ§еӨҡжҳҜеӣҙз»•зқҖ“ж•…д№Ў”еұ•ејҖпјҢд»Һе№ҝд№үдёҠжқҘиҜҙпјҢйқ’жө·ж№–е‘Ёиҫ№ең°еҢәе°ұжҳҜжӮЁзҡ„ж•…д№ЎпјҢжӮЁи§үеҫ—ж•…д№ЎеҜ№дёҖдёӘдҪң家жқҘиҜҙж„Ҹе‘ізқҖд»Җд№Ҳпјҹ
йҫҷд»Ғйқ’пјҡе…ҲиҜҙиҜҙжҲ‘еҶҷзҡ„дёңиҘҝеҗ§гҖӮжҲ‘дјјд№Һ并没жңүзү№еҲ«еңЁж„ҸиҝҮжҲ‘зҡ„дҪңе“Ғзҡ„дҪ“иЈҒй—®йўҳпјҢз”ҡиҮіеңЁеҝғйҮҢд№ҹжІЎжңүйў„и®ҫиҝҮд»Ҙд»Җд№Ҳж ·зҡ„дҪ“иЈҒеҺ»еӨ„зҗҶж–Үеӯ—гҖӮе°ҸиҜҙжҳҜиҷҡжһ„зҡ„ж–ҮдҪ“пјҢиҮӘ然иҖҢ然пјҢжҳҜеӣ дёәжҹҗз§Қз»ҸйӘҢгҖҒдҪ“дјҡгҖҒзһ¬й—ҙзҡ„йЎҝжӮҹжҲ–жҖқиҖғгҖӮйңҖиҰҒз”ЁдёҖз§Қиҷҡжһ„зҡ„гҖҒж•…дәӢзҡ„еҪўејҸеҺ»еұ•ејҖпјҢиҝҷе°ұжҳҜе°ҸиҜҙпјҢзү№еҲ«жҳҜдёӯзҹӯзҜҮе°ҸиҜҙд»ҺеҝғйҮҢжөҒжәўиҖҢеҮәж—¶зҡ„ж ·иІҢгҖӮиҖҢж•Јж–ҮпјҢеҲҷжҳҜиҮӘе·ұжүҖи§ҒгҖҒжүҖй—»гҖҒжүҖжҖқгҖҒжүҖеҝҶзҡ„зңҹе®һи®°еҪ•пјҢеҰӮжӯӨпјҢе®ғдёҺе°ҸиҜҙзҡ„дёҚеҗҢеҮ д№ҺжҳҜеңЁдёӢ笔д№ӢеүҚе·Із»ҸеҶіе®ҡдәҶзҡ„гҖӮд№ҹе°ұжҳҜиҜҙпјҢеҶіе®ҡдҪңе“Ғд»Ҙд»Җд№Ҳж ·зҡ„дҪ“иЈҒеҺ»иЎЁзҺ°пјҢжҳҜиҝҷдәӣж–Үеӯ—еңЁе®ғзҡ„иғҡиғҺжңҹе°ұе·Із»ҸеҶіе®ҡдәҶзҡ„пјҢе°ұеғҸжҳҜдёҖдёӘиғҺе„ҝпјҢеҪ“д»–дёәжҲ‘们иҖҢжқҘпјҢжҲ‘们并дёҚиғҪеҶіе®ҡд»–зҡ„жҖ§еҲ«гҖӮеҶҚиҜҙиҜҙзҝ»иҜ‘гҖӮжҲ‘жҳҜеҸҢиҜӯж•ҷиӮІзҡ„еҸ—зӣҠиҖ…пјҢжұӮеӯҰйҳ¶ж®өе°ұжҺҢжҸЎдәҶи—ҸжұүеҸҢиҜӯгҖӮдёҖдёӘжҮӮеҫ—еҸҢиҜӯзҡ„дәәпјҢеӨ©з„¶е°ұжҳҜдёҖдёӘзҝ»иҜ‘иҖ…——еңЁж°‘й—ҙпјҢзү№еҲ«жҳҜеңЁдәҢе…ғжҲ–еӨҡе…ғж–ҮеҢ–并еӯҳзҡ„ең°ж–№пјҢжҜ”еҰӮжҲ‘们зҡ„ж•…д№Ўйқ’жө·пјҢиҝҷж ·зҡ„зҝ»иҜ‘иҖ…жҜ”жҜ”зҡҶжҳҜгҖӮжҲ‘жҺҢжҸЎзқҖдёӨз§ҚиҜӯиЁҖж–Үеӯ—пјҢзҝ»иҜ‘е°ұжҲҗдәҶжҲ‘иҮӘ然иҖҢ然зҡ„дәӢгҖӮд№ӢеүҚд№ҹжңүи®°иҖ…йҮҮи®ҝпјҢй—®еҲ°еҗҢж ·зҡ„й—®йўҳпјҢжҲ‘зҡ„еӣһзӯ”жҳҜпјҢзҝ»иҜ‘жҳҜжҲ‘зҡ„е®ҝе‘ҪгҖӮиҮідәҺеү§жң¬жҲ–иҖ…жӯҢиҜҚеҲӣдҪңпјҢжҲ‘еҸӘжҳҜдёҖдёӘиў«еҠЁзҡ„еҸӮдёҺиҖ…пјҢжүҖд»ҘдёҚеҖјдёҖжҸҗгҖӮ
еҶҚиҜҙиҜҙж•…д№ЎгҖӮеҗҢж ·пјҢеңЁзұ»дјјзҡ„и®ҝи°ҲдёӯпјҢжңүе…іж•…д№Ўзҡ„й—®йўҳд№ҹжҲҗдәҶдёҖдёӘз»Ҹеёёиў«й—®еҸҠзҡ„й—®йўҳгҖӮи®°еҫ—жҲ‘еҲҡеҲҡејҖе§ӢеҶҷдҪңж—¶пјҢеә”гҖҠиҠіиҚүгҖӢдё»зј–еҲҳйҶ’йҫҷе…Ҳз”ҹд№ӢзәҰеҶҷиҝҮдёҖзҜҮеҲӣдҪңи°ҲпјҢйўҳзӣ®е°ұжҳҜгҖҠж–ҮеӯҰпјҡж•…д№Ўзҡ„иөһзҫҺиҜ—гҖӢпјҢеңЁиҝҷзҜҮж–Үеӯ—йҮҢпјҢжҲ‘зҪ—еҲ—дәҶжҲ‘зҡ„ж–Үеӯ—дёҺж•…д№Ўзҡ„иҜёз§Қе…ізі»гҖӮеҺ»е№ҙпјҢдёҠжө·гҖҠж–°йқ’е№ҙгҖӢе‘ЁеҲҠжӣҫд»ҘдёӨдёӘж•ҙзүҲзҡ„зҜҮе№…еҲҠеҸ‘и‘—еҗҚиҜ„и®ә家гҖҒйІҒиҝ…ж–ҮеӯҰеҘ–еҫ—дё»еҲҳеӨ§е…Ҳе…Ҳз”ҹеҜ№жҲ‘зҡ„и®ҝи°ҲпјҢжҲ‘д№ҹи°ҲеҸҠж•…д№ЎгҖӮжҲ‘иҜҙпјҢж•…д№ЎжҳҜйҡҸзқҖдёҖдёӘдәәзҡ„иЎҢиө°пјҢе…¶еӨ–延д№ҹйҡҸд№ӢдёҚж–ӯжү©еӨ§зҡ„жүҖеңЁпјҢе®ғжңҖеҲқзҡ„еҗҢд№үиҜҚжҳҜжҜҚдәІпјҢеҪ“дҪ иө°еҫ—жӣҙиҝңпјҢдҪ дјҡеҸ‘зҺ°пјҢе®ғзҡ„еҗҢд№үиҜҚжҳҜзҘ–еӣҪгҖӮжүҖд»ҘпјҢеҜ№дёҖдёӘдҪң家жқҘиҜҙпјҢж•…д№ЎжҳҜд»–еҶҷдҪңж°ёиҝңзҡ„жҜҚйўҳпјҢжүҖжңүзҡ„еҶҷдҪңйғҪжҳҜд»Һж•…д№ЎеҮәеҸ‘зҡ„гҖӮж–ҮеӯҰпјҢжҳҜж•…д№Ўзҡ„иөһзҫҺиҜ—гҖӮ
еҸҰеӨ–пјҢжҲ‘д№ҹи®ӨдёәпјҢз•ҷдҪҸд№Ўж„ҒпјҢжҳҜеҜ№еҺҶеҸІгҖҒдј з»ҹгҖҒж–ҮеҢ–зҡ„иҝҪжҖқгҖҒ敬йҮҚдёҺ继жүҝгҖӮиҝҷпјҢд№ҹжҳҜд»Һж•…д№ЎеҮәеҸ‘зҡ„гҖӮ
и®° иҖ…пјҡз”ұж•…д№ЎжҲ‘жғіеҲ°дёҖдёӘиҜҚе°ұжҳҜ“еҺҹд№Ў”пјҢиҝҷжҳҜең°зҗҶж–№йқўзҡ„пјҢд№ҹжҳҜзІҫзҘһж–№йқўзҡ„пјҢзәөи§Ӯж”№йқ©ејҖж”ҫд»ҘжқҘзҡ„йқ’жө·ж–ҮеӯҰеҸІпјҢжҸҸеҶҷйқ’жө·зҡ„дҪң家еӨ§дҪ“еҲҶдёәдёӨзұ»пјҢдёҖзұ»жҳҜеӨ–жқҘиҖ…пјҢдёҖзұ»жҳҜжң¬ең°дәәпјҢжӮЁи§үеҫ—иҝҷдёӨиҖ…еңЁж–ҮеӯҰж°”иҙЁдёҠжңүд»Җд№ҲдёҚеҗҢпјҹ
йҫҷд»Ғйқ’пјҡеҰӮжһңд»ҘеӨ–жқҘиҖ…е’Ңжң¬ең°дәәеҲ’еҲҶдҪң家пјҢиҝҷжҳҜдёҖдёӘж”ҫд№Ӣеӣӣжө·иҖҢзҡҶеҮҶзҡ„ж ҮеҮҶгҖӮжҲ‘зӣёдҝЎпјҢдёӯеӣҪжүҖжңүзңҒеҢәзҡ„дҪң家йғҪеҸҜд»ҘеҰӮжӯӨеҺ»еҲ’еҲҶпјҢеҰӮжһңж”ҫзңјдё–з•ҢпјҢдё–з•ҢдёҠдҪң家зҡ„жһ„жҲҗд№ҹжҳҜеҰӮжӯӨгҖӮжүҖд»ҘиҜҙпјҢиҝҷж ·дёӨз§ҚдҪң家еҸҜиғҪ并没жңүжң¬иҙЁдёҠзҡ„еҢәеҲ«пјҢеҸӘиҰҒеҝғжҖҖеҜ№ж–ҮеӯҰзҡ„иҷ”иҜҡпјҢи®ӨзңҹеҶҷдҪңпјҢ他们дҫҝдјҡжӢҘжңүеҗҢж ·зҡ„ж–ҮеӯҰиЎЁиҫҫпјҢиҺ·еҫ—еҗҢж ·зҡ„е°ҠдёҘгҖӮиҜқиҜҙеӣһжқҘпјҢиҝҷж ·дёҖдёӘжң¬дёҚжҳҜй—®йўҳзҡ„й—®йўҳпјҢд№ӢжүҖд»ҘеңЁйқ’жө·иҝҷзүҮеңҹең°дёҠзӘҒжҳҫеҮәжқҘпјҢзәөеҗ‘зҡ„пјҢеҸҜиғҪиҰҒд»Һйқ’жө·ж–ҮеӯҰеҸІзҡ„и§’еәҰеҺ»зңӢеҫ…пјҢжЁӘеҗ‘зҡ„пјҢеҸҜиғҪиҰҒд»ҺеҪ“дёӢйқ’жө·дҪң家йҳҹдјҚзҡ„жһ„жҲҗеҺ»и®ӨзҹҘгҖӮдёҚеҫҖиҝңеӨ„иҜҙпјҢеҚ•еҚ•е°ұйқ’жө·еҪ“д»Јж–ҮеӯҰиҖҢиЁҖпјҢеҸҜиғҪе°ұеӯҳеңЁзқҖдёҖдёӘз”ұеӨ–жқҘиҖ…ејҖеҗҜ——жң¬ең°дәәеҠ е…Ҙ——еӨҡе…ғе…ұеӯҳзҡ„еҸ‘еұ•еҸІпјҢеҰӮд»Ҡйқ’жө·дҪң家йҳҹдјҚеңЁжһ„жҲҗдёҠзҡ„еӨҡе…ғжҖ§пјҢд№ҹдҪ“зҺ°дәҶиҝҷдёҖзӮ№пјҢеҗҢж—¶д№ҹжҳҜеҜ№йқ’жө·иҝҷзүҮеңҹең°дёҠдёҖд»Јд»Јдәәзҡ„ејҖеҸ‘еҸІзҡ„еӣһз…§е’ҢеҸҚжҳ гҖӮ
и®° иҖ…пјҡжӮЁи®ӨдёәпјҢеҰӮжӯӨж·ұеәҰжІүжөёеңЁ“еҺҹд№Ў”д№Ӣдёӯзҡ„жң¬еңҹдҪң家жңүд»Җд№ҲдјҳеҠҝе’ҢеҠЈеҠҝпјҹ
йҫҷд»Ғйқ’пјҡ“еҺҹд№Ў”дёҖиҜҚпјҢжӣҙеӨҡзҡ„жҳҜзІҫзҘһж„Ҹд№үдёҠзҡ„пјҢдҪҶд»Һең°зҗҶж„Ҹд№үдёҠжқҘиҜҙпјҢе®ғд№ҹеҢ…жӢ¬дәҶдёӨеұӮеҗ«д№үгҖӮдёҖеұӮеҗ«д№үжҳҜ“дҪ д»Һе“ӘйҮҢжқҘ”пјҢеҸҰдёҖеұӮеҗ«д№үжҳҜ“жӯӨеҲ»еңЁдҪ•еӨ„”пјҢиҝҷзңӢиө·жқҘжҳҜдёҖдёӘдәәдәәеј еҸЈе°ұиғҪеӣһзӯ”еҮәжқҘзҡ„й—®йўҳпјҢе…¶е®һдёҚ然пјҢз”ҡиҮіеҢ…жӢ¬и®ёеӨҡдҪң家пјҢеҜ№иҝҷдёҖй—®йўҳзҡ„и®ӨзҹҘд№ҹжҳҜзІ—жө…зҡ„пјҢжЁЎзіҠзҡ„гҖӮ“дҪ д»Һе“ӘйҮҢжқҘпјҹ”жҳҜеҜ№иҮӘе·ұиЎҖи„үзҡ„жү§зқҖеӣһжәҜпјҢе°ұеғҸжҳҜдёҖжЈөж ‘жңЁеҜ№иҮӘе·ұе№је°Ҹзҡ„ж №йЎ»зҡ„дҫқжҒӢгҖӮиҖҢ“жӯӨеҲ»еңЁдҪ•еӨ„”еҲҷжҳҜеҜ№иҮӘе·ұдј‘е…»з”ҹжҒҜзҡ„еңҹең°еҝғжҖҖ敬ж„Ҹең°иҶңжӢңпјҢиҝҷз§Қ敬ж„Ҹе’ҢиҶңжӢңз•ҘеёҰеҒҸжү§е’Ңдё»и§ӮпјҢдҪҶд»Һи®ӨзҹҘдёҠеҸҲиҰҒе®ўи§Ӯе’Ңе…ЁйқўгҖӮиҝҷжҳҜдёҖз§Қе……ж»Ўд»ӘејҸж„ҹзҡ„иЎҢдёәгҖӮ
гҖҠдәәж°‘ж—ҘжҠҘгҖӢжө·еӨ–зүҲж–°иҝ‘еҲҠеҸ‘дәҶжҲ‘еҶҷдәҺд»Ҡе№ҙжҳҘиҠӮзҡ„дёҖзҜҮж–Үеӯ—пјҢйўҳзӣ®жҳҜгҖҠйәҰд»ҒзІҘй—ІиҜқгҖӢпјҢзј–иҖ…иҜ„и®әиҜҙпјҢгҖҠйәҰд»ҒзІҘй—ІиҜқгҖӢд»ҺдёҖзў—зІҘиҜҙиө·пјҢи°Ҳзҡ„еҚҙжҳҜж–ҮеҢ–ең°зҗҶеӯҰдёҺж–ҮеҢ–дәӨжөҒеҸІдёҠзҡ„дёҖзі»еҲ—йҮҚиҰҒе‘ҪйўҳпјҡдәәдёҺзҺҜеўғзҡ„еҚҡејҲдёҺж–—дәүпјҢжұҹеҚ—ж–ҮеҢ–дёҺиҘҝеҢ—ж–ҮеҢ–зҡ„е·®ејӮдёҺе…ұйҖҡпјҢдәәзұ»иҝҒеҫҷеёҰжқҘзҡ„ж–ҮжҳҺдәӨжөҒ……дҪңиҖ…з”Ёи§Ғеҫ®зҹҘи‘—гҖҒд»Ҙе°Ҹи§ҒеӨ§зҡ„笔法е°ҶдәәдёҺе‘Ҫиҝҗзҡ„е’Ңи§ЈгҖҒдәәдёҺзҺҜеўғзҡ„е’Ңи°җиҝҷдёҖдё»йўҳйҷ„дёҪдәҺйәҰд»ҒзІҘгҖҒж№ҹйұјгҖҒгҖҠиҢүиҺүиҠұгҖӢзӯүд№ӢдёҠпјҢдәҺеҜ»еёёдёӯи§ҒеҰҷжӮҹгҖӮжҲ‘жғіпјҢеңЁиҝҷзҜҮж–Үеӯ—йҮҢпјҢе…¶е®һеҢ…еҗ«дәҶжҲ‘еҜ№“еҺҹд№Ў”зҡ„и®ӨиҜҶгҖӮ
еҪ“然пјҢеҶҷдҪңеҺҹжң¬е°ұжҳҜйҒ—жҶҫзҡ„иүәжңҜпјҢд»»дҪ•ж–ҮеӯҰж–Үжң¬йғҪдёҚеҸҜиғҪжҳҜе®ҢзҫҺзҡ„гҖӮеҰӮжһңиҰҒиҜҙжң¬еңҹдҪң家еңЁеҶҷдҪңдёҠзҡ„дјҳеҠҝжҲ–еҠЈеҠҝпјҢжҲ‘жғіпјҢе…¶дёӯдёҖзӮ№еҸҜиғҪиҰҒжҠҠжҸЎеҘҪж–Үжң¬дёӯеҜ№жң¬еңҹж„Ҹд№үд№ҰеҶҷзҡ„иӮҶж„ҸжҲ–иҠӮеҲ¶зҡ„й—®йўҳгҖӮ
и®° иҖ…пјҡжӮЁеңЁеҲӣдҪңдёӯжңүжІЎжңүеҲ»ж„Ҹең°ејәи°ғиҮӘе·ұзҡ„ж°‘ж—ҸжҖ§пјҹ
йҫҷд»Ғйқ’пјҡж–°дё–зәӘд»ҘжқҘпјҢж–ҮеҢ–еӨҡж ·жҖ§и¶ҠжқҘи¶ҠеҸ—еҲ°дәә们зҡ„е…іжіЁе’Ңе°ҠйҮҚпјҢд№ҹи¶ҠжқҘи¶ҠзңӢеҲ°иҫ№ең°зҡ„ж—ҸиЈ”ж–ҮеҢ–еңЁж•ҙдёӘдёӯеҚҺж°‘ж—Ҹж–ҮеҢ–дёӯзҡ„еҲҶйҮҸпјҢд»ҘеҸҠиҝҷз§Қж–ҮеҢ–дёӯзҡ„“дёӯеӣҪе…ғзҙ ”гҖӮдёӘдәәи®ӨдёәпјҢж–ҮеӯҰдёӯзҡ„ең°ж–№жҖ§е’Ңж°‘ж—ҸжҖ§пјҢеңЁдёҖе®ҡзЁӢеәҰдёҠеҸҜд»ҘжҲҗдёәдёҖз§Қж Үеҝ—пјҢдҪҝеҫ—дҪң家зҡ„дҪңе“Ғе‘ҲзҺ°еҮәдёҖз§ҚејӮиҙЁж°”иҙЁпјҢд»ҺиҖҢд»Һдј—еӨҡзҡ„д№ҰеҶҷдёӯи„ұйў–иҖҢеҮәпјҢжҲҗдёәдҪңе“ҒжүҖзү№жңүзҡ„жҳҫиҖҢжҳ“и§Ғзҡ„иҫЁиҜҶеәҰгҖӮдҪҶжҳҜпјҢеҰӮжһңдҪңе“ҒдёҖе‘іжІүж№ҺдәҺж°‘ж—Ҹең°еҹҹзҡ„иЎЁиҫҫпјҢеҸҜиғҪдјҡдҪҝдҪңе“ҒйҷҗдәҺжҹҗз§ҚзӢӯйҡҳзҡ„иҜӯеўғд№ӢдёӯпјҢзјәе°‘ејҖж”ҫжҖ§гҖӮжүҖд»ҘпјҢдё–з•ҢжҖ§зҡ„ејҖж”ҫжҖҒеҠҝе’Ңж°‘ж—Ҹең°еҹҹиЎЁиҫҫзҡ„еҗҲзҗҶз»“еҗҲпјҢеҸҜиғҪжҳҜиҝҷдёӘж—¶д»ЈеҜ№дҪң家зҡ„иҰҒжұӮпјҢд№ҹжҳҜдҪң家дёӘдәәзҡ„дёҖз§ҚиҝҪжұӮгҖӮ
жҲ‘еҮәз”ҹеңЁйқ’жө·пјҢеңЁйқ’жө·еҶҷдҪңпјҢең°ж–№жҖ§жҲ–ж°‘ж—ҸжҖ§жҳҜиҮӘе°Ҹе°ұжІҫжҹ“еңЁжҲ‘зҡ„иә«дҪ“е’ҢеҝғзҒөдёҠзҡ„пјҢжүҖд»ҘпјҢжҲ‘зҡ„дҪңе“ҒжүҖе‘ҲзҺ°еҮәжқҘзҡ„ж°‘ж—Ҹең°еҹҹзү№зӮ№пјҢжқҘиҮӘжҲ‘зҡ„иӮүдҪ“е’ҢеҶ…еҝғпјҢиҮӘ然иҖҢ然пјҢдёҚз”ЁеҲ»ж„Ҹејәи°ғгҖӮ
и®° иҖ…пјҡгҖҠйқ’жө·ж№–з§ҳеҸІгҖӢйӣҶеҗҲдәҶж–ҮеҸІгҖҒдәәж–ҮгҖҒиҮӘ然зӯүдё°еҜҢеҶ…е®№пјҢиҖҢжҲ‘д№ҹд»ҺдёӯзңӢеҮәдәҶиҮӘ然ж–ҮеӯҰеҶҷдҪңзҡ„еҖҫеҗ‘пјҢз»“еҗҲжӮЁжӯӨеүҚеҸ‘иЎЁзҡ„ж•Јж–ҮдҪңе“ҒпјҢиҝҷж ·зҡ„еҚ°иұЎеҸҳеҫ—е°Өдёәж·ұеҲ»пјҢиҝҷжҳҜжӮЁжңүж„Ҹдёәд№ӢпјҢиҝҳжҳҜж— ж„Ҹй—ҙзҡ„е·§еҗҲпјҹ
йҫҷд»Ғйқ’пјҡеҰӮжһңиҜҙпјҢдёҖзҷҫеӨҡе№ҙеүҚе…ҙиө·дәҺзҫҺеӣҪзҡ„иҮӘ然ж–ҮеӯҰеҶҷдҪңпјҢйҒҮеҲ°дәҶе®ғеҫ—д»Ҙж»Ӣй•ҝдёҺеҸ‘жү¬зҡ„дёҖдёӘз»қеҘҪзҺҜеўғ——иҝҷдёӘзҺҜеўғе…¶е®һжҳҜйӮЈд№Ҳзіҹзі•——еңҹең°жұЎжҹ“гҖҒз”ҹжҖҒз ҙеқҸпјҢиҮӘ然иө„жәҗи¶ҠжқҘи¶ҠдёҚиғҪж»Ўи¶ідәәзұ»зҡ„йңҖжұӮпјҢеҜ»жүҫејҖеҸ‘ж–°зҡ„家еӣӯеҠҝеңЁеҝ…иЎҢпјҢиҖҢиҝҷеҸҲеј•иө·ж–°дёҖиҪ®зҡ„жұЎжҹ“гҖҒз ҙеқҸ……дәҺжҳҜпјҢжўӯзҪ—гҖҒзәҰзҝ°·е·ҙеӢ’ж–ҜиҝҷдәӣдҪң家дёӯзҡ„е…ҲзҹҘеҮәзҺ°дәҶпјҢ他们зңӢеҲ°дәҶжҜ”ејҖеҸ‘жӣҙдёәйҮҚиҰҒзҡ„дёңиҘҝпјҢйӮЈе°ұжҳҜеҜ№иҮӘ然зҡ„зңӢйҮҚе’ҢдҝқжҠӨгҖӮжҜҸжҜҸжғіиө·зҫҺеӣҪиҮӘ然ж–ҮеӯҰеҶҷдҪңзҡ„е…ҙиө·пјҢжҲ‘е°ұдјҡжңүдәӣж„ҹж…ЁпјҢ他们жүҖз»ҸеҺҶзҡ„пјҢдёҺеҰӮд»Ҡйқ’жө·жүҖз»ҸеҺҶзҡ„дҪ•е…¶зӣёдјјпјҒеҘҪеңЁпјҢз”ҹжҖҒж–ҮжҳҺе»әи®ҫе·Із»ҸжҳҜйқ’жө·дёҠдёӢе…ұеҗҢзҡ„и®ӨзҹҘпјҢ“дёҖдјҳдёӨй«ҳ”жҲҳз•Ҙзҡ„жҸҗеҮәпјҢжӣҙеҪ°жҳҫеҮәйқ’жө·еҜ№иҮӘ然з”ҹжҖҒдҝқжҠӨзҡ„дҝЎеҝғдёҺеҶіеҝғгҖӮеҜ№дҪң家иҖҢиЁҖпјҢжҸҸж‘№йқ’жө·еӨ§ең°пјҢд»ҘеҸҠеӨ§ең°дёҠзҡ„иҠұиҚүдёҺйёҹзҰҪпјҢд№ҹжҳҜдёҖз§Қд№үдёҚе®№иҫһзҡ„иҙЈд»»е’ҢжӢ…еҪ“гҖӮ

йҫҷд»Ғйқ’пјҢе°ҸиҜҙ家гҖҒзҝ»иҜ‘家гҖӮ1967е№ҙеҮәз”ҹдәҺйқ’жө·ж№–з•”гҖӮдёӯеӣҪдҪңеҚҸдјҡе‘ҳгҖҒйқ’жө·зңҒдҪңеҚҸеүҜдё»еёӯгҖҒйқ’жө·зңҒгҖҠж јиҗЁе°”гҖӢе·ҘдҪң专家委е‘ҳдјҡ委е‘ҳгҖҒйқ’жө·зңҒж°‘ж—Ҹж–ҮеӯҰзҝ»иҜ‘еҚҸдјҡеүҜдјҡй•ҝе…јз§ҳд№Ұй•ҝгҖӮеҲӣдҪңеҮәзүҲжңү“йҫҷд»Ғйқ’и—Ҹең°ж–Үе…ё”пјҲдёүеҚ·жң¬пјүгҖҒе°ҸиҜҙйӣҶгҖҠе…үиҚЈзҡ„иҚүеҺҹгҖӢгҖҠй”…еә„гҖӢзӯүпјӣзҝ»иҜ‘еҮәзүҲжңүгҖҠеҪ“д»Ји—Ҹж—ҸжҜҚиҜӯдҪң家代表дҪңйҖүиҜ‘гҖӢгҖҠз«Ҝжҷәеҳүз»Ҹе…ёе°ҸиҜҙйҖүиҜ‘гҖӢгҖҠд»“еӨ®еҳүжҺӘиҜ—жӯҢйӣҶгҖӢгҖҠеұ…•ж јжЎ‘зҡ„иҜ—гҖӢеҸҠгҖҠж јиҗЁе°”гҖӢеҸІиҜ—йғЁжң¬гҖҠж•Ұж°Ҹйў„иЁҖжҺҲи®°гҖӢгҖҠзҷҫзғӯеұұзҫҠе®—гҖӢзӯүгҖӮжӣҫиҺ·дёӯеӣҪжұүиҜӯж–ҮеӯҰ“еҘіиҜ„委”еӨ§еҘ–пјҢ第дә”еұҠйІҒиҝ…ж–ҮеӯҰеҘ–жҸҗеҗҚгҖ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