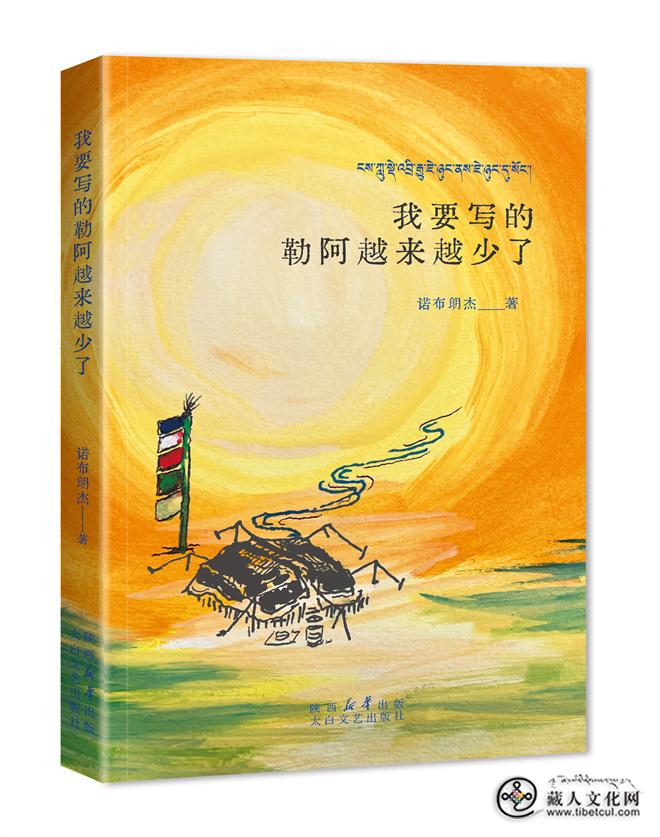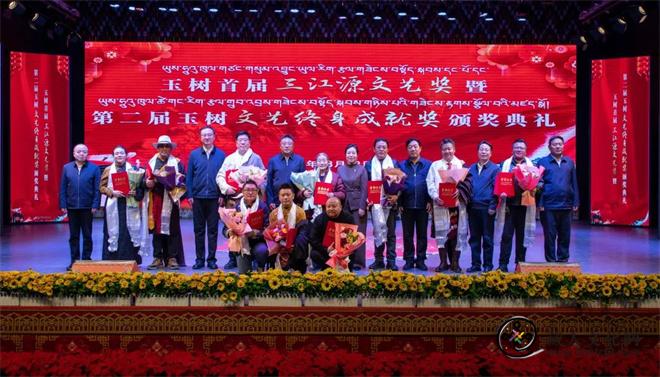《从梭磨河出发》
《从梭磨河出发》
在不少人的印象中,作家阿来是以写小说著称,他的长篇小说《尘埃落定》广为人知。但熟悉他的人知道,阿来的文学之路是从诗歌开始的。诗歌为其后来的小说创作铺陈了道路,这也正是阿来的小说在当代文学中独具语言和哲思魅力的缘由之一。近日,阿来全新整理的诗集《从梭磨河出发》,由浙江文艺出版社·KEY-可以文化推出。
这本诗集是迄今为止收录阿来诗歌数量最多的一本,其中第一辑的内容是作者1991年由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的第一本个人诗集《梭磨河》,第二辑与第三辑选自2016年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阿来的诗》,在此基础上第四辑增加收录了阿来早年发表在地方杂志等读物上的作品。诗集收录了包括《风暴远去》《这时是夜》《群山,或者关于我自己的颂词》《灵魂之舞》等风格鲜明的作品。这些诗歌通过优美的语言和流畅的叙事展现了辽阔寂静的高原生活,以质朴真挚的笔触抒发了阿来对祖祖辈辈生活的土壤以及大自然的敬畏与热爱。
“我的书写从梭磨河出发”
作为一名来自阿坝州的诗人,川西高原一直是阿来作品灵感的来源,阿来在他的诗中极力守护民族文化的根脉,在将自己完全融入这片充满生机和惊喜的大地的同时,带给读者独特深邃的阅读体验。这也是他在创作中一直努力寻找的答案。诗中永恒飘扬着嘉绒藏族村落的经幡,回荡着俄比拉尕深广渺远的歌谣,矗立着延绵不绝的群山。故乡的梭磨河水在文字的血液中不息流淌,流向阿来永恒的精神原乡。
在介绍“梭磨河”的时候,阿来曾说:“梭磨河是我家乡的河流,是我喝着它的水长大的河流,这条河是大渡河的上源之一,大渡河后来流入岷江,岷江流入长江,一直奔流到上海,这是河流之地。我就在那样一个有雪山、有草原、有森林的地带长大,当然我的书写就是以这里作为出发点。”
阿来的诗歌从梭磨河出发,他在诗里也多次提及自己出生、成长的村庄与河流,“梭磨河/梭磨河/我拆读你辗转而来的信札”(《信札》),他以诗歌的形式将这片高原上的故事娓娓道来,奔跑的白马与牦牛,游弋的天鹅,生长着的野樱桃,无不充满着原始的生命张力。
文学评论家黄德海品读这本诗集后,作出这样的评价:“我一下子回到了当时诗歌热的感觉。阿来的诗再往前追溯可以是李白,中国的诗有吟诵的传统。阿来诗中的意象可以和我们共振。抒情诗就是一种共振的传统。”
“把写作带向更广义的诗”
谈到自己写诗最初的契机,阿来说:“那个时候我身边有一帮专业不同的年轻教师,他们都在写作,也经常互相评判。我经常读杜甫、苏轼,于是口出狂言说‘你们写得不好’,但他们不服气。我那时年轻好胜,就和他们打赌写了两首诗,确实比他们写得好,他们还帮我投稿,年轻人的虚荣心就得到了鼓励。”而后自己写诗的过程,其实是一种对“文学”的摸索,从很大程度上直接影响了写作生涯。阿来提到:“我的诗歌其实是一个游戏,但没想到这个游戏把我带到了一个严肃的世界,那就是文学。我们年轻时在摸索不同的方向,也是探索人生的可能性。”
正是经过这种探究式的自我审视,在出版了诗集《梭磨河》和短篇小说集《旧年的血迹》之后,阿来开始思考该如何实现对“作家身份”的自我认同。有很长一段时间阿来并没有急于投入新作品的写作,而是选择了回归“土地”去寻找答案,去体验、感受自己跟时代、文化、族群的关系。在这个过程中阿来逐渐体会到了人与地域和自然交融、“天人合一”的感应,感受到了地域和文字之间不可消磨的连结。
写完《三十周岁时漫游若尔盖大草原》这首诗,阿来决定不再写诗了,“因为我觉得今天的社会面对的是更复杂、更丰富的存在和表达对象。”但阿来诗情并未泯灭,只是被转移了,他说:“我从来不敢忘记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说过这样的话:诗比历史更接近于哲学,更严肃。因为诗所说的比历史更带有普遍性,而历史所说则是个别的事。我要把我的写作带向更广义的诗。”
阿来的诗歌从梭磨河开始,由若尔盖草原结束,此后他开始了长篇小说的创作,创作出了《尘埃落定》《机村史诗》《云中记》等作品。即使现在他已经不再创作诗歌,但从他后来的小说、散文里还是能感受到那种独有的诗的思维、诗的表达、诗的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