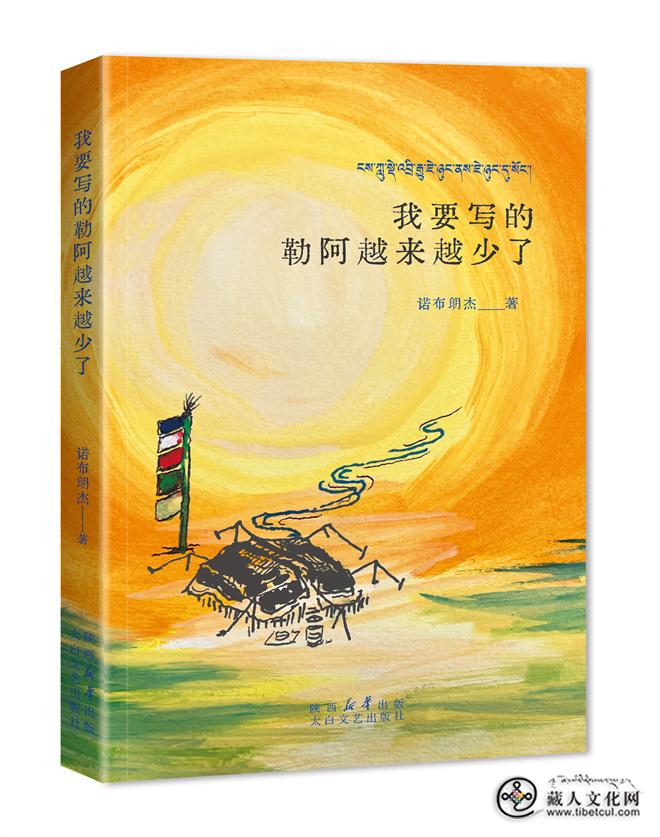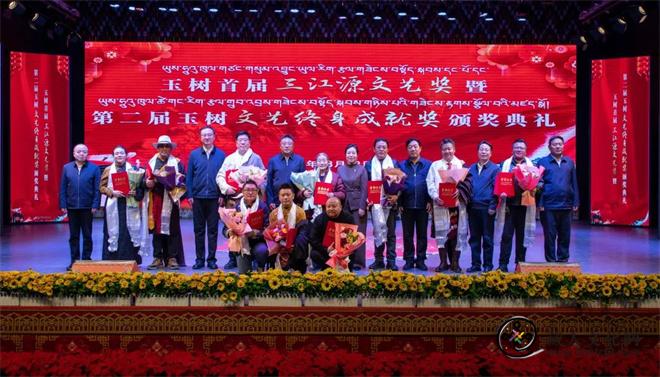2019年,阿来60岁时重新漫游若尔盖大草原。
2019年,阿来60岁时重新漫游若尔盖大草原。
9月4日,著名作家阿来在贵州遵义获得一个特别的文学奖项——首届十二背后·十月“美丽中国”生态文学奖,他荣膺“年度杰出作家”的称号。该奖项旨在鼓励作家们在古今中西的框架里讲好生态文明的中国故事和当代故事,为全球生态命运共同体建设贡献中国文化主体想象。
阿来一直是生态书写的先行者。他不断在写作实践中表达自己对生态问题的思考,传递自己对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探索。他笔下的生态文学作品每一部都备受关注:《成都物候记》,与《瓦尔登湖》相媲美;《蘑菇圈》《河上柏影》《三只虫草》这个“山珍三部曲”,被誉为“生态文学的典范”;再到《云中记》,本届“生态文学奖”的授奖词如此评价:“生与死、物与我、山川与身体、自我与他们、内部与外部,重新联结起来,成为一个完整、绵延、浑然交融的存在,天人合而为一,人与自然相亲无别……”
事实上,早在《云中记》之前,阿来还有一部体量更大、分量更重的生态文学著作。它,就是今年7月,由浙江文艺出版社“KEY-可以文化”重磅推出的《机村史诗》(六部曲)。从2005年开始陆续出版,时隔16年,历经时间洗涤,这部意蕴悠长的巨作静静散发着光芒,在这个崭新的日子再次翻开。
承前启后的“史诗”
构建立体式的藏族乡村图景
20多年前,阿来以代表作《尘埃落定》带领万千读者领略了土司家族的激荡风云;之后,斩获茅盾文学奖的他又带来了另一座文学高峰——《机村史诗》(六部曲)。《机村史诗》被认为是阿来继《尘埃落定》之后最重要的作品,在阿来自己心中也拥有不可比拟的地位。阿来说,《机村史诗》是他投入心血最多、比《尘埃落定》更令自己满意的作品。
《机村史诗》(六部曲),依序分为《随风飘散》《天火》《达瑟与达戈》《荒芜》《轻雷》《空山》六部相对独立又彼此衔联的小长篇。每部小长篇之后,各附有一则“事物笔记”与一篇“人物素描”,分别讲述有关新事物的故事,以及与新社会相适应或不相适应的代表性人物的故事。不同于一气呵成的传统长河式结构,阿来用花瓣式立体结构编织出恢宏而细腻的《机村史诗》;小说的主角不是固定的某个个人,而是“变化的”、破碎后不断重组的村庄。谈及小说的特殊结构,阿来说:“花瓣是空间的,向心的。而编年史是线性的,有始无终的。”这部关于一座藏族村庄的当代编年史,不仅在内容上反映出中国乡村变迁的真实图景,形式上亦与乡村星火般的发展进程相贴合。
在《机村史诗》中,阿来延续自己独树一帜的风格,以宏大的视野、独特的视角、诗性的语言,述说山村藏族人民世世代代的生活。《尘埃落定》故事的发生时间为20世纪上半叶,《机村史诗》则讲述发生于20世纪下半叶的故事,这两部作品紧密相连,构成一个整体。如果说《尘埃落定》为旧时代画上了句号,《机村史诗》则无疑为新时代的来临和行进书写下一串引人深思的问号、叹号,并留下意味深长的省略号。旧制度解体后,机村被纳入崭新的社会体制。这个曾深藏于大山褶皱里的古老村落,随着一次次开垦与开发暴露在轰轰烈烈的时代洪流中,迎接着外来人、新鲜事物,也承载着故人的归来与离开。以20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为背景,阿来将笔锋对准一个个小人物,以机村为舞台,刻画乡村里细微的人物与事件,以小见大,着力呈现普通乡人的生活、情感和历史,由此拼合、构建出一幅立体式的藏族乡村图景。
上下五十年
史诗的本质是为普通人而歌
《机村史诗》的创作关键词可以说是“人”与“变”。包含了6个主要故事、12篇特写故事的《机村史诗》,着力书写的主要人物有将近30个。从《随风飘散》到《空山》,随着时间的步伐,孩童步入壮年,曾经的年轻人成为行将告别的老者,故事的中心人物不断变换。散落在各处的小人物,在不同事件中各自扮演主角,轮番站在舞台的聚光灯下。面对“这么凶,这么快”的时代,巨变之中,不同角色做出不同抉择,迎向截然不同的命运。这部小说不是“旧乡村的一曲挽歌”,阿来说:“我不是一个一味怀旧的人,而是深知一切终将变化。我只是对那些为时代进步承受过多痛苦、付出过多代价的人们深怀同情。因为那些人是我们的亲人、同胞,更因为他们都是和我们一样的——人。”
人,一直是阿来书写的重点。他曾说:“人是出发点,也是目的地。”他始终在思考,如何去写人、如何去写出人在历史当中的命运。在他的心目中,小说的本质就是写“人”本身,史诗的本质就是为普通人而歌。在《机村史诗》中,一个个普通人轮番登场,继《尘埃落定》之后,阿来又搭了一个舞台,舞台上有一扇门,这些人一个个推门进来:恩波、索波、多吉、老魏、格桑旺堆、格拉、桑丹、达瑟、达戈、拉加泽里、李老板、色嫫、驼子等等,他们在阿来给的这个舞台,行动、思想、欢乐、痛苦……发生关系,发生冲突,然后就有了《机村史诗》这幕大戏。“50年,6本书,其实正是中国不同乡村阶段的特色的总结。”阿来如是说。
机村的“机”,在藏语里的意思是“种子”“根子”,诚如阿来所言,乡村是所有中国人的根。通过对具体而微的乡村人事变化的呈现,包括人心的异动、信仰的消弭、村庄的散落、古朴自然景观的消失等等,阿来想要为之立传的,不仅仅是历经半个世纪社会变革涤荡的“机村”本身的历史;他想描绘的,也不仅仅是“机村”所象征的藏族乡村在历史大潮冲击下失落的文化风情画;他想要刻画的,是处在社会变革带来的痛苦和希望交替冲击之下的乡人;他想要记录的,是被裹挟在全球城市化浪潮中、反复遭遇断裂和重组的最为广大的中国乡村。所以,阿来在表述为何写下这部长篇巨著时曾直言:“中国乡村在那几十年经历重重困厄而不死,迎来今天的生机,确实也可称为一部伟大的史诗。”
按下云头作出担当
从空间到时间的双重纵深
当年《机村史诗》横空问世,名字还叫《空山》时,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文学评论家李敬泽公开表示:“我认为《空山》比《尘埃落定》写得好:《尘埃落定》写藏族的人与事,我们或许觉得那就是我们想象的藏族——神的、半神半人的世界;而《空山》写藏族乡村,阿来按下云头,写了人的世界。人有大有小,但终究都是人,承受着与我们内容相同、但前提和节奏不同的现代历史。画神容易画人难,《空山》比《尘埃落定》难。”
“第七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杰出作家奖”给阿来的授奖词,精确道出了《机村史诗》的写作要旨:“阿来是边地文明的勘探者和守护者。他的写作,旨在辨识一种少数族裔的声音以及这种声音在当代的回响。阿来持续为一个地区的灵魂和照亮这些灵魂所需要的仪式写作,就是希望那些在时代大潮面前孤立无援的个体不致失语。”
近日,文学评论家张学昕与梁海合著的《阿来论》出版。在该书中,张学昕特别撰写了《孤独“机村”的存在维度——阿来〈空山〉论》来深度剖析《机村史诗》。张学昕认为,在这部长篇小说中,阿来做出了自己情感和精神的担当,这种担当不是对现实的某种修饰,而是对未来的一种祈愿,更重要的是,阿来发现了中国乡村自己生存的时间和空间。张学昕着重提到了阿来的一段话:“这个世界还有一个维度叫时间。在大多数语境中,时间就是历史的同义词。历史像一个长焦距的镜头,可以一下子把当前推向遥远。当然,也能把遥远的景物拉到眼前,近了是艰难行进的村子,推远了,依然是一派青翠的空山。”张学昕直言:“可以这样讲,这种表述,体现为阿来的写作从空间到时间上的一次双重的纵深,这不仅是对中国乡村未来的一个纵深,也是阿来对这个民族和整个时代的一种精神纵深,是对急剧变化的世界及其存在方式的倾心叙述、诠释和想象的重建。”
访谈
来问“来”答
《机村史诗》是什么?
一座村庄的当代编年史
阿来:这是一座村庄的当代编年史,从上个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这半个世纪,中国进行了史无前例的社会实验——从政治到经济。这场实验,改变人,也改变社会面貌。中国乡村,在国家版图上无论是紧靠中心还是地处僻远,都经历了革命性变革,与种种变革带来的深刻涤荡。我自己出生于一个偏远的村庄,在处于种种涤荡的、时时变化的乡村中成长。每一次变革都带来痛苦,每一次变革都带来希望。即便后来拜教育之赐离开了乡村,我也从未真正脱离。因为家人大多都还留在那里,他们的种种经历,依然连心连肺。而我所能做的,就是为这样的村庄写下一部编年史。
谈《机村史诗》的启示
把森林山野还给自然
阿来:乡村在时代变迁中,付出的另一个代价,是自然环境的毁败。这也是中国普遍现实之一种。在我写下的机村故事中,有大量篇幅,都涉及森林的消失。离开故乡后,有很多年,我都不情愿回到故乡的村子。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不忍心看到那些森林的消失,山野的荒芜。当年,涉笔这些森林的毁败时,我心里的痛楚,甚至会比写下乡亲们艰难的生活更为强烈。但在上世纪90年代末,中国社会从政府到民间对此都有了足够的警醒。所以,小说里有了一个人物,一个毁败过森林,又开始维护森林的人物。这是乡村的一种自我救赎。这是一直处于被动状态中的乡村的觉醒。我很高兴捕捉到了这样的希望之光。这是我真实的发现,而非只是为小说添上一个光明的尾巴。
谈《机村史诗》的更名
机村不“空”史诗不死
阿来:首版的时候,《机村史诗》叫《空山》。这名字总让人想起王维的诗,但我写下这个名字时并没有那么从容闲适的出世之想。那时的现实还让人只看到破碎的痛楚,而不是重构的蓝图。好多时候,“空”都是一种精神安慰。之后打算重版此书时,我更看到那些艰难过程的意义。所以,才给这部小说一个新的名字:《机村史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