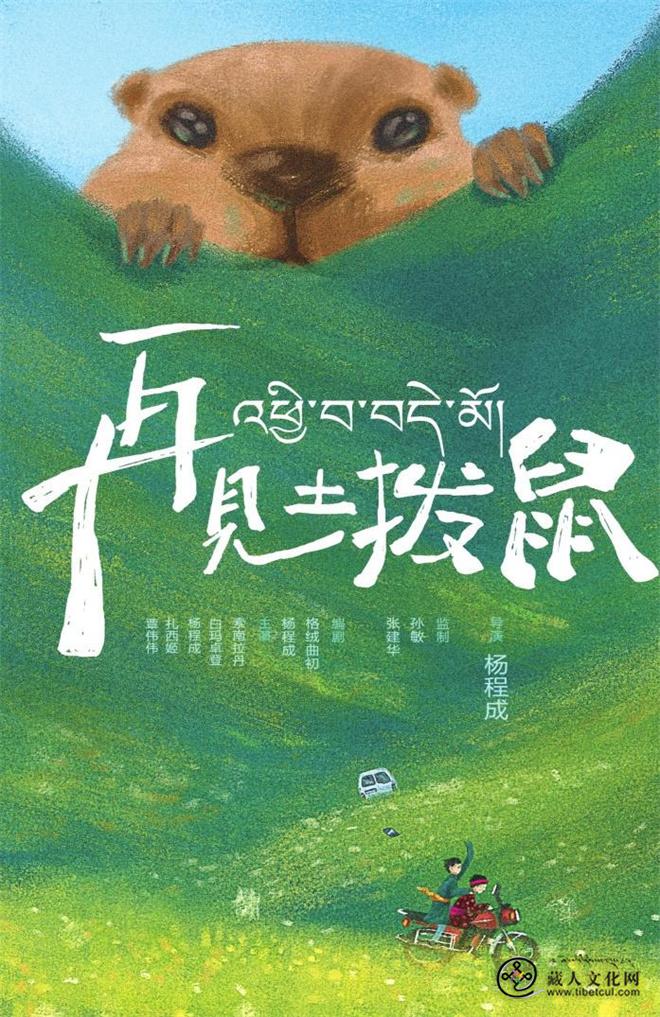摄影:觉果
摄影:觉果
摘要:“藏地新浪潮”电影坚持从民族主体性出发,实现了藏地景观及文化的“祛魅”,显现出极具辨识度的群体化风格。其在主题指向上,探讨困顿心灵、生命意义以及父子关系;在人物塑造上,塑造矛盾的男性、隐忍的女性以及天真善良的孩童形象;在叙事策略上,强调开放式结局、对偶式寓言以及“去奇观化”影像“藏地新浪潮”电影使藏地摆脱了长期以来的魅影化想象,为我国其他少数民族电影的发展提供借鉴。
关键词:“藏地新浪潮”;祛魅;文化寓言;少数民族电影
学界普遍认为万玛オ旦于“2005年制作的《静静的嘛呢石》是真正意义藏语电影的诞生”,该片以生活化的故事、原生态的景观、纪实化的视听,开启了’’藏地新浪潮”的先河。2005年至2011年,作为''藏地电影第一人”的万玛オ旦又相继拍摄了《寻找智美更登》《老狗》,与其处女作《静静的嘛呢石》并称“藏地故乡三部曲”。不过,此时的“藏地新浪潮”还处于雏形期,尚未形成鲜明的群体化风格。2011年,长期担任万玛オ旦团队摄影师的松太加,受万玛オ旦的影响,跨界执导了他的首部长片《太阳总在左边》。这部电影的题材类型与创作手法延续了万玛オ旦前三部电影的风格,在影像上进行了风格化探索,比如有意识地疏离大景别,转而借助小景别突显人的心灵困境等。此后,在万玛オ旦、松太加的合力影响下,拉华加、达杰丁增、德格オ让、西德尼玛、久美成列等人纷纷加入到藏地电影“祛魅”的创作队伍,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藏地新浪潮”。“藏地新浪潮”目前呈现出“花开三朵,各表一枝”的局面:安多藏区起步最早、发展最快,其它两大藏区虽显逊色,但也受前者影响呈发カ势头,像甘孜藏区的导演热贡•多吉彭措、阿岗・雅尔基、旦真旺甲等,卫藏藏区的导演扎西才加等都是这一时期涌现出来的杰出电影人。
21世纪以前的藏地电影多为外族人拍摄,由于藏地特殊的地理环境、民俗信仰以及民族文化间的差异,藏地常被建构、圣化为“一个难以抵达的、想象中的乌托邦”,或曰“一个魔幻、神秘和充满了灵性和魅力的地方”。聚焦宏大的藏地史诗传奇、伟岸的英雄模范、神秘的宗教仪式以及其镜头下自然景观、日常生活及民俗文化等常被''奇观”所笼罩,似乎构成了这一时期''藏地电影”在叙事路径和视听建构上“想象藏地”“凝视藏地”的刻板范式。21世纪以来的“新藏地电影”,亦即“藏地新浪潮”电影,主创团队基本由藏族人构成,他们更多的从民族主体性出发,不加修饰地呈现着藏地自然景观,探寻本民族的故事文本与文化记忆,试图通过“摆脱落后的补充、依附角色,以更具民族独特品质格调的姿态”,达到正本澄源的,“去东方主义化”的“作者表达”。它在主题指向上,多探讨困顿心灵、生命意义以及父子关系;在人物塑造上,多塑造矛盾的男性、隐忍的女性以及天真善良的孩童形象;在叙事策略上,强调开放式结局、对偶式寓言以及“去奇观化”影像。恰如饶曙光所言,“藏地新浪潮”始终是“独语而非众生喧哗,执著于面向内心的探寻”。
一、多元化主题指向
“藏地新浪潮”电影多聚焦心灵困境、生命意义以及父子关系,展现普通藏族人如何对困顿心灵予以救赎、对生老病死予以释然,以及同父辈达成和解。这些颇具共性的主题指向是藏族人民的处世哲学,更是他们共同的文化缩影与精神希冀。
(一)困顿心灵的救赎
“藏地新浪潮”电影关注人的精神困境与心灵救赎。电影主人公都不同程度地面临着“某种解不开的情感困境,这些困境来自于普通家庭的内部,而非社会的外在压カ”。因此,其故事大都是悲剧。导演对结局的“理想化”处理,体现了小人物的困顿心灵得以救赎,散发着浓厚的人文关怀。
《撞死了一只羊》前半部分主要展现了两种心灵困境:杀手金巴因放弃复仇,带着“耻辱”离开小镇;司机金巴因无意撞死一只羊,带着“愧疚”前往寺庙。而在结尾部分,导演又巧妙地通过一场梦境救赎了这两个同叫金巴的人。梦境中司机金巴替杀手金巴手刃仇人,此举不仅洗刷了杀手金巴的耻辱、解脱了杀人者玛扎罪恶的一生,也救赎了自我——眼前浮现出羊在天葬台被秃鹫分食的场面。难以挣脱的精神困境、象征性的心灵救赎,使得金巴二人构成了一体两面的双生关系。万玛オ旦镜头下的这对“双生角色皆在神性的召唤之下深刻地感受到你与他人、生与死以及爱与忍耐的一体两面性,进而从世间互生互长的二元关系之中抽离并秉持神性步入超越之境”。《红丝带》中梅朵是一名艾滋病患者,被集体视为异质性个体。村民的冷眼、丈夫的抛弃、家人的咒骂,使得梅朵内心极度灰暗,为此她用一条红围巾将自己全副“武装”。这里的红围巾俨然成了“人体的延伸”,是犹如面具般的符号,带有逃避现实的情绪指涉意义。不过,导演达杰丁增对梅朵灾难世界的刻画止步于此,给予了她足够的温暖关怀。梅朵的儿子小多吉的艾滋病毒(HIV)检测结果呈阴性,村民见到梅朵不再捂住口鼻,出走多年的丈夫回心转意,而梅朵也将裹在头上的红围巾换成了佩在胸前象征希望的红丝带(艾滋病的国际符号)。藏族导演们在用审视的眼光关注个体的生存境遇与心灵困境的同时,也以人文关怀的态度给予着他们温暖的力量,它是能够在精神层面救赎藏地小人物困顿心灵的强大力量。
(二)生命意义的探寻
“藏族老人也会随意地聊起死亡,他们认为,天葬是非常神圣的,把所有的一切都干干净净地献出去很好……他们不愿意过度治疗,愿意自然地死去。”正如松太加所言,“藏地新浪潮”电影始终贯穿着对于人类生命意义的深入探寻。影片中,藏族人对死亡的坦然接受流露着他们淡然若水的生死观念。尽管主人公最初大都难以放下生的执念,但最终都能从容看待生死。这也正是“藏地新浪潮”电影所突出强调的生命哲学:死亡也是旅程的开始。
《河》中格日与他出家修行的父亲(老僧人)有着迥异的生死观。格日对生心怀执念,常在酒后哼唱“骑马要在人世间骑,阴间没有骑马的说道”;老僧人却对生死表现得十分淡然。老僧人拒绝见临终妻子最后一面,并对前来央求自己的儿子格日讲道:“我去见她有什么用呢?死亡是不可回避的事情。”同样,老僧人自己患病后更是拒绝住院治疗,他说:“死亡来临就得面对,固执是没有什么结果的。”由此可见,老僧人早已参透了“人生四苦”。受其影响,儿子格日开始试着放下对父亲的怨恨和对生的执念。这种宽宥、释怀绝非一瞬,因为冰层的融化需要时间“跨越象征层面的’河’同样需要时机”。《生命之轮》同样也在探讨生与死。影片中,公保东珠始终无法接受妻子已经死亡的事实。吃饭时,他常会产生亡妻与他共同吃饭的美好幻象;睡觉时,他又常会陷入巨大的恐惧,与梦中手拿“嘎布拉”的上师反复进行着有关生死的对话。在经历了山神的劝诫,以及目睹了淘金者的惨死后,他跪在神山的五彩经幡下为亡妻祷告,寓意着他彻底战胜了对死亡的恐惧。在《白耗牛》中,桑杰卓玛的奶奶时常感叹:“生命讲究轮回,做事讲究因果,现在的福祸就看过去做的善恶之事,来世何去在于今生的善恶之心。”基于此种信念,扎西叔叔和桑杰卓玛的奶奶分别通过放生羊、为蚂蚁施舍藏粑的行动来践行“生命理应得到自由和解脱”的法则,体味着大自然、动物与人的关系,以及人的生命意义。他们生前广行善事,从不惧怕死亡。由于藏文化的独特性,加之藏地佛学的影响,藏族导演们总是无意识地探寻“何为人类生命意义”,其镜头下生命的诞生与轮回颇具辩证统一的关系,即生是死亡的起点,死亡也是生的开始。
(三)父子情感的回归
表现父子情感的讳莫如深、探求父子关系的和解之道,是“藏地新浪潮”电影所探讨的重要命题之一,暗含着对于理想的“母慈子孝、夫妻和睦”的向往。父亲不再是’’在场的缺席者”,而是具有强大感召カ的精神存在。
《河》中,央金的爷爷之于央金的父亲、央金的父亲之于央金,都是缺位的存在。影片中,小央金因妈妈又怀了小宝宝被强行断奶心生不安,央金的父亲格日对多年前他的父亲拒绝见母亲最后一面而耿耿于怀,无法察觉央金的焦虑。男主人公格日与父亲形同陌路,央金与父母渐渐疏远,两代父子间面临着同样的心理症候,传统的家庭结构关系处在被解构的边缘。在经历了父亲重病后,男主人公格日与父亲的关系趋于缓和,影片中原本破碎的镜子恢复如初是父子''破镜重圆”的象征;而央金则在经历了小羊被狼杀死一事后,接受了断奶的现实,甚至还要为即将出生的弟弟妹妹种玩具熊。《格萨尔藏戏》中扎德的父亲同样也是''在场的缺席者”。扎德的父亲曾坚决反对女儿扎徳学习《格萨尔》藏戏,为此还毒打了女儿。巨大的沟通屏障横亘在父女之间,父亲对女儿的爱无法直白表露,女儿也不再向父亲袒露心声。而当父亲目睹了扎德为梦想几经摔打之后,“支配-服从”的父女关系被解构,最终影片通过父女二人在草原湖畔合唱《格萨尔》藏戏重新编码了“新式”父女关系。此外《撞死了一只羊》《黄昏的默哀》中杀手金巴、オ老都分别在童年时目睹了父亲惨死,他们自幼就背负为父报仇的心结,没有半点快乐可言。《旺扎的雨靴》中旺扎父子间的沟通极为贫乏,旺扎想要一双雨靴,需要母亲传话给父亲。对于旺扎而言,就连父亲的斥责声都显得弥足珍贵。在这些影片中,导演们擅于叙说极微妙的父子关系,努力探求幸福和睦、轻松愉悦的家庭生活。
二、类型化人物塑造
成功的类型化人物塑造体现了不同年龄、性别的藏族人的处事原则及精神特质,使得故事的讲述、矛盾的化解更加流畅自然。
(一)男人:去脸谱化的被拯救者
去脸谱化即人物形象不再作概念化、简单化塑造,让读者或观众无法一眼看出人物的是非好坏、善恶曲直。在''藏地新浪潮”电影中,藏族成年男性形象的塑造便体现出去脸谱化这一显著特点。藏族导演电影中镜头下的藏族成年男性形象既高大伟岸又自私狭隘,外在形象和内在精神极具矛盾性。正因此,藏族成年男性常常会深陷于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困境之中。
《阿拉姜色》中罗尔基就是矛盾的男性。一方面,他对妻子与继子百般呵护。当他看到诺尔吾头上套了个袋子时,会细心地将袋子抠出个可供呼吸的口子;当他得知妻子生病时,更是百般劝说她入院治疗。一方面,他又自私狭隘。在对待诺尔吾的归属问题上,他拒绝诺尔吾和他们夫妻同住;在对待妻子为已故前夫朝圣的问题上,他愤怒地将妻子前夫的骨灰扔出帐篷。双重矛盾下,罗尔基陷入了痛苦的两难困境:想要接纳却无法彻底接纳,想要拒绝却无法抹掉良知。《气球》中,达杰同样是外在形象与内在精神不匹配的男性。从外表来看,达杰壮得犹如种公羊一般。然而,他也身陷迷惘的境地。一方面,他认定妻子腹中胎儿就是已故父亲的轮回转世而坚决不同意打胎:另一方面,他又无カ承受因第三个孩子的即将降世带来的经济压カ。影片中,达杰坐在文成公主的雕像下接受滂沱大雨洗礼的场面极具深意。如同远嫁吐蕃的文成公主一度在返归大唐故土与担起和亲重任之间挣扎,达杰面临着“打掉孩子会陷入精神困境,而留下孩子又会陷入生活困境”的两难抉择。文成公主借摔碎“日月宝镜”来彻底割舍思乡之情,达杰深知自己终究也要作出取舍。类似的影片还有很多,例如《撞死了一只羊》中因撞死一只羊而心生罪孽感的司机金巴、因不忍再次目睹惨剧而心怀“耻辱”的杀手金巴、因杀死金巴父亲而整日诵经以求宽宥的玛扎等藏族成年男性也都被塑造成等待救赎的个体。
(二)女人:男人成长的''催化剂”
松太加说“藏地新浪潮”电影中的藏族成年女性虽外表怯弱,但内心却无比坚强。她们遇事有主见,勇于担当,与那些自私狭隘、遇事软弱且常常深陷迷惘的藏族成年男性形成鲜明对比。在电影中,藏族成年女性显现出的精神特质——隐忍,是推动成年男性成长的“催化剂”。
《红丝带》中,梅朵便是隐忍的女性个体。感染艾滋病的梅朵被丈夫抛弃,还饱受村民的冷眼、家人的咒骂。然而,她却不曾想过要怨恨谁,依旧干着最繁重的家务,甚至把身上看病的钱全部给了婆婆,只是希望她以后能够照看小孩。从梅朵的举动中,我们不仅可以窥见她的善良,更能够看见她身上那份独属于藏族成年女性的隐忍气质。最终,在她的感召下,曾经反对在村子里做预防艾滋病宣传的旺加,也加入了宣传的队伍;梅朵的丈夫也重归家庭,在门外对梅朵再次动情地哼唱起了两人相恋时的情歌。《阿拉姜色》中俄玛既是丈夫与继子和解的“催化剂”,也是丈夫自我成长的’‘催化剂”。在俄玛执拗地坚持下,罗尔基从内心满是怨恨、嫉妒到替妻子完成遗愿,最终实现了与继子、妻子以及自我的和解。倘若不是俄玛的坚持,恐怕罗尔基永远不会放下成见,成为一个真正有担当的男人。《旺扎的雨靴》中旺扎的母亲仁吉私自用家中的羊皮为儿子换了双雨靴,遭受到丈夫的百般咒骂。《格萨尔藏戏》中扎德的母亲在看到女儿被丈夫毒打时,她无カ劝阻,只得独自蹲在墙角痛哭,与女儿的哭声混为一团。类似这样外表柔弱性格隐忍的藏族成年女性,在“藏地新浪潮”电影中极为常见。一方面,她们为家庭生活百般操劳,从不流露出半点怨言;另一方面,她们又懂得隐忍,时常用行动来感化迷惘中的成年男性。
(三)小孩:治愈成年人心灵的“解药”
“当痛苦遇见时间和小孩就会黯淡失色,没有什么是迈不过去的。”正如《太阳总在左边》里的这句台词说的那样“藏地新浪潮”电影中的孩子大都天真富有童趣,他们遇事果敢,对未来满怀美好憧憬,有时还会做出令人啼笑皆非却饱含善意的糗事。与之相反,电影中成年人的精神世界总是充满困惑,他们或迫于生活压カ而放弃内心信仰,或碍于颜面而无法打开心结,然而当他们在各自的救赎之旅中遇见孩子后,都无一例外变得阳光起来。可以说,正是孩童的天真与善良治愈了成年人的脆弱心灵。
《河》始终从央金的视角窥探父母的世界。父亲与爷爷之间的隔阂、她与父母之间的疏远,年幼的央金难以理解其中缘由,甚至还做出了诸如“将父亲的天珠藏起来后小宝宝就会不见”,“将布娃娃埋在土里就可以长出满树的娃娃”等一系列糗事。“他们说我阿爸是坏人”,“他们说我阿爸不要爷爷”,正是女儿央金的心灵拷问,推动格日“完成在伦理或精神哲学意义上的自我救赎”。《阿拉姜色》中俄玛死后,诺尔吾以为罗尔基又想要抛弃他,便大声吼道“我很想跟着妈妈,但是你不要我”。面对继子的质问,罗尔基终于无法再故作坚强,他手捧自己与妻子的合照站在寺庙的墙角痛哭了一场,泪水中饱含了太多情感,既有为自己不幸命运的哭诉,也有对妻子和继子满含愧疚之情的流露。也正是得益于此次情感宣泄,父子二人最终同心协カ,再次踏上朝圣之路。类似的影片还有很多。《白耗牛》中,父亲万德オ让背弃誓言卖掉白耗牛,女儿桑杰卓玛为此踏上千里''寻牛之路”。孩子们的善良与童真是比金子还要珍贵的财富,他们不仅用自己的阳光般感染着成年人,还以自己的行动传承着藏地传统精神。
三、风格化叙事策略
对影视作品而言,叙事策略主要包含文本和影像两个层面。“藏地新浪潮”电影显现出了叙事策略的颇具风格化,如在文本层面坚持无指向的开放式结局、对偶式的文化寓言,在影像层面坚持"去奇观化”的影像呈现等,这类电影极具东方式审美意境。
(一)无指向的开放式结局
影视作品的结局一般分为封闭式和开放式两种。封闭式结局是指故事有清晰的结局架构,观众看完不会展开过多遐想;开放式结局则是指故事没有明确的结局,人物最终命运依旧是漂泊无序的状态,观众可以任意展开想象。“藏地新浪潮”电影大多摒弃了经典叙事中惯用的封闭式结局,使用开放式结局。
《太阳总在左边》以尼玛打开盛有沾染母亲鲜血的黄土罐子的镜头而结束。这样的结尾虽然没有明确告诉观众那罐黄土是否洒在了母亲被意外撞死的地方,但却有了可供想象的空间,观众凭借自身经历和人生经验感受着尼玛此刻的心境,是固执坚持,还是毅然放下。回想起儿子意外撞死母亲的整个事件,其心灵创伤怎会在一瞬间被抚平,这样的结局符合人之常情。《气球》结尾,卓嘎走向寺庙,两只飞起来的红气球,一只破掉,一只飞向远方,卓嘎的命运似乎也与两只不同结果的气球相互关联。观众既可以想象卓嘎最终打胎,去寺庙赎罪的结局,也可以想象卓嘎没有打胎,去寺庙祈福保胎的结局。王家卫解读“浅看,是宿命;深看,是解脱”。这一开放式结局折射出导演的叙事智慧与哲学思考:在物质困境与精神困境之间,无论如何取舍都给当事人造成伤害,这种没有结局的结局反而是最好的结局。《塔洛》以塔洛独自在牧场上倚靠着摩托车为结局,画面最终定格在了塔洛孤单的背影上。它没有交代塔洛的最终命运会走向何方一一是否会去派出所控告杨措,又是否会因私自变卖本不属于自己的羊而被他人控告。然而,导演正是以这样的留白“强调情与景的外延”,传递着更为深刻的思考:以塔洛的背影来指涉当下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来回徘徊的一代藏族青年,塔洛此刻“无痛、无梦、无根”的状态,也许恰是千千万万个迷惘中的藏族青年的共同缩影。塔洛所遥望的草原深处,似乎隐喻着导演对于剥离传统后的新世界的认知、对传统善意的思忖,以及对精神家园的找寻。总的来看,“藏地新浪潮”电影虽然大多结局没有明确告知人物的命运、故事的走向,但却能够实现’’化未知为已知”的效果,观众在自行展开想象的潜意识活动中或喜或悲。这种探究式想象要远比给出答案更能够让观众共情,毕竟不完美的结局オ更能反映生活的真实感和现实的刺痛感。
(二)对偶式的文化寓言
寓言“是通过一个表面的故事来表达更深层次的含义,或以简单的故事来讲述众所周知却被忽视的道理,或作者以刻意的安排与布局来暗示自己所想表达的”。当下,寓言也被运用到影视创作领域,生动形象地阐释发人深省、振聋发聩的道理,对观众有着启迪与引领意义“藏地新浪潮”电影出现了大量的寓言文化。藏族导演们运用“拟人”的手法,将影片中的动物赋予人的思想情感,通过它们的活动来比喻人的现实处境及特定情绪,使得人与动物之间形成惺惺相惜的对偶关系。
《阿拉姜色》中俄玛死后,导演有意增加了驴子这一动物角色“按照藏族文化的解释,母亲去世后,有一个新出现的生命来帮助他们完成她的心愿,故事有这样一种寓意。”同时,驴子的出现,也为剧中父子二人的朝圣之旅增添了些许暖意。当罗尔基为妻子“煨擦塞尔”后,循着他的视线观众看到了眼里噙满泪水的诺尔吾以及一大一小两头驴子,母驴已倒地死亡多时。此刻,失去母亲的小驴子俨然就是诺尔吾情绪的外化,这一安排无疑要比诺尔吾大哭一场更能刺痛观众的心,观众在静静的沉寂中感受着诺尔吾内心的痛苦。《河》中小羊羔是央金无法接受断奶的象征性比拟。影片中,当央金拿起喂小羊羔的容器时,她也不自觉地吮吸了口奶,这一细节的设定显然象征着她和小羊羔同病相怜的命运:小羊羔的妈妈被狼咬死,央金的妈妈肚子里有了
宝宝,两者都被强行断奶。而在结尾,小羊羔被狼杀死这个事件,再次使得央金“以一种身临其境、感同身受的姿态融入动物的情感与伦理视域”,与此前不同的是,这次事件消除了因母亲强行断奶给她带来的痛苦,实现了央金的心灵蜕变。《气球》中达杰与借来的种公羊、卓嘎与不生育的母羊也各自形成了对偶式的寓言关系。影片以仰拍的方式拍摄种公羊,以俯拍的方式拍摄母羊,仰俯之间种公羊与母羊的地位差别凸显于银幕之上。种公羊眼神里的傲慢、不可抗拒的雄性力量以及强大的荷尔蒙指涉富有男性权威的达杰,母羊一脸任人宰割的木讷与老实相指涉沦为生育机器的卓嘎。影片正是通过这种力量对比,借母羊的境遇来反思藏地女性的现实处境。总的来说“藏地新浪潮”电影擅长用各种动物隐喻人的现实处境。将这些动物拟人化处理,增强了影片的生动性和趣味性,也化深奥为浅显,在增添讽刺或劝诫意味的同时,传达出影片的某种态度。
(三)“去奇观化”的影像呈现
与同类型影片《红河谷》《冈仁波齐》不同的是,藏族导演们从“主位视角”出发,去观察、反映并思索藏地现实,不再刻意展现藏地独特的风光美景、神秘仪式以及宏大历史,更多关注的是藏地普通小人物的生活境遇和困顿心灵。因此,其影像呈现大都具有“去奇观化”的美学表征。
“藏地新浪潮”诞生之初的影片,仍然有不少全景、远景场面,在影像呈现上存在着一定的造型感。尽管如此,这一时期的影像呈现已然出现了“去奇观化”倾向,大景别与小景别的镜头搭配既交代了藏族人与藏地环境的关系,又展现了他们困境中的孤苦心境以及救赎后的释然之情。在《塔洛》中,导演万玛オ旦使用不同景别的镜头表现塔洛心境的前后变化。在影片前半段,塔洛一心坚持“为人民服务”的理想信念,此时他的形象主要是以中近景来呈现,通过小景别呈现塔洛眼神的清澈、动作的木讷,表现出塔洛心性的纯良;而在影片后半段,塔洛在现代文明中迷失自我、不彻底地割离传统后,远景、金景成为影片主要的景别画面,突显了塔洛的无措、迷惘以及与现代文明的格格不入。在结尾叙境部分,塔洛孤独地倚靠在摩托车上,背对着观众望向远方的神山,在这种大景别的长焦镜头下,形单影只的背影与冷峻圣洁的神山仿佛重叠在一起,纵向距离的拉近使得塔洛与神山彼此映照,既放大了塔洛此刻孤苦无依的心境,又映射出他既想融入现代却无法彻底融入、既想脱离传统却无法彻底脱离的内心矛盾。除了景别上表现出’‘去奇观化”之外,固定长镜头、手持摄影也是主要拍摄手法。与流于形式的运动镜头相比,固定长镜头可以发挥电影最本质的记录功能,更好地反映现实世界的客观存在。再加上剧中人物的内心或不安、或热烈的反映,使得影片更为关注人的现实处境,引发观众的情感联动。在《旺扎的雨靴》中,导演以固定长镜头呈现旺扎和拉姆奔跑时的全景画面,同时辅以手持摄影。虽然摄影机镜头并没有聚焦姐弟二人的开怀大笑,但奔跑时的跳跃感却表现出两人在挡雨“诡计”得逞后掩饰不住的喜悦之色。同时,配上空灵悠长的藏族音乐,整幅画面格外舒适自然。正是在这种看似平静的叙事中,孩童们对追寻梦想的坚持与付诸实践的勇气オ更显珍贵。
四、结论
藏族地域独特的自然景观、民俗文化以及虔诚的精神信仰,使藏地电影富有民族性与生命力的宝贵资源。藏族导演们的目光始终游走于困顿心灵、生老病死以及父子关系之间,讲述的是藏地普通人的平凡故事,流露的也是藏族人的质朴情感。藏地新浪潮电影在主题指向、人物塑造以及叙事策略上面向内心的探寻,呈现出极具辨识度的群体化风格,打上了地域、民族与时代的鲜明烙印。就艺术性与思想性而言,它成功架构起了藏族文化与其他民族文化平等沟通的桥梁,在实现藏族人、藏景、藏文化有效''祛魅”的同时,也唤起了藏族人更为广泛的身份认同。
基金项目:2022年度山东省研究生优质课程’’电影导演专题研究”(SDYKC2022172)
作者简介:崔福凯,男,山东德州人,副研究员,博士研究生,专业方向:影视文化与产业。
原刊于《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24年9月第40卷第3期。原文版权归作者及原单位所有,因篇幅所限,注释及引用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