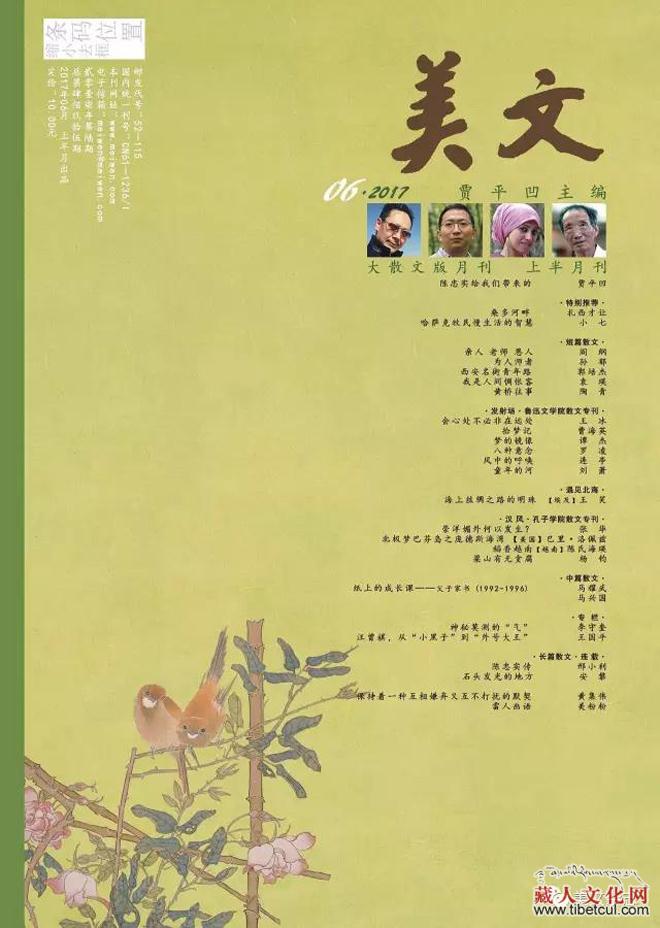
1
桑多镇的南边,是桑多河。春天,桑多河安静地舔舐着河岸,我们安静地舔舐着自己的嘴唇,是群试图求偶的豹子。秋天,桑多河摧枯拉朽,暴怒地卷走一切,我们在愤怒中捶打自己的老婆和儿女,像极了历代的暴君。冬天到了,桑多河冷冰冰的,停止了思考。我们也冷冰冰的,面对身边的世界,充满着敌意。只有在夏天,我们跟桑多河一样喧哗,热情,浑身充满力量。也只有在夏天,我们才不愿离开热气腾腾的桑多镇,在这里逗留,喟叹,男欢女爱,埋葬易逝的青春。
2
桑多河畔的蒲公英,比预想的要多得多。这些多年生的可以入药的菊科植物,看起来是多么珍贵。它们耐着性子,总比迎春、月季、桃、李、杏开得更迟些。黄色的艳艳的弱弱的花,在最后一批桑多人奔赴远方之际,就在河的两岸密密麻麻地盛开了,仿佛在赶赴某个重要的约会。其时已是阴历五月上旬,桑多河一步三回头地流向远方,蒲公英也一步三回头地开向远方。这总使桑多人想起远嫁的女人、离开的儿女,甚至久远的母族,或飘零的族人。多年来,人们看见这些蒲公英热烈地开了花,又在初秋时节携着数不清的种子飞向远方,只留下枯枝败叶,和精尽力竭的根,还坚守在生命开始的地方,等待着来年的萌发、结果和飘零。这令桑多人伤感的飘零,意味着什么?一个老人说:“和人一样,都想离开。”另一个人老人说得决绝:“蒲公英比人好多啦,人一离开,就有可能不回来,这可是断根绝族的事。”哦,这透彻心骨的伤感,也许就是绝望吧!
3
初中时的某同学,性格与别人不同,别人都在老师和家长的引导下努力学习,他不,他爱折腾。结果呢,我上高二那年,他就辍了学。先是在巴掌大的桑多镇上混,时间不长,骗了另一个同学家传的古董字画,去了兰州。几年后,又遇到了他,穿得人模人样的,开着一辆看起来蛮豪华的旅游用的大巴,据说已经是某旅游公司的副总裁。于是他组织了初中同学大聚会,但只来了七八人。七八人就七八人吧,大家在一起豪饮。酒喝大了,某诗人同学站起来,朗诵他即兴写的诗:“昨日是头颅在生锈/昨日是嘴巴在沉默/昨日是祖先的房檐被雨水打湿/昨日是失败的男人从南方回来。”开旅游公司的同学抢过话筒:“今日不是这样!”今日是怎样的呢?聚会结束后,我总在思考这个问题。想起自己多年的读书和写作的日子,顿时感慨万千,写出这样几句:“今日是桑多河畔的白球鞋/是海子说的上帝遗弃的游泳裤/是飞去又飞回的佛祖掌心的白鸽子。”我想我已到了能独立思考的年龄。但在同学聚会时,我保持着沉默。我想,我沉默的原因,或许是对那些美丽往昔,已经无法面对。
4
有了佛,就有了佛的法。这法需要宣讲,需要布道,于是就有了僧。僧一脚在佛界,一脚在俗世,于是就有了俗人对僧人的窥视:“一鱼游过边界,进入河上的天空,像鸟儿那样飞翔。北方寺院,吱呀一声,有人推门进来。功德之后,要复归南方的旧居。听说他途经桑多河时,于倒影里看到了一个莲花一样的女人。”僧人是否真的看到莲花一样的女人?不清楚,这或许是道听途说,甚至就是无中生有。那么,“你们原谅我吧,我了解河边的死,也知晓水下的生。我唯一不知的真相:那个上香的高僧,为何会病逝在返乡的途中?”是的,僧人的病逝,是事实,但他为什么病逝,就成为一个悬案,让后人猜测不已,以至于将这种猜测这种疑问,写进了诗里。
5
在组建家庭的各个阶段,爱情这一段落显然要比婚姻这一段落来得更早。比如我吧,那年还在上高三,父母亲就有了给我组建家庭的打算。于是,相亲的活儿开始了:“电线从麻雀的爪子上感受到了自身的颤抖,南风从树叶的晃动中感受到了久违的自由,我从她的眉眼里感受到了美丽的娇羞。相亲的那天,只隔着一面门帘,我和她,就已把对方印在心底。”这一步的结果,大人们是比较满意的。然而,相亲之后,爱情的缰绳,谁也无法控制了:“夏天,自然是潮湿、骚乱又慌张的季节,来自西宁的虫草商人,看上了桑多的女子。夏天过后,杏子成熟了,核桃结了仁。我和她在隆冬的桑多河边相遇,彼此冷若冰霜,背向走进风里。”父母亲试图成就的婚姻,就这样走向了另一个道路。幸好如此,否则,就没有这首诗的诞生。因为写这首诗的人,当年还不是诗人,还没有任何想做诗人的打算。
6
来藏地旅游的人,注意到这里的山,这里的水,这里的人,当然也会注意到这里的神。我曾无数次目睹过这样的情景:“桑多河畔,游人蜂拥而至,有人极目远眺,有人大呼小叫。有人按动快门,拿走了不属于自己的风景。鹰飞起来,像一顶雷锋遗失的棉帽。鱼在河里游走,如水底的珊瑚,星星般闪耀。人类在河边逗留,喟叹,钻进各色各样的铁皮匣子,尘埃一样悄然消失。”游人离开了,剩下我一人,还会在桑多河畔多待一会儿。此时,在这苍茫的天宇下,必有清风徐徐吹送,吹起一河涟漪。在这样的美景中,我也会突发奇想:会不会有人面兽身的异物,守在河的那头?她或许来自人世,或许来自兽世,或许来自禽世,也会像我们一样想些奇怪的问题,发出怅惆的叹息。这样想了会儿,越想越觉得有可能,情不自禁地四处张望,看能否找到她的行踪。然而,在这苍茫的天宇下,只有清风徐徐吹送,吹起一河涟漪。
7
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活到一定年龄,就开始思考这三个问题。有的人思考了半辈子,还是没有啥结果。有的人思考了一段时间,经历了车祸、火灾和莫名其妙的挨打,之后,干脆就不思考了。有的人,譬如我吧,爱写些对人生有所感悟的文字,且对宗教还比较感兴趣,因此,对这三个问题,还是有一搭没一搭地对付着。我是谁?“我是只野兽,有着野蛮的肉体。”从哪里来?“我想面对大河上弥漫的黑夜,诉说我的陈年往事。那预示吉凶的经卷在今夜打开,明天,也不会被圣僧收进盒子。”到哪里去?“我从深林里窜出,扑进幽暗的水里,脚被水草缠住,发被激流带走,呼吸也被窒息,绝望由此开始。”在试图解决这三个问题的过程中,我荒废了许多时日。有天黄昏,当我面对桑多河河上弥漫而起的黑夜,突然觉得自己就是一尾墨鱼,往前看,因为各种时代的原因,已无家谱可查。往后看,虽有后代在成长,但也不知道他们会走到哪条路上去,假若依靠他们,肯定有种依靠门帘的感觉。结果呢?结果就是处在人生的中途,前望望,后看看,我张口结舌,无法说清我的今生今世。
8
在这又繁华又荒凉的尘世上活着,偶尔在河边或湖边长久地站立,就会注意到自己的在世的倒影。我注意到我的倒影,并试图用文字予以表现:“群鸟已退隐山林,野兽深匿了它们的踪迹。我一个人坐在山坡上,远处是积石山脉起伏的玉脊,近处,是一大片又聋又哑的赭色草地。那座寺院的活佛圆寂了,檀香树下的农妇大梦初醒就有了身孕。神圣之树的枝叶还未脱净绿色,它也在静寂里梦见了自己的来世。桑多河畔的野草,又将根须伸进水里,我俯下身,看到自己在世的倒影,被水波鼓荡得模糊不清。”对这倒影,我不是万般留恋的,因此我又写道:“我终会离开这里,离开这里……我想,我是厌倦了这秋风翻动下的无穷无尽的日子。”
9
夏天,彩虹到桑多河边喝足了水,就倏然消失了。人在河边站得久了,也有了苍老的样子。只牧羊人在河的上游和他的羊群在一起,像个部落的首领,既落魄,又高贵。我在这个叫桑多的高原小镇生活,在首领们的带领下,安静地吃草,反刍,有时也想些问题。以前我在别的牧场:珊瑚小学啦,玛瑙二中啦,或者云里大学啦,都有着神圣又美丽的名字。而今在这桑多镇,在这牧神的牧场,我还是白天吃草,夜里反刍。想起平庸的一生,就渴望有更勇敢的牧神出来,带领我登上那积雪的山顶。在山顶,我会看到彩虹在河边低头喝水的样子,也会看到苍老的人原先年轻的样子,我会像真正的土著那样,在一袋烟的工夫里,感知到桑多山下壮美景色所蕴藏的秘密。只有在此时,才觉得自己不是羊人的身份,而的的确确是这个地方的主子,哪怕只有着倏然即逝的生命时光,也是不容怀疑的这片珍贵的山川的主子。
10
六月初六这一天,确实是适合采薪的好日子,不过,风俗流变,大家都不采薪了。山上,神灵们起了个大早,他们站在山顶指指点点,山坡上就长出各种奇异的花朵。山下,当太阳扑通一声跳下河,晚风鼓荡不息,水里就游来各种古怪的生物,它们也睡眠,也发声,也喧嚣,看上去,让人忐忑不安,又心怀感恩。有人在帐篷里打开酒壶,酒香就四溢开来。山坳里飞出蝴蝶,扑进花丛,山梁上走来曾经到处游荡的山神,三三两两的,他们也坐着,也说话,也发怒,看上去,让人无可奈何,又心怀担忧。等到那么多的人,折腾够了,疲倦了,那么多的神,不争吵了,睡着了,就有几头牛,在草地上慢慢地走,却始终走不出它们的月下的阴影。我和朋友斗酒猜拳,但又不想喝醉,想从山里匆匆赶回小镇,躺在大梦深处。半路上,我的女人找到了我,张开丰硕的双臂,将我扑倒在路边的草丛里。她像个骑手,骑着我到了遥远的天边。
11
河,花了五百年的时间,从神山下流到这里来了。水深的地方,现出青黑色,深渊一般。排子客们是清一色的壮汉,早就磨好了斧子,调好了钢锯,扎好了绳索。年轻羞涩的媳妇,也把用青稞面做成的坚硬的烙饼,装进了厚重的牛皮褡裢里。早就有老人在出发前煨起桑烟祈祷过了,但他们还是悬着心,担心被无形之物把生命遽然带走。在河面上漂流得时间一长,大家都有了孤苦的心思,觉得自己也像山上的那些树,活得好好的,突然就被浸在水里,顺流而下,不知何日才是归期。最终,他们还是回来了。说书艺人说,白天,排子客们腰插利斧,没入山林,是群北方的帝王将相。夜里,只能把生命交给神灵主宰的江河,是群老天也得眷顾的孩子。当我从城里回来,挤入他们之中,这才知道:他们也像族人那样,渴望在来世还能转世成人,最差也要转世成树木,不去别处,只生长在故乡的山林,而且,再也不愿涉足在那深不可测的江湖。
12
我把桑多一带的牦牛,不管是一群,还是一头,都叫桑多牦牛。你有空出去转,就会发现,桑多牦牛在寺院背后的一棵柏树下静静地吃草,间或抬头遥望远方的一处山谷,秋末的阳光将柏树的阴影落在它身上。你估计它曾经走过雪原,蹚过初春的小河,深匿于盛夏的丛林。这是事实。现在,它老了,形体瘦削,毛发稀少,像极了你熟悉的那个来自青海的羊皮贩子。有时候你从外地回到桑多,也会看到桑多牦牛在寺院背后的一棵柏树下静静地吃草,你不知道它还有多少这样安静吃草的时光。但你知道:远处那座山谷里有它的童年,有它的父母的精魂,它曾经眷恋过的青春的母牛。现在,你是否感觉到了隐隐的疼痛?你是否又觉得无法表达这种疼痛?别急,别急,你只要看看它的旁边的岩石上,那个放牧它的羊皮贩子,他睡在那里,发出了粗重的鼾声。这时,你就有办法表达你的痛苦了。我的诗歌,就是这么写出来的。
13
在某个地方待久了,待得没有任何新鲜感了,任何人,都会有渴望离开此地的想法。实现这想法的难度越大,渴望的力度就更强烈。那一年,我的表弟就犯了这毛病。他找到了我,让我想办法。我以诗人的身份劝告他:“你看啊,桑多河畔多么安静,晨曦自东山突现,琉璃瓦的屋顶在光中颤动,波浪般鼓荡不息。这么好的早晨,这么好的时光,这么好的人,还留不住你吗?”我的话被一阵呜呜呜声给打断了。扭头一看,来了我暗恋的扎西吉,骑着红色的摩托车。表弟跑过去问她:“哪里去?”她甩甩卷曲的长发:“县城。”天哪,早起梳妆的扎西吉,让人心疼的扎西吉,骑着红色摩托要去县城的扎西吉!表弟激动起来:“你能带走我吗?你能带走我吗?”她不回答,却看着我。“我能跟随她远离这牛皮一样韧性的生活吗?我能跟随她走向那神秘又陌生的远方吗?”显然不能!人人都在逃离,人人都追寻着陌生,但我祖先的尸骨就在这里,我的部落的历史也在这里,我不能离开,虽然我是那个因她而失明的男人,虽然我对她的爱,已在骨头里泡沫般滋生。结果,表弟跟着她走了,从此再也没回来。不过,她还是回来了,现在,我们的孩子,也到了当年表弟那样的想出走的年龄。
14
去年此时,我无法摆脱困扰自己多年的东西,比如一段感情,一桩难以启齿的私密往事。这让我觉得岁月不是金子,也不是银子,而是一个巨大的仓库,那里面可以取出我经年累积的东西。我头顶的鹰,山梁上的白马,和身边的亲人,都是从那仓库里取出来的。我心里的诗篇,也有着仓库里幽暗而潮湿的气息。现在,牧场里的家马变成野马,回到山林,道路上的头人的子孙们,在石头上歇息。听说,由于他们远离了他们引以为傲留恋不舍的辉煌时代,而今有点落魄。不过,依我看来,他们骨子里的高贵,无论时光如何流逝,也是无法被湮灭的。离他们不远的小河边,我,一个农奴的孙子,低头喝水。水面上的涟漪,波闪出我的前生:青海古道,我和父亲在高原上赶马换茶,我叫他阿哥阿哥阿哥;也波闪出我的后世:塞纳河边,一个身材高挑的金发女子,将丰硕的肉体,慢慢地没入齐腰深的水里。
15
海子说:我有一间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在桑多河畔,我也有一间房子,面朝河水,春暖花开。但我没有海子对未来的美好期待,每天都在昏睡。黎明时分,醒过来,听到了应该听到的,想起了应该想到的:“窗外风声,是我们前生的叹息。窗外水声,是我们今世的叹息。桑多河畔,水声哗哗,风声嘘嘘。你的我的他的女人,从山地牧场上背回了牛粪,从母牛那里取来了新鲜的奶子,从度母那里,领来了你的我的他的隆鼻深目、精瘦机敏的孩子。桑多河畔,我们在风声里撕打,在水声里把腰刀捅进别人的身体,在女人们的哽咽声里突然死去,——水声哗哗,风声嘘嘘。我们死去,又活过来,但还是带着人性中恶的种子。”海子把温暖和美好用诗歌留下来,然后他离开了这个世界。我活在海子笔下的温暖的人间,却要写出这么多冰冷和丑恶的东西。海子的高蹈和我的内陷,拉开了我们之间作为诗人的永远的距离。
16
深秋,河边杨树的叶子变得枯黄,但还没落下来。这时,桑多河的流水才收敛了激越的态势,慢腾腾地流淌。枯树,也伸出干裂肃杀的枝丫,力图缓解北风劲吹时的速度。蚂蚁,则深匿在又聋又哑的地下,扎成堆,紧靠在一起,显然就有着人类忧心忡忡的样子。衰败确实伴随着时间的消失,静静地到来了。然而,村庄里的人,早就走得七零八落的。冬至这天,人走屋空的日子,不像一个节气,倒像一种宿命。在蓝天、雪野和房屋拼凑出的寂静世界里,人们都能感受到的时间,仿佛失去了存在的意义。这时,会有一个女人,跪倒在佛堂里,还是像过去阖家团聚时做的那样,点上了温暖吉祥的酥油灯。我找了她整整十年,一直没有她的音讯。现在,她出现了,我呼喊她:“阿妈!”她不回答,只对着面前金铸的被香火熏黑的佛像,磕了三个头。然后,她起身走了。因为走得匆忙,没顾上拍去膝盖上的尘土。我又大喊一声:“阿妈!”她却突然消失了。我惊醒过来,顿时明白:母亲或许还在另一个世界,但她不需要我去替她解除宿命,以便重新回到这个人世。
17
听说以前,桑多河畔,每出生一个人,河水就会像往常那样漫上沙滩,风就会像往常那样把野草吹低。而桑多镇的历史,就被生者改写那么一点点。听说以前,桑多河畔,每死去一个人,河水就会像往常那样漫上沙滩,风就会像往常那样把野草吹低。而桑多镇的历史,就被死者改写那么一点点。听说以前,桑多河畔,每出走一个人,河水就会像往常那样长久地叹息,风就会像往常那样花四个季节,把千种不安,吹进桑多镇人的心里。而在现在,小镇的历史,早就被那么多的生者和死者改变得面目全非了。那么,你们这些出走的,或打算出走的人,再也不要试图改变这里的一草一木啦,这桑多河畔的历史,再也经不起如此这般的反复折腾。求求你们了!
18
“我离家出走的那年冬日,从桑多河里挑回来的水,冻在缸里。挂在房梁上的腊肉已经变硬,我和姐妹劳作过的土地,死在了山里。”少年时代,就是叛逆的时代,百分之八十的少男少女,都做过这样的决然的选择。“我离家出走的那年冬日,父亲托人带话给我:回来吧!母亲杀了只用来叫魂的公鸡,但我还是没有回去,没有回去。”我打算将叛逆进行到底。然而,我始终明白:我当时走的每一步,都有外强中干的印子。我明显感觉到了自己的茫然和无力。因此我这样写出了第三节:“我出走的那年冬日,因为仇雠,我打破了邻居的头。桑多河畔,有人在隐隐约约地喊我,回首,只有弥漫的尘埃和虚弱的自己。”
19
在藏地,据说神的法力无边,他们一脚就能踩出盆地,一拇指就能摁出山峦。他们甚至让猛虎卧成高高的石山,让天上的水落在地面,成为汹涌澎湃的江河。我还听说这里的农民,喜欢在山坳里藏起几座寺院,在沟口拉起经幡,让掠过脊梁的风念经,让流过爱恨的水念经,让照耀苦难的光念经。在这些农民眼里,从正月到腊月,春夏秋冬,不是先人们命好名的四季,而是四座金碧辉煌的经堂。我上大学后离开了这里四年,然后又回来了。我发现有佛光慢慢消失,又突然出现,有大德在粗壮高大的松柏下参悟着经卷,有庄严的法号在空谷中撞来撞去,发出高远的回响。我也发现许多香客像我的兄弟姐妹们那样,从布达拉宫归来,走入木楼,睡在牛羊粪烧热的土炕上。我拿出笔记本记下一个场景:黑脸男人刚刚牧羊回来,他抱紧了白脸女人。也写下日记:夏天到了,草地上,搭建起休闲的帐房。当然也像天文学家那样,开始了奇妙有趣的想象:有人懂得花语,悄然来去,虚掩着门窗。我真的不想离开这里,看哪,当秋月当空,晚饭之后,这里的人们总是喜欢在月下行走,看月光照亮山顶的积雪,看西风吹拂千顷森林,吹拂着祖先们曾经熟睡过的村庄。
20
有人说你会离开这里,是不是?是不是?噢,就是呀,那你把牧场上的理想,还给牧场吧。把少年时光,还给四季的风雨吧。把你的草地,还给父母吧。把祖先的灵肉,还给脚下的土地吧。光是这样还不行,你还要用桑多河的河水饮好你的马,用高原上的牛粪净过你的手,把先人传下来的哈达献给你的人。然后,你才能骑上你的那个破梦,去那你一直想去的让人伤心的天下。孩子,或许在你说的那个在闪光的土地,确实在频频召唤着你,我也就真的不阻拦你啦!我呢,不过是一条漫游的河,只想抵达我迟早会去的那里。你知道,我要去的那里,和你要去的那里,不是同一个地方。

扎西才让,藏族,1972年生,甘肃甘南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会员,甘肃省作家协会理事,甘南州作家协会主席,第二届甘肃诗歌八骏之一。在《民族文学》《十月》《诗刊》《青海湖》《散文》《芳草》《红豆》《西藏文学》《飞天》等60多家文学期刊发表作品。作品曾被《诗选刊》《小说选刊》转载并入选《2015散文精选集》《新中国成立60周年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中国好文学》等40余部选本。著有诗集三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