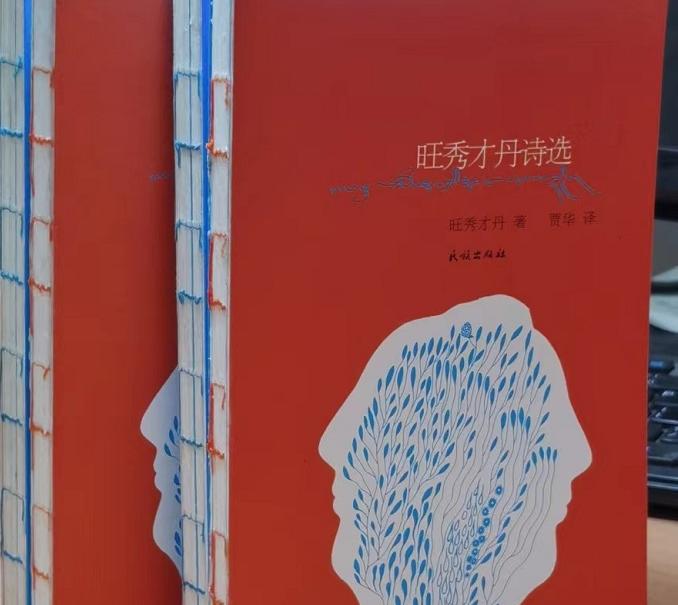大约是在七年前,那时我不写什么小说,对文学的了解停留在偶尔从哥哥的书架上抽一本乱翻的程度。我记忆中的哥哥是个忧郁的青年,时常在湖边放牦牛时阅读顿珠嘉的诗歌,或者低吟一首关于拉萨和回不来的恋人的歌,那时大家对他的评价是可靠但神经迟钝,火烧到屁股也不挪窝。
我十三岁那年,家里仅剩的七只母羊在哥哥写诗的时候被狼群掳走。我赶到现场时,羊的残肢和内脏到处都是,狼群陷入久违的狂欢之中,而哥哥正在起风的湖边给他的诗歌写上最后一句:藏北的海她没有涛声,于是风日夜替他的妻子歌唱。
我问哥哥藏北的海在哪里?他说藏北的湖就是藏北的海。
或许是受哥哥的影响,后来我的人生轨道也向着文字倾斜了过去。离开藏北牧场的家去上大学的那年,我为一个女孩写了一首藏文诗歌,名字叫作《陷入爱情风暴的雪山》,后来在学校附近的一家酒吧里,我听到主唱将其作为一段风流艳事的结尾唱了出来,于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因聚众闹事被带走发生在了那个晚上。破碎的吉他和在主唱脑袋上开花的啤酒瓶,令我蓦地想起七只母羊被肢解的惨状和哥哥的诗歌,时间已经悄然过去五年,哥哥也死了五年。
就在那个头破血流的夜晚,我突然想去看海。因为五年来哥哥的话时不时闯入思绪,即使在遇到那个来自海边的女孩之后,我仍然固执己见。她说我是从山上下来的坏脾气猴子,我说她是从海里爬上来的眼距过大的两栖动物。玩笑似乎映射着现实,猴子并不觉得海洋了不起,两栖动物也无法想象山高云深,于是不久之后她悄然离开了我。那天我像往常一样把洗好的画笔送到她的宿舍,但她始终没有出现。我坐在楼下的树荫里,回想前一天送她到宿舍的场景,那天和平常没什么不同,但她确实离开了我,正如和往日一样平常的海突然发生了船难。
总之,我决定去看海,于是等我从那场无人受益的闹剧里脱身后,应付完考试,大学开始放暑假,我去火车站买了张南下的车票,目的地是她在海边的家乡,但离学校太远,用回藏北的票钱买不起直达票,只能转乘几次汽车。
南下的火车驶过接连不断的隧道和桥梁,在突然降下的夜雨里继续疾驰。我在旅客时多时少的硬座车厢里边看书边打瞌睡,火车越是向南,天气越湿热,也愈加阴晴不定。有时连绵不断的丘陵从云雾中出现又隐去,有时晴空下目力所不及的金色田野一直延展到远方。我被窗外应接不暇的风景吸引,这里的山水和藏北沿线的风光完全不同,我认真地体会陌生又奇特的南国气息。她说去海边时最好坐汽车,而且要在沿途的小站上买汽水喝。于是我在换乘汽车后经过的几个车站都买了汽水,分别是桃子味、柠檬味和海盐味的,三位手工匠人把标签、保质期和配料表全无的玻璃瓶递给我,味道却清新可口。
在距离海边还有十几公里的最后一个车站,我在站台的展示栏里看见了她的作品,一张关于海和雪山的油画,画里的大海波涛汹涌,雪山在远处默然耸立,海的蔚蓝色艳丽张扬,天空和雪山的部分则用了更为深邃的蓝色。我第一次看到这幅画是在图书馆油画沙龙的评比活动上,那时她正在略显沮丧地看着画框前的投票箱,我把入口处领到的用来投票的三枚纪念章都投了进去,她向我微笑致谢。
“画的是哪里的湖吗?”
“不是,是大海。”她收回三分之二的微笑,“湖和海不一样,海的波浪要大很多,就像画里这样。”
“湖也有波浪很大的时候。”我说,“来自北方的风搅动湖水,湖里的一切都天翻地覆,我的哥哥冒着风浪把鱼扔回湖里,湖水又把它们扔过来。”
“有意思,可是湖并不是海。”她收回的笑容已经加倍返回。
“藏北的湖就是藏北的海。”
“不是的,无论在哪里湖是湖,海是海。”她开始收拾自己的画架,但对我的兴趣并未丧失。我帮她整理好屈指可数的票数,一起到服务台兑换了一套廉价画笔,她有点失望,但看起来并非因为那套廉价画笔。
“还记得你第一次见到大海的感觉吗?”我们并肩走在林荫小道上。
“不记得。”她想了很久才说道,“可能因为海一直就在那里。”她把一双看过海的双眸对着我,“你是第一个这么问的人。”
“关于海的回忆,就没什么特别的么?”
她花了和刚才一样长的时间思考,看来让人思考习以为常的事物的特别之处是个难题。
“要说特别的,听我父亲说我出生那天的夜晚,大海宁静得像是晚秋的麦田,渔船在月光下缓缓返程,像农民不紧不慢地走过田埂。”
我推想月光下宁静的大海,星星点点的渔船,再对比藏北十五月圆的晚上溜出帐篷看到的湖面,远没有大海那么宁静,因为藏北的风从不放过任何夜晚,那画面里有哥哥坐在湖边。
“那你呢?”她把手轻轻搭在我腋下的画架上,肌肤间清凉的触感褶皱了湖的画面,让我意识到我们现在像一对恋人一样漫步在小道上,“你第一次见到湖是什么感觉?”
“那时我只知道出了家门,西北方向全是一大片蔚蓝色的湖的领地。”我说,“哥哥告诉我书上说的大海就是西北边的那些湖,但哥哥没上过学,到死也没见过大海。”
“没事的。”她安慰我似地轻抚我的胳膊,“看到海你就明白了。”
然而,直到七年后写这篇文章的现在,我仍然说不出看到海时我明白了什么,我不理解海,海也不理解我。在大巴车缓慢向左拐过后,连片的房屋和嘈杂的海鲜街市接连退出眼帘,大巴车电视里放出路易斯·阿姆斯特朗的《玫瑰人生》,夏日午后的海完整出现在我面前,海涛声比刚才更加清晰,一股咸湿的气息夹杂在暴晒出的热浪中。堤坝上的人行道走过许多像她一样见过海的青年,应该是附近的大学生。我在大学站下车,站台就设在离海不到两百米的地方,在靠海的站台长椅上我坐了三十分钟,那是全然不觉得漫长的三十分钟,那三十分钟里我想起了比过去五年想得更多的往事,以及哥哥的样子。在哥哥从未见过的大海面前,记忆里他的容貌竟然开始模糊不清,我闭上眼,一片在高原强烈的阳光下反射光芒的湖面浮现在脑海里,哥哥的身影缓缓穿过波光粼粼的湖面,他坐在湖边开始低吟他的诗歌,而她轻轻对我说湖不是海,海也不是湖。
在站台坐够了后我从租车行借了辆自行车,沿着海岸线缓缓骑行,寻找可以更靠近海的地方。我停在一个偏离居民区无人看管的海滩上,沙子细碎干燥不时有虫子爬出,废弃的渔船在一旁静静腐烂,海浪在离我不到五米的地方拍上岸又退去。
我坐在沙滩上静静听涛声,沉入对海的遐想,仔细地观察海上驶过的每一条船,看海鸟起飞追逐,猜测浪花中不寻常的浮起。远处近似等腰梯形的海岛在雾霭中线条朦胧,海上远比藏北的湖面要热闹得多。午后海风渐起,薄薄的雨云很快赶来,我爬上岸坐在广告牌下继续看海,一阵细雨持续了十几分钟,随后不再那么强烈的阳光从薄薄的水雾中登场。我又下到海滩边看海,沙子比刚才粘脚,海水似乎开始退潮,不再刮风了。
看了一会儿后,我拍去身上的沙土准备去她家把画笔还给她,但我不确定能不能做到,我从包里掏出一张邮寄衣物的发票复写纸,上面依稀可以辨认她家的地址。有一次她去上课时我帮她寄东西,回来时把发票忘在了书包里,在咖啡渍、巧克力酱和热茶水的侵袭下它已经布满褶皱。在酒吧闹事的那个晚上我从书包里翻到了这张复写纸,或许,我是在那时就决定去看海的。记忆的真容稍纵即逝,七年后的现在更已是无法准确定位它的坐标。
然而,我却清楚记得我犹豫了很久,在海边拿出那张复写纸翻看时,我想着见面该怎么开口,如何道明来意,又或者,看看海然后坐晚上的硬座回去也不错,手上不知不觉就把那张复写纸折成了一张小船。我对着大海,把小船举起来,于是一只污渍斑斑的小船和渔船一起航行在海上。
哥哥曾经也做船给我,那时候我因为生病夜哭不止,他牵着我的手带我去湖边,从怀里掏出他用母亲做饼子剩下的面糊做成的船,船在湖面上飘了不远就被鱼一口接一口地蚕食,直到最后完全消失。见我还在哭泣,他带我去湖水退去的盐碱地寻找所谓的宝藏,不一会儿就挖出几块黄白色的筒状骨头。哥哥把它们小心包好放到怀里,晚上我看见他耐心地蹲在黑帐篷旁,按照藏医典籍说的熬煮那些骨头,远古的海留下的遗骸使我安稳睡去,一如那时原始的生命们安眠于海中。
我骑车沿着海岸线漫无目的地来回骑行,时不时停下来望向大海,周围不时有人好奇地看我,又顺着我的目光看向海,在他们眼里海当然是稀松平常的,而我却被深深吸引,像是听见她靠在我的肩头向我轻语心声,那心声是如此出乎意料但千真万确。她对我说,住在海边的人认为,探索海的对岸以及海本身是一件重要而又自然的事情,人们在海上航行,垂钓,冲浪,海不是一个悬置在人们生活之外的存在。而对我来说,牧人越过雪山,踏过草地,但唯独未曾穿过湖面,也未曾试探湖面以下的世界,湖对于我来说是值得敬畏的,是一直存在并将继续存在下去的。
我还是没勇气去找她。夕阳从西侧的灯塔背后散发出万丈金光,海上的落日气势逼人,而且和藏北不同,风早已经停了,一切都在那么柔美平和的氛围中滑向黑夜。轮船发出一阵低沉的笛声,告示着返航和一天的结束。
一轮半圆的巨日正沉下远处的海平面,我往落日的方向骑行,夕阳不久后彻底消失,轻柔的海风间令人陶醉的夜色开始缓慢降临,开往海岛观光的夜航船只也开始起航,我买了张船票上船,决定上岛去看看四面皆海的场景。船上循环播放了几遍法兰克·辛纳屈《夏日的风》,轮船开了三十分钟左右后到达小岛,游客们拍照留念,我买了瓶啤酒在岛上看了一圈,岛不大,除了灯光点缀丰富以外并无特色可言。
不久轮船返航,我走上甲板观望四周,白天的海那坚定的蓝色现在却甘愿成为瞬息变化的暮色的背景板,远近色调各有不同。接近港口的海倒映出五彩斑斓的灯光,在海浪的浮动下,近岸的海像是在把白天余光的碎片翻涌上来了。藏北的湖现在应该在高原温度骤降的夜色里暗潮涌动吧,那里没有光,可哥哥总能看见湖,在我睡不着的夏夜里,雷雨天黑暗的卧室里,哥哥突然梦醒似地坐起来呓语,说刚才的雷击中了他右手边的湖面。
船缓缓靠岸时,有个女孩骑着一辆蓝色的自行车,绕过岸边准备登船的人群驶去,那身影有些眼熟,我继续望着,才意识到那就是她。我和她仅有十几米的距离,我想喊她,可是喊不出口,只有层层海浪执着地拍上岸边发出单调的涛声,她很快就骑远了。
船靠岸后我赶紧骑车追去,她已经驶离码头熙攘的人群开始加速。我好不容易才看见她在远处海岸边依稀可辨的背影,试图加速追上她,但在一个海滩的低地处我跟丢了,这里距离刚才的码头大概有好几公里远了。
海滩的篝火边有一阵奇特又熟悉的音乐声,是藏北的锅庄舞曲。我惊愕之余再次仔细聆听,确认那是来自《牧人风暴》专辑中的一首舞曲。一群人正在围着篝火跳锅庄,看动作显得生疏,还有一张海报立在旁边。我把车靠在路边的栅栏上,走到沙滩上,一个年轻女孩坐在海报旁边的桌椅上,带着浓重的当地口音向我推销门票,海报写的是藏北面具艺术家罗聂多尔贡的作品展览,门票一张价格不菲,这个艺术家我有所耳闻,但不怎么了解其作品风格。
“这次展览有艺术家从未展出过的新作品,这些面具作品的灵感,来自高原远古的海洋中的古老无颌鱼类。”女孩照本宣科读着手上的传单,“因为艺术家的爱人来自我们本地,且恰逢他们的女儿在这里出生,所以这次展览从高原改到了海边,值得一看哟,还有免费酒品畅饮。”
“为什么要跳锅庄?”我问道。
“可能是因为艺术家喜欢吧,刚才他还在这里跳舞来着,”女孩看了看四周,“现在应该是去化装了,因为晚上还有面具舞会。”
“您有看到一个骑着自行车的女孩子从这边过去吗?”我突然想起了正事,“一个短头发,穿蓝色短袖旧牛仔裤的女孩子。”
“骑自行车女孩子有好几个,都买票进去了,”她指了指旁边停着的几辆自行车,“一个就在刚刚进去的,大概十几分钟前。”
于是我也咬咬牙买了张票,展览场地不大,艺术家的面具作品像风马旗一样挂在场地两侧,中间是一幢临时装修的藏式二层小楼,在海岸边显得很突兀,没什么创意。我走进那幢小楼,在门厅处一个身着古埃及法老面具的半裸男递给我一个面具,并示意我戴上,我戴好面具走了进去,房间很大,地板踩上去有一种不平稳的浮动感,像是踩在小型汽船上。房间里大概有几十个人,有男有女,所有人都戴着我所戴的这种面具,天花板的音响里流出《午夜巴黎》里那首著名的《如果你见到我妈妈》。我留心观察人群,其中大概有七到八个短发女孩,这时有个女孩放下手里的香槟杯,匆忙走上楼去,尽管走廊那里有二楼谢绝参观的标志,但我还是跟了上去。
短发女孩走进二楼的一个化妆间,接了个电话,从声音我判断出来那不是她。正准备下楼时,有个声音从后面叫住了我。
“二楼是不允许进来的,没看到牌子吗?”对方有些不高兴。
“抱歉。”我转身发现一个只化了半边脸的男人站在房间门口,他的左脸涂成了藏戏面具的配色,从他的口音我判断出他就是那个藏北艺术家,而刚才的短发女孩也从化妆间走了出来,原来她是艺术家的妹妹,“贸然进来实在抱歉,”我摘下面具表示歉意,“我以为她就是我要找的那个女孩。”
“有意思。”艺术家在面具下咯咯地笑了起来,“竟然真的有人在面具晚会上找人。”
“犹豫一整天了。”我说,“鼓起勇气想找她,没想到是在这种地方。”
短发女孩和他用家乡话道别,意思是:再见,祝你长寿。我再次向女孩表示歉意,和艺术家一样向短发女孩道别。
“你也来自藏北?”艺术家听到我的道别语,略显惊讶。
“是的,说实话我是来找恋人的,她的家乡就是这里。”
“这里的女孩可都不太好相处,海造就了她们古灵精怪的性格。”艺术家把我让进卧室,他继续化装,“我的妻子就来自这里,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我被她吓得不轻,心想怎么会有这样的女孩,不过我很快就爱上了她,那像是一种特殊的调味酱,一旦尝过,除了厌恶和深爱,你不会得到第三种结果。”
我坐到他后面的沙发上,他在镜子里化着半张脸的妆,“那藏北造就了我们怎样的性格呢?”
“以前我们在道别的时候互祝长寿,见面时欣慰地说路途不远吧?而对方也总是回答我们不远。因为我们深知藏北环境恶劣难以长寿,路途遥远难以相见,这就像海浪从她们出生开始就在她们耳边阵阵低语一样。”他开始在右脸上化妆,“我们无法永生因此我们永恒地祝愿彼此长寿,于是关于记忆就从语言再到艺术中体现出来。记忆是最宝贵的,虽无人理解但无可替代。今晚展览的记忆从远古的海洋开始,一直到现在你我面前的这片海洋。”
我们望向窗外,夜晚的海仍然涛声不断,无数的生命和无数的记忆似乎在其中翻涌不止。
“那应该是一段了不起的旅程。”
“是啊,那是生命最引以为傲的一段旅程,科学家称其为进化史,我称其为心灵史。”他说,“戴上你的面具,该寻找我们的记忆和那个女孩了。”
艺术家带上藏戏面具,把属于他的无骨鱼面具夹在腋下,穿上一身藏戏服和我一起下楼。我们下到二楼时所有人戴着面具向着楼梯这边,一众白色的毫无表情的面具仰视着艺术家,艺术家夸张的鱼头面具同样凝视着我们,像是落单的远古鱼在一片白色的珊瑚间摸索鱼群登陆的方向。
“今晚,生命将回溯它的记忆,重新潜入它耗尽万年游出的远古的海。”艺术家说,“我的朋友们,作为同类生命的一员,请尽情享受生命在今晚带给你的怦然心动,像亿万年前这头鱼第一次上岸一样让你的感官彻底地灵敏和好奇起来。当然,进化赋予我们思考,但也使得我们被笨重的感官压力所束缚,因此请尽情享受房间四处的美酒,你会感到万物向你迎面膨胀而来,形体和色彩灵动自由。同时,我的作品介绍也将开始!”
灯光暗了下去,地板下面有水流声,壁灯在几秒后亮起,脚下的玻璃地板被撤去了掩板,原来地板下面是一处地下室改装的水池,颜色稍显浑黄的水池里充满各种颜色的远古鱼面具,它们像是被海底的漩涡卷起一样随着水流左右翻腾。人们都争先恐后地低头看水池里的各色面具,远古鱼的面具没有躯体但形态丰富,整体拥有统一的风格但进化的丰富性已经初露端倪,像是刚从远古的海里一股脑撒网捞上来似的。我抬头看向台阶上的艺术家,他看着人们低头观赏他的艺术品的样子,向我张开了硕大的鱼嘴,应该是表示面具之下的他笑了。
“各位,请务必不要忘了脚下的美酒,美酒使神也变得像我们一样贪婪。”他指了指房间四处的水龙头说,“水龙头连接了地下的啤酒池,随着啤酒的减少,感官的轻盈,地板会慢慢沉降,“等美酒全部耗尽时,远古的鱼群上浮,现代的我们下沉,请尽情享受吧!”
艺术家说完这句话后就彻底消失了,再见到他是三年后的一次笔会上,他神情严肃地讲述关于面具的故事,也没有认出我。我在那时突然觉得那不是他,他戴上了某种面具,面具之下的他却认出了我,正向我微笑,让我想起那张硕大的鱼嘴。
于是晚会上人们开始随着音乐跳舞起哄,灯光随着舞曲的节奏闪耀不止,地板像是海浪中的甲板一样晃动。我一边留意着女孩和艺术家的踪影,一边打开水龙头帮助地板沉降。
“为什么有这么强烈的偏见?”一个短发女孩靠近我大吼道,“关于海他到底了解什么?”
“或许什么也不知道。”因为音乐声音太大,我吼叫出来的声音不像是自己的,女孩的声音也许同样如此。
“那你知道什么?”
“我知道那天的大海宁静得像是晚秋的麦田。”我突然想起她的话,向着女孩大声吼道,“渔船在月光下缓缓返程,像农民不紧不慢地走过田埂。”
面具里女孩沉默不语地凝视着我,两只手放在我的面具上摩挲了一会,我借着忽明忽暗的灯光想要看清她的眼眸时,她把她酒杯里的酒全部倒给了我,然后转身消失在了人群里。我继续拿着啤酒杯,步伐不稳地在嘈杂的环境里寻找她的身影,但这时音乐突然变得舒缓起来,随着查特·贝克的《我可笑的情人》,人们向离自己最近的人伸出手臂,或挽住她的腰,或搭在他的肩。我一个人成了落单的鱼。这时有人从背后轻轻拍我,一位短发女孩把手搭在我的肩膀上,扶住晃动的我。她身上有股淡淡的柠檬香水味,我把一只手放在她的腰上,靠近些想要看清她的眼眸,那双我曾潜泳过的如海一般的眼眸我怎么也不会认错,但我看不清。
“那天的大海宁静得像是晚秋的麦田。”我把啤酒一口喝尽,然后轻轻地说。
“或许我们这些远古的鱼就诞生在那个夜晚。”她贴到我的耳边细语。
“不是的。”有人递给我一杯啤酒,我接着说,“是你出生的那个夜晚,你跟我说过的,你出生的夜晚,大海宁静得像是晚秋的麦田。”
女孩沉默不语,而我决定继续自顾自地说下去:
“渔船在月光下缓缓返程,像农民不紧不慢地走过田埂。真是一幅宁静美好的画面,我那时就应该这样想的,也早该意识到海不是湖,湖也不是海。”
“那又有什么关系呢?”
我把啤酒一饮而尽,“我在海边坐了好久,我下定决心再见到你时,就要在这片海的面前再次向你表白。命运让我这个淡水鱼离开湖而游向海,我便毫不犹豫地跳江南下。”
“或许我也应该去看看你说的那些湖。”她轻轻地抱住我,随着音乐缓慢摇摆,所有人都在摇摆,地板晃动加剧,我们像是遭遇了一场远古无人知晓的海底地震。
她靠在我的肩头,我们随着音乐久久地抱在一起缓慢移动身体,她像是梦见了什么一样低语:“我看见好多湖,像玉石碎了一地。”
后来音乐再次切换,在酒精温软却强势的进攻下我已经站不稳,她也已经消失不见,脚下远古的大海已经隐隐见底了。我坐到角落的沙发吐了一地,哥哥的身影再次晃过波光粼粼的湖面,我的面糊船准备从藏北的湖远航到这里的海,海风轻轻拂起她的短发,她笑着把蓝色的纸船递给我。
再醒来时,我躺在一个即将拆除装饰的蓄水池,里面尽是人们的呕吐物和聚会散去后令人不快的酸涩味,除了我之外那些参加聚会的人已经全部离去。我询问了拆除场地的渔民,他们说艺术家用了三天改造他们的蓄水池,凭空建起一栋二层板房。他也凭空建起了我的一场梦。我推着自行车沿海岸慢慢走着,昨晚我到底回溯了怎样的记忆?那些女孩里到底有没有她呢?我记不清,能确定的是,付给艺术家凭空造梦的钱之后,剩下的钱只够我回到学校,在这个夏天我是回不到藏北的湖畔了。
于是那个夏天我索性就留在了她的故乡,边打工边和她再次约会,她对于我跑到那里很是惊讶。她在我打工的书店看书等我下班,晚上我们一起在海滨散步,灯光暗下去时接吻拥抱,在廉租公寓里听她带来的旧CD,淋着季风送来的细雨喝不同的汽水。后来开学不久我们再一次分手了,但这次再没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或许这次是因为我知道了这是时常发生的事情,特别是在年轻时的夏天。或许我应该在那个笔会上告诉艺术家,再特殊的调味酱也会有不再新鲜可口的一天,又或许他早就知道这一点。
七年后的早上,我和几位朋友登上哲蚌寺后的根培乌孜山,这里是拉萨城区离天空最近的山顶,冬日清冷的空气里可远眺数十里的风光。朋友们都在观赏拉萨城的风光,我望向四周如海洋般蔚蓝的天空,来自北方的风一阵阵掠过,像是海浪不断涌上海岛,我想起七年前第一次站在海边。
我闭眼听风,看见数亿年前的高原在远古的海底里沉睡,我站在名为根培乌孜的海岛上,这时四周的海就是湖,湖就是海。只不过我们已经远离了这些记忆,远离了往昔的温暖和睦,但哥哥没有,哥哥在草甸和咸湖间寻访海,他从一处湖游到另一处湖,自由地穿梭在海底。

念扎边桑,藏族,西藏那曲人,1999年出生,那曲市文化联合会民间作家艺术家协会会员,现就职于西藏拉萨中学,从事英语教学工作,有作品发表在《西藏文学》《羌塘》等,著有短篇小说集《牧童和他的骑士生涯》,长篇小说《漩涡寻忆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