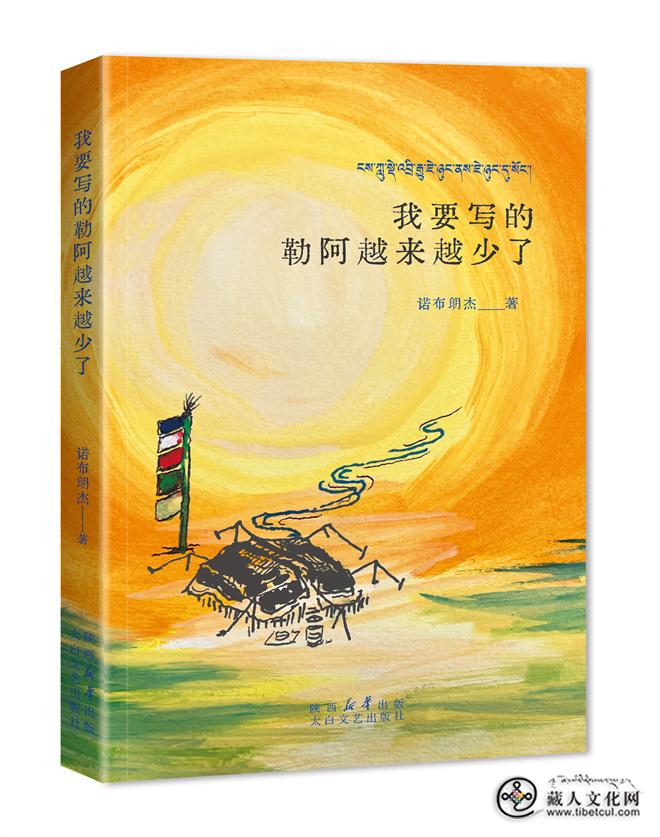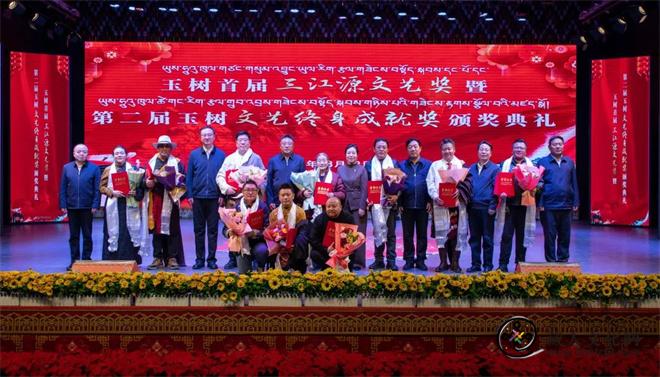正在写作中的柴春芽
近日,藏人文化网“藏人之友”柴春芽进驻甘肃省天祝藏族自治县天堂寺,开始写作其构思十年的批判现实主义幻想小说《罂粟十字公社——祖母阿依玛的一百零一个故事》。天堂寺环境舒适,地杰人灵,著名作家张承志曾在其对面的北山林场创作了《心灵史》。柴春芽选择在天堂寺写作,是基于他浓烈的藏地情怀。
2006年8月,柴春芽结束了为期一年的康巴藏区的支教生活后,创作了自传体长篇小说《戈麦高地》(最初题为《慈航与流放》)。《戈麦高地》的部分段落曾在网上广为流传。这部具有狂野散文风格的小说是对美国“垮掉一代”(Beat Generation)大师杰克•凯鲁亚克的致敬之作,以主人公漫游藏地的经历,展开了追索精神自由的宗教之旅。小说批判了现代资本主义对中国年轻一代的精神戕残,同时呼吁年轻一代摒弃虚伪无聊、僵化枯燥的城市生活,投身于大自然的怀抱,在天地之间和禅修状态中,复归纯真与灵性。戈麦高地海拔4000多米,远离城市和公路,没有电和通讯,但戈麦高地上的藏人却快乐地生活在这片被鲜花、牛羊、马匹和寺院簇拥的土地上,自由自在,无拘无束。《戈麦高地》反映和表达了藏族文化中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是现代社会人类生存的参照。
柴春芽说,《戈麦高地》已经修改了三遍,但他还要将其搁置一年,待完成《罂粟十字公社》后再做最后一稿的修定。目前,他正在天堂寺创作的小说《罂粟十字公社》,以荒诞、变形、夸张的手法,讲述一对双胞胎兄弟从肉体沦落到灵魂飞升的系列传奇故事。《罂粟十字公社》预计30万字,目前已完成15万字。
(藏人文化网兰州记者 刚杰·索木东 图/文报道)
附:评《慈航与流放》
作者:阿乙
这个华丽诗人关于自己一年西藏行走的小说,落到从不行走的我手中,有如一滴油掉落在热锅上。这阅读的过程,便是无尽误会、嫉妒的过程。我的大脑在维护一些东西,而那些文字在试图撬开一些碉堡,两者之间兵戈相见,噼趴作响。
我习惯呆在阴沉的角落,承受逐渐黑掉的光线。但是这个同事却骄傲地行走。我曾经用从农村到城市的方式摆脱某种东西,而他在用城市到农村的方式,也在摆脱某种东西。也许叫“寻找”好点——对某种类似于卡夫卡的疼痛的追问,对生命本意的破解。我在行进中坐受绝望的折磨,他在行进中强行剔除这糟糕的情绪。
假设我去了西藏(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我将陷入到乡村黑夜的悲哀当中,我将被永恒的时光囚禁在五指山下,勤勉地自伐,百无聊赖地哭泣。我并非恐惧于具体的空间,实际上我本身就是一个移动的空间,这个空间里边充满了无聊、无为和绝望。任何迁移都只能带给我一天的新鲜刺激,剩余的时间不会再发生任何化学反应。而柴春芽是怀着信念去穿州过府,他在出发前自豪地向朋友喊:兄弟,让我们明年再见吧。
他相信花和路,月亮与人民。这真是令人嫉妒的心性。
小说的书名综合了昌耀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意像,代表了写作者自己的体验。在遥远的戈麦高地,“慈航”与“流放”的体验浇铸在书写者身上。在这个地方,他像一根试管,承受着自己关于生命的试验。看起来他的答案也不清楚,也许答案本身就是行走。就像船在水流中飞驰获取自由一样。但是我仍然呆在自己的城堡,不相信这纵横千里的药方。这个世界有很多寻药的人,也有很多坐以待毙的人;有很多怀抱希望、信奉浪漫的人,也有很多悲观的人。
但这不妨碍我观看写作者壮丽的内心。某些方面,我喜欢这瑰丽的文字盛宴,和壮观的高歌行进。就好像是一部过滤干净的童话,在黑夜呈现出某种温柔来。如果作品有过分之处,便是这“纯净”。我一贯害怕纯净对自己的压力——而这本小说,多多少少带有一种道德和主义上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给人的压力,体现在那些作者碰到的人身上,也体现在阅读者身上。这使小说“寻找”的含义得到部分消解,这使作者“阐释”的意思多了一些。这多少有点背离记录与承受的初衷。
这部有勇气的小说,注定将在很多人内心形成共鸣。类似的行走也将越来越多,这些用脚写的文字,将成为中国难能可贵的状态小说遗产。一些无病呻吟的主妇故事和阴险狡诈的历史传奇将受到唾弃,写作者迟早会带着自己的脸,去承受高地的冰雹。
我关于行走的体验,集中发生于郑州的一个秋夜。我在一条街又一条街中穿梭,寻找解救自己的娱乐方式。最后直到把自己搞饿了,才在一大碗烩面里体会到动物式的感恩。
一条街,又一条街。我始终没有摆脱这移动牢房的心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