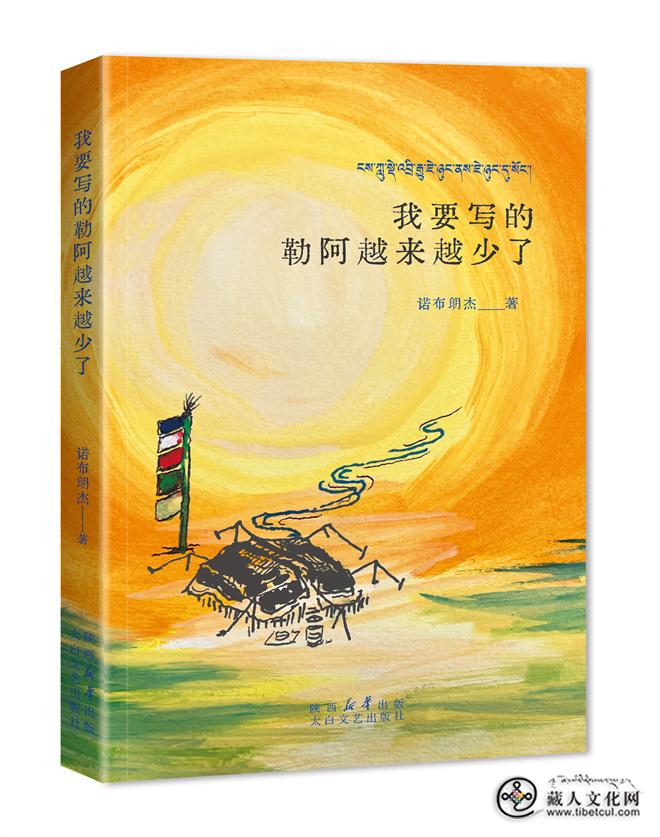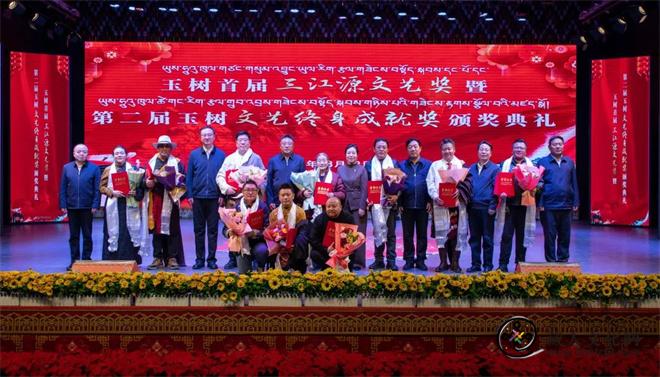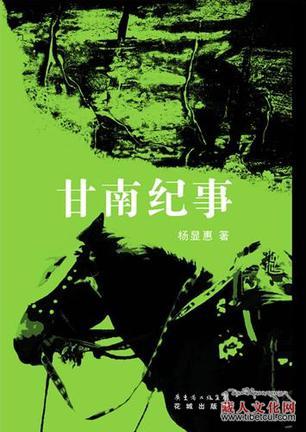
В В В В жқЁжҳҫжғ дә”е№ҙз”ҳеҚ—иЎҢзЁӢз§Ҝж”’дәҶиҝ‘10дёҮеӯ—зҡ„йҮҮи®ҝ笔记пјҢ2011е№ҙеҮәзүҲзҡ„йқһиҷҡжһ„ж–ҮеӯҰгҖҠз”ҳеҚ—зәӘдәӢгҖӢз”ЁеҺ»дә”еҲҶд№ӢдәҢпјҢеҗҺз»ӯйғЁеҲҶеҶҷдҪңи®ЎеҲ’2012е№ҙеҶ¬еӨ©е®ҢжҲҗпјҢиҝҷд№ҹе°ҶжҳҜд»–зҡ„е°Ғ笔д№ӢдҪңгҖӮ
В В В В дҪң家жқЁжҳҫжғ дёәдәҶгҖҠз”ҳеҚ—зәӘдәӢгҖӢпјҢж–ӯж–ӯз»ӯз»ӯеҺ»дәҶз”ҳеҚ—и—Ҹең°дә”е№ҙпјҢд»Һ2007е№ҙеҲ°2011е№ҙпјҢжҜҸе№ҙйғҪеҺ»з”ҳеҚ—и—Ҹең°дёӨдёүж¬ЎпјҢжҜҸж¬Ўе°‘еҲҷдёҖжҳҹжңҹпјҢеӨҡеҲҷеҚҠжңҲдәҢеҚҒеӨ©гҖӮдә”е№ҙйҮҢпјҢжқЁжҳҫжғ д»Ҙе…°е·һдёәж №жҚ®ең°пјҢеӨҡж¬Ўиҝӣе…Ҙз”ҳеҚ—иҚүеҺҹпјҢиҝӣеҮәи—Ҹж°‘зҡ„зүӣжҜӣжҜЎжҲҝе’ҢжҰ»жқҝжҲҝеҒҡйҮҮи®ҝгҖӮз”ҳеҚ—и—Ҹж—ҸиҮӘжІ»е·һиҫ–дёғдёӘеҺҝпјҢд»–и·‘дәҶе…ӯдёӘеҺҝпјҢеҺ»иҝҮзҡ„жқ‘еә„жңүдәҢеҚҒдёӘгҖӮдә”е№ҙзҡ„з”ҳеҚ—иЎҢзЁӢдёәд»–з§Ҝж”’дәҶиҝ‘10дёҮеӯ—зҡ„йҮҮи®ҝ笔记пјҢ2011е№ҙеҮәзүҲзҡ„йқһиҷҡжһ„ж–ҮеӯҰгҖҠз”ҳеҚ—зәӘдәӢгҖӢеҸӘз”ЁеҺ»дәҶдә”еҲҶд№ӢдәҢгҖӮд»–жҠҠиҝҷеҪ“дҪңиҮӘе·ұеҶҷдҪңз”ҹж¶Ҝзҡ„жңҖеҗҺдёҖж¬Ўж—…иЎҢвҖ”вҖ”66еІҒзҡ„жқЁжҳҫжғ еҒҡиҝҮеҝғи„ҸжҗӯжЎҘжүӢжңҜпјҢд»–зҡ„зҗҶжғіжҳҜзңҹе®һең°еҶҷеҮәз”ҳеҚ—и—Ҹж°‘иҮӘ1950е№ҙиҮід»Ҡзҡ„з”ҹжҙ»еҸІгҖӮ
В В В В зҺ°еңЁжқЁжҳҫжғ еңЁиҝӣиЎҢд»–зҡ„гҖҠз”ҳеҚ—зәӘдәӢгҖӢеҗҺз»ӯйғЁеҲҶзҡ„еҶҷдҪңпјҢи®ЎеҲ’2012е№ҙеҶ¬еӨ©е®ҢжҲҗгҖӮвҖңеҗҺз»ӯйғЁеҲҶжҳҜе…ідәҺи—Ҹж°‘зҡ„зІҫзҘһж–ҮеҢ–з”ҹжҙ»зҡ„жҸҸиҝ°гҖӮи—Ҹж°‘ж—Ҹзҡ„дј з»ҹж–ҮеҢ–гҖҒз”ҹжҙ»д»·еҖји§Ӯд№ҹжҠөжҢЎдёҚдҪҸзҺ°д»Је·ҘдёҡеҢ–еӨ§жҪ®зҡ„еҪұе“ҚвҖқпјҢжқЁжҳҫжғ иҜҙпјҢвҖңдҪҶ他们зҡ„е®—ж•ҷз”ҹжҙ»пјҢеҜ№дҪӣж•ҷзҡ„дҝЎд»°гҖҒеҜ№й•ҝиҖ…зҡ„е°ҠйҮҚвҖҰвҖҰиҝҷдәӣжҳҜдёҚеҸҳзҡ„гҖӮвҖқ

гҖҠз”ҳеҚ—зәӘдәӢгҖӢдёӯзҡ„еҫҲеӨҡж•…дәӢйғҪеҸ‘з”ҹеңЁжүҺе°•йӮЈжқ‘
В В В В вҖңжҲ‘зј–дёҚдәҶж•…дәӢвҖқ
В В В В В гҖҠз”ҳеҚ—зәӘдәӢгҖӢеҫҲеӨҡж•…дәӢйғҪеҸ‘з”ҹеңЁжүҺе°•йӮЈиЎҢж”ҝжқ‘гҖӮжүҺе°•йӮЈжҳҜи—ҸиҜӯйҹіиҜ‘пјҢзҹіеӨҙеҢЈеӯҗзҡ„ж„ҸжҖқгҖӮиҝҷжҳҜиҝӯеұұиҘҝз«Ҝзҡ„дёҖйҒ“еұұжІҹпјҢжө·жӢ”жңҖдҪҺеӨ„2900зұіпјҢйЎәжІҹеҫҖдёҠиө°дәҢеҚҒе…¬йҮҢпјҢе°ұдёҠдәҶеұұйЎ¶пјҢзҝ»иҝҮеұұе°ұжҳҜеҚ“е°јеҺҝеҺҝеўғгҖӮеӣӣдёӘжқ‘еә„дёҖжәңе„ҝжҺ’ејҖеқҗиҗҪеңЁеұұеқЎдёҠпјҢиғҢйқ зҷҪиүІзҹізҒ°еІ©зҡ„еӨ§еұұпјҢеҜ№йқўзҡ„еҚ—еұұдёҠй•ҝж»ЎиӢҚз»ҝзҡ„жқҫж ‘гҖӮжңүдёүиӮЎеұұж°ҙд»Һжқ‘еҗҺзҡ„дёүжқЎжІҹжөҒеҮәжқҘпјҢжҺЁеҠЁзқҖж°ҙзЈЁж—ӢиҪ¬гҖӮеұұеқЎдёҠйЈҺ马旗йЈҳйЈҳгҖӮ
В В В В жүҺе°•йӮЈжҳҜз”ҳеҚ—е·һйЈҺжҷҜжңҖзҫҺзҡ„ең°ж–№пјҢд№ҹжҳҜи—Ҹж°‘з”ҹжҙ»еҫ—еҫҲиү°иҫӣзҡ„ең°ж–№гҖӮ他们зҡ„зү§еңәе°ұеңЁжқ‘иғҢеҗҺзҡ„зҹіеӨҙеұұеұұйЎ¶пјҢеңЁжө·жӢ”3500зұіеҲ°4500зұізҡ„еҢәеҹҹеҫҖдёң延伸зәҰ150е…¬йҮҢпјҢжңҖиҝңеҲ°иҫҫи…ҠеӯҗеҸЈпјҢдёҖзӣҙжҠҠиҝӯеұұиө°е®ҢгҖӮжңүзҡ„зү§ж°‘еҲ°зү§еңәеҺ»пјҢиҰҒзҝ»еҫҲеӨҡеұұпјҢиө°дёӨдёүеӨ©гҖӮжңүдәӣеӯ©еӯҗе°ұеҮәз”ҹеңЁиҝӯеұұж·ұеӨ„зҡ„зү§еңәпјҢзӣҙеҲ°иҰҒдёҠеӯҰзҡ„ж—¶еҖҷпјҢзҲ¶жҜҚжүҚжҠҠ他们йҖҒеҲ°жүҺе°•йӮЈжқҘгҖӮ
В В В В жүҺе°•йӮЈжқ‘ж’ӯз§ҚгҖҒ收еүІзҡ„ж—¶еҖҷпјҢзү§еңәиҰҒжҠҪдәәеӣһжқҘе№Іжҙ»гҖӮзү§еңәиҰҒжҗ¬е®¶пјҲиҪ¬еңәпјүж—¶пјҢ家йҮҢиҰҒжҠҪдәәеҲ°зү§еңәеҺ»её®еҝҷгҖӮ家дәәжҠҠзЈЁеҘҪзӮ’зҶҹзҡ„йқ’зЁһйқўйҖҒеҲ°зү§еңәеҺ»пјҢзү§еңәиҰҒжҠҠзүӣзҫҠиӮүе’Ңй…ҘжІ№й©®еӣһ家жқҘгҖӮжҜҸдёӘ家еәӯзҡ„дәәдёҖе№ҙеӣӣеӯЈиҰҒеңЁиҝӯеұұзҡ„еұұжўҒе’ҢеіЎи°·йҮҢжқҘжқҘеҺ»еҺ»гҖӮ
В В В В жқЁжҳҫжғ жӣҫз»Ҹе’ҢдёӨдҪҚзү§ж°‘йӘ‘马д»Һи…ҠеӯҗеҸЈз©ҝи¶ҠиҝӯеұұпјҢеӣ дёәдёӢйӣЁе’ҢйҖ”дёӯдј‘жҒҜпјҢеҚҒеӨ©жүҚиө°еҲ°жүҺе°•йӮЈгҖӮеҮ жқЎеұұи°·йҮҢе…ЁжҳҜеӨ§еӨ§е°Ҹе°Ҹзҡ„зҹіеӨҙз–ҷзҳ©пјҢ第еҚҒеӨ©д»ҺжІҹйҮҢиө°еҮәжқҘзҡ„ж—¶еҖҷпјҢдёүеҢ№й©¬йҮҢжңүдёҖеҢ№иө°зҳёдәҶдёҖжқЎи…ҝгҖӮ
В В В В вҖңеҲ°жүҺе°•йӮЈпјҢйӘ‘马з©ҝи¶Ҡиҝӯеұұз»ҸеёёзҙҜеҫ—и…ҝиҪҜпјҢдёӢ马时дёҖеҸӘи„ҡиё©еҲ°ең°дёҠпјҢеҸҰдёҖеҸӘи„ҡиҝҳеңЁй©¬й•«дёҠеҸ–дёҚдёӢжқҘпјҢжҖ»жҳҜж‘”еҖ’гҖӮжҜҸж¬ЎйғҪиҰҒеҒҡдјҙзҡ„и—Ҹж°‘жҠұдёӢ马жқҘгҖӮвҖқжқЁжҳҫжғ иҜҙгҖӮ
В В В В дёҠеҲқдёӯзҡ„ж—¶еҖҷпјҢжқЁжҳҫжғ еңЁиЎ—еӨҙз»ҸеёёзңӢеҲ°д»Һз”ҳеҚ—еҲ°е…°е·һеҺ»зҡ„и—Ҹж°‘пјҢеӨ§йғЁеҲҶжҳҜз©ҝзқҖзҡ®иў„зҡ„еҰҮеҘігҖӮеҘ№д»¬иғҢзқҖеӯ©еӯҗгҖҒзӮ’йқўеҸЈиўӢе’Ңй…ҘжІ№пјҢеҺ»жҺўи§ҶдәІдәәгҖӮеҘ№д»¬дёҚдјҡиҜҙжұүиҜқпјҢжӢҝзқҖеҶҷжңүдәІдәәең°еқҖзҡ„дҝЎпјҢеңЁиЎ—еӨҙжӢҰдҪҸдәәй—®и·ҜгҖӮ
В В В В 1980е№ҙд»ЈпјҢжқЁжҳҫжғ зңӢиҝҮйҷҲдё№йқ’зҡ„иҘҝи—Ҹз»„з”»е’ҢдҪ•еӨҡиӢ“зҡ„и—Ҹең°жІ№з”»пјҢжңүдәҶеҺ»зңӢзңӢи—Ҹең°йЈҺжғ…зҡ„еҶІеҠЁгҖӮд№ҹжҳҜйӮЈж®өж—¶й—ҙпјҢи—Ҹж—ҸдҪң家жүҺиҘҝиҫҫеЁғжқҘеҲ°жқЁжҳҫжғ 家пјҢ他们дҝғиҶқй•ҝи°ҲдёүеӨ©гҖӮ
В В В В дҪң家жүҺиҘҝиҫҫеЁғжӣҫзәҰжқЁжҳҫжғ д»ҘжҸҙи—Ҹе№ІйғЁзҡ„ж–№ејҸеҺ»иҘҝи—ҸпјҢд»–еҸҜд»Ҙеё®еҠ©и°ғеҠЁвҖ”вҖ”д»–зҲ¶дәІеҪ“ж—¶жҳҜжӢүиҗЁеёӮй•ҝгҖӮдҪҶеӣ дёәеӯ©еӯҗиҝҳе°ҸпјҢжқЁжҳҫжғ дёҚеҝҚеҝғжҠҠеҰ»е„ҝжҠӣдёӢгҖӮ
В В В В 2001е№ҙпјҢжқЁжҳҫжғ еә”гҖҠе…°е·һжҷҡжҠҘгҖӢзҡ„жңӢеҸӢйӮҖиҜ·еҺ»з”ҳеҚ—и®ІиҜҫпјҢд»–еңЁиЎ—иҫ№д№Ұж‘Ҡд№°еҲ°дёҖжң¬гҖҠз”ҳеҚ—е·һеҝ—гҖӢпјҢиҝҷжҲҗдәҶд»–дәҶи§ЈиҝҷдёӘең°еҢәзҡ„жҢҮеҚ—гҖӮ
В В В В д»Һе…°е·һеҲ°з”ҳеҚ—и—Ҹең°зҡ„и·ҜдёҠпјҢжқЁжҳҫжғ еҘ”жіўдә”е№ҙпјҢд»–иҰҒзңҹзҡ„зҶҹжӮүи—Ҹж°‘пјҡвҖңдёҚдәҶи§ЈжІЎжңүеҠһжі•еҶҷгҖӮвҖқд»–иҠұе·ҘеӨ«жңҖеӨҡзҡ„е°ұжҳҜеҲ°зү§ж°‘зҡ„зү§еңәпјҢзңӢ他们дёҖеӨ©зҡ„з”ҹжҙ»пјҢжҖҺд№ҲжҢӨзүӣеҘ¶пјҢжҖҺд№Ҳжү“й…ҘжІ№пјҢзғ§зүӣзІӘиҝҳжҳҜзғ§жҹҙзҰҫпјҢеҲ°е“Әе„ҝз ҚжҹҙзҰҫпјҢз”Ёж–§еӯҗиҝҳжҳҜз ҚеҲҖпјҢз ҚеҲҖжҳҜд»Җд№Ҳж ·зҡ„пјҢжүҺдёҖдёӘеёҗзҜ·з”ЁеӨҡе°‘ж №з»іеӯҗжӢүиө·жқҘпјҢең°дёӢиҰҒй’үеӨҡе°‘ж №ж©ӣеӯҗпјҢй—Ёеёҳд»Җд№Ҳж ·пјҢжҖҺд№ҲжҺҖејҖпјҢзғҹжҖҺд№ҲеҶ’еҮәеҺ»вҖҰвҖҰ
В В В В жқЁжҳҫжғ жҠҠиҝҷдәӣдәӢжғ…зңӢжҲҗжҳҜе°ҸиҜҙ家зҡ„еҠҹиҜҫгҖӮеё®еҠ©иҝҮд»–зҡ„и—Ҹж°‘пјҢд»–дјҡжҺҘ他们еҺ»еҢ—дә¬зҺ©пјҢиҙҹжӢ…еҫҖиҝ”жңәзҘЁе’ҢйЈҹе®ҝпјҢеҪ“他们зҡ„еҜјжёёпјҢи·ҹе№ҙиҪ»зҡ„и—Ҹж°‘д»Ҙе…„ејҹзӣёз§°гҖӮ
В В В В жүҺе°•йӮЈдёӢиҫ№зҡ„еӣӣдёӘжқ‘еҜЁпјҢд»ҺиҘҝеҫҖдёңжҺ’еҲ—пјҢеҲҶеҲ«еҸ«иҫҫж—ҘгҖҒд»Је·ҙгҖҒдёҡж—Ҙе’ҢдёңжҙјгҖӮжҜҸж¬ЎеҲ°жүҺе°•йӮЈпјҢжқЁжҳҫжғ йғҪдјҡдҪҸеңЁдёҡж—Ҙжқ‘дёҖдҪҚеҸ«ж №зҷ»зҡ„иҖҒдәә家йҮҢгҖӮеӨҡж¬Ўи—Ҹең°иЎҢпјҢд»–е’Ңж №зҷ»жҲҗдәҶеҘҪжңӢеҸӢгҖӮиҖҒдәәз”ҹзҒ«зғ§ж°ҙпјҢиҜ·е®ўдәәе–қй…ҘжІ№иҢ¶еҗғзіҢзІ‘пјҢдёәе®ўдәәе’Ңйқўж“ҖйқўжқЎпјҢжҠҠжҢӮеңЁжҲҝйЎ¶зҡ„дёҖеқ—е№ІиӮүжӢҝдёӢжқҘжіЎеңЁж°ҙйҮҢеҒҡиҸңгҖӮ他们еҝҷзўҢзҡ„ж—¶еҖҷпјҢжқЁжҳҫжғ дјҡеёҰзқҖж‘„еғҸжңәеҺ»жқ‘еӨ–зҡ„дёҖзүҮй«ҳең°пјҢд»ҺиҝҷйҮҢеҸҜд»ҘзңӢи§Ғдёңжҙјжқ‘пјҢд№ҹзңӢи§ҒиҘҝиҫ№й«ҳеқЎдёҠзҡ„д»Је·ҙжқ‘е’Ңе®ғзҡ„еҜәйҷўгҖӮ
В В В В йҖҡиҝҮдёӘдәәе‘Ҫиҝҗе‘ҲзҺ°з”ҳеҚ—и—Ҹең°зҡ„з”ҹжҙ»еҸҳиҝҒпјҢжҳҜжқЁжҳҫжғ еҶҷгҖҠз”ҳеҚ—зәӘдәӢгҖӢзҡ„дё»йўҳгҖӮ然иҖҢе·Із»ҸеҮәзүҲзҡ„гҖҠз”ҳеҚ—зәӘдәӢгҖӢеҸӘжҳҜжқЁжҳҫжғ з”ҳеҚ—иЎҢж—…жө©з№ҒеҶ…е®№зҡ„дёҖйғЁеҲҶпјҢжӣҙеӨҡзҙ жқҗиҝҳеңЁд»–зҡ„ж–Ү件з®ұйҮҢгҖӮ
В В В В вҖңд№ҹеҸҜиғҪжңҖеҗҺзҡ„з»“жһңе°ұжҳҜй’ұзҷҪиҠұпјҢе·ҘеӨ«зҷҪиҙ№пјҢд№ҹеҸҜиғҪеҶҷдёҚеҘҪиҝҷжң¬д№ҰгҖӮдёҚиҝҮеҸҜд»ҘиӮҜе®ҡзҡ„жҳҜпјҢиҝҷжҳҜжҲ‘иҝҷдёҖз”ҹжңҖеҗҺзҡ„дҪңе“ҒгҖӮжҠҠз”ҳеҚ—и—Ҹең°зҡ„дәӢжғ…еј„жё…жҘҡпјҢд»ҘеҗҺе°ұеҶҚдёҚдјҡиҝҷд№Ҳи·‘еҮәжқҘдәҶгҖӮеҶҷдёҖзӮ№иҪ»жқҫзҡ„ж–Үеӯ—пјҢжҲ–иҖ…е№Іи„Ҷе°Ғ笔гҖӮвҖқжқЁжҳҫжғ иҜҙйҒ“гҖӮ

жқЁжҳҫжғ
В В В В з¬Ёдәәе№Ізҡ„дәӢ
В В В В вҖңжҲ‘з”ҹжҖ§ж„ҡй’қпјҢзј–дёҚдәҶж•…дәӢпјҢжүҖд»ҘйҮҮз”Ёиҝҷз§Қе®һең°йҮҮи®ҝзҡ„еҶҷдҪңж–№ејҸгҖӮвҖқжқЁжҳҫжғ иҜҙпјҢвҖңжҲ‘и®Өдёәйқһиҷҡжһ„ж–ҮеӯҰеҸҜд»Ҙзңҹе®һең°и®°еҪ•еҺҶеҸІгҖӮе®ғзҡ„д»·еҖје’Ңж„Ҹд№үдёҚеңЁд»ҠеӨ©пјҢиҖҢеңЁдәҺжҳҺеӨ©гҖӮеҰӮжһңжІЎжңүйқһиҷҡжһ„ж–ҮеӯҰпјҢе°ҶжқҘдәә们е°ұдјҡжҠҠиҷҡжһ„ж–ҮеӯҰжӯӘжӣІдәҶзҡ„еҺҶеҸІеҪ“еҒҡжӯЈеҸІгҖӮйӮЈж ·зҡ„иҜқпјҢжҲ‘们иҝҷдёӘж°‘ж—Ҹе°ұеҪ»еә•жІЎжңүеёҢжңӣдәҶгҖӮвҖқжқЁжҳҫжғ еёҢжңӣиҮӘе·ұзҡ„еҶҷдҪңеҜ№еҫ—иө·иүҜеҝғпјҢд»–еҜ№иҮӘе·ұзҡ„йқһиҷҡжһ„еҶҷдҪңд№ҹеҫҲжңүдҝЎеҝғпјҡвҖңеңЁд»ҠеҗҺдёҖж®өж—¶й—ҙеҶ…пјҢжІЎжңүдәәдјҡи¶…и¶ҠжҲ‘гҖӮ并дёҚжҳҜиҜҙжҲ‘жңүеӨҡеӨ§жүҚеҚҺпјҢжҳҜеӣ дёәеҲ«дәәдёӢдёҚдәҶжҲ‘иҝҷе·ҘеӨ«гҖӮе…үеҮӯиҒӘжҳҺжҳҜи¶…дёҚиҝҮжҲ‘зҡ„пјҢд»–йңҖиҰҒж—ўиҒӘжҳҺеҸҲдёӢе·ҘеӨ«гҖӮдҪң家们дёҚж„ҝж„ҸеҗғиҝҷдёӘиӢҰвҖ”вҖ”дёҖдёӘдәәдёҖдёӘдәәең°еҺ»и®ҝй—®пјҢеӨ§еӨҡжҳҜиҖҒдәәпјҢжІЎжңүжҳҫиө«зҡ„еЈ°еҗҚпјҢйҷӨдәҶе°ҳе°Ғзҡ„и®°еҝҶдёҖж— жүҖжңүгҖӮеҶҷеҮәиҝҷж ·зҡ„еҺҶеҸІпјҢжҳҜз¬Ёдәәе№Ізҡ„дәӢгҖӮвҖқ
В В В В жӯӨеүҚжқЁжҳҫжғ д№ҰеҶҷ1957е№ҙзҡ„еҸҚеҸіиҝҗеҠЁпјҢи®°еҪ•1960е№ҙд»Јзҡ„еӨ§йҘҘиҚ’пјҢи‘—дҪңдёӯе……ж»ЎеҜ№дәәй—ҙз–ҫиӢҰзҡ„еҗҢжғ…дёҺжҖқиҖғгҖӮж–ҮеӯҰиҜ„и®ә家йӣ·иҫҫиҜ„иҝ°гҖҠеӨ№иҫ№жІҹи®°дәӢгҖӢж—¶иҜҙпјҡвҖңзҹҘйҒ“иҝҷж®өеҺҶеҸІзҡ„дәәе·ІдёҚеӨҡдәҶпјҢеҪ“е№ҙзҡ„з”ҹиҝҳиҖ…еӨ§еӨҡе·ІзҰ»дё–пјҢе°‘ж•°е№ёеӯҳиҖ…дёүзј„е…¶еҸЈгҖӮжқЁжҳҫжғ жҠҠи°ғжҹҘеҫ—жқҘзҡ„ж•…дәӢи®ІеҮәжқҘпјҢж„ҸеңЁзҝ»ејҖе°ҳе°ҒдәҶеӣӣеҚҒе№ҙзҡ„еҺҶеҸІпјҢеёҢжңӣиҝҷж ·зҡ„жӮІеү§дёҚеҶҚйҮҚжј”гҖӮвҖқ
В В В В еӨ№иҫ№жІҹжҳҜз”ҳиӮғй…’жіүдёҖдёӘжӣҫзҫҒжҠјеҸіжҙҫзҠҜдәәзҡ„еҠіж”№еҶңеңәпјҢд»Һ1957е№ҙ10жңҲејҖе§ӢпјҢиҝҷйҮҢе…іжҠјдәҶиҝ‘дёүеҚғеҗҚеҸіжҙҫеҲҶеӯҗгҖӮ1961е№ҙе…ғжңҲпјҢеҸіжҙҫеҲҶеӯҗиў«йҒЈиҝ”пјҢжҙ»дёӢжқҘзҡ„жңүе…ӯзҷҫдәәгҖӮдёәдәҶеҶҷеҘҪгҖҠеӨ№иҫ№жІҹи®°дәӢгҖӢпјҢжқЁжҳҫжғ жҜҸе№ҙж•°ж¬ЎеҫҖиҝ”дәҺеӨ©жҙҘе’Ңз”ҳиӮғгҖӮд»–еғҸеӨ§жө·жҚһй’ҲдёҖж ·жҗңеҜ»еҲ°иҝ‘зҷҫдёӘеҪ“дәӢдәәгҖӮйҷӨдәҶйҮҮи®ҝдәІеҺҶиҖ…пјҢиҝҳжҹҘйҳ…еӨ§йҮҸиө„ж–ҷпјҢиҝӣиЎҢе®һең°иҖғеҜҹгҖӮ
В В В В гҖҠе®ҡиҘҝеӯӨе„ҝйҷўзәӘдәӢгҖӢзҡ„еҶҷдҪңд№ҹиҠұеҺ»дәҶдә”е№ҙгҖӮ2002е№ҙпјҢеӣһеҲ°еҹҺеёӮеӨҡе№ҙзҡ„жқЁжҳҫжғ еҸҲиҝ”еӣһеҪ“е№ҙдёҠеұұдёӢд№Ўзҡ„йҘ®й©¬еҶңеңәгҖӮйҘ®й©¬еҶңеңәжңүдёҖзҫӨжқҘиҮӘе®ҡиҘҝеӯӨе„ҝйҷўзҡ„еӯӨе„ҝеҪ“еҶңе·ҘгҖӮи·ҹиҝҷдәӣеӯӨе„ҝи°Ҳиө·еҪ“е№ҙзҡ„йҘҘиҚ’е’ҢзҒҫйҡҫпјҢеӨ§йғЁеҲҶдәәеҫҲеҶ·йқҷпјҢеҸҜжҳҜжңҖеҗҺи°ҲеҲ°жғЁзғҲеӨ„иҝҳжҳҜдјҡе“ӯиө·жқҘгҖӮ
В В В В вҖңжҜҸдёҖж¬Ўи·ҹ他们и°ҲиҜқпјҢжҲ‘иҮӘе·ұжіӘжөҒж»ЎйқўгҖӮ他们讲йӮЈдәӣдәӢжғ…пјҢе·Із»Ҹи¶…еҮәжҲ‘еҺ»и®ҝ问他们д№ӢеүҚеҝғйҮҢзҡ„йў„жңҹгҖӮжңүеҫҲеӨҡжқ‘еә„пјҢжҜ”еҰӮжңү50жҲ·дәә家пјҢ300еҸЈдәәпјҢзҒҫйҡҫиҝҮеҺ»д»ҘеҗҺеү©дёӢзҷҫеҲҶд№Ӣдә”еҚҒгҖӮвҖқ
В В В В иҝҷж ·зҡ„и°ғжҹҘдёҚд»…иҙ№еҠӣпјҢиҖҢдё”дјӨзҘһгҖӮдҪҶиҝҷжҳҜеҺҶеҸІеҸҷдәӢпјҢвҖңдҪ дёҚе…үиҰҒи®ІеҮәдҪ зҡ„зңӢжі•пјҢеҜ№дәӢ件зҡ„е‘ҲзҺ°д№ҹиҰҒжңүж №жҚ®гҖӮдҪ еҶҷеҮәзҡ„дёңиҘҝпјҢиҰҒи®©иҜ»иҖ…дҝЎиө–е°ұиҰҒжӢҝеҮәеӨ§йҮҸзҡ„дәӢе®һжқҘиҜҙиҜқпјҢдёҚиғҪйқ зқҖжғіиұЎиҷҡжһ„жҲ–иҖ…зј–йҖ гҖӮвҖқжқЁжҳҫжғ иҜҙпјҢвҖңжҲ‘жғіиҰҒеҶҷеҮәжҲ‘иҮӘе·ұз»ҸеҺҶзҡ„йӮЈдёӘж—¶д»ЈпјҢжҲ‘зҡ„и§ҶеҠӣжүҖеҸҠпјҢиҝҷдёӘеҺҶеҸІжҳҜд»Җд№Ҳж ·зҡ„пјҢжҲ‘е°ұжҖҺд№Ҳж ·еҶҷгҖӮвҖқ
В В В В иҝ„д»ҠдёәжӯўпјҢжқЁжҳҫжғ зҡ„гҖҠе®ҡиҘҝеӯӨе„ҝйҷўзәӘдәӢгҖӢгҖҒгҖҠеӨ№иҫ№жІҹи®°дәӢгҖӢиў«и¶ҠжқҘи¶ҠеӨҡзҡ„иҜ»иҖ…е…іжіЁпјҢгҖҠеӨ№иҫ№жІҹи®°дәӢгҖӢиў«иҜ‘дёәиӢұгҖҒжі•гҖҒеҫ·гҖҒж„Ҹеҗ„иҜӯз§ҚеңЁеӣҪеӨ–еҮәзүҲпјҢз”ұгҖҠеӨ№иҫ№жІҹи®°дәӢгҖӢж”№зј–зҡ„з”өеҪұеҸӮеҠ еЁҒе°јж–ҜеӣҪйҷ…з”өеҪұиҠӮеұ•жҳ гҖӮ
В В В В ж—©е№ҙжқЁжҳҫжғ еҸ—еҲ°зҡ„ж–ҮеӯҰеҪұе“ҚжӣҙеӨҡжқҘиҮӘдҝ„зҪ—ж–Ҝж–ҮеӯҰпјҡвҖңжҲ‘йқһеёёе–ңж¬ўиӮ–жҙӣйңҚеӨ«зҡ„дҪңе“ҒпјҢдҪҶжҳҜжҲ‘еҜ№иӮ–жҙӣйңҚеӨ«д№ҹдёҚжҳҜе®Ңе…Ёиҝ·дҝЎпјҢд»–зҡ„еҶҷдҪңеңЁдёҚеҗҢйҳ¶ж®өиЎЁзҺ°дёҚеҗҢпјҢжҲ‘е–ңж¬ўд»–зҡ„гҖҠйқҷйқҷзҡ„йЎҝжІігҖӢгҖӮжүҳе°”ж–Ҝжі°зҡ„дҪңе“Ғе’Ңжҷ®еёҢйҮ‘зҡ„зҹӯзҜҮе°ҸиҜҙжҲ‘д№ҹйқһеёёе–ңж¬ўпјҢе®ғ们дҝғдҪҝжҲ‘е®ҢжҲҗдәҶеҶҷдҪңзҡ„иҪ¬еһӢгҖӮиҝҳжңүзҙўе°”д»Ғе°јзҗҙзҡ„гҖҠеҸӨжӢүж јзҫӨеІӣгҖӢпјҢжҲ‘и®ӨдёәдёӯеӣҪдҪң家全йғЁдҪңе“ҒеҠ иө·жқҘпјҢе…¶еҲҶйҮҸдёҚеҰӮдёҖйғЁгҖҠеҸӨжӢүж јзҫӨеІӣгҖӢгҖӮвҖқ

гҖҠз”ҳеҚ—зәӘдәӢгҖӢдёӯзҡ„еҫҲеӨҡж•…дәӢйғҪеҸ‘з”ҹеңЁжүҺе°•йӮЈжқ‘
В В В В вҖңжҲ‘зј–дёҚдәҶж•…дәӢвҖқ
В В В В В гҖҠз”ҳеҚ—зәӘдәӢгҖӢеҫҲеӨҡж•…дәӢйғҪеҸ‘з”ҹеңЁжүҺе°•йӮЈиЎҢж”ҝжқ‘гҖӮжүҺе°•йӮЈжҳҜи—ҸиҜӯйҹіиҜ‘пјҢзҹіеӨҙеҢЈеӯҗзҡ„ж„ҸжҖқгҖӮиҝҷжҳҜиҝӯеұұиҘҝз«Ҝзҡ„дёҖйҒ“еұұжІҹпјҢжө·жӢ”жңҖдҪҺеӨ„2900зұіпјҢйЎәжІҹеҫҖдёҠиө°дәҢеҚҒе…¬йҮҢпјҢе°ұдёҠдәҶеұұйЎ¶пјҢзҝ»иҝҮеұұе°ұжҳҜеҚ“е°јеҺҝеҺҝеўғгҖӮеӣӣдёӘжқ‘еә„дёҖжәңе„ҝжҺ’ејҖеқҗиҗҪеңЁеұұеқЎдёҠпјҢиғҢйқ зҷҪиүІзҹізҒ°еІ©зҡ„еӨ§еұұпјҢеҜ№йқўзҡ„еҚ—еұұдёҠй•ҝж»ЎиӢҚз»ҝзҡ„жқҫж ‘гҖӮжңүдёүиӮЎеұұж°ҙд»Һжқ‘еҗҺзҡ„дёүжқЎжІҹжөҒеҮәжқҘпјҢжҺЁеҠЁзқҖж°ҙзЈЁж—ӢиҪ¬гҖӮеұұеқЎдёҠйЈҺ马旗йЈҳйЈҳгҖӮ
В В В В жүҺе°•йӮЈжҳҜз”ҳеҚ—е·һйЈҺжҷҜжңҖзҫҺзҡ„ең°ж–№пјҢд№ҹжҳҜи—Ҹж°‘з”ҹжҙ»еҫ—еҫҲиү°иҫӣзҡ„ең°ж–№гҖӮ他们зҡ„зү§еңәе°ұеңЁжқ‘иғҢеҗҺзҡ„зҹіеӨҙеұұеұұйЎ¶пјҢеңЁжө·жӢ”3500зұіеҲ°4500зұізҡ„еҢәеҹҹеҫҖдёң延伸зәҰ150е…¬йҮҢпјҢжңҖиҝңеҲ°иҫҫи…ҠеӯҗеҸЈпјҢдёҖзӣҙжҠҠиҝӯеұұиө°е®ҢгҖӮжңүзҡ„зү§ж°‘еҲ°зү§еңәеҺ»пјҢиҰҒзҝ»еҫҲеӨҡеұұпјҢиө°дёӨдёүеӨ©гҖӮжңүдәӣеӯ©еӯҗе°ұеҮәз”ҹеңЁиҝӯеұұж·ұеӨ„зҡ„зү§еңәпјҢзӣҙеҲ°иҰҒдёҠеӯҰзҡ„ж—¶еҖҷпјҢзҲ¶жҜҚжүҚжҠҠ他们йҖҒеҲ°жүҺе°•йӮЈжқҘгҖӮ
В В В В жүҺе°•йӮЈжқ‘ж’ӯз§ҚгҖҒ收еүІзҡ„ж—¶еҖҷпјҢзү§еңәиҰҒжҠҪдәәеӣһжқҘе№Іжҙ»гҖӮзү§еңәиҰҒжҗ¬е®¶пјҲиҪ¬еңәпјүж—¶пјҢ家йҮҢиҰҒжҠҪдәәеҲ°зү§еңәеҺ»её®еҝҷгҖӮ家дәәжҠҠзЈЁеҘҪзӮ’зҶҹзҡ„йқ’зЁһйқўйҖҒеҲ°зү§еңәеҺ»пјҢзү§еңәиҰҒжҠҠзүӣзҫҠиӮүе’Ңй…ҘжІ№й©®еӣһ家жқҘгҖӮжҜҸдёӘ家еәӯзҡ„дәәдёҖе№ҙеӣӣеӯЈиҰҒеңЁиҝӯеұұзҡ„еұұжўҒе’ҢеіЎи°·йҮҢжқҘжқҘеҺ»еҺ»гҖӮ
В В В В жқЁжҳҫжғ жӣҫз»Ҹе’ҢдёӨдҪҚзү§ж°‘йӘ‘马д»Һи…ҠеӯҗеҸЈз©ҝи¶ҠиҝӯеұұпјҢеӣ дёәдёӢйӣЁе’ҢйҖ”дёӯдј‘жҒҜпјҢеҚҒеӨ©жүҚиө°еҲ°жүҺе°•йӮЈгҖӮеҮ жқЎеұұи°·йҮҢе…ЁжҳҜеӨ§еӨ§е°Ҹе°Ҹзҡ„зҹіеӨҙз–ҷзҳ©пјҢ第еҚҒеӨ©д»ҺжІҹйҮҢиө°еҮәжқҘзҡ„ж—¶еҖҷпјҢдёүеҢ№й©¬йҮҢжңүдёҖеҢ№иө°зҳёдәҶдёҖжқЎи…ҝгҖӮ
В В В В вҖңеҲ°жүҺе°•йӮЈпјҢйӘ‘马з©ҝи¶Ҡиҝӯеұұз»ҸеёёзҙҜеҫ—и…ҝиҪҜпјҢдёӢ马时дёҖеҸӘи„ҡиё©еҲ°ең°дёҠпјҢеҸҰдёҖеҸӘи„ҡиҝҳеңЁй©¬й•«дёҠеҸ–дёҚдёӢжқҘпјҢжҖ»жҳҜж‘”еҖ’гҖӮжҜҸж¬ЎйғҪиҰҒеҒҡдјҙзҡ„и—Ҹж°‘жҠұдёӢ马жқҘгҖӮвҖқжқЁжҳҫжғ иҜҙгҖӮ
В В В В дёҠеҲқдёӯзҡ„ж—¶еҖҷпјҢжқЁжҳҫжғ еңЁиЎ—еӨҙз»ҸеёёзңӢеҲ°д»Һз”ҳеҚ—еҲ°е…°е·һеҺ»зҡ„и—Ҹж°‘пјҢеӨ§йғЁеҲҶжҳҜз©ҝзқҖзҡ®иў„зҡ„еҰҮеҘігҖӮеҘ№д»¬иғҢзқҖеӯ©еӯҗгҖҒзӮ’йқўеҸЈиўӢе’Ңй…ҘжІ№пјҢеҺ»жҺўи§ҶдәІдәәгҖӮеҘ№д»¬дёҚдјҡиҜҙжұүиҜқпјҢжӢҝзқҖеҶҷжңүдәІдәәең°еқҖзҡ„дҝЎпјҢеңЁиЎ—еӨҙжӢҰдҪҸдәәй—®и·ҜгҖӮ
В В В В 1980е№ҙд»ЈпјҢжқЁжҳҫжғ зңӢиҝҮйҷҲдё№йқ’зҡ„иҘҝи—Ҹз»„з”»е’ҢдҪ•еӨҡиӢ“зҡ„и—Ҹең°жІ№з”»пјҢжңүдәҶеҺ»зңӢзңӢи—Ҹең°йЈҺжғ…зҡ„еҶІеҠЁгҖӮд№ҹжҳҜйӮЈж®өж—¶й—ҙпјҢи—Ҹж—ҸдҪң家жүҺиҘҝиҫҫеЁғжқҘеҲ°жқЁжҳҫжғ 家пјҢ他们дҝғиҶқй•ҝи°ҲдёүеӨ©гҖӮ
В В В В дҪң家жүҺиҘҝиҫҫеЁғжӣҫзәҰжқЁжҳҫжғ д»ҘжҸҙи—Ҹе№ІйғЁзҡ„ж–№ејҸеҺ»иҘҝи—ҸпјҢд»–еҸҜд»Ҙеё®еҠ©и°ғеҠЁвҖ”вҖ”д»–зҲ¶дәІеҪ“ж—¶жҳҜжӢүиҗЁеёӮй•ҝгҖӮдҪҶеӣ дёәеӯ©еӯҗиҝҳе°ҸпјҢжқЁжҳҫжғ дёҚеҝҚеҝғжҠҠеҰ»е„ҝжҠӣдёӢгҖӮ
В В В В 2001е№ҙпјҢжқЁжҳҫжғ еә”гҖҠе…°е·һжҷҡжҠҘгҖӢзҡ„жңӢеҸӢйӮҖиҜ·еҺ»з”ҳеҚ—и®ІиҜҫпјҢд»–еңЁиЎ—иҫ№д№Ұж‘Ҡд№°еҲ°дёҖжң¬гҖҠз”ҳеҚ—е·һеҝ—гҖӢпјҢиҝҷжҲҗдәҶд»–дәҶи§ЈиҝҷдёӘең°еҢәзҡ„жҢҮеҚ—гҖӮ
В В В В д»Һе…°е·һеҲ°з”ҳеҚ—и—Ҹең°зҡ„и·ҜдёҠпјҢжқЁжҳҫжғ еҘ”жіўдә”е№ҙпјҢд»–иҰҒзңҹзҡ„зҶҹжӮүи—Ҹж°‘пјҡвҖңдёҚдәҶи§ЈжІЎжңүеҠһжі•еҶҷгҖӮвҖқд»–иҠұе·ҘеӨ«жңҖеӨҡзҡ„е°ұжҳҜеҲ°зү§ж°‘зҡ„зү§еңәпјҢзңӢ他们дёҖеӨ©зҡ„з”ҹжҙ»пјҢжҖҺд№ҲжҢӨзүӣеҘ¶пјҢжҖҺд№Ҳжү“й…ҘжІ№пјҢзғ§зүӣзІӘиҝҳжҳҜзғ§жҹҙзҰҫпјҢеҲ°е“Әе„ҝз ҚжҹҙзҰҫпјҢз”Ёж–§еӯҗиҝҳжҳҜз ҚеҲҖпјҢз ҚеҲҖжҳҜд»Җд№Ҳж ·зҡ„пјҢжүҺдёҖдёӘеёҗзҜ·з”ЁеӨҡе°‘ж №з»іеӯҗжӢүиө·жқҘпјҢең°дёӢиҰҒй’үеӨҡе°‘ж №ж©ӣеӯҗпјҢй—Ёеёҳд»Җд№Ҳж ·пјҢжҖҺд№ҲжҺҖејҖпјҢзғҹжҖҺд№ҲеҶ’еҮәеҺ»вҖҰвҖҰ
В В В В жқЁжҳҫжғ жҠҠиҝҷдәӣдәӢжғ…зңӢжҲҗжҳҜе°ҸиҜҙ家зҡ„еҠҹиҜҫгҖӮеё®еҠ©иҝҮд»–зҡ„и—Ҹж°‘пјҢд»–дјҡжҺҘ他们еҺ»еҢ—дә¬зҺ©пјҢиҙҹжӢ…еҫҖиҝ”жңәзҘЁе’ҢйЈҹе®ҝпјҢеҪ“他们зҡ„еҜјжёёпјҢи·ҹе№ҙиҪ»зҡ„и—Ҹж°‘д»Ҙе…„ејҹзӣёз§°гҖӮ
В В В В жүҺе°•йӮЈдёӢиҫ№зҡ„еӣӣдёӘжқ‘еҜЁпјҢд»ҺиҘҝеҫҖдёңжҺ’еҲ—пјҢеҲҶеҲ«еҸ«иҫҫж—ҘгҖҒд»Је·ҙгҖҒдёҡж—Ҙе’ҢдёңжҙјгҖӮжҜҸж¬ЎеҲ°жүҺе°•йӮЈпјҢжқЁжҳҫжғ йғҪдјҡдҪҸеңЁдёҡж—Ҙжқ‘дёҖдҪҚеҸ«ж №зҷ»зҡ„иҖҒдәә家йҮҢгҖӮеӨҡж¬Ўи—Ҹең°иЎҢпјҢд»–е’Ңж №зҷ»жҲҗдәҶеҘҪжңӢеҸӢгҖӮиҖҒдәәз”ҹзҒ«зғ§ж°ҙпјҢиҜ·е®ўдәәе–қй…ҘжІ№иҢ¶еҗғзіҢзІ‘пјҢдёәе®ўдәәе’Ңйқўж“ҖйқўжқЎпјҢжҠҠжҢӮеңЁжҲҝйЎ¶зҡ„дёҖеқ—е№ІиӮүжӢҝдёӢжқҘжіЎеңЁж°ҙйҮҢеҒҡиҸңгҖӮ他们еҝҷзўҢзҡ„ж—¶еҖҷпјҢжқЁжҳҫжғ дјҡеёҰзқҖж‘„еғҸжңәеҺ»жқ‘еӨ–зҡ„дёҖзүҮй«ҳең°пјҢд»ҺиҝҷйҮҢеҸҜд»ҘзңӢи§Ғдёңжҙјжқ‘пјҢд№ҹзңӢи§ҒиҘҝиҫ№й«ҳеқЎдёҠзҡ„д»Је·ҙжқ‘е’Ңе®ғзҡ„еҜәйҷўгҖӮ
В В В В йҖҡиҝҮдёӘдәәе‘Ҫиҝҗе‘ҲзҺ°з”ҳеҚ—и—Ҹең°зҡ„з”ҹжҙ»еҸҳиҝҒпјҢжҳҜжқЁжҳҫжғ еҶҷгҖҠз”ҳеҚ—зәӘдәӢгҖӢзҡ„дё»йўҳгҖӮ然иҖҢе·Із»ҸеҮәзүҲзҡ„гҖҠз”ҳеҚ—зәӘдәӢгҖӢеҸӘжҳҜжқЁжҳҫжғ з”ҳеҚ—иЎҢж—…жө©з№ҒеҶ…е®№зҡ„дёҖйғЁеҲҶпјҢжӣҙеӨҡзҙ жқҗиҝҳеңЁд»–зҡ„ж–Ү件з®ұйҮҢгҖӮ
В В В В вҖңд№ҹеҸҜиғҪжңҖеҗҺзҡ„з»“жһңе°ұжҳҜй’ұзҷҪиҠұпјҢе·ҘеӨ«зҷҪиҙ№пјҢд№ҹеҸҜиғҪеҶҷдёҚеҘҪиҝҷжң¬д№ҰгҖӮдёҚиҝҮеҸҜд»ҘиӮҜе®ҡзҡ„жҳҜпјҢиҝҷжҳҜжҲ‘иҝҷдёҖз”ҹжңҖеҗҺзҡ„дҪңе“ҒгҖӮжҠҠз”ҳеҚ—и—Ҹең°зҡ„дәӢжғ…еј„жё…жҘҡпјҢд»ҘеҗҺе°ұеҶҚдёҚдјҡиҝҷд№Ҳи·‘еҮәжқҘдәҶгҖӮеҶҷдёҖзӮ№иҪ»жқҫзҡ„ж–Үеӯ—пјҢжҲ–иҖ…е№Іи„Ҷе°Ғ笔гҖӮвҖқжқЁжҳҫжғ иҜҙйҒ“гҖӮ

жқЁжҳҫжғ
В В В В з¬Ёдәәе№Ізҡ„дәӢ
В В В В вҖңжҲ‘з”ҹжҖ§ж„ҡй’қпјҢзј–дёҚдәҶж•…дәӢпјҢжүҖд»ҘйҮҮз”Ёиҝҷз§Қе®һең°йҮҮи®ҝзҡ„еҶҷдҪңж–№ејҸгҖӮвҖқжқЁжҳҫжғ иҜҙпјҢвҖңжҲ‘и®Өдёәйқһиҷҡжһ„ж–ҮеӯҰеҸҜд»Ҙзңҹе®һең°и®°еҪ•еҺҶеҸІгҖӮе®ғзҡ„д»·еҖје’Ңж„Ҹд№үдёҚеңЁд»ҠеӨ©пјҢиҖҢеңЁдәҺжҳҺеӨ©гҖӮеҰӮжһңжІЎжңүйқһиҷҡжһ„ж–ҮеӯҰпјҢе°ҶжқҘдәә们е°ұдјҡжҠҠиҷҡжһ„ж–ҮеӯҰжӯӘжӣІдәҶзҡ„еҺҶеҸІеҪ“еҒҡжӯЈеҸІгҖӮйӮЈж ·зҡ„иҜқпјҢжҲ‘们иҝҷдёӘж°‘ж—Ҹе°ұеҪ»еә•жІЎжңүеёҢжңӣдәҶгҖӮвҖқжқЁжҳҫжғ еёҢжңӣиҮӘе·ұзҡ„еҶҷдҪңеҜ№еҫ—иө·иүҜеҝғпјҢд»–еҜ№иҮӘе·ұзҡ„йқһиҷҡжһ„еҶҷдҪңд№ҹеҫҲжңүдҝЎеҝғпјҡвҖңеңЁд»ҠеҗҺдёҖж®өж—¶й—ҙеҶ…пјҢжІЎжңүдәәдјҡи¶…и¶ҠжҲ‘гҖӮ并дёҚжҳҜиҜҙжҲ‘жңүеӨҡеӨ§жүҚеҚҺпјҢжҳҜеӣ дёәеҲ«дәәдёӢдёҚдәҶжҲ‘иҝҷе·ҘеӨ«гҖӮе…үеҮӯиҒӘжҳҺжҳҜи¶…дёҚиҝҮжҲ‘зҡ„пјҢд»–йңҖиҰҒж—ўиҒӘжҳҺеҸҲдёӢе·ҘеӨ«гҖӮдҪң家们дёҚж„ҝж„ҸеҗғиҝҷдёӘиӢҰвҖ”вҖ”дёҖдёӘдәәдёҖдёӘдәәең°еҺ»и®ҝй—®пјҢеӨ§еӨҡжҳҜиҖҒдәәпјҢжІЎжңүжҳҫиө«зҡ„еЈ°еҗҚпјҢйҷӨдәҶе°ҳе°Ғзҡ„и®°еҝҶдёҖж— жүҖжңүгҖӮеҶҷеҮәиҝҷж ·зҡ„еҺҶеҸІпјҢжҳҜз¬Ёдәәе№Ізҡ„дәӢгҖӮвҖқ
В В В В жӯӨеүҚжқЁжҳҫжғ д№ҰеҶҷ1957е№ҙзҡ„еҸҚеҸіиҝҗеҠЁпјҢи®°еҪ•1960е№ҙд»Јзҡ„еӨ§йҘҘиҚ’пјҢи‘—дҪңдёӯе……ж»ЎеҜ№дәәй—ҙз–ҫиӢҰзҡ„еҗҢжғ…дёҺжҖқиҖғгҖӮж–ҮеӯҰиҜ„и®ә家йӣ·иҫҫиҜ„иҝ°гҖҠеӨ№иҫ№жІҹи®°дәӢгҖӢж—¶иҜҙпјҡвҖңзҹҘйҒ“иҝҷж®өеҺҶеҸІзҡ„дәәе·ІдёҚеӨҡдәҶпјҢеҪ“е№ҙзҡ„з”ҹиҝҳиҖ…еӨ§еӨҡе·ІзҰ»дё–пјҢе°‘ж•°е№ёеӯҳиҖ…дёүзј„е…¶еҸЈгҖӮжқЁжҳҫжғ жҠҠи°ғжҹҘеҫ—жқҘзҡ„ж•…дәӢи®ІеҮәжқҘпјҢж„ҸеңЁзҝ»ејҖе°ҳе°ҒдәҶеӣӣеҚҒе№ҙзҡ„еҺҶеҸІпјҢеёҢжңӣиҝҷж ·зҡ„жӮІеү§дёҚеҶҚйҮҚжј”гҖӮвҖқ
В В В В еӨ№иҫ№жІҹжҳҜз”ҳиӮғй…’жіүдёҖдёӘжӣҫзҫҒжҠјеҸіжҙҫзҠҜдәәзҡ„еҠіж”№еҶңеңәпјҢд»Һ1957е№ҙ10жңҲејҖе§ӢпјҢиҝҷйҮҢе…іжҠјдәҶиҝ‘дёүеҚғеҗҚеҸіжҙҫеҲҶеӯҗгҖӮ1961е№ҙе…ғжңҲпјҢеҸіжҙҫеҲҶеӯҗиў«йҒЈиҝ”пјҢжҙ»дёӢжқҘзҡ„жңүе…ӯзҷҫдәәгҖӮдёәдәҶеҶҷеҘҪгҖҠеӨ№иҫ№жІҹи®°дәӢгҖӢпјҢжқЁжҳҫжғ жҜҸе№ҙж•°ж¬ЎеҫҖиҝ”дәҺеӨ©жҙҘе’Ңз”ҳиӮғгҖӮд»–еғҸеӨ§жө·жҚһй’ҲдёҖж ·жҗңеҜ»еҲ°иҝ‘зҷҫдёӘеҪ“дәӢдәәгҖӮйҷӨдәҶйҮҮи®ҝдәІеҺҶиҖ…пјҢиҝҳжҹҘйҳ…еӨ§йҮҸиө„ж–ҷпјҢиҝӣиЎҢе®һең°иҖғеҜҹгҖӮ
В В В В гҖҠе®ҡиҘҝеӯӨе„ҝйҷўзәӘдәӢгҖӢзҡ„еҶҷдҪңд№ҹиҠұеҺ»дәҶдә”е№ҙгҖӮ2002е№ҙпјҢеӣһеҲ°еҹҺеёӮеӨҡе№ҙзҡ„жқЁжҳҫжғ еҸҲиҝ”еӣһеҪ“е№ҙдёҠеұұдёӢд№Ўзҡ„йҘ®й©¬еҶңеңәгҖӮйҘ®й©¬еҶңеңәжңүдёҖзҫӨжқҘиҮӘе®ҡиҘҝеӯӨе„ҝйҷўзҡ„еӯӨе„ҝеҪ“еҶңе·ҘгҖӮи·ҹиҝҷдәӣеӯӨе„ҝи°Ҳиө·еҪ“е№ҙзҡ„йҘҘиҚ’е’ҢзҒҫйҡҫпјҢеӨ§йғЁеҲҶдәәеҫҲеҶ·йқҷпјҢеҸҜжҳҜжңҖеҗҺи°ҲеҲ°жғЁзғҲеӨ„иҝҳжҳҜдјҡе“ӯиө·жқҘгҖӮ
В В В В вҖңжҜҸдёҖж¬Ўи·ҹ他们и°ҲиҜқпјҢжҲ‘иҮӘе·ұжіӘжөҒж»ЎйқўгҖӮ他们讲йӮЈдәӣдәӢжғ…пјҢе·Із»Ҹи¶…еҮәжҲ‘еҺ»и®ҝ问他们д№ӢеүҚеҝғйҮҢзҡ„йў„жңҹгҖӮжңүеҫҲеӨҡжқ‘еә„пјҢжҜ”еҰӮжңү50жҲ·дәә家пјҢ300еҸЈдәәпјҢзҒҫйҡҫиҝҮеҺ»д»ҘеҗҺеү©дёӢзҷҫеҲҶд№Ӣдә”еҚҒгҖӮвҖқ
В В В В иҝҷж ·зҡ„и°ғжҹҘдёҚд»…иҙ№еҠӣпјҢиҖҢдё”дјӨзҘһгҖӮдҪҶиҝҷжҳҜеҺҶеҸІеҸҷдәӢпјҢвҖңдҪ дёҚе…үиҰҒи®ІеҮәдҪ зҡ„зңӢжі•пјҢеҜ№дәӢ件зҡ„е‘ҲзҺ°д№ҹиҰҒжңүж №жҚ®гҖӮдҪ еҶҷеҮәзҡ„дёңиҘҝпјҢиҰҒи®©иҜ»иҖ…дҝЎиө–е°ұиҰҒжӢҝеҮәеӨ§йҮҸзҡ„дәӢе®һжқҘиҜҙиҜқпјҢдёҚиғҪйқ зқҖжғіиұЎиҷҡжһ„жҲ–иҖ…зј–йҖ гҖӮвҖқжқЁжҳҫжғ иҜҙпјҢвҖңжҲ‘жғіиҰҒеҶҷеҮәжҲ‘иҮӘе·ұз»ҸеҺҶзҡ„йӮЈдёӘж—¶д»ЈпјҢжҲ‘зҡ„и§ҶеҠӣжүҖеҸҠпјҢиҝҷдёӘеҺҶеҸІжҳҜд»Җд№Ҳж ·зҡ„пјҢжҲ‘е°ұжҖҺд№Ҳж ·еҶҷгҖӮвҖқ
В В В В иҝ„д»ҠдёәжӯўпјҢжқЁжҳҫжғ зҡ„гҖҠе®ҡиҘҝеӯӨе„ҝйҷўзәӘдәӢгҖӢгҖҒгҖҠеӨ№иҫ№жІҹи®°дәӢгҖӢиў«и¶ҠжқҘи¶ҠеӨҡзҡ„иҜ»иҖ…е…іжіЁпјҢгҖҠеӨ№иҫ№жІҹи®°дәӢгҖӢиў«иҜ‘дёәиӢұгҖҒжі•гҖҒеҫ·гҖҒж„Ҹеҗ„иҜӯз§ҚеңЁеӣҪеӨ–еҮәзүҲпјҢз”ұгҖҠеӨ№иҫ№жІҹи®°дәӢгҖӢж”№зј–зҡ„з”өеҪұеҸӮеҠ еЁҒе°јж–ҜеӣҪйҷ…з”өеҪұиҠӮеұ•жҳ гҖӮ
В В В В ж—©е№ҙжқЁжҳҫжғ еҸ—еҲ°зҡ„ж–ҮеӯҰеҪұе“ҚжӣҙеӨҡжқҘиҮӘдҝ„зҪ—ж–Ҝж–ҮеӯҰпјҡвҖңжҲ‘йқһеёёе–ңж¬ўиӮ–жҙӣйңҚеӨ«зҡ„дҪңе“ҒпјҢдҪҶжҳҜжҲ‘еҜ№иӮ–жҙӣйңҚеӨ«д№ҹдёҚжҳҜе®Ңе…Ёиҝ·дҝЎпјҢд»–зҡ„еҶҷдҪңеңЁдёҚеҗҢйҳ¶ж®өиЎЁзҺ°дёҚеҗҢпјҢжҲ‘е–ңж¬ўд»–зҡ„гҖҠйқҷйқҷзҡ„йЎҝжІігҖӢгҖӮжүҳе°”ж–Ҝжі°зҡ„дҪңе“Ғе’Ңжҷ®еёҢйҮ‘зҡ„зҹӯзҜҮе°ҸиҜҙжҲ‘д№ҹйқһеёёе–ңж¬ўпјҢе®ғ们дҝғдҪҝжҲ‘е®ҢжҲҗдәҶеҶҷдҪңзҡ„иҪ¬еһӢгҖӮиҝҳжңүзҙўе°”д»Ғе°јзҗҙзҡ„гҖҠеҸӨжӢүж јзҫӨеІӣгҖӢпјҢжҲ‘и®ӨдёәдёӯеӣҪдҪң家全йғЁдҪңе“ҒеҠ иө·жқҘпјҢе…¶еҲҶйҮҸдёҚеҰӮдёҖйғЁгҖҠеҸӨжӢүж јзҫӨеІӣгҖӢгҖӮвҖ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