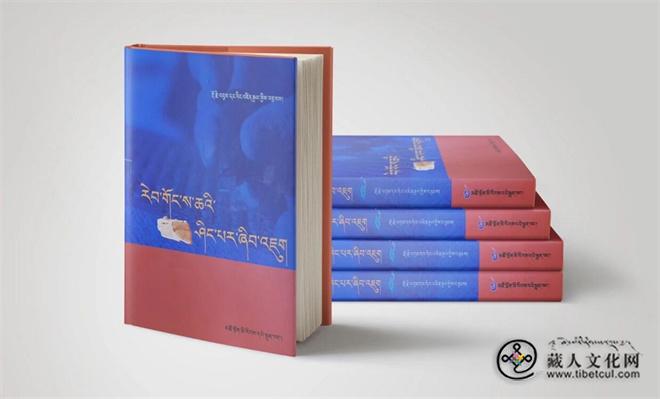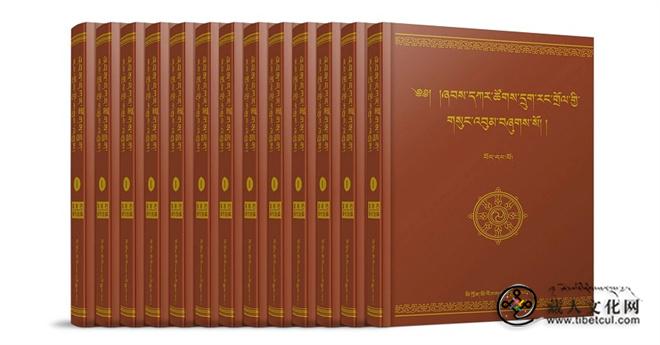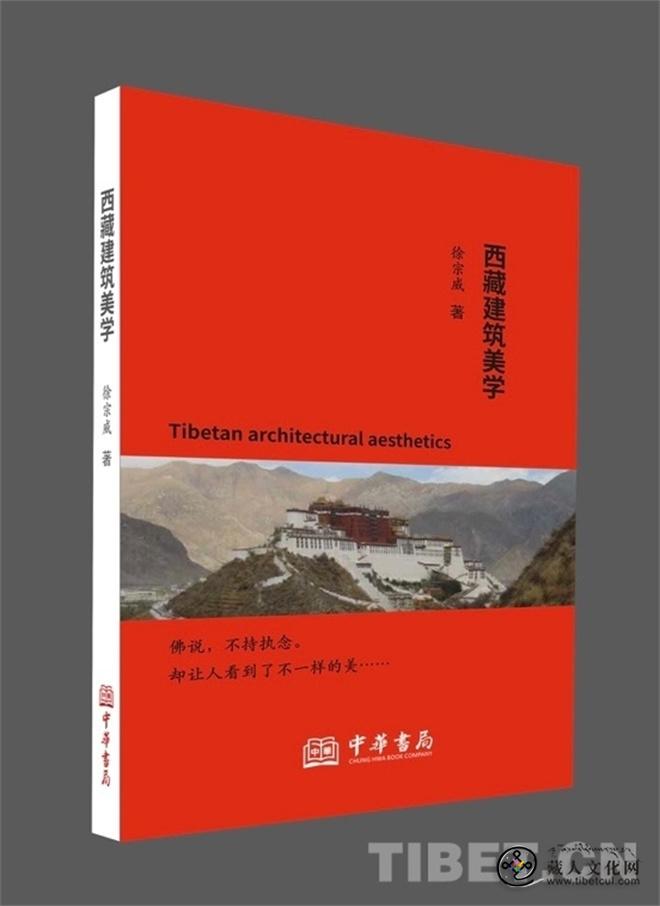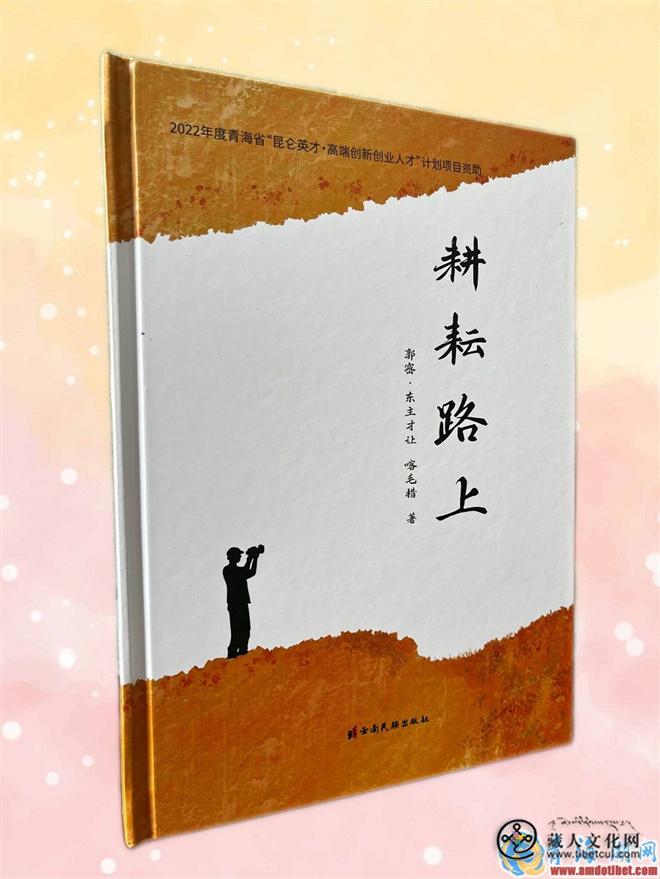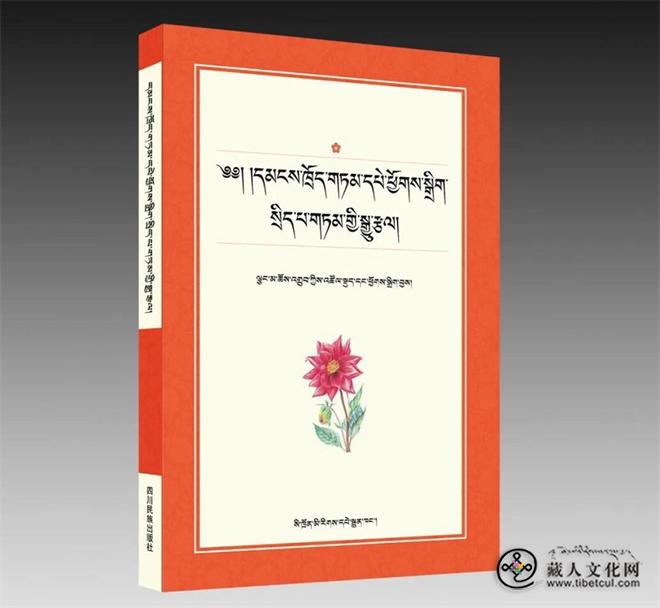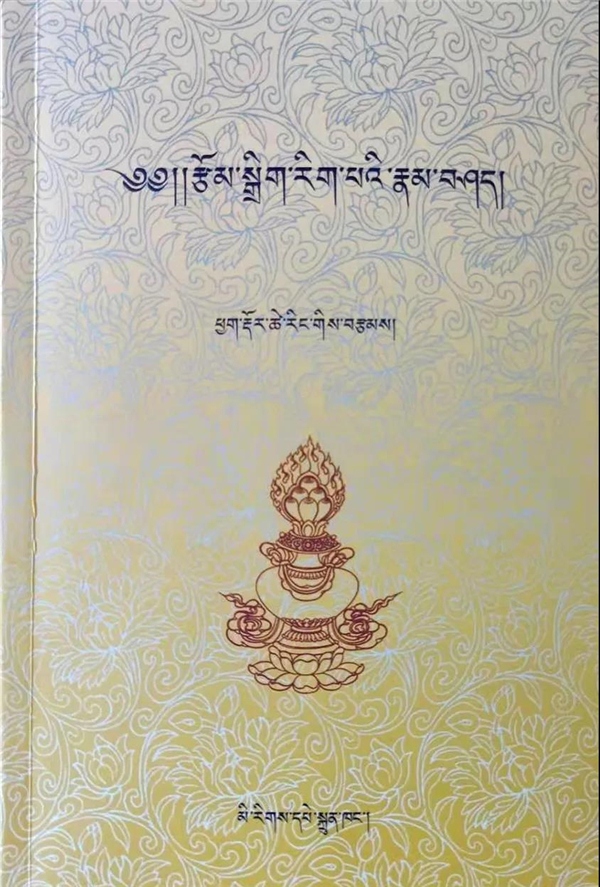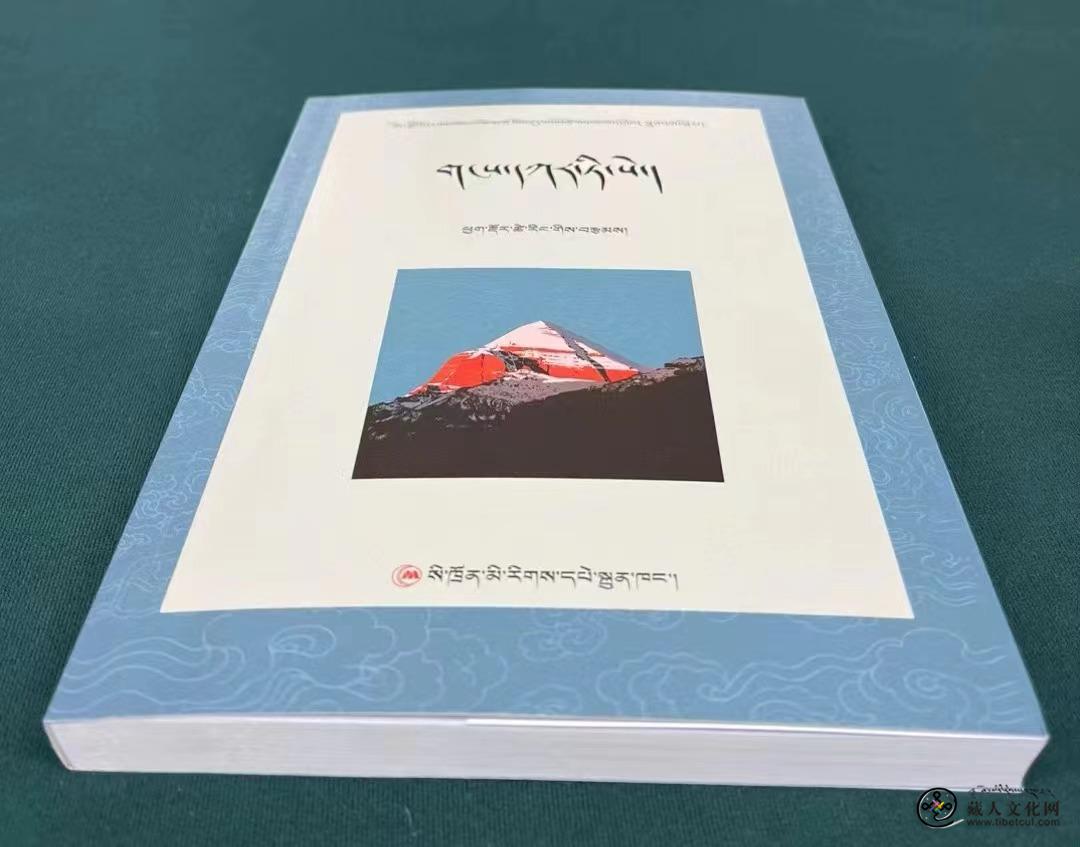гҖҖгҖҖеңЁгҖҠд№ЎеңҹдёӯеӣҪгҖӢдёӯпјҢиҙ№еӯқйҖҡе…Ҳз”ҹеҜ№вҖңд№ЎеңҹвҖқиҝҷдёҖжҰӮеҝөиҝӣиЎҢдәҶж·ұе…Ҙйҳҗиҝ°гҖӮд»–и®ӨдёәпјҢвҖңд№ЎеңҹвҖқдёҚд»…д»ЈиЎЁдёҖдёӘең°еҢәзҡ„жң¬еңҹзү№иүІе’Ңж–ҮеҢ–еҶ…ж¶өпјҢжӣҙж¶үеҸҠиҜҘең°еҢәзҡ„йЈҺдҝ—гҖҒж°‘ж—Ҹж–ҮеҢ–гҖҒдј з»ҹд№ жғҜгҖҒеҺҶеҸІз§Ҝж·ҖгҖҒиҮӘ然зҺҜеўғд»ҘеҸҠеҪ“ең°дәәзҡ„з”ҹжҙ»ж–№ејҸе’ҢжҖқз»ҙжЁЎејҸзӯүеӨҡж–№йқўгҖӮвҖңд№ЎвҖқеҲҷд»ЈиЎЁзҫӨгҖҒж•…д№Ўе’Ңе…·дҪ“зҡ„ж—¶з©әеқҗиҗҪгҖӮеңЁд№ЎеңҹзӨҫдјҡдёӯпјҢдәә们еҫҖеҫҖеҜ№ж•…д№ЎжңүзқҖж·ұеҺҡзҡ„жғ…ж„ҹзәҪеёҰпјҢиҝҷз§Қжғ…ж„ҹдёҚд»…жәҗдәҺеҜ№еңҹең°е’Ң家еӣӯзҡ„дҫқжҒӢпјҢиҝҳжәҗдәҺеҜ№дј з»ҹж–ҮеҢ–е’Ңд»·еҖји§Ӯзҡ„и®ӨеҗҢгҖӮвҖңеңҹвҖқеңЁд№Ўеңҹдёӯжү®жј”зқҖиҮіе…ійҮҚиҰҒзҡ„и§’иүІпјҢд»ЈиЎЁеңҹең°гҖҒеҶңдёҡе’Ңе®Ҳеңҹж„ҸиҜҶгҖӮеңЁд№ЎеңҹзӨҫдјҡдёӯпјҢеңҹең°жҳҜдәә们иө–д»Ҙз”ҹеӯҳзҡ„еҹәзЎҖпјҢеҶңдёҡз”ҹдә§жҳҜдё»иҰҒзҡ„з»ҸжөҺжҙ»еҠЁгҖӮеӣ жӯӨпјҢд№ЎеңҹзӨҫдјҡеҫҖеҫҖе…·жңүжө“еҺҡзҡ„еҶңдёҡиүІеҪ©е’Ңеңҹең°ж„ҸиҜҶгҖӮиҙ№еӯқйҖҡи®ӨдёәпјҢд№ЎеңҹзӨҫдјҡжҳҜдёҖдёӘзҶҹдәәзӨҫдјҡпјҢдәә们д№Ӣй—ҙеҹәдәҺиЎҖзјҳгҖҒең°зјҳзӯүе…ізі»еҪўжҲҗдәҶзҙ§еҜҶзҡ„иҒ”зі»гҖӮиҝҷз§ҚиҒ”зі»дҪҝеҫ—д№ЎеңҹзӨҫдјҡе…·жңүдёҖз§Қзү№ж®Ҡзҡ„зЁіе®ҡжҖ§е’Ң秩еәҸжҖ§гҖӮгҖҠеҳүжңЁвҖ”вҖ”Mжқ‘ж°‘ж—Ҹеҝ—гҖӢжҒ°еҘҪжҸҗдҫӣдәҶиҝҷж ·зҡ„дёҖдёӘи§Ҷи§’пјҡйқ’и—Ҹй«ҳеҺҹиҫ№зјҳзҡ„Mжқ‘пјҢд»ҘзҶҹдәәзӨҫдјҡдёәдё»зҡ„вҖңеҳүжңЁвҖқж–ҮеҢ–еҶ…ж¶өпјҢдјјд№Һжү“з ҙдәҶвҖңеҶңдёҡвҖқдёҺвҖңзү§дёҡвҖқзҡ„з•ҢйҷҗпјҢеңЁеҶңзү§з»“еҗҲзҡ„з”ҹдә§жҙ»еҠЁдёӯпјҢдәәе’Ңдәәд№Ӣй—ҙеҪўжҲҗдәҶдёҖз§ҚвҖңи¶…и¶Ҡдәәзұ»вҖқзҡ„е…ізі»зҪ‘з»ңпјҢвҖңзҶҹвҖқзҡ„и®ӨзҹҘдёҚеҶҚеұҖйҷҗдәҺвҖңдәәвҖқпјҢвҖңе®ғвҖқиЎҚз”ҹеҲ°д»–们жүҖеӨ„зҡ„еұұеұұж°ҙж°ҙдёҺзҘһзҒөдё–з•ҢпјҢеҪўжҲҗвҖңеӨҡе…ғе…ізі»вҖқ并еӯҳпјҢзӣёдә’еҲ¶зәҰе…ұдә«зҡ„е№ҝд№үдәәж–Үе…ізі»еҪ“дёӯпјҢе»әз«ӢдәҶд№ЎеңҹзӨҫдјҡзӢ¬жңүзҡ„з”ҹеӯҳжҠҖиғҪе’ҢзЁіе®ҡ秩еәҸгҖӮиҖҢвҖңеҳүжңЁвҖқзҡ„з”ҹеӯҳжҷәж…§е’Ңз”ҹе‘ҪжҷҜи§ӮпјҢдҪҝеҫ—д»ҘвҖңеҳүжңЁвҖқдёәд»ЈиЎЁзҡ„дј з»ҹзӨҫдјҡпјҢдјјд№ҺеңЁеӨҡеҸҳз„Ұиҷ‘зҡ„зҺ°д»ЈзӨҫдјҡдёӯпјҢдёәжҲ‘们讨и®әвҖңе№ҝд№үдәәж–Үе…ізі»вҖқжҸҗдҫӣдәҶжӣҙеҠ ејҖж”ҫзҡ„з©әй—ҙгҖ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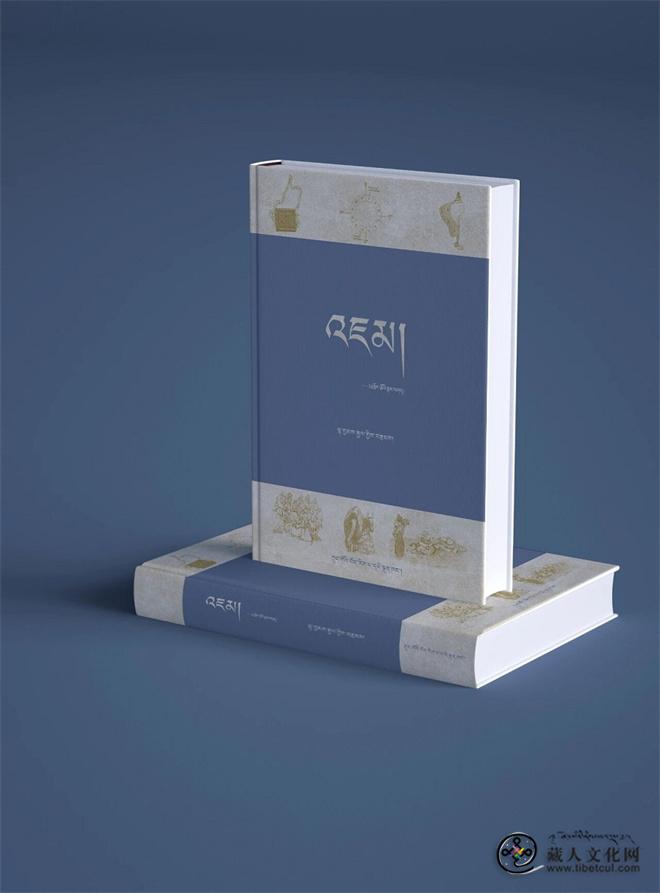 гҖҖгҖҖгҖҠеҳүжңЁвҖ”вҖ”Mжқ‘ж°‘ж—Ҹеҝ—гҖӢжҳҜжӢүе…ҲеҠ е…Ҳз”ҹзҡ„еӯҰжңҜи‘—дҪңпјҢ2020е№ҙеә•з”ұдёӯеӣҪи—ҸеӯҰеҮәзүҲзӨҫеҮәзүҲпјҢиҚЈиҺ·з¬¬дә”еұҠдёӯеӣҪи—ҸеӯҰз ”з©¶зҸ еі°еҘ–гҖӮжҳҜдёҖйғЁи®°еҪ•е’ҢжҸҸеҶҷйқ’и—Ҹй«ҳеҺҹдёңйғЁи—Ҹж—Ҹжқ‘иҗҪзҡ„зӨҫдјҡз»„з»ҮгҖҒйЈҺдҝ—д№ жғҜгҖҒдәәж–ҮжҷҜи§Ӯзӯүзҡ„ж°‘ж—Ҹеҝ—и‘—дҪңгҖӮеӣ иҜҘжқ‘иҗҪеңЁз”ҹдә§з”ҹжҙ»дёҠе…јиҗҘеҶңдёҡе’Ңзү§дёҡпјҢеҪ“ең°дәә称他们дёәвҖңеҳүжңЁвҖқпјҲаҪ аҪҮаҪҳпјүпјҢж—ўдёҚеұһдәҺзәҜзІ№ж„Ҹд№үдёҠзҡ„еҶңдёҡзӨҫдјҡпјҢд№ҹдёҚеұһдәҺзү§дёҡзӨҫдјҡгҖӮMжқ‘зҡ„дәәз©ҝжўӯдәҺеҶңзү§д№Ӣй—ҙпјҢиҮӘ然жҺҢжҸЎдәҶиҜёеӨҡеҶңдёҡзҹҘиҜҶе’Ңзү§дёҡзҹҘиҜҶгҖӮ笔иҖ…жӣҫеңЁдёҖж¬Ўи®Іеә§дёӯпјҢд»ҺвҖңең°ж–№жҖ§зҹҘиҜҶвҖқзҡ„и§Ҷи§’жҺЁиҚҗиҝҮиҝҷжң¬д№ҰгҖӮд№ӢеҗҺиҝҳеҶҷиҝҮдёҖзҜҮд№ҰиҜ„пјҢд»Ҙи—Ҹж—Ҹж–ҮеҢ–дёӯзҡ„вҖңаҪ‘аҪ”аҪәвҖқпјҲе…ёиҢғгҖҒд№ дҝ—пјүд»ҘеҸҠдәәзұ»еӯҰдёӯзҡ„вҖңеӨ§дј з»ҹвҖқвҖңе°Ҹдј з»ҹвҖқзҡ„и§Ҷи§’пјҢи®Ёи®әдәҶиҝҷжң¬д№Ұзҡ„еӯҰжңҜж„Ҹд№үеҸҠе…¶еёҰжқҘзҡ„еҗҜеҸ‘гҖӮеҶҷе®ҢйӮЈзҜҮд№ҰиҜ„еҗҺпјҢд»Қж„ҸзҠ№жңӘе°ҪгҖӮд»ҠеӨ©жӯЈеҘҪеҖҹжӯӨжңәдјҡпјҢжғіеҶҚж¬Ўи®Ёи®әиҝҷжң¬д№ҰдёӯиЎҚз”ҹзҡ„е…ідәҺвҖңе…ізі»вҖқе’ҢвҖңжғ…ж„ҹвҖқзҡ„йғЁеҲҶпјҢеӣ дёәеңЁеҶңзү§дёҡз”ҹдә§з”ҹжҙ»еҸҠе…¶еҸҳиҝҒиҜӯеўғдёӯпјҢжҲ‘и®ӨдёәвҖңе…ізі»вҖқе’ҢвҖңжғ…ж„ҹвҖқжҳҜжңҖдёәйҮҚиҰҒе’Ңж ёеҝғзҡ„йғЁеҲҶгҖӮжҲ‘зЎ®е®ҡзҡ„дё»йўҳдёәвҖңзҶҹдәәзӨҫдјҡе’Ңд№Ўеңҹжҷәж…§вҖқгҖӮвҖңзҶҹдәәзӨҫдјҡвҖқжҳҜиҙ№еӯқйҖҡе…Ҳз”ҹеңЁгҖҠд№ЎеңҹдёӯеӣҪгҖӢдёҖд№Ұдёӯеј•з”Ёзҡ„жҰӮеҝөпјҢз”ЁдәҺйҳҗиҝ°д№ЎеңҹзӨҫдјҡзҡ„еҹәжң¬з»“жһ„гҖӮвҖңд№Ўеңҹжҷәж…§вҖқжҳҜ笔иҖ…й’ҲеҜ№вҖңжӯЈз»ҹвҖқвҖңж–ҮжҳҺвҖқвҖңе…ҲиҝӣвҖқвҖңең°ж–№вҖқвҖңжқғеЁҒвҖқзӯүиҜқиҜӯе»әжһ„жҸҗеҮәзҡ„и§ЈйҮҠи§’еәҰгҖӮжң¬д№ҰдҪңиҖ…жӢүе…ҲеҠ еңЁд№ҰдёӯдёҖиҙҜејәи°ғзҡ„вҖңз”ҹеӯҳжҷәж…§вҖқпјҲаҪ аҪҡаҪјајӢаҪӮаҪ“аҪҰајӢаҪҖаҫұаҪІајӢаҪӨаҪәаҪҰајӢаҪўаҪ–пјүпјҢвҖңд№Ўеңҹжҷәж…§вҖқдёҺд№Ӣи§ӮзӮ№дёҖи„үзӣёжүҝпјҢжҳҜе®ғзҡ„еҶҚзҺ°дёҺеҶҚйҳҗйҮҠгҖӮйӮЈжҲ‘дёәд»Җд№Ҳдјҡи®ӨдёәеңЁвҖңи—Ҹж—ҸеҶңзү§дёҡз”ҹдә§з”ҹжҙ»ж–ҮеҢ–еҸҠе…¶еҸҳиҝҒвҖқиҝҷж ·зҡ„дё»йўҳдёӯпјҢвҖңе…ізі»вҖқе’ҢвҖңжғ…ж„ҹвҖқжҳҜжңҖж ёеҝғзҡ„йғЁеҲҶе‘ўпјҹжҲ‘жғід»Һд»ҘдёӢдёүдёӘж–№йқўйҳҗиҝ°гҖӮ
гҖҖгҖҖгҖҠеҳүжңЁвҖ”вҖ”Mжқ‘ж°‘ж—Ҹеҝ—гҖӢжҳҜжӢүе…ҲеҠ е…Ҳз”ҹзҡ„еӯҰжңҜи‘—дҪңпјҢ2020е№ҙеә•з”ұдёӯеӣҪи—ҸеӯҰеҮәзүҲзӨҫеҮәзүҲпјҢиҚЈиҺ·з¬¬дә”еұҠдёӯеӣҪи—ҸеӯҰз ”з©¶зҸ еі°еҘ–гҖӮжҳҜдёҖйғЁи®°еҪ•е’ҢжҸҸеҶҷйқ’и—Ҹй«ҳеҺҹдёңйғЁи—Ҹж—Ҹжқ‘иҗҪзҡ„зӨҫдјҡз»„з»ҮгҖҒйЈҺдҝ—д№ жғҜгҖҒдәәж–ҮжҷҜи§Ӯзӯүзҡ„ж°‘ж—Ҹеҝ—и‘—дҪңгҖӮеӣ иҜҘжқ‘иҗҪеңЁз”ҹдә§з”ҹжҙ»дёҠе…јиҗҘеҶңдёҡе’Ңзү§дёҡпјҢеҪ“ең°дәә称他们дёәвҖңеҳүжңЁвҖқпјҲаҪ аҪҮаҪҳпјүпјҢж—ўдёҚеұһдәҺзәҜзІ№ж„Ҹд№үдёҠзҡ„еҶңдёҡзӨҫдјҡпјҢд№ҹдёҚеұһдәҺзү§дёҡзӨҫдјҡгҖӮMжқ‘зҡ„дәәз©ҝжўӯдәҺеҶңзү§д№Ӣй—ҙпјҢиҮӘ然жҺҢжҸЎдәҶиҜёеӨҡеҶңдёҡзҹҘиҜҶе’Ңзү§дёҡзҹҘиҜҶгҖӮ笔иҖ…жӣҫеңЁдёҖж¬Ўи®Іеә§дёӯпјҢд»ҺвҖңең°ж–№жҖ§зҹҘиҜҶвҖқзҡ„и§Ҷи§’жҺЁиҚҗиҝҮиҝҷжң¬д№ҰгҖӮд№ӢеҗҺиҝҳеҶҷиҝҮдёҖзҜҮд№ҰиҜ„пјҢд»Ҙи—Ҹж—Ҹж–ҮеҢ–дёӯзҡ„вҖңаҪ‘аҪ”аҪәвҖқпјҲе…ёиҢғгҖҒд№ дҝ—пјүд»ҘеҸҠдәәзұ»еӯҰдёӯзҡ„вҖңеӨ§дј з»ҹвҖқвҖңе°Ҹдј з»ҹвҖқзҡ„и§Ҷи§’пјҢи®Ёи®әдәҶиҝҷжң¬д№Ұзҡ„еӯҰжңҜж„Ҹд№үеҸҠе…¶еёҰжқҘзҡ„еҗҜеҸ‘гҖӮеҶҷе®ҢйӮЈзҜҮд№ҰиҜ„еҗҺпјҢд»Қж„ҸзҠ№жңӘе°ҪгҖӮд»ҠеӨ©жӯЈеҘҪеҖҹжӯӨжңәдјҡпјҢжғіеҶҚж¬Ўи®Ёи®әиҝҷжң¬д№ҰдёӯиЎҚз”ҹзҡ„е…ідәҺвҖңе…ізі»вҖқе’ҢвҖңжғ…ж„ҹвҖқзҡ„йғЁеҲҶпјҢеӣ дёәеңЁеҶңзү§дёҡз”ҹдә§з”ҹжҙ»еҸҠе…¶еҸҳиҝҒиҜӯеўғдёӯпјҢжҲ‘и®ӨдёәвҖңе…ізі»вҖқе’ҢвҖңжғ…ж„ҹвҖқжҳҜжңҖдёәйҮҚиҰҒе’Ңж ёеҝғзҡ„йғЁеҲҶгҖӮжҲ‘зЎ®е®ҡзҡ„дё»йўҳдёәвҖңзҶҹдәәзӨҫдјҡе’Ңд№Ўеңҹжҷәж…§вҖқгҖӮвҖңзҶҹдәәзӨҫдјҡвҖқжҳҜиҙ№еӯқйҖҡе…Ҳз”ҹеңЁгҖҠд№ЎеңҹдёӯеӣҪгҖӢдёҖд№Ұдёӯеј•з”Ёзҡ„жҰӮеҝөпјҢз”ЁдәҺйҳҗиҝ°д№ЎеңҹзӨҫдјҡзҡ„еҹәжң¬з»“жһ„гҖӮвҖңд№Ўеңҹжҷәж…§вҖқжҳҜ笔иҖ…й’ҲеҜ№вҖңжӯЈз»ҹвҖқвҖңж–ҮжҳҺвҖқвҖңе…ҲиҝӣвҖқвҖңең°ж–№вҖқвҖңжқғеЁҒвҖқзӯүиҜқиҜӯе»әжһ„жҸҗеҮәзҡ„и§ЈйҮҠи§’еәҰгҖӮжң¬д№ҰдҪңиҖ…жӢүе…ҲеҠ еңЁд№ҰдёӯдёҖиҙҜејәи°ғзҡ„вҖңз”ҹеӯҳжҷәж…§вҖқпјҲаҪ аҪҡаҪјајӢаҪӮаҪ“аҪҰајӢаҪҖаҫұаҪІајӢаҪӨаҪәаҪҰајӢаҪўаҪ–пјүпјҢвҖңд№Ўеңҹжҷәж…§вҖқдёҺд№Ӣи§ӮзӮ№дёҖи„үзӣёжүҝпјҢжҳҜе®ғзҡ„еҶҚзҺ°дёҺеҶҚйҳҗйҮҠгҖӮйӮЈжҲ‘дёәд»Җд№Ҳдјҡи®ӨдёәеңЁвҖңи—Ҹж—ҸеҶңзү§дёҡз”ҹдә§з”ҹжҙ»ж–ҮеҢ–еҸҠе…¶еҸҳиҝҒвҖқиҝҷж ·зҡ„дё»йўҳдёӯпјҢвҖңе…ізі»вҖқе’ҢвҖңжғ…ж„ҹвҖқжҳҜжңҖж ёеҝғзҡ„йғЁеҲҶе‘ўпјҹжҲ‘жғід»Һд»ҘдёӢдёүдёӘж–№йқўйҳҗиҝ°гҖӮ
дёҖгҖҒеё•еҹҹпјҡзҲ¶дәІзҡ„еңҹе’ҢзҲ¶дәІзҡ„ең°
гҖҖгҖҖеңЁи—ҸиҜӯйҮҢпјҢвҖңж•…д№ЎвҖқиў«з§°дёәвҖңеё•еҹҹпјҲаҪ•ајӢаҪЎаҪҙаҪЈпјүвҖқжҲ–иҖ…вҖңеё•иҗЁеё•еҹҹпјҲаҪ•ајӢаҪҰајӢаҪ•ајӢаҪЎаҪҙаҪЈпјүвҖқпјҢе…¶еӯ—йқўеҗ«д№үдёәвҖңзҲ¶дәІзҡ„ең°ж–№вҖқпјҢжҲ–иҖ…жҳҜвҖңзҲ¶дәІзҡ„еңҹдёҺзҲ¶дәІзҡ„ең°вҖқгҖӮгҖҠи—ҸжұүеӨ§иҜҚе…ёгҖӢе°Ҷе…¶и§ЈйҮҠдёәвҖңзҘ–еұ…жҲ–иҖ…иҮӘе·ұеҮәз”ҹзҡ„ең°ж–№вҖқгҖӮи—ҸиҜӯдёӯзҡ„вҖңеё•еҹҹвҖқиҝҷдёӘиҜҚпјҢиЎЁжҳҺвҖңж•…д№ЎвҖқжңҖеҲқзҡ„жҰӮеҝөдёҺвҖңзҲ¶дәІвҖқжҲ–иҖ…вҖңз”·жҖ§вҖқеӯҳеңЁе…іиҒ”пјҢ并且дёҺеңҹең°жңүзқҖзӣҙжҺҘзҡ„иҒ”зі»гҖӮ然иҖҢпјҢвҖңжҜҚдәІвҖқжҲ–иҖ…вҖңеҘіжҖ§вҖқеңЁеҗҚиҜҚжһ„жҲҗж–№йқўпјҢе’ҢвҖңеё•еҹҹвҖқжІЎжңүеӨӘеӨҡзҡ„е…ізі»гҖӮеҰӮжһңжҲ‘们жҠӣејҖвҖңеё•еҹҹвҖқзҡ„еҗҚиҜҚжһ„жҲҗпјҢд»ҘеҸҠе®ғзҡ„иҜҚжәҗи§ЈйҮҠпјҢд»…д»Һе®ғзҡ„еҶ…ж¶өдёҠи§ЈиҜ»зҡ„иҜқпјҢвҖңеё•еҹҹвҖқжүҖжҢҮд»Јзҡ„иҢғеӣҙпјҢе…¶е®һиҝңиҝңи¶…еҮәдәҶвҖңзҲ¶дәІзҡ„еңҹе’ҢзҲ¶дәІзҡ„ең°вҖқиҝҷж ·зҡ„жҰӮеҝөгҖӮеҜ№дәҺжҜҸдёӘдёӘдҪ“иҖҢиЁҖпјҢеҜ№вҖңж•…д№ЎвҖқзҡ„зҗҶи§ЈжҲ–и®ёдёҚе°ҪзӣёеҗҢгҖӮж— и®әжҳҜдёңж–№иҝҳжҳҜиҘҝж–№пјҢеңЁдёҚеҗҢзҡ„ж–ҮеҢ–е’ҢиҜӯеўғдёӢпјҢеҸҜиғҪеӯҳеңЁеӨҡз§ҚзҗҶи§Јж–№ејҸгҖӮ然иҖҢпјҢдёҚз®ЎжҳҜдҪ•з§ҚдәәжҲ–ж–ҮеҢ–иғҢжҷҜпјҢеҜ№дәҺвҖңж•…д№ЎвҖқжүҖи•ҙеҗ«зҡ„ж„Ҹд№үпјҢеӨ§е®¶еә”жңүдёҖдёӘе…ұйҖҡзҡ„и®ӨиҜҶпјҡвҖңж•…д№ЎвҖқеә”жҳҜйӮЈдёӘвҖңжңҖдәІиҝ‘зҡ„ең°ж–№вҖқгҖӮеңЁж•…д№ЎпјҢдәәдёҺдәәгҖҒдәәдёҺдәӢзү©д№Ӣй—ҙзҡ„е…ізі»иҮӘ然е‘ҲзҺ°пјҢж— йңҖи§ЈйҮҠдёҺеј•еҜјпјҢе®ғзҡ„еӯҳеңЁдјҡи®©дҪ ж„ҹеҲ°еҜ№йӮЈдёӘең°ж–№ж—ўзҶҹжӮүеҸҲдәІиҝ‘гҖӮ
гҖҖгҖҖйҡҸзқҖзӨҫдјҡзҡ„еҸ‘еұ•иҝӣжӯҘпјҢдәә们зҡ„зӨҫдәӨиҢғеӣҙе’Ңжҙ»еҠЁз©әй—ҙдёҚж–ӯжӢ“еұ•гҖӮжҲ‘们结иҜҶдәҶж•…д№Ўд№ӢеӨ–зҡ„дәәе’ҢдәӢзү©пјҢд»ҘжўҰдёә马пјҢз•…жёёдё–з•ҢпјҢйўҶз•ҘеҲ°з»ҡдёҪеӨҡеҪ©зҡ„зҫҺжҷҜгҖӮжҲ‘们дёҺдё–з•Ңзҡ„иҒ”зі»еҸҳеҫ—жӣҙеҠ е№ҝжіӣпјҢжҲ‘们зҡ„иҝҪжұӮе’ҢзҗҶжғід№ҹйҡҸзқҖиҝҷдёӘжӣҙе№ҝйҳ”зҡ„дё–з•ҢиҖҢдёҚж–ӯеҸҳеҢ–гҖӮеӣ жӯӨпјҢжҲ‘们жңүеҝ…иҰҒжҖқиҖғиҮӘе·ұдёҺдё–з•ҢгҖҒдёҺд»–дәәзҡ„е…ізі»гҖӮеңЁеҸ‘еұ•иҝӣжӯҘзҡ„иҝҮзЁӢдёӯпјҢжҲ‘们йңҖиҰҒжҢҒз»ӯеӨ„зҗҶеҗ„з§Қеҗ„ж ·зҡ„вҖңе…ізі»вҖқпјҢеҰӮеӣҪ家й—ҙгҖҒж°‘ж—Ҹй—ҙгҖҒеӨ«еҰ»й—ҙгҖҒеҗҢдәӢй—ҙгҖҒз”·еҘій—ҙзӯүпјҢеңЁз”ұеҗ„з§ҚвҖңе…ізі»вҖқжһ„жҲҗзҡ„жӣҙе№ҝйҳ”зҡ„дё–з•ҢйҮҢпјҢжҲ‘们иҝҳйқўдёҙиҝҷдәӣвҖңе…ізі»вҖқжүҖеёҰжқҘзҡ„з§Қз§Қй—®йўҳгҖӮеҢ…жӢ¬еӯҰжңҜз ”з©¶гҖҒж–ҮеӯҰдҪңе“ҒгҖҒзӨҫдјҡдәӢ件пјҢеңЁеҫҲеӨ§зЁӢеәҰдёҠйғҪиЎЁиҫҫзқҖеҜ№вҖңе…ізі»вҖқзҡ„зҗҶи§Је’ҢеӨ„зҗҶж–№ејҸгҖӮеҪ“д»ҘвҖңи—Ҹж—ҸеҶңзү§дёҡз”ҹжҙ»ж–ҮеҢ–еҸҠе…¶еҸҳиҝҒвҖқдёәдё»йўҳж—¶пјҢжҲ‘жғіиҰҒйҳҗиҝ°гҖҠеҳүжңЁвҖ”вҖ”Mжқ‘ж°‘ж—Ҹеҝ—гҖӢиҝҷжң¬д№ҰжүҖи•ҙеҗ«зҡ„дёҖз§Қжӣҙе№ҝд№үзҡ„вҖңдәәж–Үе…ізі»вҖқжЁЎејҸгҖӮвҖңе…ізі»вҖқзҡ„еҸҳеҢ–дёҚд»…дёҺеңҹең°зӣёе…іпјҢиҝҳе…іиҒ”зқҖдәә们зҡ„жғ…ж„ҹдё–з•ҢгҖӮ笔иҖ…иҜ•еӣҫе‘ҲзҺ°еҳүжңЁзҡ„вҖңдәәж–Үе…ізі»вҖқжЁЎејҸеҜ№еҪ“дёӢз„Ұиҷ‘еӨҡеҸҳзҡ„зҺ°д»ЈзӨҫдјҡзҡ„ж„Ҹд№үпјҢиҝҷжҲ–и®ёжҳҜжҲ‘们еҸҜд»Ҙе°қиҜ•е’ҢжҺўи®Ёзҡ„еҸҰдёҖз§ҚйҖ”еҫ„гҖӮ
дәҢгҖҒе…ізі»пјҡMжқ‘зҡ„еұұж°ҙдё–з•Ң
гҖҖгҖҖеңЁдёӯеӣҪж–ҮеҢ–йҮҢпјҢжңүи®ёеӨҡиЎЁиҫҫвҖңе…ізі»вҖқзҡ„иҜҚиҜӯгҖӮдҫӢеҰӮвҖңеӨ©дәәеҗҲдёҖвҖқвҖңдә”дјҰвҖқпјҲеҗӣиҮЈгҖҒзҲ¶еӯҗгҖҒеӨ«еҰҮгҖҒе…„ејҹгҖҒжңӢеҸӢпјүвҖңдәәе®ҡе…®иғңеӨ©вҖқпјҢдҪӣж•ҷдёӯзҡ„вҖңеӣ зјҳиҖҢз”ҹвҖқвҖңзӣёдә’и§Ӯеҫ…вҖқпјҲаҪўаҫҹаҪәаҪ“ајӢаҪ…аҪІаҪ„ајӢаҪ аҪ–аҫІаҪәаҪЈајӢаҪ–аҪўајӢаҪ аҪ–аҫұаҪҙаҪ„ајӢаҪ–пјүвҖңдј—з”ҹзҡҶдёәжҜҚвҖқзӯүпјҢе®ғ们д»ҺдёҚеҗҢеұӮйқўиЎЁиҝ°зқҖеҗ„зұ»вҖңе…ізі»вҖқгҖӮеҫҖеҫҖеңЁжҹҗдәӣж—¶еҲ»пјҢйӮЈдәӣиў«е»әжһ„еҮәжқҘзҡ„иҜҚиҜӯиғҪеёҰжқҘе·ЁеӨ§зҡ„еҪұе“ҚгҖӮжҜ”еҰӮвҖңдәәе®ҡе…®иғңеӨ©вҖқпјҢиҝҷж ·зҡ„и§ӮзӮ№еҜ№зҗҶи§ЈдәәдёҺиҮӘ然зҡ„е…ізі»еёҰжқҘдәҶдёҖе®ҡзҡ„й—®йўҳгҖӮеңЁе…ізі»еҪ“дёӯпјҢдёҖж—Ұејәи°ғдәҶдәәзҡ„дё»дҪ“жҖ§е’Ңдёӯеҝғең°дҪҚпјҢжҹҗз§Қе№ҝд№үдёҠзҡ„вҖңе…ізі»вҖқе°ұеҸҳжҲҗдәҶдёҖз§ҚеҚ•еҗ‘зҡ„иЎҢеҠЁжЁЎејҸпјҢиҖҢз•Ңйҷҗе’Ңз©әй—ҙе°ұдјҡеҸҳеҫ—и¶ҠжқҘи¶ҠжЁЎзіҠгҖӮжң¬еә”жҳҜеҗ„з§Қе…ізі»е…ұеҗҢеӯҳеңЁзҡ„з©әй—ҙпјҢиҖҢеңЁе…¶дёӯпјҢдәәзұ»зҡ„жҖқз»ҙе’ҢиЎҢеҠЁеҚҙдјҡжҲҗдёәжһ„зӯ‘з©әй—ҙзҡ„е”ҜдёҖеЈ°йҹігҖӮиҝӣиҖҢжҲ‘们зҗҶи§Је…ізі»зҡ„ж–№ејҸе°ұдјҡеҸҳеҫ—жҜ”иҫғеҚ•дёҖпјҢеңЁи®Ёи®әе…ізі»зҡ„ж—¶еҖҷпјҢжҲ‘们еҹәжң¬дёҠеҒңз•ҷеңЁдәәвҖ”дәәгҖҒдәәвҖ”зү©пјҲиҮӘ然пјүзҡ„вҖңдәҢе…ғвҖқи®әдёӯгҖӮдҪҶд»ҘеҳүжңЁвҖ”вҖ”Mжқ‘дёәд»ЈиЎЁзҡ„и—Ҹж—Ҹдј з»ҹзӨҫдјҡдёӯпјҢзӨҫдјҡе…ізі»жҳҜз”ұеӨҡе…ғеӣ зҙ з»„жҲҗзҡ„пјҢе®ғдёҚд»…д»…жҳҜдәәвҖ”дәәгҖҒдәәвҖ”зү©пјҲиҮӘ然пјүзҡ„е…ізі»гҖӮеҳүжңЁзҡ„зӨҫдјҡз»“жһ„дёӯпјҢзӨҫдјҡзҡ„ж•ҙдҪ“жҖ§жҳҜйҖҡиҝҮдәәдәәе…ізі»з»„жҲҗзҡ„еҚ•дҪҚпјҲжқ‘иҗҪпјүе’Ңеӣҙз»•жқ‘иҗҪеҪўжҲҗзҡ„еұұе’ҢдёҺеұұеҗҢиҙЁзҡ„еұұзҘһпјҢд»ҘеҸҠж°ҙе’ҢдёҺж°ҙеҗҢиҙЁзҡ„ж°ҙзҘһжһ„жҲҗзҡ„еҢәеҹҹжқҘиЎЁиҫҫзҡ„гҖӮиҝҷж ·зҡ„е…ізі»жЁЎејҸдёӯпјҢж’ҮејҖвҖңзҘһзҒөдё–з•ҢвҖқжқҘжҺўи®ЁдәәвҖ”дәәгҖҒдәәвҖ”зү©пјҲиҮӘ然пјүзҡ„е…ізі»пјҢе°ұеҝҪз•ҘдәҶзҘһзҒөдё–з•ҢеңЁдәәвҖ”зү©е…ізі»дёӯдә§з”ҹзҡ„зүөеҲ¶дҪңз”ЁгҖӮеҜ№дәҺMжқ‘зҡ„дәәжқҘи®ІпјҢвҖңеҳүжңЁвҖқиҝҷдёӘзҫӨдҪ“жҳҜз”ұ家еәӯгҖҒиЎҖдәІгҖҒе©ҡ姻гҖҒйғЁиҗҪгҖҒеҲ¶еәҰгҖҒең°еҹҹзӯүеӨҡз§Қеӣ зҙ жһ„жҲҗд№ӢеӨ–пјҢиҝҳеҢ…жӢ¬д»–们世世代代延з»ӯдёӢжқҘзҡ„зҘһзҒөзҡ„дё–з•ҢпјҲз©әй—ҙпјүпјҢеҢ…жӢ¬д»–们зҡ„еұұзҘһгҖҒж°ҙзҘһгҖҒ家зҘһгҖҒз”·зҘһгҖҒеҘізҘһгҖҒжҲҳзҘһзӯүзӯүгҖӮиҖҢвҖңзҘһзҒөвҖқиҝҷз§ҚвҖңж— еҪўвҖқзҡ„дё–з•ҢпјҢйҖҡиҝҮеҸҜж„ҹзҹҘжңүеҪўзҡ„жӢүеҲҷгҖҒз»Ҹе№ЎгҖҒйҡҶиҫҫгҖҒиҠӮж—ҘгҖҒд»ӘејҸгҖҒз”»еғҸзӯүзәіе…Ҙ他们зҡ„зӨҫдјҡдҪ“зі»еҪ“дёӯгҖӮжүҖд»ҘпјҢеҳүжңЁзҡ„зӨҫдјҡе…ізі»еҪ“дёӯпјҢдәәвҖ”зҘһвҖ”зү©зҡ„еӨҡе…ғе…ізі»йҖ е°ұдәҶ他们жүҖи®Өдёәзҡ„дё–з•Ңзҡ„жЁЎж ·пјҢд»ҘеҸҠ他们зҡ„вҖңд№Ўеңҹжҷәж…§вҖқгҖӮеңЁжҹҗз§Қж„Ҹд№үдёҠпјҢеҳүжңЁзҡ„зӨҫдјҡз»“жһ„йқ зқҖдәәгҖҒзҘһгҖҒзү©зӣёдә’зүөеҲ¶е’ҢзҒөжҙ»еӨҡеҸҳзҡ„дә’еҠЁжҖ§жқҘз»ҙжҢҒгҖӮжҲ‘们иҝҷдёӘдё–з•ҢйңҖиҰҒеӨҡе…ғзҡ„зӨҫдјҡе…ізі»пјҢ然иҖҢиҝҷз§Қе…ізі»жӯЈеңЁзјәеӨұгҖӮеҪ“жҲ‘们ејәи°ғвҖңдәәвҖқе’ҢвҖңзү©иҙЁвҖқзҡ„ж—¶еҖҷпјҢе°ұдјҡеҫҲиҮӘ然ең°йҷ·е…ҘдёҖз§Қз®ҖзәҰеҢ–зҡ„зӨҫдјҡе…ізі»дёӯгҖӮеңЁиҝҷз§Қе…ізі»йҮҢпјҢжҲ‘们йқўеҜ№е’ҢеӨ„зҗҶзҡ„йғҪжҳҜдәәе’Ңзү©д№Ӣй—ҙзҡ„е…ізі»пјҢеҪўжҲҗз®ҖеҚ•зҡ„вҖңдёҖеҠ дёҖзӯүдәҺдәҢвҖқзҡ„жЁЎејҸгҖӮдҪҶе®һйҷ…дёҠпјҢдё–з•Ңжң¬е°ұдё°еҜҢеӨҡеҪ©пјҢеҫҲйҡҫз”ЁвҖңдёҖеҠ дёҖзӯүдәҺдәҢвҖқзҡ„жЁЎејҸжқҘжҰӮжӢ¬гҖӮжҲ‘们жүҖйқўеҜ№зҡ„дё–з•ҢпјҢеә”еҪ“еҰӮеҗҢвҖңеҳүжңЁвҖқдёҖиҲ¬гҖӮиҝҷйҮҢжңүзҶҹжӮүзҡ„дәІжңӢеҘҪеҸӢпјҢжңүзҶҹжӮүзҡ„еұұе·қжІіжөҒпјҢиҝҳжңүйӮЈжҚүж‘ёдёҚйҖҸзҡ„вҖңзҘһзҒөдё–з•ҢвҖқгҖӮдәҺ他们иҖҢиЁҖпјҢжҜҸдёҖеә§еұұгҖҒжҜҸдёҖжқЎжІійғҪжңүеҪ’еұһпјҢжңүиҮӘе·ұзҡ„еҗҚеӯ—пјҢд№ҹиӮ©иҙҹзқҖеҗ„иҮӘзҡ„дҪҝе‘ҪпјҢиҖҢ并йқһд»…д»…жҳҜиҮӘ然зҺҜеўғгҖӮдҫӢеҰӮпјҢ他们дјҡи®ӨдёәиҮӘе·ұжқ‘йҮҢзҡ„еҘідәәйғҪй•ҝеҫ—еҘҪзңӢпјҢжҳҜеӣ дёә他们зҡ„еұұзҘһжҳҜдёҖдҪҚзҫҺдёҪзҡ„еҘіжҖ§пјӣжқ‘йҮҢзҡ„з”·дәәйғҪеҫҲеӢҮж•ўпјҢжҳҜеӣ дёә他们зҡ„еұұзҘһжҳҜдёҖдҪҚиӢұеӢҮе–„жҲҳзҡ„з”·жҖ§гҖӮ他们зҗҶи§Јдё–з•Ңзҡ„ж–№ејҸе’ҢиЎҢеҠЁпјҢдјјд№ҺйғҪдёҺ他们жүҖдҫқеӯҳзҡ„еұұе·қжІіжөҒиҒ”зі»еҫ—жӣҙдёәзҙ§еҜҶпјҢиҮӘ然иҖҢ然ең°е°ұжңүдәҶвҖңзңӢеұұжҳҜеұұпјҢзңӢеұұдёҚжҳҜеұұпјҢзңӢеұұиҝҳжҳҜеұұвҖқзҡ„е“ІеӯҰеўғз•ҢгҖӮжүҖд»ҘпјҢеҳүжңЁвҖ”вҖ”Mжқ‘еҜ№зӨҫдјҡе…ізі»зҡ„зҗҶи§Јж–№ејҸпјҢеңЁеҫҲеӨ§зЁӢеәҰдёҠи¶…и¶ҠдәҶжҲ‘们жүҖи®ӨзҹҘзҡ„дәәвҖ”дәәгҖҒдәәвҖ”зү©пјҲиҮӘ然пјүиҝҷз§Қз®ҖеҚ•зҡ„дәҢе…ғи®әгҖӮиҝҷдёәжҲ‘们зҗҶи§Јдё–з•Ңзҡ„дё°еҜҢжҖ§е’ҢеӨҡж ·жҖ§пјҢзҗҶи§ЈвҖңе…ізі»вҖқзҡ„жң¬иҙЁеёҰжқҘиҜёеӨҡеҗҜеҸ‘гҖӮ
дёүгҖҒеҸҳиҝҒпјҡеҳүжңЁзҡ„д№Ўеңҹжҷәж…§
гҖҖгҖҖеҜ№дәҺи—Ҹж—ҸеҶңзү§дёҡзӨҫдјҡеҸҠе…¶з”ҹдә§з”ҹжҙ»иҖҢиЁҖпјҢеҸҳиҝҒдјјд№ҺжҳҜдёҚеҸҜйҒҝе…Қзҡ„зҺ°е®һй—®йўҳгҖӮзӨҫдјҡеҸ‘еұ•гҖҒз”ҹжҙ»ж°ҙе№іжҸҗй«ҳд»ҘеҸҠдәәйҷ…дәӨеҫҖеҜҶеҲҮпјҢйғҪдјҡдҪҝеҺҹжң¬еқҡе®Ҳзҡ„зӨҫдјҡж–ҮеҢ–е’Ңз”ҹжҙ»еҸ‘з”ҹеҸҳеҢ–гҖӮдҪҶжҲ‘们йңҖиҰҒжҖқиҖғзҡ„жҳҜпјҢеҸҳиҝҒ究з«ҹж„Ҹе‘ізқҖд»Җд№ҲпјҹжҜӢеәёзҪ®з–‘пјҢзӨҫдјҡеҸҳиҝҒеңЁеҫҲеӨ§зЁӢеәҰдёҠиў«и§ҶдёәвҖңиҝӣжӯҘвҖқдёҺвҖңеҸ‘еұ•вҖқзҡ„иЎЁзҺ°гҖӮеҸҳиҝҒеҸҜиғҪдјҡеёҰжқҘжҹҗдәӣзүәзүІпјҢеҗҢж—¶д№ҹдјҡеҫ—еҲ°дёҖдәӣиЎҘеҒҝгҖӮдҪҶжҲ‘жүҖе…іжіЁзҡ„дёҖдёӘй—®йўҳжҳҜпјҡвҖңеҸҳиҝҒвҖқжҳҜеҗҰдјҡеҜ№и—Ҹж—ҸеҶңзү§дёҡзӨҫдјҡжң¬иә«жүҖе…·жңүзҡ„вҖңеӨҡе…ғе…ізі»вҖқдә§з”ҹеҪұе“ҚпјҹеҰӮжһңдә§з”ҹеҪұе“ҚпјҢйӮЈд№Ҳиҝҷз§Қеӣ вҖңеҸҳиҝҒвҖқиҖҢдә§з”ҹзҡ„вҖңе…ізі»вҖқеҸҳеҢ–еҸҜиғҪдјҡеј•еҸ‘е“ӘдәӣзӨҫдјҡй—®йўҳпјҹ
гҖҖгҖҖеңЁзҺ°д»ЈзӨҫдјҡпјҢеӣҪйҷ…еҪўеҠҝеҸҳе№»иҺ«жөӢпјҢ科жҠҖеҸ‘еұ•ж—Ҙж–°жңҲејӮпјҢз»ҸжөҺж–ҮеҢ–з№ҒиҚЈжҳҢзӣӣгҖӮ然иҖҢпјҢеңЁиҝҷз§ҚиғҢжҷҜдёӢд№ҹжҡҙйңІеҮәиҜёеӨҡй—®йўҳпјҢдҫӢеҰӮAIжҠҖжңҜеёҰжқҘзҡ„еӨұдёҡгҖҒйҡҗз§ҒгҖҒиҷҡеҒҮдҝЎжҒҜдј ж’ӯгҖҒжңәеҷЁжӣҝд»Јдәәзұ»зӯүй—®йўҳгҖӮ科жҠҖиҝӣжӯҘдёәдәәзұ»з”ҹжҙ»еёҰжқҘдҫҝеҲ©зҡ„еҗҢж—¶пјҢдјјд№Һд№ҹдјҙйҡҸзқҖи®ёеӨҡжңӘзҹҘзҡ„йЈҺйҷ©пјҢеј•еҸ‘дәҶз„Ұиҷ‘жғ…з»ӘгҖӮдёҫдёӘе°ҸдҫӢеӯҗпјҢжҲ‘们иә«еӨ„зӢӯе°Ҹз©әй—ҙпјҢйҖҡиҝҮдёҖеҸ°з”өи„‘дёҺдё–з•Ңе»әз«ӢиҒ”系并е®ҢжҲҗж—Ҙеёёе·ҘдҪңпјҢеңЁиҷҡжӢҹдё–з•ҢйҮҢжүҫеҜ»з”ҹжҙ»е’Ңз”ҹеӯҳзҡ„ж„Ҹд№үгҖӮдәәзҡ„еҗ„з§Қе…ізі»дјјд№ҺйғҪиғҪйҖҡиҝҮз”өи„‘е’ҢжүӢжңәиҫҫжҲҗпјҢеҰӮи§Ҷйў‘йҖҡиҜқгҖҒи§Ҷйў‘дјҡи®®гҖҒиҙӯзү©ж¶Ҳиҙ№зӯүпјҢз”ҡиҮіиғҪеңЁиҷҡжӢҹз©әй—ҙжһ„е»әж„Ҹд№үзҪ‘з»ңе’Ңжғ…ж„ҹдё–з•ҢгҖӮжүҖд»ҘпјҢзӨҫдјҡеҸ‘еұ•е’ҢжҷәиғҪеҢ–жӯЈеңЁж¶Ҳи§Јдј з»ҹзӨҫдјҡжүҖе…·жңүзҡ„вҖңзҶҹдәәзӨҫдјҡвҖқиҝҷз§Қз»“жһ„гҖӮдәәзұ»еӯҰ家项йЈҷеңЁдёҖж¬Ўи®ҝи°Ҳдёӯи°ҲеҲ°дёҖдёӘзӨҫдјҡй—®йўҳпјҢиҜҙзҺ°еңЁзҡ„зӨҫдјҡжӯЈйқўдёҙвҖңйҷ„иҝ‘зҡ„ж¶ҲеӨұвҖқгҖӮд»–иҜҙзҺ°д»ЈзӨҫдјҡдәә们иҝҮдәҺе…іжіЁиҮӘжҲ‘е’Ңиҝңж–№пјҢеҜ№е‘Ёиҫ№з”ҹжҙ»зҺҜеўғе’Ңдәәзјәд№Ҹж·ұеәҰдәҶи§ЈдёҺдә’еҠЁгҖӮжҜ”еҰӮйӮ»йҮҢе…ізі»еҸҳеҫ—ж·Ўжј пјҢеҜ№зӨҫеҢәдәӢеҠЎеҸӮдёҺж„ҹйҷҚдҪҺгҖӮйЎ№йЈҷжүҖиҜҙзҡ„вҖңйҷ„иҝ‘зҡ„ж¶ҲеӨұвҖқпјҢе…¶ж ёеҝғеә”жҳҜзҺ°д»ЈзӨҫдјҡдёӯвҖңе…ізі»вҖқзҡ„еҶ…ж¶өеҸҳеҫ—и¶ҠжқҘи¶ҠеҚ•дёҖгҖӮеҰӮжҲ‘们еҲҡжҸҗеҲ°зҡ„科жҠҖе’ҢзҪ‘з»ңдҝЎжҒҜзҡ„еҸ‘иҫҫеҜјиҮҙдәҶиҝҷж ·зҡ„дёҖз§Қз»“жһңпјҢеҸҜиғҪиҝҳжңүе…¶д»–еӣ зҙ пјҢдҪҶиҝҷеә”иҜҘжҳҜжңҖйҮҚиҰҒзҡ„еҺҹеӣ гҖӮйҡҸзқҖиҝҷз§ҚвҖңйҷ„иҝ‘зҡ„ж¶ҲеӨұвҖқпјҢжҲ‘们е°ұдјҡжңүиҝҷж ·зҡ„дёҖз§Қж„ҹи§үпјҡжҲ‘们еҜ№иҝҷдёӘдё–з•Ңи¶ҠжқҘи¶ҠзҶҹжӮүпјҢдҪҶеҜ№дәәжң¬иә«еҚҙжҳҜи¶ҠжқҘи¶ҠйҷҢз”ҹгҖӮжҲ‘们йғҪеңЁиҮӘе·ұжүҖе»әз«Ӣзҡ„ж„Ҹд№үзҪ‘дёӯпјҢеӯӨзӢ¬дё”еҒҸжү§ең°е®Ўи§ҶиҝҷдёӘдё–з•ҢгҖӮ
гҖҖгҖҖзҺ°д»ЈзӨҫдјҡдёӯдәә们йқўдёҙзҡ„з„Ұиҷ‘гҖҒдёҚе®үгҖҒиҝ·иҢ«пјҢз”ҡиҮіеҗ„з§ҚеҒҸжҝҖзҡ„жҖқжғіи§ӮеҝөпјҢйғҪи·ҹжҲ‘们иҮӘе·ұе»әжһ„иө·жқҘзҡ„дё–з•Ңи§ӮжңүеҫҲеӨ§зҡ„е…ізі»гҖӮжҲ‘们дёҺдё–з•Ңзҡ„е…ізі»пјҢеӣҝдәҺз®ҖеҚ•зҡ„вҖңдәҢе…ғи®әвҖқдёӯпјҢжңӘжӣҫе…іжіЁвҖңеҳүжңЁвҖқзҡ„вҖңз”ҹеӯҳжҷәж…§вҖқпјҢи®Өдёәдәәзұ»зӨҫдјҡпјҢж—ҘжңҲжҳҹиҫ°гҖҒжҳҘеӨҸз§ӢеҶ¬йғҪжңүзқҖиҮӘе·ұзҡ„дҪҝе‘ҪиҙЈд»»е’Ңжғ…ж„ҹиЎЁиҫҫпјҢжЈ®жһ—еҸҜд»ҘжҖқиҖғпјҢеұұж°ҙеҸҜд»ҘжҖқиҖғпјҢиҖҢиҝҷдәӣжҖқиҖғжң¬иә«йғҪеңЁи·ҹжҲ‘们дәәзұ»зӨҫдјҡе»әз«ӢиҒ”зі»е’ҢжІҹйҖҡпјҢз»ҷжҲ‘们еёҰжқҘеҗҜеҸ‘гҖӮеғҸMжқ‘зҡ„дәәдёҖж ·пјҢ他们зҡ„й•ҝзӣёдёҚд»…еҸ—зҲ¶жҜҚзҡ„еҪұе“ҚпјҢиҝҳжәҗдәҺеұұж°ҙе’ҢзҘһзҒөзҡ„йҰҲиө пјӣ他们дёҫиЎҢеҗ„з§Қд»ӘејҸд»ҘиЎЁиҫҫеҜ№еӨ§иҮӘ然зҡ„ж„ҹжҒ©д№Ӣжғ…пјӣ他们зӣёдә’её®еҠ©е№¶йқһеҹәдәҺеҲ©зӣҠдәӨжҚўпјҢиҖҢжҳҜеҮәдәҺеҜ№з§©еәҸзҡ„йҒөе®ҲдёҺи®ӨеҸҜпјӣ他们иҷҪдёҚжҮӮзҺҜдҝқпјҢеҚҙи®Өдёәеұұж°ҙжңүзҒөпјӣ他们дёҚжҮӮе®Үе®ҷпјҢеҚҙжҳҺзҷҪиҮӘе·ұеҸӘжҳҜвҖңдёүеҚғеӨ§еҚғвҖқдё–з•Ңдёӯзҡ„дёҖе‘ҳпјӣ他们дёҚжҮӮж–ҮжҳҺзҡ„е®ҡд№үпјҢеҚҙзҹҘжҷ“дёҖеҲҮдј—з”ҹзҡҶдёәзҲ¶жҜҚпјҢйңҖиҰҒе°ҠйҮҚе’ҢеҸӢе–„еҜ№еҫ…жҜҸдёӘз”ҹе‘ҪдёӘдҪ“гҖӮеҖҳиӢҘжҲ‘们д№ҹиғҪеғҸ他们дёҖж ·пјҢи¶…и¶ҠдәәвҖ”дәәгҖҒдәәвҖ”зү©пјҲиҮӘ然пјүиҝҷж ·зҡ„дәҢе…ғи®әеҺ»зҗҶи§ЈвҖңе…ізі»вҖқпјҢиҝҷдёӘдё–з•ҢжҳҜеҗҰдјҡеҸҳеҫ—жӣҙеҢ…е®№гҖҒжӣҙе’Ңи°җе‘ўпјҹеҪ“жҲ‘们д»ҘеҶңзү§ж°‘зҡ„ж–№ејҸпјҢд»ҺвҖңеҶ…еңЁзҡ„и§Ҷи§’вҖқеҺ»жҺўи®Ёд»–们зҡ„д№Ўеңҹж–ҮеҢ–гҖҒзңӢеҫ…他们зҡ„зӨҫдјҡж—¶пјҢжҲ‘们жҳҜеҗҰдјҡеҜ№дё–з•Ңзҡ„еӨҡж ·жҖ§е’Ңдё°еҜҢжҖ§жңүжӣҙж·ұеҲ»зҡ„зҗҶи§Је‘ўпјҹ
гҖҖгҖҖдәәзұ»еӯҰ家зҺӢй“ӯй“ӯжӣҫжҸҗеҮәиҝҮвҖңе№ҝд№үдәәж–Үе…ізі»дҪ“зі»вҖқзҡ„жҰӮеҝөгҖӮд»–иҜҙпјҢвҖңжүҖи°“е№ҝд№үдәәж–Үе…ізі»дҪ“зі»вҖқпјҢжҢҮзҡ„жҳҜдәәе’Ңзү©зҡ„е…ізі»гҖҒдәәе’ҢзҘһзҡ„е…ізі»гҖҒдәәе’Ңдәәзҡ„е…ізі»пјҢжҢҮзҡ„жҳҜиҝҷдёүз§Қе…ізі»д№Ӣй—ҙзҡ„дёҚеҸҜеҲҶеүІжҖ§пјҢд»ҘеҸҠе…¶еҶіе®ҡжҖ§зҡ„еӨҡж ·жҖ§гҖӮеңЁжҲ‘зңӢжқҘпјҢеҰӮжһңжңүд»Җд№ҲвҖңзӨҫдјҡвҖқпјҢйӮЈд№ҲпјҢе®ғдёҖе®ҡжҳҜиҝҷдёүз§Қе…ізі»зҡ„ж··еҗҲгҖӮеӣ жӯӨпјҢеҳүжңЁвҖ”вҖ”Mжқ‘иЎЁиҫҫзқҖиҝҷдёүз§Қе…ізі»зҡ„зӨҫдјҡдҪ“зі»е’ҢзӨҫдјҡз»“жһ„пјҢеҜ№дәҺжҲ‘们зҗҶи§ЈвҖңе…ізі»вҖқжңүе…¶иҮӘиә«зҡ„д»·еҖје’Ңж„Ҹд№үгҖӮ